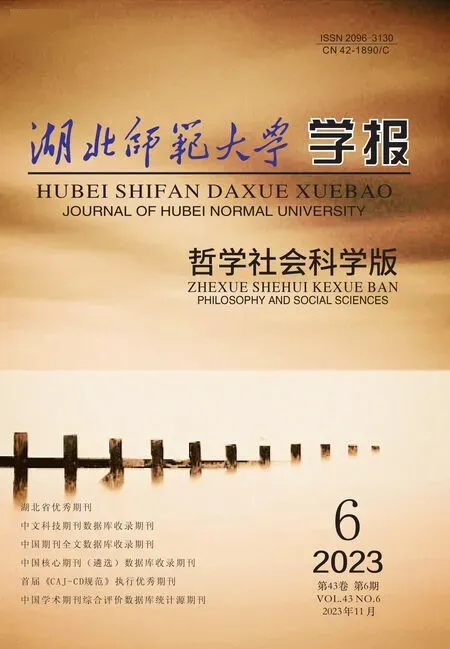师法先贤:宋元明清学规的制定与实行
徐娜娜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宋元明清时期,官学、书院、社学、家塾等各类学校进行教育管理的最重要内容即是学规。自宋初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后,宋元明清四代诞生了数量众多且影响深远的学规。这个进程的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自主制定学规。这些学者在后来的教育系统中被视作先贤,各类学校制定学规的数量和体量虽然增加了,但大多是对先贤制定的学规进行师法,所以在形式上呈现出“统一性”。
宋元明清学规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是一个筛选和取舍的过程。以陆九渊为例,其学规思想是不立学规,主要依靠个人的教育能力,启发开悟学生。但这种教育因人而异,而不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规则。所以,陆九渊的“无学规”教育因为不具有普适性而在成效上不如同时期的朱熹和吕祖谦。以至于朱熹的门人在向陆九渊求学后感到无所适从:
毛刚伯必强云:……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叹。[1]
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两相比较,陆九渊无学规,而朱熹确立了一套明确可以整合、超越和取代旧有学规并给予后代示范的学规。作为先贤,二者都有后学,但陆九渊的后学无学规可依,而朱熹的后学可以直接沿用、践行或继续充实。相对应的,陆九渊的“无学规”也就无法形成学规传统了。而朱熹的学规,自宋至清末,则成为无可动摇的第一学规。因此,学规的制定与实行,就经历了先贤的自主“争鸣”到后学的“一统”的发展历程。
清人蔡新在《平和安厚书院记》中说:“若夫讲习服行之方,师弟子之所以教且学者,则有朱子白鹿洞之遗规,在百世行者而无弊者也。”[2]乾嘉时重要学者、教育家陈寿祺也指出:“若夫五教之目,为学之序,笃行之要,则白鹿洞规备矣,苟守而勿替。”[3]这代表了学规发展中的主流,即先贤虽然各有学规,但后学基本上不出先贤圭臬。这其中,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又是主流。
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在精神层面继承先贤,以此为基础制定学规或直接继承和沿用先贤制定的学规,并进行完善和补充;二是糅合先贤学规,合并使用;三是后学对先贤学规进行的文献编撰。
一、后学对先贤学规的沿用与补充
历代学规中,对后世学规影响最大的,当属确立了书院精神的《白鹿洞学规》。自朱熹后,宋元明清理学在官方和民间都是主导。所以,学规的主流实际上就是理学学规。在这样的进程中,基于程朱理学思想,对朱熹精神及其《白鹿洞学规》的继承和沿用,就成了学规的主要特点之一。也即陈弘谋所谓“后儒振兴洞学,递有规条,要皆庚续发明朱子之意。”[4]
这一趋势首先是由宋代的朱熹门人和后学带动的。在朱熹尚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时,其门人陈文蔚就一直以传承朱熹之学为己任,其在《双溪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讲明义理”的“为学之道”,这就是对朱熹反对“规矩禁防”的思想的继承。此外,如其《克斋揭示》《师训拾遗》《袁州州学讲义》《南轩书院讲义》《饶州州学讲义》《白鹿洞讲义》等,都是其在官学和书院教育中继承朱熹教育思想和学规理念的实践结果。
在当时的各类书院和私学中,《白鹿洞书院学规》也流布较广,如:南宋时,浙江金华蒋沐居乡,创办义学,“担箧负笈者不远数百里而至,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遗规,月书季考……”[5]宋末元初教育家翁森,“隐居教授,取朱子《白鹿洞学规》以为训,从游者前后至八百余人。”
《白鹿洞书院学规》诞生后不久,朱熹门人程端蒙及其友人董铢在制定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后,得到了朱熹的认可,朱熹亲自为其作《后记》,云:“所以训导整齐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堂库术序之间乎。……于以助成后生降德之意,岂不美哉。”于是,《程董而先生学则》就与《白鹿洞书院学规》并行于白鹿洞书院。至乾隆三年,南康郡守董文炜又主持在书院重刻了二学规。
宋末,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书院和郡学学生教材,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在研习次第上,则要先《大学》,再《论语》,再《孟子》,再《中庸》。这是对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直接继承。
宋末另一位重要的朱熹后学是真德秀,其《西山先生教子斋规》是一部重要家训文献,但由于所讲内容皆为童蒙“养正之方”,因此可以视作私学学规。后来,该斋规也被纳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体系中。至清代,王澍编《朱子白鹿洞规条目注疏》,见饶鲁将《白鹿洞学规》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合用,又认为真德秀的《西山先生教子斋规》于程董学则大有补充,于是合编。
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朱熹后学,是程端礼,他在编订《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时,熔铸了“朱子读书法”、《白鹿洞书院学规》《程董二先生学则》等朱熹学规传统中的核心内容。所以,“日程”的核心就是贯穿着朱熹理学思想和精神的“读书法”。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一部分。至清代,“日程”既是不少读书人的“读书法”,更是不少书院学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目录所见《读书分年日程》有二十多种,其中又以清代为最。康熙三十年(1691),吉安知府罗京作《白鹿洞书院馆规》,在“诵读”条下明确规定:“各宜自立日课簿,每日或看经书若干,或读时文若干、古文若干,以及论表策判若干,《通鉴》《性理》若干。”[6]这是受“日程”影响所致。明确以“日程”作为学规的,根据徐雁平统计,有邵亭采的《姚江书院训约》、张伯行为鳌峰书院编的《正谊堂全书》和在紫阳书院制定的《紫阳书院读书日程》、太仓娄东书院的教规、李兆洛为暨阳书院制定的学规、宗稷辰为群玉山房制定的学规、顾广誉和刘熙载为上海龙门书院制定的“课规”、万斛泉在紫阳书院教法、吴承潞为尊道书院制定的章程、王祖畲主讲钟吾书院时所用教法、于荫霖主讲敬敷书院所用教法等。[7]无疑,在继承“日程”的同时,他们也是在继承朱熹的学规理念。
入明以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在官学和书院皆有重要影响。略举数例如下:
薛瑄担任山东提学佥事时,将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用于官学(《明史·卷二百八十二·郭琎》)。
贺钦在《辽右书院记》中指出:
谨取紫阳文公之教于白鹿者,躬勉以诲子弟暨馆下诸生……今樊公之记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以之为托,公其有意于法古乎?则亦遵文公之规而已。[8]
贺钦直接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用作辽右书院学规,其尊朱熹学规之意十分明确。胡居仁则直接撰写《续白鹿洞书院学规》,虽名为“续”,但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朱熹的亦步亦趋,并无超越性内容。周冲则在道南书院 “揭白鹿洞规而充广之”。至于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东林书院,其《东林会约》也是直接指出“愚所条具,大都就《白鹿洞规》引而伸之耳。”
明末清初,名儒汪佑在教学紫阳书院时,“以朱子生日行释菜礼,讲学三日一遵白鹿洞遗规……”[9]
到清代,情况也十分普遍。鳌峰书院创办人是张伯行,在他编撰的《学规类编》和为鳌峰书院制定的学规中,都是首列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当然,《学规类编》也被直接用作鳌峰书院的学规。又,“(雷)鋐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清史稿·列传七十七·雷鋐》)乾隆五十四年(1789),王昶任江西布政使,为友教书院制定规条,其文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朱子白鹿洞规条已举其要,诸生但宜悉心遵奉,毋庸另立规条。”[10]因此,在《友教书院规条》中,详细内容主要是考试办法、束脩、学田管理、祭祀等条目。
根据《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宋元明清全国明确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的就有岳麓书院的《晦庵先生教条》、玉潭书院的《朱子白鹿洞教条》、云山书院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湖北紫阳书院的《紫阳书院教条》、安徽紫阳书院的《白鹿洞学规》、明道书院的《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豫章书院的《朱子白鹿洞规》、信江书院的《朱文公白鹿洞书院揭示》、仁文书院的《朱晦庵先生白鹿洞学条》、鳌峰书院的《朱子白鹿洞教条》、共学书院的《朱晦翁先生白鹿洞书院学规》、关中书院的《朱文公白鹿洞书院教规》、柳湖书院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三川书苑的《朱子白鹿洞规》等。此外,还有各类私人讲学和个人修身治家等,亦多见用《白鹿洞书院学规》者,至于官学,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州县学,用《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在宋元明清皆有。
当然,王阳明的心学也曾在一些书院产生过重要影响。重要的如嘉靖时期吕高在《湖南书院训规》明确提出“圣人精蕴,发之散在典籍,而会之俱在吾心。”万历时期,海南《玉阳书院会条》又云“圣贤心法俱在六籍”,都是心学思想在学规中的体现。姚江书院也是王学重要阵地,其学规包括《书院规约》《书院规要》《书院训约》《书院任事约》《书院会则》等,其中,《书院规要六事》首列王阳明的“阐致知之蕴”,次列刘宗周的“合证人之旨”,显然是要继承心学之脉。不过,由于明末清初,王学在朱王之争中逐渐败落,王学及其学规也就逐渐没落,而朱熹的学规则在官学和书院中得到传承。
二、后学对先贤学规的合用与取舍
先贤各有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因此自主制定学规。这些学规对后来者具有示范意义,也可供借鉴和取用。在能用到多个学规的条件下,一些后学会采取合用、取舍的方法将先贤学规进行整合,再用于教学管理。
早在宋代,朱吕学规流行之时,当时的忠实拥趸或门徒,就已有意识地集合二人学规,共同用于教学。如:
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月令人一观。[1]
更突出的是魏了翁,他将朱吕学规合并使用,并指出了深层原因:
右朱文公、吕成公所著学规,县令长眉山家子鉴属某书之,以勒诸乡校,且曰:“并为我识其末。”
白鹿之规五,温温乎先民之徽言也。丽泽之规三,廪廪乎后学之大戒也。至矣备矣,无以了翁之言为也。学者诚能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范其体,则犹稻粱之养正,药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济吾身,不容一阙者。
夫二规亦异训而同指,异调而同功也。不然,规矩诚陈而不能以约诸躬也,不能以摄诸友也,词华相诩也,躁相竞也,慢相狃也,本学既措,末学滋放,则二先生异时所以风厉与县令长今日所以发挥者,亦徒为挂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不甚懼矣夫![11]
与真德秀对朱熹思想的坚定践行不同,魏了翁除了私淑朱熹外,对当时其他学者的教育理念也持开放态度。体现在学规上,就是明确将朱熹和吕祖谦学规合并使用。魏了翁认为,二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尽管就“规矩禁防”角度而言,吕祖谦学规与朱熹学规有一定悖离,但吕祖谦的学规实际上也蕴含了书院精神。因此,吕祖谦学规与官学学规的纯粹规矩禁防有本质的不同。这是魏了翁乃至许昌朝合并朱吕学规使用的重要原因。
(明)章璜的《为学次第》是对朱熹和王阳明教育思想的融合。《为学次第》一共有八条,其主要条目是:
一、学以立志为根源。二、学以会友辅仁为主意。三、学以致知格物为人路。四、学以戒慎恐懼为持循。五、学以孝悌谨信为实地。六、学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检察。七、学以尽性至命为极则。八、学以稽古穷经为徵信。[12]
李弘祺指出,它的第八条是受朱熹的影响,而第三、四、七条则反映出王阳明关于道德及知识的观点。在这八条之下,章璜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为学次第》体现出明代心学和理学交融的特点。
明代还试图将朱王合并的还有蔡懋德。崇祯初年,蔡懋德担任江西提学副使,“于是,极昌明阳明制学,刻《传习录》于白鹿洞,标洞规八条,纂《真朱子录》以申朱王合一之旨。”[13]
清康熙年间,董瑒为姚江书院撰写《书院规要六事》,前三条是“阐致知之蕴”“合证人之旨”“申鹿洞之教”[14],前两条是王学宗旨,第三条则是朱熹学规。虽然更推崇王学,但显然也比较重视朱熹学规。
明道书院监院杨凌阁制定《劝善规过条约》时亦称:“书院本以明道也。闻义不徙不善不改道何由明乎?兹谨仿吕氏《蓝田乡约》、朱子《白鹿洞学规》置一劝善规过簿,详列其目,简而不略,要而易遵……”[15]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瀛山书院经历了朱王并重到尊朱辟王的历程。明末隆庆六年,瀛山书院将王阳明再传弟子周恪奉祀于朱子之右,使瀛山书院出现了“三先生祠”。此时,瀛山书院对朱王并重。万历七年(1579)后,张居正禁毁书院,瀛山书院因主讲王学也在禁毁之列,最终因其是朱熹文教之地而幸存。此后,天启二年(1622),方世敏制定《瀛山书院学规》,开头明确指出“一曰格致”,并只推崇朱熹。明末清初后,王学流弊日深,瀛山书院在书院志中也删除了王学痕迹。[16]此后,王阳明的影响就从形式上被摒弃了,朱熹的学规传统则完全成为瀛山书院主流。
合用先贤学规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体现出一些后学和书院在确立教育理念、建立教育模式之时的思想权衡与具体实践。再从先贤学规的分合与去留,也能看出政治权力、学术思想与学规撰作之间的关系。
三、后学对先贤学规的编撰与集成
编撰先贤学规文献,也是后学走向统一的一种方式。学规文献的编撰与刊刻主体,又分为书院和私人两种。前者主要存在于书院刻书和编志中,后者多是自发的个人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如《宋史·艺文志》中收录的国家制定的学法、学礼等文献,不在该文讨论之列。
实际上,在宋代,州县学刻书的情况也多见,学规当然也在其中。早在淳熙六年(1178),朱熹也曾在南康郡斋刻过胡明仲《叙千古文》,希望“传诸小学,庶几其有补云。”[17]根据朱熹题跋,《叙千古文》是“昭示法戒”“开示正途”的童蒙养正之书,可见也有学规性质。后来,朱熹门人陈宓在其《与南康郑教授劄》中提到:“郡斋所刻学规学则各五本,有余则多印,不足则据所发券减之。”[18]南康郡斋是当时江西刻书的官办学校机构,陈宓希望南康郑教授能够刻学规学则,发挥“有补国家”的作用。但限于文献,尚不可知陈宓请求刊刻的学规学则是否包括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先看书院刻书和编志中的学规文献编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这说的是当时刻书的主流。因此,书院既是教育重地,又是刻书重地。更进一层,书院编志,实则是因为书院“皆诸儒明道继统之地。”白鹿洞书院认为,历代先贤在本书院“讲学设教,造就生徒,……其规条整饬,训诫详明,至今读之,历历可为士人法。”于是,“得此册以观……而得先儒精神志气之所在。”[19]可见,学规是书院志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仅因其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后人借此熏陶于先儒,并传承先儒道统的最好途径。
因此,编撰先儒学规并刊刻发布,就非常自然了。在书院志之前,书院学规主要以单行形式出现,或零星存在于一些学记或书院记中。书院志出现后,各书院的学规,通常都被收录于本书院的书院志。明清两代,是书院志编刻的高峰期。如明代的《象山书院志》,列于前的正是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讲义》,具有学规意义;明清多次编修的《岳麓书院志》卷三有“教条”,所列为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明代李安仁在编撰《石鼓书院志》时明确指出:“韩之《原道》、黄之《经解》、张之《希贤录》、朱之《白鹿洞规》,先后其一辙乎!在院诸生,惟我与尔,其共懋毙。”[20]清代的《白鹭洲书院志》收录了学规、讲义、章程等;清代的《钟山书院志》卷十为“教条”,卷十一为“讲义”。清人施璜始编,雍正四年(1726)由吴瞻泰、吴瞻淇完成的《紫阳书院志》卷十五“会规”即为其学规,首列《白鹿洞学规》,次列《紫阳讲堂会约》,次列《崇实会约》,次列《紫阳规约》。(清)戴凤仪编《诗山书院志》,其卷八为“名训”,以朱熹为核心,收录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书院揭示》《同安县谕学者文》《同安县谕诸生文》《上宁宗札子》《朱子读书法》《朱子劝学箴》《朱子敬斋箴》《朱子明伦堂铭》等。(清)王庚言编,同治年间钟世桢重修的《信江书院志》卷三为“条规”,“敬刊朱文公《白鹿洞书院揭示》。”[21]明清书院志辑录学规,数量最多的,无疑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而其他即使没有直接收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也大多受其影响极深。即使是推崇王阳明之学的姚江书院,在其志书《书院规要六事》中,第三条也仍是“申鹿洞之教”,强调其“五目之教”。
再看私人编撰学规的情况。如前所说,陆九渊提到的“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反映了当时私人编撰学规文献,用于教学的情况。此后历代,皆有私人集合、编修学规的情况。
据《四库全书总目》,明代贺时泰编《作师编》,收录诸如《易·蒙卦》《大学圣经》《礼记·学记》《白鹿洞学规》《程董学则》等。总目评其“无一字之发明,又属天下所习见,何必为此钞胥也。”[22]
在清代,如《壬癸札记》卷十二载“吴江诸生,任德成、象元,奉朱子白鹿洞规,因集明以前先正格言与洞规相发明者为一书。”任德成集学规亦见于《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二。根据《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可知任德成撰有《读白鹿洞规条大义》一书。
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在其《九闽课艺序》中提到:“余(抚军张公)奉命抚闽,窃不自揆,仰体皇上先行后文之意,刻学规、养正诸编及周程张朱许薛胡罗之书,先后刊布……”
《金华理学粹边》卷九《理学正传》载:
费惕庵曰:“《定志编》既列先儒遗矩格言,终之以《白鹿洞规》而名曰志,此成始成终之学也。盖人之所历不外五伦,而为学之序与夫修身处事接物之方,只此数语,包括已尽,朱子列以为规,石台取以终篇,其教人作圣之功一也。”[23]
又有如王澍《白鹿洞规条目》二十卷(见《清通志·艺文略》)这类学规“读后感”。这些都是私人编撰学规文献的零星记录。他们或是私人教学,或是自身求学修身,都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核心,再搜罗其他相近学规。
在宋元明清学规文献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清人张伯行的《学规类编》,它集成了宋元明三代程朱学派大儒制定的修身、治学、读书等内容,首列《朱子白鹿洞教条》,再列《程董二先生学则》《真西山先生教子斋规》《提学副使高贲亨十戒》《诸儒读书法》《诸儒总论为学之方》《增损吕氏乡约》等重要学规及其他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对“学规”的认定,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不仅包括常见的学规和读书法,还包括蒙学、修身等。这一时期,新的书院学规已然无法超越先贤大儒学规。因此,集成先贤学规,总而为可见可读的文献,使之为法,是比较契合实际的做法。
(清末)黄舒昺曾任常州、桂阳、凤凰等地的教授、教官,又执掌过洛学、明道等书院,并撰有《明道书院约言》《明道书院学则》《明道书院学规劝约》等学规。后黄舒昺搜罗学规,辑刊了《国朝先正学规汇钞》,随后,又在此基础上续刊了《求实书院学规续钞》。《汇钞》收录了清代书院及其他机构的学规26个,而其中如陆陇其的《嵩阳书院条约五则》《一隅集范例九则》;张履详的《澉湖塾约》《东庄约语》;汤斌的《志学会约》、陆世仪的《喻读书法》、李颙的《关中书院学程》、窦克勤的《泌阳学条规》、蔡世远的《鳌峰书院学约》、李文炤的《岳麓书院学规》、张伯行的《学海津梁》等。[24]这些学规都是清朝前期理学家制定的,无疑都是对朱熹理学思想和学规理念的直接继承。黄舒昺汇钞为一体,其目的不言而喻。《续钞》集成了李来章的《南阳书院学规》、程易畴的《教学恒言》、黄舒昺的《洛学书院学规》《明道书院学规劝约》《明道书院学则》、陈宝箴的《致用精舍学规》、吴树梅的《湘楢丛刊摘录》等八种学规。[25]此时,传统书院及其学规已然走向末路了。
综上,宋元明清学规经历了先贤到后学的统一。早期学规的制定,是“百花齐放”,但在后期,则以后学对先贤学规的继承、取用补充和文献编撰为主。在所见的学规文献编撰中,很明显也体现出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