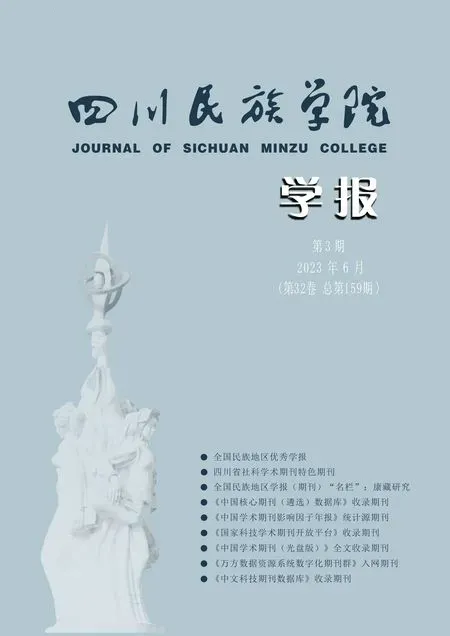四川羌族舞蹈作品创作研究
王利桥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1)
羌族,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又称“云朵上的民族”。羌族舞蹈以其独特的动律特征、体态特征、审美特征及艺术魅力,并以身体为文化符号来记录、反映羌民族的生产生活与精神品质,其始终伴随着羌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一、羌族舞蹈作品创作发展历程概述
羌族舞蹈历史悠久,但其作为舞台剧场化艺术舞蹈的形式呈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据现有史料记载,1946年,在重庆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由彭松先生主导创作、表演的羌族舞蹈作品《端公驱鬼》惊艳亮相。其“以该地羌族端公跳鬼时所用羊皮鼓舞及用于做法赶鬼的三色棍舞加工改编。舞蹈寓驱逐邪恶,迎来吉祥之意。”[1]
在此之后,羌族舞蹈以艺术表演的形式搬上舞台是在十余年之后的1957年了。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史料资料记载:“1957年,登珠编排出《一瓦白学》,古萍玉编排出《抢帕子》。”[2]自1946年由彭松先生创作并表演的首个羌族舞蹈作品起,羌族舞蹈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七十余年里,其表演团体在川内以专业舞蹈院校和专业舞蹈院团为主导,尤其是川内地方院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茂县羌族歌舞团),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四川音乐学院、阿坝师范学院)。而川外地区创作、表演团体以专业舞蹈院校为主。
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1950年建团以来,创作了大量的羌族舞蹈作品。继1957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创作了《一瓦白学》《抢帕子》之后,在60年代又创作了《扳玉麦》《摘苹果》《火盆花儿献北京》等作品,并于70年代又创作演出了《喜迎铁牛上羌寨》《喷灌好》《铃鼓声声庆丰收》《毛选五卷到羌寨》等一批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作品。从这些羌族舞蹈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年全国人民热火朝天抓农业生产的场景,以及羌族民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切拥戴之情。但由于地理位置较为闭塞,加之当时信息的传播力度等原因,其仅在四川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并未被全国广大人民所熟知。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力,羌族舞蹈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80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由蒋亚雄创作的女子独舞《羊角花开》和马寿年创作的群舞《铠甲舞》得到全国舞蹈界的极大关注,羌族舞蹈因此被国内更多舞蹈人所熟知和喜爱。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羌族舞蹈的创作和表演团体主要集中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982年,四川省歌舞团编导潘琪、吕波创作的作品《百合花》诞生,标志着羌族舞蹈作为艺术作品的样态在四川省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更多专业创作、演出人才的加入,羌族舞蹈作品的题材与表现领域也逐步扩大,其影响力也随之增强。而后又有编导梅永刚先后创作出了《腰带舞》《尔玛姑娘》《依娜麦达》等羌族舞蹈佳作。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后,受到汶川大地震事件的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为羌族舞蹈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此期间,羌族舞蹈作品相比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首先,涌现出了一批大型的舞蹈作品,例如《羌魂》这样的原生态歌舞以及《云朵·萨朗姐》这样的羌族情景诗画乐舞。虽然《震撼》舞蹈诗、大型音乐舞蹈诗剧《5.12不能忘却的记忆》以及大型史诗《大北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羌族民间舞蹈,但编导们仍然通过现代舞的表现形式成功传达了羌族民众在汶川大地震中坚强不屈、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其次,不论是在全国专业舞蹈比赛中获奖的作品,如《羌》《春到百合开》《羌绣》《跳羌红》,还是在“大学生艺术节”上展示的作品,如《羌寨欢歌》《星火》,以及在“中小学生艺术节”上获奖的作品,如《羌山羊趣》,甚至是在业余群众舞蹈比赛中出现的作品,例如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舞台艺术精品大赛业余组比赛获奖作品《绣春》,以及蓝天老年大学民族舞班创演的《太阳里走出来的羊角花》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羌族艺术舞蹈作品的身影。这些作品也充分展示了羌族的艺术创作与表演,以多层次、多方位、全视角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羌族舞蹈作品创作与政治经济的关联
(一)羌族舞蹈作品创作与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回望过去,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谓息息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专门组建了专业的艺术院团,用以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因此,羌族舞蹈作品《一瓦白学》《抢帕子》等才得以在舞台上展现。尤其是在2008年经历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受到极大的破坏,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羌族文化艺术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因此,羌族舞蹈也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涌现出了一批羌族大型舞作。例如,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羌族情景诗画乐舞《云朵·萨朗姐》以及大型史诗《大北川》等作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些年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精神层面需求也极大提高,我们发现,羌族舞蹈由于其独特的动作律动、柔美的舞姿,不论是在舞蹈作品的创作演出中,还是在业余群众的健身训练中,都有其身影。从绵阳市文化馆、绵阳市老龄办艺术团参加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舞台艺术精品大赛业余组中获奖节目《绣春》和蓝天老年大学民族舞班参加“我和我的祖国”文艺汇演的节目《太阳里走出来的羊角花》中,以及代表中国赴俄罗斯进行民间交流演出的羊角花艺术团所演出的《珙桐千姿花沐春》里,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羌族舞蹈的全民参与和推广。
(二)羌族舞蹈作品创作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
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不仅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国家政治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始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正是由于国家专业院团政策制度的建立,才使得有专门的人员从事舞蹈的创演活动,这也势必会促进舞蹈作品的产生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社会环境,中国文艺的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特别是艺术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即“高度重视和主要着眼于艺术对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效用,从而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模写、反映、认识”[3],羌族舞蹈创作也正是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到“双百”方针文艺政策的影响及关于民族民间舞蹈保护与利用的一系列政策出台,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不遗余力地向民间学习,取其精华,舞台艺术创作、羌族舞蹈作品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受其影响,涌现出了一批由专业舞蹈工作者改编传统民间舞蹈而成的舞蹈作品。编导们以原生态民间舞蹈为素材,借鉴并发展了民族民间艺术的创作手法,使之能够反应社会崭新的生活和当代人的感情。因此,创作了《一瓦白学》《抢帕子》《羌寨的春天》等作品。
20世纪60—70年,因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舞蹈艺术创作也进行了一系列贴近时代的改良,广大舞蹈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激情四溢的创作热潮,其作品和演出发挥着极大的鼓舞士气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自然且有力地推动了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发展。我们可以从《扳玉麦》《摘苹果》《火盆花儿献北京》《喜迎铁牛上羌寨》《喷灌好》《毛选五卷到羌寨》这些作品中得以明晰。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随着保护羌族文化国家政策的出台,一系列大型舞作得以面世,可见羌族舞蹈作品的创作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羌族舞蹈作品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联
(一)作品表现内容源于社会生活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因此社会生活是舞蹈创作的源泉和基础。羌族舞蹈作品以羌族民众的社会生活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从以往作品的历史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有塑造勤劳朴实、热爱生活的羌民形象的舞蹈《铃鼓声声庆丰收》《哒板》;有叙述羌族青年男女爱情的舞蹈《依娜麦达》《羌寨里的年轻人》《坐花夜》;有描绘羌年祭山会场面的《跳羌红》;更有表达抒发羌族民众迎接新生活的幸福与喜悦之情的《鸽子花开》《羌绣》等等,可谓硕果累累。这些作品不仅流露出浓郁的传统风格与民族特色,同时也具有现实性与时代性,堪称佳作。
羌族民众在婚嫁、丧葬、丰收等重要的社会活动中,通常都会举行各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编导即以此为内容,创作出了大量的舞蹈作品。例如:群舞《铃鼓声声庆丰收》——以羌族羊皮鼓和铃铛为道具,通过敲击羊皮鼓、摇响铃铛等动作描写了羌寨粮食丰收的欢乐场面并表达羌族民众丰收后的喜悦心情。舞者们通过变幻的队形和活泼生动的舞姿,展现了羌族男女充满喜悦的心情,同时表现出了羌族民众在喜庆丰收时的独特习俗。尤其是男子独舞《哒板》,舞者将劳动工具“哒板”带到舞台,通过击打带有声响的“哒板”,模拟了羌族民众在丰收时刻的喜悦景象。这一表演不仅反应了当代羌族民众内心的喜悦,还展现了他们勤劳淳朴的民族气质。勤劳勇敢的羌族民众用“哒板”既不断敲出了自我内心的喜悦,亦敲出了羌族民众新时代下幸福美好的生活态度。群舞《羌寨里的年轻人》以羌族喜事锅庄为主要元素,描述羌寨里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景,以舞蹈的方式表达了羌族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群舞《依娜麦达》以浓郁的羌族传统舞蹈形态为依托,加之幽默诙谐的情节,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羌族青年男女乐观豁达的生活状态。女子群舞《坐花夜》则以羌族古老的婚俗“花夜”为创作背景,将羌族姑娘们灵巧优美的舞姿与羌族婉转动听的民歌声及民族器乐声融为一体,随着欢快的歌声,羌族姑娘们将羌铃串成一圈圈美丽的弧线,将羌寨姑娘出嫁前载歌载舞过“花夜”的情景艺术化地呈现于舞台之上,极具民族特色。而男子群舞《跳羌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羌年》与羌族古老的“转山会”为创作背景,通过羌族传统动作的重组与创新以及道具——红色长绸的运用,极力展现羌族的生命颜色与状态,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羌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场景。
(二)作品风格特征源于社会生活
在众多羌族艺术作品中,舞蹈动作风格鲜明,动作形态主要表现为“一顺边”“出脚顶胯”“拐腿”和“胯部的轴向转动”。究其缘由,与其民族地域和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舞蹈时,羌族民众会做出同手同脚和出脚顶跨的动作,这种动作的形成符合羌族民众的生活习惯。羌族民众在狭窄的山路中负重前行时,同手同脚地进行运动是相对省力和安全的行为。这一行为在体现羌族民众劳作过程中生活智慧的同时,也形成了羌族舞蹈所特有的韵律。呈现出的舞蹈动作不仅有较好的艺术观赏性,也体现出羌民族独特的民族特色。由于淳朴的原始生殖崇拜及审美观念等因素影响,羌族舞蹈胯部动作显得极具特色,进而影响到羌族舞蹈特征、体态特征、审美特征的形成。
在羌族舞蹈作品中,不管是《腰带舞》《春到百合开》《坐花夜》,还是《羌绣》《一川春露》《瓦尔俄足》等作品,都在“一顺边”“出脚顶胯”“拐腿”和“胯部的轴向转动”的动态特征上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女子群舞《春到百合开》突出地运用了羌族舞蹈中“胯部动律”,包含了“顶胯”“摆胯”“转胯”“晃胯”“筛胯”等多种胯部姿态,姿态构图和队形变换融合在一起,羌族姑娘的青春气息、美丽气质一览无遗。女子群舞《坐花夜》则是在舞蹈语汇的呈现和表达上、在羌族极具特点的“S”形运动路线上做足了功夫,将其与“出胯”“拐腿”等动作姿态巧妙地有机结合,不仅突出了女性的俏皮活泼,更展现了女性之间深厚的情谊。女子群舞《羌绣》将羌绣的劳作过程艺术化地提取和展现,将“甩线轴、绕线轴”等羌绣劳作过程与“出胯”“拐腿”等羌族舞蹈动态巧妙结合,舞蹈就是劳作,劳作好似舞蹈,二者完美融合,取得了精妙的艺术效果。女子独舞《一川春露》通过“一边顺”和“顶胯”的动作,表达了人们在“下雨了”这个场景中的欣喜之情。[4]150并通过双膝跪地,伸展双臂怀抱大地的动作,表达着劳动人民对土地最真实的热爱,让观众仿佛也能闻到春露中羌山泥土与花草的清香,也能品尝到羌山春露带来的甘甜,充分感受到羌族民众迎接春露时的欣喜之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尤其是女子群舞《瓦尔俄足》,该作品以胯的轴向转动为主要舞蹈语汇,从细小的摆胯到带动全身的胯部转动,进行了较为大胆的发展与创新,用女性极致的美感呈现出生命力的无限延续,也充分彰显出编导独特的审美追求。
四、羌族舞蹈作品与创作人才的关联
(一)舞蹈编导对作品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羌族舞蹈作品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舞蹈编导深入生活,对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及舞蹈语汇进行充分了解和认识,再结合自身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对艺术审美的思考、提炼、加工,进而创作出反映羌族民众情感生活的舞蹈佳作。在作品创作时,编导们除了选择羌族萨朗舞、羊皮鼓舞、铠甲舞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题材作品外,还有部分编导并不局限于既定的民间风格与形式,而在文化与审美追求上寻求新的突破。例如《腰带舞》《尔玛姑娘》《瓦尔俄足》《羌》等作品。
在女子群舞《腰带舞》中,编导梅永刚将系在羌族姑娘腰胯上的“腰带”作为身体动律延展的重要道具,随着身体舞动,飘荡的“腰带”便开始发挥它的功效,逐步展现着羌族女性不同的动态情状。通过系在羌族姑娘腰胯上的腰带和“S”型的胯部动律——侧身顶胯、身体呈“S”状的体态舞姿,观众享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羌族特有的舞蹈服饰、羌族女性独特的气质以及民族的性格都得到了艺术的升华。女子群舞《尔玛姑娘》则主要采用了肩部和胯部细碎、重复地抖动甚至晃动,加以“重复”技法,将这种肩部、胯部细碎的动态运用到极致,从而表现出少女由内而外欢快的心情。女子群舞《瓦尔俄足》在保持“S”型的体态动律下,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胯部动律和肩部动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变化。从细小的摆胯到带动全身的胯部转动,从肩部微微而节奏平缓地转动到大幅度且起伏不平地变化转动,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生命力的真实状态。群舞《羌》以“5.12”汶川特大地震为创作背景,创新性地将带有羌族舞蹈元素的动作与当代舞表现方式相结合,[4]130于差异中见和谐,展现了羌族民众坚韧不拔、众志成城、战胜灾害,涅槃重生、拨云见日之景象。在作品的动态设置中,将传统舞蹈中手臂呈弯曲上撩的姿态发展为手臂贴身快速上扬的动作,将动作进行了“质”的改变,使舞蹈更加切合作品所表达的奋进、向上地精神内涵。另外,对身体轴向转动的节奏处理和对屈膝时下颤顿挫的风格处理贯穿作品始终,舞蹈动作显得沉稳有力,充满了韧劲,又不失弹性,更好地展现出羌族民众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从以上作品中,不难看出当代编导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与独特的审美追求。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羌族民众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对生命的热爱,同时也对羌族民众坚韧不拔的品质与阳光般的生活态度进行了讴歌与赞美。这些作品中显现出的艺术性与个性特征,不仅融入了编导们审美情感,更是编导们创新发展的劳动结晶。
(二)舞蹈编导对作品的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然,除了编导们对舞蹈作品审美情感的渗入、姿态动律的提炼发展外,好的作品还饱含了编导在专业技巧、形式表达上的创新。尤其是羌族肩铃舞的创新运用,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学习。
据舞蹈家马寿年(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团长、编导)和舞蹈家夺科(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舞蹈队队长)口述,编导蒋亚雄从羌族铠甲舞服装上掉落的铃铛而得到创作灵感,尝试将掉落在半空中的铃铛,进行了不同动作的探索,进而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羌族“肩铃舞”,同时完成了舞蹈作品《羊角花开》的创作。作品中编导把姑娘比作盛开的羊角花,通过一系列美丽如花般的舞姿,展现羌族姑娘灵动如花的气质。女演员在表演时,通过连续的绕肩使铃铛形成回环飞舞的舞动形态,铃铛以肩为轴甩动的动作,不仅展现出高超技艺,更是将“羊角花”盛开的形状构成一幅幅流动的雕塑,以全新的动态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人花相映,趣意盎然,将羌族姑娘灵动活泼的气质展现得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散发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该作品在1980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时,大放异彩,可谓是为羌族舞蹈作品的发展赋予了崭新的形式美。1982年,潘琪、吕波创作的女子群舞《百合花》在肩铃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作,两位编导将“肩铃”塑造成百合花朵的形状,通过舞者队形的变化,构成百合花的空间意象,在空间中通过高低对比、层次划分,舞者们变作一朵朵洁白的百合花,舞者的舞姿也犹如一片片百合花瓣在空间中绽放,轻盈又富于诗意。该作品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功,百合花朵翻飞中带出“肩铃”的运用绝对功不可没。这一作品的问世使得肩铃舞的运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女子群舞《鸽子花开的时候》越加成熟地以羌族舞蹈的动律、姿态、肩铃技巧表现为依托,通过将象征生命美好的鸽子花在肩部甩动、轴转而形成大圆甩动,使肩铃技巧与身体律动巧妙融合在一起,再加之羌族舞蹈别致的动态和韵律,从而彰显出羌族舞蹈的独特之美,表现出羌族民众在灾难之后依然充满着对生命及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该作品获得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表演二等奖;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银奖;第八届全国舞蹈比赛表演二等奖的殊荣。
如今,经过常艺、吕品、毛军豪等一批批年轻舞蹈编导的匠心独运,肩铃舞技术更加成熟,形式丰富多样、运用更加广泛。例如在全国舞蹈比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羌绣》,由单肩羌铃技术发展而来的《孜姆兰巴》,荣获第四届“荷花少年”全国校园舞蹈展演金奖的《赞姆·噌噌》等。编导们不断创新,使羌族舞蹈的表演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这种创新性的肩铃舞动运用,亦被族群、观众、业界所接受和认同,认为是美且有特色的,并且肩铃舞动已成为羌族舞蹈典型风格性语言特征。
五、结语
纵观70年来羌族舞蹈作品创作,可谓是硕果累累。羌族舞蹈正以其浓郁的民族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喜爱。从羌族舞蹈作品的发展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门艺术的发展规律,即一门艺术能够永葆青春,与杰出人才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关系。羌族舞蹈作品创作,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人才的贡献。正是有了蒋亚雄、马寿年、登珠、王志富、李楠、梅永刚、苏冬梅、杨莉等众多编导的努力创作付出,才会有一个个经典的舞蹈力作得以产生;正是有了陈红、秀花、梅永刚、易辛这样的好演员,才使编导的绝妙想法得以精彩呈现。加之各个院团的各项保障、齐心协作以及政府提供的各个展示平台,才使羌族舞蹈更好地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这些作品不仅仅将羌民族的生活状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并有着崭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也推动了羌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舞蹈的繁荣大发展,使羌民族的文化与风采得以更好呈现,有助于帮助更多民众了解羌族文化,羌族舞蹈与文化齐飞,优秀作品与民族特质共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