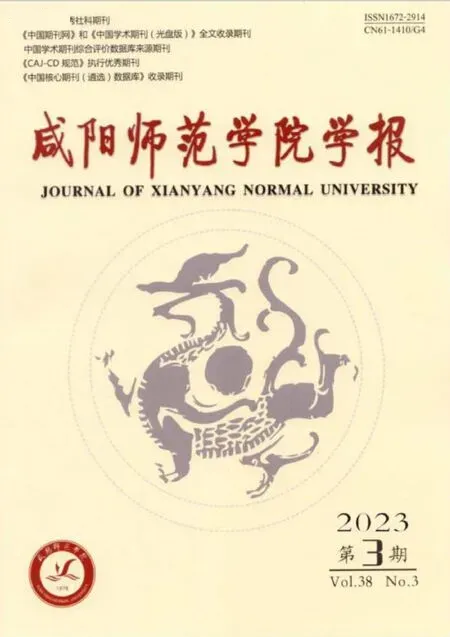王先谦“何异骈散”观及其文体批评价值
赵 静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晚清至民初的骈体批评,在延续清中后期以来创作兴盛背景下骈文作为文体之一的存在合法性得到巩固的同时,其话语言说也从推骈尊骈逐渐转换为等视、融通骈散,以推进骈体形态更臻成熟完善。与以骈文为“正宗”的重骈一派所持相异的一方,是以融合为旨趣的骈散融通论。从严划界限、禁止骈语入古到吸收骈语优化文章创作技艺,骈散体式之间的对立渐趋松缓,古文一派诋斥骈文的力度逐步减弱,平视骈散并试图融通二者。在这种文体批评趋势中,较为典型者如王先谦所倡“何异骈散”说,他以融通汉宋之学的开阔视野看待文章之骈散两体,在晚清民初的骈体繁兴氛围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目前关于王先谦文学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骈文观与文章学理论,但从文体批评角度对其骈散文章观结构和意义的阐释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①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孟伟《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文章选本与王先谦的文章学理论》(《船山学刊》2014年第4期),鑫鑫《论〈骈文类纂〉中王先谦的修辞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莫道才、刘振乾《词气兼资清新不穷——论王先谦对骈文“潜气内转”理论的发展》(《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等,均涉及王先谦骈文批评观及其文章学理论的论析,然而从文体批评角度对其骈散关系观的探究还不完备。本文从理论内涵、学术立场和文体批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发掘其“何异骈散”观的文体学价值。
一 “何异骈散”观的逻辑内涵
王先谦的文体观通达平允,他认为:“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1]393在对待骈散二体的态度上,他从明道的宗旨出发消解对骈散的刻意区分,打破骈散相争的话语习惯,指出骈散无异,同为载道之具。这其实内含着他对骈体地位的认定。正是基于对骈体的肯定,他强调:“文章之理,本无殊致;奇偶相生,出于自然。”[2]25文章无论奇偶,都与文之本体相合,骈偶合乎自然规律,也同样与文章本来之理符合。由于王先谦看待骈散的态度不偏不倚,故而他公允地指出:“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3]134-135为文者常常因才学和喜好的不同而各有所长,若把握不好,骈散二体则会处理失当。
然而王先谦平等看待骈散并非无条件接受骈散之间的破体互动,他拥有强烈的辨体意识,主张严格区分两种体制之差别。他在《骈文类纂·序目》开篇言其少时读柳子厚《永州新堂记》,对于柳文“迩延野绿,远混天碧”感到诧异,认为“俪语”中“杂厕散文”显得“不类”。根据自身“长游艺林”的经验,他发现姚鼐《古文辞类纂》“兼收词赋”,梅曾亮《古文词略》“旁录诗歌”,就连代表性骈文选本如李兆洛《骈体文钞》也“限断未谨”。有感于斯,他决计“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原;取姬传《类纂》之名,稍广其例”,编纂一部通代骈文选本,以便“综古今之蕃变,究人文之终始”[2]3。此处披露了王先谦纂辑《骈文类纂》的初衷,即欲纠已有骈文选本“限断未谨”、辨体不严的疏漏。显然,王先谦是以选本方式表达其骈散观及辨体批评意识的。
表面看来,王先谦一方面以“何异骈散”的态度看待各种文章,另一方面又严划文体之界限,不认可骈散交杂混用,似乎有着明显的矛盾。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冲突。“何异骈散”是其通达文体观的表露,内中的涵义不包括骈散混用等破体现象,主要针对文章本体而言,即在文以载道的意义上对骈散两种体类平等而观,不刻意区分高下,是一种文章“体位观”或曰“文位观”;而禁止骈散杂用是其辨体意识的展现,尤其是文章选本的编纂,更应重视选文文体特征的明确析别以确保纂辑体例的严谨,这是对骈散两种体式的析辨分别。一方面是骈散等位的文体观,一方面是辨明骈散界限以满足选本体例及文章体式严谨性的需求,共同构成了王先谦骈散观的双层结构。
王先谦以选本批评方式表明其无分骈散的文体观,具体实践就是文章选本的编纂——辑有古文选本《续古文辞类纂》和《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两部骈文选本。他“既编有古文选本,也编有骈文选本,‘骈散并重’是其文章学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4]181。一般来说,一时代之文章选本,通常是为时下文体写作明晰“轨辙”、开示门径,王先谦的选本编纂亦是如此。其《续古文辞类纂·序》有云:“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八人。论其得失,区别义类,窃附于姚氏之书,亦当世著作之林也。”[3]21他编选《续纂》的目的也在于为学者树立为文范例,与姚纂意图类似。他不仅赓续姚氏意图,而且纂辑体例也顺承姚纂依体类分的模式和框架——其间有评语置放于文尾,依文而发,或述作者事迹,或评析事理,或讨论文章作法技巧、创作得失,用语凝练,与姚鼐《类纂》品评风格相类。从“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的编选目标来说,王先谦《续纂》是为了总结相应文体的创作方法,张扬文章义理。对于骈文选本,王先谦的编纂目的也在于此。《骈文类纂·序目》称前代骈文选本“题目太繁”“限断未谨”,而“所居之代,抑又阙如”[2]3,为改善状况,他“剖析条流”,辑录历代优秀骈文作品以为当世骈体创作提供典范。同理,《国朝十家四六文钞》的纂辑宗旨为“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亦是效仿曾燠编纂骈文选本之用心,要为骈文创作树立法则。事实也正如王先谦所期待的那样,他的骈文选本尤其是《骈文类纂》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如李肖聃称其“取裁丰赡、断制精严”[5]209;《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认为,“此选汇历代之珠琲,张百家之锦绣,凡源流莫不尽识,芜杂咸在删除,执此一编,而骈俪之文,均在掌握,方之曾、李,实有过之”[6]777,此评不可谓不高。由选本编纂实践来看,王先谦平视骈散,赋予二体同等重要的文体地位。
或者可以说,王先谦“何异骈散”说的理论着力点在于骈体地位的认同上。他不分骈散二体之高下,不仅纂辑选本的态度较为平允,不厚此薄彼,且由选本呈现出的文体批评话语也不含偏见。如论骈文修辞:
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籥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2]26
此番论说从“代异”“递变”角度说明骈文隶事的正当性,由用事而成就的偶俪之美是骈体独有的审美特征,这种美感构造似“金在炉”“舟浮水”及“橐籥之妙”一般,同为造物化成之功。尽管骈体以词藻取胜,但王先谦也将“词采”与“气体”并重,其云:
至词气兼资,乃骈俪之总辖。汉魏之间,其词古茂,其气浑灏。纵笔驱染,文无滞机。六朝以还,词丰气厚。羡文衍溢,时病烦芜。宋元以降,词瘠气清。成语联翩,只形剽滑。明初刘、宋,略仿小文。自时厥后,道益榛芜。虽七子大家,阙为斯式。华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词采既富,气体特高。《明史》称工,非溢美矣。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逾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洸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2]26-27
他简要梳理骈体演进史,指出骈体发展各个阶段之优长与弊病,即不同时期骈文创作在词采和气体方面各有偏向,没能平衡二者在文体制造过程中的功能。若欲使骈体创作达至“绝境”,必定要“选词之妙”与“行气之工”齐头并进,均衡地发挥作用。“气”是各体文章都应具备的内在精神,骈体也不能缺少。由此可知,王先谦之论骈体不仅仅着眼于文体本身的外在形制特征,还从普遍意义上的文章角度指明骈体也要具备内实或曰“气”之充盈。他从文之本体同构的高度论析骈体创作,视骈体为文章之一体,既不抬高,也不贬抑,继而所创构的骈体批评话语颇显客观通达。
近几年来,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的人数逐年增长,旅游形式与内容也逐渐丰富,同时在“美丽乡村”建设与精准扶贫项目中,乡村旅游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融通骈散文体观与兼采汉宋学术立场的互证
王先谦“何异骈散”文体批评观的逻辑构造如前述,然其论说立场与理论内涵的形成须从清中后期骈散之辨与汉宋之争的演进状态以及二条学术史线索的互动中加以体察,惟此方能合理恰当地衡量其文体批评史意义和价值。这种骈散等视的文体观念是清中后期以来骈散融通趋势下的产物,也是考察晚清以迄民初骈体批评发展进程不容忽视的一维。
我们有必要先对清中后期骈散之辨的演进状态加以梳理。骈文自清中期复兴以来,通过自身的形态完善逐渐取得与古文同等的文体地位,骈散相争遂为文体领域“体位”认知的主旋律。乾嘉时期,这种论争关系突出表现为古文派与骈文派文体观的差异和对峙。桐城一方,因上承韩柳以骈俪四六为革新对象的古文文统,仍然视骈文为古文的对立面,不惜将骈体流弊放大,在创作上秉持严格的辨体意识,划清界限。例如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即贬斥骈体文和骈语,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7]3884,其禁绝骈俪之语是为了确保古文文体的纯粹性。方苞弃骈以保证古文文体之纯净的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桐城派学人的骈文观具有权威性影响。不仅桐城派,就连曾对骈体地位加以肯定的袁枚也主张古文中不应掺杂骈语:“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传文者少,传散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体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8]642这是从文章尊体的角度强调“体”之独立性。为张扬骈体以强化文体地位的认同,骈文一方展开了对古文文体本身的攻击。另如凌廷堪高度认同孔广森“荀卿为儒宗老师,萧统乃文章正派”[9]322的观点,将韩愈古文定义为文章别派:“盖昌黎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9]290其批判强劲而有力,直接瓦解了古文的正统性。沿续凌氏,阮元重新界定“文”,以“沉思翰藻”为文章根本特征,排斥古文于“文”的苑囿之外,将古文文统的瓦解推进得更加彻底。他不给古文留一席存在之地,是为了张扬骈体,便于确立骈文为文体之正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古文,又抬升了骈文的文体地位。阮元的论说增强了骈文的气势,将骈文派之举骈推向高潮,与古文派之弃骈构成了紧张的对比。可以说,此时的骈散对举不外学术论争的策略性需要,更为主要的是古文和骈文亟需辨明体制与体式特征、祛除弊病,实现各自文体形态的发展和完善,而文体形态完备目标的实现也即意味着文体地位的真正确立与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骈散论争对于文体塑型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伴随着骈散二体论争过程中文体认知的不断深入,双方态度趋向松缓。至嘉道年间,随着对骈散体式特征精准全面的认识,持骈散融通论者逐渐增多。桐城一脉,譬如位列“姚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刘开,以辩证态度论说骈散体制特点:
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是则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唯通方之识、绝特之才乎![10]425-426
骈散同属于文辞,所载之道同源,二者殊途同归。在文章创作中,两类文体宜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刘开从文统与道统的高度将骈散二体等而视之,又从补偏救弊的角度论证二体相参相济的必要性,呼吁将两种体式“合而一之”。且此种融合非外缘性的拼接,而是在文辞与所载之道或称文体外形和内质两层均无痕结合。依刘开本人而言,其骈文皆是“理”“辞”兼善之作,即为这种融合观的实践呈现。与凌廷堪、阮元等消解古文文统的举骈之论相较,刘开的融通论不仅是对骈文派的间接反驳,也是对古文文统的再确认,同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独刘开,桐城一派平视骈散、抱持融通论者不乏其人,如拥有古文家与骈文家双重身份的梅曾亮亦主张骈散交融:“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11]650文章只要实现了“辞达”的目标,不拘骈散何种体式皆可。他提倡文章应“因时”而作,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因而在自己的文章创作中也积极实践骈散交融观,未拘执于骈散区分,直以述意流畅为目标。在骈散融通的文坛气氛中,桐城文家自觉主动的骈文创作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体景观。
同时,骈文一派对融通论也逐渐予以认可,接受散语入骈文以熔炼文章体格,如李详《答陈含光书》中提到:“弟论骈文,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12]1046他主张创作中融合骈散以达到“自然”之文体风格目标。孙德谦在骈散问题上也持相同态度:“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13]8451他强调:“文章之分骈散,余最所不信。何则?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13]8443孙德谦的骈散合一观透露出骈体只有主动吸取散体之长,才能趋于形态上的完善优化进而实现文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正是由于论争双方文体形态塑型的理论自觉与策略需要,骈散两体从对峙转向有意识的互渗、吸纳。从文体学视域看,文体形态塑型的需求是骈散之争走向骈散融通的契机和动力。至晚清民初,骈散融通论已由学术话语边缘向中心移动,成为其时文体批评话语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骈散趋于融通的文体氛围下,王先谦“何异骈散”的文体批评观即为这种趋势的顺流。需指出的是,尽管融通作为一种重要的骈体批评话语而存在,但骈散所分属的两大阵营仍然持守各自的文体立场,且间有辨分、争位的文体话语伴随。王先谦无意选择任何一方作为自己的理论阵营归属,他持平允态度对待骈散,从明道角度出发赋予二种体式同等的文体地位。这种无分骈散的通达之论同其放弃参与骈散之争的学术立场有关。
换言之,无异骈散的文体认同观是其平视汉宋学态度下的产物。对于王先谦学术研究的思想特色,张舜徽先生这样形容:“他门庭广大,博洽多通,根底雄厚,实非泛泛涉猎者可比。”[14]247的确如此,王先谦治学不拘门户之限,主张汉宋兼采,一边“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徐世昌语),一边又融通汉宋学而力求学术之经世致用功能。如果说骈散之争与汉宋学术之争相伴而行,那么汉宋学术之调和便是骈散融通的学术背景与语境。通常情况下,学术场的强大磁场必然要在场内各个分支产生影响与引力,作用于文体领域那就是产出具有相应思维品格与内质的文体认知观念,故骈散二体的论争、融通便与汉学与宋学相争、交融的投射紧密关联。有学者指出:“表面上看,‘骈散之争’是为文之法或文学理论之争,然究其实质,背后乃是学术、思想理念之争,即汉宋之争。”[15]汉宋的调和、兼采亦引致了骈散二种文章体式兼用与融通的倾向。
基于背景疏通易知,王先谦无异骈散观是其兼采汉宋学术品格之外显。正是因于汉宋兼采、无分骈散,其身份归属也是个颇为纠结的问题。叶德辉在1920年接受日人诸桥辙次采访时称:“曾文正为古文家,王闿运为诗文家,王先谦为桐城古文家,皆非汉学家也。鄙人于三公皆不相同。”[16]163他将王先谦等人定位为“非汉学家”,而他自己则自命为接续传统之风的“汉学家”。与叶氏同世的章太炎将近世经师“以戴学为权度”划分为五等:“一等俞樾、黄以周和孙诒让,二等皮锡瑞,三等王先谦,四等庄忠棫、王闿运,五等廖平。”[17]118章太炎的划分能够看出,他显然认为二王比叶德辉更为“汉学家”一些。以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思维体系等方面来说,王先谦的身份归属确实不易定论,他既有汉学的治学特色,又有宋学的学术精神,所以我们也不便断定叶德辉和章太炎二人对王先谦的评价孰是孰非。这其实从侧面折射出当此汉宋融合兼采之势下,要清晰地分划学派已属不易。通过王先谦的复合型身份与其“何异骈散”的文体认同观我们可知,汉宋学关系迁变这一学术场对于文体领域骈散关系的变化所具有的强大动能。
三 “何异骈散”观的近代文体批评价值
王先谦学术身份的复杂性源于其平视汉宋学、不守门户之见的宏通学术观。他曾为汉宋学辨“名”析“实”:“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此名之为学术累也。”[1]392这段论说中,他反对将汉学与宋学符号化、污名化,指出汉学的实质是考据,宋学的实质为义理,以考据和义理来指称汉、宋学更为确当一些,能够免去因门户偏见嫌恶两种称名而引发对两种治学方法的厌弃。他拒绝汉、宋对垒,其治学倾向和态度非汉非宋,既不隶属汉学门户,又无意介入宋学堂庑,秉持一种独立的学术站位;从另种一意义来说,他又是亦汉亦宋的,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皆采而俱不偏废。王先谦的身份界定成为疑难,同时显明其治学格局之宏大与方法路径之通达。
汉学与宋学两种学术路径在王先谦的治学格局里相济相成、互相支撑。理论上他尊宋学义理之精神,而实际的治学实践仍然是以乾嘉考据的路数为主。此处暂不展开讨论其《诗》学兼采义理与考据所形成学术品格的复杂性,我们单就其选本式文体批评加以考察即可窥见一斑。在选本纂辑实践中,其所辑骈文选本与古文选本兼有,前文已述及。而在编纂思想方面,王先谦汉宋兼济的治学路径于其中充分表露。《十家四六文钞·序》有云:
夫词以理举,肉缘骨附。无骨之肉,不能运其精神;寡理之词,何以发其韵采?体之不尊,道由自敝。余曩类纂古文,赓续惜抱。既念骈俪一道,作者代出,无恧古人,而标帜弗章,声响将閟。故复采干遗集,求珠时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汉代;东海何生,阙美萧选。蔚宗述悼于莫知,表圣缠憾于既往。都为一集,共得十人。网罗众家,窃附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几体则不废江河,导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并为灵物云尔。[3]135
该序虽表骈文辑选初衷,但其“理”“词”共重之选本观已于首句标出。正如“夫词以理举,肉缘骨附”句所言,“理”“词”之相互依附关系似骨肉相连一般,倘有所割裂,则文章之精神、韵采全部丢失。而精神、辞采兼备是文章“尊体”的需要,体之“尊”又关乎道之昌明。王先谦藉“理”“词”关系探讨文章尊体,其由尊体上升至明道的含有本体性内蕴的文体认知理路充分彰显了他不别汉宋的治学精神。其中,他所举文章之“理”“词”意指文章之辞藻与内质,然辞藻与内质又同汉宋学术分野之下重理与重辞两种不同的文体旨趣相呼应,通往义理与文辞两种学术祈向,故而内中涵意在“理”“词”二语的使用上便已表明。另外,这段理词兼举、体尊道明的言说虽置放于骈文选本序言之中作为补充性说明,但视界是开阔的,传达了他文章选本纂编的整体初衷。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他同样表达求道的本体式的文体认知追求,称“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3]21,不仅有意求道,更着意于存道。从这个层面讲,其整个选本编纂实践中贯穿着兼顾汉宋的学术精神痕迹。
置入近代文体语境中进行观察,王先谦“何异骈散”论的批评价值则更为明显。骈散关系历经一番演化过程至清末,相争论在骈体批评话语结构中不再占据主体位置,而是与融通论共同成为晚清民初之际骈散文体批评话语的主要构成,此结构性特征自嘉道期间骈散呈现融通趋势时业已显露雏形。由于近代文体语境及近代思想、学术、文化的多重合力作用,融通论已被赋予了新的内质,即从骈散相争到融通的被动性转向转变为主动破解骈散区判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文章本体同构的一元视角看待骈散二体,落实于文章创作便是不加分别、不带价值评判地采用骈散二体中有益于文体构造的成分,从文体理论认知到文体制作实践自发地以文体创构为目的实现骈散二大体式及技法手段的会通。若我们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考量,王先谦的“何异骈散”说恰是一元式文体融通论的示例。当然,这并不是强调王先谦此论为孤例,而是说明其论具有近代文体批评的综合性思维特征。
仅就王先谦本人看,其治学路数还属于清学的范围,从近代中西学术交合的视域作界定的话,他依然是旧派文人。大体上看,与接受西学新思想的新派学人相比,在革新意识与辩证思维方法层面,旧派往往不及新派敏锐,具有一定程度的回护传统的守旧性。故王先谦的“何异骈散”论还不能说是他呼应近代文体发展新变大势所产生的充分理论自觉,因为其等视骈散的逻辑基础仍为旧式文体构型的技艺性规范,未涉及近代转型期新文体的构造需求,只能定位为其在传统文体框架内抛弃汉宋学术门户之见而生成的辩证通达的文体互通观。自植入西式审美性纯文学观之后,近代文体认知思想谱系的重建过程渐启对传统学术结构惯性的放弃以及新文体认知标准的形成,因而王先谦作为清式学人,没有参与随后渐进推开的近代新的文体识认标准的建构,其文体观的融通性特征仅是他自身视野开阔、思维通达的体现。这恰好预示了骈散融通作为一种文体演进形势在近代文体语境中铺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旧式文人会通骈散并自动树立的融通式文体认知思维与近代文体演进发展方向一致,为骈散融合的文体趋势增加了一层历史必然性的确据。
再从近代文体秩序重构的角度审视王先谦的“何异骈散”观。同以骈体为“正宗”的骈文一派相比,似乎其因灵活辩证的认知视角而无法凸显明确的文体立场,但从骈体地位认同来说,王先谦无意于执守汉宋任何一种学术门户,以平允、无偏执的文体认同观看待骈散,且纂辑骈文选本也是为了开示骈体写作门径,是对骈体另一种方式的肯认。王先谦基于研治传统学术的辩证态度看待文章类型,是用自有的方式为近代骈体批评增添了注重文体内实、以融通为特质的骈文观。若以“晚清—五四”衔接相续的历史逻辑来考量,中国文体批评发展至近代,一方面在文化语境的制约下面临着转型生新的压力性需求,另一方面也保持着与传统文体思想资源无法割裂的血脉性联系。于骈体批评而言,近代文体秩序的重组进程引发骈文地位的变化,骈体作为具有中华传统审美属性的标志性文体,尽管其应用价值渐弱乃至势微,但文体内实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质素依然使其葆有鲜活的文体生命力;相应地,其文体生命力的维持也亟需吸取不同的文体技法以自存,故而与散体融通便成为必由之路。因此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文体境遇中,王先谦这种调和骈散式文章观念的补充,既有对骈体生命力的维护,又意味着对传统文章质实观的汲取,具有独特的体认中华文体传统的批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