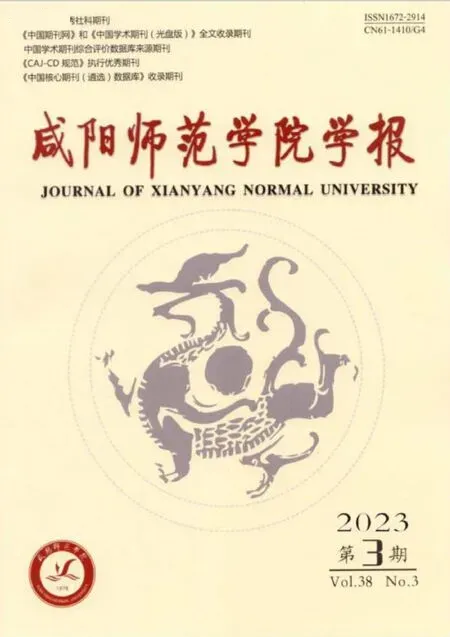洛学心性化:以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为线索
袁大鑫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工夫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儒家工夫论探讨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个人道德与境界,进而将之推扩到他人、社会。”[1]3二程所创立的洛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洛学包含众多的思想内容,其所论述的涵养、致知工夫论展现了二程如何修身成圣的思想内容。在二程思想基础之上,程门后学对致知、涵养工夫进行发挥,推动了洛学的进一步发展。张九成受业于杨时,被称为“渡江大儒”[2]1340、“羽翼圣门者”[3]1302,是程门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九成所阐述的修养工夫反映了其对心本体的认识,体现出理学向心学的发展走向。以二程、张九成的工夫进路考察,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学界已有研究。①学界对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的探讨涉及众多方面。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进行研究的有侯外庐《宋明理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从戒慎恐惧、慎独等具体工夫进行研究有刘玉敏《心学源流:张九成心学与浙东学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郑熊《宋儒〈中庸〉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敬峰《二程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从工夫与本体关系研究有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带有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在分析上具有不完整性,缺乏系统地分析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以观照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进程。本文以二程、张九成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二者工夫思想的详细探察,进一步展现理学向心学转变的思想路径与历程。
一 从“穷物理”到“穷一心之理”的转移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包含着格物、致知、诚意等八条目。二程高度强调《大学》的重要性,讲到:“《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4]1204他们将《大学》看作做是圣人的遗言,是通往圣学的门径。在《大学》八条目中,二程强调格物是“适道之始”,格物是本是始,治天下是末是终。“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4]316二程进一步提出了格物致知论。
关于格物、致知的关系,二程认为致知在于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训解为“至”,物训解为“事”“理”,“格物”即是“至其理”。二程又将格物与理本论相联系,认为格为“穷”,物为“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格物即是穷理,穷理然后可以致知。在二程看来人被万物所累,思虑被蒙蔽,通过明善可以“得其要”。明善在于格物穷理,“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4]144,通过格物穷究事物所包含的理即“物理”,进而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体认理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对于他人所问的“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程颐讲道:“不拘凡眼前物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4]247物不仅指用眼睛所观察到的事物,而是指一切事物,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理。如何才能格物?二程强调诚意对格物的重要性,讲道:“但立诚意去格物,其迟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迟。”[4]277诚意决定能否格物;聪明与否决定了格物的快慢。在二程看来格物穷理有多条途径,只要能够入“道”,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而随之变化。如“穷理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究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格物穷理主要有三种方法:读书、论古今人物、应接事物。在二程看来格物不是穷尽天下之物,而是穷究一事上的理,由此可以类推到穷究世间其他事物。不过,二程也强调格物是需要不断地积累、涵养,“格物亦须积累涵养”。程颐认为通过“集众理”,积累日久,进而实现对天理的“贯通”,达到“豁然有觉”的境地。正如他所说:“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4]175然而二程所强调的格物重心在于对人伦日用的认识与把握。在程颐看来“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如‘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泛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格物的关注点在于对道德伦理的认知、体悟。同时,二程所说的格物实质在于把握自身固有的天理。正如程颐所讲格物致知是人所固有的,并不是外在所赋予于人的,格物目的在于通过对外在天理的察识、体认来恢复人本身的天理。“‘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4]316对此,有学者研究指出:“程颐‘格物致知’并非是要向外探求知识(无论是关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知识还是内在道德世界的知识),而同样是一种以明觉内在固有道德本性(‘天理’)归宿的道德修养方式。”[5]125这就是认为二程所注重的“格物致知”,其实质是一种体认个体自身所具有“理”的修养方法。
格物是为学过程中理解、认知万物规律的方法与路径。张九成将格物重点放在心上,探讨格物与穷理的关系。
在二程基础之上,张九成也高度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他讲道: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天下之理无一之不穷,则几微之生,无不极其所至矣……倘知格物之学,则可以知圣人之心。[2]153
为学之人通过格物之学,能够明晓圣人的本心。他吸收了二程将“格物”解释为“穷理”的思想,同时也同样强调格物穷理时要无一物不穷究,突出了物所具有的普遍性。“格物者,穷理之谓也。使天下之理一物不穷,则理有所蔽。理有所蔽,则足以乱吾之智。”[2]882杨时在解释“致知格物”时,主张致知就是“极尽物理”,但“理有不尽”处,不能使人充分致知,这就需要在“意诚心正”[6]535处下工夫。同时,杨时认为事物繁多不可胜穷,将“格物致知”与“反身而诚”相联系,将人的工夫限定于内在。如:“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6]494张九成在杨时思想基础上延续了洛学“格物穷理”的基本思路,进一步突破强调“心”在格物穷理过程中的作用。他讲道:
夫学者以格物为先。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2]159
穷究心所具有的“理”,能够通晓世间万事万物的“理”,穷究一事所具有的“理”,可以知晓天下的“理”。张九成还说道:
所谓格物者,穷理之谓也。一念之微,万事之众,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验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又旋著以观微,又考终而要始,往来不穷,运用不已,此深造之学也。夫如是,则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微而万物,皆会归在此,出入在此……[2]943
对于格物穷理而言,小到一念,大至万事万物,无一不需要探究其始终,而万事万物都会归于“心”。张九成进而提出“心即理,理即心”的主张,将格物重心放在求心中之理,穷理即是穷心中之理。
格物之学是通往圣贤之心的途径。在张九成看来六经所体现的是圣贤之心,通过格物之学可以先得圣贤之心,那么“六经皆吾心中物耳”[2]1059。格物即是在为学的过程中体悟、践行圣贤之心,使己心与圣贤之心相切合。六经之理是圣贤之心、众人之心所体现的理,不必汲汲外求于书本。若是拘泥于《六经》文字本身,则是“道之赘”。张九成认为读书目的在于明心中之理,以求心为本,进而讲道:
夫六经,明天下之理者也。使吾自格物之学,穷天下之理,小大不遗,幽显皆彻,内外一致,则六经之言皆吾胸中所欲言者耳。随吾意之所在,取以用之,或断章而取义,或逆志而忘辞……故吾意之所在,理之所在,圣人之所在也。[2]947
通过格物之学进而可以明晓天下之理,我之所思、所想皆是合乎圣人之意,我心即是圣人之心。
总之,二程将格物致知与天理相联系,强调通过格物穷理以达到对理的察识与认知。同时,二程认为格物需要不断地积累与涵养,涵养日久自然通晓世间万物所显现的理。张九成在二程格物思想之上有所突破,将格物的重心放在心上,主张“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将对外在的格物穷理彻底地收归于对心中之理的穷究与认知。
二 从兼重内外涵养向内在涵养的转变
二程讲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424,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了体认作为最高本体的“理”,实现天人合一境地,二程提出了对“理”的涵养工夫。同时,二程所阐述的工夫进路体现出兼重内外的特征。
二程提出了“敬”与“诚”的修养工夫,强调敬、诚在涵养工夫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敬”,二程说道:“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4]66为学之人认识道的起点在于“敬”,通过“敬”进而能够“致知”。“诚”也是二程所重视的修养方法。二程主张为学之人应当重视诚。“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4]317
二程多次提及“心虑纷乱”的问题,认为“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为学之人常被思虑纷乱所困扰,内心不得宁静,所以要在“心”处下工夫。在二程看来“诚”“敬”是向内用功的涵养工夫。二程强调为学之人通过“诚”可以成为君子;若是人不“诚”就会产生“学杂”“事败”“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的结果。如:“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4]326二程还从多个方面阐述“诚”的工夫,讲道: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4]19
诚则自然无累,不诚便有累。[4]87
为学之人唯有心中立诚,才能“自然无累”,施行运用“三达德”,从而可以把握进德修业的关键所在。
在二程看来,“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4]14。为学之人应当以“敬”守心,充实内心,涵养天理,自然有所得。“敬”所指的具体修养方法是什么?二程讲道: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4]169
以“主一无适”来界定敬,主一即是敬,就是要求为学之人心有所主,不敢欺瞒、有所敬畏,涵养日久自然明晓天理。为了进一步解释“敬”,二程讲道:“敬则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岂须得道更将敬兄助之?犹之有人曾到东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长安,若一处上心来,则他处不容参然在心,心里着两件物不得。”[4]27在二程看来“敬”就是保持内心专一,避免心有所游离。二程还将“敬”与“静”“恭”相区别。二程认为敬源自于虚静,但虚静不等同于敬,“敬则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4]157。若是把敬当成静,这便流入释氏的思想。同时,在二程看来敬是针对人内心用功,而恭是向外待人接物。“发于外者谓之恭,有诸中者谓之敬。”[4]92二程所讲的“诚”“敬”工夫是体认天理工夫的不同表现。二程讲道:
如天理底意思,诚只是诚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别有一个诚,更有一个敬也。
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4]92
为学之人通过“诚”必然能够“敬”,而没有达到“诚”时,必须通过“敬”的工夫。可见,“诚”“敬”是涵养工夫中不可分离的范畴。此外,二程也强调“诚敬”工夫的连续性,必须持之以恒地施行。“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不诚则无物。”[4]118
二程也注重外在的涵养。程颐所讲的“敬”也是指“动容貌、整思虑”的“闲邪之道”。他讲道:
敬是闲邪之道。闲邪存其诚,虽是两事,然亦只是一事。闲邪则诚自存矣。天下有一个善,一个恶。去善即是恶,去恶即是善。[4]185
通过去除邪意、妄念的“闲邪”之道,“诚”自然得以存有。“闲邪”“存诚”是敬表现的不同形式。在程颐看来“闲邪”也是指“非礼而勿视听言动,邪斯闲矣”,就是保持人的言语、行为合乎礼节,邪意得到消除。“非礼而勿视听言动”具体是指“动容貌”“整思虑”,保持庄敬严肃的状态。程颐说道:
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诚将来存著……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闲邪更着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4]149
为学之人在外在言谈举止上保持谨慎的状态,自然产生“敬”。人们“衣冠”“瞻视”的整齐严肃也透露出“敬”。“俨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其中自有个敬处。虽曰无状,敬自可见。”[4]185
二程所注重的诚敬工夫更在于统摄内外。在二程看来“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这就指明了为学之人在施行“诚”的过程中,应当兼顾内外之道。当他人提出“如何是主一”的问题时,程颢认为“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著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4]433“敬”在于收敛个人的身与心,保持专一的状态,而不产生“毫发事”。由此可知,二程所强调的“敬”“诚”表现出统摄内外的路径。
在对“天理”的体悟中,二程“诚”“敬”工夫展现出内外兼顾的思想路径。有学者研究指出:“二程的诚敬工夫本质上都是超越二元对立、跳出习心的束缚而使心凝聚专一呈现本体的工夫。”[5]128这就说明,不论是以内在修养工夫识得本体,达到豁然贯通的诚敬之道,还是以保持整齐严肃的状态消除邪意的诚敬工夫,其实质在于通过修养工夫保证“天理”的完整呈现。
作为洛学后学,张九成在二程修养工夫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戒慎恐惧、诚、敬等范畴的阐述,进一步将修养工夫转向内在。
张九成通过对《中庸》的诠释,表现出对未发之时戒慎、恐惧工夫的重视。他以《中庸》文本“中”的概念,对“率性之谓道”进行诠释。
“率性之谓道”,此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以养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之理,此所以求中也。[2]1085
“率性之谓道”即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以戒慎、恐惧等工夫养未发之理,即是求中。杨时注重体验未发,专注于“燕闲静一”的体悟。张九成舍弃了杨时静中“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转而注重未发之时的戒慎恐惧的涵养方法。张九成认为“率性之谓道”是一般儒者尽心修养的过程。对于圣人,率性直造天命之本,就能“有乾坤造化,制为人伦之序,以幸天下,此所谓和也”[2]1088,省去“养中”的步骤,直接行人伦之序,达到中和的地位。
张九成以“率性之为道”为中心,展开对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涵养。戒慎、恐惧,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简称,指一种心理状态。《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面对不可捉摸的“道”,人需要保持谨慎的心理状态,即使一人独处时也应端正自身的言行,这即是慎独。戒慎恐惧侧重于对未发前的涵养,慎独则是侧重于从未发转变为已发之际的省察。张九成进一步强调戒慎恐惧即慎独的内向工夫,讲道:
夫不睹不闻,少致其忽,宜若无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显见于心目之间,昭昭乎不可掩也,其精神所发,道理所形,亦必有非心邪气杂于其间,不足以感人动物,而招非意之辱,求莫为之祸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独也。[2]1086
戒慎、恐惧以养中和,而喜怒哀乐已发未发之间乃起而为中和,大含元气而天下莫能载,小入无间而天下莫能破,察之之功如此。君子于慎独之学,其可忽耶?[2]1097
为学之人若是行事过程中有怠慢忽视之心,那人心难免沾染邪气、非心,人自身也容易招致意外的祸患与侮辱,因此为学之人应当在不睹、不闻处慎独;戒慎恐惧的涵养工夫也贯彻于喜怒哀乐未发与已发之间,这就将慎独视为内心修养的工夫,将慎独的范畴从未发已发之间扩展至未发前。可见,慎独与戒慎恐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夫。有学者研究指出戒慎恐惧与慎独,“二者本是同一工夫:慎独着重讲用功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处,戒慎恐惧着重讲用功的方式和态度。”[7]张九成对戒慎恐惧即慎独的重视体现了其对内心修养工夫的强调。
戒慎、恐惧的涵养工夫是求中、养中的途径。张九成认为喜怒哀乐未发时,是性本体,也是中,当以戒慎、恐惧的工夫涵养未发时的理,就是率性、求中。“惟一意戒慎、恐惧,以养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之理,此善求中之道也。”[2]1087戒慎、恐惧也是“养中”的方法。张九成说道:
夫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此养中之法也……君子欲求中庸,要当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中得味,则识中之本矣。[2]108
从“不睹”“不闻”处下工夫,即是从自我意识层面入手来涵养未发之中。在张九成看来戒慎恐惧的内在工夫亦是进入圣人之境的门径。张九成强调中庸之德为中道“无过无不及”的体现,惟圣人具备中庸之德。如何才能达到圣人之道?张九成讲道:“余尝求圣人而不可得,今乃止在喜怒哀乐未发耳,岂不近乎?子思明示天下人以入路,且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2]1093从喜怒哀乐未发处入手,通过内在的涵养工夫,为学之人能够拥有中庸之德。
戒慎恐惧的工夫在于自我内心的反省、觉察。张九成强调戒慎恐惧在于对“未形之先”“未萌之始”的省察。他说道:
夫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载,小莫能破,以其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察于微茫之功也。戒慎、恐惧,则于未形之先,未萌之始已致其察矣。察之之至,至于鸢飞、鱼跃,而察乃在焉……顾惟此察,始于戒慎、恐惧而已。[2]1095
戒慎恐惧的工夫亦在于念虑、践履的本初状态下用力。在张九成看来为学之人应当静观“心之念虑”“身之践履”,从念虑、践履的初始处出发,“察其始察其终,察其微察其著”,以达到“念虑无所逃,履践无所失”“仁义油然而生”的状态。正如,张九成阐述《论语》“君子有三畏”时,说道:“要之恐惧常修省,乃是吾心所必然。君子如云止三畏,又何终日却乾乾。”[2]1246为学之人应以戒慎恐惧的方法修养“吾心”。可见,张九成所注重的戒慎恐惧工夫正是从本心出发的内在修养工夫。
“诚”也是理学家所不断讨论的涵养工夫。张九成强调“至诚无息”,将诚化为人内在的活动,使之成为内在的修养工夫。针对“‘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得非于诚上用功否”,张九成认为“须自知有我始得。我不自诚,于物上求诚,则我与物二矣,岂诚耶”[2]1175,从自我出发用功,达到自我与物的结合。“诚”也是戒慎恐惧的涵养工夫。“诚者,岂一日遽然,安坐定气,闭目正容,便以为诚哉?当平居暇日,戒谨恐惧,积久以养之可也。”张九成否定静坐定气、闭眼正容的修养工夫,强调“诚”的工夫为未发时戒慎恐惧的修养方法。此处,张九成以“诚”的工夫纠正了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未发所出现的问题。“敬”也是理学家探讨涵养工夫时的重要范畴。张九成继承二程的主敬说,强调从人本心入手来施行持敬工夫。何谓敬?张九成认为“妄虑不起,百邪不生,是敬也”[2]356,将敬视为一种虚静的状态。如何持敬?在张九成看来“敬无定体,平居无事,皆敬也”,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敬”都深藏其中。为学之人内心持“敬”,“虽死不可变,易篑、结缨是矣”。同时敬在内心时“百念皆正,百邪皆远”[2]465。人所施行的行为都是敬的显现,“视、听、言、貌、思皆自敬中出”。张九成说道:“若于君子能修敬,敬外无缘复有余。子路不思三致问,病犹尧舜果何如?”[2]1245敬是人内心的工夫,为学的人应当从敬出发。对于持敬的作用,张九成主张为人不敬就会产生私心。刘荀在《明本释》中记载了张九成所说“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子”[8]169,敬是去除自身私欲的手段。
总之,二程所提出兼顾内外的涵养工夫,落脚点在于体认天理。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诚、敬等内在工夫的重视,实现了对二程诚、敬思想的突破,将工夫收摄于对自我内心的省察与涵养,展现了洛学工夫内向性倾向。有学者研究指出:张九成“通过重视和高扬内在的修养工夫……最终彻底将理学所极力要确立的具有普遍客观性的天理归结到纯主观性一己之意识,实现理本体到心本体的转变”[9]222。可见,张九成通过对内在涵养工夫的重视,实现了理学向心学内在理路上的转变。
三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的探究,可知洛学存在着理学向心学发展的理路。同时,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过程,可以从本体、工夫与境界等方面加以考察。就工夫而言,其与本体、境界等内容具有密切联系。首先,二程所阐述的工夫实质上是对天理的认知与践行,而张九成所注重的穷究一心之理与戒慎恐惧的内在涵养工夫,彰显其所认知的心本体。有学者研究指出:“对本体的体悟,决定了工夫应有的路数,而从工夫的路数又反过来可以彰显与证成其所体悟的本体。”[10]3这就说明通过对二者工夫进路的考察足以反映二程理学向张九成心学转变过程中本体思想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对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的考察也显现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脉络中心性思想的转变。“只有对心性问题进行穷深极微的讨论,道德践履上所下的工夫才可能有所依托。”[10]88从工夫路数出发可以体证心性思想。最后,工夫的践行必然涉及对境界的讨论,境界为工夫实践的目标与归宿。二程、张九成关于工夫的阐述,足以把握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境界思想的不同。总之,在本体、工夫及境界等范畴中,工夫涉及了本体的落实、境界的实现,是理学向心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以工夫进路为视角,足以反映洛学心学化的走向。
在洛学发展中,不仅显露出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工夫进路,仍有延续理学工夫进路的道南学派,这反映了洛学工夫论的深化。从工夫进路来看道南学派延续理学发展方向,杨时在其师格物穷理的基础上,认为“物盖不可胜穷者”,唯有通过“反身而诚”,才得以认知万事万物的规律,这就将“格物致知”与“反身而诚”相联系,通过内向性的认识,达到与万物、天理的合一。同时,杨时也强调未发时的静修,认为“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6]480。对于“至道”,要在“燕闲静一”中以心“体之”“验之”,专注于向内体验。杨时所讲的“燕闲静一”体验方法,将工夫转向到个体的自我体验中,强调内心的直觉体验。杨时也以“体验未发”的方法教授学生。朱熹曾说道:“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11]1802杨时所讲的“体验未发”也成为道南学派的基本宗旨。与延续理学工夫路数的道南学派相比,张九成突出强调穷究一心之理,进而能明晓天下万理。同时,张九成也舍弃了杨时静中“体验未发”的工夫,转而以“戒慎恐惧”体认本体,纠正了道南静中体验所存在的问题。
在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作为心学先导的张九成,也有开心学端绪的王蘋,二者工夫进路存在不同发展方向,显示了洛学心学化的多样性。王蘋认同杨时“体验未发”的工夫路数。在回答他人所问“致知之要”问题时,王蘋指出:“宜近思,且体究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12]102但他不止步于此,进而说:“莫被中字碍,只看未发时如何。”这就抛弃了杨时体验未发之中的思想。王蘋舍弃对本体的体认,也体现在对“孔颜乐处”的理解上。在他看来:“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则有所倚著。功名富贵,固无足乐;道德性命,亦无可乐。庄子所谓‘至乐无乐’。”王蘋将道与富贵共同舍弃,强调所乐并非乐道,“这就将洛学所致力于确立的理本体在乐的感受性被消解了”[13]55。同时,王蘋认为“‘万物皆备于我’,某于言下有省。”[12]104王蘋未明确指出具体工夫的详细展开,忽视了工夫向现实的落实,仅强调内向体认,这就不免走向了禅宗的修养工夫。可见,“王蘋工夫的内向、顿悟以及忽视下学工夫只求上达之特征,甚至以上达为工夫,实际上已偏离理学,将心学工夫论的特征展现无遗”[14]261。王蘋、张九成工夫进路立足于理学思想,由于工夫内倾化,二人将外在活动收缩于对自我意识的觉悟,但二者工夫呈现不同的走向。张九成所强调的对一己之心的穷究与戒慎恐惧工夫体认本体的工夫进路更多保留理学特色;王蘋简易工夫有流向佛教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