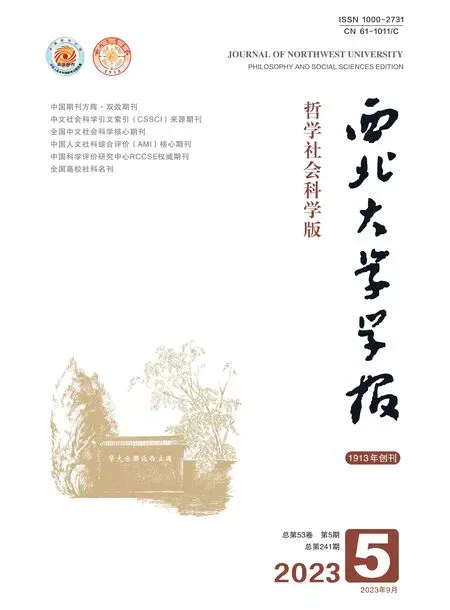如何消解他心难题?
——从维特根斯坦的“甲虫比喻”谈起
李国山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南开 300350)
他心难题由来已久。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一直为他人心灵之谜而苦苦思索。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心灵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活动,而且只有假定自心的存在才能解释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认识何以可能。可是,尽管一个认知主体可借助感官对包括他人身体在内的外在事物形成直接的认知,却无法对他人的内心有任何确切的把握。对于他人心灵,我们要么采取类推的办法“将心比心”,认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么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语行为来揣测他们的内心活动。但这两条途径注定都难以消除自心与他心之间的隔膜,最终无助于他心之谜的破解。尽管19世纪末叶兴起的实验心理学在科学地描述人类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于围绕他心而生的哲学难题似乎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作为20世纪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探讨中对心理学哲学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他认为,他心难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在语言的误导之下不当地假定了自心和他心的存在以及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分,从而执迷于自心如何认知他心的难题。维特根斯坦极力倡导对一系列心理学表达式进行详细的语法考察,尽量充分地展示它们的不同用法,让人们看清它们最初是如何被使用的,从而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并以此从根本上消解他心难题。在他眼中,这一难题就仿佛是一个顽固的哲学病症,必须为之开出诊治的药方来。维特根斯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准确把握他的思想,学术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文拟从他所提出的“甲虫比喻”入手,尝试弄清他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语法考察来消解他心难题的,并在此基础上就相关的学术争论发表一点看法。
一 、“甲虫比喻”及其寓意
在《哲学研究》§293中,维特根斯坦用到了著名的“甲虫比喻”:
现在设想每个人都对我说,就他而言他只是从自己的情况知道疼是什么!——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们称之为“甲虫”的东西。谁都不许看别人的盒子;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他的甲虫知道什么是甲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每个人的盒子里装着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东西在不断变化。——但这些人的“甲虫”一词这时还有用途吗?——真有用途,这个用途也不是用来指称某种东西。盒子里的东西根本不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甚至也不能作为随便什么东西成为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为盒子也可能是空的。[1]153
这个比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出现在私人语言论证的上下文中,涉及从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角度探讨语词意义的问题。具体而言,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像“疼痛”这样的感觉语词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在提出这个比喻之前写道:“如果就我自己而言我说我只是从自己的情况知道‘疼’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就他人而言我不也必须这样说吗?可我怎能这样不负责任地从这样一种事例来进行概括呢?”[1]153维特根斯坦这里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不能通过首先假定自己只能从私人的情形得知“疼痛”这个词指称什么,来推测他人是如何用这个词进行指称的。这是他关于如何应对他心难题的基本想法。
仔细分析下来,维特根斯坦这里主要针对的是以穆勒(John Mill)为代表的、关于他心难题的经验主义类比论证。而这一论证很容易受到怀疑论者的攻击: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自身的情形感受到疼痛并由此把握“疼痛”一词的意义,那么,在无法亲身感受他人的疼痛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推知他人是如何使用“疼痛”一词的呢?
维特根斯坦提出“甲虫比喻”,显然是想抛弃类比论证这种解决他心难题的思路,因为他认为这一论证是误入歧途的:我对“疼痛”一词的使用并非建立在对我的某个特定的痛觉的指称之上的,而这种痛觉就相当于比喻中的那只甲虫。维特根斯坦让我们注意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每个人的盒子里装着不同的甲虫,有的是金龟子,有的是花大姐,有的是象鼻虫,还有的是屎壳郎;第二,每个人盒子里的甲虫都在不停地变化着;第三,有人的盒子是空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甲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谈论有关甲虫的话题。在谈话的过程中,“甲虫”一词会被频繁使用,但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个词的每次使用都意指同样的东西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疼痛”一词在其中被反复使用的一个语言游戏,在这里,这个词同样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我们说的可能是不同的疼痛,这些疼痛或许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甚至在没有谁当下有任何疼痛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热烈地讨论关于疼痛的话题。
在提出“甲虫比喻”之后,维特根斯坦紧接着又明确指出:“是的,我们可以用盒子里的这个东西来‘约分’,无论它是什么东西,它都会被消掉。这是说:如果我们根据‘对象和名称’的模型来构造感觉表达式的语法,那么对象就因为不相干而不在考虑之列。”[1]153由此看来,维特根斯坦用这个比喻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并不是通过向内看自己的盒子而确定“甲虫”一词与盒子里的东西之间的指称关系一样,我们也不是通过向自己的心灵内部窥视而确定像“疼痛”这样的感觉语词的意义的。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依据对自身情况的这种不当设想去类推他人的情况,从而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去解决他心难题:“以自己的疼痛为范本来想象别人的疼痛殊非易事:因为我必须根据我感觉到的疼痛来想象我没有感觉到的疼痛。”[1]155
维特根斯坦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他心难题,只能借助他所倡导的语法考察方法。就“甲虫比喻”而言,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甲虫在这个思想实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维特根斯坦主张,我们只需要考察“甲虫”一词的用法,而完全不用考虑甲虫是否存在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同样,只有通过仔细考察像“疼痛”这样的感觉语词在心理学语言游戏中的各种用法,才有望把握诸如此类的心理学概念的真正意义,从而摆脱围绕它们而生出的种种哲学难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对像“意识”“感觉”“记忆”“意指”“理解”“思考”“推理”“想像”“期望”“意图”“相信”“知道”等等这样一些心理学语词的不当使用,引发了给我们造成严重困扰的一系列心灵哲学难题。
在《哲学研究》§§243-315这些被公认为展现其私人语言论证的评论中间,维特根斯坦穿插进了两段关于其哲学观的著名表达:
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1]139
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1]158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上下文中发表自己关于哲学的一般看法,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心灵哲学所遭受的形而上学危害。他想通过具体实施关于心理学语词的语法考察来清除传统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消除围绕心身问题而生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难题,以劝导心灵哲学家们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探究道路上来。在《哲学研究》§§295、299、303、314等中,维特根斯坦多次提到做哲学时会陷入的误区,并告诫我们要竭力从中摆脱出来。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经验命题和语法命题做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指科学命题或者我们日常使用的命题,而后者则指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起到规范作用的命题。针对心理学哲学的情形,他做了具体探讨:“‘我只从我自己的情况知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命题?经验命题?不是。语法命题?”[1]154他接下来指出,“我只从我自己的情况知道……”也不是一个可在语言游戏中发挥规范作用的语法命题,因为它只会对我们使用心理学概念产生误导:当我们试图通过向内看来解答涉及心灵状态的哲学问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我们倾向于说,我只是相信别人有疼痛,而我却知道自己有疼痛。而说自己知道自己有某种感觉,就是在说自己向内窥见了这种感觉从而正确地使用了代表这种感觉的那个语词。
但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正是要驳斥这种建基于“语词代表私人对象”的模型的根深蒂固的观点:“如果我想考察我此刻头疼的状态以便弄明白有关感觉的哲学问题,这就表明了一种根本性的误解。”[1]159
二 、 如何通过语法考察消解他心难题?
然而,维特根斯坦到底是如何消解他心难题的呢?如果甲虫的存在与否对我们关于甲虫的谈论毫无影响,那么,我们的谈论岂不成了毫无内容的空谈啦?关于这一点,他做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疼痛既非某种东西(something)亦非乌有(nothing):
“但确有疼痛的疼痛举止和没有疼痛的疼痛举止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你总会承认吧?”何止承认?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区别?——“你却再三得出结论说感觉本身子虚乌有。”——不然,它不是某种东西,但也并非乌有!结论只是:凡关于某种东西无可陈述,在那里乌有就仿佛和这“某种东西”作用相同。我们只是在抵制要在这里强加于我们的语法。
别认为语言始终以单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传达思想——不管这些思想所关的是房屋、疼痛、善恶,或任何其他东西;唯当我们彻底和这种观念决裂,上述悖论才会消失。[1]156
维特根斯坦这里明确指出的是,将疼痛比作盒子里的甲虫,很自然地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疼痛是某种东西,我可以具有或不具有它,另一个人也可以具有或不具有它。这种本体论假定似乎是我们关于疼痛的语言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我们在谈论疼痛,它就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东西。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盒子里有没有甲虫对于这个语言游戏无关紧要呢?
维特根斯坦将“疼痛的有无问题”称为哲学上的一个悖论,而他对心理学语词的语法考察就是要消除这个悖论。在上面引用的《哲学研究》§304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实际上成了如下这种强烈诱惑的牺牲品: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表达某种确定的意思,而在言语交流过程中,我们总是想着从他人的言语中捕捉到他们的真实想法。
为摆脱这种诱惑,维特根斯坦奉劝我们更为仔细地查看语言的各种不同用法:“一个词怎样起作用,猜是猜不出来的。必须审视它的用法,从中学习。”[1]167他提醒我们说,句子的用法有无数种,我们绝不能只是盯着“表达思想”这一种用法,以为说出的话都是要表达自己心中已有的某种想法的。他的著名的私人语言论证一方面旨在表明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借助公共语言实现交流;另一方面也是想彻底破除“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这种一般的看法。
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否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能够用这种语言写下或说出他的内心经验——他的感情,情绪,等等,以供他自己使用——用我们平常的语言我们不就能这样做吗?——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这种语言的语词指涉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涉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1]135维特根斯坦否认这样一种私人语言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一节里,他明确表达了他关于感觉语词的正当用法的观点:
语词是怎样指涉感觉的?——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我们不是天天都谈论感觉,称谓感觉吗?但名称怎么就建立起了和被称谓之物的联系?这和下面的是同一个问题:人是怎样学会感觉名称的含义的?——以“疼”这个词为例。这是一种可能性:语词和感觉的原始、自然表达联系在一起,取代了后者。孩子受了伤哭起来;这时大人对他说话,教给他呼叫,后来又教给他句子。他们是在教给孩子新的疼痛举止。
“那么你是说,‘疼’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哭喊?”——正相反;疼的语言表达代替了哭喊而不是描述哭喊。[1]153-154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发明并使用语言之前,痛苦的表情或哭叫乃是人们表达疼痛的主要手段。当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的这种表情或者听到他的哭叫声时,便知道他处于疼痛之中。而在掌握了某种语言之后,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借助表情或哭叫声表达疼痛,但多了直接说出“我头疼”“我牙疼”等等这样的表达途径。你会说,这样的表达更文明一些了。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我们所掌握的新的疼痛举止。也就是说,它们还是发挥着与表情或哭叫一样的作用:让他人明白你处于疼痛中,并从他人那里得到安慰或帮助。这么一来,你也就成功地实施了一项交流活动。维特根斯坦就把我们生活中一个个这样的事件称作语言游戏,因为到了文明阶段,我们的所有交际行为都少不了语言的介入。
可是,就像表情或哭叫声只是代替了疼痛而并没有描述疼痛一样,“我头疼”这句话也只是代替了而并没有描述表情或哭叫声,从而更没有描述作为我的一个心灵状态的头疼。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多种表达并用的。进一步来说,“我头疼”这句话并不是因为图示了我感到头疼时的某种内心状态才成为有意思的表达式的。换句话说,当我说出“我头疼”时并不是想表达某种关于我的这个疼痛的思想。维特根斯坦认为,我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说出了“我头疼”,这便是我对这个句子的一个用法,而这个用法使得它在这个语境中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表达式。这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关于命题意义的图像论的批判与超越。
如此一来,我们便无需因为无法弄清别人的盒子里有没有甲虫,或者他的那只甲虫到底是“花大姐”还是“屎壳郎”而忧愁和烦恼了。歌中唱道:“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是我对他人的真情告白。其实,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我也完全可以这样宽慰自己:“明明白白他的心”,因为我总是可以从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弄懂他的用意,并做出适当的回应,从而完成有效的交流。
不过,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让我们不要为甲虫是否存在或如何存在而焦虑,并不单单是想告诉我们:他人的心灵只是一个虚幻的假定,或者,像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者所假定的那样,他心乃是一个永远不为外人所知的暗箱。维特根斯坦并不想着如何从正面解答那些貌似深刻的传统哲学问题,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这些问题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的解答。他只是想引导我们去弄明白这些问题是如何逐步俘获我们的:“怎么就来了关于心灵过程、心灵状态的哲学问题?来了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第一步是完全不为人注意的一步。我们谈论种种过程和状态,却一任其本性悬而不决!我们以为,也许将来终会对它们知道得更多些。但正由此我们把自己固着在某种特定的考察方式上。因为我们对什么叫做更切近地熟知某个过程有了一个特定的概念。……我们似乎已经否认了心灵过程。但我们当然不想否认这些。”[1]157-158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日常关于身体、心灵、自我、意识、感觉、情绪、思考等等的谈论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恰恰是哲学家们在语言的诱惑之下,做出了一个个的“语法虚构”,这才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他这样提醒人们: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
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1]73
其实,维特根斯坦就是想要人们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中挣脱出来,不再纠结于那些再平常不过的语词的所谓哲学意义,不再试图弄懂并回答那些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单就疼痛这样一种日常的感觉经验来说,只要保持“疼痛”“牙疼”“胃疼”“脑壳疼”等等词语的日常用法,就不会陷入莫名其妙的哲学问题当中。
首先,我们都有疼痛的经验,谁也不会想着去否认它的存在。而且,即便是在尚未有过疼痛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会使用“疼痛”这个词。其次,当我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什么是疼痛,或者,各种不同的疼痛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些疼痛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和差异性时,我们会阅读相关的书籍、去询问相关专家。这些书籍或这些专家会用科学的语言向我们描述各种疼痛。
最后, 哲学无法告诉我们疼痛是否存在、 怎样存在, 而只能向我们描述“疼痛”一词的丰富多样的用法, 并展现这些用法之间的关联和相似之处。 这便是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 不会把我们引向歧途的新的探究方式: “说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考察,这是对的。 ……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 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 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 这些描述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就是说, 从哲学问题得到它们的目的。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 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的冲动进行的。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增添新经验而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 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1]71-72
三 、 我们自主地使用心理学表达式
然而,仍然存在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语言游戏中,我们借助各种语言表达式彼此进行交流时,总是在传达或接受某种东西吧?我们难道不是急切地想弄明白对方的真实想法吗?维特根斯坦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还是要求我们更为仔细地考虑所涉及的错综复杂的情形。比如,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课堂上,有位同学站起来跟正在讲课的老师说:“老师,我头疼。”老师停下来,关切地问:“很厉害吗?”学生抱着脑袋,痛苦地回答说:“很疼。”老师说:“那你现在就去医院看看吧。”于是,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室。
这个交流很顺畅:学生头疼想请假,老师确认后准假。我们现在要问:这名学生是否真的头疼对于这个语言游戏很重要吗?一方面,确实很重要。一般情况下,当他说“我头疼”时是想表达一件真实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且老师也正是因为采信了他的说法而准许他离开教室的。但另一方面,这似乎又完全不重要。可以设想,这位同学只是不想继续听课而装出了头疼得厉害的样子。而且,教师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去判定他是否真的头疼。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坚决否认语言具有像“表达思想”这样的单一功能。若是假定语言的目的就是传达说话人的思想而听话人就是要弄明白他的思想,势必就会引发诸如“他的思想从哪来?”“他何以能借助语言表达原本不为他人所知的思想?”以及“如何才能准确把握他的思想”之类的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考察了思想与实在的关系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思想,这个稀奇东西’——但我们思想时并不觉得它稀奇。我们思想时也不觉得思想神秘,而唯当我们仿佛反省着说:‘那怎么可能?’我们才觉得思想神秘。思想刚才怎么可能处理这个对象本身?我们觉得我们似乎用思想把实在捕到了网里面。”[1]196“思想和实在一致、和谐,这在于:当我错误地说某种东西是红的,那种东西尽管如此却仍不是红的。而当我要对某人解释‘那不是红的’这句话里的‘红’字,我这时指的是某种红的东西。”[1]197
这里,维特根斯坦是想告诉人们,哲学家们被这样一幅关于思想与实在之关系的图像俘虏了:要弄明白思想是什么,仿佛必须假定思想之外的实在,而且要弄明白思想如何与外在于自身的实在建立起关联,又会引起更为复杂的问题。此外,哲学家们还受惑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并倾向于假定思想乃是语言的灵魂。维特根斯坦考察了思想是如何被视作先于语词而存在、又如何被赋予语词的情形:“我们努力寻找——例如在写信的时候——正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语词之际,发生的是什么?这种说法把上述过程同翻译和描述的过程等量齐观:思想就在那里(可说先已在那里)我们只是在寻找思想的表达式。在种种情况下这幅图画或多或少相宜。——但什么又不会在这里发生!——我沉溺于一种情绪,于是表达式就来了。或者:一幅图画浮现在我眼前,我试着描述它。或者:我想到了一个英语表达式,而我要想出相应的德语表达式。或者:我作出一种表情,自问:和这种表情相应的是哪些词儿呢?等等。若有人问:‘你在有表达式之前有没有思想?’——我们须回答什么?又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表达式之前就已存在的思想是由什么组成的?’”[1]165-166
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因为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些周边情况,也很容易考虑不到各种可能性。我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都会努力做得更周全一些,但肯定做不到万无一失。对此,显然不能有过于理想化的一般要求。于是,维特根斯坦得出结论说:“思想并不是什么无形的过程,给予言谈以生命和意义,我们可以把它从言谈上剥下来,就像魔鬼把笨人的影子从地上捡走。”[1]167我们切不可被关于思想与实在、思想与语言之关系的错误图像所误导,而去追问思想到底是什么,或者在某个具体场景下纠结于对话中的某个人的某句话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样做不仅难以如愿,有时反而会妨碍交流、造成更大的误解。维特根斯坦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建立在即时的相互应答中的。这种彼此的默契乃是保障语言游戏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此外,维特根斯坦还强调指出,人们可以自主地支配语言:“只有学会了说才能有所说。因此,愿有所说,就必须掌握一种语言;但显然,可以愿说却不说。就像一个人也可以愿跳舞却不跳。”[1]166-167正因为人是语言的驾驭者,所以,在实际的语言实践中,语言表达式被大量地用做夸大、掩饰、假装、引诱乃至欺骗的手段。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这些通常被视作负面运用的用法不应被忽视。他明确主张将这些运用都视作特殊类型的语言游戏加以考察。甚至可以说,它们乃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也因此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49-250中谈到了假装的问题:
婴儿的笑不是假装的,——我们这种假定也许过于草率?——我们的假定基于哪些经验?
(像别的语言游戏一样,说谎是逐渐学会的。)
为什么狗不会伪装疼? 是它太诚实了吗? 能教会一条狗假装疼吗? 也许可以教会它在某些特定场合虽然不疼却好像疼得吠叫。 但它的行为总还是缺少正当的周边情况以成为真正的伪装行为。[1]137
事实上,我们是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亦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接触并进入各种语言游戏的。我们完全不能指望在一种纯而又纯的环境中习得一种语言。具体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或许,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教育会教给我们如何正当地使用语言。但是,一个人实际接受的学校教育、他的家庭环境、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等等都在他习得语言的过程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当我们想拿一些标准去衡量某个人是否真的掌握了自己的母语时,会遇到非常实际的困难。进入语言游戏所需的“玩家资格”,实际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最多只能这么说一个人:他接受了足够多的语言训练。其实,这些训练中包括了五花八门的语言技艺,包括说话的艺术、技巧等等。维特根斯坦特意指出,一只动物再怎么训练也无法真正掌握(比如)伪装的技艺。后期维特根斯坦倡导的语法考察具有明显的人类学视角,这已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还有一种特别的语言技艺叫做表演。我们说,这已经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了。演员们的表演是一种遵循着一定规则的语言游戏。其实,演戏就假装。我们老家土话这么夸一个演员:他装得太像啦!可以说,会装的演员才是好演员。我们还经常说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像是演员,都在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我们还经常抱怨自己活得太累,不仅身体累,而且心累:时时处处都想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位“理想的语言游戏玩家”:经过训练,他对母语的所有用法都烂熟于心,而且掌握了玩任何语言游戏所需的所有规则。实际情况是,我们每个人在一定阶段都还只是“半瓶子醋”,需要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不断锤炼。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总是只能在相互试探中进行。当然,我们期待坦诚相待,彼此拿真心换真心。但谁又能总是如其所愿?!
维特根斯坦精心构制私人语言论证,就是要表明,并不存在由指称私人感觉的语词组成的所谓私人语言。我们彼此交流只能借助于我们都已熟练掌握的共同语言。我们在语言游戏中所使用的每一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都只是它们在特定场景中的实际用法,而不是事先已然确定下来的东西。无论是语词还是语句,都没有承载着现成的意义或意思,每次使用都照着它们的本义就行了。也就是说,它们的用法并没有被预先固定下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胡乱地使用语言表达式,我们在学会这种语言时掌握了必要的规则。不过,尽管如此,每一个语言游戏都是新的,表达式的每一次使用都是新的。我们无法如实把握他人心里装的什么,也不能完全确定他人所说的是不是实话。因此,根本不必为此而苦恼,而是要安于我们所能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一切,并尽量真诚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言不尽意,甚至言不由衷,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不必过分计较。
那么,说出的语词就不代表任何东西吗?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总是努力地试图向别人表达自己。维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只是,即便我们想对他人吐露真心,但语言并不足以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总是面对着异常复杂的生活情境,而语言的表达功能是多么地有限啊!此外,在许多情形下,并不需要我们刻意表露所谓的真实想法,甚至在有些场合中,根本就没有谁谁谁的真实想法这回事儿。还有,我们难道不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采取更为策略、更为委婉、也更为适当的表达方式吗?
四、 怎样才能正确地使用心理学表达式?
既然他心如此难以琢磨,我们要实现与他人的成功交流,就必须正视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加以应对呢?维特根斯坦引入了关于标准的探讨,他告诉我们:“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1]238这种探讨被视作他的心理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对他人当下的心态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对其做出适当的回应。 就疼痛作为一种内在状态而言,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识别疼痛的同一性标准的问题:
“别人不可能有我的疼痛。”——哪些是我的疼痛?这里什么是同一性的标准?琢磨一下,讲到物理对象,是什么使得我们能说“这两个一模一样”,例如说“这把椅子不是你昨天在这里看见的那把,但同那把一模一样”。
只要说“我的疼同他的疼一样”有意义,那么我们两人也就可能有一样的疼痛。(甚至可以想象两个人在同一的——不仅是相应的——部位感到疼痛。例如暹罗连体人就是这样。)
我曾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题目时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但别人就是不可能有这个疼痛!”——对此的回答是:通过强调“这个”一词,并不就为同一性的标准提供了定义。倒不如说,这种强调只是向我们摆明了这样一种标准是通用的,但现在不得不再向我们提醒一下。[1]138-139
我所做的当然不是通过标准来识别我有同一的感觉,我是在使用同样的表达。但这并不结束语言游戏;它开始语言游戏。[1]152
维特根斯坦这里强调的是,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我们绝不只是为了识别他人的心灵状态而去依据标准做出这种识别:识别是为了交流,为了做出有效而适当的回应,为了最终完成这个语言游戏。所以,我们对于日常心理学语言游戏的考察不能执着于如何寻得判定内在感觉的同一性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根本是不存在的。我要观察的是心理学表达式的各种不同用法以及这些用法之间的联系。维特根斯坦认为,任何一个心理学表达式都没有唯一正确的用法,而只有它在不同场景中的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似性。这些都不是事先可以确定下来的。
语词的使用永远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的。如前所述,盒子里的甲虫可能是不一样的,是不停变化的,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而,哪来的心理学语词与内在私人对象之间的固定指称关系呢?!不仅在人与人之间没有同一的疼痛概念,甚至一个人自己也不可能有同一的疼痛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58中举了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们来想象下面的情况:我将为某种反复出现的特定感觉做一份日记。为此,我把它同符号E联系起来,凡是有这种感觉的日子我都在一本日历上写下这个符号。——我首先要注明,这个符号的定义是说不出来的。——但我总可以用指物定义的方式为自己给出个定义来啊!——怎么给法?我能指向这感觉吗?在通常意思上这不可能。但我说这个符号,或写这个符号,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感觉上——于是仿佛内在地指向它。——但这番仪式为的是个什么?因为这看上去徒然是仪式!定义的作用却是确立符号的含义。——而这恰恰通过集中注意力发生了;因为我借此给自己印上了符号和感觉的联系。——“我把它给自己印上了”却只能是说:这个过程使我将来能正确回忆起这种联系。但在这个例子里我全然没有是否正确的标准。有人在这里也许愿说:只要我觉得似乎正确,就是正确。而这只是说:这里谈不上“正确”[1]140-141。
我们试图为像“疼痛”这样的心理学概念确立同一的内在标准以确保将来正确地使用它,而维特根斯坦坚定地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并告诫人们:“不要试图去分析你自己的内心体验!”[1]318那么,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外在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他这样写道:“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1]279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言语行为来把握他内心的想法,并对其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从而实现有效沟通。
麦金本人则不认为维特根斯坦引入“标准”概念,是为了从正面回应他心怀疑论者:“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应视为企图为确定性做辩护,或者企图回应他心怀疑论者;这只是对日常疼痛概念如何发挥作用的描述而已。在掌握‘疼痛’一词用法的过程中,我们掌握了据以将疼痛归派给他人的证据。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促使我们回想起了标准是什么,也回想起了说某人装痛的标准是什么,还回想起了对后者的把握是如何从对前者的把握中发展出来的。要说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有某种反怀疑论的意思的话,这层意思就体现为他反复不断地致力于克服将感觉与表达感觉的行为分割开来的诱惑,但这要理解为有关与疼痛概念相关的那类技艺的语法论点,而不要理解为对我们关于他人处于疼痛中的确定性的哲学辩护。要是我们试图将它变为后者,那么,就像前面所看到的,结果会令人失望。”[2]215
确实,正如麦金所指出的,许多阐释者试图在现代知识论的理论框架下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标准的论述做出解读,但这些解读大都是引人误解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反对一切理论建构,所以,他关于心理学表达式的使用标准的考察并不能简单地同现代知识论对接起来。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对日常心理学语言游戏进行仔细的观察,以弄清相关表达式的用法,进而消除围绕它们而生的哲学困惑。我们的考察从语言实践入手,也在语言实践中收场。切不可跳出语言实践构造任何理论,无论是本体论的还是认识论的。
此外,维特根斯坦不仅自己不想通过关于心理学概念的具体考察来构建理论,而且也绝不希望后来人根据他所写下的评论构建任何心灵理论。在他看来,他心难题是个伪似问题,像所有貌似深刻的哲学问题一样,无法从正面予以解答。这么一来,基于现代认知科学成就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误解了这个难题本身。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去认知他人的心灵状态,因为完全不存在所假定的那种确定的状态。当我们总是试图弄清楚他心的内容,或者总是要求他人准确说出其内心想法时,分歧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上引人误解的假定,而企图通过构建某种理论来正面解决他心难题的努力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而正因为意识到了说谎、假装、表演等等都是人们逐步学会的、司空见惯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才力劝我们不要再纠结于如何才能弄懂他人的内心,免得徒增烦恼。
维特根斯坦极力反对一切理论建构,主张回到活生生的语言游戏当中。他要求我们彻底抛弃“他心在”和“他心知”的问题:“我们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于是我们所做的可能显得像唯名论。唯名论的错误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因此并不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而是仿佛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了一张纸面上的汇票。”[1]181维特根斯坦主张仔细考察语词的用法,而又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任何哲学诱惑,即便是唯名论这样一种反实在论的立场。一切都在观察语言中得以澄清,但语言是极其复杂的,不能指望对其功用做一般的概括。那样只会挂一漏万。我们要坚决抵制进行理论概括的强大诱惑,因为只有在语言的具体用法中才能看清概念的意思,才不至于误解它们,才不会想着找寻其本质:“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1]181“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1]178。
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学语言游戏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参与其中的语言游戏是有缺陷的:只要能够顺利地进行交流就好了。但我们总是倾向于假设确定地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而只能相信他人具有某种心灵状态。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这是对“知道”一词的误用:
在什么意义上我的感觉是私有的?——那是,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这在一种意义上是错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意义。如果我们依正常的用法使用“知道”这个词(否则我们又该怎么用!),那么我疼的时候别人经常知道。——不错,但还是不如我自己知道得那么确切!——一个人一般不能用“我知道我疼”这话来说他自己(除非在开玩笑之类)。——这话除了是说我有疼痛还会是说什么呢?
不能说别人仅只从我的行为举止中得知我的感觉,——因为我不能用得知自己的感觉这话说到我自己。我有这些感觉。
正确的是:说别人怀疑我是否疼痛,这话有意义;但不能这样说我自己。[1]136
其实,说别人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经验,这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经常知道我疼;第二,这样说也是没有意思的:说话者误用了“知道”“怀疑”“确定”这样一些日常的语词,企图赋予它们以认识论上的意义。可是,当我说“我有疼痛”或者“我有这个感觉”时,难道不是断定了它作为我所拥有的某种内在东西的实际存在吗?维特根斯坦指出,这是一种日常的言说方式,完全没有本体论的意义,我们不要被它所误导。所以,他不仅要消解“他心知”难题,还要消解“他心在”难题。这样的难题一旦提出来,就会把我们引入自我中心困境,难以自拔。我们接下来还会被引到这样的问题:如何从自心的存在过渡到他心的存在?如何从自心的知识过渡到他心的知识?维特根斯坦就是要通过劝导人们采纳语法研究的策略来摆脱传统的本体论和知识论的思考方式,进而避免陷入泥潭。他敏锐地看到,这些哲学迷惑源自于我们对语言的误用,而只有通过仔细考察语言的实际使用,才能拨开迷雾、看清真相。
五、 余论:维特根斯坦主张他心可被直接感知吗?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构建任何理论去解释关于他心的认知如何可能。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了解他人的心理活动,无法把握他人的真实想法。那么,他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赞同对他心的直接感知呢?他所说的标准难道不正是要用于判定这种直接感知吗?爱德华·威瑟斯彭(Edward Witherspoon)在《维特根斯坦论标准与他心难题》一文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标准概念突出了人的身体的表达能力。
我们遇见作为有心灵的存在物的他人,他们通过所说和所做的事情来表达自己,从而让我们得以知道他们的心灵。获取这种知识的知觉能力,像所有人类能力一样是可错的。有时,我们会误读他人的表达,而人们有时会谎报或掩饰他们的心灵状态。此乃人类关系的一个根本特征,而这绝不表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或者感觉到了什么。……维特根斯坦旨在从怀疑论的威胁中恢复人与人之间相互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开放是局部的、可错的,但又是真诚的。”[3]498国内学者王华平教授在《他心的直接感知理论》一文中指出:“在维特根斯坦描绘的新图景中,内心的并不是隐匿在深处的不可见者,相反,它就在行为表达之中。内心的与外部的这种密切关系让我们对它的直接感知成为可能。……在很多地方,维特根斯坦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他心是直接可以感知的。”[4]
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有依据的,值得重视。 维特根斯坦反复告诉我们, 日常心理学语词的用法都明摆在眼前了, 我们的考察只需如实地、 尽量详细地描述它们就行, 无需对其做任何理论解释, 因为没有什么对我们隐藏着, 需要去做深入的挖掘。 对于他心的了解, 完全不需要任何“读心术”: “‘我们看见了情感。’——相对于什么来说?——我们不是看某个人的面部变化, 而推出他感到快乐、 悲伤、 厌烦。 我们是直接地把他的面容描述为悲伤的、 喜气洋洋的、 厌烦的, 即使人们不能对面部特征作出另一种描述——人们可能说, 悲伤在面容中被拟人化了。 这对于我们称之为‘情感’的那种东西来说是本质的。”[5]420而且, 任何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的“读心术”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如果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 王华平教授的如下论断是可以商榷的: “直接感知是最基本的读心方式。”[4]人与人的交往并不是相互读对方的心, 甚至也不能说交往有赖于读心, 因为要这样说的话就假定了心灵的存在和可知性。
那些构造“读心术”理论的人不外乎是想给出关于心灵之谜的正面解答,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所谓的解答都是痴心妄想。当然,他并不会否认实验心理学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但那是两码事儿。此外,我们不能奢望科学的最新成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有关心灵的哲学谜团,或者,有朝一日单凭科学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他心难题。
延续千年的他心难题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难题。著名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康斯坦丁·桑蒂斯指出:“各色各样的阐释者们都一致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与下述想法水火不容:其他人的思想和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我们隐藏着的,而这会引出关于他心的严肃哲学难题。……维特根斯坦显然并不认为,需要对他人有一般的认知担忧。”[6]132这也就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他心难题是哲学家们的“语法虚构”,唯当回归心理学概念的日常用法,才能消灭这头怪物。我们无需费心琢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甲虫到底长啥样?既然我自己不是通过向内窥视而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的,所以,也就不劳烦他人这么做了。甚至可以说,要真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甲虫的话,那它也并没有藏在盒子里面,而是在盒子外面自由活动呢。因此,他的比喻里提到的甲虫,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存在。在日常语言游戏中,我们可以完全正常地使用“疼痛”“感知”“看见”“知道”等等词语。我们彼此心领神会,毫无芥蒂。那么,说“我们直接感知到他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不外乎是说,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即时地完成互动:我对游戏参与者的言行做出回应,而对方又对我的回应做出再回应。在这里,关于心灵的本体论和知识论难题全都消失不见了。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另一个人则回答说:“我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如果威瑟彭斯所言不虚,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是想指明并倡导人们彼此心灵之间的开放性。
事实上, 每个人的心灵都在某种意义上是透明的。 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他人面前表露着自己, 所以, 完全没有必要去试图窥视他人的内心,更不要去做勾心斗角的事情。 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猜忌、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大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 国与国之间的敌对, 都是由彼此之间的封闭所引起的。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要是每个人都做这样的透明人, 那该会是怎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当然,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为我们勾画出这样的理想蓝图。 他只是告诫人们, 不要企图通过构建理论来弄懂他人心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而是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以开放的心态彼此相待, 真诚而和平地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