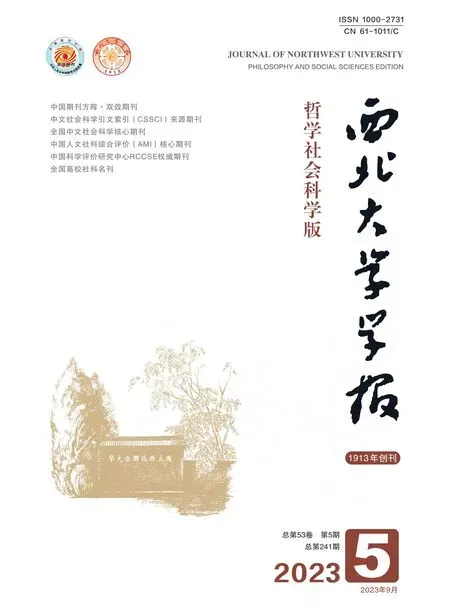维特根斯坦与反本质主义
楼 巍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1)
一、本质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交叉
提到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伴读》的作者哈勒特(Garth Hallett)在一本名为《本质主义: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批评》的书中说道:“宽泛理解的本质主义是西方思想的显著特征,我认为大体说来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1]3
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由来已久,当苏格拉底发挥其所有的才智来对抗智者学派那种张扬相对性和主观性的学说之时,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两个人的看法可以有相对性和主观性(我觉得是这样,你觉得是那样,一切都没问题,反正都是“觉得”),但表达他们观点的句子,更准确地说,构成这些句子的词语的定义,却不可能是相对和主观的,否则争论也是不可能的了。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们所说的东西有正确也有错误,但他们的语言是一致的。”[2]118
比如,《理想国》的开篇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心里,这个问题要求的是给出“正义”这个词或概念(暂且不管词语和概念的区别)的定义。但那时的苏格拉底并没有去反思一个额外的问题:那些他知道自己不知道,雅典的名人们以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并不知道的“定义”,真的存在吗?当然,如果撇开这个问题不管,那么给出比如“正义”一词的定义的最好方式当然就是给出“正义”的本质,给出那个贯穿一切“正义”(实际上是一切正义的情况)的共同之处,那个本质。
很明显,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就建基于此,所有可以被归入某个类概念(比如“美”)之下的个别物一定有一个共同之处,否则它们怎么可能都是美的呢?这个共同之处就是所有美的东西的本质,但这个本质一定不同于所有的个别物或者说所有具体的美的东西,否则它就是另一个个别物了,所以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高于这些个别物的理念世界中。
另外,如果我们想到任何一个个别物都不会只有一种性质,比如一个美的人不会只有“美”这个性质,而是可能还有“瘦”这一性质,我们就会觉得任何一个个别物其实是很多性质混合或者掺杂的产物,这些性质就是构成个别物的成分,“性质是拥有这些性质的事物的成分,比如美是所有美的事物的一种成分,就像酒精是啤酒和白酒的成分,于是我们可以有纯粹的美,它未与任何美的事物掺杂在一起”[3]21,这就是纯粹的美,即美的理念。
应该说,这两条道路,即本质学说和混合学说,都可以带我们走向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从理念学说中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思想:首先,个别物是次要的,具有更低的价值,“类”是主要的,理念或本质是主要的,具有更高的价值;其次,个别物之所以成其为个别物,恰恰是因为那个理念或本质。比如,一个个别的东西之所以是美的,恰恰是因为那个绝对的、纯粹的美或者美的理念。换言之就是:理念是个别物的基础。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公然地提出了这个看法:“在绝对的美以外的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分有了那个绝对的美,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4]203
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中,统治着西方哲学的,当然是对本质的抬高和追问,是对普遍性的渴望,其实就是对个别物的贬损,即“对具体例子的蔑视态度”[3]22。
作为“西方思想的显著特征”,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20世纪上半叶披上了一层语言哲学的外衣。维特根斯坦所处的,大致就是这种理智气氛。让我们先来引用一段罗斯(David Ross)的话:
理念论的本质就在于有意识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实体之集合的存在,这些实体可能最好被称为“共相”(universal),它们完全不同于可感的事物。任何对语言的使用都涉及对“这种实体存在”这一事实的认识,不管这认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因为每一个被使用的词语(除去专名),每一个抽象名词,每一个普遍名词,每一个形容词,每一个动词,每一个代词,每一个介词,都是某种东西的名称,这种东西总有或者总可能有一些实例。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亚里士多德,那么,当苏格拉底专注于寻找定义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迈向有意识地认识这个实体之集合的第一步,而询问一个普遍词的意义,就是从对这个词的使用本身走向认识构成实体之明确集合的共相的一步。[5]225
罗素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审查日常词语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致说来,专名代表着个别物,而其他的名词、形容词、介词和动词则代表着共相。”[6]93
前面出现的“任何对语言的使用”“每一个被使用的词语(除去专名)”“审查日常词语”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把关于本质的问题和关于语言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本质主义披上了语言哲学的外衣,本质变成了用来解释我们的语言能力的东西。
简单说来,这种解释是这样的:任何对语言的使用(准确地说是正确的使用)都应该预设这种作为本质的实体的存在,“任何对语言的使用都涉及对‘这种实体存在’这一事实的认识”,如果我们在某个个别物身上找到了这个实体(共相、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实体的名称(比如“美”这个词)来刻画这个个别物(比如“它很美”),如果找不到,那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因为用一个词来刻画某个个别物其实是一种语言活动,所以这个作为共相或本质的实体就成为了我们正确地使用某个词的根据。举“游戏”这个普遍词为例,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游戏必须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的性质就是将‘游戏’这个普遍词使用到各种游戏之上的理据”[3]21。
前面说了,说出可被归入某个词或某个概念之下的所有个别物的本质,其实就是给出了这个词或这个概念的定义,所以本质又和定义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这就又披上了一层语言哲学的外衣。
如果词语或概念有了一个精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原则上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将所有符合这个定义和不符合这个定义(关键是要有这个定义)的个别物区分开来了,于是原则上我们也就有了概念的“精确边界”。这个边界和定义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将世界上所有的个别物一分为二,一是符合定义的,在边界内的;一是不符合定义的,在边界之外的。正如学者奥斯洛(Osrow)在谈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哲学时所指出的:“弗雷格的著名主张是:一个恰当的、科学的概念是这样一个概念,关于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对象,这个概念都必须能够判断它是否落入这个概念之下。在这一意义上,一个没有‘精确边界’的概念被认为是完全无意义的。”[7]37顺便说一下,早期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的影响。
于是,这个明确定义和精确边界立刻成为了使用一个词的规则,因为说一个个别物“美”或者“不美”,说一个东西“是游戏”或者“不是游戏”,都是在使用“美”“游戏”这些词,而这些词的定义和边界立刻也就成为了判断一个东西美不美以及是不是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这样想: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精确的定义和边界,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地使用词语了,因为我们没有正确使用的标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精确的定义和边界,那么我们在使用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在使用“游戏”这个词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意谓的是什么了,“但若‘游戏’概念像这样没有界限,那么你真正说来就不知道你用‘游戏’一词意谓的是什么”[2]44。你说出一个词,比如“游戏”一词,并且用它来意谓一个东西,但如果你没有那个规则、标准来判断它是或者不是游戏,那你怎么知道你意谓的是什么呢?一个你既不能判断它是也不能判断它不是游戏的东西,你能知道它是什么吗?你会陷入一种原始的混沌。
但我们当然不承认自己无法正确地使用词语(我们都掌握了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也当然不承认自己在使用一个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意谓的是什么,因此,那个规则,那个定义和边界,因此那个本质,一定是存在的。
这些就是作为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的本质主义和语言哲学交叉的结果,也是维特根斯坦要处理的问题。
二、家族相似和反本质主义
回到前面说的那个被撇开的问题:那些苏格拉底知道自己不知道,雅典的名人们以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并不知道的“定义”,真的存在吗?
苏格拉底追问的是伦理学概念的定义,但我们还是以“游戏”这个日常概念为例吧。经过前一节的分析,其实这个关于定义是否存在的问题,就等于贯穿一切游戏的共同之处即游戏的本质是否存在的问题,就等于“游戏”这个概念有没有明确边界的问题,就等于人们是否按照严格的规则(即这个边界)使用“游戏”这个词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先从贯穿一切的共同之处开始,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
考察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的意思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等等。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就不会都叫‘游戏’了。”——而要看看所有这些是不是有某种共同之处?因为,如果你去看,你是看不到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的,但是你会看到相似性、亲缘关系,也就是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就像前面说过的:不要想,而要看!——比如,来看看棋类游戏,看看它们的形形色色的亲缘关系。现在转到牌类游戏:这里你会发现很多与第一类游戏相应的东西,但是很多共同点消失了,另一些共同点又出现了。如果现在我们转到球类游戏,那么很多共同点仍保留着,很多消失了。——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比较一下象棋和连珠棋。或者总有输赢?游戏者之间总有竞争?想想单人牌游戏吧。在球类游戏中有输赢,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球扔到墙壁上再接住,那么这个特点又消失了……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了一张由彼此交叉重叠的相似之处构成的复杂网络。那大大小小的相似性。[2]42
接下来就出现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我没法以一种比借助‘家族相似’一词更好的方式来刻画这些相似性了,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相似性也是如此的交叉重叠:身材、面部特征、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格,等等,等等。——我会说:‘游戏’形成了一个家族。”[2]43
这里顺便要打消两个与前面的讨论密切相关的误解。
第一个就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著名阐释者哈克(P. M. S. Hacker)对“综观式的表现”(Übersichtlichen Darstellung)这个概念的误解。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说过:“我们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我们没法综观我们的词语的用法……对我们来说,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有着根本性的意义。”[2]66
为了说清楚“综观式的表现”, 哈克在其《维特根斯坦:理解和意义》第一卷中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给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一封信。 信中维特根斯坦说他当时的哲学工作是“对语法, 即词语的语法性用法的罗列和综观式的表现”[8]327, 由此, 哈克主张“综观式的表现”就是对语法的罗列, 就好像把词语的语法做成一张列表。 但是, 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中根本找不到“罗列语法”的例子, 因此哈克无奈地说: “如果综观式的表现被视为对主要语法命题的罗列, 那么维特根斯坦确实很少实践他倡导的东西。”[8]332-333
哈克的理解是不对的,维特根斯坦想要对其进行综观式地表现(1)实际上这里的“Darstellung”最好译成“展示”或“展现”。的,并不是哈克所理解的词语的语法,而是词语的用法,而所谓的“表现”,也并不是“罗列”,而且维特根斯坦经常在著作中实践这种方法。前面提到的对各种游戏的展示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实践这种“有着根本性的意义”的方法,就是在对“游戏”一词的用法进行综观式的表现。
人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用法”,好像词语的典型用法就是《哲学研究》§2中提到的建筑师傅对工人喊“石板!”,然后工人把石板搬给他。“用法”这个概念要比这种简单的语言使用宽广得多。前面对各种游戏的展示,毫无疑问也是对被我们称为“游戏”的各种东西的展示,而这恰恰也是对“游戏”一词的各种不同的用法的表现或展示(2)这种例子其实很多,比如《哲学研究》第一部分§149和§150之间方框内的那段话,它是在对“理解”“心灵状态”这些词的用法进行综观式的表现。。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这里,这种表现有着十分积极的哲学意义。
第二个是某些研究者对“家族相似”的误解。有论者主张,为了解释我们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原来需要定义和本质,现在需要家族相似了,家族相似继续发挥着原先的本质的功能。比如,有论者就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将我们的概念使用到并未呈现出一组明确共同特征的例子中的,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些例子和另一个被我们视为该概念的实例的东西之间发现类似之处”[9]198,以及“对家族相似的诉诸能够解释我们的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将它们延展到新的例子中”[9]199。
但这也是一种误解,前面已经说过“不要想,而要看”,家族相似并不是一个理论(理论都是想出来的),而是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真实情况。只有理论才能被用来解释我们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看到的事实”是不行的,更何况“解释终有一个终点”[2]3。我觉得我们能够正确地使用词语这回事是无法解释的。而且解释难道不也是在使用语言,难道不也是在使用词语吗?这样的使用又该如何得到解释呢?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通过对游戏的综观式表现,已经让我们看清并不存在什么贯穿一切游戏的共同之处。既然这样,那么应该说游戏是没有本质的。体现在语言哲学上,这就意味着“游戏”这个概念是没有定义,也没法被定义的,它也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来使用这个词的。
这些结论无疑会招来各种反对意见,而且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无疑预见到了这些意见。比如,有人提出,如果“游戏”这个概念没有定义,那么我们该如何向别人解释“游戏”这个概念,如何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呢?如果有明确的定义,那么我们说出这个定义,也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但现在没有了定义,那该怎么办呢?
这里涉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回忆一下苏格拉底的“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如果“知道什么是正义”是给出这个概念的定义(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那么雅典的名人们最终确实给不出,或者发现自己的提议最终都不适合,但如果“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意思是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正确地判断某件事情或某个人是不是正义的,换言之就是能够正确地使用“正义”这个词,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雅典人都和苏格拉底一样“知道什么是正义”。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苏格拉底误解或者误导了雅典人。
维特根斯坦就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的(并且这样理解不会让人步入歧途),为了向另一个人解释什么是游戏:
我认为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并对这描述加以补充:“这个,以及与此类似的,都叫作‘游戏’。”我们自己知道得更多吗?是否我们只是不能准确告诉另一个人什么是一个游戏?——但这并非无知。我们不知道界限,是因为从未有过界限。[2]44
确实是这样,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并不是给出“游戏”一词的定义和边界,而是给出一些游戏的例子,描述一些“游戏”一词的用法,“什么是一个游戏,这一点恰恰也是这样来解释的。人们给出一些例子,希望它们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被人所理解”[2]45,仅此而已,这就是日常意义上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对“什么是游戏”的解释。
比如,还可能有人会提出:“但若‘游戏’概念像这样没有界限,那么你真正说来就不知道你用‘游戏’一词意谓的是什么。”[2]44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前面说了,如果游戏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你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东西是或者不是游戏,你怎么知道你说出“游戏”一词时意谓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个边界,你既不能判断它是游戏,也不能判断它不是游戏。
对此,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是一种带有实践或者现实意味的回应,因为前面说的这种困惑也只是在“想”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在实践中,在查看具体语言活动的时候,是不会产生的。换言之,这种困惑只有在做哲学的时候才会产生。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给出这样的描述:‘地面完全被植物覆盖了。’——你会说在我能够给出植物的定义之前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2]44是啊,我们自己在说出这个句子的时候会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当然不会。
对“概念没有明确边界”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打消了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如下看法:
只有当人们更清楚地把握了理解、意谓、思考等概念的时候,所有这些才会在正确的光照下出现。因为如下这一点也会在那时变得清楚起来:是什么能够引诱我们(而且已经引诱了我)认为说出一个句子并且意谓或理解这个句子的人是在按照确定的规则进行演算。[2]51
这里说的就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而且已经引诱了我”),那就是理解、意谓、思考一个句子是在按照确定的规则进行演算。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在早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世界的图画,命题是实在的图画,“命题是实在的一幅图画,因为,如果我理解它,那么我就知道它描绘的那个情况”[10]47。但命题和实在并不像,“孩子们在玩游戏”这个“命题”和现实中一群孩子在玩游戏这个“现实场景”并不相像,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一个命题就知道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呢?答案是:理解。理解可被比作将命题(命题由符号构成)翻译成可能场景的过程。同样道理,说出一句话并且意谓一句话,我们似乎就把可能的现实场景装进了一句话。意谓可被比作将可能的场景翻译成符号的过程。而理解和意谓,都是一种思维活动,或者说都是思考。早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明确提出了这一点:“我们用命题的可被感官感知的符号(声音或者书写符号)作为可能事态的投影。投影的方法是思考命题的意义。”[10]36在这段话中,难以理解的“投影的方法是思考命题的意义”这句话,它说的其实是我们借助“意谓”和“理解”这些思维活动来实现符号和可能发生的现实场景之间的互译。这种互译有时也被比作一种演算。
“互译”是需要规则的,这规则就是前面说的概念的边界。我们可能会认为,正是那种本质,那种定义,以及因其而来的那种边界,使得世界中的东西和词语(符号)的正确对应成为了可能,使二者形成了一种无缝的、不会搞错的联结,也使得那种所谓的“翻译”成为了可能。
随着本质的消散,定义和边界也消散了,而这种所谓的“翻译”也就失去了其根基。这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看法的一种颠覆。
三、反本质主义的其他运用
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除了体现在反对词语使用的严格规则上,还体现在更广阔的语言使用方面,比如还体现在反对将心理表达式的意义简单地还原成一个“本质”上。让我们举《蓝皮书和棕皮书》中的“根据记忆作比较”这个表达式为例。
有这样一种语言游戏,那就是一个人先给另一个人展示一块布料,然后让这个人去拿一块比这个布料颜色更深的布料。假设有两个人,A和B,在玩这样的一个语言游戏。A给B展示一匹布料,B接下来要根据记忆去拿一匹比前面那块布料颜色更深的布料。这时可能会发生如下这三种情况:
(1)当B去拿布料的时候,他心眼之前有一个记忆图像。他轮番看着布料并回想他那个图像。他在其中五匹布料上做了这件事,在一些情况下对自己说“太深了”,在另一些情况下对自己说“太浅了”。到第五匹布料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说“就是这个”,并且将其从架子上拿了下来。
(2)B心里没有任何记忆图像。他看了四匹布料,每次都摇头,心里有点紧张。看到第五匹布料的时候,这种紧张感消失了,他点了点头,将布料拿了下来。
(3)B没有任何记忆图像,他走到架子边上,依次看了看那五匹布料,将第五匹从架子上拿了下来。[3]94-95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 我们都会说B“根据记忆作了比较, 并选出了一匹布料”, “根据记忆作比较”这个表达式在这些情况下的使用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倾向于说这些描述遗漏了这种活动的本质特征, 而只给了我们一些附属特征。 这本质特征似乎是某种人们可以称其为比较和识别的特定经验的东西”[3]95。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作祟,我们总觉得在这三个“根据记忆作比较”的例子中(实际上在所有“根据记忆作比较”的例子中),一定有唯一的一个本质,即那个真正发生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根据记忆作比较”,而前面的描述,特别是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似乎没有真正刻画出那个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个作为本质的“根据记忆作比较”。如果继续想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根据记忆作比较”肯定是这样一件发生在我们心灵领域的事情:我们心里浮现出一个记忆图像,原来那匹布料的意象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逐一将眼前看到的布料与这个记忆图像作比较,然后找出一匹其颜色比意象图画中的布料颜色更深的布料。
这样说貌似完全问题,而且我们在做哲学的时候也一定会这样想,直到我们问自己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怎么知道我心里浮现的意象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匹布的意象呢?其次,我们怎么知道眼前看到的某一匹布料的颜色比我们心里浮现出的那匹布料的颜色更深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标准,我们根本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既然这样,既然没有标准,那么我们根本无法“根据记忆作比较”,根本无法选择出正确的布料?这肯定也是不对的,这就像是说我们根本不能玩刚才说到的那个根据记忆来选择一匹布料的语言游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语言游戏。
其实,不仅是根据记忆来选择一匹比样本颜色更深的布料,即使是根据记忆选择一匹与样本颜色一样的布料的语言游戏,也同样会遇到刚才提到的问题。比如,我们怎么知道眼前看到的一匹布料与我们心里浮现出的布料的颜色是一样的呢?这时,也就是在做哲学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说我们“有某种无法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样本和选出的布料之间作出区分的特殊感觉”[3]96。这种哲学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就像经验主义者那样诉诸某种感觉,并且认为这样就解决了刚才那个“怎么知道”的问题,是这种经验将心里浮现出一匹布料的经验和眼前看到一匹布料的经验联系在了一起。但是,问题还是继续,即使我们有了一种“无法区分”的经验,那又是什么经验将这种经验和这里提到的另外两种经验联系在一起呢?在前面提到的第二个例子中,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说那种“紧张感的消失”是B选出了那匹正确的布料(即比前面给他展示的那一匹布料颜色更深的布料)的标准,但谁又能表明这种紧张感的消失就是B在选出那匹正确的布料时的“那种”特定的“紧张感的消失”呢?B是否需要另外一个标准来告诉他这种“紧张感的消失”才是他想要的那种“紧张感的消失”?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这些分析有点荒唐,这恰恰是因为我们脱离了日常的情境或者说环境,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想”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B完全可以做到A要求他做到的事情。但是,很明显,让我们走向这条歧路的,恰恰就是那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考方式让我们觉得“根据记忆作比较”就是两种东西(先不管这东西是什么)的一致,一种是心里浮现的东西,一种眼前看到的东西。但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前面说的那三种情况都可以被称为“根据记忆作比较”。
而且,我们可以回忆起更多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根据记忆作比较”,慢慢地,就像维特根斯坦对游戏进行综观式的表现中那样,我们也会发现“根据记忆作比较”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家族,所有这些家族的成员都可以被称为是“根据记忆作比较”,而所有这些成员之间并没有一个本质贯穿于它们,“我们发现将所有这些比较的例子联系在一起的是大量相互重叠的相似性,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觉得自己被强迫去说必须有一个为所有例子所共有的特征。将船和码头系在一起的是一根绳索,这根绳索由纤维构成,但它并不从任何贯穿整根绳索的纤维,而是从大量彼此重叠的纤维这一事实那里获得其强度的”[3]96。
以这样的方式,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把反本质主义使用到概念词和个别物的关系上,还使用到了更多的心理学表达式和具体情境的关系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呈现出了一种更广阔、更丰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