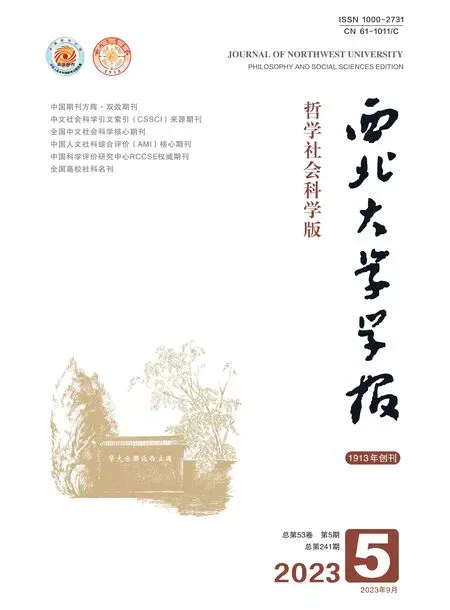共在与认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性及其功能
高小燕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追求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有质量的生活,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拥有5 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承载着人类文化意象和社会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厘清并发挥价值,提升与公众的联结,伴随人类的精神文明迈步进入新的时空。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在历史、艺术、科学、美学、民族学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和遗址。文物、遗址、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以及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的整体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也生长着作为人类想象的共同体或者说人类文化意象和记忆中的文化遗产本身。强调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传承,不仅仅可以提升和实现当代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更可以提升民众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和“溯本寻根”。
文化的传播和分享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或者载体来展开,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凝结和产物,是传播和传承文化的载体。以文化遗产地为保护和传承对象而建立的博物馆、遗址公园发韧于人类社会对文化遗存的珍视,是集文物收藏、科研、宣传教育为一体的重要社会公共文化组织,随其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展,文化遗产地在文化传播和沟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而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网络等新媒介出现之后,对传播意义的理解,越来越依赖跨空间的远距离信息传播,而空间位置在人们不确定的日常生活中所建构的人际关系及意义,几乎被排除在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之外[2]。但是物质空间给人类带来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由物质文化遗产建构起来的实体空间、物理空间以及蕴含的意义空间。基特勒(Kittler)批评2500年以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完全忽视了其自身的技术媒介”,倡导建立“媒介本体论”,从“硬件”的“物”出发,以“物”的储存、处理与传输为轴心,重构整个文化史[3]249-254。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特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属性,蕴含丰富表征和意义的空间属性,需要学术界在跨学科领域以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对其媒介属性和功能展开深入研究。
一、研究述评
(一)媒介物质性研究
传播学领域早期就有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对话媒介“物质性”,包括伊尼斯(lnnis)、麦克卢汉(McLuhan)、德布雷(Debray)、本雅明(Benjamin)等学者在物质的基础上展开了媒介的研究[4]。其中,德布雷提出“媒介域”概念,并指出媒介传播的技术和制度配置与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系统的发展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媒介技术革新不是以消弭过去的物质形式,而是改变其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功能和作用[5]。媒介不仅是作为技术的工具,起到中介的作用,还是其与社会、与人之间建构的关系和作用,通过物质载体的意义阐释,以多元符号的形式来表征和传递,建构具有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意义之网才是媒介的属性和价值[6]165,媒介的物质性逐渐在记忆研究中得到凸显。十多年来,媒介研究开始偏向“物质性”研究,其中国内学者胡翼青、周海燕、侯东阳、刘海龙、袁艳等学者媒介物质性的基础概念、理论渊源、方法论图景等领域展开讨论。在传播研究领域引入物质性打破传统重文本轻介质、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范式,物质性研究强调技术物如何介入旧关系,创造新关系[7]。媒介考古学强调梳理回顾旧的历史,深度发掘从物质性中提炼媒介的历史形态变迁和发展中的社会意义,达成旧与新的对话[8]。媒介既是连接人与社会互动与交往的物质节点,也是阐释人类与社会之间能动关系的驱动机制和系统,回归媒介的物质性探索,不是探究孤立和僵化的物,而是发现在社会建构和变迁的过程中物呈现的“本体化事件”的展演[9],是物与非物的联结和意义生成,即“共在”。而“共在”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存在与联系的方式,是关系视角上的社会行动,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本身[10]。
(二)媒介化与再媒介化研究
“媒介化”研究强调媒介作为中介和塑造力量的能力,如何改变人们互动、交流和构建意义的方式,并对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深入的理解。“再媒介化”作为媒介化的进一步发展,关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挑战和影响。延森(Jensen)提出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即媒介参与实践和社会建构,是推动社会运动的技术体系;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认为媒介化与媒介引起的社会变革有着紧密关系,媒介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提升传播的能力和范围,可以有效搭建社会事务开展和实施平台,从而媒介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匹配、相互作用,成为社会事务的有机构成部分[11]。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传统角色在不同时空中发生变化,并参与到流动的社会发展和建构中,与不同时期的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科技等方面接触和融合,将媒介逻辑和规则运作与文化、社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匹配的过程。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强调人类可以通过搭建媒介的历史叙事来理解不同时代的媒介发展与变革[12]。 旧媒介在新时代具有“再媒介化”发展趋势。 再媒介化是指在媒介化过程中, 由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推动, 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发生变化, 进一步影响着媒体内容的产生、 分发和接受的现象。 再媒介化研究关注媒体对信息的创造、加工和传播进行再调整的过程。 它强调了媒体作为媒介的动态性和互动性, 并探究了新兴技术带来的再媒介化趋势与现有传媒模式之间的关系。 “媒介化”与“再媒介化”研究跳出媒介价值是其物质性、 技术性和社会使用性的传统研究, 更应该研究人与媒介的共在关系, 从媒介本身出发了解自然和社会环境, 及其在所处时空中的价值、 文化的架构。
媒介化与再媒介化都离不开媒介的功能性讨论。拉斯维尔(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施拉姆(Schramm)等学者指出,大众传播具有监测社会环境的功能,并且推动社会组成部分相互联动,建立关系,适应环境发展,将社会遗产传承下去[13]152-154。德布雷认为媒介实际上是一个“功能位置”或“中间环节”,一个可以推动并改变传受关系的中介环节[14]125。媒介是联结社会不同节点的中间节点、界面、尺度,也是一种改变形态结构发展和关系的发展力量[15]。社会中的任何沟通都需要通过媒介来实现,而信息量的不断增加,增加了媒介数量和技术变化,还由于其传播和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使媒介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力量。伊尼斯从宏观角度理解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指出媒介是传播和储存人类文明的知识形式和技术手段的系统化整合,社会、组织和人群以及之间的关系发展与变化,都深刻地受媒介的影响[16]28。麦克卢汉从微观层面指出媒介效应演化的机制,认为媒介对人体功能的技术延伸导致分裂感和感觉之间的比例变化,在文化中不断地产生不平衡和新的发展趋势,从而产生对社会存在、发展路径的冲击和创新。媒介是人类社会互动和发展的特殊产物,无论是个人、团体、社会,还是国家都是在关系的连接和活动中又产生关系。媒介与媒介化是互动的结果,是人类变自然环境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从而产生、创造了社会运行机制规则、社会治理体系、思想观念、文化规则与规范等社会化的事物和意义。再媒介化研究将进一步发掘媒介的功能,不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也是人类对自身、环境的探索和“认同”。“认同”是心理学中人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走向社会后提出关于“自我身份”的认知问题,包括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
(三)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性研究
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城市通过其物质储存设施(建筑、拱顶、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等)继承城市的文化并且传递给后代[17]580。德布雷以“纪念物为先”分析人类社会和文化传承是蕴含“物质的思想化”和“思想的物质化”的中介过程;指出传承首先必须有传播,而传播是编织文化遗产与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在文明“传递”脉络中理解媒介[14]5,24-31。近年来,在媒介物质化和再媒介化的研究转向中有少许国内研究者将目光关注到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以文物、遗址、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从媒介传播的研究路径展开研究,为未来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借鉴。其中,潘常辉从媒介域和媒介功能角度分析殷周青铜器的文化与政治传播[18]。陈霖分析苏州博物馆新馆作为城市传播的媒介空间,通过引入叙事理论,开启叙事建构,促成参与互动实践,促成了既具有意识形态规制又具有城市认同意义提炼的阈限性体验[19]。高小燕、段清波从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可沟通性展开研究,指出媒介学视域下文化遗产的关注点在于传承,可以从媒介的角度去发现和探索人类经历彼此交往而在思想、信仰、观念上对某一类价值形成认同与共享[20]。王夏歌、林迅从媒介角度出发可发掘和确定文化遗产媒介身份,是从媒介维度重新认识其功能的重要途径[21]。董为民以南宋皇城遗址为研究对象,依托媒介地理学,探索地域文化的认同与建构[22]。冯剑从中国都城规制入手梳理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的发展变化,体现为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城市形制,单一宫城、三城制、坐北向南朝向的形制特点,分析都城规制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媒介,将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合法性等宣示于天下,在都城规制的互动传播过程中,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23]。
综上,在媒介传播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在媒介研究新的转向中对物质文化遗产展开讨论和研究较少,亟须在新学术视野下展开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性和媒介功能研究,来拓展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合作,深化理论研究,丰富实践路径。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多元文化价值、现代工艺的高速发展以及电子阅读时代到来的冲击,亟需重塑其价值和功能,不能让彰显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文物、古建筑、遗址等文化遗产被人们遗忘。本文将从传播学视域下重新审视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从“物”出发,探寻其作为联结人与物的媒介属性和再媒介化,探讨其作为传播和文化记忆的媒介所发挥的不可遗忘的重要功能,探索其在目前社会中的“在场感”或者“在场效应”,期待在未来寻找适合其发展的回归或升华之路。最终立足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厘清中华文明亘古不断的原因和规律,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共享。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性与再媒介化
(一)作为媒介的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媒介属性从媒介自身含义展开探讨,媒介的构成须有以下要素:实体、符号、信息和意义[24]。本文将以此来分析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属性。
第一,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实体性”。文化遗产具有实体性。媒介是具有一定物理特征的客观实体,当脱离了外在实体时,信息是没有依赖介质进行传播的。媒介不是一种精神意识或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可测量、有形的东西。无论是单个的文物还是由文物组成的群体、古建筑群体、或者更大范围的物质文化遗产遗址、区域等都是具有实体特质的,是一种由社会和历史共同构建的物质空间,是由物质的载体构成,是彰显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体场所。
第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符号化”。首先,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存在和符号,背后蕴含着丰富的表征意义。象征物是人类行为的特征,包含人类的知识、经验和信念[25]16。秦始皇帝陵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也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象征性媒介,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秦始皇帝陵是秦统治思想及秦帝国政治制度的象征。秦始皇一生统治着他统一的“天下”,他的陵墓也试图重构统一的“天下”,陵墓的内部结构和礼仪建制都折射了秦始皇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建构的“大一统”帝王秩序。陵墓礼仪结构的内部秩序,反映了他在现实中努力创造的帝王秩序。陵墓的内外墙、门阙、道路等形制,都反映了有秩序的统治理念,从陵墓的礼制建筑、空间格局、结构布局反映秦始皇开创的“白帝”管理体系,以皇帝为中心的秦帝国“天下为一统”的价值内核[26]224-238。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实体空间符号,物质文化遗产由多种符号系统构成,建构多元化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不同的符号体系在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传承中起着不尽相同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代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使用价值中慢慢消解,隐性的文化价值外显出来的时代,更需要传播与媒介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原有的物质存在表达出的文化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下与人类的关系。符号本质是文化的,符号也继承了文化,成为自身固有的属性,使符号能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当意义不在场的时候,需要建构符号,让符号表征和传递意义[27]。文化遗产和符号一样都是文化的,而且文化遗产也是一种符号,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符号形式统一为一体的符号,既是物质存在的对象,又是蕴含意义的特殊符号。作为承载文化的物质实体和符号,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象。
第三,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信息性和意义”。媒介是信息、信息形式和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意义空间,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隐喻,反映了一切人的意义和价值[28]。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信息,不仅是人类祖先存在过的证据,更是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在这个意义之网中,体现人类社会的社会秩序、制度、价值观,甚至文明的发展与变迁。文化遗产核心组成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即文化精神的构成,文化遗产里隐含着不同时空下的精神文明,文化精神层面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价值观又是文化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社会中层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机制的架构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助推作用,也观照着物质客观实在的存在表征和特点。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就是要让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下去,让人类深入到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层面,在可沟通的对话基础上产生文化意象。中国古代多用石碑石刻来记录古人的行为、生活和社会状态。古人认为物化的石头是可以永久保存的,通过石刻的传播,可以将艺术、美德、思想等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延伸和承续。所以到了今天,习俗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人们依然凭借碑刻等方式来传达和传递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29]。古代人类的生死观突出表现在陵墓中,影响现代人的生死观。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新的统一的天下。新的社会制度建立,需要传播于天下共知,而且需要得到共识和支持,而适合人们价值理念追求的宇宙观、天下观,被应用到新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而这在秦始皇陵墓中得到了验证,帝陵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始皇和其团队的精神、制度、理念的综合思想体系[30]。秦始皇创建的秦帝国,正是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即古代社会由王国文明发展为帝国文明的转型时期,社会血缘、宗族等架构下的礼的价值观,需要被新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代替,来满足新的社会发展特点和需求。
物质文化遗产一旦进入传播过程,就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存在,有作为媒介自身的内在特征和价值,并对社会产生潜濡默化或强大有力的影响。近年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提到了“能动性理论”,要清楚地阐释和验证人类的能动性,需溯源人类的能动性在过去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空间中的表现和意义;文物、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实体物质本身是连接人与社会互动与交往的物质节点,如果没有价值和意义认同的基础,人们与文化遗产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就会被剥夺,导致人们无法在物质空间里产生精神世界里的文化认知和意象,从而无力唤起公众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思想和行动的驱动力[31]4-7。文化遗产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发展、互动关系的体现和产物,作为意义阐释和展示的媒介“桥梁”,可传递其隐喻的“人、物、社会”的关系和意义。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媒介化”
作为媒介,物质文化遗产正经历“再媒介化”,带来物质文化遗产媒介属性和意义的变化。
首先,新媒介的“虚拟性”和“移动性”改变了传播地点的“固定性”,改变了传播逻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可移动的新媒介出现和应用到现实传播环境之中,电子媒介、手机媒介等新的传播媒介通过二进制编码的符号系统输入输出信息,数字符号系统越来越成为传播的主流,原有固定地点的传播场所被可移动的空间所替代,传播的屏障被慢慢取消,新的媒介环境建立起来,这意味着人类讯息的编码都将走上二进制编码,实现麦克卢汉的“没有围墙”的地球村的预言。数字传播时代,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和展示不再受时空限制,尤其是空间场所的局限,公众不仅可以欣赏千里万里之外的文物遗产、遗迹建筑,还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等新媒介展开各种类型的交流活动和互动行为。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传播的媒介,文物、遗址、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时间和空间中客观实物和叙事逻辑的多元结合,而且是可利用其他媒体来进行移动式阐释和展示的场所,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实现实时互动、全新参与,利用其他媒介和自身结合营造历史和现代语境的融合,提高观众沟通与参与。嵌入于传统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遗产不仅作为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存在,而且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建构,建构了新的传播生态、媒介情境和交互逻辑。
其次,作为媒介的物质文化遗产, 面临“交互性”“参与性”的挑战, 文化遗产与人的“共在”关系推动物质文化遗产“再媒介化”, 再媒介化为信息传播带来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特点改变了博物馆内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 由最初以文物实体为中介搭建的向传递文物信息的传播模式, 转向了以媒介为桥梁的传播模式。 虚拟现实为静置的文物、 遗址、 古建筑带来了新的价值传播手段, 也带来人们对文化遗产自身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和反思。 在新媒体网络传播时代, 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遗产传播, 是多端点网状信息传递与分享的结构, 突破传受双方身份、 距离和渠道的界限, 提升受众多元互动参与范畴和程度, 提升文化遗产的价值意象和社会记忆, 激发公众对身份、 民族以及国家的认同感。
最后,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和想象性,改变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媒介属性,不再是默默静置在广阔大地上文物、遗址或是博物馆。一方面,虚拟现实改变了博物馆的景观叙事模式,开始了一种视觉叙事的全新体验模式;另一方面,公众也在思考进入一个被“技术信息”充溢着的物质场所,身体的“全息”体验,成为移动网络时代核心空间叙事方式,而每一个进入者,则成为该空间的叙事主体[32]。公众通过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媒介化”来体会自身与空间的联结意义,去思考“我为什么来这儿”。虚拟现实技术为文化遗产搭建的共在空间,让进入的观众感受到了超越现实的“真实”感、沉浸感。
三、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功能
当人类凝视文化遗产时,物质文化遗产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回望人类,将自己的发展再次投射在人类的思想、精神以及现实世界中。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建构了实体的物质关系,也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存在的“共在”关系,起到联结的媒介价值与功能。文物、遗址、纪念物、博物馆等实体,本身是联结人与社会沟通交流的实体节点,能够激发人类身份建构和意义“认同”。那么,当我们以“共在”和“认同”的视域下审视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功能与传播价值时,作为“媒介”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领域有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它不仅仅是物的媒介,而且还是人类与世界沟通的“媒介化”实践,即从实体性、象征性、时空性等角度揭示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不仅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媒介技术和信息传递,更是意义的交流、共享和社会参与[33]。从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传承的价值及历史传承关系来看,对文化遗产媒介功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互动沟通,产生文化意象,激发认同,推动社会建构与实践等方面。
(一)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共在性”:信息沟通与文明交往
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现代人与古代人信息交流的媒介。过去与传统通过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编码,再通过后人的信息解码来看到过去的社会。从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物、遗址上,总能找到古人生活的印记,产生对古代社会的想象空间,循着各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到长时段、大空间的文化交流与变迁。
第一, 物质文化遗产自出现以降, 就承担着信息沟通的角色。 最早是传播真实信息,发展到象征物的仪式,形成了早期的符物系统[4]20-23。我国古代早时期的青铜器, 曾经是上古三代最重要的祭祀器皿, 不仅用于与神交流,还用于纪念成就和向后人展示,也可以在记录历史事件、 法律文件和签订协约等方面发挥作用。 张光直先生指出,青铜礼器是用于礼仪祭祀的器具, 是古代萨满在与祖先或者神灵对话沟通的媒介[34]9-10, 古代诸侯国和朝廷的联系介质。 “公牍、 委任、 褒扬、 廷告等”被书之于竹帛, 琢之盘盂, 从而被长长久久的记录和保存[35]7。 秦人凭借制作秦公镩和秦公簋, 铭记、 传播和歌颂祖业功绩, 并指出统领天下是受之于天命, 显示和宣扬了统治天下和领土扩张的正当性。 在中国铁器兴盛之前, 青铜器是我国早期社会多元复合媒介, 承担政治、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信息沟通与传播, 形成该时代的“媒介阈”[18]。
第二,文化遗产不仅承担信息沟通的角色,更是文化交流、文明交往的媒介。一方面,博物馆里很多文物留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历史遗迹中也渗透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意象和痕迹;另一方面,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文化认同功能也表现在文明的交往之中。文物见证了中华文明历经历史长河的历练,没有被割裂、被覆盖或者被孤立,原因是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及对文化的深刻认同,才造就了现有的文明的发展、平衡的发展[36]8-15。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简单的客观实在,是人类文化价值和精神理念的载体外化,是传递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媒介。物质文化遗产照应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了创造者与传播者思想观念的传递,体现不同人群之间的精神往来和文明互动,成为验证人类精神财富、文明发展的证据。
(二)“共在”激发文化意象,“认同”建构文化记忆
首先,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不同时代的文化习俗和价值。我国古代早期多用甲骨来传递和记录信息,考古发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两万五千多片甲骨刻辞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载体材质,可以再现和复原殷商社会。由于甲骨类的物质媒介体积小,导致信息容量受到限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和文化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青铜器成为最主要的信息载体之一。虽然青铜器坚固不易被毁坏,但制造起来既费时又费力,到了秦朝,为了促进生产并确保战争胜利,秦国用石刻代替了青铜器铭文。石器也是承载材质之一,在西汉中期,人们开始在石器载体上,运用视觉图像语言记录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各种记录历史的画像石[26]。这样带有视觉元素的物化载体,更加鲜活地展现了过去的历史,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实体空间符号,物质文化遗产由多种符号系统构成,建构多元化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不同的符号体系在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传承中起着不尽相同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代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使用价值中慢慢消解,隐性的文化价值外显出来的时代,更需要传播与媒介发挥作用,即原有物质存在表达的文化价值和与人的关系。
其次,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再现和文化记忆。文化传承可以通过物化载体来产生文化记忆,使得文化再现。当外在物化载体被破坏或是消失的时候,文化记忆是否会被割裂?唐大明宫是唐代文化、社会、政治的文化再现和意象表征,随时间和社会变迁,其本体外在表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造前的大明宫遗址群所在地呈现文化记忆支离破碎、文化空间被破坏和割裂的状态。保护遗址需要思考改造之后的遗址群要让人们产生凸显核心价值的文化意象,让遗址有活力和生机,而不是“墙里”“墙外”割裂文化空间的“死”文化[37]。作为媒介的文化遗产,不是彻底消亡的“文化客体”,以某一种变体进入另一种文化客体中,在现代环境中借助另一种变化的媒体技术来“复活”或“逆转”,以多重符号给人带来延伸,从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再现社会记忆,形成文化认同。
再次,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文化空间的变迁。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空间的变迁。古代都城遗址是人类历史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体现出来的文化空间也是人类精神的空间映射。在研究城市与乡村文化发展与流动时,离不开文化遗产所构建的文化空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发展,许多城市快速建设,被湮没了原有的文化气息和本质属性,出现“城市文脉”或城市文化空间失落现象。面临此景,解决之道为重塑历史格局,延续城市文脉,让文化遗产承担起它曾有的媒介功能,重塑和构建文化空间,从而唤醒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表征实体,“再媒介化”的发展,既能为公众提供真实的文化空间,又能提供“虚拟现实”文化空间,在由物质文化遗产搭建的空间里,来观察中国的文明史、兴衰史、事件史、人物史,来教育启迪人生,梳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38]21。历代都城文化发展、帝王的陵墓制度变迁、礼制文化发展传承、社会运转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发展,都体现在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实在以及精神内涵之中,几千年来持续沿袭和传承下来的文明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发展节点,是对身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信仰的认同,对中国文明的认同[39]。
最后,通过“共在”文化变迁,“认同”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记忆。作为联结公众文化意象和社会记忆的媒介,文化遗产记录着历史社会变迁、人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以及思想的变革,反映了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后人通过物质的媒介勾连理解古人的社会、思想和制度,成为后人享用或传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文化遗产的价值“共在”阐释与传播中,公众可以感受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传承文化价值。新媒体时代的“再媒介化”拓展了文化记忆的传播介质,为文化记忆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涵义。数字传播时代,静置在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和遗迹可以通过多元媒介传播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文化记忆的多形式、多平台、多样化地交流,建构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的文化记忆,催生文化和身份认同。
(三)“共在”与“在场”:推动社会建构与实践产生
“媒介化”是将媒介逻辑、规则运作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匹配的过程,而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媒介,它是一个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不断地相互匹配和完善。秦始皇在推行政令时,竹简成为传达政意、制度推行的媒介;碑刻成为歌功颂德、传扬美名的媒介;陵墓设计和建造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写照……随时代发展,媒介在时空中流转与变化,联结公众参与到社会建构和共同行动中。遗产地或历史博物馆,通过媒介的叙事空间搭建,在参与互动中将意义扩散到更广的空间中,社会再一次被形塑。文化遗产具有公共属性,为现代与过去、历史与现实构架了人们可以相聚在一起回顾历史、体会历史的公共空间;也为公众建构了共同讨论文化、社会、经济等现实问题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需要调动公众的参与性,与公众多元互动交流,因为通过多元主体和多种方式的讨论和商榷,可以避免或者解决意见不同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建立和保持身份、价值和文化的认同。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在场”功能,具有守望社会、监察社会的功能,并且推动社会实践的产生。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多元文化社会的理想形式是在建立自由文化和资源联合的根本基础之上而构建起完善的交流系统和运作顺畅良好的公共领域,实现主体平等的民主化发展路径的同时,也能保证不同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发展[40]。文化遗产作为哈贝马斯预设的“公共领域”来思考,在这样开放性与多元化的公共领域里,文化遗产可以提升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大家可以平等地在这片“公共领域”共存,监督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等保护和传承政策与措施。物质文化遗产随时间的洗礼,具有媒介守望监察社会的功能,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
四、结 语
媒介是文化意象产生和传递的载体、介质。媒介是信息传递的方式和工具,还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交往、文化乃至文明发展的再现。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总是与特定的媒介技术、媒介感知和媒介时空紧密联结在一起,其发展“连续”或“断裂”,不是存在于历史本身,而存在于对历史的建构中。由原有规则和体系建构起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联结人与社会、历史与今天的媒介,在数字化传播时代,如何延续和复活价值成为我们探讨的下一个议题。通过深挖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见证和传播载体——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我们期待:在数字传播时代,作为媒介的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复活需提升其附加价值和意义空间,将“物”的客观实在和虚拟的网络时空结合,将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激发出来,发挥数字化创造潜能,焕发文化遗产的作用。第一,立足文化遗产价值,提升作为媒介的再媒介化价值和意义,从时空的维度来发掘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还原遗产自身所含有的价值信息;与现实紧密结合,面向受众的阐释和展示价值,穿越厚重的历史遮蔽与意义隐藏而促进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的多元交流与沟通。第二,借鉴新媒体的功能,在情境叙事、参与空间、互动沟通、虚拟现实、即时交流、分众传播等新的阐释和传播态势中利用互动、虚拟、合成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将使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播更加吸引人、更加生动,有机双向地整合二者的关系,使文化遗产的内涵成为流动性、传播性、生长性的价值本身和载体。第三,物质文化遗产为人类思想的表达以及感情的抒发提供了一个新的位置和定位,过去传统的单向叙事方法和媒介的语言系统将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和需要,需要建构媒介新的符号系统和传播系统。第四,在互动传播中让用户成为文化传播的创造者与参与者,搭建可参与平台和公共空间,吸引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公共事务。
总之,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以价值为基础将文化遗产与人类联系起来,搭建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和机制,引发公众的注意、尊重、启发、共鸣和感动,使得文化价值在时空中不断地编码和解码,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复活”和“逆转”,将精神的认知和认同转化为社会的行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襄盛事。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挖掘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推动文化繁荣,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