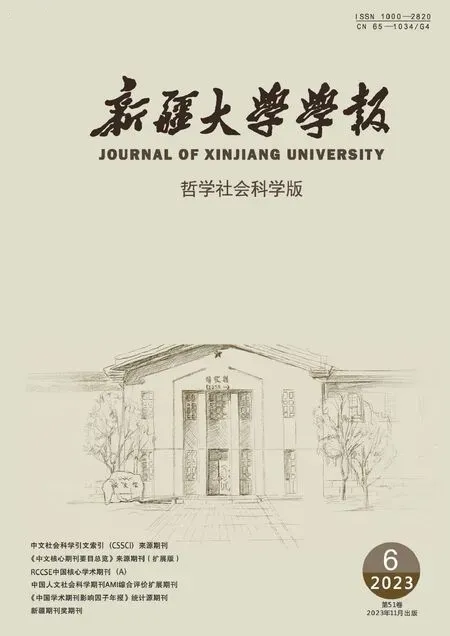清代南北疆通道穆素尔达坂路的开辟和利用*
坚 强,王金玉
(1.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2.吉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吉林 四平 136000)
乾隆二十四年(1759),跨越康雍乾三朝,历时七十多年底定准噶尔及“回部”的战争最终尘埃落定,新疆自此进入了近六十年的政治社会平稳状态。邻近新疆的哈萨克、浩罕、安集延、巴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等部纷纷向清政府遣使入贡,臣服于中国。
清政府在伊犁设立将军府统辖南北疆后,针对南疆“回部”取消了伯克的世袭制,将伯克转变为地方行政官员,为朝廷服务。并派官员驻扎“回部”各城,领八旗兵丁及绿营兵镇守。清政府底定南北疆后,首要任务为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初建伊犁时,大兴土木、经营农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均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这使得南北疆的人员、物资流动日渐频繁,而疏通因战事被破坏和暂停使用的南北疆通道穆素尔达坂路,便提上日程。
乾隆二十五年(1760),伊犁将军阿桂奏请“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子①即清代维吾尔人众。正文中以“回众”来表述。三百名,越穆苏尔达巴罕②即穆素尔达坂路,清代自乌什至伊犁的南北山路通道。至伊犁镇守办事。搜捕玛哈沁,招抚溃散之厄鲁特,即以绿营兵筑城,回子乘时兴屯,开渠灌溉”[1]87。这是清政府官兵底定“回疆”后进驻伊犁的开端。清政府对此路极为重视,底定“回疆”后随即安排人员对此路进行恢复。学界也对穆素尔达坂路给予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③学界针对穆素尔达坂路的研究成果有: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一)》,《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60-73页;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二)》,《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第93-102 页;潘志平《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第2 期,第32-41 页;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第64-80页;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二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45-47页;陈海龙《〈西域见闻录〉所载伊犁至乌什之“冰岭道”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7 期,第39-44 页;王耀《古代舆图所见达瓦齐南逃路线及伊犁通乌什道》,《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 年第5 期,第57-64+160页;王科杰《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4期,第87-94+127页。但相关研究成果均从宏观上或某单一角度进行论述和探讨。而本文利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等满文资料,对清政府恢复、开辟和利用此路的相关情况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一、穆素尔达坂路的基本概况
穆素尔达坂,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结冰的山岭,主要描述其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而非体现交通概念。只有经过人工开凿,跨越此冰达坂,开通此路并投入运营后,才具备现实的交通意义。穆素尔达坂路分为三个部分:南路、山路及北路。过去学界研究只阐述南北山口之间的山路部分,此路应包括自阿克苏至伊犁的所有路段,本文对此加以补充。
(一)穆素尔达坂路驿站设置情况
卡伦、军台、驿站、营塘等交通职能设施,为清政府传输文件情报、物资转输、战事战备、官兵流动、防御备战等方面,提供了最直接、最牢固的服务和支撑。简言之,是朝廷传递信息、运输军备的统治命脉。各个交通职能部门的属权和职责为:“军台以营员及笔帖式领之。卡伦则领以前锋校、骁骑校,而以侍卫统之。其驻兵多寡则视其地之大小简要为差。驼马车夫,分别安设,复以时酌量增裁移置。”[2]所以,各个站点硬件建设及人员配备成为最关键的两个方面,清政府在穆素尔达坂路的建制与规划上也加强了以上两方面,以便此路更好地发挥政治军事功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参赞大臣舒赫德上奏朝廷:“搜除隐匿贼匪,请于事竣后,将官兵分为两队,一队在赛哩木、拜等处之阿勒坦和硕要路,安设卡座,一队在阿克苏之穆素尔要路,安设卡座,守护台站,照看往来行走之人。”[3]册16,卷598,687获得奏准,此为清政府最初恢复此路的计划。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舒赫德又上奏朝廷,阿克苏至穆素尔岭请设六处台站,过岭后至海努克,设三大台站,委派察哈尔总管敏珠尔、原任副都统杨桑阿办理。此为清政府在穆素尔达坂路具体设置驿站的开始。当然,此前准噶尔部也在使用这条路,也曾派“回众”对此路进行修缮和维护。但因战争等原因,此路暂停使用,维修也被中断,维护和开凿冰道的“回众”数量也受到影响。清政府重新开辟此路后,在剩下的60 户“回众”的基础上,增加至120户,以保证此路的修缮、畅通及运营。
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初五日,舒赫德派察哈尔总管敏珠尔,原任副都统杨桑阿赴伊犁勘查设置驿站情况,敏珠尔和杨桑阿回复称:三月初九日,自阿克苏出发,至伊犁海努克共设置9台站,自阿克苏原设台站扎木台(jam giyamun)—腾和罗台(tenghoro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110 里)—和尔郭罗克台(horgolok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40 里)—图比拉克台(tubirak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80 里)—呼素图托海台(hūsutu tohai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80 里)—塔玛噶他西台(tamagatasi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80里)—噶克察哈尔海台(gakca hargai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80 里)—特克斯台(tekes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160 里)—色尔图布拉克台(sertu bulak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150里)—察布查尔台(cabcal giyamun,与上一台站距离为130 里)—海努克地方(hainuk,与上一台站距离为120 里),总计1 080 里。①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58-263 页。因头台扎木台为原已设台站,为阿克苏往拜、库车等城的过路台站。而针对穆素尔达坂路向北伊犁方向,扎木台则成为头台,在此基础上往北增设新台站9 处。即南麓6 台,北麓3 台,加上扎木台,此路共10 处台站。此时,海努克仍未设台,察布查尔台则为底台。伊犁官兵尚未渡河前往乌哈尔里克(即绥定)、惠远等地设伊犁将军府及总统伊犁将军。另外,汉文地名及人名后括号内为满文穆林德夫转写,皆为音译。关于行走此路所需时间,史料中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二十九,舒赫德问及赴伊犁护送屯田“回众”的阿克苏伯克,其回答道:“我等翻过达坂时,马匹、牲畜概无遗失,往穆素尔达坂缓缓前行,就近住宿,住六宿后,第七日到达察罕乌苏。”“我等自察罕乌苏出发,路上住两宿后到达穆素尔达坂。自穆素尔达坂起程缓缓前行,路上住八宿后到达阿克苏。”[4]册45,46-47
从中可以判断,护送屯田“回众”的阿克苏伯克自阿克苏出发,行至察罕乌苏需要6 宿路程,自察罕乌苏至穆素尔达坂需2 宿,至阿克苏需8 宿。此次自阿克苏行至察罕乌苏再回至阿克苏共用时16宿、17日时间②此次阿克苏伯克等人未到达伊犁海努克地方,仅行至察罕乌苏便返回。察罕乌苏至海努克地方仍需行走6宿时间。。
道光六年(1826),因平定张格尔之乱,清政府通过穆素尔达坂路从伊犁往阿克苏运送粮食,清政府在运粮过程中按当地地形和实际情况,对此路的台站进行统筹安排,由北向南具体如下:
第一段:伊犁至北部山口设有15 个驿站,即:伊犁—巴图孟克台(与上一台站距离60里)—海努克台(与上一台站距离50 里)—索郭尔台(与上一台站距离90 里)—博尔台(与上一台站距离70 里)—和讷海台(与上一台站距离90 里)—特刻斯台(与上一台站距离100里)—沙图阿满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里)。①参见《西域图志校注》,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4页。
第二段:即山路冰岭路段,噶克察哈尔海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 里)—塔木哈塔什台(与上一台站距离120 里)。“穆肃尔译言冰,达坂译言山。穆肃尔达坂译言冰山也,在伊犁乌什之间,为南北两路紧要必由之孔道。其北为噶克察哈尔海台,南为他木哈他什台,两台相距百二十里,中即冰山。”[5]159表明此路最为艰险的路段约为120里。
第三段:玉斯屯托海台(与上一台站距离70里)—图巴拉克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 里)—亮格尔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里,乾隆三十六年自和乐和罗克移此)—阿尔巴特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里,乾隆三十四年自特克和罗移动此)—扎木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 里)—阿克苏底台(与上一台站距离80 里)。②参见贺灵《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第14 卷,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0-211页。阿克苏至乌什:察哈喇克台—阿察塔克台—乌什底台,距离200里。
以上为乾隆和道光年间此路各个驿站的基本情况,驿站的位置、数量、官兵人数、驼马数量等,也按年代及军事需要变化而适量增减。总之,驿站的设置和变化始终围绕着为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服务和进行。
(二)穆素尔达坂路自然地理状况
关于穆素尔达坂路自然地理环境,我们需要做一个说明,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清政府对此路开发利用的决策和部署。此路为新疆南北疆直线距离最短、最为便捷的一条路,但因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等原因,决策者们不得不多方面考虑,宏观把握各种利弊因素。因为地理、气候等原因的限制,势必会造成人员、牲畜、物资的损失。同时,也要投入人力和库银来经营和维持此路的运营和疏通。
相关文献记载了此路的自然状况:“人畜皆于山坡侧岭羊肠曲径而过,失足落海中,则杳然沈坠,不复可见。过此二十里,即冰山矣,无土沙,无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初不知其几何寻丈,层峦叠嶂,千仞攒空,巉巉如嵩华者,皆冰也。裂隙处,下视正黑,不见其底,水流之声淜湃如雷鸣,人聚驼马之骨横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绝处亦凿有冰蹬。陟降攀援,滑聿万状,跬步不谨,辄落冰涧中。”[5]159可见此路之艰险。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二十九日,据前往伊犁护送屯田“回众”的阿克苏伯克所言:“现翻穆素尔达坂易,不必卸下行李,一直驮行即可翻过,十名回众经日在此修理冰道。”[4]册45,47说明最迟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已经开始修缮和恢复这条路,并在最关键路段安排了10 名“回众”进行修理和维护,以保证道路的畅通。清政府虽然重新开启此路,但路况依然险峻。兵丁在传输文报时,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也逃不过厄运。从舒赫德奏折中也能看出其艰难程度:“他们因递传事宜,到达穆素尔达坂之顶,偶遇暴风雪,到达台站的兵丁王政晓冻死于岭上,刘元胜冻伤了腿,滞留于彼处台站,未见回子买买亚力。”[4]册45,100说明此路虽然有专人在维修,但因为海拔高、常年积雪积冰、恶劣天气等原因,时刻威胁着官兵的生命安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参赞大臣舒赫德关于修理穆素尔达坂路及更换台站兵丁事宜上奏朝廷,“此次进山勘察,由阿克苏属的亥里巴特阿满入口进入,两面均为高峰,中间有大河流过,沿山崖前行八十里,至塔玛噶他西台站,绕行冰石路段二十里,一脉横山,皆为坚冰。再前行至噶克察哈尔海台站,皆为积雪,供官兵使用的柴火甚少”[4]册45,258。
又据熟知这条路的“回众”答复:“穆素尔达坂之冰雪,虽行走艰难,结冰之处不过两箭射程。”[4]册45,101说明此段距离虽短,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也记载了此段路程的情况:“塔玛噶他西台至噶克察哈尔盖台有八十里,需翻过穆素尔达坂。翻越此达坂需行四十里,皆需攀行冰山,且掺杂碎石,驼马行走虽跐滑,但可缓缓前行,唯行二十里,有一段近二里的横向冰山,无碎石,往高处行走时甚是跐滑,皆需凿出冰阶,方可使驼马攀行,此冰阶处常驻十名回子,终日凿冰修路。”[4]册45,260说明最险峻的路段有1~2 里距离,均为冰山,并且有10名“回众”专修冰梯,以保证此路段的畅通。
以上为此路自然样貌及沿途路况,虽然条件及环境恶劣,但官兵及修路“回众”依然克服了种种困难,全力保持此路的畅通。
(三)穆素尔达坂路值守官兵及修路人员的安排情况
乾隆二十五年(1760),参赞大臣舒赫德上奏:“臣即将派出修理道路回人一百二十户内,每日派二十人,更番槌凿。”[6]此为清政府恢复穆素尔达坂路的开始。同时,台站官兵的换防时间由两年一换改为一年一换,而修路“回众”则被安排在此路附近居住。这些“回众”具体由以下回城派出:“由阿克苏派出之六十户回子已安置于伊勒噶奇地方,不再另行派人外,自库车、沙雅尔派出二十五户人口,自乌什派出二十户人口,赛里木、拜城等地派出十五户人口,总共六十户人口,搬迁安置于伊勒噶奇,按班轮流修理冰道。”[4]册45,44轮流的人数为:照旧十名“回众”轮流修理冰道。①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页。而这些“回众”则由阿克苏噶杂纳齐尼雅斯之弟巴巴克管理。“查,为修理穆素尔达坂之冰雪,安置于伊勒噶奇之一百二十户回子,应另委一名伯克对其管理,于此地选派一名胜此任之回子,观其几月,若果为诚恳能力者,再乞奏顶戴。”[4]册45,45
清政府运用新疆南部伯克的力量,为穆素尔达坂路的建设和维护服务。如南路台站所需马匹,由乌什伯克萨里等承办;而北路台站所需马匹,伯克萨里、额塞木图拉等亦愿为承办。舒赫德同时上奏朝廷,以阿布都拉补乌什阿奇木之缺,若遇伊什罕②阿奇木伯克的副手,帮助阿奇木伯克办理各项事务,职位仅次于阿奇木伯克。之缺,也可将萨里补放,并酌量奖赏缎匹。清政府充分调动和利用新疆南部特权阶层力量,以求迅速恢复新疆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而库车办事大臣纳世通负责从库车等各城抽调修理冰道“回众”,为修理穆素尔达坂,分派并搬迁至伊勒噶奇(ilgaci)安置的库车、沙雅尔、赛哩木、拜城之“回众”共四十户。先派遣男丁,秋收后再派遣家眷,自库车十五户、沙雅尔十户、赛哩木九户、拜城六户,总共派出四十户“回众”,委于各城伯克首领,携修路所需铁锨等工具,办妥三月口粮,出绿营把总一名署以护卫,于四月二十,安置于伊勒噶奇,修理穆素尔达坂,委于小伯克巴巴克和卓派遣前往。③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挑选的“回众”均为穆素尔达坂周边城乡“回众”,因这些“回众”熟悉修理冰道的方法、沿途情况及地理气候特点。另外,他们受清政府及伯克双重管辖,清政府管理各个军台的官兵,而伯克则管理维护此路的“回众”。此路上的伊勒噶奇为修路“回众”的固定居所和供给站,修路“回众”以此地为据点进行修路、换班等活动。军台官兵和修路民户互不干涉,各司其职。
清政府针对各个台站官兵的值守工作也进行了安排,北路初建时有特克斯台、沙尔图布拉克台和察布查尔达坂台三大台站,其情况如下:“现三大驿站内均有满洲兵十人,索伦、察哈尔兵各十五人,回子十人,总共五十人。”[4]册45,371后因实际情况酌情添补和裁撤相关配置及兵丁人数,具体变化为:伊犁底台至阿克苏所属噶克察哈尔海台,总共军台8 处。“每处设有笔帖式者,惟巴图蒙柯、特克斯二台,其余皆无。每台设兵十户、十五户不等,马十五匹,牛十四只。自沙图阿满台南行五里为天桥,伊犁阿克苏交界之所,又迤南行九十五里为噶克查哈尔海台,至冰岭下矣。”[7]从中可以判断,沿路军台有一定数额的官兵及笔帖式值守,兵丁以户为单位,携眷驻扎,以保障此路人员、物资及文报等能够畅通流动。
清政府起初给官兵的日常供给为:“穆素尔达坂北麓,至伊犁台站之官兵口粮,现俱由阿克苏供给,路虽不甚远,因间有穆素尔达坂,往返行走时,携带之牲畜恐有损失,现臣决定一半为羊只,一半为米,趁水草充沛,按时用马、驴轻驮缓缓运送,惟此路台站,则为永行设置,阿克苏所存牲畜理应珍惜食用。经慎重考虑,料想于特克斯河周围能找到可耕之地。”[4]册45,341从中可以判断,驿站官兵供给大多从阿克苏转运至各个站点,因此时伊犁仍未开垦,生产生活物资仍需由外界输入,无法供给台站官兵给养。伊犁屯耕收获后,再由伊犁反向供给台站所需口粮。
另外,根据舒赫德的建议可判断,各个军台的兵丁为携眷驻扎,并以换防制度进行定期换防;而“回众”则是依附在这些台站上挣取工钱,有些为长期,有些为短期。平日各个台站的转运工作繁重,又不得出现差错。而单靠驻站兵丁10 户、15户的人数无法承担这些任务,需要靠其他人员进行辅助工作才能完成,因此才出现对“回众”的招募和雇佣的情况,以期保证此路的物资正常运转。需要强调的是:负责修路的“回众”与在台站服务的“回众”应有区别,修路民众较为固定,甚至世代在修理此路,他们与台站的联系较松散。而服务台站的“回众”,则对台站的依附性强、流动性大。当然,管理以上两部分“回众”的官员也有所不同。
二、穆素尔达坂路的利用及人口流动
(一)转移屯田回众
因伊犁驻防需要,清政府需从新疆南部迁移“回众”前往伊犁屯田,以确保军队的用粮需求。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第一批派遣回众300名,派往海努克和固勒扎两处。后经阿克苏办事大臣舒赫德上奏朝廷,再从南部派出回众500 户,“计阿克苏一百六十一户,乌什一百二十户,赛哩木十三户,拜城十三户,库车三十户,沙雅尔十三户,多伦一百五十户,于来年二月,办给籽种器具,携眷前往”[3]册16,卷615,922。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初一日,赴伊犁的阿克苏“回众”起程。初五日,在海里巴特集合。副都统伊勒图领满洲兵100人,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100人,敏珠尔、杨桑阿协办。各“回城”派出伯克1 名,护送赴伊犁的屯田“回众”。备齐马、驼、羊、官兵盐菜银及大小麦籽种器具等,屯田“回众”及眷属一并发往。而相关兵丁到达伊犁后,缓行转回阿克苏。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从派遣“回众”中挑选匠役26 户,先行派往伊犁,制造器具。①参见官修《清实录》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2页。伊犁筑城方兴之时,自新疆南部调派铁匠、木匠等,为修建驻防城硬件设施提供了保障。同时,屯田需要制造新的农具,也需要有技能的铁匠,新疆南部的“回众”工匠刚好填补了此项不足,不致劳烦内地工匠。
另外,来自近12 城的“回众”,甚至有多兰“回众”。虽同样是“回众”,他们之间也有一定差别,包括语言、风俗、服饰、饮食、生活习惯等。其中,也有在准噶尔时期,本身在伊犁进行耕种、后因种种原因回到新疆南部的“回众”。这部分民众,甚至有私自回伊犁耕种生活的。但清政府有一套完整的派遣制度,各城的派遣户数固定不变,一旦确定,不可更改。私自赴伊犁生活或耕作的“回众”,依照定例要对其进行惩处。
(二)搜剿玛哈沁
玛哈沁②即因清准战事生产生活被破坏的厄鲁特蒙古人众,为了生存,常常对清军站台、过往行人、附近民户进行抢掠。,即为准噶尔溃散之民,居无定所,以抢掠为生。经常抢掠台站、卡伦、行人、外藩使臣等,对清政府初定新疆带来一定的隐患。清政府进驻新疆初期,为了稳定社会生产生活,对玛哈沁实行了打击政策。
清政府初定新疆南部,玛哈沁四处抢掠,甚至抢掠官方设立的驿站。官兵在监督和保护派往伊犁的屯田“回众”的同时,一并搜剿玛哈沁残余,以保证南北山麓各城及官兵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新疆各地官员、特别是伊犁和阿克苏的官员更是通力合作,打击和瓦解玛哈沁残余力量,以保证新疆初定时的稳定状态。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由阿克苏送来回人等,行至赛哩木,遇玛哈沁二十余人,把总徐天成及兵丁二人被害,掠去回妇一人,马十四匹,驼四只,外委把总一员得伤,又兵丁一名、回人一名不知踪迹,今选派库车绿旗回人兵丁前往追捕”[3]册16,卷596,643。对此,清政府态度坚决:“此等玛哈沁贼人,肆行抢掠,殊可痛恨,伊等或藏匿穆素尔岭等处,亦未可定,必须搜剿净尽。”[3]册16,卷596,643另外,对提供线索的向导也给予奖励:“奋勉向导人等,酌给钱粮,如著有劳绩,或编入京师旗分亦可,其余人众,努三既许以不死,俱解赴京城备赏,现在可用之人,暂行带往,招抚事竣后,再行酌量办理。”[3]册16,卷596,64“3恐沿途流为玛哈沁,宜留心防范,毋致盗窃台站马匹牲只,如有滋事者,即行正法,以靖地方。”[3]册16,卷601,736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阿克苏北山之布鲁特噶岱密尔咱等游牧,被贼盗去马匹,随派兵越穆素尔岭,未能追及”[3]册16,卷597,655。曾有永贵等追剿玛哈沁到山间,因雪厚,无法追击贼人,无功而返。朝廷下旨责备道:“今半途而返,甚属无谓,若谓雪大难行,玛哈沁等又岂能飞越耶。”[3]册16,卷598,677玛哈沁足迹遍布阿克苏、额林哈毕尔噶、呼尔岱、都木丹济尔哈朗、玛纳斯、阿圭雅斯山等地,给当地官民生活安定带来巨大隐患。玛哈沁人众流动性大、居无定所,抢掠结束,又飞速逃至别处,甚至翻越穆素尔达坂路而去。清兵虽然实施抓捕,但玛哈沁习于山林地形,行动自如,清兵在山势陡峭之处行走,加上对地理环境不熟等原因,加大了围剿玛哈沁的难度,追捕活动多以失败告终。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所派官员德舒行至库车,被百余名玛哈沁抢掠,德舒中枪身亡。对此清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德舒虽然品级不高,但仍为清政府所派官员,玛哈沁肆意抢掠杀戮,着实让清廷颜面扫地。遂决定“务将为首之贼,解京严惩,或临阵剿杀,亦必尽歼逆党”[3]册16,卷596,646。“务期尽剿贼众,为德舒复仇。”[3]册16,卷598,677随即,清廷安排纳世通领兵400名,会同永贵、努三,追捕戕害德舒的玛哈沁等。
清政府一面剿杀玛哈沁,一面利用捕获的玛哈沁为官兵效力,实行进一步的清剿。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努三查明“拿获之厄鲁特伯楞泰,因其熟习鸟枪,令为向导,伊奋勉效力,擒获多人”。政府在剿杀玛哈沁的同时,若有似伯楞泰等“效力之人,即带领进兵,一面酌量奏请,给以职衔”[3]册16,卷597,656。说明清政府针对玛哈沁采取的策略是一面打击,一面收编。清廷大力剿杀和安抚玛哈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于呼尔岱收获男妇二十六人,杀贼三十余名,得马三百五十余匹。政府还对搜捕有功的官兵给予了“卓哩克图巴图鲁”“锡勒哈达克巴图鲁”等名号,并奖赏银两,对伤亡官兵进行了造册送部,并进行了抚恤。①参见官修《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614,第903页。对于俘获的玛哈沁,并未全行剿杀,而是采取移入内地、解送北京、分赏大臣为奴等方式办理。对玛哈沁的态度应保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些人众是准噶尔内乱及清廷底定新疆过程中被影响的民众,他们的生产生活因上述原因彻底破产,只能以抢掠为生,实属无奈。
(三)输送粮食
清政府底定准噶尔和“回疆”后,屯田“回众”及绿营兵还未到达伊犁前,官兵口粮均运自新疆南部,清廷选择穆素尔达坂路进行运粮事务。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谓伊犁驻兵屯田,于来年次第办理”“即如粮运一事,自叶尔羌等处,由阿克苏穆素尔岭,前至伊犁,乃正路也。若谓山岭难行,由库车运往,则其路更远,岂此间别另有捷径乎?”[3]册16,卷601,743
道光六年(1826)十一月,清政府为平定张格尔叛乱,需要自伊犁往阿克苏运送供三万官兵食用的口粮,此次运粮十万石,先行磨面再运抵阿克苏,这样可以节约运送成本,这些粮食先由官用车驼运至山脚台站,山路部分“由冰岭转运,恳请酌分程站,加增工食料银,均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准其作为十九站,按照道路险易,分别用车用驼用夫,其雇用民车民驼,按石照例发价,酌拨伊犁官驼三千五百只,均交驼夫承领,重运回空,每日每驼给银三钱,如有疲乏倒毙,扣价赔补,雇用回夫二千名,每夫每站给工食银一钱,事竣照所奏章程核实报销,其伊犁磨面工价,并奖赏回夫,及咨拨银两,均照所议办理”[3]册34,卷110,832。这一段需要用回夫二千名,并给予工钱。其他路段雇佣民车、官车及官驼等。期间调取官驼三千五百只,采买口袋一万余。每日运抵阿克苏的粮面有三百石,一月可收粮九千石。②参见贺灵《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第18 卷,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3页。整个运粮过程清政府并未以强势权力对“回众”进行压榨,而是根据战事和地理环境的特殊需要,略高于市场价支付了运脚银两。
(四)派遣换防官兵
清政府底定准噶尔及“回疆”时,官兵的大致流动方向为:先进入伊犁底定准噶尔,后再由伊犁和哈密进入新疆南部底定“回疆”,再由“回疆”经穆素尔达坂路返回伊犁驻防。至此结束了官兵因战事而形成的战事流动,并开启了为执行换防任务的官兵流动。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命令“阿桂专理屯田,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苏尔达巴罕至伊犁镇守办事。搜捕玛哈沁,招抚溃散之厄鲁特,即以绿营兵筑城,回子乘时兴屯,开渠灌溉,是为伊犁屯田之始”[1]87。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在伊犁设置伊犁将军府。后清政府自伊犁派官兵驻扎新疆南部,官兵自穆素尔达坂路前往“回疆”。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派遣400 名官兵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换防时便通过此路。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所有伊犁换防喀什噶尔官兵,著仍照旧章,由冰岭行走,派委协领护送,至冰岭之南塔木哈塔什台互相交替其换班之期,每岁定于八月,并著知照阿克苏,循照上届章程照料过境”[3]册37,卷264,56。从中可以判断换防官兵的行走路线、交接地点、时间等都已经形成了章程和定制。
除了以上内容以外,清政府也利用此路转运文报、牲畜、茶叶、布匹、马匹、农具、武器等等,此通道成为清代南北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三、结 语
清代新疆初定时,需要在伊犁驻军并发展农业,以保证官兵口粮之需。官兵、屯田“回众”、牲畜、粮食、物资等由穆素尔达坂路进入伊犁。同时,阿克苏、喀什噶尔、和田等地因战事、生产、驻防等方面的需要,需派官兵驻防;社会经济恢复发展,需要牲畜及谷物;战事和官兵口粮也需要粮食及物资支持;官兵驻防、牲畜粮食运送、战事军事情报传递,均需要途经穆素尔达坂路。所以,穆素尔达坂路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穆素尔达坂路台站的建立,给往来的官兵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碰到恶劣天气时,台站的建筑、食物及柴薪等都给往来官兵提供便利。同时,这些台站也负责指挥修路“回众”对穆素尔达坂路进行维修,以保证此路的畅通。另外,通过此路运输粮食更能节约时间和运费,清政府将节省下来的运费补充到战事用银,无形中降低了战争成本。
清政府控制并开辟穆素尔达坂路后,实现了对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道路和台站的所有辐射和控制,从而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为进一步统辖新疆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清政府发展新疆社会政治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此路的开辟和利用,也显现了清政府依靠新疆各阶层、各民族力量完成了对新疆的统辖和管理,正因为各民族人众的参与和建设,才使得清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得以稳定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