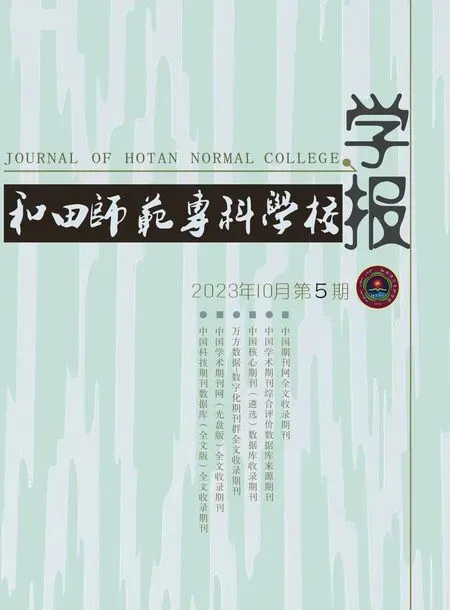从晚清民国报刊管窥近代山西的乡村危机
张梓琦 张爱明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乡村问题,历来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在当时即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成了时代的潮流,各大报刊上关于乡村危机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眼花缭乱。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突出再度引起学界对乡村危机的高度关注,对乡村危机的成因和复兴乡村举措的讨论经久不衰。检视目前学界对乡村危机的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到区域间的差异①。山西地处内陆,是具有华北区域特性的典型地区之一。基于此,本文以20 世纪30 年代的各大报刊中有关山西乡村危机的讨论为基础,从乡村危机的表现、乡村危机的成因,以及乡村危机的应对措施三个方面,对近代山西乡村危机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期对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 山西乡村危机的表现
“农村经济,为国家组织之基础。基础不固,国家本身随之动摇。农业为国民经济之渊源,渊源枯竭,国民经济必起恐慌”[1]。山西乡村危机,首要的是经济危机,其次则体现在政治、教育等方面。
(一)农家破产,前途渺茫
乡村危机前的山西农村是一幅繁荣的景象,农民对生活充满信心,“往时乡间一般人民之愿望,皆在图富庶,求积聚,他们常年的劳动经营,东奔西走,无非是要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而乡村危机时,农民的生活已大为迥异,“他们虽勤到‘废寝忘食’,少到‘俭衣缩食’的地步,总是所得供不应求,金钱半文也无可积蓄,累日的束手束足,由‘荣欲生活’的观念,一变而为‘勉强度日’的生活,合家用的油米薪具,都起了很大的恐慌”[2]。
农民陷入生存危机当中,尤其是占人口大半的中贫农生活更加悲惨,“其所耕获者,不足己食;佣工之收资亦仅足交官府粮银、捐税,又无其他物品可售,结果只好负债认饥而已”[3]。据张稼夫1933 年在太原南部一个村庄的调查表明,一个五口之家,约有15 亩地,一年的农业收入约为24.75 元,而家庭开支却接近91.35 元,如果仅靠农业为生,每个家庭每年要亏空66.6 元[4]。农家收支不抵以至于此,难怪乎对未来抱有悲观情绪了。
(二)金融枯竭,利率上涨
20 世纪以前,由于山西商人在外经营的成功,山西农村在金融上是不觉匮乏的。但此后,随着晋商的没落,晋钞的暴跌以及对外贸易中长期的入超等,乡村金融逐渐枯竭,农民借贷愈发困难。“就刻下情形而言,无论出利息若干,借债者尽可以借债度日,但至还债之时,无款还债,债主亦未可如何,一般富户或殷实商号均已洞悉其隐,故宁窑藏银钱于家,亦绝不贪图大利,出放生息”[5]。
借贷利率也随之而高,“往者借款大至三分利息,而今八分尚找不到债权人”[6]。据实业部调查,在现金借贷一项中,山西借贷年利为四分六厘,而临近的河北、山东、河南分别为二分九厘、三分四厘和三分五厘,远较三省为高[7]。农民的负债率也不断提高,据对山西定襄五个村庄农民负债情形的调查,各村负债的农户平均都在65%以上,有的村庄负债率甚至达到了87.79%,农民对借贷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8]。
(三)粮价低落,土地贬值
粮价普遍低落,即便丰收之年,亦呈下跌趋势。“往年买谷之价今可买麦,往年买糠之价今可买谷,今昔之差,诚有天壤之别”[9]。五寨的粮价在30 年代一路下跌,差不多只有过去价格的三分之一,结果是“名为丰年,无异歉收”[10]。而崞县1932 年农产品的价格与1931 年相比,小麦下跌40%,高粱下跌50%,小米下跌57%,其余农产品下跌同样严重[11]。粮价的低落使农业经营陷入困境,据汾阳一带农村的调查,即便是在丰年,农民每种一亩高粱须得亏本一到二元[12],土地竟成有害无利了。
由于农业经营的惨淡,地主丧失了对土地投资的兴趣,出现了“欲放弃土地者多,欲投资于土地者少”的现象。山西隰县,在过去地主每亩地可得租洋二元,而到30 年代时,每亩地仅可收租二三角钱,这些钱用来缴纳赋税都尚感不足,以至于一般人都想出卖土地,市场上只有卖者而无买主[13]。山西襄陵同样如此,在过去每亩水浇地可卖百数十元,而到30 年代即便是五六十元,也少有人问津了[14]。
(四)流民渐多,商人归村
乡村危机下,农民出现了大规模的离村。据中央农业实验所30 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山西省全家离村的农户总计20852 户, 占调查各县农户的1.4%, 青年男女离村的农家为50927 户,占调查各县农户的3.5%[15]。而据行龙的统计,近代山西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的过剩人口当在四百万左右[1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是“安土重迁”的,20 世纪30 年代农民的大规模离村,进一步说明了农家的贫困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农民离村固然是农村经济破产的现象,农民归村更是整个国民经济‘走投无路’ 的象征”[17]。明清以来,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全国,据当时的统计,全省经商的人大约有百万左右。晋商衰落后,数量庞大的失业商人,只得退居农村,因此出现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山西忻县的奇镇,村民多以经商为业。民国以来,由于商业不振,大量的商人因商号倒闭返乡,而又因耕地的有限,大多成了无业的游民,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人口压力[18]。
(五)村政腐败,劣绅横行
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即着手对旧社会进行改造。然而,在打破旧社会的同时,新的社会秩序却尚未构建,一时之间,整个社会陷入到失序当中。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士绅逐渐退出权力中心,各级办事人员——尤其是村长,逐渐被土豪劣绅所取代,此辈“对上蒙混隐蔽,虚心周旋;对下藉端敲诈,尽量鱼肉”[19],导致乡村不堪其扰,村事纠纷日多,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汾阳一带农村在选举政府主席等时,总是以地主及高利贷者当选,此辈利用村政机关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巧立名目侵占农田,增加捐税,甚至于带头强抢农户,无恶不作[20]。应县同样如此,包商勾结主计员私定税则,剥削民众,民众在苦不堪言的情况下,将其控告上省府[21]。该县第五区区长安怀壁以暴力统治村民,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毒打。驱使区警为其爪牙,向各村无故摊派,全部收入自己囊中[22]。政治的腐败,既是乡村危机的表征,也是乡村危机发生的动因。
(六)城乡背离,教育衰败
“所有教材,完全与都市采用者无异;一切设施,大率为都市教育之遗规。而对于真正农村所需要者,却少有人依据事实,去做正确的努力。如农村生活所需要者为种植五谷,而教育却不授以种植五谷的智能;防虫施肥,是农业上最重要的事,而教育却不以此为要务”,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背离,使山西农村的教育亦呈现衰败之势。
当时山西全省各县农村都普遍设有小学校,表面上看山西教育似较为普及,实际上山西农村教育成效甚微,各村虽有学校招牌,不过支撑门面而已。据实际调查,当时山西各村的失学儿童比例高达70%至80%。而且学校师资多不合格,经费也不充足[23]。以阳城为例,据历年对学龄儿童统计,失学者占到10%以上,而入学一二年就退学的,更是占到了70%以上,实际受教育的儿童,只有10%左右。“雇工之子,五六岁即须遣出为富家放牛;中农之子,至七八岁亦须到田中帮忙”,农民普遍贫困下,受教育成为一种奢侈[24]。
总的来看,近代山西的乡村危机,表现为:农家破产;金融困顿;粮价地价贬值;失业人群增多;土豪劣绅把持村政;乡村教育衰败等六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是一种全方位的危机。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乡村危机在各方面的表现并非独立的,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互为因果,乡村危机的某些表征,也恰恰是推动乡村危机发生的动因。
二、乡村危机的原因
乡村危机的产生,是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既有长期以来始终困扰山西乡村社会的病症,也有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尽管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各有轻重,但毫无疑问,它们与乡村危机的产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人地矛盾突出
近代山西乡村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人均耕地不断下降。据毕任庸对山西省耕地面积和人口增长数据的分析,得出“假使就固定基年说,山西省1933 年人口较1913 年增加了6%,而耕地并未增加,依旧停滞在1913 年地水准上;假使就移动基年说,1933 年和1913 年一样,人口指数同为107,而耕地面积却反从1913 年地106,跌至101”[25]。以文水县为例,清光绪七年全县有耕地803803 亩,人口1361225 人,人均耕地5.9 亩。而到1935 年,全县耕地仅剩577403 亩,人口却增到159832 人,人均耕地仅3.65 亩[26]。一般认为,在近代,人均5 亩土地可以维持华北农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即“耕地临界点”[27]。显然,山西人均耕地已经明显不足,农民家庭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
(二)生产技术落后
杨开道认为,农民的好坏、农业的发达关乎国家兴衰,而事实上“数千年来,我国农业没有一点进步,农村的衰落,一天甚是一天”[28]。山西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当时是低下的,“一切近代的农业用的进步机器,在这里是一件也不见的……他们一般现实使用的生产工具,大都是差不多千余年来传统式的陈旧笨拙的古董”[29]。旧式的生产工具如犁、镂、锄、耙、镰等,仍是农民赖以克服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工具。这些工具的生产效率低下,犁一日平均仅能耕四亩,镰刀平均能收割五六亩。
此外,畜力也甚为缺乏,无牲畜的农家占到绝大多数,农业生产仍然是以人力为主,畜力为辅。肥料也以人粪、畜粪、草灰等旧式肥料为大宗,肥田粉等人造肥料,在山西农村中几乎无人施用。因此,农民花费了大的力气,却只能收到微不足道的效果,经营方式只得是潦草应付,很难做到精通改良。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力的停滞与退化成为近代山西农业经济的特征。
(三)自然灾害频繁
晚清民国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据夏明方统计,从1912 年到1948年,华北各省在水、旱、虫、风、疫、震等自然灾害中,河北总计1510 次,河南1782 次,陕西1233次,山东812 次,山西1050 次,换言之,民国时期的山西乡村每年要承受30 余次自然灾害[30]。
频繁的自然灾害,给山西乡村造成极大的破坏。1929 年,山西爆发了严重的灾疫,“全省一百余县,不被灾者鲜矣……富者尚不得一饱,贫者则併日而食。入冬以来,藜藿一空、风雪交作、路人陨涕、哀鸿遍野,老弱死于沟壑,壮丁转为饿殍,无衣无食,死亡枕藉”[31]。1934 年,全省又爆发罕见的奇灾,南部大旱,北部连日大雨,西部中路一带则是瘟疫流行,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县份受灾,仅农产一项损失已达3068270 亩。1935 年,全省被灾田地14603 千亩,受灾面积占总面积26%。农作物大量减产,与平时相比,棉花大豆损失达12%,玉米达12%,小米达13%,高粱达12%[32]。这些大灾间隔之短,使农村社会难有喘息之机,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兵灾匪祸横行
杨开道认为,兵灾匪祸是造成农村生活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民国成立后,兵灾匪祸连年皆有,“有钱的农民都离开了农村到城市或是租界里面去过他们‘苟延残喘’的生活,没有钱的农民只好仍旧住在农村里,受兵和匪的蹂躏”[33]。
山西乡村饱受战争之苦,1926 年晋国两军、1927 年晋奉两军先后大战于雁门关北,晋北一带的农村几乎完全破产。据统计,阎锡山的军队在雁北各县共掠夺现金7 亿4 千多万元,牲畜22 万6 千多头,粮食170 多万石[34]。1930 年中原大战后,“客军”败退晋省,人数不下10 余万,其所需的粮饷军需,全部由山西供给,“差役异常纷繁,人力、车力、马力等农家所赖以耕耘者,辄终月不休”[35]。山西阳城在兵灾匪祸的侵扰下,“闾巷为之堵塞,商贾为之歇业,虽三家人村,亦常有夜盗,其较富人家之被绑票勒索,更为常闻”[36],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五)苛捐杂税繁重
民国以后,各种苛捐杂税盛行,农民负担增加数倍有余。朱偰曾说“农村破产普遍之原因,实为税捐之繁重;税捐中归农民直接负担者,阙为田赋,而田赋中之有加无已,使农民负担至不能负担者,实为附加税。故吾人可得一结论:农村经济破产的一般原因,实为田赋附加税之有加无已”[37]。
山西农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仅田赋一项,“在预算册内,有地丁,租课,米豆,及附加之省地方款,省县亩捐,征收费等,是为正供之项目;此外尚有诸种税捐,亦附属于田赋内,如警察,教育,村政,差徭,修渠等杂费”[38]。而附加税又常超出正税数倍,清源县“每亩正赋为四分四厘,县附加八分八厘,村附加一角四分四厘,附加达正赋三倍,全年每亩地负担一角七分六厘”[39]。忻县“平地正税,每亩有一角五分,县附加四角七分四,村附加也是四角七分四,附加有正税的六倍多,田赋的负担,每亩竟有一元零九分八”[40]。沉重的捐税,蚕食了本就微薄的农业经济,加剧了农民的生存危机。
(六)金融体系崩溃
金融是社会的基础,如果金融发生了变化,社会马上就会跟着变动。20 世纪20 年代早期,晋钞作为一种重要货币在山西城乡广为流通。但此后,由于政府的擅加干预,导致晋钞不断贬值,“因省钞基金被阎提去,省银行只得用做有限制的兑现,是以时价涨落无常,而常价日趋跌落”[41]。又历经多次战乱,现款大量外流,导致晋钞难以兑现,价值大为跌落。从1930 年到1932 年,不到二年的功夫,每元晋钞的价值就跌落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了[42]。
晋钞的跌落,使农家经济大损,“向之富者,转而为穷。今之富者,亦咸怀戒惧之心。或窑金于室,以备不时之需;或调金省外,以得微利”[43]。乡村金融为之枯竭,加剧了高利贷的剥削,有的被掠去土地,有的被迫出卖祖宅,卖儿鬻女乃至家破人亡的也大有所在。农产品交易也受到了影响,“买方拿晋钞买物,觉得物价太贵;而卖方则头一天收入的晋钞,到第二天就不值那么许多了,这样以来,买方固然吃亏,卖方也不合算”[44]。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同样促成或加剧了乡村危机的发生。一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恐慌而造成的向中国大量倾销货物,由此对本土的农、工业造成的冲击。二是近代以来的城乡背离化,现金和人才单向流入城市,而城乡交易上的农工剪刀差,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贫苦。不过考虑到山西地处内陆,舶来品较沿海各地为少,城市化程度也较沿海为低,这些因素相较于前述各点对农村的影响尚有不及,故不一一论述了。
三、对乡村危机的应对
面对乡村危机的发生,有识之士莫不发声,纷纷提出自己复兴乡村的主张。由于对乡村危机的认识不同,因而提出的解决路径也各有差异。这些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又主要集中在经济上。要之乡村危机首要表现为农家经济破产,因而增加收入实为当务之急。
(一)政治方面的主张
有主张整顿吏治,改良捐税以求达到复兴农村的,如庚析、黄丽泉等人。庚析认为山西农村的破产原因虽多,但大部分不能不归咎于政治的毛病,如天灾、人祸等都可归结到政治的窳败,要想剔除此种毛病,应当先从实行廉洁政治做起,他认为政治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受到经济的影响,但是也能反作用于经济,可以挽回农村经济的衰退[45]。黄丽泉认为农村破产的直接原因是连年的内战,因而他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少养兵,少要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46]。范叔远认为农村破产之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负担太重,因而提倡整理田赋,通过清丈土地、厘定等则、确定税收内容等方法,改变“胥吏之侵蚀中饱,及人民负担之不平均”的现象[47]。
主张发展农村自治的学者,有祝君达、杨中等人。祝君达认为乡村自治是改良山西社会的途径,他说“要认清今日乡村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教育的重心所在,应该马上到乡村去经营村治……使农民增加生产,改良村风,启发民智,培养自治精神,而实现真正民主的政治”[48]。杨中大力提倡乡村自治,他认为实行自治可以为人民得到政治上的利益,最小也有三种功效:一是增进人民的政治智能,二是能革除贪官污吏,三是能满足地方的实际需要,为此他提出编订农村十年建设计划书,印发农村信用合作券,扶植村公所,发展农村公营事业,增加农村生产等八点提议[49]。
(二)文化方面的主张
文化方面则是主张发展农村教育,培养人才,有翟品三、赵仁甫等人。翟品三认为复兴农村的先决条件是建设,而建设的关键在教育,因而他认为教育是建设的动力,是复兴农村的根本[50]。赵仁甫的观点与之相近,他认为“固然农村中需要事业很多,但其中以教育为最要。而以农村教育推动其他各种建设,更为重要”[51]。李希贤认为“教育与劳动分家,是阻碍国家文化进展的桎梏,也是造成我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因而他主张普及农村教育,尤其是创办职业学校,培养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生产技术的人才,以训导农村的农民[52]。积庵则是特别关注于成人教育,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为其基本组织,而成人农民,尤为农村社会组成之中坚分子”,因而“要增加农产物,建设新农村,必需由农村成人教育着手”[53]。
倡导教育,其最后的落脚点仍在经济方面。为发展农村教育而创办的呼延农村教育实验学校,即开宗明义提到“本校以实验精神,增加农业生产,改进农民生活,培养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指导人才为宗旨”[54]。刘伯英也认为“依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落之社会以言,民众教育之实施,亦应以生产为中心目标”,主要在实施农事指导,提倡各种副业,提倡合作事业,举行各种科学展览会等方面[55]。可见教育的重心之一,也在于经济建设。
(三)经济方面的主张
有主张改良农业挽救乡村危机者,如杨蔚等人。杨蔚认为“农村的重要分子是农民;农民经济方面的重要收入是靠着农业;所以改良农业,当然为救济农业经济的重要途径”,为此他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开展育种试验工作改良作物品种;经济组织改善及提倡;振兴林业;提倡水利;改良农具;成立全省农业指导及农业推广整个的有系统的组织;其他农业方面的改良如肥料、农家副业、家庭工业;农业以外的救济如交通、商业和工业[56]。
有主张发展农民合作事业的学者,如保三、刘子明等人。保三认为山西以农业为重,而又以中小农为主,欲复兴农村,必先使之结合。他认为单门独户的从事生产、运输、销售、采购等均为农民不利,而“欲舍不利,而就有利,除合作而外,再无良策”,因而主张在农村发展购买合作、贩卖合作、生产合作和信用合作[57]。刘子明认为,山西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之不适合与金融组织之不完善,因而他提倡在生产上开展耕地合作、肥料制造合作、水利合作和农产物制造合作,而金融上创办农民信用合作社,促进乡村货币流通以使农民免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58]。
有主张发展乡村工业的,有子发、刘荣亭等人。子发认为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谷贱伤农,因而提倡发展乡村工业,尤其是兴办粮食加工业如酒坊、油坊、粉坊等[59]。景阳则认为山西农村破产的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入不敷出,因而他主张改良农业及农家副业以增加生产,提倡土货以与外货抗争减少外溢[60]。刘荣亭则是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救济农村,须先使农业工业化”,且认为山西发展大工业的条件尚未成熟,因而提倡发展家庭工业,“唯一救济之方,则为普遍的在各乡村提倡农民家庭工业,当地制造者,当地用之,就近推销,其价必廉”,认为“非如是不足以救济我国农民,亦非如是不足以实现倡用国货”[61]。
总之,正如晏阳初所言:“时至今日,农村应该改造,国家急待建设,民族必须复兴。有识之士不但认识其重要,且在各处已由理论的探讨,转为实际的进行。……其观点与方法容有差异,其在努力以求实现救亡复兴之宏愿,并无不同”[62]。当时的学者们,以对山西乡村危机的直观感受,在详实的农村调查基础上,纷纷建言献策,提出复兴农村的“山西”主张。
结语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剧都是空前的,时至今日,仍引人深思。通过对山西乡村危机的梳理,可以发现,山西乡村危机既具有与全国性乡村危机共性的一面,又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如商人归村、晋钞的跌落等,可谓是明显的“山西特色”。最为重要的,则是当时学者们,在亲身经历和详实的农村调查基础上,对复兴山西乡村的建言献策,可谓字字珠玑。在当代“三农”问题愈发受到重视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山西乡村危机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有关乡村危机的研究,有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J].史学月刊,1999,(1):105-111.向玉成.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J].中国农史,1999,(4):106.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 世纪30 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J].近代史研究,2013,(5):44-59.张爱明.由农入商:近代山西的乡村危机与晋中农民经商浪潮[J].史志学刊,202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