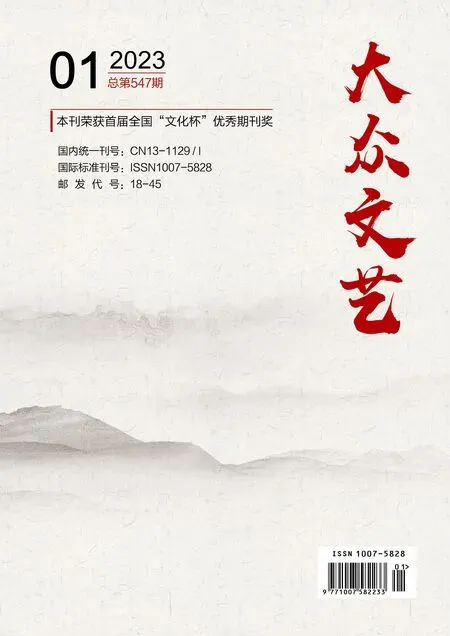论“曾点之境”审美生成的两种路径
刘 璟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1900)
“与点之叹”一事记载于《论语·先进篇》,此则记录了在孔子询问“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后四个学生的回答。在这个对话中,曾点的回答与前三个学生即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回答有明显不同。如果将前三个回答列为一类、曾点的回答列为另一类,前者表达的是以“礼”为最高目标、步步推进的显性政治成就,而曾点之“志”,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129-131在表述上与前三者大为不同。他的回答不再是明显的政治功绩表述,而与个人的某种行为和状态有关。儒家的训诂成果认为,曾点描述的境界是礼乐教化之下的理想政治的形态。比如,三国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中,曾点之行被考据为穿着春服前往沂水进行沐浴的一场祭祀活动。《注疏》曰:“雩者,祈雨之祭名。郑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请雨也’”,[2]176这是考“舞雩”为关于祈雨的祭祀活动。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暮春”是可以展开祈雨的时间,因为“月末其时已暖也”,[3]807“春服”是春季祭祀需要专门穿着的衣物,即“单袷者”,已经可以穿了。“童子”是“童男女舞之”的祭祀舞蹈,“雩”指请求降雨的行为,“沂水”在“鲁城南”,“舞雩台”是进行祭祀的地点,正在沂水附近,“咏而归”是“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2]174在这个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曾点之境与理想政治的关系毋庸置疑。张履详《备忘录》言,“四子侍坐,故各言其志,然于治道亦有次第。祸乱戡定,而后可施政教。初时师旅饥馑,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之世矣,曾晳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与叹”,[4]816从安定国家到阜俗,再从施政教到民生和乐,理想政治一步步到达最高境界即“民生和乐”。以是否认为曾点的行为与实现理想政治形态有关为界,可以概括出对于曾点之境阐释的两种不同的审美发生路径。
第一种路径中,曾点之境的审美质素与“不求为政”有关。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有的认为只有不从政、不追求政治功绩才能达到曾点的审美境界,有的则直接将曾点的境界和庄禅进行连接。皇侃属于第一类。他在《论语义疏》中提出,“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咏之至也。’”[3]811宋邢昺疏中亦言,“夫子闻其乐道,故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之志’,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2]174“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生值乱时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晳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在前文的疏通中,皇侃也已意识到了“舞雩”的礼仪活动性质,[3]807-808但他仍认为曾点的行为只与通过培养德性、顺乎性情有关,与是否建立政治功绩没有关系。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即这些思想家认为想要达到曾般的逍遥境界,必须不从事政治而专注于自身的“澡身浴德,咏怀乐道”。还有思想家将“曾点之境”与隐逸、庄列、佛禅等直接相连,这样的说法在宋代常见。有人认为“曾晳胸中无一毫事”,[5]796这样的说法完全将曾点之境理解为一种与修德、祭祀和礼乐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精神状态。曾点之所以感受到美,曾点之境之所以呈现出美,只是因为他澄心赏景而已。在现代思想家中,李泽厚亦认为曾点的境界可以作为一种出世的精神作为儒士入世精神的互补,[6]92-94这仍是将曾点之境与“为政”分开来论。在第一种路径中,大部分思想家将曾点的精神超越理解为对为政甚至一切凡俗事物的超越,正是因为这种对功利性的摒弃,他可以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到审美愉悦。
朱熹之解可作为第二种路径的代表,即在承认曾点之境与理想政治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一种美善兼具的审美话语。朱熹与皇侃一样关注个人的“澡身浴德”,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求为政”,而恰是将为政、修己与体验“乐”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四书章句集注》基本赞同前代对于字词的训诂,写道:“春服,单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墠树木也”。[1]129-131但在后段,朱子提出了不同于基本训诂成果的新看法,“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对于对谈结束后夫子的解释,朱子说道,“此亦曾晳问而夫子答也。孰能为之大,言无能出其右者,亦许之之辞。程子……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
朱熹的理学哲学体系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但此处的“天”已与孔子时不同,它已经成了“人的天”,天不再和人二分,而成为朱熹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的补充者,使“人”的境界更为阔大。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已经包涵了“天”,也包含了外在世界,更包括了外在的政治事功,这个“天人合一”境界内涵丰富,是真理境界、伦理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的统一。[7]26朱熹对曾点之境的讨论以此为基础,他认为曾点的精神境界中,天地万物无有分别且各得其所,曾点在精神上已经以天理容纳整个世界。他的行为与礼乐祭祀有关,但他不以此为外在约束,而是从本心出发遵从之,这就从一种功利的教化转为了非功利的精神状态。曾点的精神境界之所以是美的,不仅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处于理想政治之中,即所谓“尧舜气象”,还因为他体会到一种“乐”。朱熹的论述以此将道德之善与审美之美相结合。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无论在朱熹的书信或《四书章句集注》拟稿中,他都曾多次提到曾点是“狂士”。圣人人格是朱熹人格美学中推举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即天人合一的伦理、审美境界的完美融合,具有美学意味。[7]442潘立勇认为,曾点之乐是圣人气象的形象化注解,是朱熹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格理想境界中最具美学品格者。[7]420朱熹的人格境界分类中,“才人”即只有某种才能(包括从政才能)的人为最卑下,曾点虽在朱熹注解的几经易稿中被定论为“狂士”,但其主体性质仍然是多层次的,最起码不同或者远胜于只有完成政治事功能力的“才人”。曾点究竟是狂士还是圣人?朱熹认为圣人即“咏先王之风,亦足以乐而忘死矣”,[8]3730“圣人作乐以养性情”,[8]3172这里有三个值得重视的地方,首先,圣人是会修养自己的情性的,其次,圣人以先王的理想政治作为追求目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圣人可以在这些过程中感受的一种“乐”,这种“乐”是一种与生命最高价值有关的“至乐”,甚至可以让他超越现实世界达到“忘死”之境。在《四书章句集注》谈到“曾点之境”一则的定稿中,朱熹即强调了曾点的“乐”,并且认同曾点之境是先王礼乐之治的理想形态。可以认为,曾点的形象是更接近圣人的。而朱熹之所以多次以“狂”形容曾点,则是因为他强调功夫,反对空言,他担心后学者误解曾点之意,只学其胸襟而没有在事功上付诸实践。
对于“与点之叹”一则的阐释材料中,大量提到“乐”并对之进行剖析的情况始于宋代。“乐”是宋代士人、理学家都经常谈及的问题,理学家多言“孔颜乐处”,此则明确提到了“乐”;而“与点之叹”一则原文是并无明言“乐”的,对于曾点之“乐”的重视,是宋代思想家们的独特发现。“乐”是人以自我性情体验到天人合一的审美、伦理之愉悦时的情感表征,对“乐”的重视首先来自对个体情性的重视,例如邵雍认为的终极快乐即是“天理真乐”以及“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的观物之乐。这种“乐”与通过天人合一完成主体的内涵扩大有极大关系,使主体获得了真正的超越性。朱熹在回答严时亨时言,“如曾点浴沂风雩自得其乐,却与夫子饭蔬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襟怀相似,程子谓夫子非乐蔬食饮水也,虽蔬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谓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西改其所乐也。要知浴沂风雩人人可为,而未必能得其乐者,正以穷达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8]2967“孔颜之乐”和“曾点之乐”的最大不同,即颜回箪食瓢饮,从物质上讲肯定是难以“乐”的,而孔子直言“不改其乐”,那这种乐一定是以道为乐。但与“孔颜之乐”不同,“曾点之乐”是确有“吟风弄月”的剩余性的,如果忽略“乐”这种与美丽景致的关联,那点的行为只能僵死为“鲁之禊事”,无法完成阐释重心的转换。宋代人正是因为文化、思想环境的变化,释放出了剩余性,提出了“乐”,发出了前人未有之见,理学家又将之与“天理”之说相连,以“天理”言“乐”,才在理论上完成了兼顾“道”之乐和剩余性之乐的一种“尽善尽美”之“乐”。
朱熹解释“至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时说到,“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至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8]796朱熹认为,个人的“心”与万物(包括人世的和自然的)已经达到了“无无我内外之间”的状态,这时候个人的“乐”也成了天人合一之乐。这种乐须以人的体验为路径,以人精神的“无间”为最终表征,但仍与“乐而得其所”有关。在批评时人的见解时,朱熹曾说,“若夫曾晳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露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晳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8]1374-1375欲求曾点之胸怀气象,不能舍见道分明、各得其所,欲言曾点从容之乐亦是如此。朱熹详细论述了曾点之“乐”,并把它作为一种“尽善尽美”之“乐”。
总体而言,在朱熹处,曾点因为悟到了天理之“真”而体验到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在这种精神境界中,他体验到了一种“乐”,且这种“乐”中有一部分实际已超越了政事功利,成为以天理为思想基础、以风雩为外展表征、以“无物我内外之间”的审美体验为中心的生命之“乐”。总结来说,此种“乐”包含了圣人“与善为一体”,也兼具有非功利的、超越的性质。
朱熹之后,在近代,王国维循着宋代思想家尤其是朱熹和邵雍的路径,有意识地对曾点之境作出了美学阐释。在王国维的论述中,曾点一事可以作为“孔子也行美育”[9]17的例子,其审美精神超越了道德精神而成为第一义的,只是这种审美精神也可以自然地导向一种好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对于曾点之境的美学阐释由于训诂成果的坚实深厚,似乎总不能作单纯的赏景审美之解,而不得不考虑其与理想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朱熹的美学阐释虽为无意识的,但他对曾点之境和曾点之乐的阐释尤为重要,他将道德上的善与审美上的美相结合,为之后思想家有意识的审美阐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