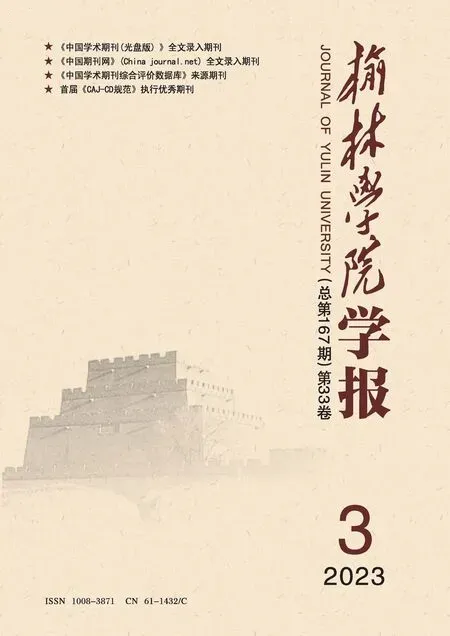空间叙事视阈下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艺术研究1
朱立华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一、引言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聚焦于“现世死亡”转向“虚构死亡”的“死亡叙事”变异、“灵肉合致”转向“灵肉冲突”的“宗教叙事”变异、“唯美意象”转向“唯美偏至”的“唯美叙事”变异、“诗画一律”转向“诗画偏离”的“诗画互文”叙事变异,以及“他者身份”转向“自我身份”的“女性叙事”变异。其中“死亡叙事”变异既是“现世死亡”到“虚构死亡”的转换,亦是“死亡恐惧意识”到“死亡不惧意识”的转化。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是其“现世死亡”叙事的变异,体现了死亡与灵魂永生、死亡与复活共存的传统文化与人类最原始的质朴心理,以及人类对死亡的情感认知与生命悲剧意识,对于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思现代人类的生命悲剧意识,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死亡叙事,即死亡学(Thanatology)与叙事学(Narratology)的交叉研究,是拉斐尔前派诗歌的主要叙事艺术之一。死亡作为叙事的永恒主题(母题)之一,在哲学、美学、诗学、文学乃至医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关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尼采、卢梭、狄德罗、弗洛伊德、伏尔泰和莱辛,都曾进行死亡这一人类最终归宿的多维度哲思。拉斐尔前派诗人斯温伯恩、罗塞蒂兄妹、巴特摩尔以及潘安、阿林汉姆等也都以死亡书写进行叙事。诗人在这些死亡叙事诗中,多采用“现世死亡”转向“虚构死亡(复活)”的叙事变异艺术,对死亡这一终极主题进行虚构的“死亡亲历书写”,即“遗书式”的“虚构死亡”书写,主要包括克里斯蒂娜的《歌,我死之后》《死后》《魂归故里》《天堂映像》《王子的历程》《魂灵的恳求》、但丁·罗塞蒂的《神女》、威廉·司各特的《死亡之后》、斯温伯恩的《生死相依》和《死生相伴》等百余首书写死亡诗歌。其死亡书写中“间接书写”与“直接书写”、外聚焦与内聚集等交叉互构,或以旁观者审视死亡,评述死亡的崇高与不朽;或以参与者“直播”死亡,讲述死亡的经历和感受。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王子的历程》中的公主之死,但丁·罗塞蒂的《神女》中的神女之死,斯温伯恩的《婴儿之死》中的婴儿之死等,通过神圣化或戏谑化的诗意书写,体现了其死亡叙事(变异)艺术魅力。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是其“现世死亡”的叙事变异,变异动因受历史在场、道德建构与宗教介入等现代性生成语境的影响,主要包括“虚构死亡(复活)”对现世“不可抗”死亡的消解、诗人的宗教信仰对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标准的反驳。例如,被贬称为“肉欲诗派”的但丁·罗塞蒂,由于自己的放荡行为,导致妻子西德尔抑郁而吸食过量鸦片后香消玉殒的悲痛内疚,愤而将自己的诗作当作亡妻的殉葬品葬入棺中。之后,为了纪念亡妻,他的创作逐渐由“现世死亡”转向了“虚构死亡”与复活。其诗集《生命殿堂》中收录的《从爱情到死亡》《爱情中的死亡》《爱之死》和《死亡歌者》等,采用隐喻式的“现世死亡”书写,而其名诗《神女》却由“现世死亡”转向了虚构的复活。现世的神女无力抗拒死亡,而诗人采用叙事变异,转向“虚构死亡(复活)”来抗拒“现世死亡”,虚构了亡妻“正立在天庭的围墙之上”,“依栏探出身”,“从天堂依栏的地方/注视着脉搏般跳动的时光/穿越了整个世界。她深邃的目光/奋力穿越前方”(本文所引诗歌译文,均引自作者的著作,篇幅所限,出处不再一一标注),注视着凡尘中的情郎。神女经历了“生死轮回”后得以“飞天成仙”而复活。克里斯蒂娜由于宗教信仰而两次失去爱情,她的叙事模式也逐渐转向了“虚构死亡”书写与复活,诠释了“变体复活”与“灵魂永恒”思想。克里斯蒂娜的《魂灵的恳求》与《神女》的叙事主题相似,只是叙述者由“情郎”变成“爱妻”,叙事空间由“天上”变为“地下”。亡夫罗宾的魂灵午夜归家,“闪身飘入屋中央”,“浑身冰凉,像寒夜的露珠一样,面色苍白像羊圈里的迷途羔羊”,恳请爱妻不要“哀啼”,不要“悲戚”,使他在地下“无牵无挂,可以安息”。总之,死亡叙事变异艺术,首先开辟了死亡学与叙事学交叉研究的新路径,更新了死亡叙事模式,拓宽了诗歌透视视阈;“由死变活”的转向,延续了生命的存在感,实现了人类永生和不朽的美好愿望。其次,升华了死亡主题,重写了死亡的崇高和超越,体现了不惧死亡的“出世”境界。再次,拓宽了叙事空间,导入了历史在场与宗教、伦理介入等元素,助推了人类死亡伦理困惑的消解。最后,透视了战争、死亡与和平三者的交互关系,提出其诗歌死亡叙事忽略“和平”元素的偏误。
二、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
“虚构死亡”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中西文化普遍存在的死亡复活叙事主题。中国文化强调生命永恒,长生不老、肉体成仙、生死轮回和涅槃等美学思想,而西方文化注重肉体死亡与灵魂永生、死亡与复活的交互,“生死轮回”“变体复活”“灵魂永恒”“飞天成仙”等美学思想。例如,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认为,人类早期的死亡问题总是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凭借古老的“灵魂”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宗教、神话的形式拒斥死亡。卡西尔也认为,整个神话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原始宗教神话关心的,与其说是死亡,毋宁说是不死,神话就是关于不死的信仰,是对死亡复活的理性思考[1]。
空间叙事是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死亡叙事艺术之一,其理论的生发、流变、表征,及其文学审美功能,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加布里埃尔·佐伦(Gabriel Zoran)、约瑟夫·凯斯特纳(Joseph Kestner)、鲁思·罗侬(Ruth Ronen)和方英等国内外学者对空间叙事理论进行了多维研究和译介[2]。空间理论是由传统“时间”叙事,扩展到“空间”叙事的一种“空间转向”(当然“时空失序”也属叙事策略),拓展了叙事学研究、文学创作与审美的路径。叙事空间理论下解读拉斐尔前派诗歌,为其诗歌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文本叙述层。天堂与天国、冥府与地狱、墓地、家园等叙事空间的人为建构,实现了空间与诗意文学接轨,赋予了天堂、冥府等虚构空间更多的人文内涵,升华了死亡主题。叙事空间通过作家的创作空间、作品的艺术空间、读者的接受空间“三分法”(类似于“接受美学”理论),使文本内部的横向语境和文本外部的纵向语境之间产生对话和交流,在作者、作品的原有意义上增加了读者的审美意义,拓展了死亡的内涵意义。
(一)“虚构死亡”叙事空间:天堂与天国
拉斐尔前派诗人采用“遗书式”的“虚构死亡”模式进行死亡叙事。依据伊壁鸠鲁的观点,“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已不存在了”,死亡和存在是排他式补充分布,永远没有共现关系。换言之,一旦死亡,人就不存在了,一个人不可能以内聚集的叙事模式,“直播”自己的死亡经历和死亡感受,而只能进行“遗书式”“虚构死亡”书写。倘若有一种模式:“存在——死亡——再存在”,那么这个“再存在”的生命就能够“亲历书写”自己的死亡体验和死亡经历,甚至还可以描述别人妆扮自己尸体的场景(如克里斯蒂娜的短诗《死后》)。现代科学早已证明,“再存在”是荒诞的悖论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再存在”,也就是“复活”,只能存在于虚构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科幻小说之中,这正是“虚构死亡”叙事产生的理据,是一种死亡复活与神话故事相生相伴的文化现象。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文本细读发现,其“虚构死亡”诗歌多取材于《圣经》故事,以天堂与天国、冥府与地狱、墓地、家园或其他场所作为叙事空间,进行“虚构死亡”叙事。以天堂与天国为“虚构死亡(复活)”叙事空间的诗歌,主要包括但丁·罗塞蒂的《神女》、斯温伯恩的《冥后的花园》、克里斯蒂娜的《天堂回响》等数十首。
但丁·罗塞蒂在《神女》中,虚构了一个恋人死后升天,进入天堂复活的“故事”:天堂的金栏杆黄澄澄,/神女依栏探出身。/幽幽的双眸比平静的潭水更深。/三朵百合手中捧,/七颗星星发间缝。……她正立在天庭的围墙之上。/那是上帝跨越无比的深邃/建立的天与地的分界。/高高地,她从那儿俯视,/几乎看不到太阳。/那是立于天宇,/跨越天地洪流的天桥。/天桥下,交替着白昼与夜晚,/光明与黑暗作为交替的边缘。/天地间的空旷,低垂到地球像/焦躁的小矮人一样旋转的地方[3]。诗人在《神女》的第一部分中,以天堂作为叙事空间,讲述了一位升天少女依栏俯视凡间情郎的“故事”。这个肉感而又神圣的可爱少女幻象,是根据诗人画笔下的贝亚特丽采的形象塑造的。这是一个不断萦绕在他脑海中的绘画创意人物。他将女人的“灵”与“肉”理想化,与她们保持距离,将她们作为渴望和崇拜的对象。哈里·布拉迈尔斯认为:“《神女》是文学中的中世纪精神的一幅富丽堂皇的织锦画。在这幅画中,超脱人间的秋水伊人‘从天堂的金栅(作者译“金栏杆”)’里探出身来,希冀看到留在尘世的郎君。如果说她手里的三朵百合花和她头发里的七颗星带有理想化的但丁式象征主义表征,那么其他形象的感官性却把我们带回到现实世界的色彩和温暖中。”[4]
《神女》是但丁·罗塞蒂“虚构死亡(复活)”叙事的代表作,是为纪念亡妻西黛尔而创作。诗人虚构的叙事情节为一位手捧百合、头戴玫瑰、发缀星星、金发飘飘、长袍飘逸的升入天堂的少女,尘缘未了,依着天堂的金栏杆,深邃的目光穿越了天地之界,久久凝望长空,幻想着凡尘的情郎来相会;叙事空间主要是天堂,包括天堂的金栏杆、天庭围墙、天宇、天桥及圣母玛利亚居住的小树林等。诗人采用内聚焦叙事视角,运用通感、隐喻、象征等叙事语言,色彩、声音等感官意向繁复鲜明,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虽阴阳两隔,但鲜见凄婉、哀怨或伤悲,而多见炙热的情感与爱情的渴望:叙事对象升天的神女,依着栏杆,幽幽明眸俯视凡尘,渴盼情郎现身。诗人极尽想象之能,构想出非常宏大的空间,地球都成了小矮人。诗人通过“虚构死亡(复活)”叙事模式,让肉体已死的少女,在天国得以复活。天国神女对人间情人的恋情,把人性和感觉的自然色彩与神性和幻觉的神秘色彩融为一体,完美再现了天地之爱的融合。在《神女》的第二部分中,仍以天堂为叙事空间,对神女灵魂升天进行复活与爱情书写。生命与爱情都可在天堂复活,体现了“死亡不惧意识”和生命永恒思想。《神女》的第三部分转为外聚焦叙事视角,用独白的叙事话语,进行爱情书写。诗人虚构了神女天堂再会情郎、倾诉衷肠的美好爱情愿望。天上的灵与地上的肉、凡尘的肉体与天国的灵魂完美统一,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和谐一致,体现出但丁·罗塞蒂的“灵肉一元”的哲学观。
拉斐尔前派诗歌中圣经故事居多,希腊神话较少。天堂这一文化意象是常见的叙事空间,是复活的最理想宫殿。但丁·罗塞蒂铺设的叙事空间——天堂,作为故事内人物角色移动与生活的环境,直接参与了叙事对象、情节和主题等意义生成的过程。首先,作为物理空间,天堂是叙事对象神女、玛利亚、侍女等的活动空间,是她们的行为或故事情节的物理发展场所或存在空间,是她们存在和故事发生的实际环境或潜在的环境,也是一种叙事结构。其次,作为心理空间,天堂的空间和其诗意的文学性接轨,变成一种抽象的精神空间,是作者与读者的心理空间的投射。天堂不仅是空间,更是赋予了文化意义、文化价值的“空间”。天堂是死后要去的地方,是“彼岸”,那里没有生命的无常、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是神与灵快乐生活的地方。因此,死亡并不恐惧,而只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是身体朽坏而灵魂得到自由后脱离身体的枷锁,离开尘世、回归天上永恒故乡轮回。这种理论对人类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天堂不只是活动的空间,而是“乐园”。天堂作为社会空间,是作家对人物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描写呈现,被人为建构,赋予了权力、阶级等社会意义。天堂经过人为建构,拓展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意义。
克里斯蒂娜在《基督、圣徒和圣灵的对话》中,虚构了天堂叙事空间,通过基督、圣徒和圣灵在天堂的对话,对死亡复活进行诗意书写:病态的欲望使我面色苍白,/因为我的心已经离开,/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微弱火光,/这个世界正渐渐地走向衰亡。/在梦中我的心已穿越/这个恼人的病痛世界,/来到阳光倾泻的地方,/在永恒的山上。/圣徒说:“那里的天使让我们得到/慰藉、圣洁与荣耀。/我们安息在耶稣那里,/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我无法得到真爱,/也无法逃避死亡。/希望和欢乐不再,/虚名却在嘲弄我。/我最爱的人已死,/但我不能随他们去死。/圣徒说:“死亡不会让我们消亡,/而是让我们长眠的地方充满荣光,/耶稣让我们长在,/而他曾为我们而死。”/哦,我的圣灵拍打着翅膀/飞向/永恒的地方。/在天堂,/她萎靡不振,几乎昏厥倒地,/这对我还有什么意义?……”[5]这首诗的叙事对象为圣经故事人物基督、圣徒和圣灵;叙事情节:在这个逐渐走向衰亡的病痛世界里,“心”已死亡,肉体已死,灵魂复活,在梦幻中穿越到阳光倾泻的地方,到永恒的圣山上。而到了圣山之后,人们就能得到慰藉、圣洁与荣耀。借圣徒之口,表达诗人自己在现实世界的无奈,灵魂“既无法超越其上,又不能待在下面”,无处安息,没有归宿。“我无法得到真爱,也无法逃避死亡”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信仰使其失去真爱,病痛使其无法逃避死亡。希望和欢乐在哪里?在天堂,在那里灵魂得以安息,心灵才有归宿,因为那里耶稣和“我”同在。“死亡不会让我们消亡,而是让我们长眠的地方充满荣光”表达了拉斐尔前派的“死亡不惧意识”:不惧死亡,灵魂复活,随耶稣去到更加美好的天堂。《无名的莫娜》第十一首,也是克里斯蒂娜以天堂作为“虚构死亡”叙事空间的爱情组诗,叙述者采用内聚集叙事视角,虚构了“生离死别而重逢无望,人世间无望,又不见天堂”的死亡而灵魂又找不到天堂的故事,但爱情会“穿过死亡的门廊”而复活,爱的力量也会感动上帝,灵魂终究会升入天堂。
拉斐尔前派诗歌中,以天堂作为“虚构死亡”叙事空间的诗歌占比虽不是很大,但它是对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学研究的尝试与开拓。叙事空间理论的导入,在传统作者、作品与读者的研究范式中,融入了“空间”概念,特别是心理和社会空间理论的导入,使原有意义获得了“增值”意义,体现了天堂空间研究的实用价值。
(二)“虚构死亡”叙事空间:地狱与冥府
叙事空间冥府,也是一种死亡文化意象,常出现在宗教寓言和神话故事之中,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西文化的死亡复活叙事中存在一个共同现象:神在天上,鬼在地下。西方文化的地狱、冥府、冥王哈迪斯、冥后和各式鬼怪,类似于中国文化的阎罗殿、冥府、阎王、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这些文化意象都与死亡相关,是常见的死亡叙事空间或叙事对象。和天堂一样,冥府也是常见的虚构死亡叙事空间。诗人很清楚所谓的天堂或地狱根本不存在,但他们还是通过“虚构死亡”意象,表达美好愿望,探究超越死亡本身的死亡意识和生命价值。事实上,死亡意义的深度思考和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是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精神传统。文明进步的局限性导致很多死亡之谜难以破解,现世人生难以拯救,只能借助神灵拯救人生。人类先祖将目光投向神秘的宗教和美丽的神话传说,用“虚构”方式寄寓永生,抵抗死亡,最终孕育、催生了宗教寓言与神话故事,如图腾文化、天体神,与人同形同性之神等。宗教与神话表现为混沌、界墙、神谱、神示、死亡之箭(时间),以及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形式,认为“死亡就像睡熟一样”并不恐惧[6]。拉斐尔前派诗人克里斯蒂娜、斯温伯恩等都曾以冥府为叙事空间,进行“虚构死亡”叙事。斯温伯恩在《冥后的花园》第一部分中构建的叙事空间:冥府,是个没有感情思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存在体。那是个“整个世界一片寂静”“什么风儿也不吹,什么东西也不长”的空间,一切都“消失在梦幻般的梦幻中”,没有播种,没有收获,没有眼泪,没有欢笑,因为叙事者“我”讨厌俗世里的“欲望、梦想和权力”,“什么都不管,只管睡觉”。这里没有“美”,只有“丑”与“恶”;只有“破船幽灵”“不开花的罂粟,冥后的绿葡萄”,以及冥后“为死人酿出了葡萄酒。”因此,冥府叙事空间所孕育的“故事”主题只能是死亡、虚无、失望、破灭,是“丑”与“恶”美学思想的表征。在《冥后的花园》第二部分中,斯温伯恩表现出明显的颓废主义诗学特征。这里生活的“鬼们”犹如幽灵,“天堂地狱找不到伴侣”,“生活总伴着死亡”,“收集一切将死的东西”,“等候着每个赶赴黄泉的人”。这里安全凋亡,只留死去的岁月和灾殃。诗人以冥府的“鬼魅魍魉”为叙事对象,虚构了戏谑化的荒诞“故事”与“情节”。《冥后的花园》作为斯温伯恩的一首名诗,通过叙事视角在叙事人物“我”“冥后”和“我们”之间切换,将宗教意象、神话和历史意象群、有形意象群和无形意象群等多种意象组合,形成意象系统进行意象叙事。诗人构建出一个死人活动的场所、一个死气沉沉、阴森恐怖、毫无生机的“虚构死亡”叙事空间:“冥后花园图”。冥府在希腊神话中,是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而飘去的地方。虽然冥府里的灵魂和主人生前看起来一模一样,但灵魂是没有思想、没有欲望、没有记忆的非实体[7]。诗人通过“虚构死亡”叙事空间,显示出反讽、荒诞和戏谑化等后现代主义糅杂颓废主义表征。这种“丑学”或“以恶为美”的美学思想也存在积极元素,如积德行善,恶有恶报,或“死后下地狱”等警示作用。
(三)“虚构死亡”叙事空间:墓地、家园与其他
西方死亡叙事主题主要包括死亡与惩罚、死亡与宿命、死亡与抗争、死亡与荣耀、死亡与爱情的勾连,体现出生活的本真快乐和生命的价值。墓地或墓园、魂归的“故里”或家园、闺房,同样承载死亡的文化内涵意义。在拉斐尔前派诗歌中,诗人以“墓地、家园”等作为叙事空间,进行“虚构死亡”叙事。墓地、家园等变成叙事空间,就意味着参与了“事件”的构建和意义的生成,显示出其背后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
第一,死亡叙事空间:墓地(坟墓、坟头)。拉斐尔前派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由于受到了自身疾病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也受到基督教天堂论和基督教死亡美学观的影响,最擅长以死亡作为叙事主题,进行“死亡亲历书写”。她在《歌(我死之后)》中,以墓地的坟头为叙事空间,采用了“遗书式”的“虚构死亡”书写进行死亡复活叙事。女诗人向“亲爱的”留遗言:不要为我唱挽歌;不要在我坟头种玫瑰,不要松柏青翠,只希望自己的坟头青草萋萋,沐浴雨露,不在乎自己是否被记得或遗忘,体现出诗人的“出世”境界与“死亡不惧意识”。其短诗《没有婴儿的婴儿摇篮》《我可否忘记?》等,也是以坟墓、坟墓与天堂的组合为叙事空间。
第二,死亡叙事空间:家园(故里、闺房)。拉斐尔前派诗歌有近百首以家园(故里、闺房)为虚构叙事空间,以“魂归故里”“午夜返家”“闺房妆尸”等为叙事情节,进行“虚构死亡(复活)”叙事。其诗歌主要包括克里斯蒂娜的《魂归故里》《逗留》《死后》,斯温伯恩的《婴儿的死亡》等。克里斯蒂娜在《魂归故里》中,发掘叙事空间家园的文化内涵意义,寻求安置灵魂的精神家园。叙述者以内聚焦叙事视角,透视一个没有归宿的飘荡游魂。叙事情节:“我”死之后,我的灵魂要返回那个我曾在里面逗留的房屋,经过门口时,看见昔日的朋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浅笑低唱,欢闹嬉戏,畅想未来。而自己飘然逝去,凡胎肉身逝去之后,化作一缕魂魄,灵魂回归故里,但只能在家门外徘徊,瑟瑟发抖。“留,我心已碎;去,我心不忍!”,灵魂无法得到安置的凄婉哀怨,感人至深,作者翻译此句时,也不禁潸然泪下。
找寻安置灵魂的家园,探究生命的价值,依然是一个文学研究课题。克里斯蒂娜的《逗留》也是有关灵魂为爱所困,四处游荡,找寻安置家园的故事:她“饥渴的灵魂将远方的人儿伫望”,她的灵魂“仿佛初次嗅到的气息来自天堂”,自己的“灵魂倍感舒畅”。女诗人将死亡、复活、灵魂、永生等文化意象并置,进行“虚构死亡”与复活叙事:他们用鲜花和花瓣熏香了我的卧房,/熏香了我安息的睡床;/但我的灵魂,为爱所困,四处游荡。/我听不到房檐下鸟儿的呢喃,/也不闻麦捆间刈割者的笑谈:/只有我的灵魂整天在守望,/我饥渴的灵魂将远方的人儿伫望:/……仿佛我灵魂初次嗅到的气息来自天堂;/仿佛缓慢的时间初次闪耀金光;/缓慢的时间首次变得金黄;/我感到我的发丝罩上荣光,/我的灵魂倍感舒畅[8]。
第三,死亡叙事空间:其他空间。拉斐尔前派诗人还构建了其他叙事空间,进行死亡叙事,书写死亡意识下的死亡困惑、焦虑、超然、崇敬、冥想,重写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探寻,实现死亡形而上的超越和对生命价值审美意义的升华。在《妻子告别丈夫》中,克里斯蒂娜用“遗书式”的“虚构死亡”叙事模式,讲述妻子向丈夫告别的故事,再现“死亡不惧意识”,反复强调“我必须去死”:……别了吧。我必须漂洋过海,/我必须埋入雪中,/我必须去死。/……别了吧。我必须妆扮好自己离去,/尽管没有充分准备,/我必须去死。/……别了吧。/你抓着我手,泪水长流,/但我必须走,/我必须去死。/……别了吧。/你必须留一缕青丝,/你必须善良仁慈,/我必须去死。/……别了吧。我俩必须别离,/死亡如此真切,我必须去死[9]。
但丁·罗塞蒂的《新生的死亡(2)》也通过死亡叙事,诠释生命与死亡的真谛,表现面对死亡的超然与豁达,决心“把所有死亡的念头抛向风中”。克里斯蒂娜的《生死之间》,同样采用其他叙事空间进行死亡叙事,感叹生死无常,体现人类对死亡的原始质朴心理。当然,否定死亡、超越死亡、获得新生已然成为一种价值趋向:死亡不再狰狞恐怖,而是一种毁灭的美的诗意,一种宁静的死的美感,是现世人生苦痛的解脱,是又一个美好生命的开始。
三、结语
“虚构死亡”的叙事视角可以选取叙事空间,当然也可以选取叙事时间、叙事主题、叙事人物(对象)或叙事者等。叙事空间视阈下的“虚构死亡”叙事的核心思想是“死亡不惧意识”,即死亡意识二元性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另一性为“物质世界的普适性”,是人类对于死亡最原始的认知和体验,表现为“死亡恐惧意识”),体现出作家在精神层面对死亡的独特认知:死亡是美好的、自由的、崇高的,表征为“死亡不惧意识”,注重死亡意识的审美意义。拉斐尔前派的“死亡不惧意识”,与其所处的现代性生成语境密切相关。其“尚古”与中世纪情结,导致其诗歌很多都是对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的重写。例如,克里斯蒂娜的死亡叙事诗歌,没有绝望的情绪,没有描写扭曲的身体、痛苦的挣扎,也没有表达死亡的可憎、死亡的痛苦、死亡的恐惧,反而礼赞死亡,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消亡,而灵魂不灭。生命换成另一种形式出现,死亡并不恐惧,反而是肉体苦痛的解除,诗歌中表现出的就是死亡不惧意识。在《甜蜜的死亡》中,她以美学意象“花”为切入点进行死亡书写。她眼中乐观的、明艳的“死亡”,是“不惧死亡”的、超然“出世”境界的写照。在《莎孚》这首诗中,女诗人认为死亡远胜于不停地哀悼与叹息,死亡可以摆脱沉重的躯体,忘却所有苦痛和忧伤,体现出作者不惧死亡的超然境界。克里斯蒂娜所体现出的死亡意识具有独特性:死亡是新生命的起始,现世的肉体死亡反照来世的精神复活,世俗的死亡反衬灵魂的不灭。
综上所述,空间叙事视阈下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既是叙事主题的升华,也是死亡崇高与死亡“出世”境界的重写,为拉斐尔前派诗歌死亡叙事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文本叙述层,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与文本支撑,开拓了新的叙事模式与研究路径。当然,死亡叙事变异研究本身是个较大的课题,希冀将来进一步研究时,可发掘出更加科学的视角来深度思考死亡复活与伦理困境、灵魂安置和文化生态等问题,不断完善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研究也表明,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死亡叙事也存在不足:忽略了和平因素。拉斐尔前派诗人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战争带来的死亡与肉体苦痛、心灵创伤与主体性分裂,以及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哲思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观照。但是由于拉斐尔前派诗人的个人视野、所处历史的局限性,忽略了战争、死亡与和平三者的交互关系中和平的重要因素,忽略了和平对于人类现实生存状况改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