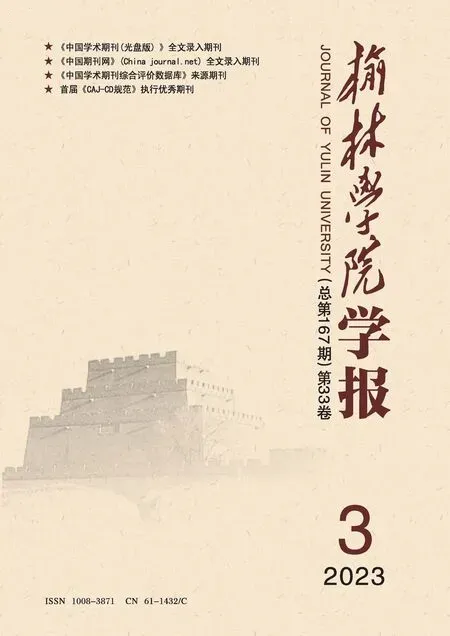抗战时期榆林地区戏剧活动探要
刘耀辉,孙元杰
(青岛科技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引言
戏剧活动是抗战时期陕北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文艺活动。因为与其它艺术活动相比,戏剧无论是在传播方面还是在观众的接受方面,当时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般来说,当论及陕北戏剧活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陕北戏剧活动时,大多学者往往以革命圣地延安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是由于延安革命文艺活动中心的地位使然。但若要建构抗战时期陕北戏剧发展史,则同属陕北的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亦不可忽略。而在学术研究趋向“去中心化”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对长期以来被延安所遮蔽的榆林地区戏剧活动的基本样貌予以揭示与探究。本文的出发点即在于此。
榆林地区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南与延安地区相接,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北靠内蒙古,现辖12个县市区。1935年,国民政府在榆林设立了陕西省第一行政区,由高双成率领的第86师驻防。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大量晋、绥部队溃退到榆林。为协调各方关系,蒋介石令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赴榆林,后任命其为21军军团长,军团撤销后,又任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是中共旧交,政治上较为进步。加上榆林自身对中共控制的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依赖,故而邓宝珊在军事、交通、物资等方面都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与延安方面也更为密切[1]。因此,在抗战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榆林地区处于抗战的后方,为戏剧活动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考察该地区在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可见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秦腔、晋剧、陕北道情、陕北秧歌等传统戏剧的展演,二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剧的演出。二者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各不相同,但都展现出了这一特定时期戏剧活动特有的思想属性与审美样态。以下谨就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形态、戏剧革新及其价值与意义进行论析,以期为进一步深研榆林地区戏剧活动史提供一块垫脚石。
二、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形态
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戏剧活动整体表现为传统戏剧继续发展的同时现代戏剧开始发生、勃兴。二者间相互交融,彼此激发,共同促动形成了榆林地区戏剧活动的新局面和新形态。
(一)榆林地区传统戏剧的延续与发展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榆林地区远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传统曲艺的萌芽,拥有悠久的戏剧传统。到西汉时期,榆林地区已发展成为“歌舞百戏之乡”。据统计,这里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所反映出的歌舞百戏有:乐舞图、鞬鼓舞、七盘舞、相和歌、清商曲、可采莲、巴渝舞等。其中的“七盘舞”画像石出土于绥德的一座汉墓,已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戏剧特征——“上有一鼓八盘,分三行排列,舞者着长袖罗衣,登盘表演;另一舞者头戴尖顶帽,为侏儒形象,似在插科打诨,作风趣表演”[2]。可见,溯其本源,榆林地区的戏剧传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戏曲艺术风貌。

陕西剧种流布图[3]
据《陕西剧种流布图》可知,榆林地区的传统戏曲剧种包括但不限于赛戏、陕北道情、陕北秧歌、二人台、秦腔、晋剧。这些剧种有的是在三秦大地广为流传的剧种,也有的是在与其它剧种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剧种。相对于陕西省内其它地区而言,榆林地区的剧种并不丰富。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外来剧种的山西晋剧,在陕西省内却是榆林地区所独有的。这里选取几种榆林地区代表性的剧种,对其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变化略作梳理。
赛戏。据佳县文人沈世昌口述,在道光年间佳县县城内就已经有赛戏演出,流行于陕北佳县、吴堡、清涧、子长、子洲、米脂、绥德等地,其演出内容以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主。榆林地区原本各地都有赛戏班子活动,到辛亥革命后,就只剩下了王家班一家还在演出,而等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建成后,赛戏的演出活动便完全停止了。这是因为赛戏本是在迎神赛会中演出的,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故而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发起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被废除[4]。
陕北道情。其产生没有明确的记载,仅有不同的说法。《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提到,陕北道情最早出现于清涧县东解家沟的玄武村,故原名为“清涧道情”,其剧目多为道教故事、历史故事、生活故事[5]。1935年,红军进驻陕北后,为配合革命宣传,陕北道情融入时代的内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据《清涧县志》记载:“1944年春节,清涧县18班秧歌于县城会演,乐堂堡秧歌队演出《做军鞋》等4个道情戏,受到嘉奖。”[6]
陕北秧歌。由宋金古墓出土的秧歌砖雕可知,陕北秧歌的舞蹈形式早在宋金时期便广为流传。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秧歌在榆林地区的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等地都有流行,其传统剧目多表现男女之情、生活情趣。同样地,到了抗战时期,传统秧歌剧经过改造,开始表现新人物、新生活,著名的《兄妹开荒》便是新秧歌剧的典型代表[7]。
晋剧。榆林地区是山西晋剧在陕北传播的核心区。“晋剧一词原是整个山西省所有剧种的统称,后来又成为山西省北路、中路、蒲州和上党这四大梆子戏剧种在山西省以外的共用之名。”[8]流行于榆林地区的晋剧主要是指中路梆子,其演出剧目多以古装戏为主。据《绥德县志》记载:“民国初年,县城一些能拉会唱晋剧的民众每逢年节自发组成‘自乐班’唱‘乱弹’。”[9]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山西战乱频仍,“晋剧名角如太古三子、元宝黑、十三红、狮子黑、明亮子等数十人从河东(山西)逃难至本区,搭班演戏”[10]。上世纪40年代以后,榆林地区本土的戏剧工作者也开始建立晋剧剧团。例如“木头峪村俱乐部”于1940年9月成立于佳县木头峪村,又如清涧县接管黄锡厚的山西晋剧班子成立了县晋剧团。
秦腔。秦腔民间俗称“大戏”,盛行于陕西的关中、商洛、汉中等地,也在榆林地区流行。据《榆林市志》记载:“民国初年,驻清涧县井岳秀部石谦旅长所领的秦腔戏班常来本县演出。因石谦腿拐,故群众称其戏为石拐子的戏。”[11]抗战时期,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部携带秦腔班入驻榆林。后来,榆林地区的各个剧团纷纷开始进行秦腔改革运动,为配合抗战而进行宣传演出。如1940年由延振伦发起成立的秦腔剧团“绥德民众剧社”,演出了自编现代戏《好男儿》等剧目[12],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综上,榆林地区的传统剧种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并没有形成如山西晋剧那样的大剧种,且在抗战初期还曾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表演形态,如赛戏。但正因其传统戏剧活动在榆林地区被很好地保留下来,才使得当陕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时,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建立以后,除上文提及的剧种外,眉户戏、碗碗腔、蒲剧、京剧等传统剧种也在本地区发展起来,并同样结合时代需求注入了新的革命内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陕北道情还是传统秧歌剧,在抗战中都被作为强有力的宣传载体,成为向民众宣传革命、传播抗战救国思想的有力武器。
(二)榆林地区现代戏剧的发生与勃兴
自19世纪末开始,一种以对话为主的现代戏剧样式伴随着西方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到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话剧天然拥有进步的思想文化特质。榆林地区较早地接受了话剧的影响,在话剧定名之前就开始了话剧演出活动。这主要得益于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子洲的大力推动。
李子洲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参加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1923年初,经李大钊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从北大毕业回到陕西,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秋,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榆林学院)校长。当时榆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若要强,扛钢枪。强上强,上学堂。”这里的学堂指的就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3]。李子洲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教育同改造社会的任务相结合,大力在群众中发展革命组织,以此传播革命火种。承载着革命宣传重任的话剧活动,随之在榆林大地开展起来。
在李子洲、魏野畴、王森然等共产党员教师的组织推动下,榆林中学早在1923年即成立了“文艺演习会”,排演革命话剧。这个戏剧团体以学生为主,先后自编自演了十多部话剧,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4]。其演出的如《孔雀东南飞》《麻雀和小孩》《可怜闺月里》等剧目,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大大促进了新文化在本地区的传播。
1938年11月,国民党内部派系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榆林总队”被撤销,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与历史教员高伯定将其改建成“三民主义青年团榆林中学区队”。该组织以宣传三民主义理论、国民党政府政策为主要任务[15]。三民主义青年团也通过话剧宣传抗战救国的思想。如在1939年冬,该组织联合榆林中学、榆林师范组建“长城剧团”,演出《国家至上》《夫与妻》等进步话剧,在宣传抗战理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戏剧在榆林地区的传播。
应该说,当现代戏剧在榆林地区发生之时,就与强调娱乐功能的传统戏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主要功能在于宣传新文化与新思想。这与话剧本身自带的新文化特质是分不开的。话剧凭借自然灵活的表演形式,逐渐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到抗战时期发展成本地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
除话剧之外,到抗日战争末期,“在革命战争时期由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传授给榆林地区的一个新剧种”[16]——歌剧也开始活跃。1945年,绥德分区文工团成功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正式拉开了榆林地区上演歌剧的序幕。该剧剧情与其自身的歌唱特质均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上演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红军长征结束后党中央进驻延安,到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再到抗战结束,承载着革命宣传内容的以话剧为主的现代戏剧艺术形式逐渐在榆林大地站稳了脚跟,并蓬勃发展起来。与传统戏剧不同,榆林地区的现代戏剧在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大都依靠剧团进行巡回展演。1937年7月,在党的领导下,定边县民众教育馆成立业余剧团。与此同时,佳县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觉民剧团”。1938年,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和榆林女子师范学校三校师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大时代剧团”,演出自编话剧《沪战一角》等。该剧团除了在榆林城内公演,还利用假期外出演出,曾在米脂县与八路军第359旅的“峰火剧团”交流学习,排演了《松花江》《夜光杯》等节目。此外,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警备三旅的“边保剧团”、三边专署民众教育馆的“七七剧团”“绥德分区民众剧社(团)”、米脂县的“大众剧社”“群众剧团”、清涧县的“县晋剧团”、安边县的“业余剧团”等,都是这一时期活跃的戏剧组织。这些剧团的演出剧目十分丰富,有《大家喜欢》《两亲家打架》《睁眼瞎子》《穷人恨》《保卫和平》《状元媒》《打金枝》《金玉奴》《玉堂春》《河伯娶妻》《四进士》《红娘子》《打渔杀家》等[17],既有传统戏剧也有现代戏剧,涵盖秦腔、眉户戏、京剧、秧歌剧、话剧等多个剧种。
综观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可见传统戏剧活动在抗战时期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话剧等现代戏剧随着各个进步剧团的巡演也开始在榆林地区勃兴,对抗日革命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革新
西方话剧在传入中国之初,便成为宣传新思想、开启民智的重要载体。其时中国的传统戏曲已经变成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玩物”,其发展趋于停滞。面对这种窘境,一批先进的有识之士期望引入西方的话剧来打破局面,使中国戏剧重现焕发生机并承担起教育民众的功能。但受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才在曲折的发展中达到成熟[18]。彼时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汪仲贤曾说:“我们借演剧的方法去实行通俗教育,本是要开通那帮‘俗人’的啊,如果去演那种太高的戏,把‘俗人’通统赶跑了,只剩下几个‘高人’在剧场里面拍手掌‘绷场面’,这是何苦来!”[19]在这种背景下,要完成宣传抗日革命思想这一时代任务,就必须高度重视传统戏剧相对于西方话剧的优势,充分依靠其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推动其与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有机融合,来实现理想中的戏剧革新。榆林地区当时的戏剧实践,亦是这样一番情景。
在抗战时期的榆林地区,很多剧团依旧以演出传统戏剧为主,如绥德民众剧社只上演秦腔,绥德群众剧团则主要演出晋剧,兼演秧歌剧。传统戏剧既然仍是能够有效吸引大众的艺术形式,那么如何将传统戏剧加以改良革新,便成了摆在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
戏剧革新的底层逻辑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林地区的戏剧革新是针对传统戏剧而言,指在传统戏剧的民族性特质中融入现代性,并发挥出戏剧的功能性。这既是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需要,也是适应戏剧艺术本身发展规律的必要。通常,戏剧工作者会利用旧有传统戏剧的形式,融入抗战救国的时代精神,使得传统戏剧在新的时期焕发新的生机。正如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发表于《团结》杂志1939年第12、13期上的文章所说:“我们的戏,内容是抗战的故事,有头有尾,唱的是秦腔,老百姓完全熟悉,这当然也是我们受到热烈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20]
(一)陕北戏剧变革的先声
在榆林地区戏剧革新运动蓬勃开展之前,这里就已曾吹过戏剧变革之风。早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李桐轩、孙仁玉等人便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创办了陕西易俗社,这标志着陕西戏曲改革的开始。该社招收戏曲学徒,利用秦腔编写新曲,以启蒙大众,改良社会风俗。
国民政府在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主要由随军剧团承担,主要演出传统以及新编的秦腔剧目。1936年,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部驻防榆林,易番号为第22军。该部原有的“秦腔化装讲演团”也改名为“二十二军新剧团”,成为榆林地区第一个正规的秦腔表演团体。一年后,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新编第十一旅驻防安边,其随军剧团的演出剧种也是秦腔。此外,还有国民党军骑六师、驻神木758团的随军剧团都是以秦腔为主的剧团,也都是以秦腔为主的剧团。这些随军剧团的服装、道具等方面都是相当优良的,且吸收了一部分易俗社的成员。他们亦曾尝试对秦腔进行改革,如京剧武功教练杨青山在加入国民党二十二军新剧团后,就曾将京剧中的优秀打戏以及铁把子戏如 《铁公鸡》《水淹七军》《西皇庄》等剧目移植到秦腔剧种中去[21]。这种尝试虽然在丰富秦腔剧种、提高演出水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只是停留在表演形式上,并未能深入起到戏剧革新的作用。客观地看,虽然易俗社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再努力用新的方法编写剧本,宣扬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但也有着局限性——在戏剧的大众化尝试中脱离了现实的要求,虽显现出了一定的功能性,但因忽视了戏剧活动背后的阶级基础而导致戏剧部分丧失了生命力。
(二)榆林地区的新秧歌剧运动和“翻身道情”
国统区的戏剧改良并没有触及到戏剧革新的实质,反观解放区,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大众、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根本方向。1943年3月,中央文委会就戏剧运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确定了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引下,陕北的戏剧工作者大力对秧歌剧、平剧、秦腔等旧剧种进行革新。榆林地区的各个剧团自不例外,也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在对传统剧种秧歌剧和陕北道情进行改良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产生于古代社火祭祀的秧歌,是陕北地区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样式,往往在春节期间进行盛大演出。剧作家们发挥秧歌艺术那锣鼓伴奏大气、剧情紧凑单纯、唱词明快风趣等特点,将这种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内容后,创造出了具有时代性的新秧歌剧。新秧歌剧大都集中反映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内容,重点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性格,流露出朴实的生活情感。由鲁迅艺术学院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的《兄妹开荒》,是这一时期新秧歌剧运动的典范。
1943年冬,鲁艺工作团赴绥德分区巡回演出新秧歌剧,此后榆林地区新秧歌剧运动蓬勃发展。全区各剧团以及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等红区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都积极编演以抗战救国为主要思想内容、以新秧歌剧为主要形式的新剧目。《王贵与李香香》《越捞越深》《小放牛》《血泪仇》等剧目频繁上演[22]。这一时期,靖边县秧歌队颇为引人瞩目。在杜芝栋的指导下,该秧歌队大胆进行了新秧歌剧的编写与表演。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办秧歌戏汇演,杜芝栋与鲁艺的工作者一同排演了他自编的秧歌剧《破除迷信》[23]。这部剧“不再谒庙敬神;秧歌队以举斧头和镰刀的工农代表领头,队员装扮的角色主要为工农兵学商的形象”[24]。由此可见,新秧歌剧运动摒弃了传统秧歌剧中的糟粕,并打破了以往戏剧“口号”式的说教以及闭门造车的所谓“大戏”理论,使得旧剧改造取得了成功,开始能够适应新生活和新任务。
新秧歌剧运动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其创作演出能够吸引农民群众主动参与进来,以及剧作家能虚心与优秀的民间艺人合作,创作出百姓能够看懂且爱看的一大批优秀剧目。正如艾青在1944年6月28日发表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中所写道的那样:“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25]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由陕北传统秧歌剧革新而来的新秧歌剧真正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被称为“翻身秧歌”“胜利秧歌”和“斗争秧歌”[26]。
新秧歌剧的得名,是由于它着重表现新生活、新人物和新世界。而因为它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又被称为“翻身秧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传统的陕北道情经过抗战时期的戏剧革新,被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同样广受人民群众欢迎,并因而被称为“翻身道情”。
陕北道情以清涧道情为主,与秧歌剧同为广场艺术,其演出内容原本多以道教故事为主,传统剧目有《韩湘子成仙记》《目连救母》《十万金》等。据《清涧县志》,该县五四运动以后的道情分为“旧道情时期”和“新道情时期”,其分界点正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7]。在戏剧革新运动的推动下,榆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道情戏,如《周子山》《家庭图》《结婚图》《二流子转变》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陕北道情作为演唱曲调也可融入新秧歌剧的表演形式中。如鲁艺秧歌队在米脂演出新秧歌剧《减租会》时,就运用了道情的曲调进行编演[28]。
无论是“翻身秧歌”还是“翻身道情”,都体现着戏剧革新的内在脉络,即以人民文艺路线为中心,并融入时代的革命思想,而非简单地改良戏剧形式。历史地看,这些新艺术样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宣传抗战救国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们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使得广大群众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新时代的主人翁,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分子。
四、抗战时期榆林地区戏剧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抗战文艺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在艺术形式的探索和戏剧启蒙的功能上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其价值之大、意义之重要,主要体现于在中国戏剧民族化、现代化和功能化的统一方面进行了可贵尝试。
自从西方现代戏剧传入中国以来,戏剧家们就开始致力于推动现代戏剧民族化和传统戏剧现代化。到上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戏剧”兴起、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国对戏剧的民族化和现代化探索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同其他文艺活动一样,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延续了江西时期的“苏区文艺”传统。这一文学思潮主张,文艺作品要强调思想斗争,并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在1937年1月26日的中国文艺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光荣的任务。”[29]
众所周知,从事戏剧活动,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受众问题——能否为广大群众接受,是衡量戏剧民族化、现代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应该说,左翼戏剧正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现代化和民族化。在革命抗战的语境中,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主动接续了“苏区文艺”的革命传统,在强调革命斗争的同时,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着力表达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如此一来,话剧、歌剧等现代戏剧就不自觉地完成了民族化改造。从形式上看,话剧的演出场地因受传统剧种的影响而变得灵活起来,街头、广场、田野都可作为话剧演出场地。这便是所谓“将话剧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与民间演出形式结合起来,发展为诸如活报剧、街头剧、广场剧、游行剧等备受大众欢迎的小戏”[30]。这种演出形式上的变革在于吸收了民间的演出形式,为现代戏剧民族化开辟了形式上的道路。从内容上看,现代戏剧的演出内容开始关注工农阶级的生活情感,集中反映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如歌剧《白毛女》取材于当地“白毛仙姑”的传说,表现的是百姓熟悉的内容,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和乡土气息。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此前的上世纪20年代,时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已将民间文学列为课程教学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等民间文学”[31]。这使得榆林地区的民间文艺精华得以保留,并促动形成了知识界主导的文艺活动要与民间文艺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
应该说,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现代戏剧活动呈现出民族化的趋势,而现代戏剧在本地区的发生与传播本身就促进了戏剧格局向现代化转变。当然,现代化转变还体现在对传统戏剧的革新上。榆林地区的新秧歌剧运动以及对陕北道情的革新,都是将传统的剧种融入时代的精神,剔除其糟粕,代之以注入关注现实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等现代化要素。
戏剧活动与时代背景具有双向关系。作为一种文艺样式,戏剧必然离不开时代大环境的塑造。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呈现出民族化、现代化的特征,都是由于时代精神使然,将二者统一起来的也是这种时代精神。而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又必然会对时代产生回馈。换句话说,戏剧的民族化、现代化的目的指向就是戏剧的功能化。一方面,戏剧具有娱乐军民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抗战救国思想的载体,须担负起对军民进行教育的功能。
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抗战救国的主题。国民党方面,邓宝珊主管榆林后,采取措施,逐渐稳定了局势,并对“联共抗日”采取积极态度,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我党在自身性质的要求以及延安文艺思潮的引领下,自然也将抗战救国作为戏剧活动的主要任务。即使在复杂的时局关系下,各个剧团在戏剧实践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抗战救国这一倾向,如为纪念“七七事变”而在定边成立的“七七剧团”、在佳县抗敌后援会支持下成立的“觉民剧团”、由榆林中学等三所学校师生共同发起成立的“大时代剧团”、“三青团”组织建立的“长城剧团”等,其名号本身就洋溢着抗战救国的热情,而其所编排演出的抗战相关的话剧、秧歌剧等,更是带有浓烈的功能化意味。
总之,榆林地区的抗战文化语境,最终使得戏剧的民族化、现代化和功能化这三者走向了统一。在这里,现代戏剧的民族化是在革命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显示出了戏剧发展的理论现代化特征;我党的戏剧工作者在对待传统戏剧时采取“扬弃”的态度,既坚持发挥传统剧目演出形式的优势,又注重融入进步的文化思想,彰显了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而追根究底,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变革又都是当时戏剧功能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抗战时期榆林地区戏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戏剧民族化、现代化以及功能化的统一,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和重要意义的独特样本。
五、结语
抗战时期,榆林地区因其深厚的戏剧文化传统和新文化风潮的引入,呈现出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并存且交互影响的格局。同时,解放区与国统区复杂的时空关系导致戏剧呈现出复杂的态势,难以梳理清楚。但其主流仍非常清晰,那就是随着抗战革命文艺理论在实践中不断革新、应用,最终留下了为人民所喜爱的戏剧艺术样态,通过戏剧革新而产生的新秧歌剧和“翻身道情”,展露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艺术形式应有的姿态。其通俗自然的表演形式,体现出对戏剧本身发展规律的尊重,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较为成功地宣传了抗战救国思想,唤醒了民众的救亡意识。可以说,作为中华民族抗战文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对戏剧民族化、现代化及功能化都着力进行了探索,这对今天的戏剧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蓝田上许村道情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