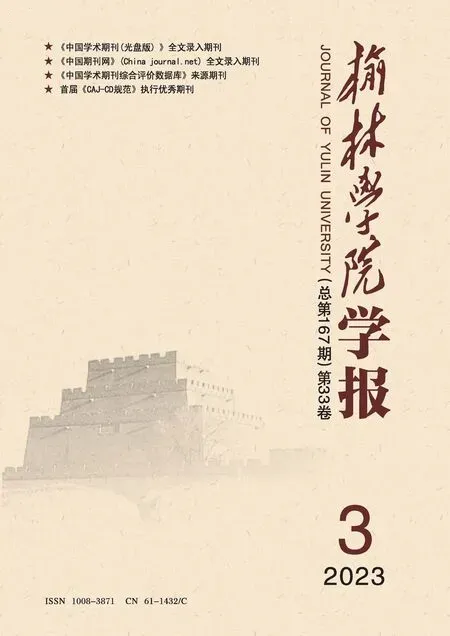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张 甜,卢征良
(1.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思政部,四川 成都 610400; 2.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神木古称麟州,位于今陕西省北部,地处陕晋蒙三省交界。历史上因其处于传统的农牧文明过渡地带,是中原王朝的边地关塞,极具战略价值,史称其“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实为榆塞上游边陲重地”[1],故历代中原王朝便在此设官而治,建立军事堡寨,以防御游牧民族南下侵扰。据考证,北宋时神木便有《麟府图经》和《新秦郡志》等志书[2],但因神木地处“荒渺之地,孤陋之区”[3],又屡遭千余年的“兵燹”等因素而亡佚,出现了“文献无征”“神松莫考,星石难稽”[4]的方志空白时期。清代官方先后纂修了两部《神木县志》,分别为雍正《神木县志》与道光《神木县志》,弥补了神木地区的方志空白。两部县志虽保存至今,但内容亦非完整无缺,如雍正《神木县志》部分内容佚失①,道光《神木县志》内容也存在残缺不全的现象。但是瑕不掩瑜,两部县志仍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研究神木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拟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雍正《神木县志》和道光《神木县志》两部清代方志的纂修情况及方志体例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探讨两部志书的纂修特点和史料价值,为后来的志书编写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代《神木县志》的纂修与版本流传考
方志作为记载地方历史和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历来备受推崇,并逐渐成为历代必不可缺的文献资料,编纂方志也成为各王朝所遵守的优良传统。清朝统治时期,为了彰显其文治武功,便积极开展编纂《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等典籍的大型文化工程,对各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志书的编纂也逐渐成为各地官员的考核标准和为政职责,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官员“皆以修志为尚”[5],编纂方志的风潮席卷全国,出现了“无地不有志”的盛况,而两部《神木县志》便诞生于此次修志风潮之中。根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6]与岩井大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7]的记载可知,清代仅有道光《神木县志》一部志书,但是在《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与《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方志汇编中,还有一部编于雍正年间的《神木县志》,即共计两部清代志书。故而笔者以《中国地方志集成》的两部《神木县志》为基础,略述其编纂事由、成书时间与版本、馆藏等相关信息。
(一)雍正《神木县志》
雍正《神木县志》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率先影印出版。此前该志处于佚失的状态,各版本的方志目录均未记载,该志的出版推翻了道光年间版本为神木第一部方志的论断[8],对于神木旧志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现存雍正《神木县志》共四卷,为手抄影印本,仅存有四卷正文,缺乏序、凡例、跋等内容,且该志未署编纂人和编纂时间,使得该志的具体编纂信息一概茫然,这也使得很多学者质疑该志的真实性。那么,雍正《神木县志》是伪志还是佚失的版本呢?
雍正《神木县志》的基本信息虽不可确定,但是雍正乾隆年间神木便有志书则是毋庸质疑。查阅道光年间《神木县志》,可以窥探《神木县志》的蛛丝马迹:道光年间的榆林知府李熙龄在道光《神木县志》的序中提及:“某故家旧有抄志四本,缺略不全。余即索而观之,当以修纂全志付明府”[9],又在其纂修的《榆林府志》的凡例中提及:“《神木志》乾隆年旧有志稿,未刻,亦未善,现王矞亭明府新立志书。”[10]再如王致云也在道光《神木县志》的序中提到“得抄志四本于藏书家,未著姓名,不知出自何人之手”[11]。综合二人的序言可知,李熙龄提及的神木旧志和王致云搜集到的四本手抄志书实为同本志书,那么通过李、王二人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是在道光《神木县志》编纂之前,神木已有旧志,且该旧志的编纂时间在清代前中期。那么,该四本旧志稿是否为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原版呢?笔者从版本的完善程度与记载内容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现存雍正《神木县志》并非王致云所搜集的四本抄志版本,兹述其详。
在版本的完善程度方面,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较四本旧志为优。王致云在搜集到四本旧志后声称该志书:“第错杂脱略,不足以付梓镢”[12],即他认为该志书已经残破不堪,甚至都无再刻板印刷的必要了,可想而知,该志已然面目全非。但反观现存的雍正《神木县志》,除缺少编纂者及编纂时间等基本信息外,内容却较为完整和清晰,偶有缺失但丝毫不影响阅读,篇目设计也符合旧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其还具有“全书语言流畅,文字工整,书寄秀丽”[13]等优点。所以从志书保存的完整程度来讲,现存的雍正《神木县志》肯定不是当时王致云所搜集到的旧志。
在记载的内容方面,道光志并非完全依照现存雍正志的版本进行纂修,而是另据其他版本纂修。王致云在道光志的序中云:“神木尚无志书”,李熙龄亦云:“此邦之人,文献无征”[14],那么可以说明文献资料对于当地人民来说是比较稀缺的,王氏在搜集到志书后必然会加以详细的引用和参考。所以,道光志引用四本旧志的概率是很大的,假使王氏所搜四本抄志为现存版本的雍正《神木县志》,那么可将之与道光志进行比较研究便可知其缘由。王氏谓旧志残缺不堪,错杂脱略,而谓新志“备而不繁,详而不冗”“悉灿若而无遗”[15],但笔者将二志对比发现,并非如其所言,王氏之道光《神木县志》在某些地方还未如雍正《神木县志》详实。如二志均设人物志一门,其下又设职官等目,但在对历任官员的记载上,雍正志明显要比道光志更详实具体。兹举一例证明,如在雍正《神木县志》的职官部分,关于官员的记载:“陈廷芝,锦衣卫人,由壬戌进士,万历元年任”“萧大亨,山东泰安人,由壬戌进士,万历四年任,历升兵部尚书”[16]。而道光《神木县志》的职官部分关于此二人的记载则为:“陈廷芝,锦衣卫人,进士”“萧大亨,山东泰安人,进士”[17],那么根据此二志的人物记载来看,雍正《神木县志》是明显的更为详实。这让人便产生疑惑,为何辛苦搜集到的志书而不详细的利用而加以记载呢?另外萧大亨后升至兵部尚书如此显赫的官职,道光《神木县志》竟然不予以记载,这也与借名人的功绩来彰显本县地望的传统做法不相符合。再者,道光《神木县志》中对于部分官员的记载信息也相对详细,如“李允生,贵州威宁州人,贡生,顺治二年任”[18],该记载至少将在任的具体时间记录下来,内容明显比萧大亨的记载更具体。这种有差别的记载方式,岂不是因为材料掌握的不够详实吗?
此外,现存雍正志与道光志在记载同一件事物时亦有不同。假使道光志采用了现存雍正志版本的记载内容,何故会有差异呢?如在建置中对堡寨的记载,现存雍正志中提到“本县设官寨十六,塞官三员,分管三路,保长十六名”[19]与“板门岭塞、神灵腰塞”[20]等军事内容,而道光志中则记载为“明制县共十六寨,设有寨官保长领土兵以守之”[21],同时将雍正志中的“板门岭塞与神灵腰塞”称为“板门岭寨、神灵腰寨”,由此可知雍正志称“塞官”而道光志则称“寨官”,究竟是“寨”还是“塞”,道光志亦并未作出详细解释,故现已不得而知,但是值得肯定的是道光志与现存的雍正志在所载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引用了不同的版本。
综上,现存版本的雍正《神木县志》并非王氏所搜集的四本抄志。若仅仅以道光志中提及四本旧志的说法就认为该旧志即为现存版本的雍正《神木县志》的观点有待商榷,即便四本旧志为现存版本的雍正《神木县志》的原版,那也是保存残缺不堪的一版,和现存雍正《神木县志》不可相提并论。至于现今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流传因缺少相关基本信息也是不明了的,仅知是由台湾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影印出版,后来流传到内地,再经出版而广泛被熟知,所以现今版本的确切源头仅可追溯到成文出版的那年,这也是其颇具争议的重要原因。
(二)道光《神木县志》
道光《神木县志》是由神木知县王致云所组织纂修并刊刻的志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传统的观念里被视为神木县的首部方志。王致云,浙江萧山(现杭州萧山区)人,以举人出仕,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任神木县知事,痛惜神木无志书之弊,认为神木为“古边要之区,历朝沿革,或省或至,其间豪俊、才智、忠烈之士,更仆难终”[22],只有依靠志书等文献的记载才可以使神木的建置沿革及历代重要人物的历史“传于世”,更可以“稽诸古,证诸今”,所以积极组织其幕僚及县域诸生员编纂县志。经各方的努力搜集和考证,《神木县志》历经一年后终于成书,并上寄于陕西分巡延榆绥兵备道郭熊飞、榆林知府李熙龄二人,邀其为志书作序,郭、李二人给予该志很高的评价和赞誉,称其“博而不杂,简亦能赅”“灿然大备”[23]。
道光《神木县志》后经正式刊刻出版,成为神木县的严格意义上的首部刊刻志书,并作为李熙龄《榆林府志》的重要文献来源,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因素,使得该志得以较好的保存和广泛的流传,成为被人熟知的神木志书。在1958年版的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道光《神木县志》被视为神木首志,仅有道光二十一年的版本,并有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图书馆等七处藏书地[24]。1982年,神木县志办经过多方的努力搜集和整理,对道光《神木县志》进行点校和勘误,并将道光《神木县志》点校本正式出版。目前广泛流传的便是《中国地方志集成·道光神木县志》和点校版的道光《神木县志》。
二、清代《神木县志》的体例沿革及纂修特点
古人云:“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25],政治体制的运行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治学著书必先掌握书籍的体例格式。方志作为传统的典籍有其相对固定的体例形式,通过对方志的体例进行研究,可以明了方志的纂修方式的变革与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清代两次编纂《神木县志》,即为《雍正神木县志》与《道光神木县志》,前者纂修于清代前期,后者纂修于清代中期,两者间隔百年左右,且在体例和内容书写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特点,那么通过对两部志书的体例进行分析和比较,便可以明了神木志书的纂修脉络,感知清代神木地区社会历史的变迁历程。
(一)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及纂修特点
雍正《神木县志》的现存部分仅有目录及正文部分,缺少序、凡例、跋等基本内容,全志共四卷,共分成十个门类,门下又列五十八个细目,为分纲列目体例。十个门类依次为封城、建置、市集、田赋、祭典、职官、宦业、选举、古迹、艺文,各门类下分设三至十一个数量不等的细目,兹据目录,将其门目整理于表1。

表1 雍正《神木县志》纲目
雍正《神木县志》的纲目设置较为详细,封城、建置、田赋三个门类均达十个子目(见表1),基本囊括该门类的每个部分,详细的展现了神木地方的地理形势、建置和赋税等基本信息。此外,在门目的设置上,突出了神木作为边塞重镇的军事功能和军事部署的情况。在封城门类之下设山川、形胜、疆域等目,详细的介绍了神木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高山大川的基本情形,主要突出军事作用,如记载白龙寺山“四面辟立,只通一径,登者拾级裹足以上,土人结庐而居可以据险”[26],称神木为“秦晋之咽喉,榆城之屏翰也,九塞要冲,莫此称最者”[27],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建置门类之下设堡寨、边维、武备等目,详细介绍了神木军事设施的发展和军事人员的情况,如“本县设官寨十六,塞官三员分管三路,保长十六名”[28]、“神木诸隘始称扼要,而武备充足恃矣”[29]等相关军事信息记载。田赋和市集两个门类主要展现了神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情况,集中记载了边境贸易集市的布局及转变与赋税来源等内容。如在市集中称“旧设市口,为北丁交易之处,但性多狡黠,倐焉乞欵,寻即塞盟,肘腋之虞,变生不测。迨至国朝定鼎,套长宾服,锋镝不鸣。每以绒皮、毡、盐、牛羊之属,易买布疋、烟茶,单民仰赖什一之利焉”[30],说明了神木作为南北民族交界之地,自古便是民族间贸易交流之地,但是仍存在较大的矛盾冲突,直至清朝时期,经济贸易逐渐稳定,集市规模也在扩大。究其根本原因是自清朝以来疆域辽阔,海内一统,不再将九边重镇作为边陲之地,神木逐步从军事要塞逐步转变为汉蒙贸易交流的枢纽,这是该志作为清初方志编纂的显著特点和基本要求。
(二)道光《神木县志》的体例及纂修特点
道光《神木县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时任神木知县王致云组织纂修,其志保存程度和所载内容均较雍正志为优,是清代神木方志的经典之作,被赞誉为“博而不杂,简亦能赅”。道光《神木县志》有序三篇,另有纂修职名、图说、后序等内容。正文共分八卷,分为四个门类,即舆地志、建置志、人物志、艺文志四个总志,为总纲系目体,各门又分上下部分,门下共分设四十七个细目,遂兹据目录,将其门目整理于表2。

表2 道光《神木县志》纲目
道光《神木县志》开篇即附有神木地图,正文共分为四个门类,囊括舆地、人物、建置、艺文四个方面,为总纲系目体例,门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见表2)。每门开篇即为总论部分,详细说明此门之下所载的内容及缘由,使读者可以明了文中的基本内容。各总志下分设诸多细目,以舆地志与建置志的细目为最多,人物志次之,艺文志的细目为少,部分细目另附加内容,细目的设置较为详实合理,全方位的记载了神木的社会经济情况。道光《神木县志》在体例上及内容上均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凸显其特点,将其与雍正《神木县志》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异同点,或许反映出神木方志纂修方式的演变及社会历史的变迁。
首先,从志书的体例来看,雍正《神木县志》为分纲列目体,而道光《神木县志》为总纲系目体,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明清时期,各地方志大都采用分纲列目体与多目无纲体两种体例书写,而总纲系目体虽然“简洁明了,但无法容纳所有复杂的内容,正确反映各事物间的关系,嘉庆后便很少有人在用了”[31],既然嘉庆后就鲜有人用了,何故道光《神木县志》却仍采取总纲系目体呢?笔者查阅同属榆林府的其余各县体例,仅有道光《神木县志》为总纲系目体,其余如道光《榆林府志》、嘉庆《怀远县志》、嘉庆《葭州志》等志书均采用分纲列目体例,唯独道光《神木县志》采取总纲系目体,说明总纲系目体并非榆林地区方志的纂修要求和特点。笔者认为道光《神木县志》采用总纲系目体书写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王致云的“统综”纂修主张。在道光志序中,王致云提出:“志求详备,尽人而知之也,惟备而不失于繁,详而不流于冗,知得所统综,不至散而无纪耳”[32]的纂修主张,即王氏认为方志的纂修应详实完备,内容需高度综合统筹,不应繁冗杂乱。故据此主张列舆地、建置、人物、艺文四纲,将搜集的各方面的信息汇总,分别进行归纳并罗列于四志之下。其二是神木文献无征的处境使然。神木“久为边陲扼要,数千百年而志乘无闻”,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加之搜集到的资料残缺不堪、内容繁杂,即所谓“神邑虽僻在边陲,其间舆地之袤广,建置之革因,人物之英奇,艺文之宏实”[33],此种现状给志书的编纂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故以四个总志来统领全志,囊括神木自然人文各方面的基本信息,能提纲挈领,文章不至于杂乱。
其次,从各细目的设置来看,二者各有详略、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雍正志较道光志的细目设置更为具体详细,但道光志的细目记载内容更为充实。兹举一例,如在二者同有的建置志中,雍正志设城池、堡寨、边维、县治、公署、学校、恤政、坊表、武备、关厢等十个细目,而道光志设城池、堡寨、边维、衙署、学校、书院、兵防、驿传、坛庙、寺院、坊表、市集、里甲、地亩、户口、民赋、仓储、解支、恤政、盐政、茶政等二十一个细目。道光志的建置志涵盖了雍正志中除县治、武备、关厢三个细目外的所有内容。若单从细目的数量来看,道光志的设置似乎更为具体;其实不然,除上述雍正建置志内容外,道光志的建置中的细目可归入雍正志中的四个门类之中,如坛庙、寺院可归入“祭典”门中,“市集”为单设一门,里甲可归“封城”门中,地亩、户口、民赋、仓储、解支、恤政、盐政、茶政等八目可归入“田赋”门中。那么二志均设建置志,而道光志的细目设置涵盖了雍正志中五个门类的内容,反映出了道光志“统综”的特点。而雍正志的门目设置更详细,如“市集”单列一门,下设市厂、城集、村集三个细目,而道光志仅将“市集”作为细目列于“建置志”之下。道光志中的部分细目之下另附加内容,使得所载内容更加丰富,如在《建置志·边维》中,除记载历代神木边塞军事设施的修筑之外,附加牌界的内容,详细的描述了汉蒙耕牧区域的划定历程。
最后,在内容的书写上,二志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道光《神木县志》所载的内容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均优于雍正《神木县志》,二志的记载内容亦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如在关于神木军事堡寨的记载概况中,雍正志的记载极为简略:“本县设官寨十六,塞官三员分管三路,保长十六名”[34];而道光志的记载为:“神木县城旧为堡,合永兴、柏林、大柏油共四堡。乾隆二十七年,拨佳州高家堡,隶神木,乃有五焉。明设专阃大员,屯兵以守。国朝边徼清平,节以制度,而防卫规模,尚循其旧,盖以重地之不可废弛也。至山寨,宋筑建宁等五寨,皆据要筑城,非小寨可比,已详载古迹。明制县共十六寨,设有寨官,保长,领土兵以守之,今废置毋庸,姑存其名可耳”[35],在关于各寨的记载中,兹举王家塔寨为例:雍正志仅载为“王家塔寨”[36],无甚说明;而道光志载为“王家塔寨,在县东七十里,即今红寺儿川”[37]。据此二条记载,姑且不论真伪,仅从内容多寡的角度来说,道光志材料的丰富程度远远优于雍正志。与此同时,二者在记载同一件事物时亦有不同。如在堡寨之下,雍正志中提到“塞官”与“板门岭塞、神灵腰塞”等军事内容,而道光志中并无“塞官”一职的记载,将“板门岭塞与神灵腰塞”称为“板门岭寨、神灵腰寨”,究竟是“寨”还是“塞”,还是为雍正志的笔误,现已不得而知,但二志之间的差异仍是不可忽略的。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能够突出展现各自的特点,以及探究清代神木的发展历史。
三、清代《神木县志》的史料价值
神木为边塞之重镇,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宋代开始“数百年中,烽烟告警,岁无虚日”[38],因此神木各项事业均是以军事为核心来发展的,文教事业迟缓,所著史书典籍甚少,又加之千百年来久经战乱、屡遭兵燹,文献典籍流传甚少,造成“文献无征,星石难稽”的局面,导致后人无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还原和感知神木的历史。但值得庆幸的是,两部清代《神木县志》均是经过大量的文献搜集和文献考证,保存和记载了神木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内容,尤对神木地区的沿革、军事设施、古迹、碑刻、诗文敕令、名流贤宦、风俗文化、蒙汉交流等内容记载详实,为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基础,可成为如今研究神木地区乃至河套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一)军事史价值
自秦朝始,神木的行政建制虽经数次更易,但是其作为边塞重镇的角色并未曾改变,历来便受中央王朝所重视,即所谓:“至于筑城缮塞,命将遣师,具在方策备御之政,何代无之”[39],随着历史的发展,神木的军事设施不断增置和修筑,军事制度亦不断调整和变革。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神木地区产生了大量与军事相关的历史战事和历史人物,虽有文献记载整理,但大都散佚,直至清代两部《神木志书》的编纂才使遗留文献得以汇集刊印。《神木县志》将神木的历代文献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关于军事方面的资料,涉及建筑、人物、纪事、军制、碑文、遗址、传说等诸方面内容,具有极大的军事史料价值。
《神木县志》的军事内容主要集中于雍正志的封城、建置、职官、宦业、艺文等门类中,以及道光志的舆地、建置、人物、艺文四门。因其内容甚丰,笔者以军事设施、战争纪事、军事人物等部分内容,略述《神木县志》的军事史价值。
1.军事设施。神木的军事设施主要为城池、堡寨、墩台、边墙等,在《神木县志》中均有相关记载。城池主要记载了由明朝至道光年间的县城修筑历史及现状,堡寨为神木的重要军事据点,志书中详细的记载了各堡寨的分布、历史沿革及现状,如载“永兴堡,县东北五十里,隋连谷县,唐麟州地,宋为黑城儿。明成化中,巡抚余子俊,遣镇羌指挥宋祥,置土城在山上,周围二里零二十五步,南面一门,东西北无门,楼铺八座。万历间,巡抚涂宗浚用砖包砌,今塌损,仅剩土城,详明列入缓修。堡内集场,无街道”[40],详细的记载了永兴堡各历史时期的建置及修筑情况,展现出堡寨的基本历史面貌,因此极具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关于边墙、墩台的记载,如“永兴堡边口,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墙长六十二里零八十六步,墩台三十九座”[41]。《神木县志》所载的内容,是现今神木各军事遗址的相关挖掘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文献基础。
2.战争纪事。《神木县志》中记载了大量的战争历史,主要集中于道光《神木县志》的沿革(附纪事)中,按朝代记载了在神木所发生的战事。如“代宗大历十三年八月,吐番寇银、麟州,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德宗贞元二年,吐番寇麟州”[42]等内容,记载了唐朝时期吐蕃侵扰神木地区与唐军的战事。志中记载宋代的战事尤多,大多为宋夏战争的内容,如“雍熙二年二月,李继迁攻麟州,诱杀都巡检曹光实于佳卢川,遂据银州。五月,付将王侁出银州北,破悉利诸寨。麟州诸番,皆请纳马赎罪,助讨继迁。侁遂入浊轮川,斩首五千级,继迁遁去”[43],详细的记载了李继迁侵占神木地区和宋将王侁的征讨战事,又载“元昊陷丰州,知州王,元庆、兵马监押孙吉死之,管勾麟府路军马张亢,败之于柏子寨,及兔子川”[44],则是记载了元昊侵占丰州并被宋将张亢击败的战事。文中所载宋夏战事不胜枚举,亦可成为研究宋夏战争的重要补充和印证材料。文中亦有大量明朝的军事纪实,内容数量稍逊宋时,兹不赘述。
3.军事人物。《神木县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军事人物内容,涉及神木的镇守将领、官员设置、忠勇事迹等方面,系主要集中于雍正志职官、宦业门类与道光志兵防、忠烈中。如道光志《建置志·兵防》中记载神木军官的设置,有副将、中军都司、城守营把总、经制外委等军职。雍正志《职官·协镇》亦记载“东协副将衙门,自古驻扎孤山堡,于顺治十三年移驻神木”[45],这些都是关于军职设置及人员的记载。此外还有对将领忠勇事迹的记载,如雍正志《宦业·忠勇》记载:“杨璘,任神木营参将,统兵至胜家墕,对敌奋不顾身,矢尽弦绝而死”[46],道光志《人物志·忠烈》载“王国安,任都司佥事,御寇于高家堡,恃勇以六骑掠阵,死之”[47],这些关于将领的忠勇事迹都可当作战事的印证材料加以利用,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文学史价值
神木作为边塞之地,自古烽烟四起,文人墨客来此甚少,但是也仍保存了一些诰敕、传记、碑刻、诗文等文章内容,其中尤其是诗文内容别具一格,多慷慨激昂、充满斗志,即“历代雄兵坐拥,恒多激楚之章”[48],形成了独特的边塞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主要集中于雍正志《艺文·题咏》与道光志《艺文志·诗词》之中,遍及各朝,内容颇丰。
经笔者统计,雍正志《艺文·题咏》中所载的诗词约有五十九首,大都为赞扬神木山川胜景、军旅生活、思念故乡、诗文互赠等内容,大部分为文官所作,武将诗篇较少。关于神木胜景杏花滩的诗歌尤多,近二十篇,如有观察使张衡《杏花滩》三首、郡丞陈昌国《游杏花滩》六首、邑侯尤何《和陈司马原韻》六首、协镇周文英《和陈司马原韻》四首等诗篇,均记叙了闲游杏花滩的乐事,如邑侯尤何诗云“二月南郊杏芷开,欣然结伴共啣杯。班荆宴坐花枝下,阵阵香气拂面来”[49],这些诗歌不仅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材料,而且也能够为如今神木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借鉴。
道光志中所载的诗词约有九十余篇,记载了从唐朝至清道光年间的诸多诗词,有些是关于久负盛名的大诗人、大政治家的诗词记载,内容极为丰富。如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维的《新秦郡松树歌》“为君颜色高且闲,亭亭迥出浮水间”[50]表达了对松树高度的赞扬之情;“诗豪”刘禹锡的《送浑大夫赴丰州》“毡裘君长迎风驭,锦带胡豪踏雪衙”[51]表达了对友人离别赴任的美好祝愿;更有宋代名臣知延州范仲淹的《留题麟州》《麟州秋词(调寄渔家傲)》二首诗词,“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52],集中描述了神木的边塞风光,及军旅生活,表达了范仲淹讨伐西夏和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其余的诗篇虽不及名家,但是亦均表达了“欲假吾王剑,长驱斩郅支”[53]抗击敌军,保卫国门的豪情壮志。边塞诗是清代之前的主要题材,以宋代和明代为多,是由当时的内外政局决定的,至清朝后,海内一统,边塞诗逐渐减少,出现了诸多赞扬神木风景名胜以及官员之间互赠的诗篇。这些诗词的记载和保存,能够使今人管窥神木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同时也是研究边塞诗词文学的重要史料。
(三)民族史价值
因神木地处农牧文明的交界地区,毗邻河套,历来便为游牧民族所侵扰,使得该地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冲突的集中地区,从而使得该地常年征战不休、烽火不绝。直至清王朝建立后,海内一统,战事消弭,神木遂安。道光《神木县志》有大量关于北方民族的记载,主要分布于《图说·河套全图》《舆地·蒙地》《人物志·职官》等门目中,兹举例略述。
道光志的《图说·河套全图》详细的记载了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七旗蒙古分布情况,内有营盘、堡寨、河流、城池等重要信息,是研究清朝时期鄂尔多斯地区蒙古历史的重要历史材料。自清朝建立后,地处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七旗蒙古,尤昭恭顺”,理藩院在此设立官员,专管鄂尔多斯七旗蒙古事务,而处于神木管理的共有郡王、札萨克二旗。所以《舆地·蒙地》详细的记载了神木分管的二旗情形,并附有杂记,即“举耳目所及,悉缀诸后,谓之杂记”[54]。主要涉及该二旗蒙古的历史人物、建筑、居民、宗教等内容。《人物志·职官》中记载了专管鄂尔多斯蒙古事务的历任神木理事司员一职的三十七名官员。此外又有《建置·市集》记载了汉蒙贸易的历史及现状内容。虽然《神木县志》所载的民族内容较少,但是仍可与相关史料进行印证,可作为民族史研究的材料并加以利用。
(四)社会风俗史价值
两部清代《神木县志》对古代神木地区的社会风俗有详细的记载,主要记载于雍正《神木县志》的《封城·风俗》《封城·节序》二目与道光《神木县志》的《舆地·岁时》《舆地·风俗》二目之中,着重体现在生产方式、阶层构成、礼仪习俗、节日禁忌等方面,对研究神木的传统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在生产方式与阶层构成方面。神木地处传统的农牧业过渡带,加之汉蒙交流贸易频繁,使该地社会形成了“多善射猎,不事绩纺,至于朖田力穑,固其本业也”[55]的兼具农业与游牧业的生产方式。此外,道光《神木县志》将民众按照传统的士农工商进行分类,分别记载了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如士人“颇有隽才,惜多寒俭”[56]、士风“至如他处之结党树盟、起灭词讼等类,斯地罕有,士风谨朴,殊堪嘉尚焉”[57];如农务“农有地者则自己耕作,无则受雇佣工,绝少游惰之人”[58];如工匠“百工技艺,大概皆具。物专求坚朴,不胜奇巧”[59];如商贾“城内晋商居多,凡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卖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60]。同时,由于该地民众久居边陲,在与“边地苦寒,砂石硗瘠”[61]的恶劣自然环境和边境侵扰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尚勤朴,文武士大夫颇尚气节”[62]的优秀品质。
其次,在礼仪习俗方面。道光《神木县志》将礼仪分为婚礼、丧礼、祭礼、宴会四类,其中婚礼是最为繁琐复杂的礼仪,而缙绅家庭与普通民众家庭的婚礼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缙绅之家对婚礼制定了严格的流程,不过大致分为择婿、放话(问名)、放定礼(纳采)、迎娶、催妆、过厨柜、背圪崂、礼拜、圆饭、回门等流程,每一个流程都极为严格,如迎娶之礼在临近大婚之日时“男家用采輿执事,选少妇二人乘轿往迎,女家扶女上輿,亦选少妇二人乘轿伴送,此均谓之妮姑。及抵婿家,将新妇扶上炕隅,向吉方背坐,彻夜不睡,灯火不息,谓之背圪崂”[63],再如礼拜之礼最为重要,将新人“扶向前庭礼拜天地,行庙见礼,先拜翁姑,次尊亲及伯叔娣姒等,礼毕归房”[64],经过这一系列的流程后,婚礼方算完成。相较于缙绅家庭,普通民众家庭的婚礼流程则较为简但,即“一经问名,婿家先以银钱馈遗,谓之放拜礼,其迎娶仪节概从简约耳”[65]。宴会亦称酬酢之礼,民众在节庆之日时,便“设席相邀,盖以八簋为率”[66]。
最后,在节日禁忌方面。两部《神木县志》均是按照一年中的节日次序来记载,经笔者统计,雍正《神木县志》与道光《神木县志》所记载的节日均为19个,二者所载的内容总体上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节日的废存、称谓、活动内容等方面却有些许不同。首先是节日的废存,如在雍正《神木县志》中有“正月十六日”“三月二日”,而道光《神木县志》并未有此二者节日的记载,道光《神木县志》中有“正月二十五日”,而雍正《神木县志》并未有该节日的记载。其次是节日的称谓,如农历五月初五,道光《神木县志》称“端午”,而雍正《神木县志》却称“端阳日”、农历七月七日,雍正《神木县志》称“秋士日”,而道光《神木县志》却称“七月七日”。最后是节日的活动内容,如农历九月九日,雍正《神木县志》记载为“馈遗枣糕,邑人携酒登高”[67],而道光《神木县志》则记载为“邑人携酒往东西山登高”[68]。
两部清代《神木县志》是神木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使得神木历代典章和历史事件得以记载和流传,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内容残缺,字迹潦草,信息不全,其真伪及成书年代仍存争议,但值得肯定的是现存版本的雍正《神木县志》并非道光《神木县志》中所提及的“四本旧志”,即道光《神木县志》并非以雍正志为基础而进行纂修,而是另据其它志书或雍正志的其他版本而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上有着较大的差异,雍正志采用分纲列目体例,纲目设置较为详细具体,而道光志采用总纲系目体例。二者在内容的纂修方式、具体信息、时空范围均有很大的差异,部分的记载内容亦相互抵牾,二者所载内容各有侧重。总的来说道光志较雍正志更为丰富详实,可读性较高,但亦不可忽视雍正志的记载内容。同时,两部志书从不同朝代、不同角度记录、保存了清代以前神木地区的历史、社会、风俗、文化、军事、经济、民族各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作为相关史料的补充,对神木地区的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等方面的研究皆有裨益。在当今发展文旅产业和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志书的丰富内容可成为神木地区历史遗迹、历史文物、风俗文化的发掘保护和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亦可为推动现今长城沿线地区历史遗迹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文献基础。因此不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都应继续深化对《神木县志》的研究。
注释:
①雍正《神木县志》由成文出版社影印,并定勘出版时间为雍正、乾隆年间(《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但存在争议,另有康熙末年说(李大海)、雍正年间(《中国地方志集成》)说等观点,虽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该部县志出版于清代前期是毋庸置疑的。
——神木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