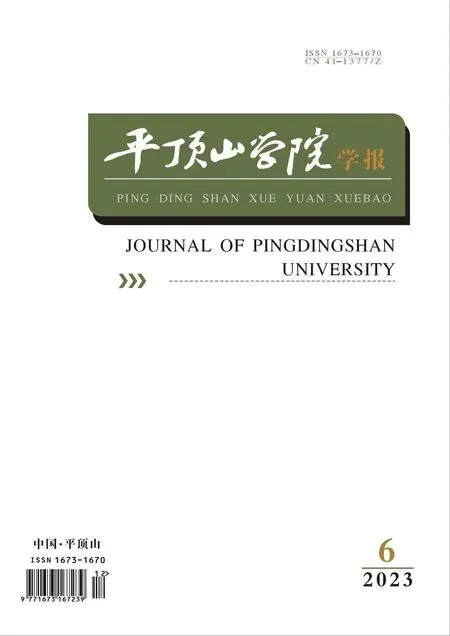“圣人未有不多能者”:朱子圣人观中的“能”
陈 磊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圣人观在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多数理学家都是从“德”的方面去理解圣人的,朱子则在“圣主于德”的前提下提出“圣人未有不多能”的观点,主张在“德”之外,亦需从“能”的角度去观圣人(1)德与“义理”“良能”为近义项,能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艺能”为近义项。。此观点尚未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2)田涵《朱熹圣人观研究》(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9页)设聪明多能、德才兼备两小节,认为朱子对圣人多能和事功的强调扩大了圣人的规模,但对于圣人多能与其德性的内在关系并未展开分析。王新宇《学为圣人——朱子理学与“圣人观”研究》(南京:南京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1—59页)有圣人之知一节,从“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两方面来描述圣人之知,并认为圣人的“生而知之”造就了其“学而知之”,但对如何造就只是以圣人气禀的纯粹清明泛解之,尚未能进一步说明此种决定性是如何发生的。,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圣人之能的性质与类型、德与能之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学理分析。
一、《论语》“太宰问于子贡”章所说圣人与多能的三种关系
《论语·子罕》篇第六章: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1]110
根据朱子的注解,此章太宰、子贡、孔子分别表达了对圣人与多能关系的看法。太宰“盖以多能为圣也”[1]110,他以孔子多能而认为孔子是圣人,是将多能作为圣人的主要特征;子贡认为孔子是天生之圣人,而又多能,则是一方面认同太宰对孔子是圣人的评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孔子之圣是天生的,同时又是多能的;孔子则先说自己虽多能,但所能者仅为鄙事,接着又说君子并不应当以多能为追求。
历来注家多据孔子之言,谓多能与圣人无关。如《论语注疏》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圣人君子当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当多能也。今已多能,则为非圣,所以为谦谦也。”[2]杨龟山云:“多能非圣人之事。”[3]321唯朱子则主子贡之说,据《朱子语类》,其曾与门人讨论此章:
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为圣,固不是。若要形容圣人地位,则子贡之言为尽。盖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艺之意,其实圣人未尝不多能也。”[4]958
朱子门人也同历代注家一样,认同圣不在多能的主张。此盖是一种常识,因为多能的“多”是没有尽头的,既然圣人是完美的人格典范,那么从多能去定义圣人就不可能达成完满性。与此不同,朱子则恰恰提出了“圣人未有不多能者”这一独特论点。
当如何理解朱子的这种观点呢?这里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朱子既从子贡之说,则对于此章孔子之言当如何安顿呢?根据上引《论语注疏》,太宰以孔子多能而疑其非圣,子贡为孔子辩护,谓孔子天纵之大圣,而又多能,孔子则顺太宰之疑而对之有某种肯认,从而表达了一种“谦谦”之德。朱子亦认为此处孔子是在自谦,但其所以为“谦谦”者则与《论语注疏》不同。朱子首先是转换太宰语意,谓太宰“以多能为圣”,而孔子的回答有两方面的意味:其一,对太宰之赞美谦不敢承,说自己之所以多能鄙事,是由于“少贱”这一偶然性的机缘,不能就此认为自己“非以圣而无不通也”[1]110;其二,对太宰之论点有所修正,谓“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晓之”[1]110,“率”读如律,“多能非所以率人”即不能用多能去要求所有人。表面上看孔子是主张“不必多能”,但上述第二方面还隐含着一层意思:朱子认为孔子“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语只是从“率人”的角度说的,而孔子实际上并未直接说出圣人与多能的关系。经过这样一番解释,朱子就在肯定子贡之言的同时恰当地安顿了孔子之言,即在“论理”和“宗圣”之间达成了统一。
以上是从经典解释方面分析朱子对此章的处理,现在可以来看看“圣人未有不多能者”这一论断本身的含义。需注意的是,朱子虽然提出了与历代注家不同的观点,但是却以肯定他们所共认的“圣主于德”为基础。所以,朱子在说“圣人未有不多能者”之前先说“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换言之,“圣人未有不多能者”是在“圣主于德”前提下的一个衍生命题。这里就有一个圣德和圣能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要能证成朱子的新命题,必须对圣人的德能关系进行解析,以说明圣人之德与多能不是不相关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必然性。在此之前,我们还需从另一个相关命题来说起,即圣人“生而知之”。据《中庸》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和困知勉行的三等区分,圣人被认定为是生知安行的[1]29,但常识告诉我们,圣人只要不是超越的人格神,那么他的多能就不可能是生知的。如此一来,朱子要主张其圣人多能论,就不得不面对圣人“生而知之”这一问题。且看朱子如何弥缝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论点。
二、“生而知之”与圣人之德能
《论语·述而》篇第十九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98
朱子注云:
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1]98
根据此注,朱子谓圣人生知而不待学的是“义理”。其后又引尹和靖语,明确指出圣人生而知之的是“义理”,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1]98。显然,尹和靖的说法比较符合常识,因为“礼乐名物、古今事变”并不能被先天地知晓,只能是在后天的经验中去学得。这样的“学”纯粹是圣德朗照下的知识之积累,而无关乎圣人之所以为圣。且圣人的“学”与大贤以下由困学而知的“学”不同,“学而知之”对应的是“生而知之”,因此常人的“学”所指向的亦是圣人之所以为圣的“义理”,而圣人的“学”只是积累知识。
论到这里,在“义理之当然”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之间似乎开始显现出了一些缝隙。如果说圣人汲汲而“学”只是对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的后天知识之习得,而无关乎其德性,则圣人之德便止滞于其所生而知之者,从而缺乏一种日进无疆的品格。同时,我们却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又因其不自圣,圣人除有生知一面外,亦能一生孜孜勉勉,而求有以进其德性,因之圣人的“学”亦必关乎其德性。如此,尹和靖所做出的区分看起来便不是那么地妥当了。
让我们再回头看朱子的理解。对于《论语集义》所收诸家解说,朱子唯独选择将尹和靖的话收入《集注》。盖诸家多谓“好古敏以求之”是孔子为了教人而如此说,不是孔子自身尚待学古而知。如范尧夫云:“夫生而知之者天也,学而知之者人也,圣人所以帅人者,学而已,其在天者,非所以教也。”[3]266杨龟山云:“盖不以生知自居,而示人以学,使知所谓不可阶而升,皆可学而至也。其循循善诱盖如是也。”[3]266-267此种解释强调圣人的教人之法,而消解了圣人本身是否需要学、是否多能的问题,但其中“不以生知自居”的说法又引出圣人的谦德一层。相形之下,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单用尹和靖说,自是认为其更符合《论语》原意。只是如此一来,“生而知之”者仅是义理,“敏以求之”者是“礼乐名物、古今事变”,朱子就会面临前后两个“之”字文义不统一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看似不统一的前提是我们将“义理”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当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假如这两者是相通的,或更确切地说,假如前者可以包含后者,那么表面上文义不统一的问题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而朱子主张“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就是要在德与能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性。
此外,于诸家所说圣人专说“敏以求之”以教人与圣人之谦德方面,朱子亦有某种肯定的倾向。此见于《语类》:
大抵如所谓“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说以教人。亦是圣人看得地步广阔,自视犹有未十全满足处,所以其言如此。非全无事实,而但为此词也。[4]890
然圣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处,也须学始得。如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有甚紧要?圣人却忧者,何故?惟其忧之,所以为圣人。所谓“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4]388
上引第一条语录中,朱子先谓孔子是“移向下一等说以教人”,肯定了教人之法的解释,紧接着又说圣人“自视犹有未十全满足处”,以及“非全无事实,而但为此词”,即尹和靖所说“非惟勉人”[1]98之意。此则不同于上述范、杨之专从教人方面说,而是有圣人自身的“事实”。此“事实”就是圣不自圣,因此,圣人总是孜孜勉勉,以求夫己所不知不能者。如此一转,圣人谦德的意味也出来了。按范、杨的说法,圣人“不以生知自居”亦是圣不自圣,但此不自圣是为了向下以教人,即此种解释下的谦虚是有所为的,故其于表现谦德方面其实是不足的。朱子谓此乃圣人的“事实”,则是由圣人自身的德与学表现其谦德,而人之效法圣人者不仅可以见到圣人所说的“好古敏以求之”这一层,亦可以看到“不以生知自居”这一层,其中所蕴含的教学之道实较范、杨诸人所说更深刻。第二条语录说得更具体。朱子肯定地说圣人亦必须学,且圣人生知,所谓“也须学始得”当然指的是圣人之能方面,紧接着就转到圣人之“忧”上。圣人之孜孜好学,在圣人自己方面并不是为了扩充其能。这是常人仰观圣人的外部视角,圣人不会自认为己德是生知的,而学只是能方面的事情。圣人自己永远有一“忧”,即忧虑自己德业不足——这在君子亦可以做到,圣人亦不过忧此而已——但圣人在大德大业之地步而能忧,则非至德不能。盖德未至则或有间断,以及德已到某一程度而又或有自信自足之感,皆不能如圣人之恒久而乾乾不息。朱子甚至谓圣人之“生而知之”只是“知得此而已”,则此“忧”之重要性不可谓不大。再推开一步说,天地以易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5],则圣人之有忧,虽云忧己之不能修德徙义,而其实效则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如此,圣人亦焉得不多能?
综上,朱子对“生而知之”章的解释,是用尹和靖“义理”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之分,将生知的对象确定为“义理”。《集注》紧扣文义,仅说到这一步,但通过《语类》的线索,我们知道,圣人生而知之的“义理”当不只是道德、人伦与政治原则,其中也包含着因圣不自圣而产生的“忧”,且圣人由此忧虑之不已,必然不断孜孜以学。虽然圣人之学亦是在“义理”上之不断进展而希天,但由于学的对象是“古”(3)“古”首先是指某种典范,其次也包含历代典章制度等。,因此,圣人之学总有一向外的面向,而不纯是在自己的道德心中打转。“义理”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由此勾连起来,对“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的学习就意味着圣人之“多能”将成为其一大特征。于是,“圣人未有不多能者”这一命题获得了初步的论证。
三、圣人之“多能”的性质与原理
接着,我们进一步讨论圣人之“多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并从能的角度分析圣人为什么会多能。
(一)圣人之“多能”的性质
要讨论能,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关于人之能的一般分类及其含义。丁纪提出“一心分三能”的理论,认为“本能一往蠢动,乃是一种动物性之能;艺能是一种后天经验习得之能;良能是一种直接作为仁义之‘知能化’表现之能”[6]7。能是心的能力,任何人包括圣人之心都有此三种能。本能既然只是动物性之能,则要成就人道,就必须超越本能。因此,就关涉于人之德来说,或是就人做工夫而说,本能不具有正面的地位,相反,它是需要被超克的对象。而在圣人分上,就更说不着本能了,在此我们只需关注艺能与良能。
作为“人之所不学而能”[1]360者,良能是仁义之性本来一如而发出之力,即先天的道德能力,它统一于人之一心,随具体的事而展现为不同的形态,但就其本来的统一性而言它是纯一的;艺能指向后天经验性知识,当然是习而后得,且经验性就意味着多样性,这样便与良能的纯一性不同。圣人之“多能”既然用个“多”字,则指的是艺能。
(二)圣人为何“多能”
圣人之德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是良能的充极,那么如何解释从德(良能充极)到多能(艺能)的必然性?
1.才能与良能
如上所述,良能是纯粹的道德力,艺能则是后天的知识之能,两者之间似乎还需要一个沟通的媒介。朱子说:
其(圣人)义理完具,礼乐等事,便不学,也自有一副当,但力可及,故亦学之。[4]891
关于“礼乐等事”,自其为后天经验性知识方面来说,当是艺能之所能者。艺能需学而能,但朱子却说圣人对于这些事、这些能,只是力可及而学,实则圣人生而知之,其完具之“义理”中已含有对于礼乐等事的“一副当”。上文谓圣人生知之“义理”中含有一种“忧”,由此“忧”圣人乃发起一种进进不已的学习之心,此学习的过程既是义理的日进无疆,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外向的、对礼乐名物的学习与考索。这里朱子又谓圣人生来就有“一副当”,它一方面是关于礼乐等事的,因此它之为能,便不直接是良能;另一方面,这“一副当”又是生而具有的,不待学习而能,因此它又不直接是具体的艺能。这“一副当”之为“能”,实是介于良能与艺能之间,而既不直接等于良能或艺能,但同时又与二者皆相关。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能叫作“才能”。
在《孟子·告子上》篇“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章,朱子注云:
才,犹材质,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性既善,则才亦善。人之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7]334
“才”是“人之能”,则凡能皆可统曰“才”。《孟子》说不善非才之罪,则才自当从善处说,因此朱子认为此处说的“才”是人“性”之能,是表现那至善之性的。从这一点看,才能与良能发生了重合,但良能毕竟指其从性直一而发,是完全地、纯粹地关联着那至善之性的,才能就其性质来说则必含有“材质”的概念,而一说到材质总是不能离了气去说。因此,良能与这一义的才能之间仍然不能完全画等号。广义地说,一切能皆是才能,良能亦属于才能,但若强调才能在材质方面的意味,则良能不直接是才能——良能由仁义之性发起,其完成需要才能的辅助。例如,由仁之性发起一对父之孝心,进而产生一事父之行为,此即良能发生作用的过程,但事父之行为具体是怎样的则不完全由良能决定,其中的仪节之类是由才能所习得与管摄的。
朱子于圈外所收程子之言告诉我们“才”的来源与其性质:
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7]335
才的来源是气,则才能本身是一种气能,而不直接是性能。性不离气,所以作为性能的良能总是要通过作为气能的才能而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良能和才能获得了一种统一性。但气有不确定性,最基本的就是清浊的差异。清浊根据气对性的表现力来划定,表现力越强气越清,反之则越浊。这种表现力体现到“能”上面则为才能之大小,表现力强的才能大,表现力弱的才能小。此外,表现与遮蔽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气不能完全清透地表现性,就是说尚有遮蔽。如果把完全清透地表现称作本然之善的话,则遮蔽便是与之相反的过恶,这就是所谓的“遮蔽为恶”。
圣人禀气“清明纯粹,绝无渣滓”[8]871,本然之性在圣人身上是完全呈现的。换言之,圣人的才能没有对其性以及本于性而发的良能有丝毫的遮蔽间隔,良能通过才能而充极。基于此,圣人的才能就有着至善与至大两大特征。至善这一面很容易理解,不用多说,关于至大,可以分别从良能和才能上看。良能当然是至大的,而且在圣人与尚未至于圣人者之间,作为从本性上发出的良能之本来的至大性没有什么不同。在才能上说,则只有圣人是至大的,他能完全而毫无间隔地表现此性理,以充分伸展其良能;而尚未至于圣人者,则不能不说因对于性理的表现力未达到至强,而其才能相较圣人为小。当然,只要尚未至于圣人,因为没有达到至善,遮蔽也在发生着。在善与大上与圣人本无不同,却不如圣人之善、不如圣人之大,因而必要去追求那善与大;又因为与圣人之别是从气质才能上区判出来的,于是就要求一个变化气质之功。
2.才能与艺能
既然良能通过才能而展现,其必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中去,如是则才能便与艺能发生联系。而且才源于气,从而与事物同样处于气的层面,则才与事物不能无关联。朱子说:
才是能主张运用做事底。同这一事,有一人会发挥得,有不会发挥得;同这一物,有人会做得,有人不会做,此可见其才。[4]1387
才亦指一种干事处物的能力,在现实中方可见之,且要具体地去干事处物,后天性的经验知识便不可缺少,这样,才能便贯到了艺能上。艺能不独不可缺少,而且还要多,因为事物总是具有多样性的,此即事物的分殊性。事物的分殊性决定了圣人之艺能必有“多”的特征。
这种“多”的特征亦不单由事物的分殊性决定。上文提到,圣人之才能是至大的,至大本来是从其对圣人之性理、良能的表现力至强上说的,但只要这种表现力具体地将性理、良能表现到事物中,它便获得了一个广度方面的意义,要求对尽量多的事物有一个认识和处置,因此,圣人便要去学习尽量多的经验性知识,从而养成自己艺能之“多”。
(三)圣人之“多能”与其德的关系
所谓“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4]958,朱子虽然认为圣人必然多能,但在圣人的属性中,他也是将德置于能之前的。因此,圣人之“多能”的必然性其实是一种从属的必然性,德在圣人的属性中不仅具有比能更根本的地位,而且从德可以推衍出多能的要求。这样的德能关系与《论语》“太宰问于子贡”章子贡称赞孔子之语相契合,同时又能兼顾孔子“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说法。《语类》说此关系最尽:
书无所不读,事无所不能,若作强记多能观之,诚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书之当读者无所不读,欲其无不察也;事之当能者无所不能,以其无不通也。观其平日辩异端,辟邪说,如此之详,是岂不读其书而以耳剽决之耶?至于鄙贱之事虽琐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习而无不能耳。故孔子自谓“多能鄙事”,但以为学者不当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务于强记多能,固非所以为学。然事物之间分别太甚,则有修饬边幅、简忽细故之病,又非所以求尽心也。[4]2361-2362
此段乃朱子论伊川之语,虽非正论圣人,但伊川大贤,于此亦可略见圣人德能之体段。门人盖以“书无所不读,事无所不能”非形容有道君子之气象,而朱子乃正面肯定之,且推至鄙贱琐屑之事,以其皆是天理流行之域,只是不主张把这种博学多能当作一种纯粹的向外求知。最后朱子还说,人之为学固然要从德着手,但博学多能也不能忽略,如果把德与多能截然分别,则心亦有所不能尽。此种议论,皆基于以上所论圣人之德能关系。
(四)圣人之“多能”的具体指向
《论语》“太宰问于子贡”章所说的“多能”本指“多能鄙事”[1]110,即朱子所说鄙贱琐屑之事[4]2361,琴子开对此有补充说明:“子云,‘吾不试,故艺’。”[1]110若以艺能指代多能之能,艺能的本义当指关于鄙贱琐屑之事的技艺之能,但当朱子说“圣人未有不多能”时,显然不是将多能限定在技艺之能的,甚至技艺之能都不是主要所指。据《语类》:
问“吾不试,故艺”。曰:“想见圣人事事会,但不见用,所以人只见它小小技艺。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业来,不复有小小技艺之可见矣。”问:“此亦是圣人贤于尧舜处否?”曰:“也不须如此说。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不在此等小小处。此等处,非所以论圣人之优劣也。横渠便是如此说,以为孔子穷而在下,故做得许多事。如舜三十便征庸了,想见舜于小事,也煞有不会处。虽是如此,也如此说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渔,也事事去做来,所以人无缘及得圣人。”[4]959
上引语录比较孔子与舜之能。礼乐制度是孔子与舜皆能者,只不过舜得天子之位,故见于用,而孔子不得位,乃述之而传万世,朱子谓此是孔子贤于尧舜处。对于技艺之能,孔子因不得位而有“多能鄙事”之显现,舜因得位甚早而似有所欠缺,但朱子谓此不足为圣人之优劣,且谓舜于其少年之时亦曾“事事去做来”。盖艺能既是经验性的,则其天然地就具有遭遇性。此种遭遇性在技艺之能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孔子与舜得位不得位之遭遇不同,故于技艺亦有多能与少能之差。另,孔子即使“多能鄙事”,亦谓自己种地“不如老农”[1]143。因此,朱子谓技艺之能的绝对多寡并不足以影响圣人的多能,圣人于其遭遇之际,事事学之,事事能之,此即圣人之“多能”。礼乐制度虽亦因地域、时代而有所不同,但其大经大法则有不易者。相形之下,朱子所谓圣人之“多能”(或“艺能”)的主要所指不是“小小技艺”,而正是此等百世不易之大法——礼乐制度之类。《论语》“我非生而知之”章孔子“敏以求之”者,朱子引尹和靖语谓其是“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正是此“多能”所能者。
朱子关于圣人之“多能”具体所指的说法影响较为深远。较著者如丁纪将艺能分成两种:“‘艺’亦如‘游于艺’之‘艺’,‘游艺’谓学者当以六艺为游心之域也;则六艺如礼乐等,乃夫子之‘多能’而所尤能者。一方面,‘多能’并不以‘鄙事’为代表或全体赅括;另一方面,虽礼乐之为‘能’,亦未必不为后天经验性知识之‘多能’。”[6]3其以“游于艺”“六艺”之“艺”去定义“多能”,此当与朱子圣人观中的“多能”相符。
四、余论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圣人之“多能”并不意味着其全能。盖多能之能虽由良能所贯注,在天理流行之域,但其为能本身终究是经验性的,进而意味着有限性,故而求其全是不可能的。不过朱子却说:
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4]2830
“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与前引《语类》“书无所不读,事无所不能”似乎都意味着“全”,上文的至大也是一个究极性概念,似乎同样要求指向某种全能。经验事物不能穷尽,朱子没理由不清楚,那么“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究竟当如何理解呢?在笔者看来,它其实指的就是多能,但这“多能”不是经验知识的机械积累。朱子之所以会用这样似乎是全知全能的表达方式,正是为了防止对多能的平铺理解。要之,朱子圣人之“多能”包含了一种贯通:一方面,多能是德性的要求,而德性本身是浑然整全的;另一方面,此诸多之能本身是具有相关性的,不仅已经习得的能之间是可以相推的,即使是尚未习得之能,亦可由此已知之能推出去。
这种“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多能类似于《格物补传》中所说的“豁然贯通”[1]7。此处可对圣人“多能”论与格物致知论的关系稍作说明。圣人之“多能”是发向事物的艺能,格物致知穷究事物之理,二者在对象上是一致的,但却不能将它们等同。盖格物致知作为八条目之首,是学者所用的工夫,如果圣人对多能的习得就是格物致知,那岂不说明圣人尚需做工夫?如果圣人需要做格物致知的工夫,那他同样需要做诚意正心的工夫,此与宋明理学关于圣人的观念显然是矛盾的。然则,同样作为面向事物的行为,如何来分辨二者呢?工夫乃“在认为自身是不完全之存在——不是圣人——的此种严格性自觉上,所实行的极具‘意识性’之行为”[9]。格物致知是尚未至于圣人的学者为了成为圣人所开展的工夫,而圣人对多能的习得则直接属于圣人分上之事。格物致知是一种极具“意识性”之行为,即学者在困知勉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思勉工夫;圣人的多能是一种“自然性”行为的结果,即不思不勉,这当然不可说是一种工夫,而只是圣德朗照之下对事物知识的自然充拓。由此而言,格物致知最终所达到的“豁然贯通”境界与圣人“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亦不能完全等同。
“豁然贯通”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事物之理的相互融涉和格物穷理工夫积累得多后达到的“觉”的状态。因为圣人生而知之,并不依赖格物致知的工夫来达成觉悟,“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与“豁然贯通”的相似性只体现在第一方面。再者,尽管学者格物致知与圣人多能有着思勉与不思勉、工夫与非工夫之别,但二者有着相同的存在论基础。《四书或问》所引程子二语可作为此存在论基础的代表:“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8]525“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8]525前一语是说万物之理的同原性,后一语则点明物我之理的同原性,此两语亦正对应着“豁然贯通”两方面的含义。另,在第二方面,圣人多能论与学者格物致知论依然存有一些差别:物我一理是二者共同具备的,但在圣人却用不着说“合内外之道”,因为“合”字仍然是工夫语。正因为在学者分上尚需“合内外”的工夫,所以此工夫表现为“才明彼,即晓此”之由彼及此的过程,而圣人之“多能”是由圣德之忧所引发的对艺能的习得,体现为由此及彼的自然充拓。
总之,圣人多能与学者格物致知有着万物一理、物我一理的相同存在论基础,因而都表现为对事物之理的穷究,但由于圣人与学者分位的不同,学者格物致知与圣人多能有着工夫与非工夫的差别,圣人多能亦可说是为学者格物致知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范例。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