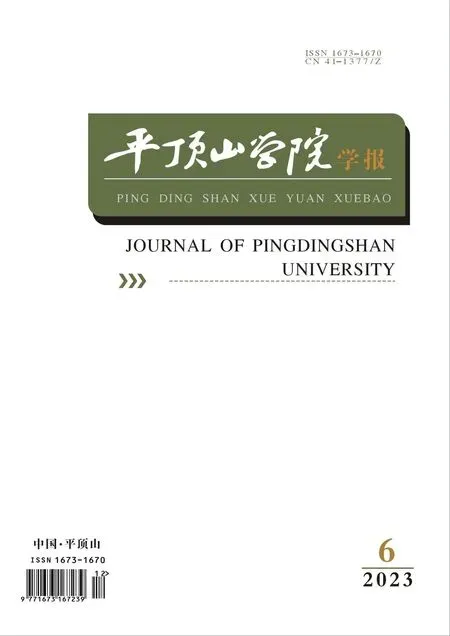从《人间词话》看“一代之文学”的现实革命性
辛 月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在论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通常认为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集大成的结论,但其实早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就已经为“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做好铺垫。一般而言,学界多认为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更多是沿袭中国传统通变说,将其定位为走古典路子的晚清遗老;并多与新锐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相比较,而凸显王氏的保守性。但实际上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多方面呈现出其来源于西方并力图拯救中国的现实革命意义。
一、《人间词话》里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一代之文学”的因袭与更迭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07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以集大成的方式明确提出。回顾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在王国维发表《宋元戏曲考》之前就已有多达30位以上的学者表述过类似观点。
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考据通常认为其自金元发端,至明清之际得以丰富发展,到王国维集大成。元代虞集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2]已初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雏形,将文体与时代相联系。但虞集所论并非纯粹的文学,谈论的是“一代之技艺”。将宋代的代表选作道学,可见其对文学的定义仍处于杂文学状态,还未完全提炼到纯文学的文体嬗变观上。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3]沿袭了虞集的观点,并将“宋之道学”改为“宋词”。
明代文学家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元人的理论,胡应麟指出:“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4]接受虞集所论,并补充“晋之书”,将文体与时代更紧密地联系。茅一相更进一步上溯到先秦文学:“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令、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5]38但“晋之字”就可见其泛而杂的文学观念。王骥德将文体限定在韵文,并认定从《诗经》开始文体演变保持的是代降说的趋势:“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上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6]认为至元曲时,文学已一代不如一代。李贽将小说正式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范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7]李渔认识到各朝文体的兴盛,指出:“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8]清代焦循全面总结发展了元明以来文体嬗变的文学发展观,并直接影响启发了王国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直言:“焦里堂《易余籥录》之说,可谓具眼矣。”[1]388“焦氏之说,详见《易余籥录》卷十五,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故周以前惟有三百篇,楚惟有骚,汉惟有赋,魏晋六朝惟有五言,唐惟有律绝,宋惟有词,金元惟有曲,明惟有八股。”[9]6只可惜他将八股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列,只重文学形式而忽视了文学内容,也没有看到明清小说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回顾前人所论,虽有涉及“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但“文学”所蕴含的内容还比较复杂,保持的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杂而泛的文学观念。此外,即使有一两人涉及对文体代嬗的原因探索,也都是寥寥数语,并未深入探究。如胡应麟就曾试图从文体自身演变规律的角度,解释其代嬗的原因:“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10]王世贞从音乐曲律和文学接受的角度加以说明:“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5]27虽论及文体嬗变的缘由,但都失于片面。而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所以成为集大成者,也正是由于其不仅将文学的概念精确定位为纯文学领域,而且还具体指出文体为何而嬗变。
(二)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一代之文学”
其实王国维早在《人间词话》中就已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表露。他提出文学嬗变的趋势是沿“始盛终衰”的路径:“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11]13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反对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摆脱了崇古抑今的传统旧文学观念束缚,并在累积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指出文学嬗变的缘由。从外部看,一代文学都是一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折现,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也相应随之更迭。从文学内部看,文学自身发展有一个从兴到盛再到落入习套而转衰的过程,文学自身的始盛终衰也推动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文体代嬗的第一个原因是随着一代文学的发展,最终流于习套,难以脱离习惯定式。“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11]19哪怕天才豪士也难有新的创造。第二个原因是一代文学在发展成熟之后,沦落为美刺投赠的工具,不再是抒写人生志趣、表露自然真情之至作。“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11]17文学成为创作者们谋取功名的功利之物,失了其本色与活力,自是难以为继,只有将真性与才性寄寓于新文体。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就是极看重文学本色与创作真情,而一代文学后期的发展不免让他失望:“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11]14从而转向新文体的创作也是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新文体对于新时代之人更易上手,更易创极工之作。“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11]13首先王国维否定了诗胜于词、难于词的传统观念,可见王氏为词正名,对于代降的文体观的反对。其次王国维认为一代有适应一代之文学,从王国维否定《提要》就可得知“宋人不知诗”并非文采浅薄,仅仅只是“能举七十斤者”,而宋人对于词更能得心应手,抒写欢愉愁怨之真情。除以上三个具体原因,王国维对文体音律、文学接受等也都有相关阐释,他提倡小说戏曲,倡导文学创作自然真情不加以矫饰,呼吁“语语皆在目前”的简明亲切,对读者来说在文学接受上便更容易,文体也能更适应时代所需。
王国维“始盛终衰”的文体嬗变观一改传统古胜于今的复古论调,并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代的新文学观念也无形中主张了新革命,为后起的小说戏曲提供了理论支撑。“始盛终衰”的文体观表明在旧文体衰落之际,新的文体已经滋生孕育,倡导创作者应顺应新的文体发展趋势,并积极加以创造。他举屈原的例子说:“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11]37《沧浪》《凤兮》已呈现与《诗经》不同的新文体之势,屈原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发挥,从而创生出冠绝一代的楚辞。王国维此言正是肯定文体代嬗,肯定新时代小说的创作。
二、王国维“一代之文学”所体现的现实革命性
在近20年的相关史论著作中,关于王国维与现实革命的话题又集体失声。要么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涉及王国维,但又不直接将他们相联系,不愿承认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属于现代意识。要么就根本认为王国维与五四并无关系,形成中国现代文论史的“集体无意识”[12]。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将王国维列入文学革命先行者的行列。吴文祺惊叹:“不料在二十年前的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只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庵先生。”[13]王德毅也说:“先生致力于文学研究为时虽不长,但其见解却为五四的新文学运动铺下坦平的道路。”[14]前文论及王国维“一代之文学”观念受前人影响,尤其是焦循,但前人之误不仅在于文学概念泛杂,且重形式过于内容。王国维在继承的同时,又暗自在内容上加以变革。缪钺曾直言:“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15]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所以有现实革命性,正是由于其接续与传播西方思想,并力图结合时代以救现实,与文学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王国维提出了纯文学的观念。王国维引进康德的“合目的性”的无功利美学和席勒、叔本华的“游戏说”,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1]25。将非功利的纯文学从传统杂文学的观念中提炼出来,开启了中国现代“纯文学”运动的先河。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严格规定了纯文学体裁,符合现代文学观念,使纯文学从此于繁杂的文学概念中独立。此外,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实乃无用之大用,他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16]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超功利的,与人生相连,最终所达到的是利用文学开启民智、拯救国民性。王国维根本上是想利用文学实现启蒙,达到情感与精神的升华,最终的目光仍是着眼于现实社会。
其次,“一代之文学”促进了文学史观的建构。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自20世纪初由西方引入。但我国传统古代的文学“或指文献典册,或表文章、学术,或说官职,或言学人,层累而下,十分难辩”。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现在所说的‘文学’,同时又指一门学科,这个学科中国本来没有,它的方法规范、概念语言全部都借鉴于西方,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在传统学术史中的空白,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它的生疏之感”[17]。1904年林传甲就曾尝试编撰《中国文学史》,“自古文、籀文、小篆……唐以后正书的第一篇起,一下则分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以至骈散等类,分篇叙述,凡十六篇”[18]3。但仅从目录上就可见其分类不清、辨体不明的问题。与此同时的黄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凡制、诏、策、谕、诗词赋曲,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无所不包,实在是一部洋洋大观,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书”[18]1。虽体质庞大、兼收并蓄,但“文学”观念实在是模糊不清。王国维提出的纯文学观念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选材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厘清了材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学史观念。
再次,王国维以“自然”为标准,与五四新文学不谋而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强调不用典、忌代字、语语皆在目前的真切自然感受。通过对比“隔”与“不隔”,强调真与自然的艺术感受:“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此。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栏杆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11]9“不隔”乃是陶渊明、谢灵运一般,写诗作词基于真情、注重自然,使人感到“语语皆在目前”。而王氏列举的“隔”则都是多用典故、用语艰涩、精思雕琢之后的词作。他认为无论是写景还是写情,都需要给人以鲜明、生动、自然、“语语皆在目前”的真切感受,反对过多的遣词造句、矫揉造作、用典代字等人为现象,崇尚真情、真切与自然。他在《宋元戏曲考》里以“自然”为标准评价元杂剧:“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1]389这些都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五四新文学的要求不谋而合。胡适提出文学八事:“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做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19]4陈独秀倡导“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16。王国维所强调的真切自然的文学标准与五四新文学遥相呼应,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积极作用。
最后,王国维并非持代降观。中国传统复古思想形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代降观,即使认可一代有一代之胜,也认为后代不如前代。胡应麟就曾说:“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虽愈趋愈下,要为各极其工。”[20]顾炎武也认为:“《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21]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晚清遗老的王国维以保守派的思想支持着代降说。但实际上,王国维所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持一代不如一代的代降说。他在《人间词话》中论及诗与词时,写道:“《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11]13王国维首先否定了传统的诗胜于词、难于词的观念,可见王氏为词正名,对于代降的文体观表示反对。随后,王国维比较唐诗与宋诗、宋诗与宋词时就说:“诗之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11]17认为到了宋代“词胜于诗远甚”,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文体自身的演变,必须更新文体才能保持文学创作的生机与活力,若是固守前代文学则必将陷入衰败境地。黄霖等学者也认为王国维“反对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解脱了尊崇往古鄙薄新异的传统旧文学观念的束缚”[11]33。破除崇古抑今的传统文学价值观,为五四新文学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解放作用。
三、“一代之文学”的影响
王国维所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助推文学革命、更新文学观念的现实革命意义,还对后世的文学思想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王国维深刻影响了胡适,促进了文学进化史观的形成。另一方面,王国维将小说戏曲放上台面,破除了雅俗之辨,为后世雅俗共赏的文学新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
首先,王国维影响了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对于王国维是否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学史,学界至今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王国维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以新文体作为‘时代文学’的评判标尺,凡新必是‘一代之胜’”[22],随之影响胡云翼等学者。也有人认为王国维秉持的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文体通变说,蒋寅曾断言王国维“没有超出古人的范围”[23],齐森华等学者也认为王国维继承的是传统朴素的文体通变观[24],只是王氏的“一代之文学”观影响了真正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熏陶的胡适,并由此影响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但无论王国维在自己的阐述中是否表明进化论的思想,文学进化论都与王国维有着密切关系。首先,王国维深受西方文艺美学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西方蔚为大观,王国维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且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严复提出了天演论、康有为等人在社会上大力倡导革新进化思想,王国维就算明面上不说,实际上也对此必有了解。此外,胡适对王国维的推崇和敬仰是不可否认的文学史事实,王国维更是在“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上深刻影响了胡适。谷永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就曾说:“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受尽先生之影响可也。”[9]9在“一代之文学”观上,胡适就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的学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9]7结合西方进化论,提出“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革新文学价值观,为文学革命助力。
其次,王国维的“一代之文学”将小说戏曲放上台面,破除了雅俗之辨。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体是有尊卑等级秩序的。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25]。小说戏曲一直都是小道之学,“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26]。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可谓是真正将戏曲放上台面,纳入中国传统文学的领域加以考察。吴文琪惊叹王国维见解的卓越:“不料在二十年前的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只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14]1王国维称:“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1]372“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曲。”[1]389在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中并无尊卑优劣之分,以“自然”为标准,极大提升了戏曲的地位,破除了“雅俗之辨”。王国维重视小说戏曲,认为无论何种文体只要能达到“自然”之境界都可以成为“千古独绝之文学”,登上文学顶峰。当时正值梁启超等人发动三界革命之时,极力倡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7]。新一代文学艺术家们对小说与剧本的创作热情正盛。王国维认为小说戏曲才是真正的文学,无意中助力了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的继续发展。
四、结语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作为传统理论的集大成,在《人间词话》中就已有明确的表述并包含具体阐发。此观点结合中国古代传统并援引西方概念,以图达到拯救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的目的,助推了五四新文学革命。王国维的现实革命性也在其中得以展现。虽然王国维对于新文化运动本身持反对态度,明确反对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方面由于他忠君保皇的保守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与他崇尚古雅美的美学观念有关。但王国维身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又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影响,是新文学革命很重要的助推者与中介。作为保守派的一方,王国维的许多主张都中和了保守与革新之间的矛盾。此外,王国维还深钻德国古典与近代西方哲学,广泛涉猎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相关领域,在改造国民思想的层面上,无论如何也都是一场现代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