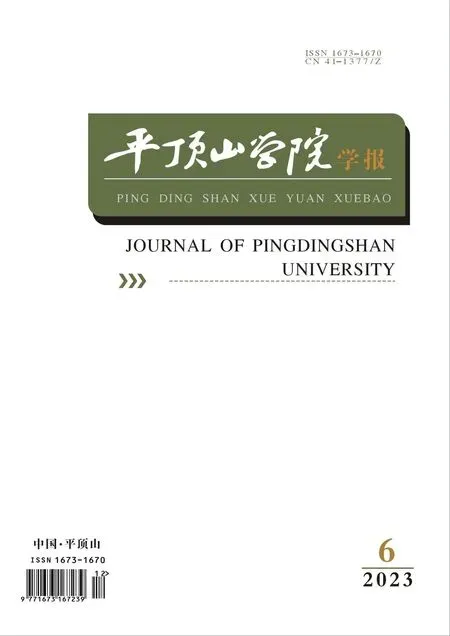宋代土兵问题试探
李 硕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元代以前,土兵多指本地武装,随着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确立,土兵越来越多地指代少数民族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从现有研究来看,土司制度下的土兵研究已经相当系统(1)详参李良品、李思睿:《中国土兵问题研究综述》,见《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3年第4期,第37—42页。该文对2013年以前土兵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梳理,但其视角集中于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下的土兵。文中还指出,宋代所称“土兵”的意思与土司兵不同。,关于宋代之前土兵的专门研究比较少见(2)笔者眼力所及,唯有朱德军、杜文玉:《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见《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145—151页。该文认为,“土军”指本州、本道的武装力量,与外来的“客军”相对。,宋代土兵研究则散见于宋代军制及地方治安管理的讨论中(3)如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8—101页)中专设“土兵”一节,强调宋代土兵本地军队之意,认为其隶属地方巡检司,主要负责维护地方治安。苗书梅《宋代巡检再探》(邓小南:《宋史研究论文集(2008)》,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也提到:“北宋中期元丰年间以后,内地巡检兵力以土兵为主。”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56—463页)指出,沿边土军在国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战斗力甚至强过更戍的中央禁军。黄宽重在《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中提到,宋朝中央正规军以拱卫京师和边境布防为主要任务,对于其他地区的军事需求往往绌于应付,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宋廷“将地方上一定户等以上的百姓组成弓手、土兵等职役的角色”,担负起维护基层治安的工作。。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宋代土兵源流及其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宋代土兵的大致构成,并着重论述宋代土兵所担负的职能。
一、宋代土兵的界定
宋代是土兵的关键发展阶段,厘清宋代土兵的发展脉络和基本概念不仅是基础工作,而且非常重要。
(一)宋代土兵的源流
“土兵”一词在北宋之前就已出现,尤其在唐中期以后的史籍中大量涌现,这应与当时的军制变化息息相关。府兵制盛行时,全国大部分士兵都可算作地方军队,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土兵自然没有相应的指代。唐中期以后,均田制被破坏,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逐渐衰落,并且随着藩镇坐大,地方军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相对于中央掌控的兵力而言,主要由地方掌控的军事力量就被视为土兵。
五代算得上地方武力强盛时期,虽然统治者已经有意削弱之,但总体上还是外强内弱。宋初继续削弱地方的兵权,并且改革募兵制,加强中央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掌控,逐渐扭转了五代时期的军事弊政。这种对于地方武力的削弱使得土兵在北宋前期没有得到重视,土兵并不被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种。《宋史·兵制》中将宋代兵制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类[1]4569,并没有土兵。直到宋神宗时期,土兵才被正式列入国家兵制中。《神宗正史·职官志》载:“凡联其什伍而教之战为民兵,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就其乡井募以御盗为土军。”[2]神宗朝单独设立土兵,并将其职能确定为维护地方治安,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宋神宗朝,土兵依然被广泛运用于国防事务中。如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边事,王安石说:“今东兵全不可用,惟土兵可用。”[3]5610又如,为加强西北边务,熙宁六年(1073),“诏以秦凤路军马六分属熙河路,人二万九千七百二十二、马三千二百七十八,驻泊兵一万三百二十八、马九百四十八,土兵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四、马二千三百二十,并属熙河路”[3]5904,其中土兵的数量比驻泊禁军还要多。
可见,自唐末五代以来,土兵逐渐成为地方武力的代名词,但宋代前期的史料中对于土兵的记载比较少,且宋人在提及土兵时常有前后矛盾、使用混乱的情况(详见下文)。这表明宋代土兵的具体所指尚不清晰,当然更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
(二)宋代土兵的概念
宋代“土兵”到底为何物?按王曾瑜所讲,其“最初仅作本地军之意”,主要招募当地土人组成,隶属地方巡检司,担负地方治安管理的任务[4]。历史类辞典中也多收录有该词条,现择其要者列举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称本地军队为土兵。宋神宗时,于禁兵、厢兵外,另设土兵,隶各地巡检司,作为地方治安部队。因土兵往往屯驻于各巡检司砦,故又称砦兵。”[5]《中华军事职官大典》称,宋代土兵系“各地巡检司招募和统领的地方武装士兵”,亦即“招募当地土著人”为土兵[6]。《中国官制大辞典》:“宋代地方治安军之一。隶属于各地巡检司,与县尉司的弓手共同维持地方治安。”[7]《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大辞典》:“宋代乡兵的一种。宋神宗时,于禁兵、厢兵之外,另设土兵,作为地方武装,隶于各地巡检司。每巡检司一般辖土兵百人左右。土兵采用禁兵中都一级编制。因土兵屯驻于各巡检司砦(寨),故亦称‘砦兵’。”[8]这些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太过笼统,而且倾向于认为宋代土兵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地方治安。其实,宋代土兵问题相当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
笔者以为,在广义上来讲,土兵就是指由当地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与之相对的是外来更戍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禁军、乡兵都应在土兵的范围之内。若是按地域划分,土兵又可分为沿边土兵与内地土兵,沿边土兵主要担负国防任务,而内地土兵的职能主要是维持乡里治安。
二、宋代土兵的构成
宋代史料中将土兵与其他军种混用的情况,表明土兵在概念上泛指地方武装力量,亦即土兵是由当地多个军种所构成的。
庆历二年(1042),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3]3316据此可知,他认为五代时期的地方武装就是土兵。随后贾昌朝又上奏了六条有关边事的建议,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属,盖土兵遗制也。”[3]3317在贾昌朝看来,强壮、弓箭手等地方武装均属于土兵。皇祐二年(1050),包拯曾上奏折《请留禁军不差出招置土兵》,其主要内容却都是表达增置民兵之意:“今河北河东沿边,兵寡财匮,卒有急难,惟有民兵可用。”[9]又如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文彦博等人争之,“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王安石反问道:“前代征琉球,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宋神宗也心生疑惑:“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对此,王安石解释道:“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10]这段对话中“土兵”“府兵”“民兵”同出,时人并不以土兵和民兵混用为错误。民兵是乡兵的另一种称呼[11],强壮、弓箭手也都是乡兵。可以说,当时,在很多大臣甚至是皇帝的眼中,土兵和耕战合一的乡兵并无差异。
除乡兵外,地方禁军与土兵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了应对西夏的进攻,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其中第七条讲道:“蕃落、广锐、振武、保捷,皆是土兵(4)原文“皆是士兵”应作“皆是土兵”。详参程龙:《〈续资治通鉴长编〉考证一则》,见《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8页。,材力伉健,武艺精强,战斗常为士卒先。”[3]3135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番号的宋兵在此之前已经是地方禁军。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诏陕西沿边州军兵士先选中者,并升为禁军,名保捷”[1]4573。次年,“命使臣分往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陇、鄜、延等州,于保安、保毅军内,与逐处官吏选取有力者共二万人,各于本州置营,升为禁军,号曰振武指挥”[1]4573。蕃落军于宋真宗天禧(1017—1021)后升为禁军[1]4593。广锐军更不必言,其隶属于宋代禁军统领机构之一——侍卫司,真宗咸平(998—1003)以后又“选振武兵增之”[1]4591。
这种地方禁军归属土兵的情况,与宋代兵制中的升格现象有关。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书、枢密院奏,乞简河东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为义勇指挥,陕西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从之”[3]3227。保捷军是地方禁军,弓手是乡兵的一种,将弓手刺面升格为地方禁军使得耕战合一的乡兵变成了职业军人。另,英宗治平(1064—1067)时,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3]4916可见,这种升格现象在战争期间很常见。加之前文已述,在宋人语境中,乡兵与土兵差异不大,相应地由乡兵升格而来的地方禁军也归属土兵。
综上所述,土兵在宋代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作为与更戍禁军相对的地方军队,就其组成结构而言既包括地方上耕战合一的乡兵,也包括由乡兵升格而来的地方禁军。
三、宋代土兵的主要职能
土兵作为一种地方武力,在宋代的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土兵涉及的军种较多,但若从地域来划分,宋代土兵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沿边土兵和内地土兵。沿边土兵的职能相对多样,既要抵抗外敌入侵、参与开边拓土,另外还负责当地的日常治安。内地土兵的职能较为单一,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如追凶捕盗、压制叛乱。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酸低氧二硫化钼的制备方法,具体为:首先将钼精矿在盐酸和硝酸中浸出、搅拌,过滤,然后将滤饼在盐酸和氢氟酸中继续浸出、搅拌,过滤,最后对滤饼用氨水和清水依次进行洗涤,并干燥,即得到低酸低氧二硫化钼。相较于一般方法,采用本发明方法制备得到的二硫化钼,其酸值与氧化钼含量均大幅度降低,提高了二硫化钼的质量,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一)沿边土兵的职能
北宋开国后,吸取五代教训,收天下精兵聚集京城,实行更戍法,形成内外相互制约的局面。此举虽然解决了五代时期地方武力过强的弊症,但矫枉过正,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的软弱。另外,禁军队伍的扩大以及更戍法的实施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为此,在边境地区以土兵代替禁军的建议早已有之。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安阳人陈贯就曾上书言:“国家收天下材勇以备禁旅,赖赐予廪给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识战,当以卫京师,不当以戍边。莫若募土人隶本军,又籍民丁为府兵,使北兵捍狄,西兵捍戎,不独审练敌情,熟习地形,且皆乐战斗,无骄心。”[3]1323陈贯这番话不仅表明西兵、北兵是由土兵组成的,并且他还以为中央禁军不适合戍边,应该加强西兵和北兵的力量,从而巩固边防。而在宋真宗朝,沿边州军的地方武力确实有明显提升,保捷、蕃落等地方禁军都设立于这一时期(详见上文)。
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元昊称帝,北宋与西夏之间局势紧张,而且随着中央禁军人数的不断增加,军人的素质持续下滑。尤其是到了仁宗朝,宋军与西夏作战时接连败退,东兵戍边的劣势越发明显,朝堂上关于增置土兵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宝元二年(1039),夏竦上陈边事十策,第六条是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3]2912。这引起了知河中府杨偕的反对:“西兵比继迁时十增七八,县官困于供亿。今州复益一二千人,则岁费缗钱又增百余万,国用民力,恐由此屈。若训习士卒,使之精锐,选任将帅,求之方略,自然以寡击众,以一当百。”[3]2958他认为增置土兵无补于防守,只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不如将现有兵力勤加训练,增强战斗力。宋廷令夏竦再议,于是夏竦详细论证了增募土兵的优点:
陕西防秋之弊,无甚东兵,一则不惯登陟,二则不耐寒暑,三则饮食难充,骄懦相习,四则廪给至厚,倍费钱帛。今募土兵,一则劲悍便习,各护乡土,人自为战。二则识山川道路,堪耐饥寒。三则代东兵归卫京师。四则岁省刍粮巨万。五则今岁霜早,收聚小民,免至春饥,起而为盗。六则增数十指挥精兵,詟伏贼气,乃国家万世之利。[3]2958
夏竦认为相比于东兵,土兵优势有六,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土兵是招募本地人,他们熟悉道路,习惯生活环境,并且是保卫自己的家乡,所以更加积极主动;其次,增置土兵后,可以放还东兵,加强京师的守备力量,并且土兵的薪俸少于东兵,以土兵代东兵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最后,收拢灾民为土兵,可以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上《再论攻守二策》,更是直接称“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3]3216。随着边事失利,越来越多的北宋官员开始认识到沿边土兵的优势及其重要性。
庆历三年(1043)以后,宋夏关系逐渐缓和,西夏迫于内外压力,积极寻求和议。这一时期宋政府关于土兵建设的步伐也开始放缓,毕竟土兵实力的增强本身是违背北宋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的。庆历四年(1044),韩琦、范仲淹上奏陕西八事,涉及“新刺保捷土兵内,有尫弱不堪战阵者,减放归农”[3]3623,建议裁减老弱土兵。庆历(1041—1048)中后期河北地区兵变频发,更是给北宋政府敲响了警钟。张方平于庆历八年(1048)奏请“发在京禁军就逐州驻扎,使其势足与土兵相制,庶乎置器于安也”[3]3927,要求重新开始限制地方武力发展。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捐,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12]
苏辙认为一个土兵的材力能够抵三个禁兵,而供养一个禁军的费用却能够供养三个土兵,这样来看用土兵戍边的好处要远大于用更戍禁军。苏辙之语还是比较可信的,宋神宗朝能够取得较大的军事成就,确实离不开土兵的参与。熙宁五年(1072)十月设置熙河路后,次年二月“诏以秦凤路军马六分属熙河路,人二万九千七百二十二、马三千二百七十八,驻泊兵一万三百二十八、马九百四十八,土兵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四、马二千三百二十,并属熙河路。遇有边事,则以泾原将官领本路土兵并山外弓箭手防托为策应兵”[3]5904。沿边诸路的土兵不仅积极参与熙河开边,并且负有跨路的军事任务。范学辉也认为,宋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陕西鄜延、泾原、环庆、秦凤、熙河等各路地方兵马即‘西军’更持续壮大”,成为北宋全面夺取宋夏战争主动权的关键(5)详参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7—468页。另,作者还随之指出,靖康之变时陕西“西军”积极地效忠勤王,直到南宋初年,“西军”仍是宋廷维持统治的中流砥柱。。
除宋夏战争外,宋仁宗朝名将狄青率兵平定西南边境的侬智高叛乱时,尤其是在宋军大破侬智高于广西归仁铺之际,土兵也起到关键作用。皇祐四年(1052)十月,从狄青之请,“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3]4175。皇祐五年(1053)正月,“其战于归仁也”,右班殿直张玉为先锋,如京副使贾逵将左,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将右。“及节搏贼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数困而心慑易衄,苟待令必为贼所薄,且兵法先据高者胜,乃引兵疾趋山,立始定而贼至。逵拥众而下,挥剑大呼,断贼阵为二,玉以先锋突出阵前,而青麾蕃落骑兵出贼后,贼遂大溃。”[3]4193此战中贾逵临机应变,所率土兵的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违令而胜”,狄青亦肯定其此举曰:“权也,何罪之有!”[3]4193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沿边土兵作为国防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防守中还是在征伐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土兵作为地方军队,可以在很多军事任务中代替东兵,并且发挥东兵所没有的优势。南宋建立后,随着国防形势的变化,地方军马的数量虽然依旧可观,但逐渐不再称为土兵,其职责也基本上是维持地方治安。
(二)内地土兵的职能
相比于沿边土兵,内地土兵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作为地方巡检司之下的兵力,没有戍边的职责,主要负责管理地方治安。《宋史·职官志》中对巡检司有详细的记载:“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捍御盗贼。”[1]3982此外,有些寨堡也由土兵驻守:“寨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寨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1]3979苗书梅在《宋代巡检初探》中将巡检分为两类,一类是戍边巡检,另一类是治安巡检,前者在北宋逐渐减少,南宋时近乎绝迹,后者的数量则逐渐增多,并且职能逐渐明确[13]。她在《宋代巡检再探》中又提到,北宋中期元丰年间(1078—1085)以后,内地巡检兵力以土兵为主[14]。加之内地土兵的史料分布主要在北宋中后期,并以南宋居多,可以说,内地土兵在元丰(1078—1085)以后逐渐增多。
所谓“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15],作为治安军的内地土兵常与隶属于县尉的弓手一起出现,两者作为基层维稳力量,相互之间紧密配合。对此,地方官员看得更加清楚,南宋绍定(1228—1233)初年平江知府李寿朋“到任之初,首访军籍”,并在《新军省札》中谈到,“国家置禁军以壮蕃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盗贼”[16]。在时人看来,弓手和土兵都是地方治安管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相比之下,土兵比弓手更加专业化。宋代土兵应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正规军人,百姓主动应募的热情并不高。熙宁九年(1076),知彭州吕陶进言:“今若招土兵数未足,则莫若多募弓手,阅习既久,籍而为卒,彼亦愿从。”[3]6710土兵兵员不足,地方官员建议先招募弓手,加以训练后再将其添为正规军。
由于分布地域广泛,不同地区的土兵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元丰四年(1081)河北路转运副使贾青言道:“福建路山川险阻,人材短小,自来民间所用兵械,与官兵名件制度轻重大小不同。欲乞依本路民间所用兵械制造,以备捕贼。至于新招土兵所用枪刀、排笠坐作进退法式,亦乞依民间精巧之法。”[3]7572因为身材的原因,福建土兵不习惯使用制式武器,而有改用当地常用兵器的需求。同样因为地域原因,元丰六年(1083)知宣州陈侗“乞沿江湖州军各置水军三五百人,以巡检主之,教以水战”,以便捉贼捕盗,“诏应已招置土兵巡检地分,如有江河海道”,要训练土兵进行水战[3]8074。
综合来看,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作为维护基层治安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内地土兵的作用和地位均不可忽视。
四、余论
将土兵放到地方武力体系中来看,其发展变化深刻反映了自唐中后期至宋代地方武力的起伏。唐中后期的地方武力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掌控,转化为受地方控制的武装力量。后周时期,地方武力的控制权逐渐被收归中央,北宋前期对地方武力的控制继续加强,土兵的实力随之不断减弱。但北宋长久以来受到辽与西夏的军事威胁,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加强地方武力,逐渐构建了受中央严格控制的地方武力体系,宋代土兵尤其是沿边土兵就是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从具体职能上来看,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沿边土兵在国防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补足中央禁军短板的最强保障;内地土兵则在地方巡检司的指挥下,长期担负起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任务。
同时,宋代土兵特别是内地土兵的实际功效一直受到质疑。元丰六年(1083),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孙览言:“看详诸路巡检土兵立法之意,盖谓土人习知本处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缉捕盗贼。近巡历诸州,见所招土兵多老弱,堪被甲可擒盗者十无三四,仍未必皆土人。”[3]8183时人不仅常有巡检土兵缺乏战斗力之虞,而且倾向于认为其易于徇私枉法。元祐二年(1087),据枢密院“今岁久,(土兵)以亲戚乡里之故,或庇其为奸。请以禁军相兼”之言,“诏诸路巡检土兵,以元额之半差禁军”[3]9639,用来防止土兵滋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