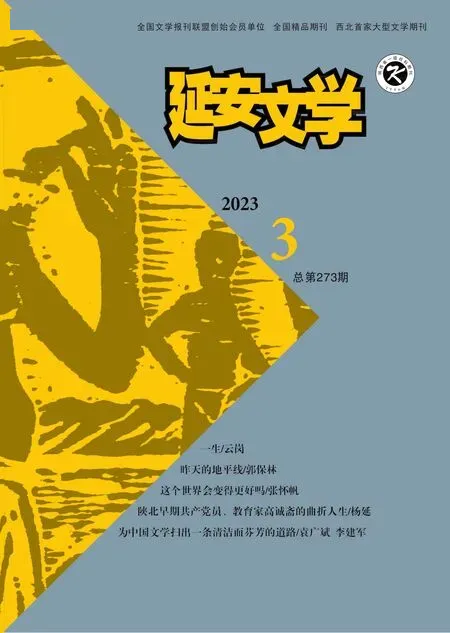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与回乡知青、知青文学
南生桥
2020年冬,读了解志熙《经典的回味——〈平凡的世界〉的几种读法》,深为感动以至震撼——此文不但是我当时首次见到的正式论及回乡知青之文,而且在论述中进入角色,由小说中的孙家兄弟联系到哥哥和自己,不但最为深刻,尤其倍感亲切。作者说:“《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特别是指出:“‘回乡知青’中的优秀分子大多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为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普遍秉持着来自乡土社会的质朴踏实、善良仁义、自尊好强、富有责任心等优秀品格,……其二,这些乡村青年在村队、乡镇和县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学到了知识,也开阔了社会视野,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对城乡的差别体会深刻。”
作为一个有十足十七年“农龄”的回乡知青过来人,读罢此文顿生知己、知音之感,再次激起强烈的表达愿望。感触虽多,在此只择要谈其三点。
第一,“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主要指回乡知青。虽然他们“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但在后来的文学世界里却几乎缺席。
我曾在书评《热血知青桑梓路,悲歌一曲向天鸣——读〈血染白丝巾〉》中说过:
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相同,《血染白丝巾》的叙写对象是回乡知青,其题材是回乡知青的人生命运和遭际。所异者在于前者的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此书却是在其前的六七十年代。因而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她是在“知青文学”一边倒地写下乡知青的语境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回乡知青这个曾经重要的群体,提醒人们城乡二元的天悬地隔。
实际上,“文革”前的知青原来主要指回乡知青,另一部分则指1962-1965年下乡的为数不多的老知青。当时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如徐建春、邢燕子、董加耕、韩志刚、吕玉兰等许多人都是回乡知青。毛泽东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个按语里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源于刘少奇讲话的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都是主要就回乡知青而言的。
对此,我在最近的一探究竟中才知,早在1998年定宜庄、刘小萌就分头撰写、同时出版过两本《中国知青史》,定著的副题是《初澜:1953~1968年》,刘著的副题是《大潮:1966~1980年》。两部书都曾“正式论及回乡知青”。定著的《前言》说:
“回乡知青”与“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其实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
该书在封底勒口的《内容概要》重申上述说法。虽然作者说“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回乡知青”,实际上书中论及回乡知青的文字总计只有23页,仅占全书326页的7%。这也难怪。回乡知青实在太分散了,何况也没有其他可靠的文本依据。但两书却为上述说法提供了部分数据支持。定著曰:“1964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4000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因“几十万”是个模糊数字,在此权且参照刘著之表述,以1962—1966年五年间上山下乡知青总计129万人计算,也不过占1964年一年知青总数4000余万的3%,其余97%全为回乡知青,二者数字相差31倍之巨。即使在“文革”中有1647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回乡知青人数也至少是其3倍以上。
但经过“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再到后来的集体回城,及随之而起且持续数十年的“知青文学”,人们心目中的知青似乎专指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这批人了,而“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并曾辉煌多年的回乡知青倒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其原因主要是这次上山下乡的人数之多、声势之大,空前绝后;他们原来又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有极强的凝聚性和话语能力,并曾弄出过很大的响动(如集体卧轨事件等),惊动过中南海。而回乡知青的人数虽多,却由于“分散在广大农村,与其祖祖辈辈的先人一样,处于社会边缘,没有什么凝聚性,容易被漠视或遗忘,于是终于成了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当年在官方话语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回乡知青,在后来的文学世界里却几乎缺席。”
第二、“文革”前也有反映回乡知青的文艺作品和大量通讯报道,但并无“知青文学”之名,且其都是代言体。
“文革”前也有不少反映回乡知青的文艺作品。最早著名的是马烽1954年发表的书信体短篇小说《韩梅梅》,其主人公韩梅梅就是一个回乡养猪的高小毕业生。此作当时影响甚大,1955年改名为《三封信》选入高小语文第三册(此课本我现仍保存),还改编成多种戏曲,我在当时就演过改编为眉户剧的《韩梅梅》中的梅梅她爹,至今还能唱出其中的一段唱词。而1959年拍摄的马烽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更广为人知,其主要人物孔淑贞、李克明等是回乡中学毕业生。还有同年首演、1963年拍为电影的豫剧《朝阳沟》,其男主人公拴保是回乡高中毕业生,跟着他下乡的同学恋人银环是城里人。时逾一个甲子,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豫剧《朝阳沟》的影响依然存在,前者由郭兰英演唱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后者的主要唱段《亲家母,你坐下》《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至今仍是广受欢迎的电影金曲。虽然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巨大而持久,当时媒体上也有大量宣传上述回乡知青典型的通讯报道,但并无“知青文学”之名。而且它们与后来的知青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其作者与笔下人物(作品主人公)的社会角色不同,是代言体;而知青文学的作者与笔下人物的社会角色相同,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是“自言体”。至于同时期反映回乡知青悲剧人物钱宗仁的报告文学《胡杨泪》虽然也影响巨大,却似乎未被视为知青文学。
第三、《平凡的世界》影响深广而且持久,远非知青文学可比;对知青文学后来也出现负面评价。
以数量而言,写回乡知青的名作几乎只有路遥亦属自言体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知青文学却曾以强势的联翩而出辉煌一时,再辅之以影视和其他媒体的助威,终于形成声势颇大的立体舆论场。于是无意之间,路遥似乎是在单英战群雄。但知青文学声势虽大,持久影响却不及《人生》尤其是至今仍为热点的《平凡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的天平渐渐向后者倾斜。恕我直言,对前者那些因人生落差大而产生的浓厚落难、悲切情调产生强烈共鸣的,大多是其同命运者、亲属以及其他具有悲悯情怀的人,至于那些哀怨诉苦也为后来所谓的“青春无悔”所冲淡。而《平凡的世界》所表现的回乡知青在艰苦生存条件下发愤图强、昂扬向上、改变命运的拼搏精神,能产生强烈的激励感召作用,激发起千千万万、常增常新的一切边缘生存和胸怀大志者的奋斗雄心。于是曾经赢来无数眼泪和赞美的知青文学,渐渐听到不同以至批评的声音。
贾平凹曾不止一次谈及此事:
“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见厕所里的啜泣呢?”
另一位年轻学人黎学文对知青文学的批评则颇为激烈:
当他们……如此不厌其烦地唠叨其苦闷哀怨,宣称自己是不幸的代名词时,他们当然不会反问自己:在他们一个个如逃离魔窟一般抽身远走的农村,他们的同龄人,我父母那样的农村青年不是依然躬耕劳作如故……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屑的是:他们……所摆出的那种极度煽情,反反复复吟咏个不停的‘大曝伤痕’的自恋病。仿佛世间的最不幸……被他们全都承受了”。
显然,这不可能与《平凡的世界》同日而语。
至于在农村度过18—35岁人生黄金时期的我,后来终于身带农活“全把式”、粗木工和腰腿伤病这些“可视资产”忝供教职。这就是我以前为解惠英的自言体之作《血染白丝巾》怆然写评、最近又深为解志熙之文所震撼并写出此文的内在原因。
——纪念上山下乡4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