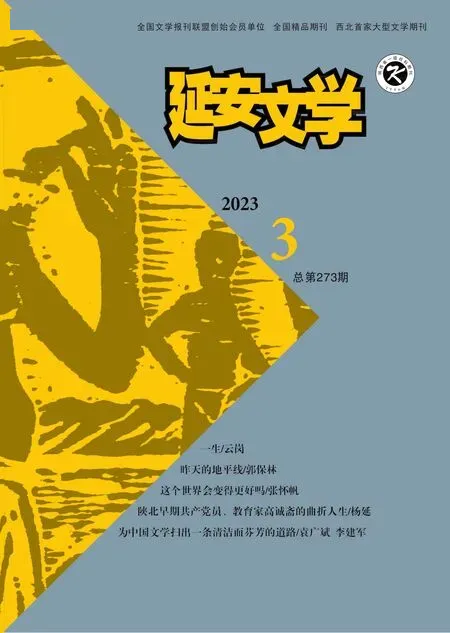放 套
李培战
蕙溪村地处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此地向北数十里,沟壑连绵,崖畔如拼凑不齐的糕点,大小不一的黄绿色块田是山坳里为数不多的耕地。盘山路蛇行期间。
近来,流经蕙溪村的溪水日渐变少,一时间,村民众说纷纭。较赞成的一种说法是,蕙溪村北山多林密,野生动物泛滥,有人疑心“黄大仙”操纵了蕙溪村的未来与命运。几天工夫,村民个个像丢了魂,陷入极度慌乱之中。靠天吃饭到底没有保障,村民纷纷流出,靠打工、经商营求生计。
蕙溪村没了往日的生气,原先能把村子笼住的炊烟,仅存孤独的几缕,白布似的在空中悬着,不久又散了。村里人少了,荒郊野岭的小动物就来猖狂。大白天,黄鼠狼在巷道自由自在地穿行,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势。蕙溪村北边面山而居的七户人家,仅剩两户没有外出谋生,其余都大门紧闭。一年到头,门上的铁锁也开不了几次。这两户人里,一户是于姓独居老汉,已七旬有余,靠政府和村民接济过活。这几年,于老汉身体状况越来愈差,如风里的灯。他常常一个人游走在村巷里,或蹲在门口的碌碡上,目送西边又红又大的落日沉进山里。他不吸烟,不嗜茶,干净整洁,自由可怜。在于老汉心里,同巷的朝兴俨然他的半个儿子。于老汉有时同朝兴说:“兴娃,要是叔的门哪天长时间没开,你就进来瞅瞅,若门里进不来就翻墙,兴许叔早就硬在炕上了,你可要捏个时间,让叔走得清白。”朝兴表面只当玩笑话,漾出满脸的笑容答应着:“没问题,于叔!”转过身,心里却感到沉沉的。
朝兴姓郝,是这七户当中最中间的一户。但蕙溪村的人很少叫他郝朝兴,老的少的都喊他“好高兴”。那时候,郝朝兴还小,他自己也觉得叫“好高兴”挺好,听着就欢喜,也就默认了大家对他的称呼。若遇上外人来村里打听郝朝兴,大多数人都会说:“蕙溪村没有这个人,你去别处问吧。”若来人打听的是“好高兴”,这就好办了,连村里的娃们都能带着来客抄最近的路,径直来到郝朝兴家门口,比导航还精准。
来客还真能这样找到郝朝兴。一回,来人自报家门后,开门见山地说,要郝朝兴帮他造一杆枪,夜间打兔用,价钱好说。来客似乎又觉得这样说太过直白,接着又补充了一大堆恭维的话。郝朝兴先是一愣,看着面前这位衣帽整齐的不速之客,平静地说:“私自造枪,那可是违法的事,我虽然懂一些枪械方面的知识,那也是早年在部队的时候,现在早不碰那玩意了,自然也生疏了,你还是去别处打问吧!”来客看了郝朝兴一眼,显得有些失望,二话没说就走了。郝朝兴看着那人出了村,噗噗跳动的心也回归了正常。郝朝兴心想,土枪以后不能用了。一同看着来客走出村子的还有于老汉。于老汉随即来到郝朝兴家里,忧心忡忡地问:“兴娃呀,你没犯啥事吧?”郝朝兴故作镇定,假装不解地问:“于叔,你问这话啥意思嘛?”于老汉扭头看着远处的山丘,山尖正有一丝云被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薄。于老汉缓缓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刚刚那人,叔在派出所见过,给我老伴销户口时,还是他领我去的户籍室呢!”于老汉接着说:“你夜间出去放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大家只是不愿当着你的面说。现在看来,有人把你怂举报了,帽子(警察)都寻上门了,你娃可得小心哩。你听叔一句劝,往后甭打了。你还真只顾自己高兴,那些小东小西也是有命的种。你得谋个正当事干,倩倩现在大了,也懂事了,你叫娃咋向外人说你?”
一提到倩倩,似乎碰触到了郝朝兴最敏感、最柔软的一根神经。三十九岁那年,郝朝兴为闺女的降临喜极而泣。郝朝兴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倩倩和这个家庭。至于丽芳,比他小六岁的妻子,他自然也是疼爱有加。经于老汉如此一说,郝朝兴若有所思。前些日子,他夜间带枪出门时,丽芳的脸上总是露出一副忧郁的神色来,似如鲠在喉。但丽芳也未公开反对过,郝朝兴也就没放在心上。
自此,蕙溪村夜空里,除了虫鸣鸟叫和大地的呼吸声外,再没有过一声枪响。于老汉拉长耳朵,听了一宿,除了黑夜发出的声音外,他没有听到任何响动。月色铺在窗棂上,静谧安详。于老汉心想,郝朝兴收手啦。
夜里十点钟左右,郝朝兴总要按时带一些器具出门,那些家什磕磕碰碰,发出清脆的响声。不悦耳,反倒刺耳。倩倩问丽芳:“为什么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出去?”丽芳看着女儿光溜溜的眼睛,毫不隐瞒地说:“你爸爸去放套了,那些套夹能套住野鸡,野兔,黄鼠狼,还有肥胖的狗獾……”倩倩听得兴奋,越发没了睡意。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倩倩睡熟了,放完套的郝朝兴也回来了。为了不惊动母女两,他小心翼翼地褪去衣服,摸黑悄悄上了炕,睡下了。丽芳低声问:“都放好了?”郝朝兴这才知道,丽芳没有睡着,应了一声“嗯”,不再作声了。
凌晨四点钟,郝朝兴带了手电出去收套。当然,更是拿回他辛苦付出后的回报。他昨晚放了八个套夹,有的在崖畔上,有的在深草里,有的在包谷地里,有的在坟头……凡夜间动物频繁出没的地方,郝朝兴都能想到。令他高兴的是,八个套夹,只有两个落了空,郝朝兴为自己的能干和多年来积攒的捕猎经验感到满足。一只野兔拦腰被牢牢地夹住了,四足却直直地蹬着,显然是在临死前进行过无济于事的抗争,眼睛仍瞪得鼓鼓的,不肯合上。郝朝兴用刺眼的手电筒光束照过去,那兔子的眼睛射出一道亮光来,这亮光似乎又刺在了郝朝兴的心上,他顿觉头皮发麻。郝朝兴当然不会害怕,这种场面他早习以为常。等他满载而归时,天依然没有大亮,深蓝色的天际里,依稀闪烁着几颗亮星。蕙溪村还在熟睡中,倩倩和丽芳也在熟睡中。郝朝兴又一次轻轻躺下,属于他的夜晚,才刚刚降临。
于老汉在巷子碰见丽芳,问她:“最近咋不见兴娃出来?”
丽芳不知如何回答,顺口说郝朝兴最近身体不大舒服。
于老汉咳了两声,背着手走了。
太阳挪到西边山头的时候,郝朝兴走出房子,狼吞虎咽地吃了丽芳给他热好的饭菜。郝朝兴来到后院,见一只黄鼠狼仍在套夹上挣扎,一只腿已经被夹断,另一只腿也在套里,皮骨已完全暴露,套上的流血已结成了黑痂。郝朝兴卯足了劲,他要开始拾掇这些战利品。丽芳早烧好了滚烫的水,郝朝兴拿来明晃晃的道具,处理过程井然有序:去毛,开膛,掏内脏,清洗,又往肚里塞进可食用的内脏,一只只小家伙被装进一个个塑料袋,放入冰箱。做完时,天将黑了。
倩倩目睹了整个过程。
黄昏时分,西山头上一团云火烧火燎一般,嵌上了一道金边。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郝朝兴门口,车门上贴有几个残缺不全的广告字样,写着某某餐厅,还有一串显示不完全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儿,郝朝兴和那面包车司机从放有三四台冰柜的暗房里出来,两人各怀抱了大包小包的东西,他们抱得很吃力,那些包裹得很严实的东西被他们塞入面包车后备箱,反复跑了好几个来回,两人都累出了汗。面包车司机没顾上喝一口水,往郝朝兴手里递了一沓钱,让他点一下,郝朝兴转身把钱转交给丽芳,丽芳攥着钱进了房子。倩倩呆呆地站在一旁,她还不懂大人之间的交易。面包车司机弯下腰去抚摸倩倩的脸蛋,倩倩忙躲开了。“这女子长得真亲!”司机说完后上了车,车门“哐”地一声,巷子里随即悬起一溜烟,面包车消失不见了。
于老汉坐在他家门房里,又咳了一声。
郝朝兴的手还没从洗脸盆里拔出来,门口又来了一辆黑色小车。
“兴娃,寻你的。”于老汉站在门口喊了一句,声音不似先前那样扎实硬朗。
来人先是问,是不是好高兴家里。郝朝兴应了一声。来人接着说,家里老人得了重症,急需两只黄鼠狼用作药引子,他是多方打听才找到这里的。郝朝兴看出了对方的急切,内心的戒备疑虑自然消除了。郝朝兴擦干了手,友好地解释说:“你来得真不巧,你想要的东西,刚被拉走咧。”那人急了,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让郝朝兴想想办法。郝朝兴让来人留下电话,说是逮着了,打电话来取。又是一股烟尘,黑色小车消失在了夜色中。
平日里,黄鼠狼多得能把人绊倒,可当郝朝兴有目的地去套时,连续三个夜间,一只也没夹着。郝朝兴心想,是自己不该挣这钱,还是那患了重症的人,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终于在第四个晚上,套了一只。隔了一晚,又得了一只。郝朝兴打电话叫那人来取,价钱同卖给饭店的一样。那人临走了,几乎向郝朝兴作揖告别。郝朝兴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感觉,他突然能为自己帮别人延长寿命而自豪起来。用黄鼠狼的命来换人的命,当然值。如此想着,郝朝兴觉得他的钱挣得很干净,心里的负罪感减轻了许多。
怪事还是发生了。最近几日,郝朝兴去收套时,套夹总是提前被人拿走几个,当然也可能是夹住的家伙体型过于庞大,连带套夹一起逃回洞穴了。也可能是,他的行踪被同村人发现,有人恶意整他。郝朝兴不断地做着各种假想,决定再观察观察。
后来,还是一样,每次都会固定地丢失一两个套夹。装套不够用,郝朝兴不得不多加工一些。一天夜间,郝朝兴放完套夹后,并未迅速离开,他用黑夜将自己包藏起来,蜷在疯长的蒿草后面,默默注视着一切。果然,一个缓慢行动的黑影出现了,那黑影弯下腰时,简直变成了一个黑球,一眨眼的工夫,黑球又站立起来,郝朝兴没有着急打开手电筒,他想抓现行。于是,郝朝兴大踏步追上去,黑影像幻化魔术一样,又不见了。郝朝兴打开手电筒,光束像黑夜的眼睛,四处搜寻,仍一无所获。现在,郝朝兴在明处,对方在暗处。郝朝兴本想大喊大骂一通,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郝朝兴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儿,周遭没有了一丝响动。回家的路上,村里的狗叫了几声,声音传得很远,彷佛能划破静谧的夜空,郝朝兴感到脊背发凉。
郝朝兴连续几天没有放套了。他在筹备一个更大的套夹,他要用这个更大的套夹来对付那个偷取他套夹的人。他从市面上买来胳膊粗的弹簧,一指厚的钢材。郝朝兴已顾不上专心吃饭睡觉,他用全部精力来打造更大、更具威力的套夹。
倩倩看到郝朝兴脸上的笑容少了。豆大的汗珠从郝朝兴的额头上滚下来。
一天傍晚,更大的装套做好了,样子像一个张大嘴的怪兽。郝朝兴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叹服着自己的手艺,满意地笑了。
这天夜里,倩倩哭闹着不肯入睡,丽芳用手触摸倩倩的额头,也没觉发烧。倩倩说:“爸爸刚才带出去的怪兽要吃人,我害怕!”丽芳没有说话。
郝朝兴找了一块隐蔽的地方,放好了新造的套夹,他希望套夹有用,又希望没用。最好只是用来吓唬一下那偷取套夹的人,给个教训。郝朝兴心想。
回去的路上,一声惊雷在郝朝兴头顶炸裂开来,巨大的威力简直是要把天地彻底分开,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罕见的大雨。郝朝兴回到家里时,浑身湿透了,他连续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忐忑不安地睡了。
半夜,郝朝兴突然被尿憋醒,他摸索着开了灯,正要下炕,回头看见睡在妻子一旁的倩倩不见了。他在慌乱中急忙摇醒了丽芳,朦胧中的丽芳先是闭眼伸手摸了身旁,除了炕褥,她啥也没摸到。丽芳唰一下坐起来,像失了魂,脸色变得极其惨白,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穿透雨声,回荡在蕙溪村的角角落落,回荡在漆黑的雨夜。两个人的意识越来越清醒,倩倩丢了。
雨落不止,他们在泥泞中,一遍一遍,带着哭腔呼唤着倩倩的名字。两道无助的手电筒光束在夜空毫无目的地挥动着。雨似乎又大了一些,仿佛为他们丢失孩子营造一种悲凉的气氛。雨声,哭声,雨滴,眼泪,已无从分辨。两个人嗓子都喊哑了,力气也没有先前那般大了。两个人蹲坐在村口一块石头上,头沉沉地埋了下去,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脸颊,滴落在他们脚下的泥水里。
郝朝兴思绪回到倩倩出生那天。产房外,妇产科大夫悄悄告诉郝朝兴:“你爱人的身体太虚弱了,这个婴儿能保住都是你们前世积了德,以后不能生了,否则,你爱人会有生命危险。”从那一刻起,倩倩就成了郝朝兴生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郝朝兴一定会替倩倩挡在前面。想到这里,郝朝兴又哇哇地哭了。
“倩倩会不会去了我放套的地方?”郝朝兴似乎想到了什么。大约九点多钟,那时天还没有下雨,郝朝兴掮了新造的套夹,怀着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心情,匆匆出了门。倩倩一直跟到门口巷道里,目送郝朝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走!赶紧走!”丽芳顾不上仔细盘问,拉着郝朝兴朝雨中奔去。
倩倩没了。
怪兽一般的套夹死死咬住了倩倩的左腿,皮肉像开了花,白花花的腿骨裸露在外,因雨水不断冲洗,倩倩身上已看不到大量血迹。丽芳瘫软在泥水地里,仅存一丝呼吸。郝朝兴扑上前去,却如论如何也打不开套夹,他的脑子空了,乱了,他根本找不到机关设在哪里。他又哭着去搂倩倩的头,倩倩眼睛睁得很大,那眼神像极了郝朝兴平日里套住的小动物临死时绝望的眼神。不同的是,倩倩的脸上带着微笑,她那表情好像在说:“爸爸,你的手艺真好,这怪兽真的能吃人!”突然,那些曾被郝朝兴套夹贩卖的小家伙们,有的被扒光了毛发,有的少足,有的眼睛像两个黑洞,有的敞开着膛肚……它们都像插上了翅膀,由四面八方向郝朝兴飞冲而来。
“不要!不要!”郝朝兴发疯般地吼着。
屋外,下了一整夜的雨,消停了。
郝朝兴还没醒来,额上浸出细密的汗液,丽芳赶忙用手推了推郝朝兴。郝朝兴慢慢睁开了眼睛。
“你昨晚回来淋了雨,发烧了。”丽芳平静地说。
“爸爸醒了。”倩倩在炕边眨着会说话的大眼睛。
“你做噩梦了?咋还哭了呢?”丽芳又问。
郝朝兴没有说话,先是瞅着丽芳发愣,又盯着倩倩好一阵子。他忽地从炕上坐起来,半裸着身子,将两人紧紧地搂抱在胸前,久久不愿松开。丽芳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弄得不知所措,眼睛也湿润了。
“好几天不见于叔出门了。”丽芳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郝朝兴像是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快速穿好衣服,来不及洗脸,去隔壁敲于老汉的门,任凭多大的劲,手也敲麻了,还是不见于老汉来开门,郝朝兴感到情况不妙。郝朝兴又回到家里,从后院的院墙上翻进于老汉家里。
于老汉家里安静得像一处荒园,几只山雀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喳喳叫唤。
“于叔?”郝朝兴试着叫,期待有人答应。
院子,前厅都找遍了,还是不见于老汉。郝朝兴只好朝于老汉房子走去。推开门,透过昏暗的光线,郝朝兴看见于老汉平躺在炕上,早已没了气息。一只苍蝇嗡嗡地在于老汉面前飞来飞去。郝朝兴上前摸了摸,于老汉全身僵硬了。郝朝兴第一次和不是自己亲人的已故人如此靠近,吓得手心冒出汗来,身子不由得向后退去,突然,他被什么家什绊了一下,差点儿跌倒。郝朝兴定睛一看,于老汉的脚地摆满了他曾经丢失的套夹。郝朝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眶里装满了泪水,他似乎明白了一切,竭力哭叫起来:“于叔,你兴娃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干那缺德的事了。”郝朝兴似乎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糊涂求得谅解。可惜,于老汉已经听不见了。
于老汉也有过一个儿子,和郝朝兴一样,都当过兵。郝朝兴部队复员能回家,而于老汉的儿子一去不回。那一年,南方暴发特大洪水,他儿子所在的部队,受命前往抗洪抢险。在与洪水搏斗中,于老汉仅有的儿子被无情的洪水吞噬了,最终尸体也未能打捞着。部队来人慰问于老汉,一些知情的村民也围拢在于老汉家门口。首长将一张照片交到于老汉手里,于老汉双手接过儿子的照片,反复抚摸了几遍后,将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于老汉的老伴已无力支撑身体,由几个村民左右搀扶着,勉强站立在于老汉后侧。突然,于老汉迎头冲着蕙溪村的天空大喊:“蕙溪村走出去的娃回来咧!我娃是为国家牺牲,是为保护人民群众牺牲,我娃光荣,我光荣!”于老汉已声嘶力竭。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为之动容。于老汉当时没哭,等全部人离开后,他和老伴在家里抱头痛哭,好些天没有出门。前年,老伴也走了。现在,一家人总算又团聚了。于老汉一生坚强乐观、爱憎分明、为人正派,蕙溪村在外的村民接到讣告后,纷纷从各地赶回来,送于老汉最后一程。大伙儿合力给于老汉办了一场简单又不失体面的葬礼。当然,郝朝兴是哭得最凶的一个。
于老汉入土为安。郝朝兴和丽芳也商量好了,带着倩倩跟大伙儿一起出去打工,倩倩激动得手舞足蹈,红扑扑的脸蛋笑起来,像开在春天里的一朵花。
“你前几天放的套还没收呢!”丽芳这句话像是在表达疑问,又像是提醒郝朝兴。
郝朝兴瞅着丽芳摆了摆手,笑着说:“任谁拿去吧!”
“万一伤了人,可咋办?”丽芳的担心不无道理。
“我放套时拆了弹簧,咋会伤人呢?”郝朝兴刚一说完,一家人哈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