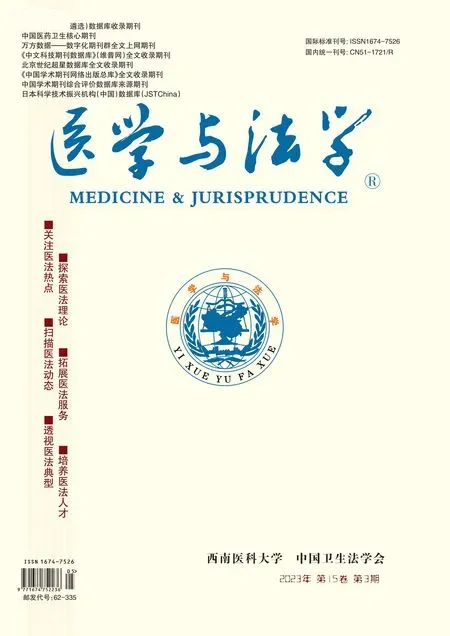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规则探析
唐克
一、问题的提出
在英美法早期,由于人类在医学上缺乏对心智认知的深入研究,并且因为精神层面的损害具有无形性而难以被证实,导致法院并不重视精神上的伤害。但随着人们“精神安宁权利意识”的觉醒,法院逐渐承认人身伤害案件中的精神损害,即因人身伤害行为所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可获得救济(即使精神痛苦或与其他因素相关)。①对上述问题的担忧,使得非因人身伤害而致的纯粹精神损害②(Pure mental/psychiatric injury)的可赔偿性更是久遭质疑。
然而,随着现实主义思想的兴起,人们更加重视内在心理状态,也愈发认可行为科学的解释力。人们依托生物学、医学的心理诊断技术以及对人类性格的心理学解释,更加了解精神障碍的症状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从而使精神疾病逐渐具有了可被客观化诊断的标准。[1]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精神损害不再囿于人身伤害情形,而成为一个可被独立诉请赔偿的侵权行为类型;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诉讼泛滥,并妥善处理侵权法有关“法益保护”和“行为自由”维护的关系,设置合理的责任措施便成为平衡“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矛盾的实践表达方式。[2]因此,“纯粹精神损害”的赔偿往往被要求满足一些“控制条件”,从而将责任限制在相对可接受之范围内。相较于故意所致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过失所致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往往需要更多的附加条件,其中“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学者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考量因素”,即受害人之精神痛苦是否达到可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程度,这就要求受害人能证明自己罹患了某种“可辨识的精神疾病”[3];然而,其在发挥界定“纯粹精神损害”范畴之重要作用的同时,亦遭受着深刻的质疑。该要求往往被认为是具有压迫性和缺乏正当性的,也正因此,有学者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的实施状况描述为“仍然跛行中”[4]。
我国有学者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在“Page案”提出反对意见的Lloyd 法官认为,受害人身处危险境地但仅仅因为偶然而未发生身体损害,却导致法院采取了一种与产生实际身体损害所完全不同的标准,没有理由将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视为不同的伤害种类③,孙维飞教授提出质疑,若承认身体遭受伤害之危险与身体所受伤害应采用同样的处理办法,那么,既然因为身体所受伤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无须要求受害人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那么是否身体有受伤害危险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无须要求受害人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5]“可辨识性精神疾病”对于有效地限制“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究竟是否必要?倘若否认这一限定条件的必要性,法院又该如何衡量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以达到平衡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困境?
遗憾的是,国内现有文献并未能关注到这些问题;即便部分文献有些许涉及,但也囿于对基本规则的考察而未能进行深入讨论,且僵硬地照搬而不加以反思总结的论述,并无益于我国司法实践的进步。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考察“可辨识性精神疾病”的渊源及形成的历史原因;其次,阐明“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这一要件的弊端,并通过考察英美侵权判例对该要件所持态度的转变,着重就201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所判决的“Saadati 案”进行介绍和评析,以探明其可资借鉴的做法;最后,结合域外立法经验与典型判例,探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精神损害严重性”规则的进路,并进一步地反思“严重精神损害”规定的合理性,从而提出引入动态系统论解决方案的展望。
二、“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规则的适用现状
(一)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其赔偿救济的沿革
长期以来,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往往持谨慎态度,这源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第一,精神损害通常较为短暂或轻微;第二,精神损害之症状易伪装,若允许救济则恐激励欺诈性诉讼;第三,一场事故的潜在受害人数量非常广泛,若承认赔偿则会导致加害人承担过重的责任,致使其所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程度不成比例;第四,对于“诉讼洪流”(水闸理论)的担忧。④彼得林斯基也曾指出,“纯粹的精神损害”完全取决于受害人主观上的感受,倘若于任何情形下都承认其诉请赔偿的要求,这将导致行为人遭受极大的不利与困难。[6]然而,一概而论的否认做法亦有失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故“不能因为难以找寻客观、物质化的损害构成以及进而在提供救济方面的困难而放弃对这种损失提供救济”[7]的态度,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认可。
正因如此,普通法国家多从行为人主观状态、对于侵权行为的评价以及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这三个角度,来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而言可赔偿的“纯粹精神损害”应当考虑受害人与事故或其紧接后果在时空上的接近性、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的血缘关系、原告应当是具有一般毅力的理性人、受害人遭受了可辨识的精神疾病等因素。而在“Kelly v.Hennessy”案中,首席法官Hamilton 就“可获救济的精神打击”提出了五项要件:一是可辨识的精神疾病;二是这一疾病是由于突然的打击所引发的;三是该疾病为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四是该疾病是“由于对原告或第三人造成实际或可能发生的身体伤害”而产生的;五是非以精神打击的形式造成可合理预见的伤害。⑤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法域,对于可赔偿的“纯粹精神损害”所要求的条件有所差异,但其相同的做法是,各国基本都认可将“可辨识的精神疾病”作为限定要件之一,即“可辨识的精神疾病”成为了衡量“精神损害严重程度”的一般标准。而原告所负有的证明其患有“可辨识的精神疾病”(recognizable psychiatric illness)⑥之义务,其起源可追溯至英国上诉法院大法官丹宁勋爵于1970 年在“Hinz v.Berry 案”中所作的判决意见。在该案中,辛茨夫妇驾驶房车带着四个孩子出去游玩,彼时辛茨夫人已怀有第五个孩子数月;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因爆胎失去控制而撞上了在房车内饮茶的辛茨先生及其孩子,致使辛茨先生当场死亡,几个孩子受重伤;辛茨夫人目睹了这一幕,随后患上了病态抑郁(morbidly depressed)。丹宁勋爵在此案中提出,“在英国法律中,因人的死亡引起的悲伤或悲伤所致的损害不予赔偿。对孩子的担忧、经济压力或适应新生活的困难所致的损害,不予赔偿;然而,对于神经性休克(nervous shock),或者从医学角度来说,对于因被告违反义务而引起的可辨别的精神疾病,可以获得损害赔偿”;⑦法院最终认为辛茨夫人有权获得赔偿,因为她证明了自己遭受了一种“确认的精神状态”,而非仅仅是一种悲痛的感受。
(二)比较法视野下“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规则的应用考察
丹宁勋爵的上述表述区分了“单纯的精神痛苦”与“可辨识的精神疾病”,使得精神损害在赔偿与否之间被划定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界限,并很快获得许多国家判例以及立法的承认。⑧例如,在奥地利,对他人造成精神损害并构成“可辨识的精神疾病”(如厌食症或严重的抑郁)的情形时,受害人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三百二十五条请求损害赔偿。[8]同属大陆法系的瑞士法院则要求近亲属所受惊吓损害应构成精神疾病,才可藉由健康权受侵害之路径而获精神损害赔偿。⑨而德国法对受惊吓损害赔偿问题亦是通过健康权的解释路径来予以含括,即所受损害需达到《德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第一款所界定的侵害健康程度才可获得赔偿,而存在(借助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来确定的)精神疾病是构成健康权损害的必要要件。[9]不同的是,奥地利、瑞士采医学标准,一般需要医生证明构成公认的精神疾病,并需要医生治疗;德国采法学标准,强调是否构成精神疾病由法官予以判定。[10]“以宪法为导向”的意大利虽然发展到将某一受到保护的利益所受到的侵害本身即视为可赔偿性损害的高度,但其国内的数项裁判仍表明了“原告证明自身所受损害的程度(损害自证’理论)对于获得赔偿具有重要意义”。在英美法系中,加拿大自1970年起,就规定因过失而致“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之一,即必须患有“可辨识的精神疾病”。[11]而在澳大利亚,以David Ipp为主席的专家小组于2002 年提交的《过失侵权法最终评价报告》中的内容亦表明,行为人对于“纯粹精神损害”并无责任,除非所致损害构成“可辨识性精神疾病”。[12]
(三)DSM与ICD的司法认定
那么,各国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确认“可辨识的精神疾病”以区别于“单纯的精神痛苦”呢?许多域外司法机构选择借助精神病学标准对此进行界定与识别。事实上,精神障碍并无一个明确的分类体系,但目前被较为广泛接受的参考标准当属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1)。[13]前者主要按照症状学分类原则进行区分,而后者则遵循病因病理学分类和症状学分类兼顾的原则[14];此外,前者仅专注于精神健康,因此相较于后者而言,也被精神病学家认为更加完善;但随着该手册的更新迭代,二者在分类系统、疾病结构安排方面越加呈现出交相呼应的态势——其中较为常见的、为法院判例所承认的“可辨识的精神疾病”,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⑩、创伤性歇斯底里(traumatic hysteria)⑪、病理性悲痛障碍(pathological grief disorder)⑫等。二者作为列出诊断标准的示范性蓝本,经常为医学专家的认定意见所引用而出现在诉讼中,从而促进法官对精神疾病相关特征的理解:一方面,这种诊断工具有助于法官对特定个体的精神疾病是否有所伪装或臆测而进行核查验证;另一方面,倘若涉及法官对受害人过往所存在的或未来可能产生的精神症状问题进行判断时,纵向病程的诊断信息可能会帮助法官作出决定。[15]
可见,在示范性的国际参考蓝本的协助下,“可辨识的精神疾病”这一要求对于划定值得救济的“纯粹精神损害”与单纯的“精神悲痛”之间的界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因此为各国立法所广泛采纳。
三、理论检讨:精神疾病要件的质疑与反思
(一)“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规则所引起的学界争论
尽管受害人证明自己患有“可辨别的精神疾病”是获取赔偿的的关键要件,但人们对此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质疑:
第一,有观点认为,当事人一般可因肉体上的伤害所致严重精神后果诉请赔偿,但在直接因精神上的伤害诉请赔偿时,却要求达到“可辨别的精神疾病”程度,如此有区别的限制条件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放大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区别[16];进而言之,这涉及是否应对人格权的价值位阶作出划分的问题。人们往往认为诸如身体完整性等物质性人格权处于人格权保护的中心位置,其价值位阶高于非物质性人格权[17]。霍夫曼勋爵曾提及精神损害领域存有两个极端学派,其中之一则为Mullany和Handford所提出的废除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控制,即精神痛苦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其不仅可被客观证明,且其不亚于身体伤害的严重性亦被逐渐认同,因此法律应同等对待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⑬笔者认为,这一所谓“极端”的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显其合理性;唯需注意的是,即便是认可同等看待精神损害与身体伤害的学说,其内部亦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如澳大利亚《过失侵权法最终评价报告》第三十七条提出,将患有“可辨识性精神疾病”条件同等地适用于因身体伤害所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上[18],即通过提高附属的精神损害之门槛,以便将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同等对待。这与当今社会主张降低精神损害赔偿的门槛以扩大对其救济范围的精神有所冲突,应不可采。
霍夫曼认为,无论选择哪种解决方案,都应当取决于侵权法的立法目的。如果其目的是为了提供矫正正义,那么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区别就应予消除。[19]在此立场下,若仅因身体在极其偶然情况下未受损害,就采取与通常人身所遭受损害情形下差距甚大的赔偿认定标准,那么这种因细微区别而使得法院可能最终判决完全不予赔偿的做法,将无可避免地引发公平正义问题,并且还会滋生伦理道德问题——受害人为获得救济而追求或维持严重的精神障碍状态,进而拒绝接受精神治疗。进而言之,法院为了避免出现过度显失公平的结果,还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控制责任成立的前提要件,从而损及裁判的可预见性。[20]
第二,精神损害与精神疾病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并非毫无联系。精神疾病通常属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后果,而精神损害本身即存在诸如悲痛、焦虑、哀伤等症状。由此而言,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表述为更为剧烈、加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单纯的精神痛苦与构成精神疾病的症状之间的界限是较为模糊的,有时还难以区分。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对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意见征询的答复中肯认了这一困难,并指出精神健康与单纯的精神痛苦之间的确存在一部分因医疗诊断无法适应法律目标而存在的“灰色地带”。[21]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所作报告得出结论:“精神疾病”与“单纯的精神痛苦”并非属于种类的区别,而仅为程度的不同,并且随着医学认识的发展还会发生变化。⑭奥地利法院在损害赔偿项目上并未严格区分精神疾病和精神损害的做法也可作为佐证。正如前文所述,在奥地利,受害人所受到的惊吓损害必须构成精神疾病才可获得赔偿。受害人为近亲属的,奥地利法院仅赔偿健康损害,但往往以精神损害的名目进行赔偿;若受害人为本人的,则将精神疾病与精神损害相统一,仅赔偿精神损害。[22]
第三,为了促进结果的客观性、确定性、可预测性而诉诸DSM或ICD,将其视为“可赔偿精神损害的最低门槛”的做法也遭到质疑。首先,其所提供的客观、确定等标准可能有所夸大,这是因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与医学上的精神障碍分类并无必然联系。实务中多采取此种客观化的外在判断标准,而忽略了主观化的评判标准,即一个具有通常毅力(ordinary fortitude)的理性人处于同等情况时,是否无法适当应对因该事件或行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其缺陷之处即在于,这会忽略一些未被诊断参考标准收录、但对个人而言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虽然精神损害的程度因个体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无形损害具有难以证实性,但却不能因此否认损害的客观存在。其次,精神损害的诊断在精神病学专业领域内可能会存在争议,并且诊断的标准还在不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将可赔偿的精神损害限定为此类诊断工具可识别的情况下,“从法学角度来说,这本身即是可疑的”[23];其原因在于,可合理预见的精神损害与疾病诊断分类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过失加害人只需证明能预见到损害即可,而非具体精神疾病。将评估是否为可赔偿的精神疾病这一任务交由DSM和ICD时,就相当于引入了一种专横控制机制,使得损害赔偿并非以伤害的法律原则为基础,而是以符合与法律无关的精神障碍分类手册为条件。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种价值因素的影响,但诸如DSM-5 或者ICD-10 这种医学中的鉴定蓝本并非专为确定法律上可获赔偿的损害标准而设计,其所包含的损害类型无法反映创伤所致心理影响的复杂程度[24],由此可见,法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之间的学科话语差异仍客观存在。此外,由于这些医学参考标准发展的滞后性,这也导致了部分已被普遍接受而应获救济的精神障碍种类并未被涵盖其中。举例来说,在著名的“Page v.Smith 案”中,受害人所罹患的慢性疲劳综合症(CFS)应予赔偿已广为法院所认可,但却至今未被DSM-5或ICD-10涵盖。⑮另一个例子则是首次出现于1980年的DSM-Ⅲ中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这一病症主要是对参加越南战争的军队人员所遭受之创伤进行大量研究总结的成果。但相关症状早已在DSM-I 中出现并被称之为“急性应激反应”(gross stress reaction),随后在DSM-Ⅱ中被删除。[25]由此可见,可赔偿的精神损害不应受到精神病学程式化定义的限制,而应更直接地受到精神或情感痛苦的严重性的影响[26];换言之,其应重点考量的是受害人的特定症状所代表的伤害程度,而非医学上所给定的精神障碍分类等级。
(二)域外司法的裁判动向之转变
基于上述观点的考量,实践中一些司法判例所持的立场逐渐发生转变。例如,在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的“Brown & Anor v. The Mount Barker Soldiers’Hospital Inc 案”中,因医院过失导致原告年幼的女儿在事故中严重烧伤,正在住院的Brown 女士以因闻知此事而遭受到“精神震惊、不适以及不便”的理由而被法官裁判予以赔偿,但她是否罹患“可辨识的精神疾病”却不无疑问。⑯2008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Mustapha V.Culligan of Canada Ltd案”⑰的判决意见中评论“可补偿精神损害”的门槛时,没有使用“可识别的精神疾病”一词,有评论员认为其避免使用这一用语,或意在重新反思“可识别精神疾病”这一要件。[27]然而,彼时加拿大最高法院并未明确驳斥该标准,直至2017年,其在“Saadati v.Moorhead案”⑱中才明确突破了这一传统规则,从而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该案的基础情况是,2005 年萨达蒂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驾驶一辆拖拉机,随后与一辆过往汽车发生碰撞,其本人看起来并没有受伤。但复杂的是,在2003-2009 年期间,他共遭遇了5 起车祸,而本次是第二起。事实上,在第一起车祸发生后,他便患有持续性疼痛,直至第三起车祸后(2005年后期)疼痛加重。2007 年,萨达蒂就第二起事故提起过失诉讼,要求赔偿其非财产损害以及以往的收入损失。2008年、2009 年其又分别发生了两起事故。2010 年,他被宣布患有精神疾病,由监护人继续进行诉讼。主审法官认为,第二起事故造成了萨达蒂的精神损害,包括性格变化与认知困难。而这一观点并非基于已确定的医疗证明或专家证据,而是基于萨达蒂亲友关于他2005年事故前后的变化差异的证词所得出。法官还认定,其后的几次车祸与第二次事故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不可分割的。法官最后判决其获得10 万加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来被告上诉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律适用错误,因为萨达蒂并未证明自己患有医学上承认的精神病。Brown 法官提出,在过失所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只要现有证据能表明由于事故而导致原告情绪、个性、记忆力丧失和认知障碍,也即存在某种形式的精神损害即可。这一意见也为其他法官所接受,因此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其症状完全符合精神损害的标准参数:受害人性格、认知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丧失亲密关系等,这一损害严重且持久,超越了一般的情绪不安或痛苦。尽管这些症状可能并不足以在DSM-5 或者ICD-10 的范围内得以界定,但只要原告表现出上述严重且明显的精神障碍症状,即应获得赔偿。
至此,秉持“可辨识精神疾病”要件数十年的加拿大最终摒弃了这一限制,为一些不能够达到精神障碍程度的症状打开了大门。毫无疑问,该判决所作的突破也将为其他国家及地区治理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极为有益的参考。
四、规制路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中对“严重”要件的域外借鉴
前文已述,域外判例法就“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发展出一系列规则与判断因素。我国虽不乏有学者建议因袭成例、予以引入,但《民法典》对此并未专设条文、有所回应。在立法有所缺失的情况下,盲目地照搬而不加以反思地引入,无益于我国法律体系的融洽,而更为适当的做法,当是应先立足于本国现行法律体系,再通过解释论寻找解决方案。
(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中的“严重精神损害”
在解释论的视角下,倘若承认延续《侵权法》第二十二条而来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所强调的“人身权益”包括了“精神利益”,即认可“精神利益”作为独立法益存在[28],那么《民法典》该条作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便可涵盖以精神利益为客体的“纯粹精神损害”⑲。依此观点,“纯粹精神损害”之救济除应当符合我国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也即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构成要件外,还因精神损害之难以被证实性,而尚需符合其他特殊要件的规定。事实上,我国法院虽多仿照大陆法系国家藉由健康权侵害之路径解决此类问题,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予以救济,多数国家立法或司法裁判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精神损害需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同样地,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就此亦规定了受害人需存在“严重精神损害”的要件,即当事人的行为除需符合过错责任一般要件之外,在精神损害后果方面还要达到“严重”程度。
不可否认,我国立法对“严重精神损害”之表述更具弹性,为保护更多未上升至权利的利益提供了空间。然而,宽泛的语词表述也具有内涵不确定的弊端:该条规范的法定用语含义极其模糊,立法也仅从反面描述了“偶尔的痛苦和不高兴不能够被认为是严重精神损害”[29]而未能从正面对“严重”一词予以界定。有学者参照域外做法,提出以构成医学上的精神疾病作为“严重精神损害”的考量要件,而精神疾病的认定则采“医学标准”——由医生提出鉴定意见,证明构成公认的精神疾病,并采用我国通用的精神疾病标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予以判断。[30]司法实践中,不乏有法院采纳这一意见,将受害人是否罹患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作为判定标准,构成此类公认的精神疾病者才可获得救济,以此限定“严重精神损害”这一不确定概念的范畴。[31]然而,在许多情形下,被害人虽未罹患可被证实的精神疾病但仍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法官则囿于这一标准而判决不予赔偿或仅予以象征性补偿。由此,这一为我国司法裁判所广为接受的标准同样因过于僵化而面临着缺乏实质正义的质疑。可见,前述有关域外以医学诊断目录为精神疾病判断标准的争议,在我国亦存在着讨论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时代也勃兴了许多诸如个人信息权益等新型权益,其遭受侵害时所致精神损害具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其所面临的“侵害的难以证实性”也在呼唤着重新考量我国法规范中“严重精神损害”的合理性。[32]目前而言,我国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深度仍显不足,就如何理解“严重精神损害”这一要件在理论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原发性、非自觉性的回应思路也较为混乱。故而,笔者希冀以外国法域的判例及立法经验为借鉴,以探究更为妥适于我国的司法裁判路径。
(二)客观外在标准与主观理性人标准的结合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前述域外司法裁判动向之经验是否能融洽于我国现状,从而可被完全移植于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即是否不再以“可确定的精神疾病”作为判断“精神损害可赔偿性”的考量标准?换言之,是否应不以“可辨识性的精神疾病”作为限制“严重精神损害”的门槛条件?
有学者虽对这一做法持肯定态度,但也认为需要审视其实际效果。笔者以为,无论是全面肯定还是全面否定这一要件的做法都具有偏颇性而不可采。应当说,精神障碍的鉴定目录这一客观标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原因在于,上述去除“可辨识精神疾病”的主张并未能完全消除人们对诉讼闸门、不确定性的担忧,彻底移除需要鉴定为精神障碍诊断目录中所示精神疾病的条件并不必要。实务显示,在一般的悲伤、难过情绪和高门槛的精神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值得救济的中间地带。而中间地带的确认仍有赖于“可辨识精神疾病”这一客观外在标准,但应扩大“可赔偿精神损害”的入口点,允许不满足DSM-5 或ICD-10 标准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获得支持。[33]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中,一名儿童目睹了坐在汽车前座的父母因车祸撞击而死亡,但是没有任何医学上的证据证明她遭受了“可辨别的精神性疾病”。⑳依据既有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该原告将难以获得赔偿。但显然,这一结果令人无法接受。不满足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症状并不代表不构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换言之,衡量“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不能完全取决于此类医学目录,即“像使用菜谱一般”地诉诸于临床指南和诊断标准,[34]而应回归到对受害人实质伤害症状的考量,即受害人的认知功能和日常活动的参与受到损害的严重性、损害的持续时间以及向被害人提供的任何治疗的性质和效果等。[21]必须存在“严重和长期”的困扰,并且这种困扰超出了社会中一个理性人的一般容忍界限。[22]总而言之,原则上以精神疾病鉴定标准(客观外在标准)来认定精神损害的“严重性”,但例外地,对于虽不符合医学上精神疾病标准的症状,倘其严重程度超出了一个理性人的一般容忍界限(主观理性人标准)则仍应被认为符合“严重精神损害”而予以救济。
唯需注意的是,这并不同于我国司法机关所提出的“应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和被侵害人的精神状态等具体情节加以判断”的做法[35]。这些考虑因素过于抽象而无法为法官裁判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规范内容[36],并且其事实上已落入了普遍意义上论题学范畴——不限制考量因素的开放结构[37],从而难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只有形成综合客观外在标准和主观理性人标准的做法,并确定各衡量因素的价值位阶,从而构建精神损害赔偿的弹性评价机制,才能更好地平衡侵权法中“利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这一紧密交织的基本矛盾。
(三)精神损害赔偿中动态系统论的引入
颇值一提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要求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的程度,这是否意味着“非严重”的精神损害就一定不予赔偿呢?法谚有云:法律不理琐事。“轻微损害不予救济”(Trivial damage is to be disregarded)这一思想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将其明确作为规则而予以规定[38]。那么“非严重”的损害是否等同于轻微损害而不应予以救济?[23]
笔者以为,与对“未达到精神疾病就不予以救济”的态度类似,这不应成为一个完全确切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精神损害赔偿不应以严重损害后果为限制条件,对于一般程度的精神损害应予以救济[39],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采用一般侵权条款的国家,法院甚至会将“范围宽泛的情感伤害和精神痛苦”纳入考虑范畴[40]。换言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等同起来,即承认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具有同等的破坏性。但我国关于精神损害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显然还没有“走那么远”,并且考虑到“诉讼洪流”问题,因此对精神损害赔偿严重程度的限制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然而,以“存在表征的精神疾病”作为责任成立的判断标准存在着要件-效果规范模式的僵硬性。为克服这一弊端,未来或可采用威尔伯格(Wilburg)所提出的动态系统论,即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考量法律规范的目的价值,从而最终提炼出适当的要素,形成动态评价标准框架[41]。在动态系统论下,实体法规范由传统叠加式的要件模式(A+B)规范转变为相互关联的复数要素模式(A×B)规范,且待考量要素的列举并不再遵循要件划分时“相互独立、完全穷尽”的原则,而是通过赋予各要素以不同的价值权重,进而实现法院判决结果的妥当性。[42]
具体而言,可通过一般侵权条款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表达,并结合行为正当化(或可归责性)与被侵害权益重大性之内在原理,从而提取过错程度、后果严重性、因果关系贡献度与确定性程度、被侵害权益受保护程度以及侵权行为样态作为支撑因子(要素)。[43]倘若其他要素的充足程度远超损害的轻微性要素,那么前者要素的充足即可补足后者要素的缺乏,进而借助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依旧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如果加害人主观上可被谴责性较深,那么即可适当降低对精神损害后果严重性的要求。考茨欧认为,若加害人故意以有悖于善良风俗之方式造成他人的精神损害,那么受害人即使仅遭“纯粹主观感受上的损害”,其依然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确定精神损害是否严重不应是一个僵化、绝对的标准,而应采取一个动态的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各种具体要素的强度。[44]
五、结语
萌发于英美法系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内容纷繁复杂,法院基于实用主义而不得不采取的赔偿与限制赔偿规则更像是“责任规则的拼凑图”[45]。值得深思的是,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纯粹精神损害”得以赔偿的部分限制,但最初促使其产生限制的怀疑却并未消除[46]。因此,对如何在给予赔偿与拒绝赔偿之间划定一条恰当界限问题的讨论,在这一怀疑的牵引下仍将继续存在。
“可辨识精神疾病”这一要求虽稍显僵化,但由于“纯粹精神损害”不同于传统的附随于人身伤害所致的精神损害,为防止“诉讼洪流”的产生,确定一种客观的标准实有其必要性。鉴于对精神疾病后果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较为苛刻且更新迭代较慢,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因此应当认为这一客观标准并不具有决定精神损害产生与否的效力。也就是说若无此项精神疾病鉴定,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发生了精神损害。[47]我国立法也应吸取这一经验,规定在判断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时,绝不能单纯以医学的精神障碍鉴定标准为根据,而应采用一种更为动态、柔性的判断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影响判断的各项要素不应仅仅是可以被综合弹性评价的因子,而应是体现法律规范目的的法原理。[48]此外,各项要素的选取与价值权重的排列也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这几乎是各法域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最早形态。参见G.爱德华·怀特.美国侵权行为法:一部知识史[M].王晓明、李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9。
②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精神损害场合不存在人身损害,根据医学、生物学领域的认知,精神损害亦会引起身体反应,甚至产生身体上的伤害(如消化系统等)。虽然纯粹精神损害在诉因上脱离了人身依附,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被完全割裂。参见Walter B.Cannon.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 An account of recent researches into the function of emotional excitement [M]. D Appleton & Company,1915.因严重精神痛苦所导致的生理表征与附属于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二者存在“因”与“果”的差异。此处更在于强调加害行为对精神利益的直接侵害。
③曾任美国法学会主席的Herbert Goodrich也曾表示,精神痛苦与身体伤害都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可被进行“科学性的”理解。Page V.Smith,[1996]AC 155,at 187,参见Herbert Goodrich.Emotional Disturbance as Legal Damage [J].Michigan Law Review,1922(20):499.
④这也是社会妥当性原理要求的体现,即处于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精神上的不利。参见Elizabeth Handsley.Mental Injury Occasioned by Harm to Another: A Feminist Critique[J]. Law and Inequality: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1996(14):424.
⑤Kelly v Hennessy[1995]IESC 8,[1995]3 IR 253.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编著.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6 卷[M].王文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77-279.
⑥在澳大利亚The Civil Liability Act 2002 和The Civil Law(Wrongs)Act 2002 两个法案中都明确规定了“recognized psychiatric illness”,而非“recognizable psychiatric illness”。然而,前者意味着原告陷入了对精神障碍的历史理解,更偏向于“可确认的精神疾病”之含义,而全然不顾科学见解的快速发展。后者则反映了原告在出现了可以被描述为精神疾病的症状时,会被认为遭受了精神损害,而有关此一状况可能尚无一个公认的名称,此时即不能满足“recognized”的要求。由此可见采用“recognizable”一词更为恰当。有关其具体区别,参见Desmond A.Butler.Gifford v Strang and the new landscape for recovery for psychiatric injury in Australia [J].Torts Law Journal,2004(12):124。
⑦Hinz v.Berry[1970]2 QB 40 at[42].
⑧欧洲著名的侵权行为法学者冯·巴尔教授虽反对使用类似“纯粹精神损害”的概念,但也明确指出诸如悲伤、忧虑、痛苦之类并未构成精神疾病的精神损害通常不能获得赔偿。参见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M].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8。
⑨但需注意的是,谢鸿飞在此提及的“纯粹的精神损害”之内涵与本文主题的内涵并不相同。前者是指不构成精神疾病的精神损害,通常不获赔偿。美国的概念更关注损害的发生原因,只要是独立的、非衍生性的精神损害都属于赔偿范围;而欧洲各国强调不构成精神疾病的精神损害。参见谢鸿飞. 惊吓损害、健康损害与精神损害[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3):103-109.
⑩White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1998]3 WLR 1509.
⑪又称“癔症”,see to Brice v.Brown[1984]1 All ER 997.
⑫Vernon v.Bosley(No 1)|[1997]1 All ER 577.
⑬另一极端则为Jane Stapleton 教授呼吁彻底取消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回归到19 世纪“Coultas V. Victorian Railway commissioner”案中的裁判立场,即无基础人身损害时,当事人仅就其精神损害提起诉讼的,不予赔偿。
⑭The Law Commission.Liability for Psychiatric Illness[R].[1998]EWLC 249,54.
⑮Page v Smith [1996] AC 155(CFS);Vernon v Bosley(No 1)[1997]1 All ER 577(PGD).
⑯Brown & Anor v. The Mount Barker Soldiers' Hospital Inc.[1934]SASR 128.唯需注意的是,国外论著在介绍此案中均聚焦于法官致力于寻求人身损害的踪迹(甚至包括眼泪)以此避免精神损害严重性之要求,或可能招致误解。该案所强调的乃是由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身体上的反应,参见Danuta Mendelson.The Interfaces of Medicine and Law:The History of the Liability for Negligently Caused Psychiatric Injury(Nervous Shock)[M].Dartmouth Pub Co,1998:108-109。
⑰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原告在看到被告(瓶装水制造商)将装有一只死苍蝇和另一只苍蝇的残留物密封在大型水箱中并送到他家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并声称自己再也不敢喝酒、洗澡等。Mustapha v Culligan of Canada Ltd.,2008 SCC 27,[2008]2 SCR 114.
⑱Saadati v.Moorhead[2017]1 SCR 543.
⑲当然,基于侵权法整体的规范目的,此种对精神利益的保护并非不受限制。
⑳McDermott v. Ramadanovic Estate(1988)27 BCLR(2d)45.
[21]上述考量因素并非要求必须具备,并且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也应根据具体案件予以确定。
[22]诸如被困在电梯里近一个半小时所造成的“心理上不安”基于社会妥当性原理应被视为一般社会风险而不能获得赔偿,参见Reilly v.Merseyside HA(1994)23 BMLR 26(CA).
[23]张新宝教授将精神损害,进一步划分为轻微精神损害、一般精神损害与严重精神损害。轻微损害不予救济,而一般损害则可给予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救济。参见张新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