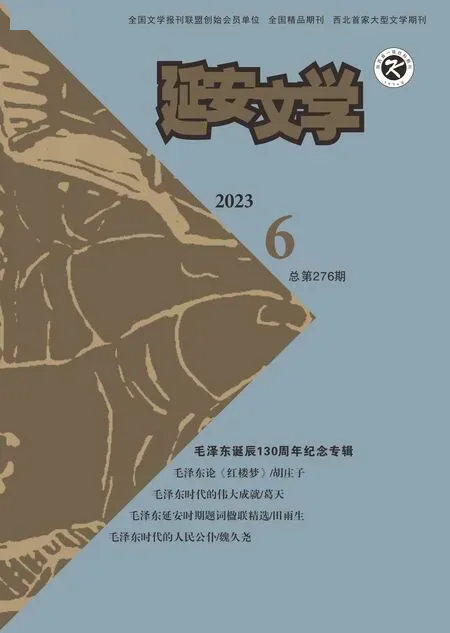南新路的烟火
杨 萍
我在细碎的时光里往返,看见他们的坚韧与努力。
一
黄昏时分,倦鸟归林,人们从四面八方抵达同一个方向,在即将隐匿的光里,南新路散发出另一种生机。
南新路南北朝向,是一条没有公交通行的巷子。两边原本是燃气公司、供电局等单位的家属院,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新楼盘也适时地在这里安身。新房子由深色的高档墙砖和宝石蓝玻璃做了外墙,显示出一些时尚和大气。家属院大多被乳黄、灰白、灰粉的涂料刷过,已经呈现出很多破旧。被冬青包围的路两边是整齐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十几年过去,枝干挺拔,冠如华盖。在西侧的梧桐与小区的外墙之间,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夜市,它的存在看起来极具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人口密集的地方,是小商贩们喜欢奔赴的地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更是一种生活的及时补给。无数个黄昏,我在这里徘徊、张望,寻找适合自己的食物,看看来往间一张又一张面孔,感受一些相投的气味。
其实,喧嚣声一般从下午四点就开始了。摊主们必须赶在人们下班前做好准备。三轮车的突突声,电动车的铃声,商贩们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人们见面的问好声,南腔北调地交织在一起,拉开了烟火人生的又一个帷幕,显现了另一种丰富和喧嚣。凉皮、包子、馄饨、砂锅、麻辣烫、炸串等,香味阵阵扑鼻。各种季节性水果摊就地铺在一张张塑料纸上,来人就用水果刀切上一块递过去。也有卡车拉来西瓜、苹果、梨、橙子等,找一个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停下来,随便一块纸牌子上用黑色的粗笔写着价格。偶尔,路边会停放一辆面包车,撑开几个架子,或鞋子或衣服,还有商场里打折撤柜的床单被罩。
每一条散发着烟火气的小巷,总是真实反映着一座城市的图景。临路的陈设和卫生条件有限,但因为实惠和快捷,对于步履匆匆的工薪阶层来说实在是一种安慰和欣喜。老主顾们常年在这里消费,与摊主们十分熟悉,摊主们也不好意思上调价格,期间几次物价上涨也是在其它地方调整几个月以后。一年也有那么几次,会有几张折叠床拼成的书摊,上面摆满了各种书,从小孩的拼音识字到名人传记,各种励志、营销、烹饪、旅游,也有一些文学书籍。我家里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白鹿原》《静静的顿河》等就是从这里买回的,除了包装简陋外,并无其他不适。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卖菜的,从菜不够漂亮的长相和没褪去泥巴的新鲜劲来看,必是刚从地里出来不久。岁月把痕迹毫不留情地刻在卖菜人的脸上手上,让他们生出一些衰老和沧桑,也生出一种被信任和亲近感。品种单一又长短不齐的菜经过他们的挑选和归置,铺在一张张东拼西凑的广告彩页上,显示出一种朴素干净,卖菜人拘谨的表情和期盼的眼神让人心疼。路过的人看上哪个就拿了哪个,账也好算,免去很多称菜找零的麻烦。
每年七月到十月,卖核桃的人总会准时出现。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总是面无表情,与几米之外热情招呼顾客的其他商贩完全不同。他蹲在一个人为踩踏出来的小路口,背后刚好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很多时候,他蹲靠在树前,好像与这棵树有着亲密的关系。几大袋青皮核桃堆在他身边,一把弯曲的小刀在核桃皮上划一下,圆滚滚的核桃就掉在面前的小盆里,发出阵阵咣当声。他的核桃总比其他地方贵,但他根本不理睬买主的还价,付完钱后也不愿意多给一两个。他冷淡的态度和表情,让我想起奥利维亚·莱恩在《孤独的城市》中讲述的情形。他处在喧闹中,又与喧闹中的人们有一种疏离。他拒绝与人沟通的冷漠让我觉得卖核桃这种事情最适合他,只是偶尔会想,卖完核桃以后的日子他去了哪里。
二
生活每天看似在同一条轨道上穿行,又不乏遇见一些不同的事,它们微小、细致、坚韧,就像路边不断冒出的草尖,让人在漫不经心中动容。
如果没有例外,我每天下班都会穿过车流如潮的大庆路,在红绿灯亮起的间隙,从一个喧嚣走向另一个喧嚣。卖面皮的生意好了,卖麻辣烫的就过来帮忙,卖熟食的没零钱找,卖炒面的就把零钱递过来。面对各色买主,摊主们也不吝啬,这个调料要重,那个辅菜要多,这个要宽状那个要细条。他们记性出奇地好,总能记住购买者的嗜好,甚至忙里偷闲还拉几句家常。收钱的箱子大多是一个小塑料箱子或者纸盒子,它们随意摆在边上,放钱找钱都是顾主们自己动手。灯光下,伴随着操持者被映照的面庞和不停歇的双手,一碗又一碗的美食端上了高高低低的桌子。
面皮摊的老板是个圆嘟嘟的漂亮女子,肤白,发卷,长得好看,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娜娜。娜娜见人开口就笑,取、切、调、装、递,简直堪称飞速。“娜娜,娜娜”,人们亲切地称呼着,仿佛娜娜是自己的侄女或小妹。
卖麻辣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玻璃橱柜上写着醒目的几个字“爱情麻辣烫”。媳妇白净大眼,小伙子留着时髦的卷发,身边的音响里常年流淌着好听的音乐。两人配合默契,不由得让人想到爱情的美好。时光荏苒,他们的女儿也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那个在小推车里挥舞着小手的婴儿已经长成白净的小姑娘,梳着亚麻色的头发,看见她蹦跳间阳光健康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
卖卤煮的小伙子几年间戴上了眼镜,不知道是装饰还是有实用价值,看上去增添了信任感。他因为性格的开朗生意特别好。他时常哼着一些流行歌曲,双手忙碌的同时不忘记与来往的人热情招呼,言谈间不断夸赞自己的新菜品和手艺,招呼别人品尝,过路的人经不起他的诱惑,买与不买间不由得停下来,一看二看的就忍不住买点熟食回去。
靠着围墙凹进去的是一个四、五平米的小房子,因为光线的原因屋子里面特别黑,只有走到门口才能发现屋内的摆设,一排排简陋的货架上稀疏放着一些饮料与食品,门外的桌子上是馒头面包酸奶,方便过路的人随时拿取。它的经营者大约有五十多岁了,她把房间内的东西搬出搬进,不忙时会原地跑步或者压腿拉伸,也去旁边的摊位帮忙。
卖炒面炒米粉的两口子是外地人,媳妇负责收钱,把各种待加工的面条米粉提前按量盛到盘子里,老公不断翻炒,额头有汗珠下来,头一侧,媳妇就用毛巾给擦一下。好几次我都在观察他油少饭香的窍门,他奋力颠勺翻滚的样子简直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卖肠粉的女子常年戴着口罩,我几乎没有看清过她本来的样子,唯一露着的眼眸里像聚集了一汪水。她在清晨的路口承包了流动早餐车,我是从她的眼睛认出来她的,有次吃肠粉,便主动询问是不是一个人,她说早上时间短,东西也是统一配送,还不算辛苦。说话间隙,我看见她在雪白软糯的粉上浇了芝麻酱和辣子油,简直让人垂涎不己。
卖小笼包和米线的原本是两口子,都是五十多岁的样子,男人的右腿有点跛,人看起来有几分儒气。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出摊,再出摊时就只有女人一个了。有次吃米线,看人不多,随口问一句,她淡淡地说,男人脑溢血走了。我为我的多言感到自责。她的眼神停顿了几秒,有些淡淡的哀伤,即刻又转换话题,问我饭的味道咋样。我不知道要不要多问一些,又怕自己廉价的关心和安慰引起她的心事。她依旧娴熟地忙着手下的活,招呼来人坐下。一阵风吹乱了灶头的火苗,也吹落了几片树叶,这是谁也没法改变的事实,日子总是要向前走的。这么多年,我企图用一些修辞来描述更多的情绪,但总有一种时刻,让我觉得没有任何修辞可以配得上一个人突如其来的遭遇。
南新路东边的路口,有个裁缝摊和修鞋摊。裁缝摊的老太太应该是附近家属院的,她的缝纫机锁在院子围墙的栏杆上。天气晴好时,一米高的纸壳子竖在墙前,写着“修补衣服”四个字,字是用毛笔写的,楷书,很见写字者的功底。老太太头发基本全白了,烫发,戴眼镜,胳膊戴两个袖头,给人心灵手巧的感觉。我改过裤边,给孩子衣服换过拉链,手艺绝对可靠。
与裁缝老太太相比,修鞋的人形象就差一些。乱糟糟的头发和黝黑的脸庞,衣服也是黑的,腿上永远盖着一大块旧皮子,使我怀疑他的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身边随意摆放几个又低又矮的马扎,上边的帆布颜色也已经发黑了。几把旧伞堆在一块塑料纸上,几个木头盒子围在他脚边,我路过几次,暗暗观察,并没发现各个盒子里的东西有什么区别。有次,我去修鞋,我等得心急,他却不紧不慢,和旁边的人闲聊着。来人给他发烟,他也不擦手,接了放进嘴巴,那人又用打火机给他点着,他并不用力吸,只是把烟叼在嘴上。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妇人,她的要求高,不断提醒他胶要多线要密。我看见了他收的对方的钱数,到我时他要了比老妇人高二倍的价钱,我问他为什么价格不统一,他狡黠地说老年人没钱。旁边几个人就起哄,说他看人下菜,让我给他少付些,他也不多言语,只是讪讪地笑着。我终究还是不好意思少付。
与大路连接的西边拐弯处是个药店和果蔬店,门口是一排凳子,这里一年四季围满了年龄稍大的人,下棋的抽烟的闲聊的歇腿的,除了下棋像吵架外,其余的人神态悠闲,熟悉不熟悉的都能搭个话,说说物价、养老、子女和身体里不断扩张的疼。
三
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因各种原因,这里的摊位会集体消失几天,也有心急者会在晚上八点多以后潜出,如同玩一种游戏。幸好再集体出现时,一切又恢复之前的喧嚣。
忽然有一天,摊位里会多出几个年轻人,他们明媚、干净、明亮,有一种对未来跃跃欲试的热情,这种热情如同一阵清风,将树木和花草中的清香吹起,只是没多久便不再看到。我想象着他们一定有了更好的谋生方式,在更宽阔的地方奔跑,像路边的梧桐一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生长的土壤。
南新路最寂寥的时间是冬天。黄昏来得快,走得更快,仿佛有人故意把时间的表盘拨快。梧桐叶在冷风中飞舞,来往的人夹紧衣物,缩着身体,大家急着回家囫囵一顿晚餐应付,很少有人慢条斯理地坐着闲聊,出摊的也会一天比一天少。平日里的路人仿佛失踪或者绕道而行,南新路很快变得空荡荡。摊主们表情落寞,眼巴巴地盯着路口。偶尔来一位客人,大家奉上所有热情,当客人选好一个摊位时,他们像啄食的鸟,呼啦地全围过去,顺便沾些炉火的热气,咒骂几句天气,宣泄下某种情绪。
我在南新路往返,细数每一个摊位,和不认识的人对视,抬头仰望路边的梧桐。梧桐的整个树荫笼罩着大地的时候,是每年最热的时候,也是南新路最有活力的时候。酷暑拉长了南新路的黄昏,也照亮了南新路上人们的希望。夜晚来临,宝蓝色的玻璃幕墙上不再映射出夕阳的金色,飞鸟们也一只只回到了鸟巢,只有南新路上的盏盏灯光给了这里更多的温柔。我不大会向眼前的场景主动询问,但眼前触手可及的鲜活常常让我觉得内心有种从容和踏实。我嗅着美食的味道,也嗅着人生的庞杂和不易。
夜空幽远,南新路的各种声响渐次消失,唯有路边的梧桐树,带着慈悲的目光,安静地守候着南新路的烟火和众生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