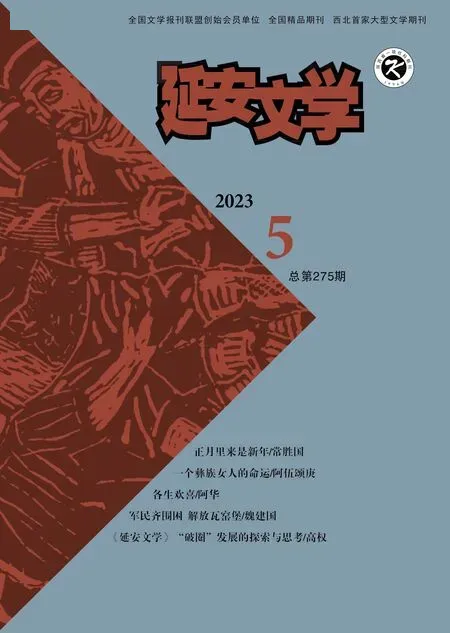黑牛来过
柳 笛
老周终于有钱买了根上吊绳,走了。
晨练回来路上,罗茂林碰见老姜。听了老姜的话,罗茂林小腿肚子哆嗦起来,问,啥时候的事。老姜说上星期。估摸罗茂林还会继续问下去,老姜又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吊死在小王村外的槐树上。
老周是丑角,也是团里的台柱子,老姜的好搭档,比老姜小十来岁。老姜从县戏剧团调到文化局当副职时,准备把挑子撂到老周肩上。那时候县戏剧团已经发不出工资,老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见了团里的老伙计都是那句话,我想上吊,手里没钱买那根绳。
玩笑话不能乱说,老周一言成谶。
老周老婆原来是化肥厂宣传科科长,化肥厂也是县里第一家倒闭的企业。老周老婆下岗后到集贸市场卖蔬菜,到超市里当理货员,反正没闲过一天。平常情况下,日子紧巴点也能过得去,但老周老娘慢性病卧床好多年,每月得几百块钱的药费。老周老丈人换肾花了几十万,还得药物维持。两口子家里都有病人,都是亲爹亲娘,又不能不管,老周有时候能拿回家几个子儿,有时候一连好些天没进项,孩子还要上学,跟老婆磨嘴生闷气的时候自然不少。
有次罗茂林跟老周喝闲酒,看老周喝酒的样子有点害怕,知道他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老姜调文化局时,老周下决心离开戏剧团单干,给个团长也不再稀罕。老周领了几个人成立了商演公司,参加各企业年会庆典活动,到县城各大商场搞活动促销。老周有丑角搞怪搞笑的家底子,除自个编排的小节目,还能根据雇主要求编排新节目。一开始,商演公司业务不错,老周带着几个人还能落个辛苦钱。没过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先是业务少了,即使偶尔有了业务,老周原来那一套也搞不起来气氛。不是说不叫好,而是连看的人都没有,台下稀稀拉拉两三个人,这活动这演出就没什么意义。不光没人气儿,这几年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庆典公司,都是年轻人操作,老周学不来那些年轻人的东西。学不来新东西,企业商场的业务都丢了,老周只得把业务一竿子插到乡镇村子里,无非是婚丧嫁娶红白事儿。见了罗茂林,老周说,我这张老脸彻底不要了。
团里这么些老人,怎么都没听说这个消息呢。罗茂林问老姜。
老周不愿当团长,老姜自然找到了罗茂林。罗茂林三推五推推不出去,勉强接了。接了团长,罗茂林跟老姜说,又跟团里的老伙计们说,谁也别指望我能把担子放在肩上,我可没那股子力气,上边派个人来正好,不派人来我等着,哪位有力气随时把担子接走。
罗茂林是相声演员,跟团里的大队人马挨不上边,情急之下搬搬戏箱,干点跟相声无关的杂活,虽说能上台表演,毕竟不是团里的中军大帐。接了团长的位子,更大意义上是帮了老姜的忙。老团长要调走了,找不出新团长来,老姜怎么走马上任?所以,罗茂林跟老姜说话向来有底气。
老姜想苦笑,却笑不出来,一张表情很奇怪的脸,说,我也是前天才知道,人在殡仪馆放着,还没有火化。老周老婆不让我问半句,不但不让我问,还不让我往外说。叫孩子给我磕了个头,说,老领导的好意心领了,老周走得不风光,不愿意让老领导老熟人知道。
可能怕罗茂林再问什么话,老姜又说,昨天我想了一天,想给你打电话,我心里不好受,在家里躺了一天,想了想,今天还得在这儿等你。
罗茂林晨练的地方和路线是固定的,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跟老姜碰面。老姜想找罗茂林,在罗茂林晨练路线上一等一个准儿,比打电话还靠谱。
老周去小王村演出是为件白事,死去的老汉八十六岁。按习俗,活到这个岁数办丧事算是喜丧,孝子贤孙们都不伤心难过,虽然还是披麻戴孝,却没有那么多禁忌了,也能多少有点插科打诨。老周就搞了个小剧本,其实也是老周搞白事上的通用剧本,哪家办丧事都是这个本子,无非是走的人多么德高望重,后辈们多么想继续尽孝。既然想搞笑,一味干数落也没多大意思,老周加了点料,说如果老汉还活着,后辈们恨不得再给老汉找八个姨太太。办完了事,老汉几个儿子说他们老娘还活着,给他们老汉找姨太太的戏词不合适,本来他们老娘就伤心得劝不下来,听了戏词受了刺激,非得跟着老汉走,省得老汉找姨太太。老周说事先给你们看过剧本呀,你们也没提出来修改。老汉儿子们根本不听,到底少给一千块钱。吃罢喝罢,老周让其他人先走,只说自己找个熟人,晚上回县城。谁也没想到他吊死在离办丧事那家不远的小河滩里一棵槐树上。
这年头,一千块钱,世上再没老周这个人了。罗茂林插话道。
老周老婆当年在化肥厂也是能晃动膀子的人,人放在那儿不火化,肯定不会让这事儿这么过去。我还想,老周不是特别冲动的人,区区一千块钱让他走极端的可能性也有,但不会这么大,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所以,老周的事儿,咱们都想送他最后一程,可他老婆横在那儿,咱们过不去呀。
罗茂林明白老姜话里的意思:老周跟他老婆家里都有一个常年花钱的老人,日子过得又凄惶,肯定因为钱的事儿没少生气,谁也说不准老周是不是跟老婆生气在先,办丧事那家少给一千块钱等于往火药桶上扔了一个燃烧着的火把。何况老周老婆压着不办丧事儿,更让人看不透。
从县戏剧团出去另起炉灶的也不单单老周,头把唢呐老端也出去了。没带走人,只身一个人出去的。老端的唢呐独奏得过省民乐大赛奖,也是团里的宝贝。本地习俗,只有丧事才用唢呐,所以老端出去只有东奔西走奔丧事。用老端的话说,专业奔丧,天天浑身晦气,说不定哪天就跟哪家的人走了。
有名气在,老端不成立班子,等别的班子来请。当然也有办丧事的知道老端的名气,又想把丧事办得风光些,就找到老端。老端毫不含糊地对来请的人说,你找我,我也得配人手,干这行的都认识,我请谁不请谁呢?不如你找好唢呐班,跟人家唢呐班说也想叫我去,我准时去,不耽误把人送走就行了吧。来请的人只得照办。只要答应人家,老端有请必去。一来二去,老端不但名声渐涨,行情也渐涨。老端却说谁给我涨行情了,忙活一场,我伸手接过来的还是那么多。言外之意,那些唢呐班从他老端身上揩油了。
都以为老端会玩儿,活也不断,日子好过。罗茂林却看出来了,老端只是端着架子,从团里出来了,不能让大家笑话,实际情况怎么样,谁也没跟着老端。在团里时候,老端喜欢跟罗茂林喝两口。老端出来单干的前两年,似乎很忙,跟罗茂林小酌的工夫不多,后来跟罗茂林喝闲酒的工夫多起来。罗茂林想,老端架子端得稳而不大。丧事嘛,死人埋人,过一周年三周年十周年,又不会哪年事多哪年事少,用流行词儿说,是刚需。老端怎么能闲下来呢?
二两酒下肚,老端的苦水就倒出来了。唢呐吹得再好,还是那些老曲目,现在操办丧事的年轻人根本就不听那些传统曲目。唢呐班不再靠传统曲目招揽业务,上了些泼辣娘们,男人不能说的娘们能说,男人不能脱的女人能脱。老端一口酒整个满杯,墩下酒杯说,越来越看不懂了,老话说死者为大,灵棚下的事儿是多讲究的事儿呀,现在比闹洞房还腥荤。闹洞房不下流,现在唢呐班子弄得比闹洞房下流得多。这还不算,原来唢呐班不管怎么说还都是熟人,现在都是外聘的年轻女子,反正跟唢呐班的人非亲非故,更放得开了。过去唢呐班不要脸,现在脸和屁股都不要了。你说说罗团长,操办丧事的后辈们是让他们先人走啊,还是不让走啊。
见老端喊自己团长,罗茂林赶紧端起酒杯跟老端碰一下,说,寒酸我呢。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听老端一大堆牢骚,罗茂林只得附和。
闲暇时间多起来,罗茂林也学会了玩微信、抖音。说是玩,就是刷刷屏,光看,从来没有发布过内容。老端这么一说,罗茂林就想起自己在抖音上看的视频:一个是乡村大片空地上,舞台上的演员扮正妆走台唱念做打,台下只有两三个老汉和一个骑玩具车的小娃娃。那画面经常在罗茂林脑海中闪过,如果那个骑玩具车的小娃娃走远了,台下又会少个老汉。另一个视频也是乡村空地舞台,下着大雪,舞台上的毡布上溜了冰,看样子是连着好几天的场子,一个跑龙套的轿夫脚下打滑,一屁股蹲在台上,很快爬起来继续跟鼓点走台。虽然扮了妆,罗茂林一眼看出来,那轿夫至少小六十的年龄。视频转向台下,空无一人。除了行业内的人,没人知道台下没一个观众,对台上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老兄当得起团长,没寒酸你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你带着一帮子人闹腾得不错,让团里几十号人隔三岔五挣几个钱。谁不知道姜团长调走时候咱们大半年没开过一回工资了。也不是说姜团长,咱们这个行业就这样,再有能力的人也折腾不起来。
是啊。罗茂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是戏剧不行了,是听戏的人少了。从家家户户有电视开始,咱们戏剧就不行了。现在年轻人连电视也不看了,打开手机,什么东西没有?听戏的人已经老了,年轻人又不听戏,就这么简单。
话说完,罗茂林沉默良久,又说,我哪有本事领着大家折腾,还不是借着给黑牛配戏,厚着脸皮在外面晃悠了几圈?
县是普通的山区县城,是个穷县小县,没有地理优势,交通说不上便捷,没有矿产资源,更没有像样的企业。硬要找出特点,种植有十几万亩茶叶,当然也不是名贵茶叶。
历届政府发展经济都是茶叶搭台,经济唱戏。经济的戏也没什么好唱的,搞了一条山沟发展旅游,勉强挂了4A 的牌子,年接待量也就二三十万人。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好玩的?每年春茶上市时候,也正是景区开始上人时候,县政府牵头组织茶艺节。县城中心规划了茶艺街,全县的茶叶种植户经销商都在茶艺街上开了店。茶艺节盛会就在茶艺街广场上举行。无非请些明星艺人,种茶大户采茶大户登台亮相。每年的茶艺节人山人海,比过年热闹得多,能不能推动创收暂且不说,确实有轰动效应,让整个县城兴奋好些天。
要说茶艺节上请的明星艺人多了去了,但最有名气的是黑牛。其他明星艺人要么是某个年龄段的红人,年轻人知道,上了年龄的不知道,或者上了年龄的知道,年轻人不知道。要么是行当里面的红人,比方说杂技演员,报幕说表演的节目得过什么什么杂技节大奖,观众只看杂技惊险不惊险,谁也不知道那个杂技节大奖属于什么水平。但黑牛不一样,黑牛是全国范围内妇孺皆知的大明星,国家一级演员,十几年间,年年上央视春晚,在春晚上演出的小品年年叫好,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代小品王。
罗茂林研究过黑牛的演艺生涯,一开始也是说相声的,甚至第一次上春晚表演的还是相声,反应也一般,属于勉强说得过去的水平。严格来说,黑牛是相声演员出身,跟罗茂林是同行。黑牛在茶艺节上表演的小品是《秀才作诗》,通知罗茂林跟黑牛搭档演出《秀才作诗》的是老姜。罗茂林心里没底,自己一直是说相声的,虽说跟小品有点关联,但小品就是小品,跟相声的差别还是很明显。老姜说跟这么个大腕合作,机会多难得啊,你先不要推,推给谁去?这不是你个人的机会,得把它看成是咱团里的机会。
再问细节,老姜也说不上来。给黑牛找配戏人选的任务是县领导下达的。县领导是从茶艺节筹备组得到的消息,筹备组是从黑牛经纪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不但老姜,就是县领导,不但没见过黑牛,连黑牛的经纪人都没见过。老姜毕竟是行业出身,直接找到筹备组负责人,追着负责人联系黑牛经纪人,提前几天要来了《秀才作诗》的本子。看完本子,老姜和罗茂林都松了口气。虽然茶艺节演出节目单上说《秀才作诗》是小品,却是双口相声的本子,连肢体动作都很少,而且时间不长,十分钟不到。
黑牛来县城那届茶艺节是最热闹的一届茶艺节。不但请了黑牛,请的歌手也是最当红的,另外还请了在星光大道上红起来的两个外国留学生艺人。好在筹备组对这届茶艺节人气爆满的状况有充足准备,把演出现场搬到了新落成的实验中学大操场上,还卖了演出票,而不是像往届那样就在茶艺街大广场上演出,人人都能随便看。
茶艺节演出的直接效应是“黑牛来了”。这消息如过年的鞭炮,响彻在县城街头巷尾。第一波声浪过后,才传出次声波:黑牛在茶艺节上演的小品《秀才作诗》,光出场费就五十万啊。至于跟黑牛搭档是谁,鲜有耳闻。罗茂林坦然接受这样的结果,鲜花一朵,谁会注意鲜花周围有多少片绿叶。一个是全国著名的小品王,一个是不知名的小县城戏剧团里的小演员,混了一辈子混了个国家二级演员,从来没有上过省级甚至地市级的舞台。倒是团里的老伙计们,打来了祝贺电话。罗茂林想不出自己哪儿可喜可贺,人家黑牛几十万出场费拿走了,自己一分钱没见着。想着既然跟黑牛搭档演出了,即便不安排跟黑牛坐在一桌接待酒席上,最起码安排个跟黑牛碰个酒说几句话的机会,罗茂林还偷偷准备了个精致的签名本,让黑牛签个名。可直到酒席结束,也没见黑牛的影子。
老姜也暗自发力,趁着热乎劲儿跟领导申请县戏剧团的排练经费。县领导说,排练什么,那个小品演得很好?你们老本行自己看看,是不是毫无瑕疵?
老姜没跟罗茂林说县领导的原话,只是满脸无奈对罗茂林摇摇头。罗茂林并没有央求老姜到县领导那儿申请经费,但老姜到底是从戏剧团出来的,事儿没办成,也算尽心尽力了。只不过后来罗茂林还是听到了县领导拒绝老姜说的那几句话。这话说得!县领导真懂行吗?小品《秀才作诗》是黑牛的本子,演得哪儿有瑕疵?到底是黑牛有瑕疵,还是我罗茂林有瑕疵?县领导根本就不想给戏剧团一分钱,信口雌黄!
县领导那句话,成了罗茂林的心病。不给钱就不给钱吧,罗茂林不计较,戏剧团几十号人也早习惯了。可是县领导懂表演吗,怎么能随便对表演指手画脚?
罗茂林拿到《秀才作诗》的本子,仔细揣摩了角色,又把历届央视春晚上黑牛的剧目收集起来,研究黑牛的台风、语气、停顿、眼神、表情还有肢体动作。只可惜没找到《秀才作诗》的表演视频。没办法,只得凭着自己的心得一遍一遍练习。因为茶艺节筹备组送本子时就说过,黑牛档期排得满,没有彩排时间,只有候台那几分钟交流时间。罗茂林也理解,国内一线大明星嘛,不到十分钟的节目,怎么会抽出时间彩排呢?不要说黑牛,一块儿来的那些歌星也没有一个提前来的,都是直接登台。县城搞了这些年的大型演出,来那么多明星艺人,罗茂林自然知道。
小品《秀才作诗》其实是个小笑话,用两段顺口溜串讲一个秀才出游寻找作诗灵感,碰见一个叫花子跟着胡乱对诗,把秀才作弄的小故事儿。罗茂林饰演叫花子,黑牛饰演秀才。一开始是秀才登场作自我介绍:春光大好,高秀才我诗兴大发,怎奈找不到妙词佳句,特来郊外散心,把肚子里的好诗找回来。叫花子从另一侧登台,念白作自我介绍:叫花子我肚里像虫咬,沿街挨户的剩汤剩饭叫我受不了,刚来村外拉一泡,迎面看见……秀才开始念诗:河边一群鹅,见人就下河。叫花子接过秀才的诗开始念:北风吹屁股,明天接着屙。这时候台下会有笑声、掌声。台上呢,秀才见叫花子接他的诗,又见叫花子蓬头垢面,一副不愿搭理的样子。叫花子见秀才轻视自己,只管揉自己肚子,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这时候没有台词,全靠表情赢得台下叫好,推动故事往下发展。如果非要说《秀才作诗》是小品不是相声,也只有这点小品元素。
故事往下走,秀才走一步,叫花子在后面跟一步。秀才继续念诗:春光无限好;叫花子接一句:心慌满地跑;秀才念:才华一肚子;叫花子念:心事你知道;秀才念:心急嘴起泡;叫花子念:这事犯不着;秀才念:新诗哪里找;叫花子念:树下小土坑。这时候秀才转身打量叫花子,问:土坑有新诗?叫花子答:一挖一大泡。秀才又问:一挖一大抱?叫花子答:一大泡。如此反问对答两次,秀才到树下扒小土坑,以夸张表情甩着两只手,念白道:树下土坑里,新诗哪里找,两手粘稀泥,臭死我老高。然后,鞠躬谢幕。
罗茂林想,即便黑牛不提前来,演出当天总要碰个面说说戏吧。可是直到登台前几分钟,才见报幕员引导着黑牛来到后台处。报幕员指指罗茂林说,黑牛老师,这是跟你搭档的罗老师,咱县戏剧团团长。黑牛很随意对罗茂林点点头说,罗老师好,辛苦罗老师了。罗茂林忙说,应该的。接着罗茂林就想对对戏,说说小品里的两三个关键点。不料,黑牛客气后,把脸转向舞台外面,视线透过学校围墙,落在远处的山岭上。看样子黑牛没怎么见过山,对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山岭非常好奇。
不到十分的小品,台下响起好几次掌声欢笑声,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的舞台效果。但有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那么两三个地方,罗茂林很不满意。
罗茂林演的叫花子上台第一次念白,念到“沿街挨户的剩汤剩饭叫我受不了,刚来村外拉一泡”,正想念还没念“迎面看见”时,黑牛就念了“河边一群鹅,见人就下河”,抢了罗茂林的词儿。只有叫花子念出“迎面看见”四个字时,才能说明叫花子看见高秀才了,然后才跟着秀才念下面的打油诗。叫花子没念出“迎面看见”就跟着秀才念下面的打油诗,秀才跟叫花子碰面的前因后果就没交代清楚。说书面语就是人物和背景没理顺,逻辑关系不合理。
到了“被风吹屁股,明天接着屙”,罗茂林想着跟黑牛有几个表现“你不理我,我不服你”的意思的夸张表情和动作,引起台下叫好、掌声。喜剧小品,搞笑嘛。但黑牛直接就跨到了下句台词“春光无限好”,罗茂林准备的几个表情和动作都没用上。原本能成为一个高潮部分的机会,就这样白白流失了。当然,这个地方只是罗茂林自己的想法,既没跟黑牛事先交流,又没有彩排,罗茂林心里也放下了。
让罗茂林心里放不下的还有结尾:秀才问,一大抱?叫花子对:一大泡。因为“报”和“泡”两个字是近音字,得反复对答几次,本子上是反复两次,只有反复几次,才能反映出秀才求诗心切,才能增加喜剧效果。黑牛只念一次就到树下扒小土坑去了,随之而来的掌声叫好声是冲着演员鞠躬谢幕,而不是冲小品最后一个喜剧高潮。罗茂林感觉自己像一个给买客称好重量又趁买客不注意拿下两棵葱的偷斤短两的小菜贩子。
接到跟黑牛配戏的通知之后,罗茂林找到县文化馆一个搞摄影的朋友,跟他说了茶艺节上跟黑牛搭档演出的消息。搞摄影的朋友很灵透,马上明白了罗茂林的意思,说,放心吧。搞摄影的朋友是个发烧友,不但摄影技术好,相机更是顶配。果不其然,演出结束后搞摄影的朋友发给罗茂林好几十张《秀才作诗》的剧照,连罗茂林跟黑牛的表情都非常清晰。罗茂林请摄影师朋友喝了几杯,摄影师朋友又替罗茂林精挑细选了十几张照片,彩扩后加了水晶框,还专门制作了两幅杂志大小的水晶框,可以装在手提包里。
县电视台也给罗茂林发来了演出视频。实际上,茶艺节演出大会上也只有罗茂林一个本地演员。电视台发来的视频是大会整台演出的视频,文件太大。罗茂林又请人剪辑出《秀才作诗》那段,存在手机里。
有了跟黑牛演出的剧照和视频,罗茂林再出去拉业务就容易了。不只罗茂林自己,团里两三个跟罗茂林关系好的演员外出跑业务时,也会把罗茂林摆在桌子上的剧照拿出去,也不跟罗茂林打招呼。看见桌子上摆的剧照不见了,罗茂林就知道又有人出去跑活了。有时候碰见同行,罗茂林晃晃手机上的剧照说,活到这个份儿上,越老越不要脸了。
在手机上看视频有个好处,能看见视频总共多长时间,现在播放了多长时间。罗茂林反复播放,牢牢记住了小品开始、中间、结尾三个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掏出手机给人看时,果断地把那三个不满意的地方跳过去。
不管是罗茂林还是团里几个能说会道的演员,揣着《秀才作诗》剧照跑业务的效果出来了,陆陆续续接到了演出,让团里几十号人过了一段能发下工资的日子。罗茂林还意外接到市里几个演出,虽然仍是企业年会、庆典之类的商演,但市里的条件规格仍比县里高出一大截。也有企业咨询能不能演小品《秀才作诗》,罗茂林解释,《秀才作诗》是黑牛老师的本子,咱私下演出不妥当,可以演风格相近的剧目,也可以根据要求专门创作写本子,你们满意了,再排练演出,保证跟《秀才作诗》没有水平差距。大部分企业能理解,也有一两家坚持让罗茂林演《秀才作诗》,罗茂林只得放弃业务。打着跟黑牛同台的幌子出来找业务,已经让罗茂林汗颜,又怎么能侵权偷演黑牛的本子呢?
市里的几个演出,大部分都是罗茂林个人的演出,偶尔有两人或多人演出的节目,也都是市里同行来做搭档,酬金都很薄。严格来说,在市里演出只是罗茂林的个人私活,不管单人演出多人演出,跟县戏剧团没直接关系。第一次到市里演出,罗茂林不知道什么情况,通过熟人口头通知,也不签演出合同,演出结束后一顿接待酒席,按说好的数给个红包,简单利索。第二次再去市里,罗茂林带了团里的会计,接了红包直接递给会计。
罗茂林心里藏的话让老端说出来了:得当得起这个团长。但不景气的现状超出了罗茂林的预料,戏剧团很快就跟着老周的路子走下去了,一头扎进乡镇村子的红白喜事儿。戏剧团仅有的传统业务很快被市里省里的庆典公司抢去了。
县辖范围内几百个村子里,县戏剧团还是块牌子,大锅占了老周的小碗。罗茂林找到团里几个老伙计商量,老周活最多的几个乡镇,县戏剧团不下去,如果非得请县戏剧团,也请老周参加,收入平分。其余乡镇算县戏剧团的,如果也非得请老周,团里派人出人出力,收入也平分。团里有几个人摔脸子,罗茂林说,原来跟老周一个锅里吃饭,艰难时候咱还在一个锅里吃吧,就这么个现状,还不知道能一块吃几顿呢。摔脸子的人也不再吱声。
把老周带上后,不管罗茂林还是老周接到活,都会叫上老端。罗茂林叫老端时都是那句话,走吧,一块儿解解闷去。老端胸中的郁闷就像唢呐里的气流一样,被强行排出来。实际上,除了罗茂林跟老周,几乎没有唢呐班请老端了。
罗茂林不相信老周因为一千块钱把自己挂在河滩槐树上,再怎么说也是几十岁的大男人,那么多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这么低一道坎还过不去吗?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罗茂林也不敢贸然猜测老周老婆到底怎么挤兑老周的,也有可能老周一时半会儿想不开。
老周这么个死法,罗茂林的心尖尖疼。
说了老周的事儿,老姜又问罗茂林,老端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老端又怎么了?前几天我还跟他喝闲酒。罗茂林差点惊掉了下巴。
癌。老姜低声吐出一个字,前几天碰见他老婆,我也是没话找话,问老端还忙活着往外跑吗。他老婆没说几句话就掉泪珠子,全家人都知道,就瞒着老端一个人呢。
老端脾气不好,性情孤傲,在团里时也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其实人不错,就那么点儿小毛病。丧事上的唢呐班不是原来的唢呐班了,老端看不下去,有时候他看不上的班子来请也不再去。人家唢呐班现在根本不靠唢呐揽活,有的班子连个正经唢呐手都没有,带了音响放录音,缺了现场吹奏照样接活,全靠那些老端看不上眼的袒胸露乳搔首弄姿的年轻女人表演,照样有人叫好。
我经常想,咱这行成用不着的老古董了。罗茂林说。
老古董也不能扔了呀。老姜说,老古董没实用,为什么人收藏得小小心心?不管什么时候拿出来,那价格不是一般能比的,越是眼前实用的,反倒越不值钱了。为什么?古董就是岁月,就是情怀呀。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做思想工作做得叫人心服口服。
别再叫老领导了,退下来了,就是个没用的老头,叫老姜!我听了心里最舒坦。
咱团就像一艘小破船,水面上风又急又大,船又破又小又漏水,船上人多,我早已经没有力气,再也划不动了,也不想往前划了。老姜不让罗茂林再喊领导,罗茂林也不好意思转脸就改口喊老姜,只得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的话,罗茂林早就想找个人说说,但跟谁说也没有跟老姜说合适。
别泄气,一泄气几十口人都得到大街上找饭吃,人不就活一口气吗?不管你能把小破船划多远,只要有一口气力,只管往前划。老姜伸手狠拍罗茂林的肩膀,拍得罗茂林有点趔趄。老姜又说,比咱周边几个县城的剧团,咱是最好的。那几个县的剧团好几年前就散伙了。咱东隔壁的县剧团散伙了不说,几个年轻女演员到外地大城市会所里表演色情节目,没出路的演员气不过,把剧团宿舍的床铺门窗全拆了,只要能发泄的地方,没有放过的。
罗茂林不语。
老姜说,知道你不容易,就算哪天咱也散伙了,团里不会有人说你半个不字,干这行了,就是这个行业的命。跟黑牛配戏也好几年了,手里的招牌也不新了,往后还会更难。
罗茂林说别提黑牛了,丢死人了。
老姜眨巴几下眼睛,问,我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也怪我,是不是没给你说起过黑牛演出那天的事儿。
演出那天,黑牛有什么事儿,过场不全走完了吗?罗茂林有点丈二和尚。
老姜笑笑说,你不愿意提跟黑牛同台演小品,是因为黑牛在开场和结尾抢了你的词儿,中间有个地方表情动作都没到位。抢了你的词儿,你在台上表现得有点僵硬,外行人觉得你跟黑牛水平有差距。可这事儿我门清啊,本子我也看过呀。那时候跟领导要经费,我专门拿了本子跟领导理论过,当时不给经费跟《秀才作诗》的演出效果没有一点儿关系,就是县财政挤不出钱。
对呀,老姜看过本子看过演出全过程!堆积在罗茂林胸口好几年的冰块开始融化了。
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你就想着怎么跟黑牛对戏了,没研究过那年茶艺节演出节目单吧。
节目单怎么了?罗茂林不知道老姜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的,到底想说什么。
黑牛那天差点赶不上场,把节目单上的节目往后推了三个,才赶上你跟黑牛上场。而且那天黑牛还紧赶下一场,下了台直接走了,连县里一帮领导都被他放了鸽子。他抢你的词儿是急着下台走人呢。发过来的本子,就那《秀才作诗》,从来没有公演过,只是在县一级城市商演专用的。后来我在《传统相声经典剧目大全》上看到过,黑牛做了很多修改。如果是地市级城市商演,是另外一本子,《穿高跟鞋走钢丝绳》,同样没有公演过。那天黑牛走得急,留下助理办理出场费手续,筹备组里的人跟助理闲聊聊出来的。
罗茂林再次无语。
老周这事到底怎么办呢?良久,老姜长长叹口气,像自言自语,又像问罗茂林。
罗茂林此时的心情跟老姜一样,想去送老周,可老周的丧事儿就是一潭想蹚又不敢蹚的浑水。
送别一个人,也变得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