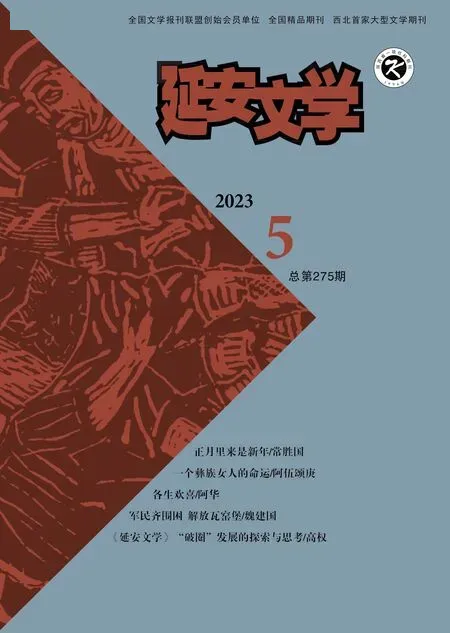读书琐忆
张北雄
年逾五十,看淡了很多事。这不是刻意的“断舍离”,更谈不上通达,就像日子一天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节气跟着年轮就这么过来了。似乎比先前更好说话了。妻问,午饭吃什么?答:随便。再问,衬衣旧了,要不要添两件?答:你看。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其实不然,有些事还是挑剔。在外上学的女儿毕业前夕处理书,电话问有没有要的。本来有点瞌睡,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要求她一本一本报上书名。《传习录》要不要?要。《荀子译注》要不?注译者谁?哪家出版?许是问得太仔细,女儿一会便烦了,在电话那头说:我都寄回来,你自己选吧。
不得不承认:我依然爱书,还挑剔。
启蒙始于读报
我出生在陕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按照叙述惯性,紧跟着是“自幼家贫”之类的话。这当然是真的,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绝大数农村,谁家不贫?贫穷意味着落后,连带着愚昧。好在父亲虽是农民,却念完了“高小”,母亲也在小学上过三年,在村里人看来绝对有文化。大约在我四五岁时的一天吧,父亲突发奇想手指着糊在炕墙上的报纸试着教我识字。先认黑体标题,没想到我很快就记住了。猜想,父母应大为惊讶,于是有了兴趣继续教我。不知父母这样的教学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反正我认识了不少的字。这事情在村里也传开了,有些人出于好奇,见了我就要进行随机测试。比方,我正在大队部的院子前捉蚂蚁玩,路上过来一个人看见我,停下脚步,指了院墙的标语说,哎,你认得这几个字不?待我一字一顿地念完,那人有些吃惊地在我小脑袋上拍了拍说,哈呀,一字不差。能行!被夸奖总归是件好事情,我很高兴。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自家硷畔上玩,坡底下大队基建队的人在挖水渠,有人渴了喊我送点水下来。我不太想去,那人扬了扬手里报纸说,送了水,给你折个飞机玩。我觉得这事划算,跑回家在水瓮里舀了一搪瓷缸子水,一溜烟跑下去。跑到跟前,水洒了一半。那人喝了水,见我不走,想起了刚才的许诺,笑眯眯地说,都说你认得很多字,能把报纸上的标题念对两个,这张报纸就归你。忘了我是否全念对,反正基建队的知青们都表扬了我,我也赢得了那张《人民日报》。
后来,父亲赶集的时候在镇上的新华书店给我买了本《看图识字》。我不光识字,也开始趴在炕上照猫画虎学写字。和现在装帧精美的童书相比,那本黑白印刷的《看图识字》相当简陋,但一点也没妨碍它成为我童年最珍贵的宝贝。我不光在这本小册子上,学会了不少字,通过图画还认识了花生、棉花、水稻等不曾见识的事物。
从长篇小说到儿童文学研究
在村里上了小学,识的字自然更多了。我也渴望更多的阅读。最盼望的事是开学时发新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有故事,有插图。薄薄的课本不过瘾,用不了半天就读完了,心里有些怅然。家里只有一本毛选,翻过几遍觉得没什么意思。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从插队的北京知青那里借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线装,繁体竖排,且是下卷。父亲每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很少有闲工夫看书。我没事时就乱翻,起先发现那些繁体字大多认不得,翻多了又发现似曾相识,慢慢地竟意会了大致内容,看得多了似乎还入了味。有一天看到黛玉之死,鼻子一酸,忍不住失声哭了。这次阅读经历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也尝到了“甜头”,觉得读书就要读小说,比别的好看。开始想方设法找小说看,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放假期间,村里的孩子没事时还到学校去玩。有几个同学发现一间老师办公室里有图书,偷偷从窗户里钻进去“窃”了几本。我素来胆小,那次却眼红得不行,鬼魂附体般干了同样的勾当。同学拣连环画,我专挑大部头的小说。在惶恐和兴奋中读了长篇小说《钻天峰》《新来的小石柱》。这两部小说都是那个特殊年代“三结合”“三突出”背景下的产物,前者讲述铁道兵筑路,后者写农村少年小石柱如何挑战世界体操最高难度动作,成为中国体坛新生力量。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文学性比较差,但我没明没黑地读,生怕没读完被学校发现索回。好在赶开学读完了,老师勒令我们主动上缴偷窃的书,口头教育后再未深究。
随着我阅读胃口的增长,村里的书似乎也多起来。初中毕业的四叔,算是返乡知青,也爱看书。我有时把他正看的书偷偷拿走先睹为快。我在四叔那里看过《水浒传》《今古奇观》,浩然的《艳阳天》《西沙儿女》等。还从北京知青那里看过科普书《十万个为什么》,期刊《北京少年》。从一期《北京少年》的封二上读到过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报道,觉得电视机这东西太神奇,神奇到我无法想象。
我很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几本好看的书。父亲大概每隔一两个月要到镇上赶次集,采购点灯的煤油、食用盐等生活用品。那个年代,村里人手里都没钱,赶集置办东西要卖点鸡蛋、小米、豆子之类的农产品。每次父亲赶集,我都央求给我买本书。父亲要是去赶集,下午放学后我便跑到村口等候。有时直等到天黑了,还不见赶集的人回来,就圪蹴在家里的硷畔上等。终于听到坡洼里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我像只兔子一蹿跑上去,人还未到跟前,嘴里急切地问:爸,给我买书了没?黑暗中的父亲先不吭声,后来有些尴尬地说,他带去的小米不好卖,直到快散集了才出手,那时新华书店已经关门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想哭,但看见父亲疲惫的样子,便忍住了。那种失落,好长时间无法释放。
失望的次数多了,不再抱有希望。没想到父亲有次赶集,主动说要给我买本书,见我不放心,答应带我一起去。是夏天,在小镇的集市上,我生平第一次吃了冰棍。父亲带去的小米想卖个好价,果然迟迟出不了手。同去赶集的三叔和四叔带我去书店。两位叔父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走过通往新华书店的小巷时,我兴奋得不知自己是谁了。估计是书店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书,觉得自己有文化的四叔自信地说,儿童文学方面的。售货员就找了本《儿童文学研究》。我们惦记着父亲的东西卖了没,赶散集还要走三十多里路回家,就痛快地买下那本书。等回到家里细看,才懊悔不已。那本书没有一篇小说和故事,主要内容是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这样,我还是把那本书读了几遍,具体内容不太懂,但从此记住了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等人的名字。
心心念念的《红楼梦》
我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候,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文艺开始复苏,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迎来黄金时代。学校阅览室虽然不大,却有《人民文学》《收获》《儿童文学》和创刊不久的《当代》《十月》《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刊物。阅览室就在我们宿舍的旁边,每天下午吃过饭,我在阅览室总要待到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镇上的文化馆也有个阅览室,星期天要是不回家,我就跑到那里去看书。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小说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
小巷深处的新华书店里的书也丰富起来,虽然囊中羞涩买不起,但去得多了,售货员允许我走进柜台在书架上自己翻阅。有一个星期天,我走近书架,惊喜地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1982 年出的新校本。自从小时候读了一半《红楼梦》,一直想把这个“梦”圆了,经常打听谁有此书。有个父亲在镇上工作的同学说他家有《红楼梦》,并答应借我读。等把书拿来,发现也不全,是人民文学出的1974 版,分四册,同学的父亲只有第二和第四册。那天在书店,我爱不释手地把新出的《红楼梦》翻了一遍又一遍,很想拥为己有,可4 元多的定价对我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我一学期的学杂费才6元5 角,学校灶上的一份汤菜5 分钱,肉菜1 角。走出书店的时候,我决定从此每天不吃菜,也要把这套《红楼梦》买下。等到下一个学期,钱攒得差不多时,再次印刷的《红楼梦》涨了价,变成了6 元多,我又买不起了。等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增加了刘旦宅先生的彩色插图,定价涨到12 元多。这下我知道可能永远也买不起了。可还是念念不忘,把这个难以实现的心愿讲给一个要好的同学,顺便大谈《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一部书,连毛主席都说没读过《红楼梦》的只能算半个中国人。同学听了也动了心,他说我有个好办法,放了暑假咱挖药材,卖了钱,一人买一套。我一听这法子还真不错,心想受多大的苦也要实现这个计划。
虽然出生在农村,由于从小体弱,加之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比较娇惯,干活和村里同龄的孩子比,差了很多。放了暑假,当我说要去山里挖药材时,母亲劝了半天。母亲越劝,我越坚决,说自己能吃得下这苦。我们村周围的山上,药材相对容易采的是甘草,村子附近的早被人挖光了,只能去七八、十来里远的山里。那天,我斗志昂扬,带了干粮和一壶凉水,扛着镢头雄赳赳地爬上山。翻了几架山,才在邻村刚刚割过的麦地里发现了零星的甘草。过去只见过别人挖甘草,没想到亲身实践才发现这太难了——指头粗细的甘草根,有的简直垂直生在地里,顺着根系一直挖下去要刨一个越来越大的坑。六月的太阳把人能烤焦,刨了一会儿,我便浑身瘫软,没了力气,干脆跪在土里挖。被汗水洇湿的衣服上沾了一层土,很快成了个“泥人”。快天黑时,我再也没有力气举起镢头了,瘫坐在地上盘点自己的劳动成果,沮丧地发现总共才挖得十几根,最粗的跟拇指差不多,细的就没法看了。一斤甘草,药材公司的收购价好像是两毛多,我估计自己一整天挖的都卖不到一块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算起床,浑身散了架似地疼,便黯然中止了这个计划。
同学比我有苦,也会干活。开学了,用卖甘草的钱买到了《红楼梦》。他看过后,就借给我,我一直赖着不想还。毕业后各奔东西,我继续上学,同学去了海南打工,后来在那边娶妻生子。大约五六年前,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多年在外,很是想念家乡,想回老家一趟。我说回来了陪你好好玩几天,一起怀旧。同学最后没有回来,几个月后因突发病去世了。现在这套《红楼梦》还在我的书柜里,我想有一天亲手还给他的孩子,并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后代听。
无论贫富都要买书
到了九十年代,小镇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街上的砖瓦房,被一栋栋楼房取代。我上学时学校马路对面的菜地成了一排一排的门面房,中间是个大市场。唯有新华书店还在那个老旧的巷子里,仿佛时光还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书店鲜有顾客,人人都忙着去赚钱,加上电视机、录像厅、大众舞厅的普及和流行,没有多少人看书了。书店里的书也不多,我隔三差五总要光顾一次。有时候不是为了买书,在那个安静凉爽的大房子里一个人静静地翻会书,觉得也是享受。
现在,我走过书店那条老巷子的心情不一样了。在市里的中专学校上了三年学后,我在小镇有了一份工作,谈不上薪资丰厚,但兜里终于有了买书的钱。单位还给我分了单独的宿舍——一孔窑洞。上班几个月后,我定制了一套连带着书桌的组合书柜,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
我在市里上学期间,读书主要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星期日也常逛书店,还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买得少。有一次,看见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砖头一样厚,装帧也特别漂亮,可定价不菲,16 元多,犹豫了半天没舍得买。那时候母亲在一个乡镇做临时工,月工资只有80 元,一个月要汇多一半给我做生活费。之后每次去书店,先看那本书还在不在了,生怕像以往喜欢的好多书,卖完后再不见了。有一次又翻着那本书纠结,一狠心,咬牙买下,心里总算踏实了。
有段时间,离新华书店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旧书店,店里所有的书五折出售。其实大部分书也不旧,多是无人问津的冷门书,也有一部分微瑕书。我在这里淘到《冬天里的春天》《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抒情诗选》《台湾现代诗拔萃》等,可惜这个书店的书处理得差不多时就关门了。后来,市中心的科技馆前有了个体售卖的书摊,多为封面艳俗的盗版书,有两家品位不错,书是正版,上新书的速度比新华书店还快。我买过贾平凹的散文《报散集》,张爱玲的《私语》。还买过劳伦斯的《查泰利夫人的情人》,估计是盗版,读这本书还有些不好意思,特意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这样我毕业的时候就拥有了一箱子书。加上参加工作后不断地添新书,我的小书柜很快就满了。
我的窑洞宿舍虽然简朴,但有了这一柜子的书,自觉雅致舒心。不久就有人来借书,有一次连隔壁中学的校长也要借刚买的《废都》,我抹不下脸拒绝,在一张明信片的背后用粗笔郑重其事地写下“请勿开口,恕不外借”几个字,贴在书柜的玻璃上。可是,在小镇上认识的几个文友,借书时视此告示是写给别人看的。
工作两年后,我认识了妻子。恋爱的时候就多次很认真地说,结婚以后不论贫富要支持我写作,也不能干涉我买书。妻子答应得很痛快,我逛书店的时候就多了个伴,我选书付钱,那个人常喜滋滋地要提书。我暗自想:这也是个傻子,跟了个穷书生,还把她高兴的。
除了热爱还有什么
1998 年,延安大学给我、倪泓、崔完生、胡同4 人召开了一个名为“延川青年作者作品研讨座谈会”。我们几个人在同一个小镇生活和写作,年龄还都不到三十岁,频频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并已相继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被本地文学圈关注似乎也没什么稀奇,被延安大学关注却是没想到的事情。让人感动的是座谈会不光中文系的老师来了不少,连时任校长也来了。会上,大多数老师对我们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临到结束时,一位青年教师发言说,对于今天这几位基层作者,我觉得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对生活的热爱,一是对文学的热爱。我们几个确实学历都不高,没有上过大学接受系统的学习。不过,有时候也觉得写作要看有没有天赋,否则中文系的那些老师自己为什么不写小说,不写诗歌。年轻气盛,觉得这位老师太藐视人了,在他的眼里我们仅仅在热爱的层面。回去的路上,心情有些沉重,觉得自己尽管读了不少书,和科班出身的还是有差距。不久,我在一本期刊上读到那位老师的小说,确实写得好,技法成熟,比我的小说有深度。如果硬要比,他的成熟里没有我们不经意间的野性蓬勃。冷静下来,我觉得他有资格那样讲,我们的综合素养确实不够。仅靠天赋的写作是走不远的,再说我对自己究竟有没有文学天赋,一直很怀疑。也为没上过大学而有些自卑。
从那年开始,我读书的范围开始扩大。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似乎书越厚,越有分量。实际上,这样急功近利的恶补,收效不大。直到三十岁以后,认真读了《西方哲学史》《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西方美学史》等,回头再看很多书,就觉得相对容易理解了。恶补导致读书有些贪,购书更贪。碰上一本名家的书,如果自己没有就好像吃了亏,读懂读不懂,先请到家里再说。
到今天我都觉得要感激那位大学老师的直言,让我看了很多有意思的书。可惜他后来也不写小说了。
《中东石油史》和美学研究生
其实读书越多,越发现自己无知。就像木心当年的感叹: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延川《山花》前主编,现在央视的资深导演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多年前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戏剧文学,见室友从图书馆借阅《中东石油史》,老师不解,问他怎么看离专业十万八千里的书?室友答,去图书馆发现与专业相关的书过去都读过了。老师大惊,感叹与室友的阅读差距,于是在校两年,读完了学校馆藏的所有中外剧本。很多年以后,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谈卡尔维诺,谈尤瑟纳尔。老师说,我在中戏上学时就都读过了。这回轮到我感叹了。
有一年,我的工作有变动。文化人出身的领导很开明,让我不必坐班,专心在家读书写作。那一年是我过得最充实的一年。除文学作品外,读了许多哲学、历史、美学方面的书。甚至有个想法,把北大陈晓明教授给自己当代文学博士生开的书目全部读完。一年之后,我有了新的工作任务,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读书当然会有困惑,这时候就很想和人交流。生活在小县城,有共同兴趣的人比较少。有一次,工作上要配合某大学一个学美学的研究生搜集资料,我和那个女生在酒店神侃了一中午柏拉图、席勒、福柯、罗兰•巴尔特,害的那女孩不光没休息,还吸了几个小时的二手烟。事后回想起来都难为情,那天就像醉了书一样话题不断。本意是觉得人家专业,想验证有些认知是否正确,后来简直是贩卖浅薄的心得。
还有一次是和一位前辈作家交流。这位前辈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创作水平远远在我之上。那段时间我正好读的是卡尔维诺、安贝托•艾柯、米兰•昆德拉等人的书,觉得老师“典型人物”之类的文学观过于老套,老师自然也不认可我否定传统的观点。两个人在酒店房间辩论到半夜都有些饿了,出去买了泡面吃后继续引经据典想说服对方。到凌晨三点,老师终于困得不行了,语重心长地说,我虽然说服不了你,但对你今后的写作有些担忧。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几年后我发现,囿于一种迷人的理论,对于写作来讲有时候也是危险的事情。
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拒绝读书是一种愚蠢,因为读书而滋生出骄傲与傲慢是一种更大的愚蠢。我的这些荒唐事原本是因为爱读书想和人交流,有时也因为爱读书喜欢给人荐书。但这句话还是警醒了我,因读了几本书而自诩或卖弄,实不可取。
摊大饼还是细品茗
前些年,本市的报纸约我就纪念改革开放的变化写篇稿子。我那篇应景短文的大致意思为:于我而言,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从买不起书到几乎随心所欲地买,从购书不方便到网上尽兴地淘。
网上购书的确便捷,加之搞活动的折扣力度,让我这样随性的人都管不住自己的手。随意购书也带来一个问题,手头老有一些读不完的书。读书也从有目的到随兴趣而读。有天忽而想到,改革开放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城市“摊大饼”式的急速扩张,而我读书也越来越像摊大饼。比方,为写剧本,买本《人间四月天》学习。一读觉得徐志摩这人太有意思了。再买徐的传记读,读的过程中对才女林徽因也感兴趣了,转到读林的诗文和传记。读完发现有林的女儿梁再冰口述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这可能更靠谱,要读。书还没读完,对梁思成的学识很是佩服,他的《中国建筑史》那么有名气,还没读过,要补上。这还没完,后来又看见新出版的《小脚与西服》,作者张帮梅可是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的亲侄孙女,张幼仪八十多岁时回忆往事,可能更客观。要读。
读沈从文也是这样。读他的《湘行书简》,从写给妻子张兆和的那些信,转到《从文自传》。又转到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再转到张兆和的家族《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又读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从对作者的介绍中,发现她的老公竟然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史的重要作品有《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等,我恰好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感兴趣,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版本,这个美国佬写的可能更有意思。读。“饼”就是这样摊大的。
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见识当然会更开阔。问题是人的精力和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世上的好书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退化,我开始反思自己贪婪的“胃口”,就像反思忙碌的人生。与其马不停蹄地一路观花,不如在自己最喜欢的风景前驻足欣赏,浸心品味。我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内心依然纠结,和认识的好些师友比,我那点读书量实在不算什么。也许是愚钝,我感觉自己缺的课依然很多。也许,在广泛阅读的同时,我缺少的是细嚼慢咽的精读和细读。这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识。就比如在文学范围,很多人都说一个写作者应该形成自己的读书谱系,这个谱系确实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实现,同时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既然是谱系,它也不是无边无垠的。实际上,这个谱系更像是一个人自己的文学史。如果你要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就需像苏轼所说“熟读深思子自知”那样反复读了。
为什么喜欢读书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于我而言,读书能让我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读书能让我结识许多有趣的灵魂。这样的旅行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