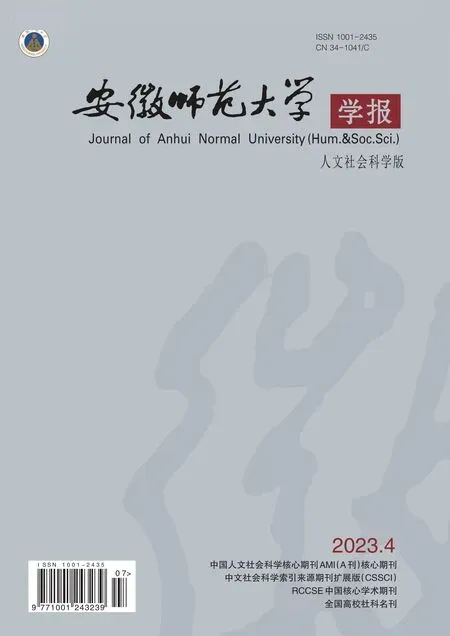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陈博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中国文学的“诗史”传统与杜诗有着密切联系。最早以“诗史”来看杜诗的是唐代士人孟棨,他在《本事诗》中写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①[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其内涵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特指杜甫在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二是通过诗歌记录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三是对所见所历之事进行价值判断。②李科:《“诗史”说本义辩》,《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随着杜诗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诗史”内涵在不同诗人和批评家那里发生了变化,后世“诗史”说逐渐走出杜诗的影响,成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理念和文学阅读传统。①张晖:《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4页。然而,由杜诗而来的以诗记史、内含褒贬的基本创作精神却没有发生变化。“诗史”传统在朝鲜半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高丽诗人李齐贤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一、李齐贤入元西行及其追求真实的诗学观念
李齐贤,字仲思,号益斋、栎翁,是高丽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恭愍王时期曾拜为右丞相,权断征东行省事务,被后学评为“道德之首,文章之宗”②[高丽]李穑:《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益斋先生文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集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册,第448页。。他一生之中多次奉王命使元,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在此期间,他以诗歌形式记录行踪,描写所见所闻,为高丽诗歌创作走出僻滞之习创造了典范,也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朝鲜士人李德懋说:“其诗华艳韶雅,快脱东方僻滞之习。虽在中原,优入虞扬范揭之室……其游历见于诗,若井陉、豫让桥、黄河、蜀道、峨眉、孔明祠堂、函谷关、渑池、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焦山、多景楼、姑苏台、道场山、虎丘寺、漂母墓、涿郡、白沟、邺城、覃怀、王祥碑、崤陵、长安、郑庄公墓、许文贞公墓、关龙逢墓、望思台、则天陵、肃宗陵、邠州、泾州、宝陀窟、月支使者献马,足迹所到皆伟壮,东人之所不及。”③[朝鲜]李德懋:《清脾录》卷三,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7页。
李齐贤能够入元并结识当朝众多文章大家,创作大量纪行诗,与高丽忠宣王王璋是分不开的。王璋的身份极为特殊,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他是第一位具有高丽王室和蒙古贵族混合血统的国王,也是高丽政争中遭受非议较多的一位君主。早在贞元、大德之际,王璋一度以忠宣王身份继承王位,任贤使能,去邪革弊,但不久便遭到政敌的诬陷而被废。被称为前王的王璋因此入元做了十年的宿卫,但因祸得福,他与龙潜时期的元武宗海山、元文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建立了兄弟般的友情。④李齐贤说:“潜谋以公主失爱,诉于中宫,以故召入宿卫者十年。武宗、仁宗龙潜,与王同卧起,昼夜不相离。”《益斋乱稿》卷9上《有元赠敦信明义保节贞亮济美翊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忠宪王世家》,《益斋先生文集》,第562页。这十年来,王璋与再次继位的父亲忠烈王的关系虽然不十分融洽,但却因结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而带来人生的通达。李齐贤记载道,大德十一年(1307),王璋“与丞相达罕等定策,奉仁宗,扫内难,以迎武宗,功为第一,封沈阳王,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驸马都尉,勋上柱国,阶开府仪同三司,宠眷无出右者。仁宗为皇太子,王为太子太师,一时名士姚燧、萧㪺、阎复、洪革、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辈,多所推毂,以备宫官”。⑤[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9上《有元赠敦信明义保节贞亮济美翊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忠宪王世家》,《益斋先生文集》,第562页。得到元廷无上宠眷的王璋,随即开始了对高丽政争的清算,并重新从忠烈王手中夺回政权。至大元年(1308),忠烈王去世,王璋再次以忠宣王身份继承王位。
忠宣王在高丽开展了为时不长的政治改革后,便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上奏元廷将王位传给儿子忠肃王王焘,又以爱侄王暠为世子,自己则退居幕后,在京师构建万卷堂,终日沉浸在佛法礼仪中,自得其乐。李齐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忠宣王的眷顾被召入大都的。据李穑记载,忠宣王说:“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遂于延祐元年(1314)正月召李齐贤至大都。⑥[高丽]李穑:《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益斋先生文集》,第445页。李齐贤的到来,确实为忠宣王在众多文学之士中赢得了足够的面子。《东国诗话汇成》载:
王以前王入元,遂封沈阳王,贵宠用事,开万卷堂。学士阎复、姚燧、赵子昂皆游王门。一日王占一联云:“鸡声恰似门前柳。”诸学士问用事来处,王默然。益斋李文忠公从傍即解曰:“吾东人有‘屋头初日金鸡鸣,恰似垂杨袅袅长’,以鸡声之软比柳条之轻纤。我殿下之句用是意也。且韩愈《琴》诗曰:‘浮云柳絮无根蒂。’则古人之于声音亦有以柳絮比之者矣。”满座称叹。①[朝鲜]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第六卷,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4册,第3042页。李齐贤的妙语连珠不仅化解了忠宣王的尴尬,也成为中韩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佳话。由此带来的文学互动以及君臣关系的加深,使李齐贤在东亚文化交汇中,成为元丽友好的重要代表。延祐三年(1316),李齐贤奉使降香峨眉山,而有西蜀之行。在西行之际,中原士大夫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人均以诗送别。作为感谢,李齐贤一一奉和,先后创作了《奉和元复初学士赠别》《张希孟侍郎见示江湖长短句一编以诗奉谢》以及寄呈赵孟頫的《二陵早发》等诗,以示友情的珍贵。
正如李穑所说:“公周旋其间,学益进。”②[高丽]李穑:《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益斋先生文集》,第445页。在与中原士大夫不断切磋中,李齐贤确实提高了自己的学识修养。尤其是他在西行途中,高调议论唐人之诗,对诗歌创作的真实性问题发表议论。他在到达峨眉山时写道:
延祐丙辰,予奉使祠峨眉山,道赵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踰大散关,过褒城驿,登栈道,入剑门,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谓峨眉山者,因记李谪仙《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之句,太白在咸阳西南,峨眉则在成都东北,可谓悬隔。然而自咸阳数千里至成都,或东或西不一其行。又自成都东行北转六百余里,然后至峨眉。虽山川道路之迂度,其势二山不甚相远,人迹固不相及,鸟道则可以横绝云耳。白乐天《长恨歌》云:“黄尘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此言明皇幸成都时所历也。如其所云,峨眉当在剑门成都之间,而今乃不然。后得《诗话总龟》,见古人已有此论,盖乐天未尝到蜀中也。③[高丽]李齐贤:《栎翁稗说》,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139-140页。
李齐贤通过游历峨眉山的实践活动,亲自验证比较李白《蜀道难》和白居易《长恨歌》对峨眉景致的描写,指出白居易在创作中有借用他人典故之嫌,根本没有亲临蜀地。这种求实精神,亦体现在他对杜诗的理解上,他说:
杜少陵有“地偏江动蜀,天远树浮秦”之句,予曾游秦蜀,蜀地西高东卑,江水出岷山,经成都南东走三峡,波光山影荡摇上下。秦中千里地平如掌,由长安城南以望,三面绿树童童,其下野色接天,若浮在巨浸然。方知此句少陵为秦蜀传神,而妙处正在阿堵中也。④[高丽]李齐贤:《栎翁稗说》,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143页。
道听途说与亲自体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知,二者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就有“隔与不隔”的差别。李齐贤借着对唐诗的评论,直接表达追求真实的诗学主张,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是在鼓励诗人要走出书斋,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扩大诗境,呈现浑然天成之美。朝鲜士人朴趾源曾专门梳理李齐贤纪行诗中的代表性诗句,如《思归》诗云:“穷秋雨锁青神树,落日云横白帝城。”《二陵早发》诗云:“云迷柱史烧丹灶,雪压文王避雨陵。”《舟行峨嵋》诗云:“雨催寒犊归渔店,波送轻鸥近客舟。”《多景楼》诗云:“风铎夜喧潮入浦,烟蓑暝立雨侵楼。”《函谷关》诗云:“土囊约住黄河北,地轴句连白日西。”并评论道:“我东诗人用事,率皆借用,而真能目睹足踏者,惟益斋一人。”⑤[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另一方面他又是在为“以诗记史”张目。李齐贤有着长期在高丽艺文春秋馆从事史书编纂的经历,对高丽史料尤为熟稔,言必有据、实事求是是其重要的史学观念。他曾以《王氏宗族记》《圣源录》为依据,认真考订金宽毅《编年通录》有关高丽世系起源的诸种错讹,这一点得到了朝鲜史官的高度肯定。①《高丽世系》说:“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蓄文书。’其后闵渍撰《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圣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第1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由此可见,追求真实是融贯在李齐贤史学与文学主张之中的。诗歌的真实性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突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描写,这与史家治史的态度是相通的。“以诗记史”坚持史家精神,采用诗性语言,客观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后人可以通过诗歌作品认识诗人及其时代。可以说,李齐贤追求真实的诗学观念,为其“以诗记史”的书写方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第二次西行与李齐贤的“诗史”之作
在同僚崔瀣写给李齐贤《后西征录》的序言中,我们得知李齐贤延祐三年(1316)的西蜀之行曾编辑成《西征录》,《后西征录》则指李齐贤至治末年第二次西行所写的纪行诗歌总集。李齐贤的第二次西行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这是形成此期纪行诗创作风格的重要语境。
按照忠宣王对高丽的人事安排,他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复位五年之后,先将王位传给嫡子王焘,为忠肃王,又以侄子王暠为世子,后将沈王王位传给王暠,自称太尉王,虽位居幕后,但仍以钧旨、晓谕等形式实施垂帘听政,对忠肃王朝政过多干预。如忠肃王元年(1314),上王忠宣以辛蒇为选部直郎、安珪为散郎,委以铨注,并晓谕忠肃王说:“王专断国政,兼崇佛法,戒诸仓库吏,毋以幼主之命,耗费财用。”②[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一》,第3册,第1089页。又,忠肃王五年(1318),忠肃王以上王忠宣的钧旨对张公允、张允和等人实施了囚禁与流放。③[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一》,第3册,第1096页。延祐七年(1320)三月,在仁宗刚刚崩逝不久,元英宗即位之际,忠宣王承皇太后懿旨,对本国宦官伯颜秃古思等人强占他人的田产进行了没收,并归还本主。④[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5《忠肃王二》,第3册,第1101页。这成为忠宣王罹难的开始。同年四月,忠宣王即向元英宗请命降香江南,离开大都。李齐贤写道:“延祐己未,请降香,南游江浙,至宝陁山,盖知时事将变,冀以避患。”⑤[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9上《有元赠敦信明义保节贞亮济美翊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忠宪王世家》,《益斋先生文集》,563页。忠宣王预知“时事将变”,所指就是伯颜秃古思等人的报复。忠宣王与伯颜秃古思的矛盾由来已久,对于这个家奴出身的高丽宦官,忠宣王从侍奉元仁宗开始就没有对他留下好的印象。二人矛盾的激化正是忠宣王在失去政治靠山之际,对伯颜秃古思发起的没收田产事件。伯颜秃古思通过行贿蒙古贵族八吉思,使其在元英宗面前构陷忠宣王,不仅为自己重新夺回田产,更陷忠宣王于危难之际。⑥[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22《任伯颜秃古思传》,第9册,第3712页。跟随忠宣王一并降香江南的侍从和官员们,在六月到达金山寺后,目睹了上王被抓回的场景,皆知是伯颜秃古思从中作祟,为避免累及自身而纷纷逃窜,唯有朴景亮、李连松等人为忠宣王尽忠而死。⑦[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24《朴景亮传》,第9册,第3752页。
《高丽史》载:“九月,王还至大都,帝命中书省护送本国安置。王迟留顾望,不即发。十月,帝下王于刑部,继而祝发,置之石佛寺。十二月戊申,帝流王于吐蕃撒思吉之地。”⑧[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4《忠宣王二》,第3册,第1081页。元英宗对忠宣王的处置发生了两次重要变化,他先是改变将忠宣王护送回国的安置,将其置于刑部审查并削发为僧,发配到位于西蜀的石佛寺;不久,他再次决定将忠宣王流放到西藏地区。由于李齐贤在延祐六年(1319)第一次陪同忠宣王降香江南后随即返回高丽,未能亲历第二次江南之行的骇人事件,他于延祐七年(1320)冬天返回大都,在路过黄土店时听说了此事,感到悲愤不已,遂创作纪行诗《黄土店》,以为忠宣王鸣不平。诗云:
世事悠悠不忍闻,荒桥立马忽忘言。几时白日明心曲,是处青山隔泪痕。烧栈子房宁负信,翳桑灵辄早知恩。伤心无术身生翼,飞到云宵一叫阍。
咄咄书空但坐愁,式微何处是菟裘。十年艰险鱼千里,万古升沉貉一丘。白日西飞魂正断,碧江东注泪先流。满门簪履无鸡狗,饱德如吾死合羞。
寸肠冰炭乱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谁谓鳣鲸困蝼蚁,可怜虮虱诉虾蟇。才微杜渐颜宜赭,责重扶颠发已华。万古金縢遗册在,未容群叔误周家。①[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2《黄土店》,《益斋先生文集》,第491页。
朝鲜诗论家徐居正特意将这组诗歌与杜诗进行比较,对诗中蕴含的忧国忧民的忠君思想给予充分肯定,他明确指出这些诗篇,“忠诚愤激,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矣”②[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173页。,评价还是很高的。这也说明,李齐贤寓忠愤于其中的纪行之作较为符合杜诗的“诗史”精神。与杜诗相似,这组诗集中关注了本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寄寓强烈的人事感怀。所谓“寸肠冰炭乱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白日西飞魂正断,碧江东注泪先流”,写出诗人心如刀割般的伤痛。而“谁谓鳣鲸困蝼蚁,可怜虮虱诉虾蟇”,又将奸党得势,互相攻诘的现实呈现于前。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李齐贤并没有选择逃避或归隐,而是毅然而上,坚决维护国家纲常,表现出士人应有的责任担当。他继而在长诗《明夷行》中对忠宣王的作为进行反思,其诗云:
杨朱曾哭路多歧,鲁叟亦叹麟非时。荒鸡未鸣夜何其,丧狗独立迷所之。忆昔吾君初入相,两扶红日上咸池。功成不退古所诫,坐令西伯玩明夷。式微胡为寓旄丘,已老曷不营菟裘。古闻骖乘致芒背,今悟曲突贤焦头。唐虞揖让冠千古,有城底事名尧囚。沧浪水清耳不洗,羞向尘编对许由。③[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2《明夷行》,《益斋先生文集》,第491页。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为日入地中之象,象征光明受到损伤。《卦辞》曰:“利艰贞。”郑玄解释说:“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意为君子在明夷之际,要自艰守正,不能忘记艰难,轻易用事。④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彖辞》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⑤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208页。这里提到了周文王和箕子两个历史人物,用以阐释“明夷”的卦辞。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城达七年之久,文王在此据伏羲八卦推演而作《周易》。文王于蒙难之际,凭借内在的文明柔顺之德渡过难关,谓文王之“明夷”。箕子为商纣王的叔父,因不愿见到殷商大业被纣王毁于一旦而披发佯狂,隐志自悲,纣王遂将其囚禁并贬为奴隶,此谓箕子之“明夷”。大体而言,“明夷”卦的意味在于,君子罹难时,要学会运用策略与方法来坚守内在的精诚之志,以不失君子之德。
李齐贤所谓“明夷”饱含着自己对高丽的一种政治判断。他深知忠宣王对于本土稳定的重要意义,自忠肃王即位以来,忠宣王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没有减弱,这导致忠肃王的权威很难树立起来。《高丽史》载:“上王之留元也,国家政事、仓库出纳,一委亲近,虽有过举,然仓库盈羡,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后,宦官左右谋改忠宣之政,放逐旧臣,仓库俱竭。”⑥[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5《忠肃王二》,第3册,第1105页。忠肃王执政八年之际,高丽仍称“忠宣之政”,可见忠宣王权威之重。由此,忠宣王的西谪意味着高丽政权出现真空,心怀不轨之人便撺掇沈王王暠与忠肃王王焘陷入王权争夺的泥潭,即忠宣王所谓的“阋墙之变”。①《高丽史》载:“(忠肃王)十年,泰定帝立。明年,敕王还国,复赐国王印章。忠宣戒谕国人曰:‘从臣引曹交构国王及沈王,以致阋墙之变。其听奸臣诳诱请立沈王者,予已谕国王,毋念旧恶,一皆原宥,其悉知之。’”《高丽史》卷91《宗室二》,第7册,第2850页。李齐贤在诗中反思了忠宣王因过多干预忠肃王朝政带来的政治困境,即“功成不退古所诫,坐令西伯玩明夷”,有责备君王之意,但他也承认忠宣王被流放确属政敌构陷,遂使高丽陷入“明夷”境地。而“明夷”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士人身陷此境提供了应对之策,即士人应该高尚其志,坚守君子之德,不去做随波逐流、各谋私利的事情。不能不说,李齐贤的纪行诗蕴含着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
李齐贤的政治判断与忠宣王的顾虑不谋而合。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到达吐蕃独知里的忠宣王在写给崔有渰、许有全、赵简等人的书信中说道:“予以命数之奇,罹兹忧患,孑尔一身,跋涉万五千里,向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国王年少无知,向之惮我群小辈,必幸我如此,肆其奸巧,焉知不间我父子乎。幸诸国老同心协力,敷奏于帝,俾予速还。”②[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5《忠肃王二》,第3册,第1106页。为此,许有全、闵渍等人入元为忠宣王请愿,特别是许有全以81岁高龄,不顾病危的妻子,永诀而去。由于沈王之党的阻拦,他们在元滞留了半年也没有达到目的。③[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09《许有全传》,第8册,第3325页。
沈王之党,顾名思义是攀附沈王王暠的人。作为忠宣王宠爱有加的侄子,王暠无论在高丽还是在元廷,都享有较高的声望,他不仅顺利继承沈王王位,还迎娶了一位元朝公主,并得到当朝皇帝元英宗的宠幸。在这种情况下,王暠开始笼络人心,觊觎王位,聚集在他身边的曹頔、蔡河中、柳清臣、吴潜、权汉功等人不断构陷忠肃王,为己谋私,制造混乱。李齐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忠肃王入朝,沈府用事者,煽起阋墙之祸,谗口交腾,举无全人。”④[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7《有元高丽国匡靖大夫都佥议参理上护军春轩先生崔良敬公墓志铭》,《益斋先生文集》,第545页。先是王暠在英宗面前诬陷忠肃王手裂圣旨,致使忠肃王入朝被扣,没收国王印。⑤[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91《宗室二》,第7册,第2848页。后有权汉功等人汇集百官于慈云寺,上书中书省,请立王暠。⑥[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25《权汉功传》,第10册,第3795页。又有蔡河中等人携元使假传圣旨,妄言元帝以王暠为国王。⑦[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25《蔡河中传》,第10册,第3796页。在谋立无果的情况下,柳清臣、吴潜等人又上书请立省本土,比同内地。⑧[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25《柳清臣传》,第10册,第3791页。这就是忠宣王西谪期间,高丽遭际的阋墙之变与立省之争的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高丽士人为维护本土利益不断奔波、四处求援,他们都清楚一点,只要忠宣王平安归来,朝廷局势就能稳定。至治三年(1323)正月,在闵渍、许有全等人共同努力下,李齐贤、崔诚之等人向当朝右丞相拜住写信求助,请求召还忠宣王。二月,元英宗同意拜住所奏,将忠宣王迁至离大都较近的朵思麻之地。⑨[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5《忠肃王二》,第3册,第1109页。四月,李齐贤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大都,不辞艰辛,前往临洮远谒忠宣王,开启了他的第二次西行。
出发前,他用诗歌表达了忠孝难以两全的苦衷,其诗云:“主恩曾未答丘山,万里驱驰敢道难……唯念慈亲鬓如雪,数行清泪洒征鞍。”⑩[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2《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发京师》,《益斋先生文集》,第492页。根据李齐贤的纪行诗,我们得知他此行途经涿郡、白沟、相州、邺城、端午、覃怀、孟津、洛阳、新安、函谷关、华州、长安、邠州、泾州等地,穿越了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广大地区。他曾在河南新安驿站目睹了蕃僧杀害站吏的情形,足以见出路途的凶险难测。新安之地,扼函关古道,西通长安,与渑池县为邻,自古为中原要塞,军事重地。李齐贤在延祐三年(1316)“奉使西蜀”归来途中,过函谷关、渑池、新安等地,艰难跋涉于“崤函”古道中。如今时过境迁,故道重行,应该别是一番滋味。他在纪行诗中写道:“车马函关道,风尘季子裘。辙环天下半,心逐水东流。万事唯呼酒,千山独倚楼。青云有知己,未用叹悠悠。”又云:“倦客重游秦树老,佳人一去陇云赊。愁听杜叟三年笛,怅望张侯万里槎。梦里家山空蕙帐,酒阑檐雨落灯花。宦情已似秋云薄,胸次唯余一寸霞。”①[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2《题长安逆旅》其一、二,《益斋先生文集》,第494、495页。经行山势险峻、路途坎坷的函关古道,李齐贤切身感受到远在吐蕃的忠宣王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主分忧的愁苦使他对波诡云谲的官场产生了厌恶之情,即使如此,他对忠宣王的忠诚依旧没有改变。他继而毫不隐晦地对时政加以批评,将其忧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云: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具锦谁将委豺虎(谓伯颜豆古),干戈无奈到参商(谓曹頔使兄弟不和)。扶持自有宗祧力,会见松都业更昌。
早信忠诚可动天,孰云仁圣竟容奸。鸡竿曙色开旸谷,凤阙春光到雪山。谶雨池蛙喧欲鬪(谓奸党徼功者),唳云皋鹤倦思还(谓闵渍、许有全两老,以忠宣王事,上书陈乞,而有沮之者。二老不能久留,将归国也)。区区吴薛何为者,自鼓咙胡彻帝关。②[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2《题长安逆旅》其三、四,《益斋先生文集》,第495页。李齐贤在诗中以夹注的方式,对制造混乱的奸党进行点名批评,其所谓伯颜豆古,即利用蒙古贵族八思吉构陷忠宣王,使其遭受西谪之苦的高丽宦官伯颜秃古思,他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李齐贤喻之为豺狼虎豹。曹頔累仕忠烈、忠宣、忠肃三朝,权倾中外,后与蔡河中等人谄事沈王王暠,挑拨宗室关系。李齐贤点名批评曹頔,借指沈王之党利用忠宣王之“明夷”,煽起阋墙之变。“参商”指的是星空中的参星与商星,二星象此出彼没,不能共见于星空,隐喻为不和睦。他在第二首诗中继续批评沈王之党各怀私立的争斗,将他们喻成池中喧闹的虫蛙,而对闵渍、许有全等老臣的上书未果感到悲愤不已。尽管李齐贤在诗中也责备君王“容奸”之意,但他坚信,奸党之力始终无法撼动宗室的百年基业。
随着元英宗的突然崩逝和泰定即位后大赦天下,忠宣王得以召还归国,忠肃王也被复赐国王拿回执政权,历时三年之久的“明夷”局面宣告结束。这一政治事件以伯颜秃古思与忠宣王的矛盾为起因,牵涉到元丽复杂政治势力的持续纷争,是元丽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受此影响,身为近臣的李齐贤不仅对忠宣王的遭际以及高丽政争给予了极大的关切,还不断为解救忠宣王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并开启第二次西行,远谒忠宣王于临洮。他创作的纪行诗,以亲历者身份观察、记录事件原委,以“诗史”之笔,真实反映时代之变,饱含着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为此,崔瀣评论道:“词义沉玩,本乎忠义,充中遇物而发,故势有不得不然者,其媱言嫚语,盖无一句。”③[高丽]崔瀣:《拙稿千百》卷1《李益斋后西征录序》,第402页。李穑亦说:“忠宣王被谮,出西蕃。明年,公往谒,讴吟道中,忠愤蔼然。”④[高丽]李穑:《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益斋先生文集》,第445页。可谓知音。
三、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李齐贤自入元以来,主要经历了两次西行,其纪行之作被辑为《西征录》和《后西征录》。在这些纪行诗中,有很多咏史之作,从其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评价来看,李齐贤的“诗史”意识还包含着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李齐贤在《明夷行》《题长安逆旅》等纪行诗中已经毫不隐晦地批评了忠宣王的不足。他在写给元郎中的书信中也不忌讳这一点,其言:“老沈王即公主子,而世祖亲甥也。自世祖之时,以至于盛代,历仕五朝,既亲且旧。但以功成不退,变生所忽,毁形易服,远窜土蕃之地。”⑤[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6《同崔松坡赠元郎中书》,《益斋先生文集》,第520页。客观上讲,忠宣王的西谪确实是遭到了伯颜秃古思的构陷,但从主观上看,忠宣王退位后没有放松对权利的控制,致使忠肃王无法建立权威,是导致奸党攀附王暠,以谋私利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李齐贤所说的“功成不退”。《高丽史》中这样写道,忠宣王“乃逊位于子焘,又以侄暠为世子。父子兄弟卒构猜嫌,其祸至于数世而未弭。贻谋之不臧如此,吐蕃之窜,非不幸也”。①[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35《忠宣王二》,第3册,第1081页。“贻谋不臧”与李齐贤所说的“功成不退”相类似,都有责备君王之意,并以此反思整个事件的主观因素。
在第一次西行途中,李齐贤途经比干墓,撰写了关于比干的两首咏史诗,他在诗序中对历史上所谓“贤明”之君的行为进行反思,其言曰:
墓在卫州北十许里,盖周武王所封。而唐太宗贞观中,道过其地,自为文以祭。其石刻剥落,亦可识一二焉。夫二君之眷眷于异代之臣者,岂非哀其忠愍其死乎?而武王忽伯夷于胜殷之后,太宗疑魏征于征辽之日者,何耶?因作此诗,亦《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也。②[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1《比干墓》,《益斋先生文集》,第485页。
比干是王室重臣,商朝末年,以忠言直谏得罪商纣王,而遭杀身之祸,其忠义之行深受后世敬仰。周武王灭商之后,在比干墓前立木为识,以表达对前朝忠直之臣的尊敬。后世的唐太宗也以撰文立碑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心情。让李齐贤不解的地方在于,这两位历史上的明君,为什么如此眷顾已死的忠贞之士,却容忍不了当世的贤者。归根结底,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史家不应有所回避。李齐贤在诗中评论道:
周王封墓礼殷臣,为惜忠言见杀身。
何事华阳归马后,蒲轮不谢采薇人。
从来忿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
哿矣亲祠比干墓,胡然却仆魏征碑。③[高丽]李齐贤:《益斋乱稿》卷1《比干墓》,《益斋先生文集》,第485页。
显然,相较于比干受到的礼遇,李齐贤有充分理由质疑周武王对待殷商隐士的态度,并批评唐太宗因一时愤怒而推倒忠臣魏征之碑的行为。这种在真实空间中抚今追昔的纪行咏史之作,是李齐贤咏史诗的独到之处,同时也彰显着他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
同样,在第二次西行途中,他经过陕西关中的武则天陵墓时,创作了长篇咏史诗《则天陵》,诗序中对欧阳修的历史观进行了批评,这篇序文亦保存在《栎翁稗说》中,并交代了写作经过,兹引述如下:
至治癸亥,予将如临洮,道过乾州,唐武后墓在皇华驿西北,俗谓之阿婆陵。予留诗一篇,其序云:“欧阳永叔列武后《唐纪》之中,盖袭迁、固之误,而益失之。吕氏虽制天下,犹名婴儿以示有汉。若武后则抑李崇武,革唐称周,立宗社定年号,凶逆至矣。当举正之,以示万世,而反尊之乎?谓之《唐纪》而书周年可乎?或曰:‘纪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所以使条纲不紊也。如子之说,中宗既废之后,将阙其年而不书,天下之事将安所系乎?’曰:‘鲁昭公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尝不书昭公之年。房陵之废,与此奚异?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其诗略曰:“欧公信名儒,笔削未免失。那将周余分,黩我唐日月。”后阅晦庵《感遇》诗“如何欧阳子,秉笔迷至公”之一篇,拊卷自叹。孰谓后生陋学?其议论有不谬于朱子耶!④[高丽]李齐贤:《栎翁稗说》,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140页。《则天陵》全诗的重点在于批评武则天不守臣道,以周代唐的窃国行径,并对欧阳修这样的大儒将武则天列入《唐纪》表示不满。实际上,是否将武则天放入《本纪》中,在唐代已有争论,德宗朝的沈既济曾撰写过一篇名为《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的奏疏,对吴兢在修国史时将武则天纳入帝王本纪表示不满,主张应该将武则天列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其主要依据是《春秋》之义。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49《沈传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36页。到宋代欧阳修重修唐史,对武则天事迹选用了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延续前朝修史传统列武则天于本纪之中;二是又为其单独列传,附于《后妃传》“高宗废后王氏”之下,其依据也是《春秋》之义。在欧阳修看来,司马迁、班固对《高后纪》的处理,偶合《春秋》之法,是唐人修史取法的主要依据。②[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页。因此,遵循前朝体例重修唐史并不违背《春秋》之义。但欧阳修在材料使用上,表现出前褒后贬的倾向,有意在《后妃传》中对武则天的负面形象进行揭露,以此体现《春秋》“著其大恶而不隐”的笔法要义。即使如此,他的修史之法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宋人范祖禹、陈振孙、朱熹等人均不同意将武则天列入本纪。
李齐贤未必对争论的始末有所了解,但从儒家经典文本《春秋》出发,他对欧阳修的折衷处理方式并不满意。他认为,欧阳修取法的源头上就存在错误,司马迁、班固对吕后事迹的处理本身就不恰当,欧阳修据此将武则天列入本纪,就更加荒谬。况且,吕后保存汉朝天下的做法与武则天以周代唐的做法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有篡逆之嫌,应该举而正之,垂戒后世。他进一步指出,修史应该遵循《春秋》之法,不能因为臣子悖逆而不使用本朝纪年,欧阳修重修唐史以周纪年,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李齐贤对史实客观性、原则性的把握,来自《春秋》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流露着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这一点让他与南宋大儒朱熹的观点不谋而合。
四、结 语
总而言之,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大都,亲身经历了忠宣王复位之后遭遇“明夷”的始终,对高丽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内部斗争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室的忠诚和对奸党乱国的愤懑,显示着这位高丽大儒可贵的君子人格。他先后多次游历中国内地,创作了一大批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这些诗歌创作因不同的历史境遇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倾向,总体看来,李齐贤的纪行诗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影响,在用诗歌记录行踪的同时,有意融入对时政的关注和对历史的评价。在第二次西行途中,李齐贤对忠宣王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愤慨,诗中流露出的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使评论家将其与杜诗相提并论。与此同时,李齐贤在其纪行诗中还创作了系列咏史之作,他对历史把握的基本原则来源于《春秋》,被崔瀣评为“第一等议论”。也可以说,杜诗精神和《春秋》史学观念是李齐贤纪行诗“诗史”意识的两大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