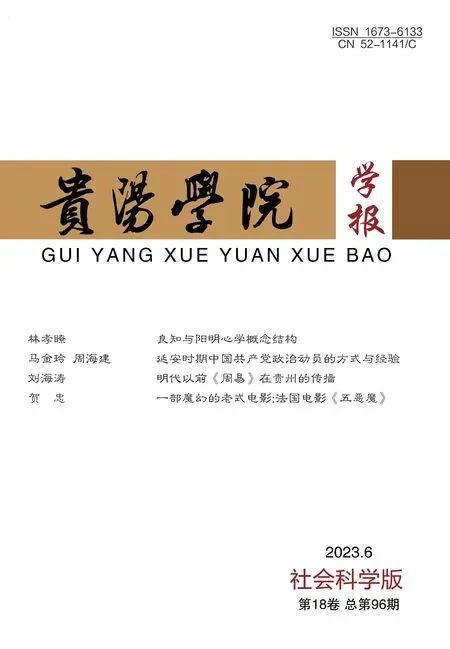明代以前《周易》在贵州的传播
刘海涛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周易》是在中原地区产生的典籍,其自身即经历了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历程。《易经》是指六十四卦卦象和卦辞、爻辞部分,大致成书在西周初年。《易传》则是战国以来系统解释《易经》的著作,共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易纬·乾凿度》和东汉的经师称此十篇为“十翼”,“翼”是辅助之意,表示用来解释《易经》的。《易传》大致成书在战国后期[1]45-59。《周易》在贵州传播,必然是在贵州与中原的交往与互动中完成的。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周易》传入贵州的确切时间以及明以前在贵州流传的具体情形均已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零散的相关文献资料中找寻蛛丝马迹,作一粗线条的勾勒。
一、春秋时期与《周易》的接触
最早提及贵州与中原交往的,是《管子》一书。《管子·小匡》在记叙葵丘之会的情形时,引用了齐桓公的一段话:“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2]425-426葵丘之会发生在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是齐桓公会盟诸侯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的一次会盟。在这段文字中,齐桓公讲到自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包括牂牁在内的各国莫不宾服。如此说来,贵州与中原的交往当在葵丘会盟前。然而,《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但并非管子所作,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一书中通过将《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相比较,发现“《管子·小匡》篇中与《国语·齐语》同者甚多”,由此“知其在《齐语》后”,并认定《管子·小匡》是汉初人所作[3]38-44。汉初人之作是否可以证明春秋时贵州地区即有牂牁古国,且牂牁古国与中原有交往,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小匡》篇是“西汉人的追述,旨在为汉王朝统治者向外拓展张本,不尽可信,不能以此为据论证春秋时即有牂牁”[4]10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托古人之名著书自古有之,内容并非都不可信:“《管子》既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总汇’,自然保存了这一时期的资料,即令《小匡》篇为西汉人所作,至少说明在汉代人的心目中确有牂牁。《小匡》篇所记齐桓公会盟之事,虽有某些事属传闻,但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正如《华阳国志·南中记》关于竹王传说和庄蹻入滇的记述一样”[4]108。虽然牂牁古国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但汉、晋许多著作中都提及“牂牁”“牂牁江”,这也说明“牂牁”之名早已有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以“牂牁”命名设郡,也可视为对历史的一种记忆。
本文所要考虑的是,如果牂牁古国真实存在且与中原有交往,那么是否有机会接触到《周易》?接触到的《周易》是什么样的?古有“三易”之说,即《周礼·春官宗伯》所言的《连山》《归藏》《周易》。此“三易”均是周王室用来占筮之书,由专职的周史、卜者、筮者掌管使用,其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周王室内部。西周未期,随着王室的衰落,包括《周易》在内的大量典籍开始流向各诸侯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其(敬仲)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有学者推测“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这件事大致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也说明至迟在春秋前期,已经有《周易》的书面文本在诸侯国间传播[5]。《周易》在诸侯国之间传播,也可以在《左传》《国语》中找到大量佐证[6]。葵丘之会发生在鲁僖公九年,而《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以及闵公元年、二年有关《周易》的记载均早于鲁僖公九年,这也说明牂牁古国与中原的交往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有可能接触到《周易》,而此时在诸侯国之间传播的《周易》文本应该是六十四卦卦象和卦辞、爻辞组成的《易经》,是仅仅作为卜筮之书而存在的。
二、战国时期《周易》的传入
三、汉代《周易》在贵州的传播
汉代,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南的控制,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拜唐蒙为郎中将通夜郎,率兵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而入,喻以德威,约国置吏,夜郎、且兰及旁小邑皆归附于汉,以其地属犍为郡。与此同时,“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后又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且兰、伐夜郎,设立牂牁郡,共领十七县。牂牁郡设立后,汉武帝实施“募豪民田南夷”的政策,招募“三蜀”豪族大姓,连同其依附的农民,一同迁入进行垦殖。大量巴蜀人士的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对稳定西南局势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巴蜀文化带入贵州,并为贵州易学的发展作了人才的储备。
汉代西南地区巴蜀经学已经非常繁荣,这得益于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宣化。《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十余人,亲自饬励,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弟子,为除更徭役。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宫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武帝时,依仿文翁的作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犍为郡与巴蜀毗邻,得风气之先,经学也首先繁荣起来,其代表人物舍人就是汉代第一个为《尔雅》作注的犍为郡文学卒史[9]。《尔雅》是一部以释义为主的词典,其成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多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而且,汇编也不是一次而成,而是逐步完善”[10],按照学术界较公认的说法,《尔雅》在战国时期即初具规模,在汉代续有增补[11]。然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尔雅》中的有些释义已经非常难懂,且传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讹误、脱漏的情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需要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五经之训诂’的《尔雅》亟需有人进行正定文字、补充注释的工作,以便其在注经和阅读古籍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于是犍为文学《尔雅注》应运而生了”[12]。对于这部开风气的《尔雅注》,学术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清代马国翰在《尔雅犍为文学注自序》中说:“舍人在汉武帝时释经之最古者,本多异字,尤可与后改者参校而得《尔雅》之初义。”黄侃先生也说:“所存盖虽零文支义,皆可葆珍,探讨《尔雅》者,究不能不首先及于此焉。”其实,舍人的重要贡献并不仅仅是在《尔雅》学上,更在于其对贵州经学的开创上,郑珍在道光《遵义府志·人物志》中即言道:“当孝武通西南夷,初置犍为,继置牂牁、汶山诸郡。其时榛榛狉狉,风教睢盱。文学以郡人膺学史选,诣阙上书,即挺生古所未臣之地,而即注古所未训之经。其通贯百家,学究天人,与相如、张叔辈上下驰骋,同辟一代绝诣。淑文翁之雅化,导道真之北学,南中若奠先师,断推文学鼻祖。”[13]1255郑珍讲舍人“通贯百家”,由此也可见舍人涉猎之广,而这得益于文翁将“七经”引入蜀郡,《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记载:“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14]《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亦记载:“(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5]所谓的七经,舒大纲认为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加上《论语》《孝经》,而且“‘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16]。舍人注解“释六艺之言”的《尔雅》一书,必然要求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非常精通,由此也可想见易学在犍为郡讲授的情形。
继舍人而起的是毋敛人尹珍。对于尹珍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华阳国志·南中记》中:“自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17]260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17]260此段文字虽然将尹珍生活的年代误记成“明章之世”,“毋敛”是何地也指向不明,但非常明确地记载了尹珍学习的内容,所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在纠正了《华阳国志·南中记》中的错误后,直接指出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的事实:“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8]2845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句包涵着丰富信息量的话却被学术界忽略了,其根源则在于后世对许慎的误读。史籍对许慎的生平事迹的记载非常少,《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仅有短短的85个字:“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18]2588文字虽短,但可知许慎当时是以经学闻名,其最重要的著作即是《五经异义》。经学从诞生之日起即面临着今古文之争,从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到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古文经学渐渐在学术上超越今文经学。许慎“从(贾)逵受古学”,继承了贾逵“结今文兼容并蓄”的观点,并以私人论经的方式撰写《五经异义》,从而使汉代古文经学在学术上的优势得以确立,东汉大儒郑玄则继承了许慎的思想,最终完成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由此也可见许慎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许慎著《五经异义》,必然是精通易学的,而且是对孟喜、京房的今文《易》以及费氏的古文《易》均有深入的研究。其《说文解字》中也有大量引自《周易》的例论,据学者统计,“《说文》全书引《易》作书证的(包括注音读音中引《易》)共有八十处”[20]。除了向许慎学习五经外,尹珍还向应奉学习图纬。图纬即是谶纬之说,谶纬二字本各有含义,“谶为一种记载有征验的预言的书,且其义隐微,非细加探求不能明了。当然,这种预言被认为是发自上帝,是符合天意的,故谶又被叫做‘符’或‘符命’。后来,人们为显示谶书的特殊性,就把它染上绿色,所以又称为‘篆’。谶书中往往有图有文,所以又被称为‘图篆’‘图谶’,或简称为‘图书’。”[21]纬与经相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的典籍才可称为“经”,阐释儒经义理的书便被称为“纬书”。西汉盛行以阴阳灾异说经,所以纬书皆以阴阳灾异来穿凿经文,后来又发展到以谶解经,至西汉末年,图谶之说大盛,谶与纬合而为一,故称为谶纬。谶纬之学与《周易》有着非常密切有关系[22],汉宣帝时,孟喜言其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异之书”,元帝时京房以《易经》的卦爻和每日的气象变化相结合,从中推衍吉凶。尹珍向应奉学习图纬,必然要有较深的易学素养为基础。所以尹珍从许慎学五经,从应奉学习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其学习与传授的科目,应包括《周易》以及汉代诸家之《易》。
然而,随着汉代经学的衰微以及宋学的兴起,《五经异义》这部给许慎带来巨大声誉的著作在宋代即已亡佚,许慎经学家的身份也渐渐为世人所忘,取而代之的是原本为“通经”之用的工具书——《说文解字》流传至今并使许慎获得“文宗字祖”的称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术界在解读尹珍“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时,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五经”两字的分量,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尹珍在贵州易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四、魏晋到宋元《周易》在贵州的传播
自魏晋历唐、宋以至于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多采取羁縻政策,但仍有大量土官、流官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他们在其所任之地兴学举材,不断推进儒家经典在贵州的传播,如晋愍帝时成主李雄“虚己好贤,随材授任,……刑政宽简,狱无滞囚,兴学校,置史官”(《华阳国志·南中记》)。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杨端割据播州,形成世袭土司政权,其后世子孙中亦有非常重视文化的教育,如杨氏八世孙杨光荣“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闻四方士有贤者,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13]1136;杨氏十二世孙杨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13]1137;十三世孙杨粲“建学养士”[13]1138;十四世孙杨价“好学,善属文”[13]1138。此种重学之风一直延续至元代,播州十七世孙杨汉英“为政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喜读濂洛书,为诗文典尚体要,著有《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卷”[13]1449。杨汉英之妻田氏“亦善读书,人以为难能”。正是由于杨氏家族对儒学的尊崇,播州境内儒学非常兴盛,《大元一统志》卷十记载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即可说明这一问题。五代天成三年(928年),后唐明宗以李承约为黔南节度使,李承约到任后,“以恩信抚诸夷落,劝民农桑,兴起学校”。元代亦非常重视儒学的设立,元初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即于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创立了顺元路儒学,郭子章《黔记·学校志上》曰:“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黔之学自元始,元有顺元路儒学,有蔺州儒学。”所以顺元路儒学也被称为黔学之发端。延佑四年(1317年),普定路判官赵将仕在位于川黔边界的永宁宣抚司“立学校,明礼义,通商贾”,这些都无疑会促进易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除了官学的兴起之外,私学在贵州地区也获得较大发展,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下敕“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卷三十五)。宋代书院兴起,绍兴年间在绍庆治彭水县境内即建有銮塘书院和竹溪胜院。元代亦重视书院的建设,《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世祖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即下令:“凡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此举也造就了元代书院繁盛的局面:“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23]元代贵州最早的书院是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于元皇庆年间在顺元路儒学的旧址处创立的文明书院。书院的设立,无疑也会极大地促进易学在贵州民间的传播。
自魏晋历唐、宋以至于元,在这长达千余年的时间内,虽然贵州与中原的交往日渐频繁,然而有关贵州易学的文献资料仅有两条。一条是上文提及的元代播州十七世孙杨汉英“喜读濂洛书”,由此可以想见播州易学的情形。另一条文献则见于乾隆十九年编纂的《开泰县志·秋部·流寓》中的一段文字:“魏了翁,字华父,蜀临筇蒲江人。幼颖异,称神童。登进士,宁宗嘉定间官工部侍郎,不为时好所容,谪靖州,与永坪县令张辖相往来。其傍梅读易之亭及芙蓉洲渚,华父皆有题咏。后永坪改驿,隶五开。理宗朝诏华父还。”[24]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后世多将其与真德秀并称而不敢轩轾,但黄宗羲、全祖望则有更高的评价:“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宋元学案·鹤山学案序录》)对于南宋易学的发展,魏了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魏了翁儿童之时即“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庆元四年(1198年)省试以《易经》居同经生之冠。后读朱熹之书,学术思想大变,开门授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史·魏了翁传》)。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魏了翁上书言事被弹劾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至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始诏复原职。在靖州期间,魏了翁于城东纯福坡建鹤山书院,筑读易亭,友人李肩吾摘取诗句命名为“傍梅读易亭”。关于与士人读《易》研《易》的情形,魏了翁在与真德秀的书信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是间士人近忽来商量读《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两三日看,先从王《注》、程《传》读起,且令文义分明。如游、杨、吕、谢诸儒所以辅程者,固不可废。而横渠之奥涩、康节之图数、汉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论象占,皆字字钻求。一月余间,读者、听者,人人自谓有益,旁近郡亦有来者。”(《答真侍郎德秀》)由此可见,魏了翁于各家易说并无偏废。在此基础上,魏了翁博采众说编纂了《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部易学著作。《周易要义》是对宋代以前《易》注的一次系统性的批判与总结,“其体例以孔颖达《正义》为主,兼采王弼、韩康伯注及《经典释文》,并析其辞为若干条,每条以小标题作纲领,统辖该条内容”[25]。《周易集义》则是对宋代《易》注的全面回顾,此书集宋代十七家,即“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之《易》论合而为一。这两部易学著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四库馆臣称赞《周易要义》“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方回则称赞《周易集义》“文靖公集百卷,明《易》之义者二百三十章有奇,《易》学最精”(《周易集义跋》)。魏了翁在靖州读《易》研《易》,也使得此地成为易学文化传播的中心,《宋史·魏了翁传》记载:“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由此也可以想见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宋代靖州属于荆湖北路,其治所在今湘西地区,但其辖区有今黔东南部分边缘地带,永坪县在雍正年间改为永坪驿,隶属于五开卫,所以乾隆年间编纂《开泰县志》时收录了魏了翁的相关内容。《开泰县志·风俗志》亦记载魏了翁之言“此邦之人有三不恶,时和年丰,惟以礼乐诗书为事”,这也显示出当地在接受儒家文化熏染后的变化。《开泰县志》所言魏了翁之事虽然无法说明黔东南易学发展的具体情形,但至少可以说明易学在此地区已经开始传播,而明清五开卫易学的兴盛,其源头或许就在于此。
结语
在对贵州学术进行溯源时,学术界常推至汉代的舍人、尹珍等人身上,如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即将舍人列为人物之首,并称赞道:“淑文翁之雅化,导道真之北学。南中若奠先师,断推文学鼻祖。”何绍基则认为是尹珍开贵州学术的先河,其在《题阳明遗像》中说:“学术孰始开黔陬,许君弟子尹荆州。图书业成授乡里,千载坠绪悬悠悠。”这些论断皆是建立在直接文献记录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就会发现一些间接的论据,有助于对贵州的学术重新溯源。就易学而言,或许贵州最早在春秋时期,在参与齐桓公的会盟时就接触到了《周易》。战国时期,随着秦将常頞通五尺道以及楚将庄蹻入滇,《周易》也会被带入贵州。当然,这一时期的《周易》还是卜筮之书,是用来占卜用的。西汉初年,文翁化蜀,巴蜀之学遂“灿焉与邹鲁同风”。受巴蜀之学的熏染,犍为郡文学舍人注古所未训之经——《尔雅》,盛览问赋于司马相如。东汉以后,儒者说经不专主一家,“至许、郑集汉学大成”。桓帝之时,毋歛人尹珍远从许慎受五经、从应奉学习图纬,还授乡里而“南域始有学”。虽然没有相关的文献资料能明确说明文学舍人、尹珍等人对《周易》有所研读,但汉代的学术即以文学训诂为本,文学舍人等必然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十分熟稔。对于这一点,郑珍在《汉三贤祠记》中早有说明:“六经联字以成文,字之声、形、义明,其于治经,如侍先圣贤之侧,朗朗然闻其耳提面命也。文学公深明《雅》,故不待言,盛公与相如游,尹公从许君,凡将十五篇之传,必熟闻其终始。”由此亦可想见汉代易学在贵州传播的情形。魏晋以至宋元,大量任职于黔地的官员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兴学养士,这也必然会进一步推动《周易》在贵州的传播。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无法具体深入地了解明以前《周易》在贵州传播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播已经为明代贵州易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