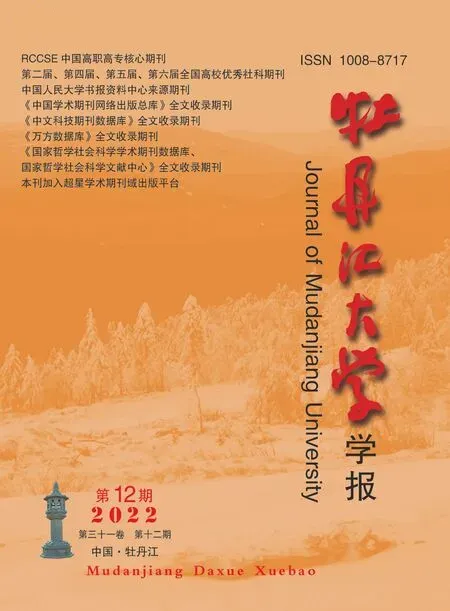文本与历史的互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仲维琪 高建华
(1.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00)
引言
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曾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其生长于美国南方,使他便于将熟悉的家乡故土和南方历史作为创作素材,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名为“约克纳帕塔法郡”的地方,并以此为背景,构成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这片土地上,福克纳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所经历的兴衰变迁以及北方新兴资本对南方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其中又不乏对于南方腐朽罪恶的历史现实的揭露。《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便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极具特色的一篇,同时也延续了这一系列小说的基本主题与写作风格。
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女性主义视角,以此来分析爱米丽的悲剧命运及其走向悲剧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关于作品中表现出的哥特风格的解读,对于叙事特点的探究也占有一定比重。但鲜有学者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作品进行研究,这为该文本的研究留下了阐释空间。此外,福克纳对于文本与历史关系的认识,以及他关于边缘化声音的叙述也与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不谋而合。因此,文章聚焦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探究福克纳笔下关注的美国南方历史。
一、爱与恨交织的南方情结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同时又能动地参与历史的建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主人公爱米丽在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及工业文明的产物已经入侵南方之时,依旧保持着旧时代的物品,同时,又不愿意接受新时代的产物。此外,在新旧时代的过渡阶段,旧时传统与新兴事物之间又无法实现良性的互动,旧的传统在新时代下无法得到传承与延续,长期处于脱节断裂的状态,这与当时南北方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北战争这场决定双方命运的大环境下,南方的落败使其以奴隶制为主的种植园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北方资本的入侵使南方本就糟糕的悲惨境况变得更加沉重不堪。对于南方陈旧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来说,这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是十分巨大的。
文本中多次提到爱米丽的房子,对于其内外环境的描述以及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作家并不吝啬笔墨。在尚未揭开木屋内部的真实情况时,妇女们对于她屋子的内部充满了好奇心。而爱米丽的这座房子不仅仅作为一个供人参观的尊贵场所而存在,它还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内涵,它象征着一个家族的没落,一个时代的变化,是南方社会转型的见证者。大木屋位于当年最考究的街道,屋顶和阳台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因而在工业文明洪流的冲击下显得格格不入。诸如汽车间和扎棉机之类的工业化产物充斥在小镇四周,而爱米丽小姐屋子周围的棉花车和汽油泵这种传统工具在这样的衬托下显得极不和谐,曾经独属于格里尔生家族的庄严肃穆早已被打破,可这座木屋却依旧岿然独存。如今的房子真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丑中之丑”[1]28,这一切表面上是对房子的描述,实则是作者对像主人公爱米丽这样苦苦维护尊严与身份的没落贵族的嘲讽,其中包含着福克纳强烈的批判意识。爱米丽是旧时代的代表,“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1]28,“纪念碑倒下了”[1]28意味着南方传统贵族的衰落,以土地和奴隶为主的种植园经济土崩瓦解。南方古老的农业文明与北方新兴的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阴暗的门厅、破败的家具、厚厚的灰尘以及失去光泽的画架和拐杖头的镶金依旧在房间里存留,但是却早已经与新时代脱节。
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失败使南方经济一蹶不振,北方资产阶级的冲击并没有唤醒南方沉睡的贵族,他们依旧沉湎于过去的光辉,墨守成规,无视历史的进步。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新生事物被拒之门外,他们坚决抵触新时代到来对其产生的任何影响。在沙多里斯上校时期,爱米丽因父亲的缘故享有免于纳税的权利。而到了第二代镇长上任时,她依然停留于旧时代赋予她的特权,“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1]30是她据理力争的筹码。然而,沙多里斯上校早已去世,这样的“胜利”无疑增添了悲剧与讽刺意味,同时也将格里尔生家族由盛转衰的现实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当免费邮递制度在全镇实行后,爱米丽却拒绝装订金属门牌号和邮件箱,她用实际行动顽强地与新时代做抗争,坚决排斥和无视新时代的变化及其应运而生的产物。
爱米丽瓷器彩绘课的停授是新旧时代矛盾下的必然结果,是旧时代的传统无法被新时代所容纳的表现。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孩子送到爱米丽那里学画,这是对传统文明的尊崇和重视,也是对爱米丽作为南方贵族地位的尊敬与肯定,她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可是,新的一代兴起,学画的学生们长大成人后却没有让他们的下一代到那里学画。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传统艺术与现代产物之间由于未能实现恰到好处地融合而产生了断裂和缝隙,由此造成了传统事物的渐趋衰落。学画的传统并未在现代化浪潮中得以保留和传承,而是被吞没直至消失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也代表着旧时代南方传统文明的没落消亡。当最后一个学生离开时,前门永远关上了,爱米丽也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状态。旧时的一切都被关在门的另一边,爱米丽也把自己关在了里面。这道门使爱米丽与世隔绝,留恋在过去的美好而停滞不前,其中饱含着福克纳对于成长故土的怀念,与此同时,他又无法摆脱南方千疮百孔的腐败现实带给他的伤痛,渗透着作家对于南方固步自封、维持现状的批判。对此,福克纳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本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 即便是怀着憎恨。”[2]
文题中的“玫瑰花”在文本中并无确指,更没有指向对象,仅在文末才有所提及。这里的“玫瑰花”并非实物,而是作为形容词性出现,即“玫瑰色的”。因此,它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如同早已褪去贵族光环的昔日南方,从前的一切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而爱米丽与荷默之间的婚姻也是如此,还未开始就已败色。将这样的一朵玫瑰花献给爱米丽,无疑是对她最大的讽刺。然而,福克纳对于爱米丽又是怜悯和尊敬的。“这儿有一个遭遇悲惨的女人,她的悲剧是无法改变的,任何人也无能为力。我可怜她。这是向她表示敬意,就像你在这种情形下要向人作出某种姿势、行个礼什么的一样。对一个男人,你会敬他一杯酒,而对一个女人,你则会献上一朵玫瑰。”[3]这朵玫瑰花包含着福克纳对她的复杂心情,更是对已逝南方的缅怀与献礼。
二、边缘叙述下的南方历史
新历史主义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传统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将文学文本介入历史,把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纳入文化文本进行阅读,打破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发挥了文学记录历史、建构历史的功用。新历史主义者强调文学对历史的建构作用,它能够参与历史的建构,促进历史的形成,这与福克纳对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1995年,福克纳曾在访问马尼拉时说:“作家的责任是记录历史,向人们展示他们未来的希望,作为抵御他们过去的措施。”[4]因此,他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构建和促进历史形成的作用。新历史主义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文本与历史的二元对立,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历史不再是绝对地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撰写”。[5]福克纳对于南方历史的“小说化”处理正是对新历史主义者所提出的“历史的文本性”的践行,历史不过是以文学虚构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文本。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福克纳小说是对历史的重新书写。福克纳消解了权力中心的话语体系,注意到一直以来被置于传统主流历史之外的黑人的声音,以此通过他的文学文本参与了南方历史的建构。福克纳对于历史中边缘化人物的叙述与书写,将隐藏于南方昔日辉煌下的创伤历史展露出来,给予了边缘群体一定的关注和观照。
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文学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尽管福克纳在此着墨不多,但从寥寥数语中依稀能感受到黑人长期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生存境况。在显赫的贵族面前,黑人是没有话语权力的失语者,地位低下,尽管人物在场而实际上声音却不在场,是没有话语权的无声者。文本中服侍爱米丽的黑人男子便是长期生活在这种双重压迫下的失语者,他的身份是受白人贵族支配的黑人奴隶。黑人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受主人支配,为主人服务,随时听候主人差遣,只要爱米丽下达命令,他便将不速之客请出门外。对此,黑人没有呈现出任何言语或态度上的反应,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二者之间的地位差别悬殊,种族界限不可逾越。尽管有关黑人奴仆的叙述贯穿于小说的各个角落,但整体上文本中对于他的描述却十分有限。他为主人买东西,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忙前忙后,从青年到老年,一生都是如此。在文本中,他是声音的缺席者,“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1]38此外,黑人同时也是屈辱性的存在,法官不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称呼他,还随意怀疑和诬蔑他。爱米丽的黑人男仆被法官称作“黑鬼”,毫无尊严可言。当爱米丽因屋子里难闻的气味而遭到妇女的抱怨时,法官首先将矛头指向了黑人,“可能是她用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1]31由此可见,黑人是被怀疑的对象,是一切坏事的始作俑者,更是作为一个没有位置的他者而存在。面对这些无端的侮辱与诬蔑,指责与谩骂,他们始终是不能表达自我的边缘人物。
随着北方工业逐渐向南方入侵,来自北方的建筑工头荷默·伯隆带领黑人和机器开始在镇子动工,在准备铺设人行道时,黑人们勤勤恳恳,吃苦肯干,通过自己仅有的廉价劳动力为现代化进程贡献力量。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被尊重和认可,甚至遭受着不堪入耳的责骂。他们是被压制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是没有自我的他者。他们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依附于贵族而存在,一旦贵族阶级倒台,蓄奴制随之走向败落,奴隶们便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因此,在爱米丽去世后,黑人离开了爱米丽的房子,并且从此消失了。“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1]39这不仅意味着拥有奴隶身份的黑人暂时摆脱了奴隶主的压迫和束缚,在肉体上获得了解放,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仆之间情感的淡漠,黑奴甚至没有参加主人爱米丽的葬礼就离开了,其中隐含着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不可跨越的种族边界。然而,黑人作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在新的统治阶级占据主导的社会历史中何去何从,依旧是一个未知并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历史主义强调对边缘人物历史叙述的关注,将单数的正统的“大历史”化为复数的边缘的“小历史”,发现以往被忽视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他者,从而折射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弊端。美国南方蓄奴制早已在南北战争后就被废除,黑奴本应获得人身自由,但没落的南方贵族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阶级特权,黑人在战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好继续依附于旧秩序下的主人,直到爱米丽去世后黑人才离开格里尔生家族。而这一附属性身份造成了黑人群体心灵世界的封闭,作家也并未对其内心活动进行描述,但黑人奴仆长期被压制的生存境况随处可见。在读者眼中,黑人就是无休无止工作而没有感情的服务机器,永远为格里尔生家族的主人而转动。可见,南方黑奴制度和种族歧视不仅禁锢了人们的身体自由,更在他们的精神层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所以,福克纳对于南方行将腐朽的传统文明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尤其是对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对黑人身心的残害和奴役进行了与深刻地批判。福克纳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关注到“黑人”这一类边缘人物,以独特的叙述声音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历史的另一个横断面。
三、“颠覆”与“抑制”的权力模式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揭示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某种对立性关系。为此,在福柯话语与权力理论的影响下,格林布拉特在《看不见的子弹》中提出了两个具有政治化的概念:“颠覆”和“抑制”。“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6]从宏观的历史层面来看,北方新兴资本与南方传统文明之间就构成了“颠覆”与“抑制”的权力模式。深入到微观的文本细节之中,爱米丽作为维护南方传统文明的抑制性力量,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清教主义父权制的“抑制”,因而产生了一些具有反叛意味的“颠覆”行为。
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前曾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存在,爱米丽作为南方贵族的代表,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1]28在南北战争中,南方战败、北方获胜的结果颠覆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传统的社会价值面临无法逆转的困境。北方工业文明入侵后对南方造成了巨大冲击,汽车间和轧棉机等工业文明的产物进入到人们的世界,而爱米丽岿然独存的房子与这些新生事物显得格格不入,可谓“丑中之丑”。在统治阶级的权力运作层面,新兴资产阶级渐趋取代传统的贵族势力,占据统治地位,打破了南方旧有的贵族秩序,并将其价值观念引入南方社会,建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北方的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形成了针对南方旧秩序的颠覆性力量,成为权力话语的中心。
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战败给南方本土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南方传统的农业文明受到了冲击,种植园经济走向崩溃。面对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爱米丽作为格里尔生家族的末代人物仍然高傲地维护着自己贵族身份的尊严,坚守逝去的南方传统,并以决绝的态度奋力与新潮流抗争。文本中对这种颠覆性力量的“抑制”表现为爱米丽对于过去的无限沉醉,她一直深陷于过去辉煌的历史之中无法自拔。除此之外,这种“抑制”行为还体现在爱米丽在面对现状时的拒绝与排斥,如牢牢坚守曾经被赋予的纳税豁免权,无视政府当局,拒不交税等。在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的现实面前,她竟然叫代表团去找沙多里斯上校评论此事。不仅如此,爱米丽对于北方资本进入南方后产生的新事物也断然拒绝,概不接受。然而,她的一切“抑制”行为都无法与强大的新兴统治力量进行抗衡,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自我封闭的牢笼。“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出现在大街上。”[1]37爱米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最终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淹没,“纪念碑倒下了”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爱米丽出身高贵,作为贵族出身的女性,她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始终是大家关注的对象。她长期受到父亲一代的影响,时刻保持着格里尔生家族的尊严,冷酷孤傲,自视甚高。父亲的炭笔画像一直伴随在她左右,可见父亲对她的影响颇深。她在世时将这幅父亲的画像放在已经失去红色光泽的画架上;她过世了,这幅父亲的炭笔画像则悬挂于停尸架上方。由此可见,无论生前或死后,父亲犹如影子一般跟随在爱米丽身边。在父亲死后,爱米丽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一丝哀愁,她不相信父亲已经死去,不肯埋葬父亲的尸体,她要“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1]33。而父亲就是那个剥夺了她幸福人生的根源,父亲的性格时常在她身上具有明显的呈现,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恶毒狂暴的性格使她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爱米丽自身的悲剧命运与来自父辈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不无关系,这也是加快南方蓄奴制经济制度解体的因素之一。面对来自北方的工头荷默,她又爱又恨,荷默既是爱米丽倾慕已久的爱人,与此同时,他又是导致南方走向破败衰落的入侵者,爱米丽最终用砒霜杀死荷默的行为是她作为南方贵族对于北方入侵者的强烈报复,是试图挽救昔日南方贵族尊严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尽管这种方式是徒劳的。因此,爱米丽也成为为了维护南方贵族特权而毒死爱人的施暴者。
在如此深受压制和束缚的环境下,“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30,失去人作为生命个体的生命力与活力。她的父亲曾经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致使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父亲的专制态度与行为使她一直处于情感缺失的状态,这导致她对于荷默·伯隆的爱是极端的、病态的。因此,当她被心上人抛弃后,她选择用砒霜毒死他,将他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并将楼上的房间布置成婚房的样子,与永恒长眠的尸体同床共枕。直到她去世,人们才发现男子腐烂的尸体和留在旁边枕头上那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爱米丽的这一极端做法是对格里尔生家族带给她的贵族女性典范形象的颠覆,更是对父权制社会的极端反叛。在父亲死后剪短头发,与荷默一起乘马车出游也是其颠覆性行为中不足挂齿的一隅。美国南方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成长的压制与束缚使女性逐渐失去自我,丧失了人类个体的主体性。爱米丽就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她被塑造成为一个符合格里尔生家族规范的女性,而这种压制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对此,福克纳表示了对爱米丽悲剧命运的的惋惜。“我为爱米丽的悲剧感到惋惜。她的悲剧在于她是那样父权当道家庭的独生女”[7]
四、结语
福克纳本人出生于美国南方的一个庄园主家庭,爱米丽所经历的家庭败落正是福克纳心中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使他多次以南方历史为素材,加之个人的成长背景与经历,创作出符合他的历史观下的文本,这其中包含了福克纳对于过去历史的无限感怀,同时流露出与新历史主义相似的历史意识。爱米丽作为福克纳的发言人,将南北战争后南方破败的一面展现出来。南方种植园经济瓦解,贵族走向没落;工业文明的入侵使旧有的阶级、制度、文化等渐趋衰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应运而生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统治力量出现。格里尔生家族的没落就是当时美国南方社会以小农为主的种植园经济崩溃的真实写照。此外,福克纳对边缘叙述声音的关注将人们从官方历史叙述的对南方无限美好的憧憬中抽离出来,揭露出深谙于主流历史语境之外的丑恶现实,《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就成为构建南方历史的话语之一。福克纳通过这一作品践行了新历史主义对边缘历史叙述的关注。
福克纳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一方面无法抹去心中对南方历史的怀旧情结;另一方面,又对南方罪恶历史大加鞭挞,将种族主义、蓄奴制以及父权制等弊病透过文本展现出来。这使得福克纳的作品上升到人性关怀的高度,在其对南方的无限伤怀之中表达了对于人性复归的渴望。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