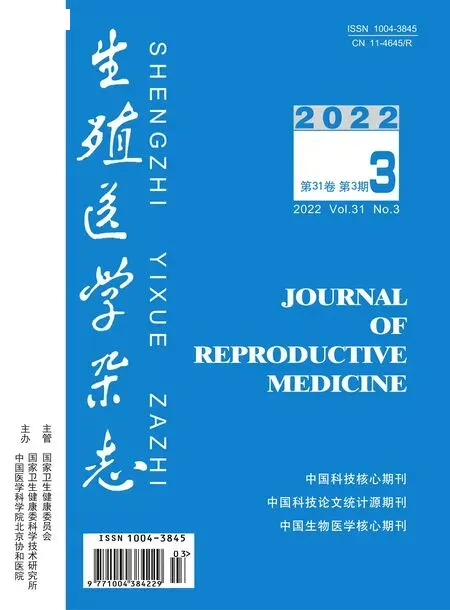前后两次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的患者新发乳腺癌的讨论
崔丽丽,邓姗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石家庄 050000;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妇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病例资料
患者C,女性,43岁,G2P1。1998年经阴道分娩一次,药物流产一次,无生育要求。主因第2次曼月乐置入术后8个月,发现乳腺癌3个月,咨询曼月乐的去留,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门诊。
既往月经规律,6~7 d/30 d,量中,痛经VAS评分6~7分。8年前开始出现月经量多,约为平素经量2倍,血红蛋白(HB)最低80 g/L。于当地医院行妇科超声(2013年5月6日):子宫内膜增厚为14 mm,其内可见一团块11 mm×9 mm×8 mm,血流丰富。于当地医院行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术后病理示子宫内膜呈增殖期改变。术后口服妈富隆治疗8个月,效果欠佳。于2014年8月宫腔放置左炔诺酮宫内缓释系统(LNG-IUS,曼月乐),放置曼月乐后阴道淋漓出血2+月,其后闭经4年。2019年开始出现不规则少量阴道出血半年余,于当地医院行妇科超声提示:子宫增大,多发性子宫肌瘤(肌壁间多发低回声结节5个,大者40 mm×38 mm×36 mm,左后壁肌间低回声22 mm×21 mm,挤压内膜),宫内节育器。于2020年9月2日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宫腔镜下粘膜下肌瘤切除术+刮宫术+宫内曼月乐放置术。术中宫腔见直径约4 cm Ⅰ型粘膜下肌瘤,术后病理提示“多发平滑肌瘤,子宫内膜不规则增生”。再次放置曼月乐后阴道淋漓少量出血3月,其后闭经至今。
2020年12月发现左侧乳腺包块,于2021年1月25日于天津肿瘤医院行左侧乳房根治术+同侧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提示:左乳腺中上浸润性癌,未见淋巴结转移。免疫组化:雌激素受体α(ER-α)阳性细胞<1%,孕激素受体(PR)阳性细胞<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1+),Ki-67阳性细胞约占60%,p53阳性细胞<1%,CK5/6阳性细胞约占10%。术后目前已化疗5个疗程。
经门诊咨询,患者为三阴乳腺癌,对激素的影响顾虑相对小,而曼月乐对乳腺癌的预后并无明确的负面证据,初步决定保留曼月乐,随诊观察。
病例警示
一、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概况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约有80%的乳腺癌为ER阳性,65%的乳腺癌PR阳性。一般而言,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应接受内分泌治疗,能有效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
目前内分泌治疗有3种选择: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包括他莫昔芬、雷洛昔芬和托瑞米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下调剂(SERDs,氟维司群)和芳香酶抑制剂(AIs)。目前美国FDA仅批准他莫昔芬和雷洛昔芬用于乳腺癌高危女性的一级预防。他莫昔芬(TAM)是第一代SERM,用于治疗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对正常乳腺细胞和乳腺癌细胞,TAM有阻断内源性雌激素的作用,而在子宫、骨骼、肝脏和凝血系统中可产生弱雌激素样效应。所以长期服用TAM可以引起不规则阴道出血、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息肉甚至子宫内膜癌。Nelson等[1]的系统综述报道,在美国每1 000例应用TAM的女性中子宫内膜癌发生增加4例;TAM与安慰剂相比,最初5年内的子宫内膜癌风险升高[OR=3.76,95%CI(1.20,15.56)],但5年后未见风险升高[随访5~10年,OR=0.64,95%CI(0.21,1.80)]。
三阴乳腺癌(TNBC)是指不表达ER、PR和HER2的恶性肿瘤。根据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的指南,将TNBC定义为:免疫组化(IHC)测定ER和PR的表达≤1%,HER2表达为0~1+或IHC 2+但荧光原位杂交(FISH)结果阴性(无扩增)。TNBC约占全球乳腺癌的20%,更常见于40岁以下女性,通常为高级别肿瘤,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上具有生长迅速、复发高、转移早和预后差等特点。TNBC的危险因素包括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突变阳性状态和绝经前状态。因为没有相应的雌、孕激素受体或HER-2表达,所以TNBC不适合内分泌治疗和抗HER-2靶向治疗。目前TNBC的辅助治疗主要采用全身性化疗治疗,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推荐TNBC的优选化疗方案为含紫杉类药物和蒽环类药物的剂量密度方案。激素与TNBC的关系尚有争议,总体而言,应用雌孕激素(包括口服避孕药、IUS、更年期激素治疗)后TNBC的风险无明显增加,但细化分组后,随使用时间的延长,无论是口服避孕药、含孕激素IUS,还是绝经激素治疗,都可能轻微增加TNBC的风险(相关OR为1.20~1.79),而难以理解的是,IUS超过10年组的OR又下降至0.75,并非风险与暴露时间呈正相关的趋势[2]。本例患者为TNBC,术后不进行内分泌治疗,也就不存在药物诱发内膜病变的可能,而患者有曼月乐在体,对内膜的保护效应是比较有保证的。而曼月乐释放的孕激素是否对乳腺癌有不利影响便成为现阶段重点考虑的问题,鉴于TNBC没有PR,曼月乐的影响应该比普通乳腺癌更小。
二、LNG-IUS与乳腺癌的关系
曼月乐(LNG-IUS)是一个含有52 mg左炔诺孕酮(LNG)的“T”形缓释支架,在宫腔内以20 μg/d的速率持续释放LNG,有效使用年限为5年。LNG-IUS置入宫腔后数周血清LNG浓度趋于稳定,约为150~200 ng/L。子宫内膜的LNG浓度高于子宫肌层100倍以上,高于血清1 000倍以上。宫腔内高浓度的LNG对子宫内膜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除避孕和特发性月经过多这两项获批的适应证外,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LNG-IUS具有更多的非避孕获益,如治疗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子宫腺肌病,预防子宫内膜息肉复发等[3]。本例患者在乳腺癌发病之前无疑就是LNG-IUS的受益者。在乳腺癌患者中,也有使用LNG-IUS来防治内分泌治疗过程中的内膜增生性病变的经验报道,但LNG-IUS对于乳腺癌患者的利与弊一直是医生和患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1.LNG-IUS使用者的乳腺癌风险:宫腔放置LNG-IUS也会有微量LNG释放入血,Depypere等[4]通过检测18例使用LNG-IUS女性的血清、乳腺组织中LNG的浓度发现,血清中LNG的平均浓度为(0.18±0.16)ng/ml,乳腺组织中LNG的平均浓度为(0.26±0.28)ng/g,均远低于口服LNG 迷你片(30 μg) 的血清及乳腺组织浓度(分别为0.315 ng/ml及1.17 ng/g)。Siegelmann-Danieli等[5]通过回顾性研究13 354例LNG-IUS使用者及27 234例非LNG-IUS使用者,发现两组患者在总的乳腺癌和导管内原位癌的发生风险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但LNG-IUS使用者发生浸润性乳腺癌的风险稍高于非使用组(5年发生率1.06% vs. 0.93%,P=0.051),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显现于40~45岁的女性(0.88% vs. 0.69%,P=0.014),而在46~50岁的女性中无显著差异(1.44% vs. 1.21%,P=0.26)。Jareid等[6]在挪威进行了一项纳入104 318例女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NOWAC),其中9 144人曾经使用过LNG-IUS,随访中位时间为12.5年,结果提示使用LNG-IUS的乳腺癌发病率并没有增加。
Soini等[7]在芬兰纳入93 843例LNG-IUS使用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较一般女性人群,LNG-IUS使用者导管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标化发病比(SIR)=1.20,95%CI(1.14,1.25)]和小叶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SIR=1.33,95%CI(1.20,1.46)]均有所升高;且其中患乳腺癌风险最高的为使用LNG-IUS 2次以上者[以小叶性乳腺癌为例,SIR=1.73,95%CI(1.37,2.15)]。Mørch等[8]在丹麦进行了一项纳入1 797 932例女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平均随访时间为10.9年,结果显示,与从未使用激素避孕药的女性相比,近期或者目前使用激素避孕者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略有增加[RR=1.20,95%CI(1.14,1.26)],每7 690名使用激素避孕1年者中大约增加1例额外乳腺癌患者,其中LNG-IUS使用者发生乳腺癌的风险略高于使用激素类避孕药者[RR=1.21,95%CI(1.11,1.33)]。Conz等[9]通过一项纳入7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得出,无论年龄和适应证有无区别,LNG-IUS使用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均存在联系[OR=1.16,95%CI(1.06,1.28)]。而针对于此,Silva等[10]的另一项荟萃分析从494篇研究筛选出8项研究,纳入两项队列研究和两项病例对照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包含28 054名LNG-IUS使用者和158 485名对照女性,结果表明在绝经前或绝经后使用LNG-IUS均无增加患乳腺癌风险,并且针对性指出Conz等[9]的研究有不合理之处:在同一分析中合并了病例对照和队列研究设计;包括了一些从荟萃分析中排除的研究;同时使用来自芬兰的同一数据库,导致数据重叠的可能性等。
2.乳腺癌患者应用LNG-IUS的风险:Fu等[11]为评估LNG-IUS对TAM引起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疗效,经系统检索和荟萃分析共纳入3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359例乳腺癌患者,其中LNG-IUS治疗组175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LNG-IUS治疗组的乳腺癌复发率[OR=1.75,95%CI(0.64,4.80),P=0.28]和乳腺癌相关死亡率[OR=1.22,95%CI(0.42,3.52),P=0.71]并无显著增加,同时显示LNG-IUS能有效预防TAM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内膜息肉的发生。类似的,Dominick等[12]的荟萃分析纳入了4项随机试验543例乳腺癌患者,其中LNG-IUS治疗组273名,与对照组相比,LNG-IUS治疗组子宫内膜息肉或增生的复发率明显下降的同时,乳腺癌复发率[OR=1.74,95%CI(0.64,4.74)]和乳腺癌相关死亡率[OR=1.02,95%CI(0.36,2.84)]也均未显示有显著增加。加拿大的避孕共识中也同样认为:服用TAM的患者使用LNG-IUS与乳腺癌复发无关(I类推荐)[13]。
然而Omar等[14]随后根据既往的的研究证据及世界卫生组织避孕药具使用医疗资格标准中关于“患有乳腺癌的妇女使用LNG-IUS为第4类,过去有乳腺癌病史且5年无疾病证据的妇女使用为第3类”的规定,仍认为乳腺癌患者应用LNG-IUS有一定风险。
肖雪莲等[15]曾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乳腺癌术后应用TAM的患者59名,其中30名患者宫腔放置了LNG-IUS。结果表明:LNG-IUS可有效降低乳腺癌术后TAM引起的子宫内膜改变。贺永艳等[16]通过将LNG-IUS与乳腺癌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倾向中国女性使用LNG-IUS不会增加乳腺癌发生,也不会增加乳腺癌复发与死亡风险,但仍期待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对此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综上,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支持LNG-IUS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以及乳腺癌患者使用LNG-IUS增加肿瘤复发率及死亡率,推测对三阴乳腺癌的影响更小。期待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对乳腺癌患者使用LNG-IUS还是应持审慎态度。
事实上,孕激素对于子宫内膜和乳腺的正常组织和癌变组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多效性和复杂性,至少有两种受体亚型在多个水平以及不同的微环境下受到不同的调控,凭借传统的雌孕激素效应规律以及不区分亚型的受体免疫组化检测,很难正确或全面地评估其个体效应。孕激素对不同组织的作用之所以不同,区别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有表达PR的基质及其与上皮细胞的旁分泌相互作用。与子宫内膜含有大量具有PR的基质细胞不同,乳腺缺乏显著表达PR的基质成分,孕激素的靶细胞直接为乳腺上皮细胞,因而具有一定的致肿瘤性,作为妇科内分泌医生,应该有更客观的认知和考量。
——既能避孕又能治病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