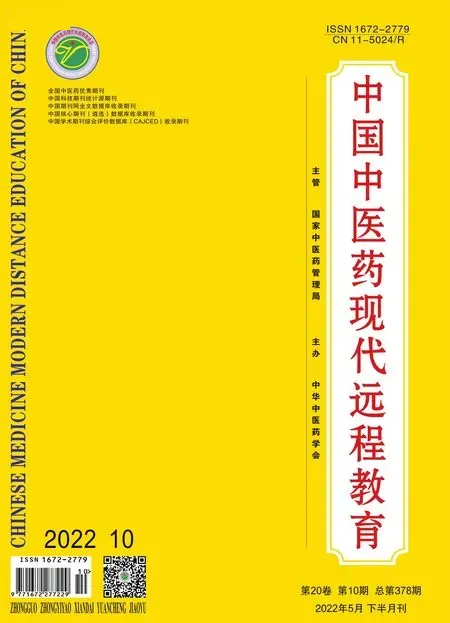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的中医术语翻译规范构建*
余 静 韩 露
(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
史料显示,中医药翻译与传播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本草植物通过丝绸之路走向欧洲。明清之际,中西方科技双向交流活跃,涉及中医药的译著多达70 余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中医翻译和传播的研究随之受到更多关注。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是中医翻译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对提高中医翻译质量,准确传达中医核心概念,避免文化误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学家、哲学家之一,与A·吉登斯和J·哈贝马斯一起被称为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巨头。布迪厄的研究深入社会学、哲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为许多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20 世纪70 年代末,国内外翻译研究者逐渐脱离“翻译过程不受外界干扰”的预设,开始关注社会作为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1]。从社会翻译学角度来看,翻译活动既属于翻译学,也属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翻译学尝试从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描述和重构翻译实践背后的社会体系,及其对翻译主体、翻译风格、翻译效果的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社会翻译学的理解,本文从翻译尝试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对中医术语翻译规范进行探讨,以期拓宽中医翻译的研究视角,掌握中医术语翻译标准构建的话语权,向世界讲好中医故事。
1 场域理论及其核心概念
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迪厄提出了社会分析模型的简要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2]。此公式含有3 个核心概念,即“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之间的关系映射到翻译实践中,则表达为:译者带有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
1.1 场域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3]。布迪厄认为,如同物理学场域是力的相互作用空间,社会场域也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场域是由人类根据自己的信仰构建的,每一个场域有清晰可辨的逻辑。社会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特定的历史轨迹发生改变的。在某一个微观场域中,社会行动者并不处于同一平面,他们通过运用策略来维持和改变他们的位置,以获取竞争优势。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反映的是社会场域的空间性、场域间力的关系,以及场域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研究中。在翻译学研究领域,翻译实践中的作者、译者、出版商都是某一翻译场域的行动者。他们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本和策略相互影响,来改变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本文将中医术语翻译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场域,以此探讨各方面因素对于中医术语规范构建的影响。
1.2 资本 布迪厄的资本(capital)概念承接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把资本定义为社会行动者从事社会实践的工具。“这种工具可以是物质的(经济资本),也可以是非物质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还可以是符号化的”[4]。布迪厄认为不同形态的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传递和转化的,比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具体映射到翻译场域中,文化资本就是译者对于文化资源的占有,比如个人的文化素养、教育水平、语言能力、审美偏好等,都被视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权力资源。所谓社会资本,可以理解成为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布迪厄强调,这种潜在的隐形资源分布在场域中,行动者通过有意识地交流、不断投资、长期的经营和维护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行动者在此过程中花费时间和精力,并直接或间接花费部分经济资本,来达到社会资本再生产。而从这一关系中产生的社会资本,即行动者积累和维持社会资本的增值,要远远超过其个人原先拥有的资本。
1.3 惯习 布迪厄在其著作《实践感》中,阐释了惯习的概念:“惯习是持久的、可转化的潜在行动倾向系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性情倾向。即个人的风格不是某一个时期的偏移,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联结,是共时和历时交互的结果。在翻译场域中,译者在接受教育、学术研究、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维习惯(即译者的早期习惯),而后内化成为其译者惯习,并在翻译实践中外显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等[5]。
2 场域理论下的中医术语翻译规范化
2.1 综合考虑场域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影响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社会场域无处不在,每一个场域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彼此联系、互动的。身处在某一个微观场域的社会行动者,能感受到来自不同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不易察觉的、潜在的形式存在。比如文化场域、美学场域、时尚场域等等。
中医术语翻译也牵涉到场域问题,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又与其他场域相互作用。首先,中医术语主要来源于中医典籍、文献、医方等,是不同医家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诊法、疗效、症状的高度凝练和表达。不同历史时期的术语,在语言、语篇、叙事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医家流派的术语,在哲学思想、思维方式、逻辑表述上各不相同。译者不能只把中医术语局限于医学场域中去考虑,而应该结合术语产生的历史场域、文化场域、语言场域、哲学场域等进行综合考虑,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和描述好一个术语。其次,目的语文化也构成了一个场域。中医术语翻译的过程,是从原语文化场域到目的语文化场域的转化过程。中医术语的内容和气韵是由原语文化场域决定的,但是否能够通过翻译活动被目的语文化接受,是由目的语文化场域的本质决定的。以中医术语英译为例,英语是翻译活动的目的语,但不同的说英语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场域,对于同一种译本的接受是不同的。考虑到目的语文化场域问题,中医术语翻译应该以目的语文化为坐标选择翻译策略,而非以目的语为坐标来选择。
例1 《黄帝内经》译为:(1)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2)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3)Huangdi's Orthodox Classic;(4)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5)The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6)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等。多个译本将“黄帝”译为Yellow Emperor,值得进一步商榷。
在中医文化场域中,黄色是万世不易的大地之色,代表天德之美,被尊为帝王之色。皇帝的文告叫“黄榜”,天子穿的衣服叫“黄袍”。而在欧洲文化场域中,能代表皇权和高贵的颜色是紫色和蓝色。古欧洲时期,传说地中海的贝壳能提炼珍贵的紫色染剂,是专供英国皇室使用的尊贵之色。同时,罗马教会也认为紫色是正义之色,象征智慧与尊贵,主教的服饰多为紫色。而黄色则并不是高贵的颜色。据《圣经》记载,犹大为了获得30 枚银币把耶稣基督卖了,当时就身穿黄色衣袍。因此,yellow 一词在基督教文化场域中,常被引申为背叛、胆小之意。
最后,术语翻译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中医文化场域是中医术语翻译的基本话语情境,是翻译活动的逻辑起点。中医术语翻译必须在中医文化场域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才能保证术语翻译的学术性、民族性、文化性。如果脱离中医文化场域,势必会使中医术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失去其本身的文化内涵和气韵,或造成谬误。
例2 伤寒:译为typhoid;typhoid fever;abodomial typhoid。
根据WHO 援引的概念,Typhoid 是由伤寒沙门菌引起的系统性感染,通常是因为受污染的食物或水造成的(Typhoid fever is a systemic infection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usually through ingestion of contaminated food or water.)。在中医文化场域中,伤寒指感受六淫之邪所引起的急性热病,即一切外感热性病之总称。《素问·热论》记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可见,中医文化场域中的“伤寒”与西医场域中的“typhoid”完全无法对应。因为伤寒虽为热证,但病因往往由于感受寒邪所致,也有一些译者将其翻译为:cold damage,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较之于typhoid,则明显保留了中医文化的本质内涵和逻辑线索。
2.2 充分考虑资本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影响 布迪厄将其重要概念“资本”划分为4 种类型,分别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6]。在中医术语翻译场域中,文化资本处于最基础的底层结构中,决定着场域的等级和功能,并通过场域中的行动者转化为其他资本。中医术语翻译的译者在进入翻译场域前,应同时拥有能够准确理解术语的医学知识、文化知识、语言学知识,以及熟练使用目的语进行转译的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来自译者接受的系统性培养,是译者投入的积累性劳动的结果,可以被理解为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在译者进入翻译场域之后,文化资本依据其所处的环境转译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原则,也就是转译成为一种身体性或认识性的倾向,成为译者的一种特定行事方式。可以说,译者本身就是翻译场域所制作出来的肉身,因而他的知识结构与场域结构是同源的。而如此一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往往符合场域所希望其所是[7]。在这种情况下,场域的结构是与作为肉身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并表达为个人的涵养、姿态、品味和对生活的选择。这就是所谓文化资本的具身化(embodied)。在中医术语翻译活动中,一些译者通过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方式实现文化资本的客观化,从而带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同时,译者获得业界承认的时候,也就获得了信用、学术地位等象征资本,从而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转化。
在中医术语翻译场域中,各种不同资本都对场域的结构和原则产生影响。首先,译者所占据的文化资本,直接决定了场域的结构。中医术语翻译场域中的译者群体比较复杂,主要由几类人组成:中医专业人士中外语强的人、外语专业人士中懂中医的人、懂一些中医的外国译者以及中西合译者。这几类人占有的文化资本不完全相同,因而形成了原则和结构各异的微观场域。不同类型译者的文化倾向、审美偏好也不尽相同,从而使翻译文本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中医术语翻译的规范性难以达成一致。其次,经济资本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翻译场域。在经济资本的影响下,从读者的购买欲望角度,出版商倾向于易于受大众关注的主题,而忽略学术性较强的术语翻译领域。中医术语翻译相关的教材、专著、论文都不易受到经济资本的追捧,而使译者具备更强的资本转化动能。因此,译者从事中医术语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提高其自身的能力和学术地位,以便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长期不受到经济资本的关注,会影响译者推动中医术语翻译规范性研究的动能。
2.3 着重考虑惯习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影响 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被结构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些性情或者倾向是持久的,而又会在社会活动广泛而又多样的戏剧中旋即(transposable)成为一种生成行动的能力[8]。映射在翻译场域中,惯习指由行动者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物质结构,同时也根据其自身的结构生成实践、信仰、感知、感觉等。根据布迪厄的分析模型,术语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受到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惯习影响。讨论个体行动者的惯习,对中医术语翻译规范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考虑作者的惯习。与文学作品不同,术语来自不同典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每一个术语的背后有一个作者,而这些作者的认知结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惯习亦不相同[9]。如上文所述,中医术语不仅涉及中医场域,也涉及文学场域、哲学场域、民俗场域等。也就是说,中医术语的生成受到多种场域的影响,而身处不同场域中的作者会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秉性和风格。这就造成了中医术语翻译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风格不统一。基于这种认知,要构建中医术语翻译规范,就要着重考虑不同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以便使其特征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其次,要考虑译者的惯习。在翻译场域中,译者是从原语到目的语之间的中介,译文的面貌最终取决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者对于译者的影响[10]。而惯习对译者的影响,最为显著。有的译者强调术语翻译的民族性,主张用拼音翻译术语;有的译者强调翻译的目的性,主张借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术语;有的译者强调受众的接受度,主张用异化的方式翻译术语。中医术语翻译场域中,译者惯习所造成的差异和冲突,是文学翻译场域中所不常见的[11]。要构建统一的中医术语翻译规范,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译者惯习的影响,或者说译者惯习应服从术语翻译规范的要求。最后,要考虑目的语受众的惯习。翻译的目的是交流,没有考虑目标受众的翻译活动是不完整的。中医术语翻译规范必须考虑具体文化场域中的受众,他们的文化习惯、历史背景、审美偏好、禁忌等。总之,在中医术语翻译的规范构建中,行动者要充分考虑术语的作者、译者和读者的惯习。
3 结语
中医术语翻译是中医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中医术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讨论上,而术语翻译规范和标准化研究还有待加强。在翻译实践中,各种不同的译本仍在同时被使用,造成交流和传播的困难。为促进中医术语规范构建,不仅需要对具体术语进行纵深的探讨,也需要从社会学、传播学、叙事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审视影响中医术语翻译规范构建的因素及其背后的原因。中医翻译研究者应从多学科研究的角度,重构中医术语翻译规范,从根本上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