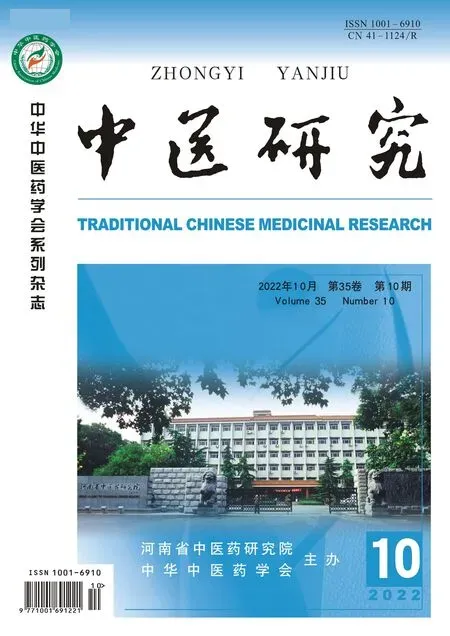高翔教授“守正化瘀浊”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学术思想探析*
王雪霞,高 翔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8)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属于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病因尚不清楚,病变常累及直肠、结肠黏膜及黏膜下层,临床症状多有反复发作的腹痛腹泻、黏液血便。根据临床表现,UC可归属于中医学“泄泻”“久痢”“痢疾”“肠澼”“腹痛”“肠风”“便血”范畴。西医学认为,UC发病原因错综复杂,也与自身免疫相关,治疗起来往往迁延难愈。高教授认为,UC病因实为脾肾阳气先虚,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可获良效。脾肾阳气的正常对机体的健康非常重要。《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温病条辨》曰:“伤脾阳,在中则不运痞满,传下则洞泄腹痛。”叶天士言:“久病不已,穷必及肾。”脾肾阳气同源同用,脾阳虚则肾阳乏后继之滋,命火虚衰,则脾土不温,运化失职,导致泻利。汪讱庵言:“久泻皆由命门火衰,不能专责脾胃。”有研究已经证实,中医药配方加减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特点,是中医药治疗UC的优势所在[1]。基于此,笔者将升降气机、健脾和胃、温补脾肾贯穿于UC治疗的各个阶段,又根据病情的具体表现和不同阶段采用清热化湿、调气行腐、养血润燥的治疗原则。
1 升降气机肠气通
人体气的运动具有升、降、出、入4种基本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失去协调平衡,各种病理变化则出现;升降出入休止,生命活动亦终止。与升降密切相关的脏腑是脾胃,《临证指南医案·脾胃》曰:“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清气在下则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故UC 的治疗可以考虑从脾胃气机恢复着手。UC病位在肠,《灵枢·本输》曰:“大肠、小肠皆属于胃。”《素问·五脏别论篇》曰:“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临证指南医案·脾胃》曰:“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用各殊也。”胃肠之腑通降正常,方可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通降失常则百病由生;故有“六腑以通为用”之说。高教授在治疗UC时重视气机的升降有序,临证多用六磨汤之类理气方加减,主治因寒热互结所致气机升降失职,胃脘不适等。六磨汤见于《世医得效方》,由木香、枳壳、槟榔、大黄、乌药、沉香组成,具有导滞行气通腑的功效。《本草纲目》中记载:“木香乃复气之药,能升降诸气。”而大黄、枳壳、槟榔合用可强力攻积导滞、通腑泄泻;木香、沉香、乌药合用可提高疏肝理气止痛的功效。郭子霞等[2]临床研究已证明,大黄可有效减轻上消化道出血症状,其中的没食子酸等成分可促进创伤部位血小板的聚集,凝血而止血。此外,大黄还有活血止血的功效,能缓解 UC 患者肠道溃疡出血、血便症状,临证常需加减灵活运用。高教授将六磨汤作为主方治疗腹泻腹胀症状明显的UC 患者,疗效较好。
2 健脾和胃肠运达
UC脾肾阳虚为本,正虚邪恋是病程迁延不愈的本质。饮食入胃,脾主升清,则大便正常;若脾阳不足以升清,则反生泻。李杲《脾胃论》中记载 “内伤脾胃,乃伤其气……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3]。高教授临证多用黄芪建中汤、香砂六君子、参苓白术散化裁。
黄芪建中汤出自《金匮要略》,关于该方治疗脾胃系疾病的文献很多,主要治疗胃肠炎、便秘、消化性溃疡、腹泻。王春艳等[4]研究发现,黄芪建中汤具有保护胃黏膜、调节胃酸分泌、降低胃蛋白酶活性作用。高教授认为,治疗UC时恢复脾胃的功能与顾护脾胃不受攻伐非常关键,故用黄芪建中汤加减化裁治疗阳虚腹痛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显著。香砂六君子汤出自《古今名医方论》,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党参可抗溃疡,对胃黏膜损伤有对抗作用[5];白术具有抗应激性溃疡的作用[6];茯苓富含多糖类物质,可起到抗肿瘤、提高免疫的作用[7];法半夏可通过减少胃液分泌,帮助胃黏膜的修复,防止溃疡及消除胃部炎症[8];陈皮抗炎及促消化的作用显著[9]。参苓白术散首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疗证属脾胃虚弱的消化系统疾病,如李东垣所言:“脾胃虚则百病生,调理中州,其首务也。脾悦甘,故用人参、甘草、薏苡仁;土喜燥,故用白术、茯苓;脾喜香,故用砂仁;心生脾,故用莲肉益心;土恶水,故用山药治肾;桔梗入肺,能升能降。所以通天气于地道,而无否塞之忧也。”研究证实,参苓白术散能使肠黏膜 NLRP3、NF-κB mRNA 表达下调,肠黏膜 MUC2、TFF3 mRNA 等基因蛋白表达上调[10],同时提高肠道 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数量,发挥肠道黏膜免疫功能[11]。
3 温补脾肾肠化用
UC病程迁延难愈,属“久痢”范畴。病位大肠,与脾肾关系密切。“久泻无不伤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肾阳是气、阳之元,主司二便的排泄,大肠的传导须赖肾阳的温养、肾气的固摄。张景岳提出“肾为胃之关,开窍于二阴……肾阳中虚,命门火衰,阴寒独胜而致洞泻不止”[12]。UC泻痢日久,损脾伤胃,终累及肾,或者初起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脾阳失养,致脾肾阳气俱虚,关门失固,下痢滑脱难禁。高教授认为,脾肾阳气的恢复是UC病情转机的关键,故治疗当重视温脾暖肾、涩肠止泻,还需兼顾升提阳气。可用四神丸、附子理中丸、真人养脏汤加减。四神丸是《证治准绳》中的经典方剂,组成为《普济本事方》中所载的二神丸(补骨脂、肉豆蔻)和五味子散(五味子、吴茱萸)组成,具有温肾健脾、涩肠止泻作用,临床多用于治疗脾肾阳虚之五更泻。四神丸可通过降低某些蛋白表达以降低破坏机体炎症体系的重要通路,如TLR/MyD88 信号通路,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上调白细胞介素(IL)-10和干扰素(IFN)-γ水平,抑制激活 TLR/MyD88信号通路,从而有效缓解 UC 的炎症反应[13]。理中汤出自《伤寒杂病论》,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附子理中汤,有补虚回阳,温中散寒之效。姬培震等[14]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附子理中汤治疗大鼠UC,可通过抑制大鼠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IL-8、IL-1β和核转录因子B 的分泌释放,发挥其减轻炎性反应、保护肠道黏膜和调节免疫的作用。真人养脏汤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主治久泻久痢、脾肾虚寒证。有研究[15-16]发现,真人养脏汤可多途径降低肠道黏膜通透性,增强肠道上皮细胞黏膜屏障功能,发挥对UC的治疗作用。韩莹等[17]发现,真人养脏汤对缓解轻、中度活动期脾肾阳虚证UC 患者的临床症状疗效尤著,能有效降低UC的疾病活动指数,提高临床疗效。
4 清热化湿肠浊除
UC的症状之一是泻下黏液血便。“湿多成五泄”,《类证治裁》中“由胃腑湿蒸热壅,致气血凝结,夹糟粕积滞,进入大小肠,倾刮脂液,化脓血下注”。《杂病源流犀烛·泄泻源流》曰:“泄虽有风寒热虚之不同,未有不源于湿者也。”均说明了湿邪为患是泻痢的重要病因。由此可见,治疗UC时清热除湿的重要性。党全伟等[18]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有清热除湿作用的清热除湿方能够治疗30 g/L硫酸葡聚糖钠盐诱导的UC疾病,保护结肠损伤,其可能是通过降低组织中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因子的含量,从而降低结肠黏膜炎症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UC急性期往往有湿邪为患的症状表现,高教授临床多用白头翁汤、连理汤化裁治疗。白头翁汤出自《伤寒论》,为热毒血痢之良方。现代研究表明,白头翁汤可以抑制数种炎症细胞因子如IL-1、IL-6、TNF-α、IFN-γ的合成表达,促使肠道细胞的免疫平衡,利于肠道黏膜恢复正常微生态平衡[19]。连理汤出自《证治要诀类方》,该方作用正如《医略六书》载“清阳敷布,而寒滞自化,升降如常”。高教授认为,脾升胃降正常是胃肠疾病康复的关键,故用连理汤治疗湿热错杂的UC患者每获良效。
5 调气行血肠腐祛
《素问·调经论篇》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互用互存,生理上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病理上互相影响。在《医贯·血症论》中有“血之所以不安者,皆由气之不安故也”的说法,《医林改错》曰:“久病必有瘀……气血阻滞肠络失和而血败肉腐成脓。”现代医学研究[20-22]也证明,UC肠道多数呈高凝状态,活血化瘀药的运用既能改善组织瘀血状态,又可增强创面的抗感染能力,利于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创面血管再生和细胞增生分化,从而改善UC肠道缺血状态,加强组织营养供给,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高教授正是在临床中发现UC中后期多气血运行异常,常用芍药汤合连理汤、六君子汤加减。芍药汤出自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其治法总结为“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药物组成以气血并治,兼以通因通用为特点,可配合香连丸行气止痛,注意加减六君子之属,重在气血同调、化瘀祛腐、顾护正气,升提脾胃阳气,临床获效显著。
6 养血润燥肠燥安
津血同源,气血互存,久痢伤津则伤气耗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伤则血损,叶天士创建了脾胃分治理论,在《临证指南医案》明确提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久病便血必虚,便血日久,津液气血亏损,补益气血莫过于补益多气多血之阳明经,势必要养血补血、滋阴润燥方能安养脾胃。因此,高教授遇UC日久有伤阴血症候时多增液汤合四物汤化裁。增液汤是滋阴增液的常用方,四物汤为行气活血的经典方,在蔺氏《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记载:“凡跌损……且服散血药,如四物汤之类。”“凡损,大小便不通……且服四物汤。”“如伤重者……或四物汤,通大小便去瘀血也。”[23]清代莫枚士《经方例释》曰:“《局方》取此方中地、芍、归、芎为一方,名四物汤,治一切血热、血虚、血燥诸证。”[24]高翔教授化用经典,临证发现UC患者久病气血多虚,故见久病患者,辨证而用,补血滋阴,常有佳效。
7 小 结
UC迁延难愈,发生发展复杂多变,虚实寒热错杂,但总归是病位在大肠,病机不离脾肾阳虚,及至后期,伤气损血,影响患者正常生活。也因其临证多变,更需深思处方,临床诊疗需谨察寒热虚实转化,多法联合应用。脏腑虚实、寒温偏盛、气血的虚实与UC发生发展及症状表现息息相关,故其治疗上要辨虚实寒热,再辨气血,又要考虑病位病机的脏腑特点。高教授临床多年治疗UC,辨证论治临症化裁有迹可循,以期为中医药治疗UC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