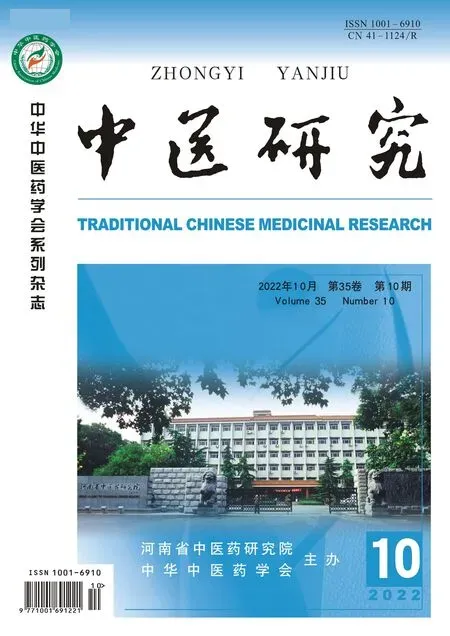基于“同病异证”的肺系疾病代谢组学运用*
张晨曦,王海峰
(1.河南中医药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 450046;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代谢组学是对生物细胞和组织中的小分子代谢物(相对分子质量<1 000)进行识别、量化和剖析,鉴定可能改变细胞或生物体表型的生物标记物的一门学科[1]。近年来,学术界积极探索代谢组学的功能特征,并将其用于解决多方面的关键问题,如疾病的发病机制、药物治疗与发现、营养问题、农业问题、环境毒理学和微生物进化等[2]。中医药在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多靶点、个性化、兼容性、毒副作用小等优势,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3]。然而,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不断进展,中医药诊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成为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证型差异的代谢组学研究能将中药药理与代谢组学技术相融合,筛选不同证型背景下的差异代谢物,寻找疾病的标志性生物分子,为临床诊疗和评价方药疗效提供科学依据[4]。笔者总结概括了代谢组学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运用与发展,着重突显“同病异证”理论指导下的代谢物差异,旨在为中医药治疗肺系疾病提供理论依据,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技术不断进展。
1 代谢组学研究进展
1.1 代谢组学概述
组学包括多个重点领域,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表型组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等[5]。这些组学通常基于使用高通量分析方法和生物信息学对生物样本进行全局分析,并可能提供对生物现象的新见解[6]。代谢物是细胞的基石,代谢组拥有大量能够预测机体性状的信息[7]。代谢组学是对病理生理或基因修饰等刺激产生的生物体代谢物质动态应答的定量测定,该概念于1999年由英国帝国理工大学Jeremy Nicholson教授首次提出[7]。代谢组学的最终目标是对生物体内低分子的综合研究,生物和环境因素如药物治疗、营养、生活方式、遗传影响或疾病等均可导致体内代谢物的时间动态变化和物种改变,因此,代谢组学为研究机体内在变化和外在表达提供了巨大的潜力[8]。代谢组学研究的工作流程包括样本采集、样本制备、化学分析/检测、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和生物解释等。代谢组学要求代谢物筛选要有非选择性(扩大检测覆盖面)、检测过程步骤少且快速(检测到尽可能多的代谢物质)、步骤可重复性、代谢终止(使用低温、加酸或快速加热阻止代谢终止)。目前,代谢组学技术参与疾病研究已涉及心脑血管及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等多个方面,确定能够诊断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标志物,寻找药物作用的通路[9]。有研究通过液质色谱-质谱法(LC-MS)联用技术,对健康人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血浆样本进行检测,结果得出胆碱能系统、能量代谢,以及氨基酸、脂质通路可能参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10]。有学者通过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分析对比抑郁症患者的血浆标本,发现草酸和硬脂酸组合有望作为诊断抑郁症的生物标志物[11]。Debik J通过核磁共振(NMR)发现原发性乳腺癌患者中期和晚期阶段的血清代谢物对预测患者的生存期有显著意义[12]。Dong S[13]使用LC-MS技术分析尿液样本,证明能量和氨基酸代谢通路及磷酸戊糖通路参与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病理过程。
1.2 代谢物检测平台
在数量众多的代谢物中,只有少数可以从全局分析中识别出来,极少数可以从目标分析中识别出来,经常进行定量分析的代谢物数量更少[14]。因此,代谢物的数量和结构多样性构成了检测和注释方面的一大挑战,其结果准确性和真实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谢组数据存储库和相关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15]。代谢组学技术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平台,即NMR和质谱(MS)。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有4种技术被广泛应用,即NMR、LC-MS、超性能液相色谱-质谱(UPLC-MS)和GC-MS[16],这4种技术彼此并不冲突,而是在所覆盖的生物面上相互补充和延伸,为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代谢领域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方向[18]。目前,NM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氢谱和碳谱两类原子核的波谱,NMR 数据在很宽的动态范围内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和定量性,对于确定未知物的结构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无需复杂的样品制备或分级分离,但具有较低的相对灵敏度和有限的动态范围。NMR所适用的样本较为广泛,如血清、血浆、尿液、脑脊液、唾液、滑膜液、羊水、腹水,以及各种组织提取物如肿瘤、大脑、肌肉[17-18]。MS是一种测量离子质荷比的方法,因其具有高特异性和高灵敏度,且操作简单,检测样本量少等特点被广泛用于能源、化工、医学等多个学科,常与色谱技术相连用,如LC-MC和GC-MC,此两者具有敏感性强、覆盖率高的特点[15]。大多数疏水性且极性大的物质如有机酸类、核苷类、核苷酸类物质使用LC-MS进行分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脂类和可衍生分子的分析是使用GC-MS进行分析的[19]。然而,无论是LC-MS还是GC-MS,都存在着相似的缺陷,其分离技术的关键性、样品制备的必要性(如蛋白质沉淀和衍生化),以及分析特定基质的难度会降低其重复性,增加该平台的工作和时间要求[20]。除此之外,代谢物检测范围可分为靶向与非靶向[21]。两者相比,靶向分析主要是为了支持一个特定的生物学假设,涉及识别和量化有限数量(数十到数百)的已知代谢物或一组代谢物,涉及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代谢途径,这种靶向代谢与临床中通过化学检验对体液、血液中的小分子测量十分相似[22];而非靶向方法可以对生物样品中所有的代谢物进行全局检测,提供了确定新生物标志物的潜力[23]。
1.3 样本收集与数据处理
代谢物质具有动态性演变、复杂化、量大多样的特点,又易受内外因素干扰,因此,对样本的采集和处理过程要求规范、严谨、科学,如血液、尿液等临床样本要严格统一样本采集时间、工具及储存条件等。根据研究类型的不同,样品准备包括一些中间步骤的组合会有所区别,主要差异体现在代谢淬灭、样品储存、代谢物提取等过程[24]。尿液、血液、唾液、细胞、组织和培养液等均可作为生物样品应用于代谢组学中[25],当需要对尿液等含水生物流体样本进行分析时,通常需要经过离心、稀释,特别是啮齿类动物的尿液样品,需要蛋白质沉淀来保护色谱柱。对于血浆、血清等样品来说,蛋白沉淀是必不可少的,固体样本如组织、粪便等则需要根据样品种类使用水溶剂、有机溶剂及水-有机溶剂的混合物对样本进行优化提取[26]。根据分析平台的不同对样本的处理也有差别,如LC-MS通常要求使用有机提取液对样品进行蛋白沉淀,达到停止代谢的目的,同时又能保留有意义的代谢物质;而对于GC-MS来说,样本需要提前进行化学衍生之后才能进入分析流程,这是因为样品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气相色谱分离[27]。对于所得到的原始数据,通常会进行对数转化、归一化、缺失值填补、数据清理、过滤和标准化处理[16],最终于代谢数据库相比对进行生物注释,通过主成分分析、富集通路分析等获取有效信息[28]。
2 中医证候与代谢组学
证候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关键,是疾病过程中某一病理概括,围绕证候进行辨证论治、理法立方是中医诊疗的核心与精髓。证候具有整体性、模糊性、恒动性、时空序列性、时空动态性的特点[29-30]。因机体内部的邪正相争、虚实转换、寒热互化或药物、环境、饮食等刺激而动态演变,反映疾病在不同阶段的内在病理特点和外在征象。从代谢组学观点来看,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证候反映机体内在联系和阶段性病理病机,涵盖了机体对致病因素的功能状态,属于机体内部稳态的改变[31]。代谢组学可以捕捉在内外环境影响下的机体器官、组织等产生的内源性代谢物,及其产生与作用机制[32],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特点,与中医证候本质相契合。由此,许多学者提出将代谢组学技术用于中医疾病证候差异研究,通过筛选“同病异证”背景下机体所产生的代谢物,确定生物标记物和相关代谢通路,阐明其有效性和效用机制,能够体现中医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实用价值[33]。“中医证候相关代谢图谱”为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34]。随着当前生命科学的全球化和“大数据”研发的到来,两个知识层面在不断地交融,多组学策略在中医药中的应用已经开始为中医药的本质和分子基础提供新的见解[35]。临床已有众多学者将此理论应用于实践,多集中于证型差异代谢物研究、中药复方代谢研究、特定证型代谢研究等。本文主要以肺系疾病为主展开探讨。
3 “同病异证”肺系疾病代谢差异研究现状
3.1 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归属中医学“哮病”范畴,又可称为“喘鸣”“哮吼”。因外邪入侵、饮食不当等原因诱导喉中宿痰交搏壅于气道所致。因发病机制、病理因素不同,有虚实之别、寒热之分。在临床上可分为急性发作期、慢性持续期和临床缓解期。刘世刚等[36]收集20例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的血清,采用GC-MS技术发现4-氨基丁酸、苯甲酰甲酸、异肌醇、二十四碳烷可作为哮喘虚寒证与虚热证的差异代谢物,参与β-丙氨酸代谢通路,其中4-氨基丁酸可能是鉴别虚寒证和虚热证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的生物标记物。严兴海等[37]采用NMR技术,对60例哮喘缓解期患者的血浆样本进行检测,数据显示相对于肺气虚证而言,肾气虚证患者血浆中的亮氨酸、缬氨酸、乳酸、柠檬酸等代谢物下调,而丙酮、乙酰乙酸呈上调。有学者通过LC-MS 技术对患者尿液样本进行检测,发现L-酪氨酸、4-吡哆酸可能是肾气虚证患者区别于健康人的生物标记物[38]。历代医家常说“小儿有阳无阴或阳盛阴微”,哮喘多发生于青少年时期,小儿哮喘发作期常见痰热阻肺证、外寒内热证和风寒束肺证[39]。陶嘉磊等[40-41]分别采用GS-MS/MS、LC-MS技术对痰热证小儿的尿液标本进行代谢物检测,发现痰热证与其他证型相比,草酸、嘧啶、乙酰赖氨酸、琥珀酸等有机酸、酮类化合物呈下调趋势,且与乙醛酸、甘氨酸、生物素等代谢途径有关。也有研究发现,基于GS-MS技术分析的尿液样本中,磷酸盐、半乳糖酸、阿糖醇可作为小儿肺脾两虚证和气阴两虚证的差异代谢物,参与机体能量、肠道菌群、氨基酸等代谢途径[42]。
3.2 肺恶性肿瘤
肺癌总体属于本虚标实,其病机不外乎脏腑气血阴阳亏虚,气滞、血瘀、痰浊、热毒积聚而成。采用中医药措施干预肺癌,在临床中有独特的优势。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肺癌的代谢组学研究更多体现在西医学中,但也有不少中医学者尝试将中医的证候与代谢组学相融合,力图寻找证型差异下产生的生物标记物。周贤梅等[43]通过GC-MS技术在呼出气冷凝液中发现,痰湿蕴肺证和气阴两虚证患者的代谢物有明显的差异,3-氨基-2-苯甲酰基-4,5,6,7-四氢苯并[b]噻吩和1-(苯基磺酰基)吡咯分别为两者所特有的化合物。马俊杰等[44]通过GC-MS技术对非小细胞肺癌的病理组织进行检测,发现虚证与实证相比,柠檬酸、乳酸、肌醇等含量明显上调,缬氨酸、葡萄糖、谷氨酰胺酸等化合物明显下调。陈卓等[45]通过LC-MS技术对非小细胞肺癌气阴两虚证患者的粪便标本进行检测,有11种差异代谢物可以区别于健康人群,参与癌症等相关通路。
3.3 肺炎与毛细支气管炎
肺炎是一种由多种不同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肺部感染,具有高发病率和病死率[46],属于中医学“风温肺热”“咳嗽”范畴。基于代谢组学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肺炎,发掘生物标志物有利于肺炎的准确诊断和风险分层[47]。有学者通过GS-MS技术发现,由病毒引起的肺炎风热郁肺证患儿相比于健康儿童而言,其血清中的丙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有机酸上调,而甘油、乙醇酸、氨基丁酸等呈下调趋势[48]。亦有学者通过采集患儿尿液标本,采用GC-MS平台,发现肉毒碱、嘧啶、果糖、1-苏氨酸等代谢物可作为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痰热闭肺证与风热闭肺证的差异代谢物,且两者的代谢途径有明显的差异[49]。笔者发现,关于肺炎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小儿肺炎居多,这为后续进行成人肺炎代谢组学研究提供了启发。
3.4 肺纤维化
肺纤维化是一种进行性、不可逆且通常致命的肺部疾病[50]。绝大部分患者发病原因不明,随着病情和肺部损伤程度不断的加重,肺功能进行性丧失,呼吸功能逐渐衰竭,且药物疗效有限。中医药在抗纤维化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51]。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大样本、多中心的中医证型肺纤维化代谢组学的临床研究。部分学者尝试使用LC-MS技术发现了磷脂酰胆碱、白三烯4、溶血磷脂酸、脂氧素15-epi-LXB等成分可作为肺脾气虚证为主的肺纤维化患者的潜在证候标志代谢物[52]。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可以帮助肺纤维化疾病的临床诊断,评估疾病程度,甚至进行风险预测和靶点识别,更能为今后的临床药物研发提供新思路,提高对其发病机制的认知[53]。
3.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属中医学“喘证”“肺胀”范畴,因疾病不断进展,肺、脾、肾受损所致,临床常见肺气虚证、肺肾气虚证、肺脾气虚证等虚证,亦见痰浊阻肺等实证。根据COPD的发展进程分为急性加重期和缓解期。张瑞等[54]采用LC-MS技术对60例痰浊阻肺证急性加重期的COPD患者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乳酸、琥珀酸、葡萄糖等代谢物质在两组人群种有明显差异性,且痰浊阻肺证患者的氨基酸、能量和脂肪代谢有特异性改变。以同样的技术手段对肺气虚证COPD患者的血浆进行全谱氨基酸代谢组学检测,发现同型半胱氨酸、肌肽、组氨酸、赖氨酸等多种代谢物质在患者诊疗过程中可以区分于健康人群[55]。关于COPD代谢组学的研究目前多体现在西医临床诊疗、不同发病阶段的代谢物筛选、疾病发生机制等方面,中医证候本质研究方面涉及较少。若能通过代谢组学鉴定协助COPD的证型诊断,将对COPD患者的临床诊断、个体化规范诊疗、肺功能康复等具有重要意义。
4 小 结
目前,代谢组学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其敏感性、适用性、可靠性随着科研需求在不断优化。该技术有助于确定疾病的标记性代谢物和通路,通过差异代谢物区分同种疾病的不同证型,为评价中药临床疗效和作用机制提供依据。在中医证型理论指导下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药临床诊疗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发展前景。代谢组学作为新兴的技术领域,具有广覆盖、大数据、技术先进、可选择性强、重复性高等特点。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推进,两学科领域的相互交融能够推动肺系疾病的临床诊断、疗效评价、风险预测、药物研发等多方面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为中医药的临床诊疗和广泛应用提供新思路。但目前的代谢组学技术多样,代谢物种群繁多,样本采集和数据分析各有所异,研究样本量小,尤其是在中医药领域未能得到大规模的开展,诸多问题给疾病代谢物数量、种类及代谢途径的客观化、具体化、统一化带来了挑战。就肺系疾病而言,本文主要探讨了“同病异证”导致的代谢差异,只是目前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动物实验,西医临床诊断、中药研究等方面涉及病种较少,常见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支气管炎、肺结节等疾病有待补充丰富。相信随着代谢组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中医证型、证候规范化,关于中医证候本质的代谢组学研究将会不断深化,为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