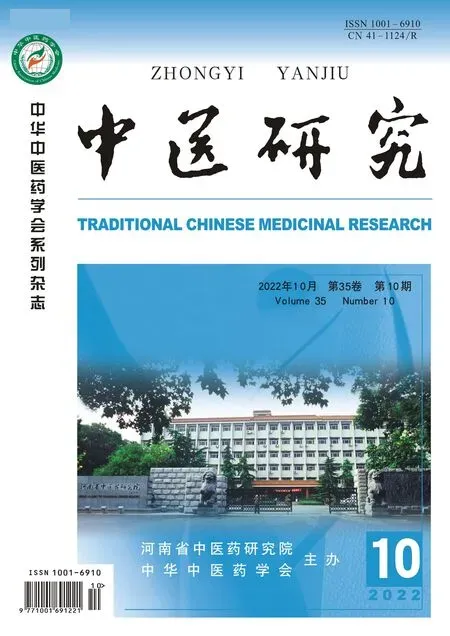胡凯文教授采用中药外治肝癌探讨*
何世阳,孙宏新,姜 敏,胡凯文
(1.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河南 新郑 451191;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3.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 100078)
胡凯文教授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博士生导师、附属东方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他首次将肝癌的中医外治手段与现代肿瘤介入、消融技术相结合,首倡肝癌治疗领域“绿色疗法”[1],在肝癌的治疗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肝癌是指原发于肝脏的恶性肿瘤。我国每年肝癌新发病例占全球的55.4%,病死病例占全球的53.9%。肝癌发病隐匿,进展迅速,致死率高,已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切除治疗、微创介入、化疗、内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等。早期肝癌患者以手术切除治疗为主;中晚期患者以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消融为主,综合靶向、化疗、免疫药物及中医药治疗。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肝癌治疗的临床疗效及生存期有一定改善。然而,我国有近七成肝癌患者初诊即为中晚期,且多并存乙型肝炎、肝功能差、肝脏失代偿、腹水、黄疸、门静脉癌栓等复杂因素,其治疗效果差,生存期短。因此,如何有效逆转这一困境,重新认识、探索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模式尤为必要。众多学者将目光重新聚集在中医药治疗上,利用现代肿瘤介入、消融技术结合中药内服外治,带动肝癌治疗手段创新,在缓解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然部分学者对中医药理论、实践认识不足,对中医相关治疗如肝癌外治的理法方药、内外治的地位、与现代治疗手段的结合等方面存有异议。笔者曾有幸跟随胡教授学习,亲见胡教授采用中药外治恶性肿瘤尤其是肝癌,可快速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减轻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现以胡教授所创之“绿色疗法”为突破口,对胡教授采用中药外治肝癌展开探讨,以释众疑。
1 理论溯源和创新
中医外治历史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中“有诸内必形于诸外”为其首论;清代吴尚先在《理瀹骈文》中提出“内治之理,即外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认为内外治殊途同归[2],奠定了中医外治的地位。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医外治理论不断更新,实践手段如穴位贴敷、脐疗、离子导入、红外线、磁疗等不断增加,效果突出[3]。胡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外治的临床研究,将中医外治与肝癌的病因病机充分结合,逐渐探索出集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系统的、独具特色的肝癌外治理论体系。
1.1 对肝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胡教授认为,认识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癌需深刻理解肝脏的生理特点,据此探索肝癌外治的关键因素。中医学理论认为,肝五行属木,主升,主动,喜条达,恶抑郁,不耐阻塞,故肝主疏泄,宣畅气机;肝居下焦,属阴,肝又藏血,体阴而用阳,主气,主血,调畅气机,通利血脉。故气为全身动力之源,气可行血,气可行津,气虚、气滞、气逆等均可导致气机不畅、升降出入失常,进而导致血瘀、湿滞,化热、成毒,瘀积于肝,久之成肝癌[4-5]。胡教授强调,在整个肝癌的致病因素中,原动力最重要,即肝气功能。肝气为病理第一要素,气机阻滞则血瘀、湿滞、毒聚,这些新的病理因素进一步影响气机,导致枢机不利,上下内外升降失常,形成恶性循环。临床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肝癌内治如此,外治同样重要。因此,治疗肝脏相关疾病尤其是肝癌时应以治气为先,只有气机通畅,气血津液运行无阻,周流全身,才能最终达到内外平衡,肝癌可控可治[6-7]。
1.2 对治则的认识
基于肝气在肝癌发病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胡教授认为,治疗肝癌应以治气为第一位,以活血、祛湿、清热、攻毒为辅,气虚则补,气滞则行,气逆则调,气机调畅,则血可行、湿可化、热可清、毒可解。胡教授强调此为肝癌治疗的总核心,以此为指导进行内外辨证,用药无差。肝癌内治法根据辨病、辨证原则将肝癌分为气滞血瘀、湿热蕴毒、肝肾阴虚、肝郁脾虚等;外治法同样注重辨证和辨病论治,讲究阴阳、虚实、寒热及三焦分治[8]。中医外治更侧重于攻邪为主,扶正为辅,临床多着眼于气滞、血瘀、湿滞、毒结等,予以破气、化瘀、祛湿、攻毒等诸药,达到快速行气、活血、利水、止痛等功效,同时结合血管介入、氩氦刀、射频消融等微创方法,达到尽快控制肿瘤的目的。
2 组方规律
基于对肝癌病因、病机及治则的全面深刻认识,经过临床长期验证,胡教授针对肝癌外治制定基本方,药物组成:丁香20 g,沉香20 g,细辛20 g,蟾皮20 g,延胡索15 g,桃仁20 g,芍药20 g,穿山甲20 g,薄荷20 g,生大黄20 g,生半夏15 g,冰片10 g。其处方法度严谨,有一定规律可循。
2.1 行气药、芳香类药物居首
胡教授认为,肝癌治疗以治气为先,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津行。行气药、芳香类中药走窜力强,内至脏腑,外达腠理,通行全身,无所不至,具有以气为先、以气为用之特点。临床该类药物众多,如丁香、沉香、木香、细辛、青皮、冰片等药物辛香走窜,多主肝脏,兼顾他脏,通达内外,调畅气机,通行血、津之道,使血行津行、瘀去湿化,为临床外治肝癌组方中必用药物[9]。临证时丁香、沉香、木香多用至30 g,细辛用至20 g,青皮用至15 g,能快速缓解疼痛,且未见毒副作用,相较于补气药物、滋阴药物、养血药物等可于内服药物中配备,正所谓补虚以缓图、祛邪以急速。
2.2 活血药物必备
肝癌属于“癥瘕”“积聚”范畴,瘀血阻滞为肝癌的重要病机。肝为血脏,主藏血、调血。胡教授认为,早期肝癌多因气机异常,单纯调整气机常可取得较好疗效;中晚期肝癌常病机复杂,多为气滞血瘀或瘀血阻滞,临床多出现肝脏肿大,影像学检查多提示巨块型肿瘤或肿瘤肝内多发转移,中医辨证多为气滞血瘀型,根据“血实宜决之,菀陈则除之”的理论,在行气的同时可配合活血化瘀药物,临床常用三棱、莪术、水蛭、丹参、桃仁、大黄、炮穿山甲、三七、红花、花蕊石等改善血瘀情况,不仅能够缓解肝脏瘀血肿大,还可缓解因气滞血瘀所致肝区疼痛等症状[10]。临证时,三棱、莪术可用至15~30 g,水蛭、丹参、桃仁、红花15~20 g,大黄一般用至20 g左右,炮穿山甲、三七因其贵重多适量冲服,花蕊石因其质重可用至30 g以上。
2.3 解毒止痛药物的运用
中医学认为,毒邪留滞为肝癌病因中的重要一环。中医学所谓的毒既包括今人之邪气流毒,又包括因气滞、血瘀、湿蕴、热毒等积聚形成的毒[11-12]。胡教授认为,肝癌之癌毒则倾向于后种。癌毒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可解释当前恶性肿瘤尤其肝癌晚期的病因病机现状,为肝癌的治疗提供了可行方向。临床可供选择的药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①植物根茎类,如生川乌、生草乌、生半夏、马钱子、白芷、细辛、生胆南星、白芍、薄荷、苦参、白花蛇舌草等。其中生川乌、生草乌、马钱子等本身有较大毒性,不可内服,外用量少难以取效,故多加大剂量,临床可用至15~30 g,研末分次外用;生半夏、细辛、生胆南星等内服有毒性,外用可适当加大剂量,可用至15~20 g;白芍、薄荷、苦参、白花蛇舌草等本身无毒或有小毒,内服、外用均可,外用时可加量至30 g以达到辅助止痛等作用。②动物及虫类药物,如守宫、乌梢蛇、土鳖虫、蟾蜍、全蝎、蜈蚣等[13]。该类药物本身有大毒,多不可内服,外用可不受内服之限制,临床粉碎外用可达到非常好的解毒止痛作用,可用至20~30 g而无毒副作用。在临床治疗中,以上这类药物本身虽具有一定毒性,但用于疾病有解毒散结止痛的作用,正所谓以毒攻毒之法。
2.4 软坚散结药物的运用
中医学认为,瘤者,留滞不去之谓。胡教授遵循《素问》“坚者削之,客者处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治瘤原则,认为软坚散结为肝癌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软坚散结药物多质地坚硬,通行内外,水陆俱行,且味咸,咸能软坚,用之可达以坚攻坚之意,同时可得祛湿化滞之效。临床常选用龟甲、鳖甲、龙骨、牡蛎、炮穿山甲配合行气活血药物使用,该类药物通常无毒或小毒,其用量可用至30 g左右,同时可适量加入青蒿、夏枯草作为引经之药以增强疗效[14]。
针对肝癌外治,胡教授强调,外治基本方有其自身规律,行气药物、化瘀药物、解毒散结药物等多为必用药物,方可保证基本功用,临床在此基础上可根据阴阳、寒热、虚实调整相应药物比重,随症加减。热毒盛者可于基本方中加龙胆草、白头翁、黄芩、黄连、栀子、连翘等清热解毒药物,湿滞明显者可于基本方中加茵陈、泽泻、苍术、黄柏、薏苡仁、茯苓、猪苓等祛湿药物,同时药力欠缺部分于内服方中补足[15]。总之,该基本方及其加减方临床运用广泛,临床凡是符合肝癌如下特征均可使用:①影像学检查符合肝癌特征或术后病理确诊为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癌者;②符合影像学特征及甲胎蛋白(AFP)明显增高,临床AFP>400 μg/L,持续2个月以上者;③CT或彩超检查提示肝脏占位,症状表现为肝区胀满、疼痛,体格检查可见肋下肝脏肿大、压痛、肝区叩击痛,伴或不伴腹水、黄疸等患者;④具有上述症状行保守治疗或配合中药内服治疗者;⑤恶病质状态、预后差的患者。
3 药物特色
胡教授临床用药特色鲜明,主要表现为辛用、生用、毒用。
3.1 辛 用
基于对肝气理论的深刻研究,胡教授结合辛味的特点,认为辛可破气,辛可通滞,辛可止痛,辛可散结。其中代表药物为细辛、冰片。
细辛味辛性温,专入肾,兼入肝、胆。《本草求真》曰:“味辛而厚,气温而烈。”李时珍言:“气之厚者,能发阳中之阳也。”该药可行气、散寒、止痛,为诸经尤其是肝肾经止痛之佳品。胡教授认为,细辛外用可内通外达,引领诸药直达病所。临床有“细辛若单用……多即气闷塞不通者死”“细辛不过钱”之说,对此,胡教授临床外用细辛至20 g左右,未见明显异常[16]。冰片辛、寒,专入心、脾、肺经。《本草求真》言:“冰片专入骨髓……体热而用凉。”较其寒性,其辛更甚,可内入骨髓引邪外出,故疮疡痈肿、热郁不散可用之。胡教授曾解释冰片之用,肝癌晚期多以热毒为多,痛入骨髓,疼痛难忍,临床使用大剂量吗啡控制且不理想,而冰片之辛可入心、入骨髓,寒可祛热毒、止痛,故临床外用药多以此为佐,可明显缓解肝癌灼热、疼痛等症状[17]。肝癌外治中,细辛、冰片多配伍使用;若肝癌表现为热毒壅盛,适当加大冰片比重,反之则减少冰片用量或不用。
3.2 生 用
顾名思义,生用即药物生用、鲜用。胡教授指出,药物生用、鲜用最能保持药物原始本性,发挥出最大的药用效果。代表药物为生半夏、生胆南星、生川乌、生草乌。
生半夏味辛温,有毒,归肺、脾、胃经,《药性本草》谓其“生者摩痈肿,能除瘤瘿”,《珍珠囊》载其“消肿散结”,临床主要用其消肿散结、止痛等。相较于制半夏,生半夏毒性更大,临床按毒性中药管理,针对肿瘤细胞坏死亦优于其他炮制品。该药内服达到一定剂量可中毒,故不用于内服[18]。外用生半夏可适当加大剂量,未见相关毒副作用,且具有控制肿瘤生长、止痛等显著功效[19-20]。生胆南星味辛温,专入肝、脾、肺经,《药性本草》谓其主“癥瘕”,《开宝本草》载其“破坚积,消痈肿”。该药辛可散风,性紧而毒,凡疝瘕结核、水肿不消,得以攻逐,以其性紧急迫而坚自去[21]。胡教授临证时尤其擅长将二者生品合用,因生半夏辛散并内守、专走胃肠,生胆南星辛散无内守、专走经络,二者功同而用有别,外用治疗中晚期肝癌可达到较好的抗肿瘤作用。
乌头辛苦大热,有毒,专入肝经,兼入脾经,功可搜风除湿、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长沙药解》载:“乌头温燥下行,其性疏利迅速,开通关腠,驱逐寒湿之力甚捷。”胡教授认为,川乌专搜风湿痛、痹痛,少温经之力;草乌性悍烈,仅堪外治。相对于炮制品内服而言,该药生用外治具有皮肤刺激作用,可产生麻木感,临床外用可麻醉止痛[22]。因此,临床常用其治疗肝癌晚期肝脏肿大、肝区疼痛,可迅速缓解疼痛。
3.3 毒 用
胡教授肝癌外治方中有毒药物的使用为其重要特色,如全蝎、蜈蚣、守宫、蕲蛇等。对于中药的“毒”,胡教授认为“毒”为限制和适用,超出限制和适用,产生不良反应即为毒。临床无毒药物多内服,剧毒药物多外用;中毒、小毒药物可外用,也可在合理炮制、配伍、煎煮后用于内服。
胡教授临床最常用的药物为蟾蜍。蟾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谓“蟆”,味辛寒,有毒。《本草求真》言:“蟾蜍气味辛寒……以其辛有发散之能,寒有逐热之功,外敷固见神功。”临床肝癌外用药中,蟾皮为主要入药部分,蟾蜍全物亦可入药。胡教授结合传统观点认为,蟾蜍为有毒之物,其毒强于全蝎、蜈蚣、蕲蛇等,内服因其腥臭、易刺激消化道令人产生不适,多难以接受,故用于肝癌外治,既可以毒攻毒、克制肿瘤,又可以制约燥热太过,为外治方中有效且毒副作用小的不可缺之物[23]。
4 制作方法
传统古方外用药有膏、丸、散、丹等,临床用药应博采众长,多学科开发,方便患者,提高疗效。胡教授指出,条件允许或处方固定时可请专人制膏,方便携带和使用;如无专门机器或需灵活处方时,当以现制药粉为主,混合蜂蜜、醋、姜汁、白酒等辅料,即时摊贴,省时省力。对于辅料的选用,胡教授亦强调“气”的作用,重在辛、峻、烈、重,可增进药物吸收、渗透,同时可降低外用药物的毒性。必要时,可配合艾灸或红外线治疗,以增加疗效。临床需要注意的是随时观察,防止皮肤过度刺激引起不良反应。
5 小 结
肝癌的治疗是一个长期、复杂且多变的过程,故临床治疗时要切中靶点,精准用药。对于肝癌的治疗,胡教授主张全面深刻地理解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特别强调肝虽居下焦但为气之枢纽,自气之产生、运行、消散等处,其功用无处不在,若气的功能受损,则衍生出气滞、血瘀、湿滞、毒结等病理因素,循环往复,肝癌乃成。基于此,针对肝癌的治疗首先要着眼于肝之本身,调气为先,明白这一点才能抓住肝癌病理因素中的关键环节。基本组方突出芳香类药物的作用,视证之不同灵活配伍活血、解毒、散结类药物,整体组方用药体现出辛用、生用、毒用等鲜明特色,诸药有机组合,疗效显著。此外,胡教授认为,临床所见之肝癌多为正气受损、癌毒积聚、本虚标实,中药外治偏于攻行,内治偏于补益,二者相伴而生,理论共同发展、相互补充,故临证时要处理好内治和外治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有失偏颇[24-25]。
综上所述,采用中药外治肝癌作为胡教授治疗恶性肿瘤“绿色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形成集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结合现代血管介入、氩氦刀、射频消融等肿瘤治疗技术,在恶性肿瘤尤其是肝癌治疗方面形成一种新的绿色治疗观,值得临床推广和学习[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