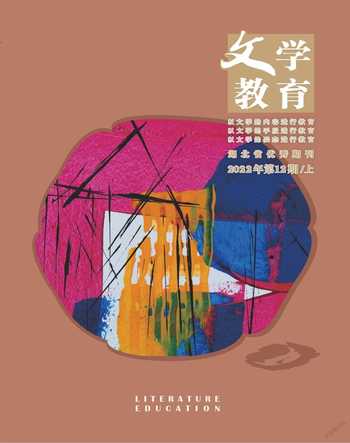刘守华“龙女”研究的比较故事学述评
尹冰雪
内容摘要:刘守华是建设比较故事学理论的重要学者,本文以其关于“龙女”研究的《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为例分析其研究特色。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方法多元:有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母题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另一方面,比较故事学虽成就显著,但也存在书面与口头、世界性与民族性无法很好融合的局限。
关键词:刘守华 比较故事学 《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
刘守华老师建设了独特的民间文学研究范式,他将我们熟悉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故事学两者结合起来,立足本体,发现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他将比较故事学定义为“广义来说……就是以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学科……对民间故事进行跨国跨民族以及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学科”[1]这样看来,比较故事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关系密切,但同时又有新的民间叙事的广阔视角。
在比较故事学领域下,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没有先后之分,并不是民间文学创造了比较文学的概念,也不是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投机地套用在民间文学学科上。“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2],刘守华老师的比较故事学研究方法就是最好的实践论证。1979年,《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发表在《民间文学》上,成为“中国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复兴的信号”。这一信号给了比较文学新的方向,也打开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征程。本文主要依据刘守华老师论文《中印龙女报恩》(《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尝试以其最早开始讨论的完整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话题——“龙女”为例,探讨其创新性的比较故事学方法是如何具体运用在故事研究中的,并试着反思比较故事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困境。
一.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
民间文学比较故事研究,需要有强大的文献资料做支撑。《中印龙女报恩》这篇针对“龙女”的文章,篇幅并不算长,但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二手资料进行佐证。
首先是一手文献,以丰富的宗教典籍为研究蓝本,为了找到“龙女”故事的出处,中国、印度佛经都是作者搜寻的对象。刘守华摘录了最早载有龙女故事的代表性佛经——《经律异相》,《经律异相》中“经律”概称佛经,“异相”相对于指示宇宙真相的“同相”,“同相”不可说,那么“异相”就是用来譬喻、说明佛法的一种方式,“经律异相”也就是佛法教义的变体。它内容宏大,包含天、地、佛、诸释、菩萨、僧、诸国王等二十二部,作为现存最早的佛学类书籍,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并不容易,再加上该文本在东晋以后翻译并流传,导致研读佛经时不仅需要钻研中国古代文化还需要溯源至印度古文化身上,极大增加了文献研究的难度。作者需要从《经律异相》中摘编出《僧祇律》《大智论》等具体有关“龙女”的章节,因此无论是查找还是阅读方面都是比较庞大的工程。除此以外,《大唐西域记》《旧杂譬喻经》等其他中印文学融合的典范都成为刘守华重点研读的文本,这些具有中印文化融合特征的佛教书籍,都是龙女故事比较研究论述的重要材料支撑。
除了前面提到的佛教经典外,还有许多其他关于“龙女”故事的一手文献。譬如有关于“龙”生态习性描述的《周易》,最早考据字源的《说文解字》。在传奇小说方面,《柳毅传》讲述了一个龙女与书生的故事,这相当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变形,刘守华表示,自此唐传奇后,中国开始了自创龙女故事。到后来有能逃脱龙王并与凡人結合的龙女琼莲(《张生煮海》,不择手段、甚至变成了报恩工具的龙女如愿(《朱蛇记》)等不过是故事形式发生了变化,本质都是在讲述龙女故事中国化。在最后涉及母题研究时,刘守华还分别从二个首次出现在《录异传》《旧杂譬喻经》中的母题——“如愿”和“祸斗”着手,谈到它们后来在《求如愿》《原化记》的演化意义。
最后是二手文献,比较故事研究法虽然排斥二手文献的不可靠,但同时也需要一些二手文献作为批判和学习的参考。譬如,刘守华虽然对白化文的《龙与中国文化》只举例文人创作,忽视民间口头文本表示质疑,但同时又十分认同白化文采用的历史演进论证方式的合理性,它能够理清“龙女”故事本土化的过程。同时,刘守华利用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分析出的具体“龙女”类型,比对中国与印度、官方与世俗的核心着眼点,使得他的研究能够更加聚焦于比较故事领域。
(二)比较研究
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指的是狭义上的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在《中印龙女报恩》中,比较研究方法表现为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互结合、共同作用。
文章第一段,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龙女”故事来源于印度佛经。刘守华老师认为“中国唐以后在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中盛传的龙王龙女故事,并非直接由古代关于龙的叙说演化而来,而是见于印度佛经的龙女故事传入中国之后”[3]。我们并不是要看这个结论正确与否,而是关注其中的论证方法。在有此确切结论的基础上,文章从第二段开始便引用事实阐述前者结论,刘守华老师选用中国东晋翻译的印度佛经故事《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作为模本展开分析。我们看看他的论证程序,首先是得出结论,然后通过大篇幅摘录原文,继而以用通俗语言复述故事的方式援引材料,最后讲述佛经中“龙女”故事的特点以及文化意义。紧接着,作者将视角转到中华民族,与前面同样的模式,用故事佐证自己的结论,然后论证该故事的特点及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核。我们可以看到,中印两者的论证方式是一一对应的,刘守华力图将印、中的“龙女”话题放到平等的地位,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影响与联系。
因此,在AA平行研究同时,刘守华老师借鉴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继续展开讨论。自从“龙女”故事由印度佛经进入中国唐宋传奇后,中国“龙”的形象再也不仅仅是《周易》《说文解字》中的简短描述,由于加入了剧情,龙女形象日趋世俗化,渐渐有了人情味,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刘守华老师具体从龙女的地位、形象以及故事叙事策略三方面叙述龙女的曲折演变,这种系统研究印度佛经演化进中国唐宋传奇的观点来自于白化文,刘守华老师虽认为白化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缺陷,但其关注两者之间事实联系的人类学视角却值得学习。最后,在历时的影响研究策略下,刘守华发现“龙女”由印度特色的宗教教化形象变成完全脱离佛教的中国本土神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这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也能够承认“龙女”故事跨国历史演进的合理性。
于是,刘守华在平行研究帮助下聚焦中、印两种具体对象,又借助影响研究的方法大胆提出中印龙女关系的假设,为接下来进一步深入地论证奠定了基础。单一流传学派那种过度拘泥于发源地的传统方法早已经过时,因此,刘守华最后采用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总结出中印龙女故事之间文化、形象与叙事这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提出关于作者本人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独特看法。
在深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时,刘守华老师需要搜集大量记载龙女故事的资料,与此同时,他发现“中印龙女比较”这个话题可以更加精确细化,可以从跨国跨文化的大视角落于某种小的主题上。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刘守华发现各民族的某些龙女故事类型都具有与印度佛经相关度极高的“报恩”内核,汉族的《张打鹌鹑李钓鱼》、苗族的《木匠与龙女》中的龙女与男主人结合都是因救命之恩,此外藏族的《奴隶与龙女》、朝鲜族的《水宫公主和农夫》等无不与此类型相关。因此,刘守华更加肯定,中印比较故事的研究策略应该聚集于某主题中的一个小的情节单元——“报恩”的母题。
(三)母题研究
阅读《谈比较故事学的方法》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看刘守华把母题研究作为相关理论的重点。他首先引述刘魁立对“母题”的概述,赞同母题是“内容叙事的最小单位”这个概念,但同时借美国学者阿姆斯基的观点,将母题作为含糊、多变、易被滥用的概念之一。为了消解这种模糊性,刘守华老师努力划分“母题”在民间文学以及比较文学中的不同,以及“母题”和“主题”两个细微概念之间的差异。这样将“母题”细分并明确为“情节单元”后,它自然而然成为了故事形态构成的基本性元素。作为最小的核心单位,母题成为比较故事学研究方法的重点,它从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最后刘守华老师得出结论:比较故事学中的“比较研究也就可以从分析母题入手了”[4]。那么回到本文主要讨论的“龙女”话题,看看刘守华老师在《中印龙女报恩》中是如何具体表现母题研究的。
刘守华老师首先根据摘取的佛经故事原典将“龙女”故事分为两类,一类是龙女报恩,龙女一般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偿还救命之恩,以《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为例;一类是龙女爱情,这种爱情的最大阻碍多数是因为存在阶级壁垒,以《沙弥于龙女生爱遂生龙中》等为例。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龙女”故事类型好像更多,依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收集的故事类型主要有“感恩的龙子和龙女”(555型),“乐人和龙王”(592A型),“煮海寶”(592A1型),此外还有“螺女”、“百鸟衣”这类派生的亚型[5]。刘守华老师在文章伊始就指出中国“龙女”故事来自印度佛经,于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就得研究从佛经演变至中国民间故事的链条是什么,也就是研究中印两民族“龙女”故事的最大契合点是什么。刘守华研究发现,以《僧祇律》为例的“报恩”母题代表了印度佛经中龙女故事的核心,而从有“中国民间故事总集”之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判断出得与佛经故事最接近的是“感恩的龙子和龙女”这一母题,通过《张打鹌鹑李钓鱼》这些具体的例子,刘守华老师确定了结论:中国“龙女”故事中“报恩”母题来自印度佛经故事,并从印度故事中吸取艺术滋养[6]。
在论文末尾,刘守华老师继续延展了“母题”这一话题,呼吁人们重视母题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龙女故事虽从佛经中发展而来,但最终形成过程也经历了长期演变,逐渐融合了中国本土特色,在这个长期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的变化就是各种母题的逐渐加入。以“如愿”和“祸斗”两个母题为例。“如愿”最早出现在中国周秦典籍《录异传》中,是属于中华民族本土的母题,然而随着“龙女”故事在民间流传,“如愿”母题和“龙女”故事合二为一,明话本《朱蛇记》中的形象便是例子。另外一个母题“祸斗”首先来源于《旧杂譬喻经》,属于汉译佛典的元素,唐代以后,该母题与“龙女”故事渐渐融合,这一实例可以在传奇小说集《原化集》中找到, 以其中的一篇《吴堪》为主要代表。刘守华老师认为,中国“龙女”故事与佛经故事有所不同的因素有很多,除开文化背景是最深层次原因外,母题的不断加入便是导致两者差异的最直接原因。
(四)文化研究
前面我们提到的比较故事学研究方法,无论是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还是母题研究,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
研究民间文学的大家似乎都将文化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终点,例如刘守华老师欣赏的丁乃通先生就非常关注民间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以及现代发展。由于民间故事正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因此比较故事学研究方法最终都会从跨国跨民族比较回归到背后的文化根基上来。
《中印龙女故事之比较》的前文大篇幅都是印度佛经和中国民间“龙女”故事的引用和简单讲述,但刘守华老师显然不仅仅停留于此,在结束两者的平面叙述后,总结性地提出了中印“龙女”故事的三大不同特征:第一是龙女地位的不同,第二是龙女形象的不同,第三是叙事形式的不同,而这三个总结性的要点最后都归结在了文化价值方面。刘守华老师详细讲述了三个差异后面对应的不同文化背景,在印度,“龙”属于畜类,而且由于宗教因素被当做宿业未尽的罪孽象征;相反,中国将“龙”尊为神族,最高统治者是龙,所有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是神圣高贵的代表。除开这些神话和宗教背景,刘守华老师在论文中继续说,“龙女”形象还被长期压抑着的中国女性们拿来作为宣泄不平等的力量符号,是自由、抗争、智慧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同一故事类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会拥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在刘守华老师眼中,跨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并不是最终目的,挖掘故事背后的民族文化才是他的创作意图,这也是比较故事学的核心。正如在《中印龙女报恩》这篇论文中,我们清楚看到作者在文末做了中、印对比的总结,但我们细看这个差异总结后发现,作者不像是对前文所有论述的归纳,而是在说明“龙女”故事在不同地域产生差异的民族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向故事的讲述者和接受者提出疑问:文化差异是否会带来社会功能的变异?正是在这个研究上,刘守华老师给了读者新的文化领域的启发,这使我们发现,中印两地的宗教观、叙事观以及女性观等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截然不同的意识体现,探究背后文化原因并预见带来的社会演变才是比较故事研究的最后目的。
二.《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的困惑
(一)书面与口头的偏移
在比较故事学研究领域,学者们都明白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相结合的重要性,然而往往因时代或自身局限而无法将两种研究方法很好地统一,对大部分学者来说,能够专注于书面或口头其中之一就足有成就了。但是显然这对比较故事学的发展是不够的。刘守华老师虽在民间文学领域成就巨大,可是其早期的比较故事研究也存在书面与口头发生偏移的问题。
从《中印龙女报恩》中我们能明确看到刘守华老师对口头文本更加“高看”一眼。他在原文中这样说:白化文的《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可惜的是它只限于从文人创作的传奇小说中来考察这个故事的演变,完全未涉及见于民间口头创作,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大量龙女故事,其内容便显得不够完整”[7]。对于白化文研究只关注文人文本,而不是民间口头文本,刘守华老师表示质疑,在“龙女”故事流传这一问题上,他始终坚信这是跨国演变和中国本土人民传播共同影响的结果,学者们在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正是中国众多民族的口头文本传播才给予了龙女故事不断更新活跃的空间。
我们看到刘守华老师始终不断强调口头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发现这里存在矛盾,这个矛盾在《中印龙女报恩》中体现为作者始终在空洞地得出“口头文本是重要的”这一结论。论文虽多次提到不能忽视口头文学,但是全篇文章论述却都是围绕书面文本展开。作者无论引述的是印度还是中国“龙女”故事都来自古早的由知识分子汇集的典籍,这些当然并不属于真正的口头文学。我们显然知道作者内心是明确赞成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作用的,但是我们也明白,可能是为了消解口头文本论证不足带来的争辩,作者必须用结论性的话语反复阐述口头传承的重要性,却又始终拿不出实际行动。
然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间口传文本体系庞大,诸多因素都给研究造成了较大阻碍,学者们不得不屈服于无法掌握口头文本的困境当中。“对于以口传文本为主,文献记载不成体系的中外常见故事类型来说要梳理出比较完整的传承路径远比顾领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复杂。”[8]因此,学者们一方面知道口头文本的研究需要提上日程,一方面又不得不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导致研究停滞不前。于是,一边引述书面文本进行论证,一边在结论中高喊口头文本十分重要的矛盾便诞生了。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刘守华老师及八九十年民间文学研究的诸多学者身上,也存在于一直影响至今的比较故事学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使比较故事学研究面临难题,但也正因如此才值得去突破。毕竟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才是比较故事学发芽的肥沃土壤。
(二)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天平
由于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学派还没完全建成体系之前,提倡跨国比较也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这也成为了局限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难题。20世纪末,刘守华老师创造性地提出了这种将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结合起来的比较故事研究法,但是,时代的局限并不能使人们立马转头去关注这种新兴学科,大多数学者依旧将视野停留在国与国之间,而忽视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当人们过分去强调广域的“世界”,而忽视个性的“民族”时,就会渐渐丧失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丢掉比较故事学研究方法的初衷。
在刘守华老师用比较故事学方法探究的“龙女”故事时,我们从中看到了明显的世界性。他以宏观的视野从中、印两个民族入手,在文章第一段就早已提纲挈领地说明中国“龙女”故事源于印度,继而在展开的论述中挖掘两者文化内涵。这种广域的视角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存在:印度佛经对中国传统故事是否真的如一些学者所说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显然这还有待商榷。因此,当我们普遍把眼光看向全球时,是否也可以停下来,把眼界“窄”一点,试着思考一下本民族文化,或许会别有收获。
虽然,我们知道刘守华老师的研究是关注了民族性的,但是,与前面同样的问题,刘守华老师的民族性论述在这篇论文中只关乎思考,没有化归所用,仍旧是从法国、美国学派那儿吸收来的跨国视角,是陈旧的比较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局限。根据前面“书面与口头的偏移”部分,我们能够发现刘守华老师始终强调活跃在中国民间口头的那部分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在他心里,民族性的文本内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守华老师一再强调,现今龙女故事的成型是民间大众进行长期融合传播的结果。他认为“龙女”故事虽然来自其他民族,但却是在本民族的创造下变得更加丰满,本族人民的补充流传才使得“龙女”成为世俗的民间故事的一员。但另一方面,刘守华老师根据当时主流研究,潜意识地将视角放在大的跨国范畴,消减了他要强调的民族本土功能,使天平发生了细微倾斜,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总的来说,刘守华老师当时的这篇论文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突破,正如本文前面说过的,作者已经极大强调了民众本土的、世俗的力量,无奈时代无意识造就的局限,导致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全面。这为当代比较故事研究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告诫它在总结前人经验时也要批判地学习并创新,以期能够探索出一个更合理、更科学的比较故事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第4页.
[2]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页.
[3][6][7]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1999.
[4]刘守华.谈比较故事学的方法[J].民族文学研究,1995.
[5]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7,第191、206、209页.
[8]漆凌云,周超.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述评——以“求好运”故事研究为例[J].民俗研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