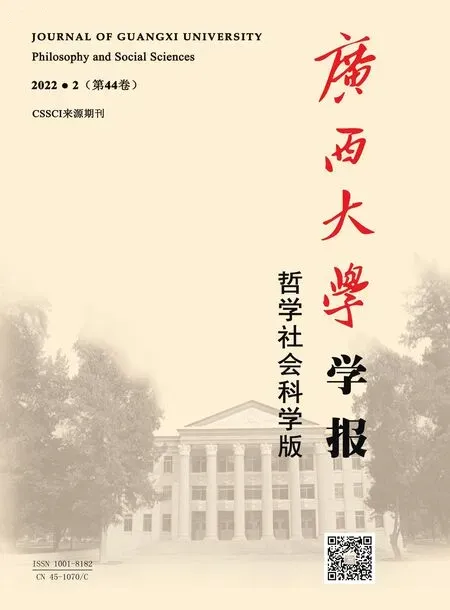道德秩序与理智秩序同一的精神诉求
——基于儒家修身观念与阿道哲学诠释的共文化性分析
陈群志
在论及天人关系时,道德秩序与理智秩序的同一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人不仅是道德的存在者,也是理智的存在者。然而,理智的、哲学论说的、道问学的“求知”的方式与道德的、哲学实践的、尊德性的“成仁”的方式如何获得一致性,一直是个需要深究的问题。西方有所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中国有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大体都属于这样的论域。与此相关的延伸论域就是理论和实践如何统一、知行如何合一、心性与天道如何合一的问题。
在当代法国哲学家中,米歇尔·福柯解释希腊化-罗马哲学时考虑过“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①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4 页。但对他而言,“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仅仅是对话、阅读、注释和书写等的趋求结果,而不是必然前提,不是一种先天存在根据。②陈群志:《阿道与福柯的修身哲学之争》,《世界哲学》2015 年第6 期。然而,皮埃尔·阿道的思路则不同,他指出,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神圣精神”的追寻与“生活技艺”的操持也是始终如一的。本体(“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既是工夫(对话、阅读、注释和书写等操持工夫)的上达目标,也是工夫的存在根据,工夫与本体是合一的。③阿道:《关于“自我修身”观念的反思》,陈群志译,《世界哲学》2017 年第4 期。就如王阳明所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功夫的,方识本体。”(《传习录拾遗》,第3 条)④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3 年版,第390 页。
余英时在《天人之际》中说,阿道所言的“精神操存”(exercitia spiritualia/exercices spirituels/spiritual exercises)(因阿道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诠解此术语,故而本文汉译为哲学含义的“精神操存”,⑤“操存”即宋明儒家所谈“操持存养”的意思,与阿道所使用的“exercitia/exercices”含义比较相符。参阅朱熹、吕祖谦所编《近思录》中的“存养”一卷,详见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4 年版,第243—302 页。此外还有宗教含义的“精神操练”可供选择,均可简称为“神操”,①陈群志:《“神操”概念的古代起源与当代转化——以阿道的修身哲学为中心的诠释》,《哲学与文化》2021 年第3 期。前者涵摄于宗教的“灵修论”,后者涵摄于哲学的“工夫论”②阿道着重分析了古代和早期基督教有关“精神操存”的区别和联系,他用exercices spirituels 这个词来解释希腊文askêsis 一词,这与中国哲学中的“工夫”(修身、修行与修炼)概念非常接近。参阅何乏笔:《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阿道与福柯修养论之差异》,黄瑞琪主编:《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63 页注释②。)的功能在于不断“自我转化”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但要如何提升呢?阿道提出了两条“似相反实相成”的修身之路:一条属于内向性的“自我和良知的省察”,一条属于外向性的个人“与宇宙的关系和‘我’的扩大”。③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Paris:Gallimard,1995,pp.303-314;英译见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M.Chase,tran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8-206.余英时由此指出,第二条修身之路恰好能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相会通。④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215—216 页。实际上,不仅是第二条修身之路,第一条修身之路同样能够与中国古人的合一论相应合,因为内在的反省(心灵秩序)与超越的归宿(宇宙秩序)是同体的。只是,我们还需要思考,个人修身为何要上达“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上达。
一、道德秩序(实践理性)统摄着理智秩序(理论理性)
在《何谓古代哲学》中,阿道说:
我很乐意接受,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哲学是一种理论的和“概念化的”活动。然而,我也相信,在古代,正是哲学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制约和决定了他们哲学论说的根本倾向。我也认为,这是一切哲学的最终真相。当然,我并不是指,哲学家由一种盲目的、任意的选择所决定,我指的是,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反思由“令理性感兴趣的东西”激发和指引,换言之,是由生活方式的选择所引发。⑤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p.410;英译见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p.272-273;中译见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296 页。译文根据法文本与英译本有所改动。
由是看来,阿道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见解:第一,哲学是一种理论论说的活动,但哲学家的生活实践决定了理论论说的倾向;第二,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生活方式的选择指引着哲学的反思活动。表面观之,阿道似乎并未言明道德秩序与理智秩序的同一,而是表明道德秩序(实践理性)要优先于、决定着、统摄着、指引着理智秩序(理论理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道也提示说,他“乐意接受”哲学自古至今都是一种“理论”(概念化)活动,只不过这种“理论”(概念化)活动与生活方式的“实践”选择相一致,前者受后者的指引与决定。从这个角度看,道德秩序(实践理性)和理智秩序(理论理性)是同一的。因此,阿道主张,哲学修习不仅是理智上的,也是精神境界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本身就包含某种不可或缺的论说方式”。⑥阿多:《古代哲学:伦理抑或实践?》,《古代哲学研究》,赵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6、207 页。
如果与宋明儒者相较,阿道的看法与朱熹正相反。朱熹虽说要在知处求行,在行处求知,但他认为“致知”在先,“践行”在后,人要“践行”必须先“致知”,并且,知行不仅分先后,而且也分轻重,论先后则知为先,论轻重则行为重。⑦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87—88 页;周天令:《朱子道德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版,第47—49 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8—320 页。换言之,朱熹走的是一条“由智成德”的思路。⑧周天令:《朱子道德哲学研究》,第357—373 页。不过,朱熹的观点却与胡塞尔很类似。胡塞尔说:“不管怎样,认识的理性是实践的理性之功能,知性是意志的仆从。但是仆从在自己本身中执行指向认识构成物本身的意志之功能,而认识构成物正是到处引导意志,为它指出正确目的和道路的必要的手段。认识的意愿是一切其他意愿的前提,如果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形式的话。”①胡塞尔:《第一哲学》(下册),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276 页。胡塞尔虽也赞同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但还表明理论理性的认识是前提,知在先,行在后。而阿道的思路与朱熹和胡塞尔都不相同,他倾向于“由德成智”的构成理路,认为理智秩序(理论理性)是由道德秩序(实践理性)所指引的,道德秩序(实践理性)才是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阿道倒是很接近王阳明的看法,如阳明之言: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传习录》,第25 条)②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64 页。
阳明门人徐爱对此概述说,先生之教开始时让他摸不着头脑,后来修习既久反身实践,才知“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③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54 页。众所周知,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但在“知行合一”中,“知”是道德本体,“行”是操持工夫,道德秩序(实践理性)优先于、决定着、统摄着、指引着理智秩序(理论理性)。阿道提出“实践逻辑学”“实践物理学”“实践伦理学”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想说,道德和理智的修习或者说德性与智慧的修习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原本就是同一的,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激发着理论论说。
当然,阿道并没有贬低理论论说的价值,而是认为,哲学家的理论论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理智秩序(理论理性)中涵摄着道德秩序(实践理性),道德秩序(实践理性)的选择影响着理智秩序(理论理性)。就此而言,哲学论说也非常重要。阿道区分了两种“论说”方式:第一种是内在的论说,主要是与自己或门人弟子对话。这种对话往往涵摄着具体的实践活动,也会与自身的生存处境联系起来,所表现的自然属于“精神操存”。第二种是外在的论说,它特别涉及某些抽象的形式结构,尤其是与之相关的理智化内容,一般的哲学史会比较关注,比如普罗提诺的三本体学说。④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p.172-179;Arnold I.Davidson,“Introduction:Pierre Hadot and the Spiritual Phenomenon of Ancient Philosophy”,in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A.I.Davidson,ed.,M.Chase,trans.,Oxford/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p.26-27.而在古代,哲学家被称为哲学家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生命存在的基本态度,各派哲学家都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来与自己进行或内在或外在的对话,都会表现出对某种生活风格的选择。
再有,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辩证法作为建立理智秩序(理论理性)的方法论就与实践活动的“精神操存”分不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逻辑工具,更是一种运用在伦理学论域及其他学科中的批判规则,并常常应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比如作出是否对错、可疑不可疑等的判断。在这个范围内,辩证法就要求人的理性与自然的理性相匹配,进而避免错误的判断。严群对柏拉图的辩证法有如下描述:
辩证法的形式是问答,内容是分析和综合。他的回答不是通常谈话间的问答,乃是深层次的,所谓分析和综合的问答。这种问答表现深刻的思想作用,包涵系统的名学(按:即逻辑学)程序,所以便成一种做学问的工具。这方法背后所根据的是思想,所以它把思想加于官感之上——以为官感所告诉我们的,不过是事物的外表,不是可靠的知识,只是无常的意见;惟有思想才能穿进事物的中心,才能认识宇宙的本体,给我们的才是可靠的知识。⑤严群:《柏拉图及其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0 页。
与亚里士多德稍有差异的是,对柏拉图而言,哲学本质上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所根据的就是思想,它奠定了对话本身的可能性。哲学原本就是在活生生的对话中共同探索而形成的真理表达。“真正的辩证法,作为哲学之专业,绝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对这种理论的运用;活生生的哲学乃是一种永恒的、审慎的关注,为的是在思想与论说中一直守持那关于实存之精准表象。”①阿多:《古代的哲学、辩证法、修辞学》,《古代哲学研究》,第170 页。如此看来,斯多亚派的辩证法(逻辑学)也依然保持着柏拉图辩证法的特征,辩证法(逻辑学)在他们这里是一种“精神操存”。
至于在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普罗提诺那里,辩证法虽然脱掉了对话的外在形式而变成了一种独白,但在内在精神上依然是作为哲学的最高部分,专注于“理型世界”,使我们从事理智的沉思,向着最高的神圣境界攀升。在《论辩证法》中,普罗提诺说:
辩证法是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哲学还有其他部分。哲学借助于辩证法考察物理世界的本性,就像其他技艺要借助于数学一样,尽管自然哲学在语言使用上与辩证法的关系更密切。同样,道德哲学的沉思源于辩证法,当然还要加上德性和产生这些德性所必需的训练。……辩证法和理论智慧以一种普遍而无形的形式为实践智慧提供一切可用的东西。②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卷),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1—32 页。
至此,道德秩序(实践理性)与理智秩序(理论理性)的同一依旧可见。除了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视为“工具”或“技艺”,古代的大部分哲学学派都将其视为一种哲学,辩证的实践活动带有一种生存的意蕴,是走向神圣理智的自我认知。阿道在考察了辩证法与哲学的关系之后指出:“哲学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理论,即使当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试图成为一种纯粹理论时,也仍然是以一种具体的生命抉择而献于理论。换言之,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就总是意味着转变——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转变。”③阿多:《古代的哲学、辩证法、修辞学》,《古代哲学研究》,第179—180 页。
二、由工夫(操持工夫)上达本体(宇宙理性)的修身诉求
孔子说:“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下学”是学技艺、学人事,“上达”是达天道、达天命,如果依宋明儒者的解释,“下学”的关键是“去人欲”(克己),“上达”的指向是达“天理”(达道)。朱熹引程子语:“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158 页。不过,“上达”都在“下学”之中,古代的圣贤教化世人,就“下学”的工夫说得多,“上达”的本体(道体)说得少,只因本体不易领悟和把定。如在论及“阅读”的操持工夫时,谈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实际的具体“操存”往往是以“游于艺”为最先,以“志于道”为最后。这是就工夫处来说本体。《传习录》中记载:
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传习录》,第24 条)⑤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62—63 页。
回到古希腊-罗马哲人的教诲,与儒家哲学相似,作为一种“工夫论”的修身实践,对话、阅读、注释、书写等这样的操持工夫当然不是“精神操存”的最终诉求,而是上达“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所运用的方法,工夫(操持工夫)必须与本体(宇宙理性)相应才能达至“堪比神性”的至善。在《蒂迈欧篇》行将结尾处,柏拉图说道:
人要是沉溺于欲望和虚荣,所作努力不外于此,他的所想所要都是可朽物。就可能性而言,他不可能不成为可朽者,因为他所培养的都是可朽性。但是,如果他心思意念乃是爱学问和真智慧,并首先训练的就是这个方面,那么,他就一定会想到永恒和神圣的事。而且,他会把握住真理,从而充分地把握人性中所隐含的永恒性。因为他总是热心于培育他的神圣部分,使他的指导者在良好的居所居住,这样,他就将是最幸福的。(Timaeus,90b-c)①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 页。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精神操存”,是因为人都有欲望和虚荣,气质中都会有污浊的那个部分,要“爱学问和真智慧”,就需要“变化气质”,反己修身,训练灵魂中最高的那个神圣部分,使之与宇宙和谐一体。②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p.108;英译见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66.也就是说,人只有借由操持工夫来控制自己的思想,训练自己的理智,“把握人性中所隐含的永恒性”,进而符合于“宇宙理性”的总持状态,才能得到非凡的幸福。应该看到,柏拉图是想告诉我们,惟有灵魂的纯化才能达至精神的不朽、精神的永恒。理智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至善,“精神操存”却能让我们获得至善。
在《斐德若篇》(Phaedrus,249e)中,柏拉图认为,灵魂一旦堕入身体,就会认识不到可知世界中的一切,即不会知晓真理、正义和智慧。然而,在《会饮篇》(Symposium,210a-212c)中,他认为要对“爱”的体验加以引导,从“爱”身体到“爱”灵魂、“爱”知识,进而达至永恒之美。借由“爱”的体验,灵魂即可孕育出德性本身(212a)。哲学于是就成了一种生活体验、一种生活实践,从对所爱之人的体验上升到对超越境界的体验。因此,灵魂由此“精神操存”而实现净化,上达神圣本体。
精神操存事实上能够由大量不同的哲学论说证明是合宜的,以便描述和论证那些生存密度最终逃离了所有旨在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经验。例如,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出于各种不同的、几乎是对立的理由,劝告自己的信徒这样去生活——总是意识到死亡临在,使自己从对未来的忧虑和过去的负担中摆脱出来,关注于当下瞬间。但是,践行这种凝神修习的人,用一双新眼看见宇宙,仿佛自己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见它那样。通过自己当下的享用,他发现生存和世界在非常时刻的壮观和神秘;同样,他经验到引发忧虑和烦恼的事物是如何地相对,从而获得宁静。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派都有各自理由,劝勉他们的信徒把自己提升到一种宇宙的视角,投入无垠的时空中,由此改变自己的世界观。③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pp.414-415;英译见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p.275-276;中译见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99 页。译文根据法文本与英译本有所改动。
阿道此言通览了古代包括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派在内的学者上达“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他特别关注“当下”的体证,犹如禅宗的“当下即是”或“直下便是”,所谓“即时豁然”“自心顿现”④详见慧能:《〈坛经〉校释》,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8 页。之说。王阳明亦谈及“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传习录》第187 条)⑤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68 页。,“当下具足”(《传习录》,第189 条)。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70 页。综合言之,我们能借由“当下”的瞬间直觉,领悟到内心具足的那种内在的德性本体或永恒的神圣智慧。阿道依据希腊化-罗马哲学常常谈到“活在当下”的概念,只因“当下”一词在古代备受关注,无论是斯多亚派还是伊壁鸠鲁派都是如此。⑦Hadot, The Inner Citadel: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M.Chase,tran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1-143;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p.197-198.
实际上,阿道特别揭橥的这个“活在当下”,显然是对一般的欲望生活的净化和超脱。它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作为过去和未来分界线的抽象时刻,而是真实的内在时间经验,是现实的“精神工夫”,由“当下”顿悟宇宙与世界的美妙和奥秘。①陈立胜也曾专门谈到阿道的这一论说,如其所言:“诚如Hadot 指出,常惺惺之精神、‘关注当下’时间取向乃是斯多亚学派的‘一个基本精神态度’,亦是‘精神修炼的关键所在’,它让我们从激情之中摆脱出来,毕竟激情或是由留滞于心的过往情节,或是由萦绕于怀的未来算计而造成的,而正是因此系于过往或未来的激情,心灵才不得自由,亦不能合理应物。通过这种基本时间取向意识的不断训练,最终我们会与宇宙意识合一,接纳每一个生存的当下。”(陈立胜:《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 年版,第172—173 页。)何乏笔认为:“‘当下’也意味着阿道所谓的‘醒觉’,意谓发现自我,并且超脱某种含有私欲的异化状态。若要实现‘当下’则必须透过自我反省的工夫,尤其是‘良心的省察’。‘醒觉’首先是指对‘自我的双重性’的体会,即现实中作为情欲奴隶之我与理想中与‘普遍理性’合一之我(圣人)间的落差。可见‘当下’有‘存在的’和‘道德的’两种意涵。一方面要过更真实、更自由、更平静、更幸福的生活,而同时此生活方式也将要符合严格的道德标准。”②何乏笔:《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阿道与福柯修养论之差异》,黄瑞琪主编:《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第165—166 页。简言之,借由“当下”的反省工夫,进而上达“纯一”的理想境界。
除了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上达之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也谈及上达问题。他认为至善是超越生命的,上达至善是最伟大的事情。“人只要成了他凝思的对象,成了所有其它事物以及他的思想对象的凝思者,成了实体、理智、‘完全的生命物’,不再从外面来看它——当他进展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就近了,至善就在他上面,已经非常靠近他,照耀着整个可理知世界。”③普罗提诺:《九章集》(下卷),石敏敏译,第882 页。因此,普罗提诺提供了多种“精神操存”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上达至善:第一,类比方式;第二,否定方式;第三,肯定方式;第四,次第方式。④Arnold I.Davidson,“Introduction:Pierre Hadot and the Spiritual Phenomenon of Ancient Philosophy”,in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p.28.不过,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纯化精神,都是在给予一种实践的美德,使我们的心灵秩序能够不断地接近至善。依阿道的解释:“当普罗提诺描述灵魂朝向善的上升时,他主张,一方面有教导我们朝向善这一主题的,即理性神学论说,如类比法或否定法;另一方面,有实际引导我们到善的,即诸如净化、德性、对内心秩序的调节,总之:实际的精神修习。”⑤阿多:《古代哲学:伦理抑或实践?》,《古代哲学研究》,第212 页。
如此看来,个人修身需要上达“宇宙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和“最高善论”是势所必然。牟宗三说:“古希腊哲学一词意味‘爱智慧’。何谓‘智慧’?洞见到‘最高善’即谓智慧。何谓‘爱智慧’?向往最高善、衷心对之感兴趣、有热爱、有渴望,即谓‘爱智慧’。所以哲学或智慧学(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因此,哲学,依古义而言,亦可径直名曰‘最高善论’。”⑥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 年版,序言第4—5 页。这与阿道在《何谓古代哲学》中的“做哲学”之谈若合符节,哲人生命所共契。⑦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pp.27-34;英译见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pp.15-21.
三、由本体(宇宙理性)纯化工夫(操持工夫)的修身诉求
上节大体阐明了由工夫(操持工夫)上达本体(宇宙理性)的诉求,是一种“工夫上说本体”的论述,这个时候的本体还没有具体落实,还只是目的因,是从工夫的无限接近(上达)来谈。本节将换一种方式,从“本体上说工夫”,由本体(宇宙理性)纯化工夫(操持工夫)来谈上达的必要性,那么此时的本体就已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具有逻辑的在先性。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上,王阳明曾与弟子钱德洪、王汝中有过对话:“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传习录》,第337 条)①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381 页。其大体意思可分为两段:
(1)本体是工夫的基源,是工夫的存在根据,因而肯定“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此时本体已落实为“存在性”的本体(有心俱是实),是就本体处言工夫。工夫必须是由本体所纯化的工夫,如果没有本体作为存在根据,操持工夫必然无着落(无心俱是幻),不能离开本体言工夫。
(2)工夫是本体的实现,是本体的道德感应,因而肯定“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此时是就工夫处言“构架性”的本体(无心俱是实),本体尚未落实为“存在性”的本体(有心俱是幻),惟有借由切实的操持工夫,本体才呈现为存在着的终极实在(至善),不能离开工夫言本体。②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年版,第55 页;杨国荣:《良知与心体:王阳明哲学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年版,第192—201 页。
以上据《传习录》中的例子所论只是想说明,本体(宇宙理性)与工夫(操持工夫)在阿道的修身哲学中大体也是这种关系,“即本体以做工夫与即工夫以还本体,原是一体两面之关系”。③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11 页。在《精神操存》④Hadot“,Exercices spirituels”,in 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pp.13-58;英译见Hadot,“Spiritual Exercises”in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pp.81-125.等篇中,阿道更加偏重于即本体(宇宙理性)谈做工夫(操持工夫)的诉求,亦即如何依持工夫(操持工夫)转化灵魂而上达与善同一的本体(宇宙理性),而在《马可·奥勒留》⑤Hadot,“Marcus Aurelius”,in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pp.179-205.等篇中则侧重即工夫(操持工夫)以还本体(宇宙理性)的面目,亦即如何依据本体(宇宙理性)来纯化工夫(操持工夫)以达至德性的圆善。也就是说,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诠释,阿道在两方面都尤为注重:具体实践的操持工夫和至高至善的宇宙理性(神圣理性)。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
我们俯仰于这样的宇宙之间,乐此最好的生命,虽其为欢愉也甚促(宇宙长存,此乐与此理长存;而吾人不能长在此世间),然其为实现者既所同然,则其为乐也亦同。吾人由此所禀受之活动与实现,以为觉醒,以为视听,以为意想,遂无往而不盎然自适,迨其稍就安息,又以为希望,以为回忆,亦无不悠然自得。而以纯理为活动与实现者尤佳,思想必致想于事物之最佳最高者,由此所启之思想方为嘉想,思想与所想者相接触,相参与,而两者循合于一体。凡能受致理知对象之怎是者,才得成其为理性。于思想活动之顷间亦正思想持获其所想对象之顷间。是以思想[理性]所涵,若云容受神明,毋宁谓禀持神明,故默想[神思]为惟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如云吾人所偶一领会之如此佳境,神固万古间未尝一刻而不在如此之佳境,这不能不令人惊奇;若谓神所在境宜更佳于如此者,则其为惊奇也更甚。而神确在更佳更高之处。生命固亦属于神。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Metaphysics,1072b15-30)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248 页。
依亚里士多德,人的思想(理性)的涵摄与其说是“容受神明”,倒不如说是“禀持神明”。什么叫“禀持神明”?就是文后所说的“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此即“禀持”的所在。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位于宇宙顶层的神圣理性推动着思想的进展,而人之生命的神圣部分就是理性,就是精神的至高点,人就是要在与此神圣理性的相合中,实现超越的生活。用阿道的话说: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在灵魂之中的神圣现身,本身并不足以确保人之幸福,必须意识到这种现身,“关注”这一内心之神,根据精神提升自己的生活。这种神的现身因此便是一种对善好之爱的呼吁,也是整个存在向神圣精神进行皈依的呼吁。①阿多:《希腊-拉丁古代世界的智慧者形象》,《古代哲学研究》,第304 页。
职是之故,由本体(宇宙理性)纯化工夫(操持工夫)的实现就必然要求整个存在向“神圣精神”的皈依。尽管在普通人的识见中,甚至通过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考察,“精神操存”的品性塑造、良心审视、性情修养、意念集中等都被看作德性的标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宇宙理性”(神圣理性、普遍理性或大全自然)作为存在秩序的立法根据,那么道德的获取就常常会混杂太多的恶性因素,进而无法得以纯化。因此,惟有借由内在于人心中但却高于人的本然理性,亦即“宇宙理性”,才能把定自己是一个“德性生命”的存在。“人的生命,有正负两面。正面的是德性生命,负面的是气质生命或说情欲生命。对于正面的德性生命,要求涵养、充实、发扬、上升,以求得最后的圆满的完成。对于负面的气质生命或情欲生命,则须予以变化和节制。变化,是对气质而言,化掉气质中的偏与杂,使生命变得中正合理而无所偏,变得清澈纯一而无所杂;节制,是对情欲而言,要使情欲纳入轨道的限制中而不放纵、不泛滥。”②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 年版,第1 页。对“气质生命”或“情欲生命”的克制和驯化,对“德性生命”的涵养和升进,这种观念在晚期的斯多亚主义中,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着更清楚明白的表达。
在斯多亚派看来,幸福生活就是要过德性生活,而德性生活在于根据“自然”生活,这个“自然”就是指“大全自然”(“宇宙理性”或“普遍理性”)。塞涅卡说:“古人提醒我们,不要过最快乐的生活,而要过最好的生活;从而,不要让快乐领导生活,而要让它担任正当合宜的欲望的伴侣。因为我们必须以自然为向导;理性只倾听自然的指示,依言而行。因此,幸福生活就是根据自然生活。”③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51 页。“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有两样最好的东西随同我们前往——大全自然和我们自身的美德。”④塞涅卡:《哲学的治疗:塞涅卡伦理文选(2)》,吴欲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4 页。显而易见,在塞涅卡的表述中,人的操持工夫若想要获得至善,就必须顺应“大全自然”生活,根据“大全自然”(“宇宙理性”或“普遍理性”)的规律和模式来塑造自我,净化灵魂。
在此思想的范限下,爱比克泰德也说:“你的心里应该完全抛弃所有这些享乐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意识,意识到,你正在服从着神的意志,这种服从不是语言上的服从,而是行动上的服从,而且,其所做的事情正是一个智慧的善人所应该做的事情。”⑤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442 页。马可·奥勒留则指出:“永远把宇宙看做是一个活的东西,具有一种实体和一个灵魂。”⑥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39 页。这两位斯多亚主义的继承者还特别展现了面对不同境遇的三种态度:严格坚持实践判断的客观性;按照正义生活并服务于人类共同体;以虔敬之心接受自己作为宇宙理性的一部分来修习。⑦Hadot,“Une clé des Pensée de Marc Aurèle:les trois topoi philosophiques selon Épictète”,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1978,33:65-83;Hadot, The Inner Citadel: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p.70;阿道:《关于“自我修身”观念的反思》,陈群志译,《世界哲学》2017 年第4 期。因此,对真正有智慧有德性的趋求至善者而言,他们都关注一件事情,即如何在服从“宇宙理性”(神圣理性)的情况下完善自身,并且达至宇宙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合一。
四、结语
诚如阿道的哲学诠释,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古代哲学,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演进,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提升人的灵魂。因而,与之相关的方式是理性的追寻和精神的沉思,最终希望能够实现与神的连接,达到精神生活的至高点。依斯多亚派的哲学,人的理性是从神圣的宇宙理性流溢出来的一小部分,但它随时都可能被肉体生命、气质生命、情欲生命所污染和扭曲。“唯有智慧者方能使他的理性重新恢复完善,使之与宇宙理性相吻合。”①阿多:《希腊-拉丁古代世界的智慧者形象》,《古代哲学研究》,第225 页。因此,个人如果要成为理想人格(希圣希贤)就必然得纯化自己,上达宇宙理性实际上就是从肉体生命、气质生命、情欲生命转向神圣生命的纯化通道,也只有在这条通道中,人才能贞定自己。
陈少明在论及中国哲学形态时,也谈到阿道(陈译为哈度)的修身哲学及其“生活方式说”,认为“生活方式说”与正统的哲学史思路虽然完全不同,但却更加贴近古代的思想经验。他同时指出,阿道富有洞察地探索了西方古代哲学在“生活方式”中的呈现过程,解读人、事、物所构成的古代生活世界,这与中国哲学正可以遥相呼应。如其所言:
不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不论斯多噶学派还是伊壁鸠鲁学派,都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去实践的,即使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其哲学也不能够被归结为哲学论说或者知识内容。但是,哲学在中世纪及现代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不断趋向今天的理论化的形态。哈度强调,研究作为生活方式的古代哲学,在领会古人灵修的要旨时必须注意,对话是哲学生活的重要形式,它包括不同对话者间的对话,也包括修炼者自身的对话。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其代表。毫无疑问,哈度所描述的这种西方古代哲学图景,与中国思想传统有更多交相辉映之处。②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
陈立胜在比较儒家与斯多亚派修身问题时,特别运用了阿道在《何谓古代哲学》一书中的一个基本论断,即哲学从本质上说不是抽象的理论谈辩,而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是西方古代的斯多亚派哲学与中国的儒家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修身学方面进行跨文化“会通”的“共法”。依此,他言道:
近三十年来西方哲学界对哲学自身的“异化”现象渐起反思。福柯(M.Foucault)、阿多(P.Hadot)以及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对作为一种“生命之道”、“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精神气质的重新认识,已生“攻玉”之效应。儒学之修身学、工夫论面向渐次由学术之边缘而进入关注之焦点,学界认识到围绕人情事变、喜怒哀乐进行修身活动乃是中西古典哲学的共法。③陈立胜:《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第139—140。
综合而论,古代哲学思索的目的是转变个人的生活方式,最终要求一种“精神性”的“变化气质”,以达到个人的修身实践与宇宙理性的合一。因此,我们不仅考察了道德秩序(实践理性、尊德性)与理智秩序(理论理性、道问学)的同一,而且就“由工夫(操持工夫)上达本体(宇宙理性)”和“由本体(宇宙理性)纯化工夫(操持工夫)”两方面说明了东西方的“共文化性”特质。显然,“操持工夫”是基于个人修身的“内在性”向度而言的,但从“超越性”向度看,“操持工夫”还需要与“精神本体”相应合,才能达至“至善”和“至福”的境地。这也印证了我们潜在的探究思路,它是从关注“个人问题”(修身哲学的操持工夫)转向关注“宇宙问题”(修身哲学的道通天地),并由此上升到特别关注“天人问题”(修身哲学的凝合统一),亦即处理宇宙与个人如何达到最终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