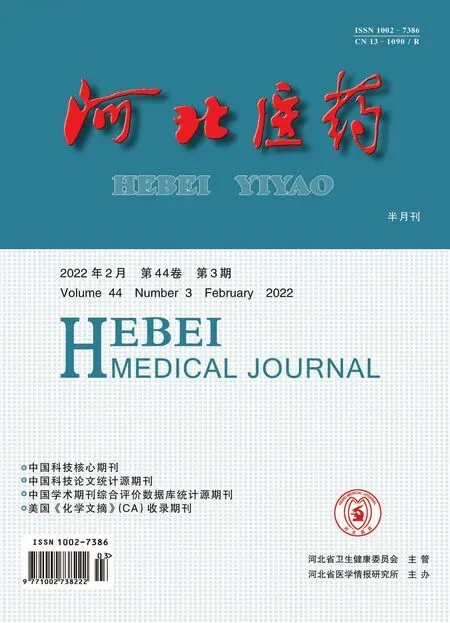肿瘤靶向药物抗体-药物偶联物的研究进展
冯恬 张慧林 童华
自第一种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于2001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批准, 进入临床研究的ADC数量逐渐增加,其对肿瘤的靶向治疗前景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ADC的发展历程
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著名的德国医师和科学家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提出了选择性作用于肿瘤细胞的“魔术子弹”的概念[1],其设想可以将抗体和具有细胞毒性的化疗药物这两种具有互补性的治疗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更高治疗窗口的高选择性和高细胞毒性的癌症治疗方法。1975年,分子生物学家科勒和米尔斯坦在自然杂交技术的基础上,创建了杂交瘤技术,从而开启了鼠源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时代[2],为抗体技术的临床应用带来了突破。但由于单克隆抗体是鼠源性,故易引起免疫原性而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随着重组DNA技术与抗体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低抗原性嵌合、人源化以及完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的相继出现降低了单克隆抗体的免疫原性,进一步推动了ADC领域的发展[3]。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 ADC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的ADC通常使用的是经典化疗药物如阿霉素和甲氨蝶呤等[4],除了药物效力不足外,鼠源性单克隆抗体的免疫原性、实际内化的药物数量少以及抗体与药物连接稳定性差等问题都导致药物疗效欠佳[5]。第二代的ADC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和治疗安全性,其中有三种新型ADC通过了FDA批准,但是脱靶毒性导致其治疗窗狭窄,而且较高的药物与抗体比率引发的药物耐受性低和血浆清除率高等问题仍然存在[6]。随着接头设计、偶联技术以及高效的细胞毒性药物等方面的发展,第三代ADC逐渐显示其巨大的应用潜力[7],目前除获得FDA批准的四种ADC外,仍有约110项研究正在探索新型ADC对多种恶性肿瘤的疗效[8],这些都为ADC作为单一药物或与经典化疗药物联合应用于癌症治疗提供了可能。
2 ADC的结构及功能
ADC主要是利用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将有效的细胞毒性药物选择性地递送至表达相应抗原的肿瘤细胞以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ADC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药物。尽管其概念简单,但是设计ADC必须要考虑各种参数,优化各组成部分,才能达到稳定、高效、安全的治疗目的。
2.1 抗体与靶抗原 ADC抗体部分的主要功能是选择性地结合靶细胞上的抗原,从而将细胞毒素集中在肿瘤部位。IgG由于对靶抗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和较长的半衰期,成为构建ADC理想的单克隆抗体来源。其中IgG1还具有较强的次级免疫功能,如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DCC)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作用(CDC),都可为肿瘤治疗带来疗效[9]。
抗体通过选择性地结合靶抗原触发抗体—抗原复合物有效内化,以发挥抗肿瘤作用。因此,适合作为靶向治疗的抗原应在肿瘤中高水平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有限表达或无表达[10]。此外,抗原有限的异质性、可及性、介导抗体有效内在化的能力以及在肿瘤治疗期间维持作为有效靶抗原的最小阈值等都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目前应用于临床研究的大多数ADC针对的都是肿瘤表面抗原,此外还有少部分药物的靶抗原是位于肿瘤微环境的基质和脉管系统中,例如作为靶抗原之一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就是在多种实体瘤的新生血管内皮上表达[11]。
2.2 连接子 连接子的作用是将毒素偶联至抗体,要求既不能影响抗体结合抗原的能力,又要能确保其缀合的细胞毒性药物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链接子一方面需要能够维持药物的稳定,避免脱靶毒性;另一方面在ADC有效地内化之后要能够迅速释放细胞毒性药物以杀伤肿瘤细胞。目前临床研究中的连接子通常可分为两类:可裂解连接子和不可裂解连接子。可裂解连接子也有三种不同的细胞毒素释放机制:(1)溶酶体酶敏感性,例如:溶酶体酶识别裂解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中的肽键后释放毒素[12]。(2)酸敏感性,例如:Gemtuzumab Ozogamicin(GO)连接子中酸不稳定基团可在低pH的溶酶体中水解后释放偶联物[13]。(3)谷胱甘肽敏感性,肿瘤细胞内较高浓度的谷胱甘肽可通过还原连接子中的二硫键释放药物[14]。第二类的不可裂解连接子则需要在抗体完全水解后才能发挥毒素的抗肿瘤作用,例如T-DM1中的硫醚键就是在曲妥珠单抗水解后释放毒素DM1发挥抗肿瘤作用[15]。另外,与可裂解连接子相比不可裂解连接子在循环中会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2.3 细胞毒性药物 细胞毒性药物作为ADC的有效载荷,对ADC的效能和活性影响很大。第一代ADC使用的是经典化疗药物,例如阿霉素和甲氨蝶呤等,但研究发现肿瘤中有效的细胞毒性药物的浓度极低,这可能与抗体的低渗透率、抗原表达受限、药物无效内在化和连接子的代谢等因素相关[16],因此,这就要求ADC所携带的细胞毒性药物至少在皮摩尔或纳摩尔浓度时就能发挥作用[17]。而在目前的ADC的开发中主要应用两类高效的细胞毒性药物:微管抑制剂和DNA抑制剂。
2.3.1 微管抑制剂:微管抑制剂主要是在有丝分裂过程中破坏微管组装,因此对快速增殖的肿瘤细胞具有相对选择性,下面介绍两种较为成熟的微管抑制剂。
2.3.1.1 Auristatins,其通过阻断微管蛋白组装使细胞停滞在G2/M期诱发肿瘤细胞凋亡,目前其衍生物MMAF和MMAE已经作为有效载荷应用到多种ADC的研发中。且MMAE由于其膜渗透性,可透过靶细胞扩散到附近的肿瘤细胞诱发旁观者效应,从而增加药物的抗肿瘤效果[18]。临床上,将抗CD30单抗与MMAE偶联的Brentuximab Vedotin于2011年已经获得FDA批准,主要用于复发率较高的CD30阳性的霍奇金淋巴瘤(HL)以及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的治疗[19]。
2.3.1.2 美登素类化合物,主要用于ADC研发的是其衍生物美登木素生物碱DM1和DM4,通过与修饰过的抗体进行二硫键交换来形成复合物,一系列相关的药物在临床研究中均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效果[20]。进入临床试验的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就是将抗叶酸受体α(FRα)的抗体与毒素DM4相连,用于治疗FRα阳性铂耐药的卵巢癌[21]。
2.3.2 DNA抑制剂:DNA抑制剂主要通过结合DNA双螺旋小沟致核酸链断裂、烷基化或交联而发挥细胞毒性作用。它的优点是较少依赖细胞周期进程,可有效地作用于生长和代谢缓慢的肿瘤干细胞或肿瘤起始细胞[17]。
2.3.2.1 吡咯并苯并二氮杂(PBD)是一类DNA烷基化药物,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PBD二聚体能够导致肿瘤细胞链内或链间DNA交联,且多耐药基因(MDR1)的产物对其作用无效,使得其在多重耐药和难治性肿瘤中仍具有良好的活性,可减少耐药的产生[22]。
2.3.2.2 卡奇霉素(Calicheamicins)能够结合到DNA小沟上并诱导DNA双链断裂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23]。临床上的Inotuzumab Ozogamicin就是将靶向CD22的抗体与卡奇霉素偶联,在2017年由FDA批准用于成人复发性及难治性前体 B细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24]。
2.3.2.3 喜树碱类药物(CPT)是通过与拓扑异构酶I和DNA的复合物结合,阻止DNA重新结合,致DNA损伤后诱导细胞凋亡。其中,FDA已经批准了两种水溶性CPT类似物即拓扑替康(TPT)和伊立替康(CPT-11)应用于ADC的研发[25]。CPT-11的活性代谢产物SN-38就是Labetuzumab Govitecan的有效载荷,其在复发性或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26]。
除此以外,其他类别的细胞毒性药物仍在开发中,例如RNA聚合酶抑制剂、RNA剪接体抑制剂等,均具有良好的研究前景。另外,将放射性核素与抗体缀合也是治疗肿瘤的一种方式,例如ZevalinR将靶向CD20抗原的单抗(替伊莫单抗)与标记放射性同位素Y90偶联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HL)[27]。
3 ADC的临床进展
目前,已经有四种ADC药物获得FDA批准用于临床治疗:Gemtuzumab Ozogamicin、Brentuximab Vedotin、Trastuzumab Emtansine和Inotuzumab Ozogamicin[28]。此外,仍然有一些新型的ADC正在实验和临床研发中,以下介绍的就是一些进展较快且成果较瞩目的ADC。
3.1 Enfortumab Vedotin(EV) Enfortumab vedotin是由完全人源的单克隆抗体通过蛋白酶可裂解链接子与微管破坏剂MMAE偶联[29]。该项ADC的靶抗原是与肿瘤发生相关的细胞黏附分子Nectin-4,其在包括尿路上皮癌,乳腺癌,胃癌和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过表达,而在正常上皮不表达或低表达[30]。Enfortumab vedotin以高亲和力结合表达Nectin-4的细胞触发MMAE在靶细胞中的内化和释放, MMAE通过破坏微管动力学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31]。Ⅰ期剂量递增/扩展研究临床试验EV-101评估了药物在治疗患有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UC)或其他表达Nectin-4的恶性实体瘤的患者中方抗肿瘤活性及安全性,以及分析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及其免疫原性[29]。实验的初步结果表明,药物在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方面显示出相当的疗效。甚至在接受过铂类化疗和(或)抗PD-1/L1免疫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患者中也能观察明显的疗效。初步确定了EV的建议剂量方案为1.25 mg/kg(最大剂量为125 mg)[32]。在之后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的Ⅱ期临床试验EV-201中,实验主要的观察终点是客观缓解率(ORR)。该研究的第一组队列招募了既接受铂类化疗又接受免疫疗法的125名患者,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44%(95%CI:35.1,53.2),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7.6个月(95%CI:6.3,不可估算)。完全缓解率(CR)为12%,部分缓解率(PR)为32%。总体数据表明,EV可产生持久的抗肿瘤疗效并具备可接受的安全性。目前针对仅接受过免疫治疗患者的第二组研究仍在招募中[33]。正在进行中的EV-301项目是一项Ⅲ期试验,其目的是在接受过铂类药物和抗PD-1/L1免疫治疗后疾病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中比较EV作为单药治疗与单药化疗(多西紫杉醇,紫杉醇或长春氟宁)这两种治疗方法的抗肿瘤效果及药物安全性。实验的主要观察终点是总体生存率,通过总体生存率来证明药物的生存获益及提供其他长期疗效数据[34]。至2020年7月,共有301例死亡(EV组134例,化疗组167例)。EV组的总生存期比化疗组更长(中位总生存期,12.88个月对8.97个月;死亡风险比0.7;95%CI;0.56至0.89;P=0.001)。EV组的无进展生存期也要比化疗组长(中位PFS:5.55月vs.3.71月,进展或死亡风险比0.62,95%CI,0.51vs.0.75;P<0.001)。2组与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3级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2组相似(分别为51.4%和49.8%)。初步结果表明,与标准化疗相比,EV显著延长了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生存期[35]。
3.2 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 15%~20%的晚期胃癌和胃食管交界癌存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过表达或扩增,因此HER2可作为免疫治疗的靶点应用于胃癌的治疗[36]。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DS-8201a)是由人源化抗HER2抗体通过可裂解的链接子与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相连的一种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其通过在肿瘤细胞中过表达的溶酶体酶裂解释放细胞毒性药物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毒素具有较好地细胞膜通透性,因此也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旁观者效应,可以不论HER2的表达量在靶细胞的细胞膜上扩散并影响周围肿瘤细胞。因此可以较好地靶向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胃癌。一项Ⅰ期临床试验探索了以推荐剂量[37]T-DXd治疗HER2阳性胃或胃食管交界癌患者的安全性和初步抗肿瘤效果。研究中有19位患者以5.4 mg/kg的剂量接受治疗,而25位患者以6.4 mg/kg的剂量接受治疗。44例患者中有35例实现了疾病控制,中位PFS达到了5.6个月(95%CI,3.0~8.3),中位总体生存期为12.8个月(95%CI,1.4~25.4)。这些结果初步表明T-Dxd疗法在HER2阳性胃癌患者中可显着改善应答和总体生存率,其中值得注意的毒性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和间质性肺疾病[38]。在之后进一步的Ⅱ期临床试验中,招募了在接受了至少两种治疗方案(包括氟嘧啶,铂类药物和曲妥珠单抗)后进展且表达HER2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交界癌患者,评估了T-Dxd与化疗药物(伊立替康或紫杉醇)相比对HER2阳性胃或胃食管交界癌患者治疗效果和安全性。187例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有125例患者进入T-Dxd组和62例患者进入化疗组(55例接受了伊立替康和7例紫杉醇),试验结果显示:T-Dxd组的客观反应患者比例显着高于化疗组(51%vs. 14%)。且T-Dxd组的总生存期比化疗组更长(中位数为12.5个月vs. 8.4个月),T-Dxd组中总共10例患者已达到完全缓解,该试验的结果肯定了T-Dxd在Ⅰ期试验中对晚期HER2阳性胃癌患者的疗效,也初步表明了T-Dxd的疗效要优于化疗组[39]。
此外,乳腺癌患者中15%~20%存在HER2的过表达和(或)基因扩增,一项Ⅰ期剂量扩展临床实验探索了以推荐剂量T-Dxd治疗之前接受过T-DM1治疗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试验对118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的115例患者进行了至少一剂推荐剂量的T-Dxd治疗,其中 111例患者中有66例(59.5%,95%CI,49.7~68.7)有确诊的客观反应,有104名(93.7%,95%CI,87.4~97.4)达到了客观反应疾病控制,中位反应时间为20.7个月(95%CI,0~21.8)。中位PFS为22.1个月(95%CI,0.8~27.9)。这些结果表明药物具有可控的安全性,并在T-DM1治疗后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显示出初步活性,且有必要在HER2阳性乳腺癌的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中进一步探索[40]。一项Ⅱ期的临床试验就研究了T-DXd对HER2阳性并曾接受过T-DM1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MBC)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患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肿瘤缩小,临床相关反应率为60.9%,中位PFS达到了16.4个月(95%CI 12.7-NE),临床受益率(定义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和疾病稳定至少6个月)为76.1%(95%CI 69.3~82.1),中位缓解时间为14.8个月(95%CI 13.8~16.9)。该试验的结果进一步肯定了T-Dxd在Ⅰ期试验中在HER2阳性的乳腺患者中的抗肿瘤活性。目前,还有三项针对T-DXd对乳腺癌治疗的前瞻性Ⅲ期临床试验正在招募和进展中[41]。
另外,令人振奋的是T-Dxd在HER2低表达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也表现出了初步的抗肿瘤活性和较好地安全性,这样的结果可能由于T-DXd具有较高的药物-抗体比率以及释放的有效载荷较高的细胞膜通透性诱导了旁观者效应[42]。除了对乳腺癌和HER2阳性胃癌和胃食管交界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方面的研究,在HER2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和HER2阳性的结直肠癌的Ⅱ期试验中,T-Dxd也引起了很高的应答率[43]。
3.3 Labetuzumab govitecan(IMMU-130) 癌胚抗原相关的细胞黏附分子5(CEACAM5)抗原在多种实体肿瘤中呈过表达,尤其是在超过80%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呈过表达,因此可作为免疫治疗的有效靶点[44]。Labetuzumab govitecan就是由抗CEACAM5的单克隆抗体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物SN-38偶联而成[45]。2017年,该药物首先在人结肠癌异种移植模型中证明了其强大的抗肿瘤效果,提供了Labetuzumab govitecan用于临床上治疗mCRC患者的证据[46]。之后在一项Ⅰ/Ⅱ期针对先前接受过伊立替康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的临床试验中,38%的患者在治疗后肿瘤大小和CEA浓度显著降低,1名患者获得了部分缓解,并持续了2年,其中半数以上的患者获得了病情稳定(SD),患者的中位PFS和OS都有所延长,分别为3.6和6.9个月[47]。数据表明IMMU-130在治疗经过预处理的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可以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48]。
3.4 Sacituzumab govitecan(IMMU-132) Trop-2作为一种细胞内钙信号的跨膜转导子,在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多种上皮肿瘤中呈过表达,通过多种生长调节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49]。三阴性乳腺癌(TNBC)与激素受体阳性或HER2阳性乳腺癌不同,其发病年龄小、侵袭性强,容易发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且可用于治疗TNBC的靶向疗法有限[50]。而Trop-2在TNBC和多种实体肿瘤中过表达,因此Trop-2可作为TNBC和其他表达Trop-2的上皮癌的有希望的治疗靶标[51]。 Sacituzumab govitecan就是一种抗体与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SN-38)相结合的靶向Trop-2的特异性的ADC[28]。在一项Ⅰ/Ⅱ期临床试验评估了Sacituzumab govitecan在至少接受过两次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mTNB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实验结果表明:在以推荐剂量接受Sacituzumab govitecan治疗的108例mTNBC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为33.3%(95%CI,24.6~43.1),其中包括3例完全缓解和33例局部缓解。中位缓解时间达到了7.7个月(95%CI,4.9~10.8),临床受益率为45.4%。中位PFS为5.5个月(95%CI,4.1~6.3),OS为13.0个月(95%CI,11.2~13.7)。通常,接受标准化疗的mTNBC患者的应答率在5%~15%,而在该试验中观察到的33%的应答率已经优于标准化学疗法。这些数据都初步证明了该项药物对mTNBC患者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52,53]。目前,该药物的Ⅲ期临床试验已经在HR+/HER2-的转移性乳腺癌(MBC)患者中开展,目的是将其与化疗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进行比较[54]。另外,还有一项Ⅰ/Ⅱ期的临床试验正评估Sacituzumab govitecan与PARP抑制剂(talazoparib)联合应用于转移性乳腺癌治疗的疗效以及患者耐受性[55]。2020年4月Sacituzumab govitecan在美国已经获得了加速批准,主要用于治疗mTNBC的成年患者[56]。目前,Sacituzumab govitecan对尿路上皮癌疗效的研究也正处于Ⅱ期临床试验中[57]。除此以外,其他研究也表明了该项ADC对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胰腺癌、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前列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都均可以起到治疗作用[58,59]。
综上所述,虽然在早期ADC的研究中,人们遇到了诸如抗体制备、新型毒素探索、连接接头优化等难题,但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力推进了ADC的发展进程。数十年来,除了FDA批准进入临床使用的药物,一些具有前景的ADC已经进入临床研究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试验结果,为其作为肿瘤患者的靶向治疗方法提供了可能性。虽然并非所有开发中的ADC药物都能从临床试验成功过渡到正式临床治疗,但是这些经验和教训都为了解药物的疗效、代谢机制和治疗安全性做出了贡献。无论是作为单一疗法治疗难治性或复发性肿瘤,还是作为姑息治疗的维持治疗手段,或者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用药作为一线治疗方案,ADC都将成为肿瘤药物研究的一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