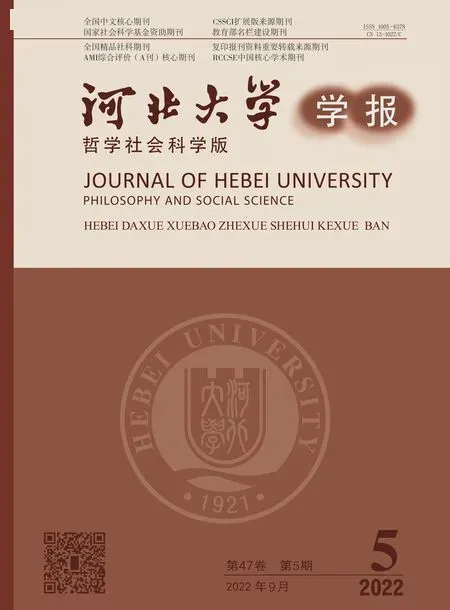李商隐古文思想内蕴及对其骈文写作之影响
况晓慢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唐以降,古文创作整体呈衰微之势。在承认这一总体趋势的前提下,还应把视角放在部分文人崇韩慕古的古文创作上,他们以韩柳古文创作理论为指导,将古文思想渗入骈体公文写作中,进而指导和影响骈文文体创新与内涵丰富,力求为古文创作寻找新的出路和更大的创作空间。晚唐李商隐虽是骈文大家,但其古文作品相较韩门弟子,水平和造诣不比他们差。本文以李商隐古文创作为切入点,对其古文作品进行分类梳理,借此剖析其古文思想渊源,探究其古文对骈文写作的影响。文中所论李商隐古文涉及论说文、抒情文和叙事文,涵盖书、序文、行状、杂文、传等文体,其他文体如赋、黄箓斋文等不在论述范围。
一、任性自然:古文分类及其思想意涵
现存李商隐文章作品中,体量较大的骈体章奏虽为后世所重,于他而言却“非平生所尊尚”,李商隐从事骈文写作前“以古文出于诸公间”,因此为骈文大家令狐楚赏识,古文才是他真正看重的文章体式。在体量较少的古文作品中,李商隐将其在骈体公文中无法表达的看法、情感通过古文展现出来,用自己专富才情的笔调传达了古文写作的态度,彰显个人写作特点。
(一)论说文笔锋犀利反传统
在仅存的两篇论说文《断非圣人事》《让非圣人事》中,李商隐以犀利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圣人行事的看法和见解。
这两篇论说文以哲学的视角考察世人常言的论断,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文章内容上,延续《上崔华州书》(“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和《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中的观点,对儒家教条大胆挑战。《断非圣人事》一文实质是指出尧、舜、禹所为与儒家教义相悖,以犀利的笔调抨击那些盲目追随儒家教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于尧、舜、禹的盲目崇拜导致他们在评价三位的行为时仅仅从“善断”的角度思考,并未从事情的本质出发。《让非贤人事》则抨击世人盲目信从伊尹、太公望,对于何为“让”并没有深入思考,“让”与“不让”之间,反衬儒家教义下的伊尹与太公望也存在不担当的人格缺陷。
这种反传统思想的缘由要从唐代“道”学成风谈起。初唐伊始,文人士子将现实环境遇到的各种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山水玄言、任性自然的黄老思想来消解。李商隐进士登科前,曾问道玉阳山,期间积累了大量的道学知识,他欣赏道家自然说,内心渴望通过老庄思想解除仁义道德的束缚,得到精神和灵魂的自由逍遥。道家提倡的自然之道与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恰好相反,这也是李商隐矛盾人格形成的原因之一。他虽深受儒家教义濡染,却在内心深处与儒家思想保有对立的空间,这是一片属于个人的独立空间,在这里,李商隐在自然的感召下任意骋怀。他认为元结之文“以自然为祖,以元气为根”[1]2256,本质上将元结之文与儒家教义撇开,以道家的自然、元气说来阐释。晚唐末世,传统文人习业儒家理论,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儒家教义俨然成了摆设。与儒家理论相较,道家将一切都归于自然,自然真实、生动的存在生息让末世文人精神上得到安慰。
(二)抒情文笔势流畅反功利
如果说韩柳古文成功的关键在于借鉴先秦诸子和史传文学的精髓,将诗赋抒写情性的特征融入新古文中,那么李商隐的古文作品更是将这情性渗透到每个字句中。李商隐古文中流露出以“情感”为主线的反功利思想。《上崔华州书》中的“直挥笔为文”与《献相国京兆公启一》提到“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1]1911-1912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人是有情感的物种,表现于文章便是将喷薄欲出的情感直接流露于笔端。从时间来看,《上崔华州书》写于开成二年(837)正月,正是李商隐第五次参加科考、荣登龙榜之时,说明李商隐早期未开始骈文写作前,已明确为文宗旨,要“直”挥笔写作。《献相国京兆公启一》写于大中五年(851)十二月,莲幕辗转的李商隐此时已心灰意冷,但是对于写作骈文这件事,他仍认为人非草木,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强调“性灵”,也就是文才,他将早期“直”的理念一以贯之,对文体的认识和把握依然遵循文体发展的趋势,不掺杂任何杂念。
最能体现李商隐真“情”流露的古文作品当属写给叔父、曾祖母、二姐裴氏的三篇志文状。三篇文章均写于李商隐母逝守孝期间(会昌二年,842),李商隐先将曾祖母卢氏迁葬怀州,和曾祖父安阳君合葬,接着把二姐裴氏、小侄女寄寄等亲属迁葬至荥阳祖坟,又另择新穴重新安葬旧坟圮坏的叔父,并请卢尚书专门为曾祖妣、处士叔、仲姊裴氏分别撰写志文状。三篇志文状虽是邀约卢尚书所作,但卢尚书写作前,在文章情感的表达上、内容的安排上定与李商隐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因此,文风与李商隐代笔文相似。李商隐一生为他人代笔,对代笔文写作应有的立场、角度以及情感表达的尺度都已十分娴熟,因此在文章内容的安排上以及内容的呈现上,代笔者将三位亲人的一生与晚唐社会的现状结合,将小人物与大社会勾连在一起。写给处士叔的志文状中,以处士叔力辞徐帅王侍中招募之请,与晚唐社会各类幕佐汲汲于通过幕主改变生活窘境、期图仕途腾达形成强烈反差,映衬处士叔高洁的人格魅力。写给曾祖妣和仲姊的文中,均提到了刘稹叛乱,将家世变迁与国家乱离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小人物在乱世生存之艰难,也反衬李商隐虽丁忧在家,仍心系家国乱离之大情怀。李商隐作为颓败晚唐的亲历者,虽未挂朝籍,整日为生计奔波各幕,却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先后追随的恩师令狐楚、岳丈王茂元、知己郑亚,都曾是朝廷重臣,这让他比一般文人多了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甘露之变”“牛李党争”“刘稹叛乱”等大事件面前,他看到了社会的颓败、朝廷的无能、藩镇的猖獗,所以,他的诗文中针砭时弊、抨击社会现实,指责朝廷腐败、君主昏庸的内容很多,由此引发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想便有别于同期其他文人。
(三)记人叙事笔法简约反驳杂
序文是全书的重点,其写作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写作缘由、经过、意图和特点等,是全书的首篇,也是全书正文部分的引子,起到统领全集的作用。《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两篇古文是李商隐为自己的骈文集所写,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也突出了古文在他心中的地位。正是在序文的指引和感召下,其骈文作品的面貌、内涵均与古文相近,也满足了李商隐刻意为古文却因现实因素阻隔而不能为的心理。
两篇序文的叙事笔法简约,以简练的语言表明结集缘由、写作心态以及文体观念。甲集开篇说道:“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1]1713,古文成就带给李商隐的自豪感可见一斑,他也提到仲弟圣仆“常以今体归我,而未焉能休”[1]1713,还提出自己的“四六文”特点: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乙集则以桂幕府罢、折返京师、选为盩厔尉、先入范阳公幕、选为太学博士、又入东川柳仲郢幕等事件为节点,以无奈落寞的笔调叙述骈文结集的缘由,指出骈文“非平生所尚”“不足以为名”[1]2177,奈何“本胜多爱我之意”[1]2177,与甲集誓要“削笔衡山,洗砚湘江”[1]1713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甲乙两集分别作于大中元年(847)和大中七年(853)。前后心态以及文体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写作目的也在发生变化,始剋意事佛,愿为清凉山行者,一派无奈、落魄、失意景象。
李商隐古文中以传记体撰写的几篇文章,韵味匪浅,文章或多或少地传递了李商隐借所叙之人为自己申诉的声音。葛晓音《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中便说:“这类人物小记在传神方面能得韩文真髓,而其简洁隽永,已有晚唐杂文小品的意味。”[2]20她也指出:“李商隐是骈文大家,古文功底却并不比韩门弟子差,由此也可见出中晚唐古文的深入人心。”[2]20他的古文大部分是向韩柳古文中的简约文风致敬。《李贺小传》兼有人物传记和唐传奇的特点。传文以李贺英年早逝对比其盖世奇才,以李贺生时未被重用对比死后得天帝赏识,中间穿插其长相、交游以及苦吟之写作经历的叙述,末尾连续六个问句,表达自己对李贺遭遇不公待遇的愤慨,言外也有对自己才华不被承认的控诉之意。《刘叉传》通过塑造刘叉重义任气、直爽落魄,既能写作歌诗、又有点无赖没品的形象,表达自己对任性随心人生的渴望,这是对落魄文人品格的重提。宋代谢采伯在《密斋笔记》卷三中说:“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白乐天墓碑》《刘叉传》,文体奇逸,不应止取其诗。”[3]864谢采伯此说实是充分认可李商隐诗歌的基础上,又对其传记文章给予特别肯定。
在古文式微、骈文复起的社会背景下,骈文的社会功用远远胜于其他文学形式,这就决定了文人写作不得不屈从于现实需求,李商隐内心也存着这种矛盾和无奈,文集在文体呈现上以古文为序,以骈文为主体内容,便是其内心矛盾与无奈的客观体现。在反传统、反功利、简约清俊的古文写作指导下,其骈文注入真情,以“能感动人”为时人所尚,古文写作的灵活技法也逐渐浸透到骈文作品中,展现于文风是骈散兼行,表现于思想则是文以明道。
二、崇韩慕古:古文创作的思想渊源
唐代中期,大量文人尝试古文创作,因过度强调革除骈文流弊,反而将古文写作引入了艰深胶滞、晦涩难懂之境。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很多古文作品专门追求新奇脱俗,以期形成迥异于骈文写作的独特风格。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4]143“奇辞”就是“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然一旦过度,便会使文字生涩怪奇;“奥旨”就是文章主题要严肃深刻,若过分强调,也会流入深奥怪奇、纠缠难解之境。韩愈较为推崇的元结和樊宗师亦是此种风格。元结散文风格与韩愈路数相近,内容偏于古奥,语言流于艰涩。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论元结文就说道:“元(结)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5]369胡氏认为元结文章不仅艰涩,还切近怪诞迂腐。樊宗师为文造句追求“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4]540,其文生造杜撰较多,艰涩难懂,韩愈却赞誉他“善为文章,词句深刻”[4]222。其他追随者如皇甫湜、沈亚之等作文风格均片面模仿韩柳且流于形式,未得韩柳精髓。这种过分追求奇崛与新变风气以及形式上的片面模仿在后期愈演愈烈,与“古文运动”最初反对骈文初衷相悖,最终导致“古文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对韩愈及其倡导的“古文运动”,李商隐当是进行了深入研究的。韩愈是李商隐较为崇拜的作家,长篇诗歌《韩碑》是李商隐为颂赞韩愈而作,诗中赞同韩愈《平淮西碑》的观点,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对平叛统一给予了高度评价。韩愈推崇的元结、李贺、李翱等古文作家,都是李商隐十分欣赏的前辈,他分别以写序、作传等方式一一表达崇拜之情,这些致敬之作都是以古文形式写成的。韩柳古文愤世嫉俗、抒怀明志,晚唐以后并无多少作家作品与韩柳古文风格相类,韩门弟子虽极力模仿,并不得其作文精髓。但李商隐早期所作古文《别令狐拾遗书》《上崔华州书》《与陶进士书》三篇,均充溢着怨愤不平之气,所述均非一般文人敢为之观点,与韩柳文章主题相同、文气相近。董乃斌《李商隐散文简论》也将此三篇与韩愈古文相较,得出三篇文章“表现出韩愈式的议论纵横、言辞犀利和悲愤激越等特色”[6]120。可以看出,晚唐诸家中,李商隐实为韩柳主张、风格之承续者。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说到的“行道不系今古”以及“不爱攘取经史”,强调文章无须援取古书经史,摘章择典,在援引故实上与韩愈“陈言务去”相近,委婉讽世。《献侍郎钜鹿公启》中提出的“属词之工,言志为最”与韩愈“文以明道”主张如出一辙,均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断非圣人事》一文中,李商隐将韩愈《原道》开篇所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4]13进行了推演和发挥。《李贺小传》中,李商隐对天帝满腔愤恨之控诉口吻,与韩愈“不平则鸣”的为文态度何其相似!
与大多数“古文运动”的追随者不同,李商隐对韩、柳古文的承继并非简单模仿,而是认真地思考韩、柳古文变革的精神实质,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理解和改造。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文学复古,看重的是文学的实际功用。韩愈《答刘正夫书》曾说:“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4]207“尚其能”与“不因循”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之前文学教义中的审美趣味,而直接表现为重功利的文学思想。多数“古文运动”的追随者,没有结合时代的发展,去认识和理解“文”与“道”之关系,只是临摹词句形式,最终落入艰涩古奥之窠臼,势必导致古文运动的失败。李商隐在接受古文运动文学主张、努力深入研习古文创作的时候,没有简单肢解韩愈之古文句法,没有单纯潜心于析句造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古文并对其进行了自觉的改造,从整体观照文章全篇,深刻理解文章主旨,勉力支持韩愈主张,深入申述韩愈理念,最终形成独特的文道观。
李商隐对古文写作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古文创作主题和文体体式的把握也始终坚持雅颂正声的初心。李商隐对韩愈虽推崇有加,但并不盲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吸收韩愈思想精髓的同时,也吸纳了古代先哲观点。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提出做文章要“直挥笔为文”,所谓“直”挥笔,便是对文学重功利思想的抗拒。这又与韩愈提倡的过分追求“去陈言”“不因循”、人为地制造生词、开辟奇句的文学现实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陈言务去”上,李商隐赞同韩愈写文章不必援引故实的做法,但也对过分“去陈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道统、仁义、圣贤的意义和内涵进行了审慎的思考,也在文章中清醒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对于“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拘泥论调,李商隐并不赞成,“常悒悒不快”。对求古道、师文法,李商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1]108在众人强调尊圣、强调师承,以为学“道”必须学古,作文必有师从的时候,李商隐却一反众论,指出:“道”并非专指周公、孔圣之“道”。周公、孔子虽是圣人,但“道”并非他们独专,是众人都能享有的。李商隐甚至坚持,自己的一己之“道”也是“道”,所以他说“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将自己与众人仰望的周孔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在当时实是一种过于大胆之见解。这种说法也是受孟子“人皆可为尧舜”、庄子“万物齐一”和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思想的影响。韩愈的“文道观”力排佛、老,《论佛骨表》以“佛不足事”为核心,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他的目的是要推行儒家教义。而李商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教义虽居重要位置,却并不排斥佛老。李商隐年轻时有学道玉阳山的经历,年老时又有遁入佛门的打算,他的思想是三家并蓄以为己用,儒释道相互调和,形成独有的一己之“道”。所以,李商隐的“道”并非韩愈以儒教为宗的“道”,他坚持的是与儒家之道并行的一己之“道”。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大中三年(847)李商隐为元结文集所撰的后序中:“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1]2257世人以元结不师孔子为非,李商隐则以为孔子固然是圣人,但也不必一定师礼待之,以此表达对元结的肯定和支持。“此书可以无书”援引《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典故,意在讽刺那些迷信圣贤、人云亦云的人,反衬元结有思想有见解。
李商隐深受周、孔儒教浸润多年,却并未一味迷信地将儒家思想奉若天理,而是辅之以释老,最终形成兼容并包的思想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于思想,是儒释道的完美结合;表现于文章,是古文骈文兼善的创作。
三、骈散相兼:古文思想对骈文写作之影响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李商隐骈文时说道:“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7]603四库馆臣注意到李商隐骈文并非一味地追求句式的整饬与辞藻的华美,其中蕴含中唐文人尤其是“古文运动”倡导者提出的恢复雅颂正声的余韵,故而评其骈文“雅饬”之称,骈文格调上远超他人。
中唐古文家对骈文改其弊有余、取其长不足。他们不是把古文与骈文看成此消彼长的文体互补关系,而是自筑藩篱,拒骈文于门外。柳宗元《乞巧文》便是以否定骈文为主旨,明确站在骈文对立面。李商隐是在经过严格的古文训练的前提下转向骈文写作的,他的骈文没有完全沿袭六朝骈文的固定套路,也没有极力回避骈文的创作技巧。他在写作时并未全盘否定骈文,而是将六朝骈体美文审美特质继承下来,并将自己对古文写作雅颂正声主题的追求、对韩柳古文精髓的吸纳融于骈文写作中,这便在写作基调上远超他人,最终形成内容充实、形式精美、独具特色的骈文作品。李商隐古文思想对其骈文写作之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情入文,情遣辞隐;二是骈散兼行,以散济骈。
所谓融情入文,情遣辞隐,是说李商隐骈文作品以“情”动人。他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一》和《献侍郎钜鹿公启》两篇骈体公文中分别以“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和“属词之工,言志为最”明确阐述了其骈文创作是以“情”为主线的,这与其古文《上崔华州书》中提倡的“直挥笔为文”的情感基调是一致的,也为其骈文创作融情入文确定了理论基础。相较韩柳古文之风范,李商隐古文中“情”的主张是不同于韩柳的说论,这份“情”既富有古文的典雅,又富有骈体美文的诗情诗意,这份诗情诗意融入文章写作,深于情,长于理,华实相扶,文质彬彬,与晚唐诸家相比,便是清代馆臣文人所说的“别格”。
李商隐骈文多为代笔文,此类文章较为程式化,最易流于形式,内容空洞苍白,难入人心,若施以真情,实为难事。但李商隐骈文中不乏真情流动之作,他以“同理心”将幕主心理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从李商隐代令狐楚、王茂元、崔戎的三篇遗表来看,遗表除贴近三位文主文风外,还真挚地表达了文主对皇帝的感恩和国家的忠心,可谓悲怆感人,令人动容。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二案语评价“四六文”时称赞李商隐骈文“意思精密,情文婉转,至义山极矣”[8]654。
李商隐《樊南甲集序》明确指出其骈文以“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为主要目的,他试图通过骈文写作达到像散文一样自如表达个人情志的目的。为了打破骈文固有模式的束缚,李商隐在骈文写作中进行个人有意识地改造,以骈文之“形”,营造内容上的“散”,从而传递真实动人的情感。最能体现李商隐骈文“能感动人”的当属其祭体骈文。祭文多为最亲近的人所作,所祭之人最能触动作者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李商隐祭文不仅将这种浓烈的亲情渲染到极致,还借祭文之悲怆引发对个人身世、漂泊经历等人世慨叹,从而使文章更加感人。被称为李商隐骈文“压卷之作”的《祭小侄女寄寄文》全文无一处用典,用日常浅白素朴之语言,以叙述之口吻娓娓道来,将自己对侄女寄寄的深厚感情全然体现。“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归大茔之旁。哀哉!”[1]830文章开篇用散体交代写作缘由,之后的段落虽以四六句式为主,但对句较少,多是上承下接的叙述语句,严格来讲,此文从形式上已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骈文,此文吸取了韩愈《祭十二郎文》散文写作的优势,用骈文形式,却以散体古文的铺陈叙述为主,实现了内容上的“散”,从而传递至真至诚的情感。《祭裴氏姊文》中,李商隐回忆“年方就傅”一段,以散体叙事方式叙家事、发悲叹,文体形式上以四六对句为主,句式却并非严整的对句结构,散体与骈体间隔出现,既实现了形式上的骈散互融,又传递了真挚情感。其他写给至亲之人的文章,或通过环境描写渲染悲戚氛围,或以回忆过去之悲伤经历更增当下之怆痛,以景衬情,怀旧伤今。悲伤往事更能激发李商隐内心郁积的情感,他利用骈文典雅的偶俪、华美的辞藻将个人强烈的情感融入其中,从而委婉地表达含蓄蕴藉、细美幽约的情愫。以上两篇文章可见,李商隐在写作骈体祭文时,没有局限于四六文固有的模式和体例,抛却官样文章的规矩与原则,以表达情感为主要目的,以真情打动人,这也是其骈体祭文动人之所在。从形式上看,这两篇文章表面上是四六文,实质上与整饬的四六文却不同,做到了四六文与散文的有效融合。
所谓骈散兼行、以散济骈,是说李商隐将中唐以来的骈散兼行之风持续推进,实现了散体与骈体互相融合,以散济骈,使文气俊逸洒脱。李商隐从事骈文写作前,深受早期古文熏染,已具备博闻强记的遣词造句能力。因此,在写作骈文时,他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套用应用文体相对固定的体式,而是根据不同文体的需求采用不同的行文方式。对于表、状、牒等官用文字,李商隐多以典故铺排,衬之以骈俪词语,表现官用文字的典雅庄重;对于渐为私用的书、启等文体,多以说理、叙事为强,李商隐则用散句穿插于文中,以使文气流畅洒脱;而对于抒情为主的祭文,则真切考虑所祭之人的年龄、身份特点,如写给恩师令狐楚的祭文,语言厚重典丽,表达对恩师的敬重之情,而写给侄女寄寄的文章,则直白晓畅,几乎都是白话,表达对侄女早夭的悲痛和怜惜。
纵观文章发展历史,自汉魏六朝以至晚唐五代,骈文和散文一直相伴而行,始终处于此消彼长之势。其实,六朝骈文初盛之时,骈文中便或穿插散句或以虚字连接对句,形成骈中运散、骈散结合的写作手法。为了达到舒逸清晰的目的,徐陵骈文写作中,墓志、铭文或碑文中常“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联语”[8]8450。倪璠《注释庾集题辞》云:“子山之文,虽是骈体,间多散行。”[8]8443也是说庾信骈文多是骈散兼行写法。孙德谦《六朝丽指》有云:“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舒逸,而叙事亦不清晰。”[8]8443这里是说若无散句穿插于骈文之中,则骈文必会形式呆板,抒情不畅,言事不明。初唐时期,“四杰”在骈文与散文文体的调和上也进行了革新。王勃《秋日饯别序》中关于秋日景色特点和悲凉韵致的描写,用的便是散体古文的简洁写法,骈句中以“之”“则”等虚字打散,转换为散句。翟兑之《骈文概论》以为:“四杰代表另一时代的骈文,而这种骈文渐渐到了化骈为散的程度”,“他们的骈文,不但含散文的精神,有时兼散文的形式”[9]8。中唐陆贽骈文则骈散自由结合,于景祥《骈文论稿》中强调陆贽骈文“散句双行,运单成复”的重要特征[10]24。
李商隐骈文在吸取前人写作优点的基础上,更加有意识地将散文与骈文进行区分,他并不局限于以单一的文体进行写作,而是尽量在骈文与散文之间作出调和。他以敏感的文体意识为骈文结集,却以不同于骈文的散体古文为序,《樊南四六》甲、乙两集的序文全以散体写成,足可见古体散文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能够了解他并非过分倚重骈文的写作心理。孙梅《四六丛话》评论李商隐习文之经历时曾言:“李玉谿少能古文,不喜声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变而为今体,卒以四六名家。”[11]663李商隐年少时先学古文,后师从令狐楚学习今体骈文,成为骈文名家。他在骈文写作上取得的成就,与其先学古文和深厚的古文功底不无关系。他的骈文深蕴散体古文的形式特点,他将散体古文的一些写作技法运用于骈体文写作中,提高了骈文的写作水平。以散体古文作序,并非只体现在樊南甲、乙两集的序文中,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李商隐以散体发端,简叙元结之生平,之后又以工整的四言对句概述元结一生所历典型事迹,至“吁!不得尽其极也”则又转为散句,首尾段散体,中间部分全用骈体。元结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多是古文(散体),李商隐为其写序之时,定是考虑到元结作文之喜好,又结合序体写作要求,采用骈中有散、运散于骈的行文方式,将元结生平、文风特点统统写进序文中,宜骈则骈,宜散则散,使文章既有散文的灵动,又有骈文的工整。《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是李商隐受郑亚所托,为李德裕文集所作序文,此篇序文整体以骈文为主,散体间行文中,形成骈散结合的形式。李德裕是力主取消“诗赋取士”的,他对骈文的态度与元结一样,都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李商隐却用骈文为他的文集作序,当是充分考虑文集作者的文体取舍的,也一定是得到他的应允的。就写作状态而言,序文创作骈散兼行的表现,足可见李商隐在文体的转换与运用上,已达到十分醇熟的状态,而这份醇熟的状态显然与深厚的古文功底影响以及长期的骈文习作训练分不开。从文体观的角度来看,李商隐在为自己和他人的文集作序时,都选择了有别于主体文体(骈文)的散文,说明李商隐有着非常敏感的文体意识,在不影响序文本意的前提下,以骈散兼行或运散于骈的方式,刻意调和骈文与散文关系,尽量发挥骈文与散文各自的文体功用,在写作实践中践行着独特的文体观。
骈中运散的另一个体现便是骈文中散体虚字的运用。虚词的恰当使用,可以调节句子间的节奏,起到或停顿或转折或承上启下之作用,还可以有效调节作者的情感走势,主观调整了文章转承的逻辑关系。较之前人,李商隐骈文对虚字的运用可谓变化多端,如《代彭阳公遗表》中虚字出现在句首:“伏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华夏镜清,是修教化之初,当复理安之始。”[1]414还有出现在句中的虚词,如《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中:“父之于子也,有严训而无责善,君之于臣也,有掩恶而复录功。”虚词“之于”强化了后一句的作用,语气上起到舒缓作用,如无此虚词,“父之于子也”就变成了“父子也”,语气上就会弱很多,后一句的作用也不会得到强化。《六朝丽指》云:“作骈文而全用俳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8]8452-8453在四六对句中,适当地加以虚字串接,四言、六言变为五言、七言、八言,可使文气舒缓动宕,避免因句式整饬而窒塞。李商隐文中,以虚字调和四六句,有五言句如:“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1]118亦有七言句如:“仍世之徽音免坠,平生之志业无亏。”[1]118也有八言句如:“虽殁者之宅兆永安,而存者之追攀莫及。”[1]815个别文章还出现三言、九言句如:“天,普覆也,应运而健若龙行;日,至明焉,有时而气如虹贯。”[1]27字数的变化引起句式的灵活转变,使文章形式上呈现错落有致的层次美,气质上显得轻灵飞动,增添自然流美之感,在呆板的应制公文中营造轻松俊逸的文风,变枯燥为流美。
晚唐时期,骈文虽为文坛主流,但受中唐“古文运动”的挤压,骈文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李商隐虽为晚唐骈文的主力作家,但他对待古文与骈文之态度,势必影响其骈文写作。现有的古文作品可见李商隐早期尊古重道,文风犀利泼辣,议论时政敢言人之不能言,在晚唐古文式微的背景下,他的古文别有风味。后期文风有了明显变化,一改犀利之笔锋,逐渐转为悲伤哀怨,想来当与彼时古文式微以及对骈文文体的主动改造有关。对于骈文的不断实践练习,让李商隐掌握了骈文的写作技巧,早期崇韩慕古的古文思想,渐渐减退消隐。李商隐一生幕府漂泊,希图以骈文举业的理想并未实现,随着理想的破灭,他对骈文的态度也变为不以为然,最后以教太学生“古道”回归“古文”而终。纵观李商隐骈文,其作品之所以丽而不伤,被清代馆臣文人评为“雅饬”“别格”,与他推崇古文、古道不无关系,散体古文的影响和融入,不仅体现在骈文作品中散体叙事模式推动的情感真切流露,更体现在形式上融散于骈、骈散兼行的写作手法,在有意识地彰显骈体美文审美特质,这也是其骈文在晚唐异彩厥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