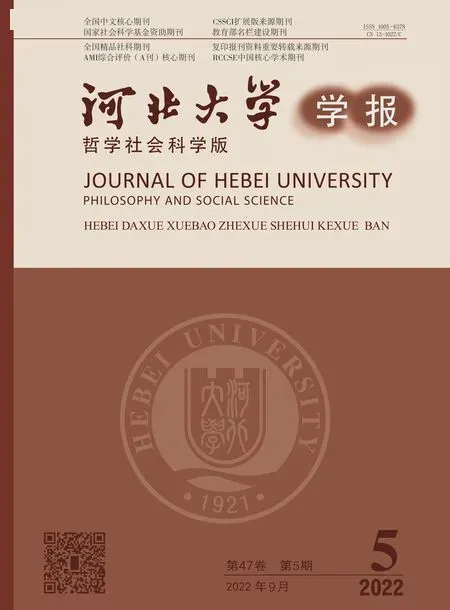恋爱故事包裹下的“自由魂”
——以茅盾早期创作《野蔷薇》为中心
黄乔生,辛 玲
(1.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 100034;2.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927年7月,因偶发事件滞留牯岭的沈雁冰从革命中心退居边缘,这一契机使他有机会以革命“旁观者”的身份重新思考这场亲身经历的“革命风潮”。1927年8月下旬,回到上海的沈雁冰为躲避通缉,封锁消息闭门不出。在此背景下,他化名“茅盾”,将自己在这场革命中的经历与思考借用文学手段传达。自困居沪上到避难日本,茅盾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与散文作品借以寄托自己内心的迷茫困惑,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便是这种心境下的产物。
相比于茅盾其他文学作品,学界对《野蔷薇》的研究相对薄弱,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其作品中的时代女性形象①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的有:李喜仁《〈野蔷薇〉:混沌社会里平凡者的悲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27-129;张霞《“革命文学”潮流中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新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49-53;卜繁燕《“恋爱的外衣”与象征的背后——茅盾〈野蔷薇〉解读》[J].《作家》,2012(8):12-13;王功亮《一个完美的思想和艺术世界——〈野蔷薇〉新探》,《茅盾研究》(第三辑),1988:133-148;秦林芳《镌刻在历史漩涡里的人生思索——〈野蔷薇〉思想意蕴新探》,《茅盾研究》(第五辑),1988:445-456;游路湘《野蔷薇的色香与多刺——略谈茅盾〈野蔷薇〉对时代女性的塑造》,《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27-32。。丁帆、邱文治以及陈幼石②丁帆《论茅盾早期的短篇小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7-14;邱文治《〈野蔷薇〉的政治寓意和主题的二重性》,《天津师大学报》,1986(1):70-76;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对《野蔷薇》的研究中试图揭开小说“恋爱的外衣”[1]586,结合
1993.时代背景探寻深藏于其中的政治历史内涵,将作品的解读引向深入,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茅盾在革命落潮时期的思想复杂性。大革命的落潮引发了茅盾思想的巨大波动,虽然他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深信不疑”[2]426,但是结合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不难看出当时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迷茫和幻灭。旅日期间,茅盾散文突出的意象就是“霜”与“雾”,惨淡压抑成为他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基调。大革命的遇挫、中国革命的现状触发了茅盾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深入思考,各种理论在他头脑中冲撞、融合,构成他反思中国革命的思想背景。
一、茅盾在革命落潮期对“个性解放”的再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注意到文化结构的生成性,并以“场域”概念凸显文化结构中复杂的资本关系,指出不同文化层级之间存在非单向性的重叠与循环。从时间角度讲,文化积累确有“前后”之分,但是不同层级的文化构成并非是“垒砖头”,每一层都界限分明,而是存在着一种渗透和融合。前期的文化积累或许会在很久以后才发生作用,以前被否定的文化成分在新的环境中或重新转化为积极的建设因素。对文化场域中的各个因素“新旧”“优劣”的判定都是相对的,它们都是文化有机体的细胞,它们发挥作用的时间以及功能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同,这些文化因素或休眠,或隐身,但是不会完全消亡。
身处复杂社会环境的作家也会融入于“文化场域”,在其中接受教育,参与文化活动,形成适应场域要求的思考习性,并进一步成为自己接受新环境、新思想的理论预设。因此,从“文化场域”的角度分析,一个人很难“脱胎换骨”完全抛弃已有的文化质素。高质量的文化吸收,不是对新思想的完全模仿,而是在个人文化场域的作用下进行选择性整合。这种整合过程,通常体现的是一个人对新环境、新思想的辩证分析与批判。
茅盾20世纪2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设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宣传的自由精神在茅盾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30年代末期,他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认为“五四”在思想建设上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提出了“人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3]188。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社会自由平等的总目标如同一个磁场,帮助他不断批判吸收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以之充实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围绕革新社会文化制度、实现平等与解放的最终目的,茅盾对自己接触学习的各种社会理论都进行了批判思考,舍弃其中不合理成分,将其调和融汇,使之成为自己思考社会人生的理论武器。
他从尼采的思想中汲取了“价值重估”“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等思想,同时批判了尼采思想中“弱肉强食”的思想糟粕,认为在尼采的道德世界里没有怜悯,他否定平民力量,将牺牲弱者视为实现“超人”的有效途径[4]84。这种观念不利于弱小民族培育民族自信心走向革命之路。因此他又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概念,强调弱弱联合,强弱互助,以此协助弱者实现独立和自由。茅盾重视倭铿(现译为奥伊肯)、柏格森等唯心主义思想家理论中对个人道德和自由意志培养的观念,并将其融合进自己关于中国思想革命的思考当中,强调青年无论是在思想革命,还是政治革命中,都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这其中都包含着茅盾对人力量的肯定,对个体精神世界塑造的重视。受新文化运动伦理革命的影响,茅盾将自由意志的实现视为文化场域重建的核心目标。因此无论是面对尼采、柏格森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对茅盾产生强大吸引的均是其中打破强权束缚、促进思想解放的部分。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复杂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茅盾开始反思这场亲历的社会变革。在以“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中,如何平衡群己关系从五四时期的理论问题变成了实际问题。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处理群己关系的理论逻辑强调个人解放在前,有了自由的人民才能有强大的国家,在群己双方的博弈中,个人独立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理论成为组织革命力量的主要思想武器,五四时期大肆鼓吹的“个人”在实际斗争中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便是在“个人”独立意识没有完全觉醒的前提下,阶级团结的效力也会大打折扣。大革命期间无论是政党还是革命者,思想批判习性的缺失使茅盾更深刻地领悟到思想解放任务的艰巨性。秉承他一贯的批判态度,他借用文学形式对这场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总结,在《野蔷薇》前言中,他总结自己的写作心态是要拔除尖刺而非空许未来,与其幻想遥不可及的自由社会,不如在白色恐怖面前反思过往,寻找共产党在独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尖刺”。
无论是在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还是在国内团结革命力量方面,年轻的革命党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都应该冷静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国际经验介入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看待国外经验,破除对国际权威的迷信;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在国际合作中掌握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员如何在党内保持思想独立,这些问题刺激茅盾重新调动自己的理论经验,结合现实深入思考如何在保持个体思想独立的提前下,实现群己关系的和谐发展。处于历史现场的茅盾虽然不能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尽力分析问题出现的根源,他曾经借以用来反抗封建文化的“自由平等”“合作互助”等思想因子又一次在他的“文化场域”中被激活成为反思历史的工具。在《野蔷薇》前言中,茅盾将自己的小说人物分成三类,代表了茅盾对阻碍“自由意志”实现的三重困境的思考。
二、《野蔷薇》中的三种女性形象塑造:反思通往自由的三重阻碍
茅盾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里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指出自己创作的目的是要“揭破现实”,警惕无限发放的、预言幸福的“历史的必然”的预约券,他小说的主人公里“没有一个勇者,或是大彻大悟者”[1]585-587。新文化运动将“伦理革命”视为社会变革的核心使命,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茅盾,从1917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社会论文开始,就自觉承担起这一时代使命。新旧道德更替的第一步就是对旧道德的“反抗”。但是,经历了社会巨变的茅盾意识到,青年如火如荼的“反抗”背后,内核还是“利己主义”。实现意志自由是当时先进青年反抗封建伦理的首要目的,但是他们的反抗却始终受到旧伦理的束缚,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质存在隔阂。
首先,茅盾对娴娴和桂奶奶的塑造,展示了青年未能脱离旧伦理束缚的第一种表现:他们意识到了封建伦理的不合理之处,甚至是接触到了新的革命概念,然而他们的反抗并未脱离封建文化的基础,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以实现“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新伦理要求存在差距。
《创造》开篇自然主义式的家庭环境描写在读者头脑中展现的不是一副整洁、充满青年人生机的生活场景,而是杂物凌乱、毫无章程的家居环境。联系茅盾在妇女解放问题中关于家庭服务的观点,这一系列环境描写暗含了他对青年中存留的由于轻视体力劳动而形成的怠惰生活习性的批判态度。茅盾将“家庭服务”从封建伦理下含有歧视性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中抽离,从责任与义务的角度重新定义,他利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解读家庭服务,男女分做,各尽所能,讲求的是“体力”与“心力”的调和[5]53,家务不是束缚女性的工具,而是展现妇女能力和责任的平台。一味取消家庭服务的主张在他看来是削足适履,与旧家庭认为家庭服务是妇女专职一样是一无是处[6]157,打着“解放”旗号而不屑管家务的行为也无异于旧家族文化中的“懒惰主义”,是缺乏现代家庭责任的行为。
在茅盾的妇女解放观念中,家庭服务是现代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反观娴娴和君实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性还残留着封建分工的影子:他们缺少主动承担家庭服务的意识,日常社会生活需要女佣来维持。虽然他们读着洋装书,接触了进化论、唯物论,但是在思想上并未进入新伦理的范畴,尊卑意识尚存,平等观念淡漠,封建伦理的魅影依旧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即使她们提倡革命,她们的革命行动却更像是“少奶奶们”的生活装饰品,正如君实对李小姐的批评:“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7]5可见她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根本上是依托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行动。看似洒脱的行为背后难以摆脱家庭的“供养”,与五四思想革命所追求以自立为目标的“个人解放”存在隔阂。
年轻守寡、困居封建家庭的桂奶奶因为青年丙的出现,打破了自己“娇羞,幽娴,柔媚的三座偶像”,但是打破偶像后,她不是看到了自身解放的康庄大路,而是落入了青年丙为她准备好的肉欲漩涡。桂奶奶与青年丙的结合并非出于双方人格平等条件下的“恋爱”,而是性欲冲动下的产物。青年丙在散文一样的桂奶奶和诗一样的表妹之间的犹疑,揭穿了他“斯文,清高,优秀的假面具”[8]98。青年丙看似“自由恋爱”的行为背后,是对女性人格的贬低和折辱。桂奶奶报复丙的做法显示了她不甘被选择的心理,但是她的复仇源于个人愤恨不甘的情绪而非思想觉悟,这意味着她与新的文化场域要求的伦理革命存在差距,在青年丙离开之后,桂奶奶回归封建家庭少奶奶生活的可能性远大于她继续反抗的可能。在桂奶奶的“反抗”中,丝毫不见“自由意志”的因素,她的行动全靠一时情感的支配。
娴娴、桂奶奶受到新思想的激荡产生了反抗意识,但是他们的反抗只是为了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他们反抗家族的压迫、喊着革命的口号只是为了满足私欲。娴娴渴望摆脱君实的控制,然而又心安理得地享受君实提供给她的唤奴使婢的舒适生活;桂奶奶报复青年丙的始乱终弃,反抗行为背后难以忽略其中性欲冲动的行为动因。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青年们意识到封建伦理的缺陷,主动向西方理论寻求解放之道,然而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习性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成为他们接受新伦理的牵制力。
其次,茅盾将环小姐和张女士归为一类的原因是她们代表了在无意识中继续受到封建伦理规训的一类人。同是受到旧伦理的影响,这一类女性形象与前一类女性形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娴娴与桂奶奶在意识到自己受压迫时表现了积极的反抗态度,她们失败的原因是对新伦理本质认识不清,因此思想陷于新旧伦理的拉扯中。环小姐和张女士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封建伦理压迫的妥协。
环小姐是一个生活在相对开明家庭中的新女性,家庭赋予了她自由择偶的权利,然而一次出游、一个少年男子的出现成了她人生中的转折点。男子诱导了环小姐冲动,诱使她在行为上打破了封建贞操的束缚,享受了性爱带给她的短暂幸福。可是男子的突然消失却将环小姐打入了比之前更加艰险恶劣的深渊。背负不贞秘密的心理压力、外界对女性失贞的不能容忍都成了压在她身上的巨石,孩子的意外到来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造成环小姐悲剧的原因与其说是她“离经叛道”的行为,不如说是隐藏在这貌似“自由恋爱”的行为背后封建文化中的“耻感”心理。渴望冲破封建家族束缚,追求个性独立婚恋自由的新女性,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她们在行动上渴求恋爱的刺激,思想上却无法摆脱封建贞操观念引发的“羞耻感”,更不能赋予“恋爱”深刻的思想意义。
环小姐在发现自己怀孕后,想到了两条出路,一条是勇敢宣布自己的秘密,另一条就是找一个人来“顶名义”,“社会上需要虚伪的名义”,“最聪明的办法是赶快找一个人来掩护”自己的过失[9]52,而她选择的却是第二条路。这种“秘密主义”将她肤浅的“恋爱”彻底转变成了旧社会才子佳人般的“风流韵事”。在茅盾的“恋爱理论”中,“恋爱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既已了解双方全人格后的两个灵魂的合一。不是一方面主动的‘挑’而他方面被动的‘感’”,“女子方面呢,仅仅是被男子的热情挑动了春心,依一时的性欲冲动而愿为男性所有,绝对谈不到爱字”[10]69-71。环小姐对于自己的“恋爱对象”完全说不上对“全人格”的了解。她的恋爱徒有其表,因此无法在现代意义的自由恋爱观念中合理评价自己的反叛行为,反而在社会的舆论氛围中迷失自我,重新跌入封建伦理的泥淖。
与环小姐相比,身处封建官僚家庭中的张女士是生活在父权阴影下的“旧女性”。她虽然憎恨自己的家庭,但是只因父亲不允许,她连出走的行动也未曾有,她不仅是“行动的矮子”,也是思想的“侏儒”,她的“解放之路”其实是一种“逃避之路”,她渴望何若华的恋爱并非是出于对情感自由的认同,而是要逃避自己成为“姨太太”的命运。当逃避婚约的意图瓦解时,她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兰女士与何若华的恋情上,认为他们的恋爱是导致自己无法行动的直接原因——她原将何若华视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的一个候选者,如今却落了空。张女士的不满只是父亲并未给她选择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不是质疑自己在家庭中不平等的地位。无力改变父亲心意的张女士,最后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逃往自己的家乡“广州”,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张女士的出逃暗示了她参加革命的将来,然而从小说开头张女士对家乡与母亲美好生活的回忆来看,她更有可能是在对“往昔”的留恋中坠入虚无。
再次,茅盾借用“琼华”这一形象批判了革命中的盲动主义。琼华本是一个出身于乡村开明士绅家庭的单纯少女,她相信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存在,她不信世间当真会有凶险的人,也不信人们彼此之间会抱有恶意。但是因为张彦英而引发的一系列流言,使她抛弃了对世界单纯美好的幻想,“她感得有一种异样的荒凉的悲哀兜上她的心头”“她骤然感得人类是比想象中的阴险还要阴险些”[11]71,她觉得人类是不配受到热爱的,她要学习虫豸适应自然的天性作为和世间的“魔鬼”周旋的手段。在复仇的初始阶段,她似乎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周围的男性对她更尊重了,她俨然已经成了一乡的女王。但是,当寂静的深夜来临时,她依旧感觉到内心的迷茫与深深的痛苦。她的复仇与反抗似乎并没有带给她更加光明的未来。
很快她遭遇了人生的第二次挫折——身为“名流”的父亲葬身火海。这一遭遇让她体会到了“从高贵到式微”的巨大反差,她对世态炎凉的体会更加深刻了。这一次的遭遇激发起琼华更加强烈的“复仇”心理,她将社会视为粪窖,身边人都是生活在龌龊环境中的“蛆虫”。她想要报复身边这群虚伪的人,但是她并未改变自己所谓的报复策略,失去了身份加持的报复行动在他人眼中荒诞可笑。在此刻,她也终于认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一病不起,徒劳地耗尽了年轻的生命。
琼华的经历显示出具有一定行动力的新女性在遭遇人生挫折时想要反抗、想要行动的决心。她反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形势缺乏分析,不能寻求外界的有力援助。她是一个类似尼采式的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她也有意成为超脱时代环境的“超人”。但是她脱离群众式的反抗行动缺少对自身情况的准确分析。琼华在人生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不能联合同情自己的力量,反而认为除却父母以外的他者都对自己怀有敌意,都是自己的对立面。
琼华的“复仇”缺少理性,只是凭着内心的一股愤恨情绪作为推动力,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封建伦理的产物,复仇的目的和标准由自己掌控,缺少社会价值的动因,导致了复仇行动本身具有盲目性。她很清楚“少年们对于她的崇拜是为了某种目的”[11]75,但是又无法分析出他们的“目的”所在,这种不明确来源于她自己对社会环境和自身情况缺乏透彻了解。父亲死后,她依旧按照过去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复仇”,结果白白引来别人的一番嘲笑,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澜。她的复仇缺少理性的动机,不能科学地分析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复仇行为。理性缺失,全凭冲动支配的行动,也不能算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这些都说明琼华的反抗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化的、盲目的行为,必然不能起到“震撼”社会的目的,反而会将自己引向“死亡”之途。
通过塑造“琼华”这一具有封建文化特质的“复仇者”形象,茅盾批判了在不能认清自身形势、革命目标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便采取行动的盲动主义策略,而且对当时中共阶级斗争政策中绝对排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做法不以为然。盲动主义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革命群众中激起的一种“复仇心理”的产物,对革命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927年时任中共领导的瞿秋白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其中在谈到中国革命是否低落的问题上指出“革命潮流始终不是低落,而是高涨”[12]684。同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也做出判定,认为这一时期在“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爆发”,“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严厉镇压”[13]455。李维汉在晚年回忆当时的革命形势时指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而出现了革命急性病,党内“左”倾情绪发展,甚至延伸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中来[14],影响了党内对阶级关系的判断。茅盾也对当时一概否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做法提出质疑,“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那便是很大的武断”,“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15]215。中国革命如果盲目排外、在未能分析革命形势的情况下盲目采取武装暴动,只能走向与琼华一样无路可走的险境。
如何将个体力量最大化是这一时期茅盾针对革命形式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也体现了在革命斗争中他对个性解放认识的继续发展。五四时期群己的关系就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议题,并且已经意识到获得自由意志的“个人”最终应落脚于国家。茅盾利用琼华的故事将对个性解放思考推向阶级联合的层面。个人觉醒之后的斗争如果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阶级联合的互助,失败是必然结局。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在这一时期催化了茅盾对群己关系认识的深化,“任何生物都不是营个体生活的”,互助可以保证“群”的共存和个体的继续发展,险恶的环境中个体很难单独生活,互助性弱的群体最终会面临淘汰的命运[16]2。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实力弱小的中国工农群众,如果想要发动旨在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革命,就不能脱离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和支持。不分析中国具体的阶级现状一味地扩大阶级对立,从当时的革命形势看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需求,势力单薄的无产阶级应该广泛寻找自己的革命同盟,盲目排外、不辨情况的盲目反击不能成为中国革命冲破黑暗的途径。
三、《野蔷薇》的独特反传统意义
如果从故事情节赏析《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作品,其选材结构并不具有新意,依旧以当时流行的婚恋和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作为文学作品集,《野蔷薇》并没有为文学界提供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与其将这些女性主人公看作“人物”,不如将其视为茅盾用以进行思想与文化反思的“符号”更为贴切。《野蔷薇》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先锋的描写手法,也并非塑造了带有国民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它的独特意义在于展现了具有忧患意识的创作者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敢于进行文化批判和自我批评的勇气,是现代知识分子家国意识的体现。
当茅盾暂时“脱离”革命,反思革命受挫的原因时,他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对“理论”和“经验”的迷信态度产生质疑,甚至在晚年回忆当时的心境时指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没有弄清楚!”“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2]426茅盾肯定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有向苏联学习革命经验的必要性,但是也对中共领导教条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过分依赖国际经验,导致独立话语权缺失以及忽视本国实际情况的做法表示忧虑。
“打破偶像”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确立的文化革新目标之一,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方面还未彻底将孔子请下神坛,另一方面又请来了另一尊“偶像”——苏联经验。就像茅盾在《鲁迅论》中借用鲁迅关于“长城”的比喻所发出的感慨,“旧有的和新补添的联为一气又造成了束缚人心的坚固的长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情状”[17]161。新的权威逐渐成为一股束缚中国共产党独立发展的力量。茅盾并不是要否认新理论和苏联经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反思为何先进的理论和经验植入中国后会产生“消极”作用。
茅盾将自己在革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折射进《野蔷薇》中的三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引导读者发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文化心理的积习难除。茅盾此时重新调动新文化运动中新道德建设的经验,将文化场域的思想革命与政治场域的政治革命进行衔接:如果政治革命不能以全新的文化场域为基础,即使有先进的理论加持,革命也会成为封建文化下的“畸形儿”。新文化运动呼吁倡导的“新道德”体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准则——培育新的“自由意志”思想,实现个体精神解放。它的伦理建构模式要打破封建文化枷锁,彻底脱离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语境,在新的文化场域基础上构建新的道德要素,使个体精神在新空气中自由生长,培养内在的理性意志来实现个人精神“自由”。传统伦理想要压抑个体以服务权威,现代道德则是试图在群体中保持个人存在的价值。
茅盾并不否认政治革命中阶级斗争理论的合理性,而是要利用文化场域文学创作反思“人”如何在阶级中实现个人力量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理论,而现代革命的目的要同时实现自由和解放,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18]17-21,这不仅是政治场域内的政权更替,也是文化场域内的更新换代,是伦理价值的重新定义。可以说现代阶级斗争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在精神上与封建时代的彻底脱离。在这种层面上,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化场域中进行的新道德建设应该是政治场域中阶级斗争的重要辅助力量。茅盾创作《野蔷薇》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在政治场域内的革命挫折之后,将反思的矛头深入到文化场域之中,指出造成现代革命运动似是而非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文化干扰。
作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茅盾重新召唤出以促进个人自由意志觉醒为目标的伦理革命经验,警醒革命青年在政治斗争中不断进行思想层面的自我批判,逐步清除在封建文化中形成的奴性和依附心理,在不断地自我批判中促进自由意志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将具有现代伦理意识的个人联合为阶级,进行现代革命斗争,促进社会的全面解放。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中,代表进步阶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应该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合作中应该保持主动,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他者的附庸,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外来理论和经验,发展自己的独立意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用平等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去。
茅盾在晚年回忆自己创作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虹》时指出,“梅女士思想情绪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能不说就是我写《虹》的当时的思想情绪”,并且评价说“梅女士是一个形式上的共产党员,精神上还是自己掌握着命运”[19]469-470。梅女士的“表里不一”形象暗示了茅盾自己当时思想状况的复杂性,从革命漩涡中暂时脱离的茅盾,经历了革命理想的短暂幻灭,但是他迅速整理自己的心情,借用五四时期深刻影响自己的思想理论,对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独特分析。
形成于五四时期,以发展“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文化场域成为一种理论背景,在这一时期帮助茅盾吸收、消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有意识地将思想革命与阶级革命结合,将获得新伦理规范的人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力量,阶级斗争又成为建设新伦理的最终依归。虽然在由“个人”到“阶级”的发展过程中,茅盾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思想上的迷茫,但是他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信念从未消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茅盾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他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无论是作为社会活动家还是文学作家,茅盾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热切关注着中国的革命与发展。他以冷静的头脑、无畏的勇气正视大革命落潮期的黑暗现实,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