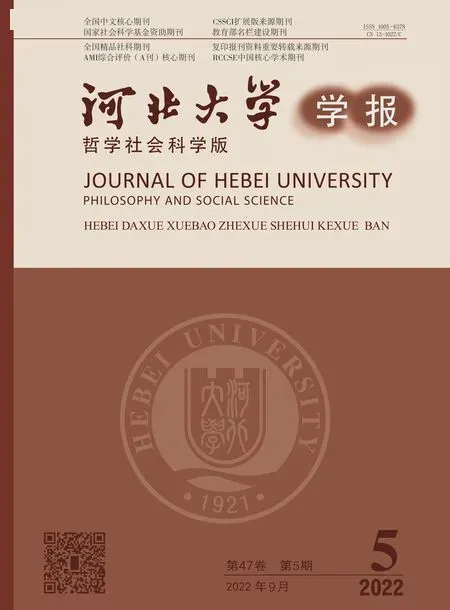屠城了无痕
——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
王瑞来
(日本学习院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 东京都 171-8588)
1279年,崖山之战,陆秀夫负帝蹈海,南宋王朝画上了终止符。不过,历史纪年表上所显示的时代终结,并不完全反映实际状况,历史的余音还在回荡。尽管失去了皇帝与中央朝廷,三百年大宋王朝所凝聚的象征认同意识还在发挥着影响,华夷对抗情绪还很高昂,江南各地的抗元依然此起彼伏,久久未能平息。于是,翻检史书,江西南安一隅宋末抗元的一幕,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宋末抗元的南安一隅
(一)《宋史翼》的记录
《宋史翼》卷三二立有《李梓发传》。传记讲述了南宋末年江西抗元的史事。传记很短,引述如下:
李梓发,字材甫,上犹人。德祐元年,以世族举为南安三县巡检。元兵围上犹,梓发随邑令李申巽及邑中诸义士坚守不懈。元兵死伤甚众,旋解去。文天祥表梓发为团练使、督府咨议,收之幕下。申巽请梓发往来赣图战守。祥兴己卯,元兵复至。梓发与邑令城守益坚。时天祥兵败绩,行朝亡,邑士黄桂绂为元卒所获,令赍榜入城招降,且传崖山之难。梓发大怒,戮桂绂。无何,城陷,梓发与子姓四十七人皆自焚。同时有唐仁、黄贤、张伯子、刘渊子、张南仲、阳清叟及邑令李申巽俱遇害。[1]347
《宋史翼》本传之后,记出处为《人物志》。检寻之下,可知是原封不动转录自《雍正江西通志》卷九三[2]。《宋史》虽未为李梓发立传,但在卷四七《瀛国公纪·卫王》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壬寅条亦有一笔述及:“大军破南安县,守将李梓发死之。”[3]945《宋史》本纪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事件存在的真实性。
(二)《元史》的记录
这一事件,也进入了明初修纂《元史》的史官视野。《元史》卷一五三《贾居贞传》载:
(至元)十五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未至,民争千里迎诉。时逮捕民间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系巨室三百余,居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挟兵入民家,诬为藏匿以取财者,取人子女为奴妾者,皆痛绳以法。大水坏民庐,居贞发廪赈之。南安李梓发作乱,居贞虑将帅出兵扰民,请亲往,卒才千人,营于城北,遣人谕之。贼众闻居贞至,皆散匿,不复为用。梓发闭妻子一室,自焚死。比还,不戮一人。[4]3624
这段史事叙述的后半部,才是南安事件的记载。之所以整段引述,因为记载的几件事情都以贾居贞爱民的主线相贯穿。而后面所述南安事件,更是强调了贾居贞的不滥杀戮。这样的记载,跟《宋史翼》的《李梓发传》不大一样。看《宋史翼》的记载,南安事件并非“不戮一人”,还是死了一些人的。那么,对于南安事件,到底哪一种记载比较接近真实呢?历史研究往往需要有一种对真相的执着探求。
二、当时人与当地人笔下的南安事件
从《宋史翼》的记载看,李梓发跟宋末抗元的文天祥有一定的关联,传记提供了“文天祥表梓发为团练使、督府咨议,收之幕下”的事实线索。根据这一线索,我在《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收录邓光荐所撰《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中找到了关于南安事件的更为详尽的记载:
李梓发,字材甫,南安军南安县人,世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发为南安三县管界巡检,江西陷,南安守杨公畿迎降,独南安一县不下。邑人黄贤与梓发共推前南安尉永嘉叶茂为主,治守具,北军至城下辄败。景炎元年十二月,北丞相塔出与张、吕二元帅引大军万余,围之数匝。邑犹弹丸地,城墙及肩。北军攻之百计,梓发率邑人并力死守。昼则随机应变,夜则鸣金鼓劫寨,杀无算。塔出等相顾曰:“城子如堞大,人心乃尔硬耶?”明年正月六日,塔出与张、吕至城下谕降,邑人裸嗓大骂,俄炮发,几中塔出。即日徙寨水南,犹力攻凡三十五日,北军死者数千,不能克。二月,叶茂出降,北军乃退。梓发与贤坚守如故。戊寅冬,丞相被执。己卯二月,崖山亡。三月,北参政贾居贞往谕降,城上诟骂如初。时邑人稍稍徙去,心力懈于前时。贾命方文等进攻,十五日城破,屠之。梓发全家自焚,望烟焰五色,或以为忠义之感。邑人多杀家属巷战,杀敌犹过百。[5]
《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所记,除了一些具体事实稍详外,最大的事实补充就是《宋史翼》本传语焉不详的“城破,屠之”。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一也依据《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又有所补充,为李梓发立传云:
李梓发,上犹人。元至元中,托尔楚元帅次上犹,梓发等不肯降。托尔楚元帅围城七旬弗克,退师。己卯,贾参政复至,不降。邑士黄桂发才英逆知屠城,忘命入城,拟救父母,中道获于贾参政,以实告之。参政曰:“汝可将省榜入城招降,不惟汝父母可安,合城俱安。”桂发等入城,为李所杀,卒至屠城。梓发率民巷战,势穷力屈,回家以酒肉酌别老幼,令健卒自杀由幼而老四十七口。梓发与子举火自焚而死。事详《文山先生督府忠义传》。[6]
就是说,在崖山宋廷彻底覆亡之后,对于江西赣江上游小城南安的抵抗,元军实施了残暴的屠城。
那么,出自作为当时人邓光荐笔下站在亡宋立场的记述是不是事实呢,或者说,未曾亲历的邓光荐,记述有没有道听途说的成分呢?检寻之下,我又找到了更为详细的记载。这是出自元代人的记载。在明人刘节纂《嘉靖南安府志》卷一五《建置志》一中全文引述有黄文杰《上犹县治记》,其中有关抵抗和屠城的部分有如下述:
己卯三月,贾参政复至,谕以城降。邑令李申巽誓居民李梓发之俦曰:“犹未城前,遇有变故,民散而之吉、赣。绍定壬辰,邑令胡泓徙邑筑城,正为吾民义守具也。前人建城,后人降城,于义弗许。”卒至十五日,大兵屠焉。使合邑廨舍、仓库、碑名及一千五百一十六家之生灵,玉石俱焚。纵有苟免于城者,则又不免于四境。一木而支大厦,万有余人同日死,闻者为之痛心。参政召申巽而过之曰:“汝宰邑非才,是围民以城,诲锋镝而自戕,吾虽命将分问善良,其道无由也。”遂杀申巽暨路帅张伯子。临刑,有雷一声,晴空而震,或者疑其为星殒也。邑由是改名永清,属行省,擢邑士黄桂开簿邑事。桂开草创邑治于劫灰之末,抚集遗亡,仅存七十有二。荒城白骨,四顾萧然。①商文昭、卢洪夏纂修《南安府志》卷一〇,明万历刻本。按,《全元文》于卷一四二〇亦据清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六一收录有《上犹县治记》,文字较《南安府志》有所节略。
《上犹县治记》的记述,展示了屠城的惨烈。全城万余人同日而死,过后抚集遗亡,幸存者只有七十二人。《南安府志》记有作者黄文杰的小传云:“黄文杰,字显明,上犹人。元大德间擢安远教,寻辞归,守家训,居处建祠祀。”[7]据此可知,黄文杰就是上犹当地人,他根据耳闻目睹,在延祐元年(1314)写下的记述,距屠城发生仅仅过去三十来年,当可取信。因此说,阅读《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万姓统谱》以及《上犹县治记》,让我们不容置疑屠城发生的事实。《宋史翼》援据的《雍正江西通志》,在卷六五引述明代方志,也明确记载说:“乃坚守至七十五日,城屠,李梓发全家自杀,申巽死之。”
从元军征服方式的角度看,南安屠城也实属必然。蒙古征服世界各地,基本采取降伏怀柔、抵抗屠城的政策。美国学者贾志扬指出:“对抵抗者施行屠城,是蒙古征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志性行为。”[8]246其实,关于元军的这种做法,当时南宋抵抗的军民也很清楚。北宋直臣唐介的后代唐泰岳宋末节度宁国军,在元人劝降的时候,就对其夫人说:“元令,围久者,下之日屠其城。”[9]当时许多地方放弃抵抗,可以说就是慑于元军的这一做法,出于求生本能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与秉持什么理念关系不大。“时无敢拒北兵,拒即屠。”[10]354元军久攻南安不下,围困达两三个月,其间造成伤亡数千。城下之日,怎么可能“不戮一人”?与元人惯行政策有违的“不戮一人”,只能是出自后来的掩饰。
三、《元史》记载溯源
一场残暴的屠城,到了《元史》那里,居然变成了“不戮一人”。上千个家庭的消亡,近万人生命的丧失,没有一点痕迹,没留下一丝血色,事实进入史籍,发生了黑白颠倒的逆转。让我陷入深思的是,事实的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其源头究竟在哪里?
跟《元史》相近的记载,我首先在元人苏天爵辑撰的《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参政贾文正公》中发现:
十六年,李梓发盗据南安,公虞他将往则为暴,坚其不下,请身往平,才从兵千,营于城北,为檄推诚招怀。梓发度其猖獗日久,势不敢归,以其徒知公有素,战不为用,乃闭妻子一室,自焚死,众皆散还其乡。不戮一人,平南安归。[11]230
这段记载与《元史》的记载相似度极高。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有一个特点,即所辑录史事均注明出处。关于南安事件的上述记载,注明出自“神道碑”。据《参政贾文正公》首段出处的详细记载,可知这一“神道碑”是指“牧庵姚公撰神道碑”。牧庵姚公就是姚燧。果然,在《牧庵集》卷一九,我看到了《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相关记载如下:
明年,李梓发盗据南安,公虞他将往则为暴,坚其不下,请身往平。才从兵千,营于城北,为檄推诚招怀。梓发度其猖獗日久,势不敢归,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贰其操,战不为用。惧左右窃取其首为功,乃闭妻子一室,自焚死。众皆散还其乡,不戮一人,平南安归。[12]462-467
苏天爵还纂辑有《国朝文类》,即《元文类》,在卷六一,全文收录了署名姚燧的这篇《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13],南安事件相关部分,与《牧庵集》全同,比《元朝名臣事略》个别字句稍详,但“不戮一人”则均无异。上述两种皆源于《贾公神道碑》的文字与《元史·贾居贞传》在表达上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元史》记载贾居贞平南安“不戮一人”的源头,就是姚燧的这篇《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
四、姚燧改变事实书写蠡测
过去撰写墓志铭或神道碑,撰者或是与墓主有着亲密的过从,或是应墓主家人的请求,写作时间也与墓主过世相去不远。通观这一篇神道碑,姚燧与贾居贞生前看不出曾有过从,写作时间也是在墓主去世29年之后①姚燧《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载:“后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圣言念尽瘁大帝,功加生民,赠推忠辅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定国公,谥曰文正。哀褒之典,无一遗者。”。因此姚燧所依据的贾居贞生平事迹资料,是当时尚可寓目的行状或墓志铭,以及贾居贞家族后人可能提供的资料。《元朝名臣事略》中的《参政贾文正公》叙述贾居贞事迹,除了使用了姚燧所撰神道碑之外,根据所注出处,还使用有“汶上曹公撰行状”。遗憾的是,这篇贾居贞行状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不过,从记述南安事件一段所注出处为神道碑来看,“不戮一人”的记载还是来自姚燧笔下的神道碑。
其实,过去受邀撰写碑志,从家族那里可以获得的资料,大多只是任官、行历等基本履历数据,其他内容多为撰写者的发挥。清初的戴名世就曾这样讲过:“凡士大夫之卒,必有行状;其葬也,必有志铭。行状则他人代为,而其子出名;志铭亦他人代为,而以贵公出名。据其状铭,则人人皆大贤君子也。其实未必然,十有二三之真,则已仅矣。余至京师,闻西北诸公状铭,多凿空撰出,并无事实,余颇未信。久之,有以状铭属余者,但具官爵、生卒与子女多少而已。问其事实,曰唯君为之。大约言居家则如此如此,居官则如彼如彼,务期铺叙繁多,逞意尽辞无稍缺略,使览者好看而已。”[14]60
戴名世讲的,正是碑志撰写的一般状况,姚燧撰写神道碑也不会超脱例外。那么,姚燧的记述为什么会出现与真正的事实截然相反的状况呢?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姚燧是受到所获参考资料的误导。因为作为负有盛名的文章大家,当时许多达官贵人都来请求姚燧为他们的先人撰写碑志。《元史·姚燧传》就如是云:“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贾居贞神道碑的书写背景亦当如是。
不过,除此之外,会不会有姚燧主观因素的主导呢?我们来看一下姚燧在神道碑中对贾居贞的综合评价:“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当睿圣大有为之时,与二三元臣,上以毗赞其经国,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经理南纪,谋猷大军,于襄阳,于湖广,于江西,新造之邦向化未纯,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获其所。一有海隅之难,盗贼附起,祸譬而赏劝,德绥而威挞,徐革其面,而浃其心,俾方三数千里之氓,一喙同辞,称其仁人。”上述这番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行仁政。神道碑还特别强调了贾居贞的不杀:“求能推守大帝谕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杀’之训者,无公亚匹。”姚燧认为,在遵循忽必烈训示伯颜学习曹彬平南唐不杀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贾居贞。
我们来观察一下姚燧的生平。他是道学在北方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姚枢的从子,三岁而孤,由姚枢抚养成人,成年后又师从另一位道学大家许衡。姚燧后来成为元代文章大家,与虞集齐名。一般认为姚燧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多理学因素,这与他接受姚枢和许衡的影响密不可分。姚燧后来从政,也做到过跟他写神道碑的贾居贞一样,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一生从政,遵循儒学经典,秉持道学理念,赈灾济民,做了许多行仁政之事[15]。姚枢原来在金朝为官,担任军资库使,在蒙古军进攻许州时被俘,成为蒙古的官员。元人陈桱《通鉴续编》载:“初,蒙古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皇帝见枢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太子南伐,俾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至是,破枣阳,大将忒没歹欲坑士人,枢力与辨,得脱死者数十人。”[16]10在这种仁爱观念主导之下,姚燧很有可能有意识地放大了资料中贾居贞行仁政的一面,强调仁爱止戈。
碑志从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面向死者的歌功颂德,还是留给活人的教谕,树立起一个个善人完人的榜样,让后人效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碑志也起到了史书的作用。因此,作为基础资料,也成为修史之际重要的取资参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张“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17]的姚燧看来,如何以求真来叙述几十年前的史事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碑志书写向执政者宣传行仁政的理念。于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之下,姚燧的书写便改变了事实,一场残暴的屠城便成了“不戮一人”。
从这一视点来看,姚燧的书写并非仅仅出于对墓主贾居贞隐恶虚美,而是借碑志的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抒发自己的理念。尽管姚燧的书写有悖于史学规范,但对其善意应当抱有一定的理解,无须苛责,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
秉笔直书的良史本来就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对于碑志这种特殊体裁的文体写作,隐恶虚美和歌功颂德是基本规则。不过,规则可以遵守,不便书写的内容可以回避,但不应当改变事实,颠倒黑白。对于姚燧的碑志写作,历来评价很高。有的学者说:“其(姚燧)碑志尤足以补史乘之阙。”[18]273还有的学者说:“姚燧文章有信史之称。”[19]138-140更有的学者说:“古文家的传记创作多是从史传的角度出发,以补史之漏或备史官采集,他们的创作一般都以史著为准绳,坚持秉笔直书、指事说实的实录精神,姚燧也不另外。”[20]在姚燧的碑志写作中,对南安事件的书写,或许是一件个案,但从把事实彻底颠倒来看,完全谈不上是秉笔直书,神道碑也难膺信史之称。从道德意义上说,也是对南安上万屠城死难者的冷酷漠视。关于这一点,不能讳言。当然,姚燧在字里行间贯穿的仁爱遏暴思想,在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能说没有客观的积极意义。
五、史实记载如何取信
对姚燧改变事实书写尽管无须苛责,但通过对南安事件书写的考察所引发的省思,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明初史官对私家碑志不加认真鉴别,修入《元史》,已历来为人诟病。《元史·贾居贞传》照抄姚燧的神道碑,从而造成事实颠倒的重大错误。并且,作为官修正史的《元史》,由于是记载元代历史的主流史籍,影响很大,为后世所取信者甚多。正因为如此,对其中的这类问题才不能忽视。
具体就《元史·贾居贞传》的问题,我又翻检了清人重新编纂的几种元代史书,无论是屠寄所撰《蒙兀儿史记》[21],还是邵远平所撰《元史类编》[22]、魏源所撰《元史新编》[23],以及晚清柯劭忞所撰《新元史》[24],都原封不动地转抄了《元史》的“不戮一人”。
姚燧的“不戮一人”进入具有权威性的《元史》之后,不仅造成了后来多种新编元史的沿误,还影响了许多引述这一事实的书籍。如明人黄汝亨辑《廉吏传》中的《贾居贞传》[25]、清人嵇璜撰《续通志》[26]、胡文炳撰《折狱龟鉴补》[27],皆采《元史》之说。最为典型的是清初以撰《南北史合抄》而闻名的李清在其《诸史异汇》卷九《仁类》专立《不杀》一条,采自《宋史》云:“曹彬伐南唐,戒以弗杀。及金陵破,彬与诸将相约,誓不杀一人。”接着又云:“粘合重山取定城、天长二邑,不杀一人。南安李梓发作乱,贾居贞营城下,遣人谕之,众皆散,梓发自焚,不戮一人。”在这两件事的记载之后,李清注有出处云:“俱《元史》。”[28]
姚燧的“不戮一人”经由《元史》,谬种流传甚广,让后人信以为真,当作具有正面意义的信史来加以宣传,而方志中记载的另一种事实,则犹如微音稀声,被无视而不闻。
姚燧在神道碑中对南安事件的误书,足以提醒我们,在日渐重视碑志这种 “地下史料”的当下,也应当对以虚美隐恶为宗旨的碑志所讲述的史实抱有足够的警觉。以前我曾写过《碑志难以尽信》一文,以宋人所撰碑志为例,指出了这一问题[29],这次则以一例个案再次做了印证。
对历史人物的虚美隐恶问题,作为官修史书,状况稍好一些,毕竟在集体编纂过程中,史官会对一些史料进行鉴别之后再采择入史。然而,任何事情皆不可一概而论,任何史书的编纂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都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就这一事例来说,明朝史官修《元史》,恐怕不会为元朝隐恶,有意抹杀南安屠城事件。然而,我们审视《元史》的修纂背景与过程,可以肯定地说,特殊的因素无疑对《元史》的质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洪武二年(1369),明朝建立伊始,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于北方草原的状况下,为了宣示明朝的正统性,承继后朝修前朝史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编纂《元史》。这一举动等于是在帝国一系的认知下,从法统上宣告了元朝的结束。这种政治上的需要,让宋濂和王祎两个文臣,率领16个儒生,用188天的时间就编竣了《元史》的主干159卷。第二年,宋濂和王祎又组织了15人,用143天的时间编写了53卷。最后整理定稿为210卷。总共编纂费时不足1年[30]。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匆忙的编纂,让史臣无暇充分遍检群籍和辨析史料的真伪,只能利用编纂之际可以寓目的史料入史。在这种背景之下,在编纂过程中,刚好看到了姚燧撰写的神道碑,并且又惑于姚燧的大名,没有印证其他相关史料,便盲从曲信,采纳了神道碑的记载。
诚如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对文献记载的所有史料,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碑志,皆应抱有审慎怀疑的态度,因为任何落在纸上的历史叙述,都有载笔者有意无意地增饰或阙笔。出于主观意识的增饰或阙笔是出于特定目的的作为,而无意的脱漏和载笔之际的史料阙如,也影响史像的真实传达。认真考辨鉴别之后采择使用,方可减少错误。在我看来,不真实的历史叙述,很像是古籍中存在的伪书与伪篇。古籍中的伪书往往是有意作伪,而古籍中混入的伪篇则是流传过程中的无意成伪①王瑞来《略谈古籍校勘中的辩伪问题》,《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15期,1989年。又见氏著《古籍校勘方法论》,中华书局,2019年,187-191页。。不管出于哪一种状况,都需要在研究之际辨讹证误,去伪存真。
去伪存真的作业,不仅需要辨别除去增饰的“假语村言”,还要综合驱使多种相关史料来补足“真事隐去”的部分。对于后者,有一个典型的案例。2005年在西安李建成陵出土的墓志。墓志只有55个字:“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从这一墓志,不仅看不到太子李建成在创立唐朝的重大功绩和多彩人生,也嗅不到玄武门之变的血腥。李建成墓志的这种状况,完全是唐太宗主导操作或强势影响而形成的结果。
关于墓志值得警惕的问题,我还想举一个北宋的例子。北宋后期有一个人叫钱遹,由于主张打击元祐党人和再废元祐皇后,变得很有争议。尽管《宋史》已经为其立传[31],晚清陆心源编纂《宋史翼》,又再度立传,归入《奸臣传》中[1]。钱遹晚年乡居,死于方腊暴动。对于钱遹之死,现存文献史料呈现了三种死法。阅读史料,颇值得玩味。
《宋史·钱遹传》载:“方腊陷婺,遹逃奔兰溪,为贼所杀。”《宋史翼·钱遹传》转录明宋濂的《浦阳人物记》所记略同:“方腊陷婺,遹走兰溪灵泉寺,为盗所刺。”[32]这是避难丧命说。
元人吴师道辑《敬乡录》引述墓志则云:“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寇犯兰溪,公集众趋之,遇于灵泉寺,力战冒阵死。赠大中大夫。梅尚书执礼铭墓识其详。”[33]这是抵抗牺牲说。
不过,《敬乡录》还引述了一种记载:“郑亨仲云,腊寇犯浦江境,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对巨魁痛毁时政,以幸苟免。寇谓遹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为讪上之言,亟命其徒杀之。亨仲在浦江,目睹其事。”这是投降被杀说。
在上述三种死法的记载中,毫无疑问,抵抗牺牲说是最为光辉,最为高大上。这是来自墓志铭的记载。避寇丧命说相对中性,而投降被杀说则凸显否定的一面。三种记载,一为正史,一为墓志,一为目睹云云。究竟哪一种记载更为接近真实?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死后的命运也被时代翻弄,所谓的盖棺论定,也呈现出种种面相。因此,一定要做具体分析。
在投降被杀说的记载之后,《敬乡录》还有追加记述:“汪彦章诏旨中作遹传,亦甚诋之。”这一记载反映的时代背景是,南宋初年重修《徽宗实录》,主旋律为是元祐而非崇宁,因此汪藻在撰写《钱遹传》时,对钱遹也是极加诋毁的。投降被杀说尽管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眼见也未必为实,恐怕还是迎合时风的产物。
来自墓志铭的抵抗牺牲说,有死后赠官大中大夫为佐证,似乎也有几分可信。其实,以钱遹的地位以及在元祐党争时所起的作用,在熙丰党主导的徽宗朝,死后获得赠官恩泽是不足为奇的,这跟其死因没有必然联系。抵抗牺牲说可信度较低这一点,从《浦阳人物记》没有采用的事实也可以窥见。作为乡邦文献的《浦阳人物记》跟正史不同,对钱遹记载了不少担任地方官以及退居乡里后的正面事迹。从这一逻辑出发,如果抵抗牺牲说可信的话,一定会被大书特书,来体现这位乡贤的光辉形象。未采用,则说明了此说的可疑。
投降说与抵抗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源于宋朝国史《宋史·钱遹传》,一定是在对元祐党争逐渐转向平和态度的孝宗朝以后的产物,所以经过史官的鉴别之后,采用了比较中性的避难丧命说,竭力诋毁和颂扬的记载都没有被采信。关于钱遹之死的三种记载以及正史的选择,既显示了对所谓耳闻目睹的“实录”的怀疑,也提醒着对以歌功颂德为宗旨的私家碑志的警惕。
其实,前人对来自私家撰述碑志的问题,多有警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四在记载喻汝砺知遂宁府一事之下,李心传写有一条考证:“谭篆撰汝砺年谱云:知遂宁府,陛辞,玉音亲出‘卿见闻殚洽,词采英奇’之语。寻改除潼川路转运副使,词臣即采陛辞日皇帝所出八字以宠之。按,林待聘《外制集》,此八字乃汝砺知遂宁府告词,篆之诞妄如此。史堪作汝砺墓志,又因而书之。由是观之,私家行状、墓志所书天语,要未尽可凭,须细考之乃可。”[34]李心传讲的这个例子,从年谱到墓志,都把告词中的两句话直接当作皇帝亲口所言。在以歌功颂德为主旨的碑志作者看来,这无疑是最高褒奖。李心传在找到了这两句话的原始出处后感慨说道,私家行状、墓志所转述的皇帝话语也不可完全凭信,一定要加以仔细考辨。这一事例警示我们,包括碑志在内的所有史料,都需要投以审视的目光,缜密地辨析。日本学者一向对笔记小说记载的史实报以怀疑的审慎态度①[日]平田茂树《书评:王瑞来著〈宋代皇帝权力和士大夫政治〉》:“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一般仅仅在可以避开可信度的问题上作为补充材料时才利用小说随笔,或者撇开事实,从当时人们的言论,即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问题这一视点利用小说随笔。”见《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页。,其实对于碑志所记载的墓主言行,凡是涉及道德评价的部分,则需要比笔记小说的记事持有更严格的审视。换句话说,碑志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比作为他者记述的笔记小说更不可信。
其实,前人写作私家碑志,不光仅仅是迎合墓主家人歌功颂德,《春秋》载笔意识的影响所及,往往会让秉持理念的士人透过碑志叙述,阐发自己的理念,将碑志作为一种传递理念的史书来看待。《宋史翼》卷二五《张淳传》就记载张淳:“时为文章铭人墓,有讽有劝,皆不虚书。”“不虚书”并非仅仅不向壁虚造,还是指不枉书没有意义的话。而“有讽有劝”则正是传递理念给读者,让碑志也拥有教育意义。
从这一视点来看,碑志这类历史资料除了歌功颂德,还往往会有这样一种讽喻的特征,也需要注意。不过,对于义理和实证的把握,则肯定会因人而异,失衡之处也往往而在。前面分析姚燧撰写神道碑强调仁爱止戈,恐怕就有理念压倒事实的记述偏颇。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逻辑的力量敏锐地分析,刊谬补缺,揭示表象背后的实际,凸显水面下的冰山,去接近走向历史真实的无穷大。
此外,对正规史籍和碑志史料,在绵密辨析的基础上,应当予以重视的同时,对于方志文献中的记载也不能忽视。方志文献多为各处当地文人所编纂,往往会保存一些珍贵稀见的独家史料,并且在编纂之际会不遗余力地去搜寻与本地相关的史料入书。同时,方志由于具有递修的特点,即使晚出的史料也多是转录自前代的方志,颇可取信。比如前述《嘉靖南安府志》就收录了黄文杰的《上犹县治记》,而《嘉靖江西通志》以及《康熙上犹县志》等也明确记载了南安屠城②[明]林庭㭿修、周广纂《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七载:“李梓发,上犹人。丙子岁,元塔出元帅攻犹,梓发与都帅张伯子、同邑阳清叟、刘渊子、张南仲固守。城围七旬,弗克师退。己卯,贾参政者复至,获邑士黄桂发才英,劫令将省榜入城招降,梓发杀之,率民巷战。势穷,以酒肉别家人,令健卒杀老幼四十七口,乃与子自焚死。城遂屠,伯子等同遇害。”章振萼纂《康熙上犹县志》卷一载:“元参政贾居贞攻上犹,邑人李梓发等率众守城,不屈城屠。”。
去伪求真,揭示并是正错误的历史书写,这种知识考古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一项基本研究作业。在大数据时代,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存在,给了研究者充分驱使史料的广阔空间,让检索史料变得相当便捷。只要手勤且方法得当,自会集所需各种史料于一编。而史料的充分把握,则会使研究者不再一叶障目,接近历史真实。然而,这就更为考验研究者的考证功夫与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