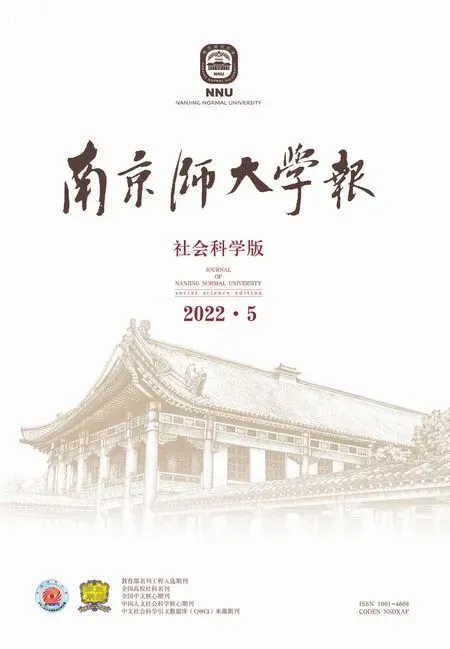控制股东义务的法构造
潘 林
控制股东规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中的关键问题。一方面,我国公司实践中,控制股东往往享有真实的治理权力,责任追究中却难以将其识别为责任主体,公司治理中的权力与责任错位,造成了“有权者无责,有责者无权”(1)赵旭东:《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及其法律规制》,《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的局面。另一方面,封闭公司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突出,遭受股东压制的中小股东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基于比较法上的观察,我国公司法学研究中存在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诚信义务、利益冲突交易的司法审查、控制股东转承董事义务、股东压迫、实质董事等等多种学理与规范方案。所有与经营分离、表决权自由行使、资本多数决等是公司法的基本假设与逻辑前提。对股东的问责,也存在基于股东身份的表决权行使以及超越股东身份的实质控制公司经营两个层面。(2)参见张辉主编:《公司法改革的思考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0页。厘清控制股东所负有的义务,应区分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以及作为管理者的控制股东两个层次。作为所有者,应界定控制股东所负义务的性质,当控制股东介入公司经营,应限定所有者与管理者身份转换的条件,进而给出我国控制股东规制的线索和方法。
一、 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
基于资本多数决,控制股东的表决权行使能够支配少数股东在公司中的利益。控制权转让使公司易主,控制股东对其控制股份的处分也直接关系少数股东的利益。由此,控制股东在表决权、处分权等权利的行使中负担某种义务。但这一义务作为公司所有者的义务,在性质上不同于管理者的信义义务,只要不存在控制股东的利益冲突交易,这种义务停留在民法层面,并非一种组织法上的义务。
(一) 表决权行使中的义务
即使是在董事会中心下,控制股东也往往能够通过行使表决权控制公司的管理者选举、章程修改以及公司的结构性、根本性变化。我国《公司法》给予了股东会相当的经营决策权力,包括增资、减资、利润分配等等。基于控制股东表决权行使对少数股东的支配或者影响,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在表决权行使中负担何种义务?
首先,控制股东表决权行使中容许控制股东的“利己”,不同于公司管理者,控制股东并不负有“利他”的信义义务。在控制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行为,基于控制股东身份和董事身份所作出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Thorpe v.CERBCO,Inc.(3)676 A.2d 436(Del.1996).一案中,既是控制股东,又占据了一半董事席位的Eriksons家族收到了购买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的要约。Eriksons则提议买家购买其在母公司的股份,并暗示他们会利用表决权来阻止子公司的出售。Eriksons并未将最初的要约通知其他董事会成员,并最终与买家达成了溢价出售所持股份的协议。法院认为,在买家就购买公司资产与其最初接触时,Eriksons作为公司董事,与公司竞争,且未将该要约告知其他董事,Eriksons违背了作为董事的信义义务。但是,既然Eriksons作为公司股东,有权利投票反对子公司的出售,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司机会损失。在In re Digex,Inc.S’holders Litig.(4)789 A.2d 1176(Del.Ch.2000).一案中,法院也基于类似的事实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控制股东在表决权行使中,并不负有董事作为管理者所负有的充分披露、将公司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忠实义务。“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属于具有信赖基础的组织法意义上的契约关系。”(5)李安安、张仪昭:《董事离职补偿制度的理论反思与规则再造》,《证券市场导报》2022年第3期。控制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不同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董事应回归委托关系的法律语境,控制股东与公司是股权投资关系,并非受托关系。(6)参见傅穹:《公司利益理念下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本土治理与重构》,《学术论坛》2021年第4期。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出发点是股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无须牺牲自身利益,股东的利己是公司资本形成的基础,也是无法扭转的逐利动机。股东在表决权行使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类似于民法上所有权的行使,并不为组织法所评价,或者说公司组织的逻辑就在于“通过锁定多数股股东,并禁止非按比例地分配,多数股东在最大化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同样会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价值”。(7)E.B.Rock & M.L.Wachter,“Waiting for the omelet to set:Match-specific assets and minority oppression in close corporations”,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Vol.24,No.4,1999,pp.913-948.
其次,控制股东的表决权行使不容许“损人利己”,即不允许控制股东通过牺牲少数股东利益换取自身利益,控制股东的利益冲突交易受到公司法的规制。例如,在Sinclair Oil Corp.v.Levien(8)280 A.2d 717(Del.1971).一案中,控制股东持有公司约97%的股份,并提名了公司的全部董事。由于控制股东的现金需求,它推动公司进行大量的现金分红。公司小股东起诉控制股东,认为其促使公司分红的行为存在不良动机。除此之外,控制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并存在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违背合同约定的最低购买数量等违约行为,但控制股东没有使公司寻求违约救济,对此原告小股东要求控制股东作出赔偿。此案中,法院对分红与违约行为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在公司分红中,尽管控制股东获得了大量现金,但小股东并未被排除在外,也是按比例获得了分红。控制股东尽管存在自利的动机,但并未排斥小股东按比例获益,因此并不构成利益冲突。相反,法院支持了原告在违约问题上的赔偿请求,控制股东从违约中获益,而小股东则因公司放弃违约救济遭受损失,控制股东通过牺牲少数股东利益而获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公司决策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是一种常态。但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分歧并不必然构成公司法所规制的利益冲突。例如,在In re Synthes,Inc.Shareholder Litigation(9)50 A.3d 1022(Del.Ch.2012).一案中,董事会着手为公司寻找买家。公司面临两个可选的要约:一是由私募基金作为买家,以现金收购股份,但由于无力支付全部股份的转让款,买家要求控制股东将其部分持股转换为收购后的新公司的股份。二是由强生公司作为买家,收购公司全部股份,但其中65%以强生公司股票的形式支付,35%以现金形式支付。由于控制股东拒绝将其持股转换为新公司股份,公司最终接受了强生公司的要约。公司的小股东提起诉讼,认为控制股东对流动性的追求构成了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法院认为,本案中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都希望获得流动性,控制股东有权根据自身利益行使表决权,控制股东不必放弃自身利益以达成少数股东所期望的交易,进而驳回了少数股东的诉讼请求。
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公司的决策不可能对所有股东毫无偏袒,公司的决策也不可能不受控制股东风险偏好、现金需求、流动性追求等私人动机的影响。实际上,公司决策作为一种商业判断,法官也难以估算如果排除控制股东的影响,公司作出另一种选择是否更优。公司的决策对大股东有利本身并不构成利益冲突。(10)P.J.Dalley,“The misguided doctrine of stockholder fiduciary duties”,Hofstra Law Review,Vol.33,No.1,2004,pp.175-222.除非公司决策以牺牲少数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控制股东获益,控制股东对公司决策的控制、控制股东私益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并不受到组织法的特别评价。这仍然是一种民法层面的义务,是一种利己但不损人的市民社会朴素观念,这种义务与公司管理者负有的将公司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信义义务相比,仍然是微弱的。
(二) 处分权行使中的义务
控制股东对所持股份的处分同时转让了公司的控制权,这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未来走向,进而影响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同时控制股东基于其持股比例和控制地位,在转让股份、获取流动性方面具有相对于中小股东的优越地位。这种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以及相对于中小股东的优越地位是否产生某种义务?
首先,控制股东转让控制股份是所有者对财产的自由处分,尽管会影响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并不负有公司法上的信义义务。美国一部分判例认为控制股东在转让控制股份时负有对买方作出调查的注意义务,这类判例被称为“劫掠(looting)”判例。(11)J.Dammann,“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duty of care:A dogma that should be abandoned”,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Vol.2015,No.2,2015,pp.479-506.在这类案件中,受让控制股份的买家在取得公司控制权后,通过自我交易等方式掠夺公司财产,最终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控制股东转让股份时,往往已经出现了买家是劫掠者的危险信号,但控制股东并未停止出售或者作出进一步调查。买方的出价包含了控制公司后劫掠公司财产的预期,控制股东从高价中获益,牺牲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劫掠”判例中支持控制股东注意义务的理论基础,有判例认为控制股东选任以及控制公司董事,所以应承担董事的责任。但控制股东转让股份无须董事的参与即可达成交易,公司董事并未违反信义义务。(12)J.C.Carter,“The fiduciary rights of shareholders”,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Vol.29,No.4,1988,pp.833-834.此处控制股东对买方作出调查的注意义务也迥异于公司出售时董事的注意义务,董事应负有知情决策、尽职调查等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高度注意,而控制股东只有在买方可能是公司劫掠者的危险信号出现时负有进一步调查或戒绝交易的义务,(13)参见朱锦清:《公司法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32页。除此之外控制股东并不负有对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注意义务。财产自由处分仍然是控制股东处分控制股份的原则。控制股东负有的仅仅是不将控制权转让给公司劫掠者的义务,这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信义义务,而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协助他人侵权的义务。(14)Perlman v.Feldmann,219 F.2d 173,179(2d Cir.).
其次,控制股东在获取流动性方面的优越地位并不使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负担义务。在这一问题上,Jones v.H.F.Ahmanson & Co.(15)460 P.2d 464(Cal.1969).一案饱受争议。该案中,控制股东组建了一家控股公司,并将其持股转让给了这家控股公司,然后推动该控股公司公开上市,由此为控制股东所持股份创造了市场和流动性。法院认为,由于控制股东的这一行为,少数股东的股份不可能再享受公开市场,因此判决少数股东胜诉。学者认为,股东为其股份创造市场其实是股东为其股份找到买家的另一种说法,股东在处分股份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在任何时机将其股份转让给任何人,除非股东有理由相信买方将从事不当行为。(16)P.J.Dalley,“The misguided doctrine of stockholder fiduciary duties”.该案中控制股东的行为并没有使少数股东的处境变得更糟,不同于之前的判例,控制股东也没有通过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而获益。因为,控制股东控制公司,所有股份包括少数股东的股份是否具备公开市场这一问题本来就在控制股东的控制之下。(17)P.J.Dalley,“The misguided doctrine of stockholder fiduciary duties”.
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无论是行使表决权还是处分控制股份,并不负有管理者的“利他”的信义义务,控制股东有权利“利己”。实际上基于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利己”与“损人利己”的界限也并不十分清晰。“一些法院很明显地感觉到存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在这一范围里控制董事或股东以其私利行事,即使少数股股东因此而受损。”(18)Wilkes v.Springside Nursing Home,Inc.,353 N.E.2d 657,662(Mass.1976).基于控制股东的所有者身份,“损人利己”应排除控制股东的私利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控制股东相对于少数股东的优越地位本身,而被限定为通过牺牲少数股东利益换取自身利益的利益冲突交易。控制股东基于所有者身份的权利行使,这一层次上控制股东所负有的义务更多地停留在民法、侵权法层面。
(三)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与股东压迫的关系
作为公司所有者,控制股东以私利为出发点行使表决权、处分权等,并不负有将公司与少数股东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忠实义务,也不负有知情决策等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高度注意。因此,控制股东并不负有信义义务。比较法上经常可见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这一表述名实并不相符。类推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及强调救济实效的实用主义传统,造成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名称与内涵之间的疏离。(19)参见靳羽:《美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原厘定与移植回应》,《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在我国《公司法》中简单移植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不仅是对控制股东的公司所有者身份的误解,也会造成成文法中概念体系的混乱。
从制度源流与功能的角度审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它与股东压迫制度发挥了近似的功能,旨在为封闭公司中的受压迫股东提供救济。封闭公司股东人数少、股份缺乏市场以及股东参与管理的特征决定了封闭公司中的股东存在雇佣、薪酬等方面的期待,这一期待受到法律保护,公司法通过股东压迫制度为期待落空的少数股东提供股份回购、公司的非自愿解散等救济。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在Donahue v.Rodd Electrotype Co.(20)328 N.E.2d 505(Mass.1975).一案中,法院将封闭公司类比合伙,认为封闭公司中的所有股东互相负有展现最大善意及忠实的信义义务,而且不能出于贪婪或私利违反他们对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忠实义务。但封闭公司显然在本质上不同于合伙,最为关键的,合伙人并不享受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马萨诸塞州法院仅在一年之后就修正了该案的立场。在Wilkes v.Springside Nursing Home,Inc.(21)353 N.E.2d 657(Mass.1976).一案中,法院认为,控制股东有权利以一种“自私”的方式管理公司,法院将以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对这种“自私”的方式进行平衡。法院认为,控制股东在以下情况即满足信义义务的要求:其一,控制股东表明其行为的合法商业目的;其二,少数股股东无法提供一种替代方式,这一替代方式将对少数股股东的利益造成较少的损害。
一方面,美国有十三个州缺少股东压迫的成文法,以马萨诸塞州为典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在这些州发展起来,以回应封闭公司的特殊规制需求。(22)R.B.Thompson,“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Business Lawyer(ABA),Vol.48,No.2 1992-1993,pp.699-746.尤其是,在采纳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院,判断违反信义义务的标准与其他法院非自愿解散救济中对股东压迫的认定标准基本相同。(23)R.B.Thompson,“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一些存在压迫立法并承认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州,法院也是基于个案事实,在解散、回购救济与基于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中进行选择。当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仍可维系,法院基于信义义务作出判决,当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难以为继,法院则提供解散或回购救济以解除关系。(24)R.B.Thompson,“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美国判例法中名不副实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发挥了股东压迫的制度功能,股东压迫则有其特有的适用情境与条件,在此意义上,通过移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实现控制股东有效规制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二、 作为管理者的控制股东
控制股东的控制地位本身并不产生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比较法上所谓基于控制股东对董事的控制,控制股东转承董事信义义务的主张,应重新审视其实证依据。当控制股东越过所有者身份,指令、操纵公司的经营决策,此时控制股东已经由所有者身份切换到管理者身份,所负有的义务性质也彻底转变。但只要认同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公司法前提,就应严格限定这种身份切换和义务转型的条件和情形。
(一) 股东控制是否转承董事义务
控制股东转承董事义务的逻辑在于,董事由于顺从控制股东,其行为背离了公司利益最大化目标,董事即违反对公司的信义义务,此时公司得基于代理法向股东提起诉讼。(25)J.C.Carter,“The fiduciary rights of shareholders”.控制股东转承责任的依据在于代理法,控制股东被拟制为委托人,董事则被拟制为控制股东的代理人,控制股东承担责任不是基于其对公司的直接义务,而是源于代理关系,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转承责任。(26)参见范世乾:《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国公司法相关制度的构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72—76页。
控制股东转承董事的信义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责任,实际上这一主张依据不足,或者至少是不清晰的。美国判例法中的转承理论并未被清晰界定,适用也较为随意。一方面,转承理论被应用于“劫掠”判例。例如,在Harris v.Carter(27)582 A.2d 222(Del.Ch.1990).一案中,法院认为,当股东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利,指示公司的行为,股东就承担了与董事相同的信义义务。而实际上,在“劫掠”判例中,控制股东仅仅是转让控制股份,这一行为并不需要董事介入,也不存在控制股东对董事的干预。在此情形下,控制股东转承董事义务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控制股东转承的义务与董事义务并不一致。对于注意义务,美国绝大部分州允许通过公司章程豁免董事因违反注意义务产生的赔偿责任,转承董事注意义务的控制股东能否享受此种责任豁免并不清晰。(28)J.Dammann,“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duty of care:A dogma that should be abandoned”.对于忠实义务,在董事的自我交易中,如果存在股东会批准或者多数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同意,司法审查标准将由严苛的整体公平标准退回到商业判断规则。而在控制股东的自我交易中,由于法院认为控制股东带来的威胁远远高于董事,无利害关系股东的批准以及多数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同意等安全港程序通常不会改变整体公平标准作为司法审查标准,仅仅是可能带来证明责任的转移。(29)J.Dammann,“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duty of care:A dogma that should be abandoned”.
转承理论之所以难以被清晰界定,在于其拟制了控制股东与董事之间的代理关系。代理关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委托人指示、命令代理人作出经营决策仅仅是其中一种直接的情形,除此之外,尚存在代理人在委托范围内为委托人利益行事等间接的情形。究竟在何种情形下对应控制股东与董事之间的代理关系,进而使控制股东转承董事责任是模糊的。转承理论作为美国判例法中论证控制股东承担董事信义义务的理论依据,难以被我国成文法移植和借鉴。控制地位本身并不附加义务,除非存在显失公平、欺诈或者胁迫,法律通常并不干预商业世界中财富、议价能力、成熟度等方面的不平等、不均衡,因为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必然会为能力或投资方面的优势带来回报。(30)P.J.Dalley,“The misguided doctrine of stockholder fiduciary duties”.控制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在何种条件下应切换到公司管理者的身份,承担公司管理者的义务与责任,需要清晰且严格的限定。
(二) 影子董事的认定
在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假设与前提之下,公司组织以董事会为权力中心与决策权威,董事拥有公司业务中“独立的自由裁量权或者判断”,(31)[马来]罗修章、王鸣峰:《公司法:权力与责任》,杨飞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91页。董事的权力与责任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线索,成为识别、评价公司行为的依托。控制股东对公司决策的操纵通过对董事的干预、指示、命令而实现,比较法上规制控制股东的一种路径就在于将操纵董事判断和决策的控制股东识别为实质意义上的董事,进而使控制股东承担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实质意义上的董事包括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前者是指缺乏有效任命,却以董事身份行事的人,既包括从未被任命为董事的情形,也包括有任命瑕疵的情形。后者是指“公司董事习惯于根据其指导或指示而行事的人”。(32)葛伟军译注:《英国2006年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10—213页。影子董事与事实董事的区别在于,影子董事并不以董事身份行事,而是通过操纵董事以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影子董事的指示和命令替代了董事的独立判断和自由裁量。控制股东、作为公司担保债权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构成影子董事。影子董事的认定有着严格的限制和条件。首先,影子董事的认定是基于一定时期的多种行为,董事对影子董事的服从必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33)C.M.Hague,“Directors:De jure,de facto,or shadow”,Hong Kong Law Journal,Vol.28,No.Part 3,1998,p.308.其次,服从影子董事指示的董事必须达到董事会的多数,仅仅是少数董事的服从不足以构成影子董事。例如,在Kuwait Asia Bank v.National Mutual Life Nominees Ltd.(34)[1990]BCLC 868.一案中,公司的五名董事中,控制股东仅仅控制了其中的两名,不足以成为影子董事。
事实董事以董事身份行事,与董事承担相同的义务与责任。但董事的义务是否当然适用于影子董事,在判例法中并不清晰。英国公司法第170条(5)的表述是:“当能够适用时并在此范围内,(董事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公司的影子董事。”(35)葛伟军译注:《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41页。按照这一规定,影子董事是否承担董事义务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分析。“影子董事需要就其对结果做出指示的任何相关决策承担事实董事所有的一般义务,但对于影子董事是否也要承担其他义务,例如寻求公司机会的义务,则需要基于个案而做出更为细致的认定。”(36)[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上册),罗培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498页。实际上,相较于事实董事,影子董事对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有力,事实董事仅仅是个人履行董事职务,而公司大部分董事习惯于听从影子董事的指令。(37)C.R.Moore,“Obligations in the shade:The application of fiduciary directors’ duties to shadow directors”,Legal Studies,Vol.36,No.2,2016,pp.326-353.但影子董事是对董事决策施加影响与控制,除此之外,影子董事仍然具备公司所有者身份,与事实董事以董事身份行事、身份完全切换到公司管理者不同,影子董事的身份切换并不彻底。影子董事对董事会的控制是与其发出指令的决策相关的,其作用于董事决策的方式是间接的。因此,影子董事是否承担董事义务不能一概而论,这并非因为对影子董事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弱于事实董事,而在于两者影响与控制公司的方式不同。
三、 控制股东规制的公司法构造:以董事责任为中心的规范体系
控制股东首先是公司的所有者,其负有的义务具有层次性。规制控制股东,应区分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与作为管理者的控制股东。基于这一层次,公司法上的控制股东规制一方面应承接公司机关决策权力配置中的董事会中心,由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衍生控制股东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义务与责任。另一方面应确立控制股东规制的规范体系,形成影子董事、关联交易、股东压迫等制度的协同与合力。
首先,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中心与决策权威,规制控制股东对公司决策的干预、指令,仍应承接董事会中心,将控制股东识别为实质上的董事,使控制股东承担董事的义务与责任,以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衍生控制股东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义务与责任。“通过实质董事的规制路径和通过控制股东的规制路径是存在价值差异的,其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肯认董事在公司管理中的中枢地位。”(38)刘斌:《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将其识别为实质董事之所以是最佳的规制方案,在于控制股东本来具有公司所有者身份,公司所有者的多数行为可类比民法上所有权的行使,从而落入侵权法的规整范围。直接向控制股东施加公司法上的义务,将产生公司法上以所有者为线索的义务和以管理者为线索的义务,这一方面与所有者的身份不符,另一方面也会使公司的权责逻辑产生混乱,进一步模糊董事会的中心地位。比较法上已经出现对实质董事制度及其逻辑的大范围借鉴。例如在韩国,“1998年修正商法为防止公司的运营被控股股东的影响力歪曲,新设了追究作为非董事者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业务执行者责任的制度”。(39)[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8页。韩国公司法中指示业务执行者责任制度的要件同样被严格限定,例如“行使影响力的对象应为公司。实质董事对董事个人行使影响力的情形并不包含在内”“指示应为通常的、惯例性的指示,而非一次性指示”。(40)[韩]崔埈璿:《韩国公司法》(上),王延川、崔嫦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74—475页。在日本公司法中,“作为一种间接规制,通过判例确立了所谓的‘事实董事制度’”。(41)朱大明、[日]行冈睦彦:《控制股东滥用影响力的法律规制——以中日公司法的比较为视角》,《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指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被认为是借鉴了域外的影子董事制度。但《公司法(修订草案)》以及这一认识有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1条沿用了民法上共同侵权的逻辑,它并未将控制股东对公司权力的行使纳入组织法的权责逻辑之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所谓教唆行为,是指怂恿、指使他人为加害行为,为他人作出加害决定发挥了影响力”。(42)邹海林、朱广新:《民法典评注·侵权责任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50页。《公司法(修订草案)》中控制股东的“指使”即符合《民法典》第1169条中的“教唆”,此时控制股东与受指使的公司管理者被视为共同侵权人。第一,《公司法(修订草案)》的描述实际上并未突出公司组织对控制股东的规制,如果是其他主体“指使”“教唆”公司管理者,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公司法(修订草案)》并未将控制股东的责任承担纳入公司治理与权责框架,在组织法的逻辑中,“指使”与责任承担之间缺少了控制股东的身份切换,由此控制股东担责的依据只能诉诸民法共同侵权的原理来解释。第三,“承担连带责任”从法律后果与民事救济的层面规范控制股东行为,规制效果不及组织法中将控制股东认定为影子董事,使其直接承担董事信义义务与责任。第四,《公司法(修订草案)》以“指使”描述控制股东的行为,失之粗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组织法中职权替代、董事丧失独立判断的语境,与影子董事的严格界定相去甚远。
其次,区分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与作为管理者的控制股东,这一层次性也说明控制股东规制无法诉诸单一制度,而需诉诸一个规范体系。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这一主张之所以备受争议甚至名实不符,根源也在于混淆了控制股东的所有者与管理者身份,忽视了控制股东规制的层次与体系。在判例法中,这一概念和制度或可通过法官造法,进而在特定情境中以不同的解释回应个案事实,成文法下,引入这一概念和制度则会带来体系上的混乱。除非存在控制股东为求私利而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交易,作为公司所有者控制股东规制在相当程度上归入侵权法范畴。由是,公司法上规制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应集中于利益冲突交易的制度建设。同时旨在维护少数股东期待的股东压迫制度回应了封闭公司股东人数少、股份缺乏市场以及股东参与管理的特殊性,畅通股东压迫的救济渠道也可在封闭公司中分解对控制股东的规制。作为公司所有者,控制股东向管理者的身份切换被严格限定,实质董事制度有着严格的规范构成。关联交易、股东压迫与实质董事各有制度适用的场景和逻辑,共同形成控制股东规制的制度合力。
我国公司法中的关联交易制度、股东压迫救济制度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关联交易的规制角度在于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这并不能涵盖所有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冲突交易。尤其是,关联交易制度仍存在忽视公司程序对交易公平性的引导和控制、缺乏商事交易中程序性公平的经验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规定,关联交易损害赔偿中,“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实质大于形式”的朴素立场下,有必要重申,合法程序掩盖实质不公与公司制度中程序技术的粗疏是两个问题。规制前者固然重要,因应利益冲突交易的复杂多变,针对安全港程序的类型化、精细化作业可能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此外,有关股东压迫救济,《公司法》第74条中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制度,“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易被规避,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科学且清晰的“合理价格”计算标准。同时《公司法》第18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表明,股东压迫无法适用司法解散救济。(43)李建伟:《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而比较法上,非自愿解散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并列为股东压迫的主要救济。我国实质董事制度缺位,加之关联交易制度和股东压迫救济制度的疏漏,制度合力远未形成,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等主张未及在比较法中系统审视、在成文法语境下充分论证,便被寄予了有效规制控制股东的期待。
四、 结语
控制股东首先是公司的所有者。规制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主要是一个民法、侵权法问题。在“利己”与“损人利己”之间,公司法对控制股东的规制应排除控制股东私利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控制股东相对于少数股东的优越地位本身,而应被限定为控制股东的利益冲突交易。当控制股东越过所有者身份,指令、操纵公司经营决策时,控制股东的身份切换到公司管理者,但这一身份切换的条件应被严格限定。区分作为所有者的控制股东与作为管理者的控制股东,决定了公司法对控制股东的规制应承接董事会中心,通过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衍生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这一层次也决定了,控制股东的公司法规制无法通过诸如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等单一制度实现,因应控制股东的身份与特定的情境,影子董事、股东压迫、关联交易等应形成制度协同与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