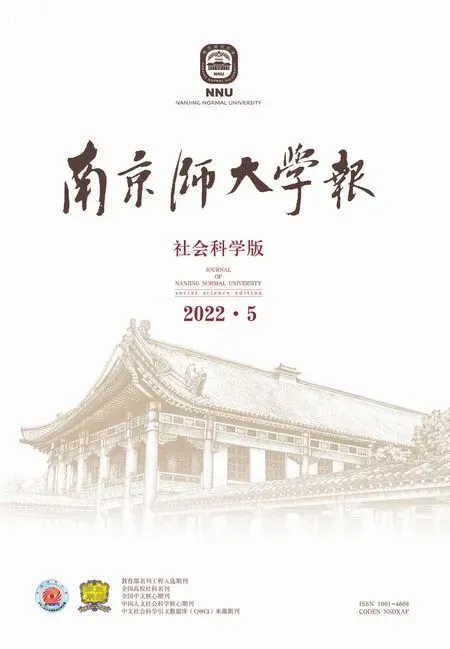立德树人:教育学科实践属性的新时代锚点
宋 萑 付 钰
长期以来,教育学科的学科地位、学术定位都是有争论的议题,即便中外教育学人在两百年的时间对教育学科贡献良多,但是“‘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1)[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3页。等类似于华勒斯坦的批评仍悠然在耳。当然不只是社会科学领域内部有异议,更大的质疑来自教育领域内部,来自教育实践者,教育学科所提供的种种理论、策略、方法总被指责对实践适应不良。实践者对教育学科的“距离感”并不意味着实践领域不需要理论(2)吴黛舒:《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探析》,《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而是在对教育学科所追求体系完美与抽象还原的象牙塔式理论构建路径的失望之后(3)李军靠、胡俊生:《论面向实践的教育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意义》,《现代大学教育》2009年第5期。,只能依靠实践内部的积累、互动与不断试误所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认识,虽然没有前者“高大上”,但是“接地气”,能解决问题。而反观国际教育学界,自杜威以来,教育学的实践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哲学思辨式的概念演绎和理论建构已然不是国际教育学的主流,量化研究、质性研究、行动研究进入教育学的方法论范围后,基于证据的教育学知识建构成为主体,并在实践领域中通过不断应用、检验、再建构实现知识不断创新迭代。从近年来国内所翻译的国外教育书籍中越来越多的是指向实践且具有理论支撑的应用类著作就可见一斑,而从SAGE、SPRINGER等国际出版公司中教育领域著作类型占比也能看出应用类更高一筹。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翻译、引介去吸取国际教育学领域的优秀成果、前沿成果,这些成果可能会对中国教育实践者有所助益,但正如吴康宁教授所言:“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和本土实践之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规引中国人的教育实践”(4)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学界“尊奉”西方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因此中国教育学科要回答其他学科异议、要回应实践者的诉求,原先那条书斋式“水中捞月”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把希望落在引介外力也非长久之道,惟有回归教育领域的丰富实践,在对教育现实问题的不断提炼、探求、分析、解决中,才能建设“把学问书写在祖国大地之上”的中国教育学科。
一、 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
杜威早在1896年出版的“Pedagogy as a university discipline”中就提出教育科学本质上是实验的科学而不是演绎的科学,需要通过实验学校来验证、批判增进专门领域的事实与原则(5)J.Dewey,“Pedagogy as a university discipline”,University Record,Vol.1,1896,pp.353-363.。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学科是为服务于教师的教育教学专业工作而确定其核心内容与价值。
一方面从教育学科的历史溯源来看。教育学一开始就是作为教师教育的教育学的形态而诞生的(6)薛晓阳:《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课程功能辨析》,《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从早期讨论如何教育儿童,到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以心理学为基础来塑造科学教育学的尝试,再到泰勒“八年研究”中建构系统化课程论和布鲁姆对目标分类学及其评价理论创新,西方教育学主流一直致力于对教育实践领域系列问题的研究和推进。而从教育学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并独立建制的历史回顾来看,虽然有教育学术研究、教师教育专业建设和社会问题解决等多种路径,但是教育学对教育实践持续关注、对教师培养的支持功能发挥、对教育教学工作科学化地提供支撑是核心主线。当然其中也有特例,像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取径完全脱离教育实践专注高深学问的社会学式路径,进而被并入社会科学学部,终究摆脱不了被关闭的命运。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兴衰实际上已然说明,想通过脱离教育实践,借力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外部学科来进行杂烩式教育研究,是无法让教育学科在大学真正获得一席之地的。而相形之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一直所坚持的以服务教师教育教学实践为中心的教育学术之路,却赢得来自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双重尊重(7)孙岩:《美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历史考察》,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7年,第404—461页。。
另一方面从教育学科的价值原点来看。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在学术领域中立足,形成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不取决于其学科知识体系是否完备,也不取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专一性和独特性,而是取决于其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价值”功能(8)林丹:《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抑或学科功能?——理性审思教育学学科地位的独立原点》,《教育学报》2007年第3期。。以现代医学科学为例,虽然其学科重大发展主要集中在19世纪到20世纪,却在传统大学学术圈树立了极高的学科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为人类健康和疾病治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现代医学学科通过对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建构和丰富着循证式诊疗知识,从而在治病救人的功能发挥中建构起学科的价值(9)S.Straus,P.Glasziou,W.Richardson & R.Haynes,Evidence-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5th Ed),Edinburgh:Elsevier,2019,pp.18-22.。相较社会学、人类学等传统社会科学,教育学科从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医学,因为前者更偏重对现象的解释、对规律的发现,而后者则是在解释现象、发现规律的基础上去解决问题、不断改善,进而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进行知识化和迭代化。因此教育学作为以教育领域现象、问题为对象的学科,不能只停留于解释与分析,而更要发挥指导和改造的功能。因为其他社会科学都能够以教育为对象,并借助其各种理论工具来开展解释和分析,而教育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和改造。与此同时,传统上高等教育中教育学院的建制与医学院、法学院类似,是作为一种专业(profession)学院而存在,其专业核心特质就在于其服务他人的使命,与医学、法学一样,教育学指导改造实践的独特价值是与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养子使作善”的道德活动密切关联着的,教育学科各种知识构建不可能离开“向善”的目标而价值无涉的存在。
这里我们已经初步言明教育学科应是一种实践属性的学科,那么在当前时代背景中,由于中国教育实践有着独特的脉络、现象、问题,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内涵也必然随之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对当前中国教育的任务、特征做了系统阐明,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必然会反映到中国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之上,教育学科必须要从立德树人高度重新确立学科发展定位。而从“学科”概念的核心内涵来看,其一是指知识的系统,其二是指对人的培育和学科规训(10)庞青山:《大学学科结构与学科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第11页。。考虑到教育学科作为服务教育实践的专业性学科,其在培育规训上则会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支持肩负实践使命教育者的培育,二是教育学科专业研究者的培育。这一点就与医学学科类似,其首先透过循证式研究夯实专业知识基础,进而支持医护人员培养以践行专业使命,并着力培育基础医学研究人才来延续学科自身发展。因此,本文就参照专业性学科构建的三个主轴来分析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知识谱系、专业使命、人才培育——以进一步探讨教育学科如何从立德树人定位重新定义实践属性。
二、 新时代教育学科的知识谱系拓展——创新立德树人研究
教育学科从诞生到现在,其理论形态主要经历了经验描述形态、哲学思辨形态、科学实证形态、精神科学形态和综合规范形态(11)张忠华:《教育学学科科学性研究探索》,《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2期。。虽然学界对教育活动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尚有异议,但是教育学作为一个专门性学问或知识系统,其本质上一定是科学,是需要对特定对象开展研究并进而形成能经得起实践或实验验证的专门知识。在当前我国教育工作核心任务定位于“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前提下,教育学科需要关注研究立德树人教育实践工作的现象和问题,并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教育学理论,从而实现教育学科知识谱系的拓展。
(一) 新时代教育学科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合力以立德树人工作为对象开展研究
教育学科要系统考察当前教育工作的新现象、新挑战、新矛盾、新问题,着力发现背后的立德树人规律,并在不断反思、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迭代型知识库。由此,新时代教育学科的研究主体就不限于高校的研究工作者,广大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者、教育决策者都是教育学科研究的主体,他们可以通过行动研究、自我研究、叙事研究等方式,把研究工作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而高校研究工作者一方面要推进教育学科理论研究,通过思辨批判、国际比较、文献梳理来实现理论丰富;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实证研究进入实践场域,并且与实践者通过协作式行动研究、实验研究来解决问题、验证假设和重构理论,最终实现思想创新。管理学领域中的组织创新研究发现,传统“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知识创新传播方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组织变革加速的需求,实践和理论是一对互动的知识建构组合,需要在相互刺激和碰撞中实现创新性解决办法。而边界学习(boundary learning)理论也指出,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边界可以形成“第三空间”,让双方带着各自知识、经验进入,并共同解决问题实现知识建构。其尤为强调当双方既有的一般性知识和专门性知识都无法解决当下的新问题时,问题背后不确定性与不可知挑战中反而蕴含着更多创新可能(12)P.R.Carlile,“Transferring,translating,and transforming: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managing knowledge across boundaries”,Organization Science,Vol.15,No.5,2004,pp.555-568.。事实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所孕育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等新兴科技不仅重新定义产业,甚至重新定义了“人”的概念(13)K.Schwab,“Four leadership principles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2016,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10/four-leadership-principles-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教育形态也必然随之更新,翻转课堂、智慧学习、在线教学、VR交互都在重塑着信息时代的教育教学,实践者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正如此次疫情所带来教育全面在线化,很多教师难以适应,如何组织在线师生、生生互动?如何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如何和家庭形成支持型共同体?如何利用疫情来进行生命教育、价值教育?这些新问题并没有成例或现成答案,都需要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管理者、决策者共同关注和研究,在问题解决中实现思想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立德树人实践及其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脉络只有参与到教育思想的构建和教育学知识的创新之中,才有可能创生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真正有意义的教育思想(14)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学界“尊奉”西方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
(二) 新时代教育学科要基于立德树人循证实践实现循证教育学转向
虽然我国教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引入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开展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叙事研究、个案研究,但研究成果的实践影响力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不少实证研究的研究问题缺乏实践价值,一些量化研究所验证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在实践者眼中多是不证自明的常识,而部分质性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解释总带有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印记。与此同时,教师做科研、写论文也从一时风潮转而成为专业制度的必要功课,虽然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从成果形式上看仍多停留于经验总结、案例合集,甚至很多时候,研究变成教师的负担而非实践的助力。这里并不是否认这类实证研究和经验总结式论文的价值,而是希望教育学人能多注意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和实践者亟需的专业支持。那么何种研究范式更符合教育学科实践属性的要求呢?其实同为专业学科的医学是可做借鉴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强调整合最佳研究证据、临床专业智慧与经验、病患的独特价值与环境,通过“界定可回答的研究问题—追溯最佳研究证据—审辩式判断证据可靠性与可行性—依托专长经验整合到医疗实践—评估效能并寻求改善”的循证模式来不断丰富和推进知识迭代(15)S.Straus,P.Glasziou,W.Richardson & R.Haynes,Evidence-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pp.18-22.。教育实践作为同样面对人的工作,儿童的特殊性和环境差异、变化都意味着难有某种“独步单方”能解决所有教育教学问题。因此教育学科的知识积累必须要有研究者、实践者和实践活动的共同参与,一是研究者要进入实践,并提供支持实践的可靠研究证据;二是实践者要信赖研究证据,以证据来支持专业决策和行动;三是要把实践活动的情境特殊性、对象差异性视为助力而非障碍,不是为验证理论去寻找实践,而是利用实践复杂多变来实现知识创新。可见,循证实践可以将研究者的知识优势、实践者的专业经验、教育对象与环境的独特价值都发挥出来,共同为做好立德树人工作贡献力量,其必将为新时代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一条康庄大道。
(三) 新时代教育学科要逐步构建有关立德树人的多元知识体系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技术理性所主张的知识客观性、中立性、一致性、确定性提出一系列的批评,“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主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生活环境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6)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因此知识具有差异性、不确定型、个体性、权力性(17)宋萑:《后现代主义与课堂教学改革》,《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4期。,应当“将各种知识作为相互协调的人类经验,消解知识间的等级和科学界限。”(18)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32.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有着相似的知识观,特别是教育者所建构的实践性知识,就包含着情境性、缄默性等特质。如果从杜威的识知(knowing)视角来看,教育学科中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都是来自探究过程中经由识知浮现出的认知性经验,都终将服务于更为明智的教育实践(praxis)(19)陈向明、赵康:《从杜威的实用主义知识论看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因此新时代教育学科所构建的立德树人知识体系应当包含多种类型的知识,尤其要重视实践性知识积累与提炼。只有在立德树人的具体实践和问题情境中,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发挥自身“知性主动性”(intellectual initiative),将已有知识和经验融入行动设计,并在观察、思考、行动和不断的证据收集中进行证实;同时借助个人叙事、审辩式反思、集体协商、边界互动来实现缄默知识的外化提炼与系统联结,最终反哺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如此识知过程所逐步搭建起来的知识大厦,方能既有问题意识、实践关怀,也能彰显理论深度、推广价值。
三、 新时代教育学科的专业使命更新——培育立德树人主体
立德树人的主体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一线教师,对于一线教师的培养是教育学科最为核心的专业使命。大学学科从功能角度看主要有三种形态,分别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知识体系,根据科研发展要求所建构的知识范畴,根据社会服务需要所划分的工作领域。(20)别敦荣:《论大学学科概念》,《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9期。教育学科作为一门具有实践属性的大学学科,在培养一线教师这一立德树人的主体过程中,既需要注重对其专业知识体系的培养,也需要对其科研能力进行训练,更需要面向社会中存在的教育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因此,对于一线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实践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的培养是教育学科当之无愧的专业使命。
(一) 培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
教育学科是培养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核心学科,而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培养核心则是学科教学知识。教育学科在教师专业知识培养方面传统上只依赖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论“老三门”的状况广受各界批评,而传统教育研究所关注的教育性知识和传统学科研究所关注的学科内容知识又往往无法直接为师范生日后工作中的教学提供直接助益,导致教育学科在教师培养过程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师范生两方面的压力。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自1986年由舒尔曼(Lee Shulman)提出以来,(21)L.S.Shulman,“Those who understand:Knowledge growth in teaching”,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15,No.2,1986,pp.4-14.由于其直面课堂教学中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立德树人的范畴下,教育学科需要思考如何将师德培养通过学科教学知识来有效达成。有学者提出中国化的学科教学知识的基本内容包括学科教学法知识、学科教学论知识、学科教育学知识三个层面。(22)邢红军、陈清梅、胡扬洋:《教师教育学院:学科教学知识中国化的实践范本》,《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5期。既涉及怎么教的具体问题,也涉及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面向未来(FUTURE)学士后教师培养项目在师德培养的过程中通过特级教师口述史、教学设计等课程理解学科德育教学的基本规律,通过教育戏剧、校内实训等基于教师实践场域的课程,掌握学科德育教学方法,新时代的教育学科需要通过类似的课程将立德树人的学科教学知识进行实践性创生。
(二) 培育教师的实践科研能力
教育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既有应用和实践的成分,也有基础理论和价值的成分。(23)张斌贤:《教育学科本质上不是“应用学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因此教育学科在培养教师的过程中既涉及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培养,也涉及科研能力的训练。教育学科如果秉持着庸俗实用主义的定位而不重视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必将导致其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浅薄,面对一线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缺乏认识深度,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斯腾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埃利奥特(John Elliott)进一步提出“教师成为行动研究者”。(24)J.Elliott,Ac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hange,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24.行动研究是由实践者在实践中进行的一种研究形式,是由社会(包括教育)情境的参与者所进行的旨在增进理性和正义行动的自我反省的一种探究。(25)洪明:《基于“行动研究”的教师教育——埃利奥特教师教育思想探略》,《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9期。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其面对的对象是自身真实的实践困境,收集的是教学中的实践数据,改善的是自身实践生存状态。教师通过行动研究来提升自身实践科研能力不但可以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也可以更好地解决立德树人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三) 培育教师的社会服务意识
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了教师培养必须面向社会发展实践,培养出来的教师也应对社会中的实际教育问题报以应有的关切并提出符合学理逻辑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有学者指出“教育研究对教育教学和管理决策实践的服务水平决定了教育学科的地位。而大学的教育研究与教学和管理实践相脱离是教育学科的通病”。(26)陈晓宇:《关于我国教育学科发展若干问题的认识》,《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立德树人既需要教育学科培养出来的教师有足够的社会担当,也需要大学教育学院针对社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例如面对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特别在地广人稀、条件艰苦的农牧区中小学师资极端匮乏的问题,大学传统教育学科专业分科的培养模式很难满足中西部一线对于“一专多能”教师的能力需求,传统高校培养出来的师范生也很难在西部农牧区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青海师范大学探索开展的“西部农牧区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目,按照“综合培养,一专多能,学有特长,素质全面”的思路,从当地农牧区选拔优秀生源定向培养,培养过程方面构建了适应青海省农牧区小学教学需求的基础课、专业课、特长课和公共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课程中增加了诸多西部民俗文化符号,并构建了以顶岗支教为主轴的实践能力培训体系。(27)王金锐、冶成福:《青海农牧区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师范生培养的管理机制、课程体系、实践体系等方面均要面向当地对于教师的实际需求而设置,满足了社会对于教师的期待,实现了教育学科的实践价值与时代使命。
四、 新时代教育学科的学术人才培育变革——引领立德树人典范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立德树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是新时代赋予教育学科的崇高使命,也是教育学科实践属性的具体体现。这就需要一流高等院校作为教育学科育人改革先行者从本土理论研究、实践关怀、世界眼光等不同方面为我国高校教育学科学术人才培养引领立德树人的典范。
(一) 注重本土理论研究,打牢未来教育学人学术根基
学术人才培养是教育学科建设的第一服务对象,(28)别敦荣:《论大学学科概念》。也是教育学科制度的基本功能,(29)庞青山、陈永红:《试析大学学科制度的功能与局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更是立德树人的关键所在。教育学科整体发展情况依赖于、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具有学术创新力的教育学学术人才队伍,尤其是教育学科培养的硕博士人才,他们不仅要走进基础教育学校,而且更是高等学校教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30)朱旭东:《论教育学科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时代内涵》,《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了教育学科必然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受到特定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制约。因此教育学科需要扎根于中国大地,立足于中国教育教学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来培养中国教育学人。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历史和教育传统,而中国的教育学科研究在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学习苏联思潮和改革开放后的学习西方思潮后,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教育理论,讲好中国的教育故事。
新时代教育学科的首要任务就是注重基于本土实践的教育学理论研究,厘清中国语境下教育学科的基本定位、价值和学术理论研究规范,对青年教育学人进行面向本土实践的教育学学术范式和方法的规训,注重中国本土教育理论的传授,为教育学人未来应对中国教育实际问题提供根植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境脉的理论基础与适切的方法论依据,打牢未来教育学人的本土学术根基,培养一批又一批能服务教育实践、引领教育变革的学术人才,开创新时代中国教育学人培养新风范。当前我国教育学学术人才的培养处于师范院校为主体,北大、清华、厦大等高水平非师范研究性大学共同参与的阶段,师范院校侧重于教育教学等应用型研究,而高水平非师范研究型则以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见长,二者是教育学科建设命运共同体。(31)刘海峰、袁浪华:《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与作用》,《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这就要求新时代教育学科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有效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提升我国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有效服务我国教育实践。
(二) 走向实践关怀,建立面向实践的研究人才培养体系
回归立德树人的教育学科建设需要走向实践关怀,用饱含对中国教育实践的热情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有学者指出,“实践关怀”实质上是教育学者与实践者的互动,是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结合,也是理论与实践、学者与实践者的共同成长。(32)陈振华:《论教育学者的实践关怀》,《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第6期。教育学科走向实践关怀既需要教育学者带领青年教育学人亲近实践、走向实践进行教育研究,也需要建立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例如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生命·实践”教育学团队扎根中国大地教育实践,关注人的生命质量提高,通过对沪京苏浙鲁豫闽粤滇桂等12个生态区的18所合作研究校、200余所基地校和试验校进行贴地式介入研究,从理论反思、实践探究、方法论更新、学科元研究等四个重要方面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构建,促进学校这一生命场域的变革,(33)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教育学报》2013年第5期。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人才,开创了中国教育学派。
教育学科的立德树人根本在于培养教育学人的实践热情与实践品性,教育学人不走入实践场域必然无法从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感受到教育理论的强大力量,进而获得解决实践困难后的欣喜。但是如何建立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需要高校中的教育学科培养单位进行实践探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于教育专业的学科特性和教育家、教育学家的成长规律,确立的以扎实的学术基础、丰富的实践能力、赤诚的教育之爱、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不竭的创新精神为核心素养的教育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在四年一贯制见习实习制度,国际实践、社会实践、教育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等方面,注重培养师范生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感情,进而生发对于教育实践的热情,将从事教育实践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有效提高教育学科人才培养质量。
(三) 保持世界视野,与全球教育人才培养思想共鸣
教育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了其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要有中国的教育立场与教育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归立德树人的教育学科要闭门造车,走进一条盲目自信、故步自封的死胡同。教育学科人才培养需要一种世界视野,“在中国”以“在世界”为背景,“在世界”以“在中国”为依托。(34)李政涛:《“在中国”与“在世界”:“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学术景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中国高校教育学科在人才培养理念、模式、课程、保障体系等方面应做到总结好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与全球教育人才培养思想进行理性的共鸣。
中国教育学界自清末便开始译介西方教育思想,在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也有着长久的与世界交流融通互为镜鉴的传统。教育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人类事业,任何对于中国教育人才培养的学术研究或政府决策均应置于世界性的场域之中,在对世界同行同一问题域的综合考察之下进行理性研究与比较分析,做出符合世界潮流的探索创新。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学科在立德树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所积累的优良经验也需要提炼归纳,与全球教育学界同仁探讨交流。这既需要搭建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东亚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等交流沟通平台,也需要推动国际联合培养、海外教育实习等培养模式创新,为中国教育研究人才培养经验的世界表达创造条件。
——评《批判教育学的当代困境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