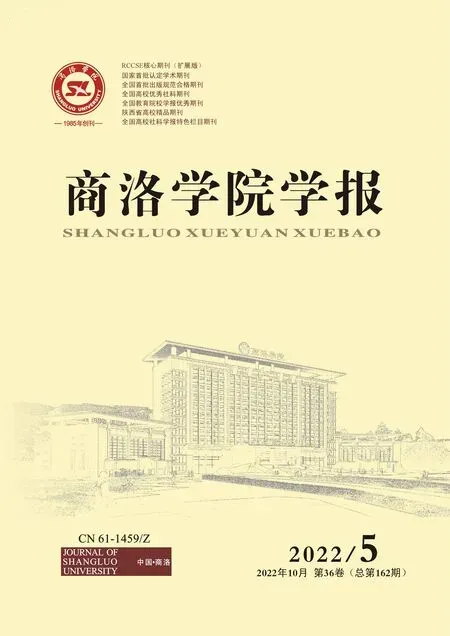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
——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刘育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127)
《诗经》研究是古代儒士、思想家、哲学家的入门功课。以“理”解《诗》是朱熹借《诗经》文本阐释其“理本论”思想的体现,亦是经学阐释史上一大创见。朱熹对历朝历代的《诗经》研究成果都有着深入的认识和总结,但又能不被传统经学思维模式所限制、不囿于理学家的身份,相对客观真实地探究诗文的本义。陈战峰[1]将两宋《诗经》学诠释方式概括为“据文求义”与“以今论古”两种,并点明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与以“理”解《诗》注重性理的特征联系紧密。夏传才[2]认为朱熹对《诗经》的解释“许多地方超过了汉、唐人的诗说,方法上也比他们高超;书中充分表现的理学思想又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诗集传》对其理学体系的成熟意义重大。蔡方鹿[3]指出:“把天理论运用于解《诗》之雅、颂上”是朱熹《诗经》诠释方法所体现的不同于汉唐儒学的时代性。王玉琴[4]认为:“朱熹之诗法观是其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在诗学问题上的反映”,并认为朱熹的目的仍是用诗教将诗歌情感与义理思想融合起来。
朱熹注意到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所蕴含的道德教化与修身智慧,认为其与理学思想有相通之处,故以《诗集传》为载体、以继承“孔孟道统”为目的,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哲学与社会伦理观念,这正是其“以诗论道”的主旨所在。对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进行探析,是把握其专经思想的基础,也是理解朱熹弥合专经研究与理学思想的重要手段。朱熹对《诗经》的反复涵咏、解读,有利于其理学思想的成熟与完善,对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进行梳理,有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朱熹理学的发展过程。
一、朱熹以“理”解《诗》的主旨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主体,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变革而演化。朱熹以变革经学为途径构建自己的“理本论”哲学思想体系,《诗经》研究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朱熹《诗经》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也与其理学思想的完善不无关系。他将“理”看做万事万物的原则,并以此为标准对《诗经》内容进行分析,旨在利用《诗经》的教化功能来论证自己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
(一)返本求真,还《诗》本旨
出于对学术发展的考量,朱熹以“理”解《诗》试图打破先儒附于经典上的层层束缚,使得《诗经》文本的本义得以体现。相比于《论语》《孟子》等专以格言、故事反映道理的著作,《诗经》的表达方法更容易影响读者对其深层含义的理解。
春秋时期孔子曾以《诗经》为教材教导学生。到了西汉年间,《诗经》随着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而被奉为儒家经典。汉代的儒学家们因赞同“《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5]的说法,而强调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歌体裁下蕴涵着的教育性。汉文帝时,《诗》最先设立博士,也体现了统治者对《诗经》教化功能的看重。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正是在这种“儒术独尊”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下,汉儒们借助训诂、考据等方法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在增强经典的可阅读性的同时建立起了“儒家的政治哲学”[6]。唐代的经学研究在东汉末期到魏晋时期兼采今古文的基础上,又打破了北学重名物训诂、南学重微言大义的隔阂,趋向于统一。总的来说,经学在汉唐时期虽有发展变化,但基本上维持着“疏不破注”的传统。
宋代理学家在注经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经典本身的神圣性及汉唐儒家经说、师说的权威性产生怀疑。欧阳修著《诗本义》将《诗经》中的诗篇看做独立的个体,致力于探求诗文原意、诗人本旨。苏辙著《诗集传》怀疑《毛诗小序》,动摇了其在《诗经》研究中的地位。二程主张不以文害道,在文道关系上主张重道轻文,“以‘理’贯经”[7]137的治经态度导致了其注解《诗经》不顾文义而曲从义理——两宋儒者注经多有此弊端。朱熹的《诗经》诠释既受到前代儒者解经思想的影响,亦体现着宋代重视义理的社会思潮。
朱熹注解《诗经》思想与其独特的《诗经》诠释方法是在对历代的《诗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自身治《诗》所得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读《诗集传》,不难发现,朱熹对《诗经》汉学与宋代《诗经》研究都有着批评与继承,他既不满汉儒为《诗经》披上“政治哲学”的外衣,又不满宋儒舍弃《诗经》文本而说理太过。朱熹的以“理”解《诗》实际上兼采了汉唐《诗经》研究的方法与宋代注解《诗经》重视发掘伦理道德观念的思路,承认诗歌寄托着作者的精神情感,要求读者不以他人之言先入为主,而是通过反复涵咏领悟诗文本义——返《诗经》之本以求“诗教”之真。
肖满省[8]从宋代经学的特点出发,强调朱熹的《诗经》解释并非是“为了阐述其义理之学”而是体现了宋儒的“求真”精神。姜广辉[9]则强调“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正是朱熹经学著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两者说法均有可取之处:前者从纯学术的角度对朱熹的经学诠释思想进行分析,重在梳理经学发展脉络,后者以元代科举考试所采用教材为标准来评定程朱经学著作成功与否,则是看到了朱熹“以‘理’解经”所包含的政治意蕴。
(二)政教合一,维护纲常
从政治层面上讲,朱熹以“理”解《诗》旨在强调“三纲五常”与等级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诗集传》之所以能够受到元代统治者的青睐,成为科举的指定教材,正体现了朱熹思想具有入世的特点,其经学诠释思想亦饱含终极关怀的意味。正因如此,任继愈、李申等将朱熹看做儒教教主,他们认为朱熹能在死后陪祀孔子为“儒者的最高荣誉”[10]。与道教、佛教不同的是,朱熹的信仰核心并非是太上老君、如来佛祖等具有神迹的人格神,而是具有主宰性质、能够从内在解决人们安身立命问题的“天理”,“天理”往往又通过先贤之言、儒家经典得以表达。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的朱熹的儒教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化宗教,它建立在对经典的信仰之上,倡导着“人们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11]133。
朱熹的以“理”解《诗》的实质类似于“政教合一”,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诗经》诠释中说明伦理道德与等级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将“诗教”与“政教”画上等号,用以维护封建统治。《诗集传》以政治化的视角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解释诗篇,在其“天理君权”思想基础上,要求统治者扶持“天理”,在治国中注重民生、在行政中遵循德化的原则。例如:朱熹注《豳风·七月》一诗主旨为“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朦朝夕讽诵以教之”[12]142,突出了圣君贤王关注民生的一面。同时,他认为《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中描绘了主祭者亲至田亩、查看收成、与农夫同食的场景,着力体现了君王注重民生后所达到的上下相亲、相赖、相报的和谐关系。
在《诗经》中,朱熹尤为看重《国风》,亦与其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周朝的立国之本就在于以德治国、以德化感人,由此指出:“《鹊巢》《騶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12]2,将《野有死麕》《湛露》所述女子贞洁自守、不畏强暴均归于文王德行风化于下的功劳。这就提示统治者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才能像文王一样,不用武力镇压、不靠强迫约束,就能使得臣民心甘情愿地“从化”。而贤明的君主、圣人之所以能够以德化万民,就在于先天禀受之气是清明纯粹的,纯然合乎天理;众人则或多或少禀受到了厚浊之气,朱熹注《卫风》引张载之言以为“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12]63。又注《秦风》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12]121明言人的心性、行为、处事风格会受到禀赋气质的影响,加之常人易于被私欲所蒙蔽,于是需要三纲五常来进行约束。由是可知,不论是朱熹的“神道设教”或是心性论思想,其根本目的均不在于对逻辑、概念本身进行研究探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其以“理”解《诗》旨在论证纲常伦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一是出于儒士气节的选择,二是宋朝政局的内忧外患、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更加要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和国家归属感。
(三)修齐治平,以《诗》行教
着眼于社会治理层面,朱熹以“理”解《诗》旨在结合时代背景发挥“诗教”的现实功用。“诗教”即是“以《诗》为教”,《礼记》亦云“温柔敦厚,《诗》教也。”[13]我国已知的最早将《诗》作为教材的便是孔子,后人认为“‘诗教’作为教化的一种形态,在孔子那里是被用以践修其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之‘道’的”[14],即通过《诗》的感染熏陶作用,教导读者达到“温柔敦厚”的“仁”的境界。《论语》中亦有多处体现了孔子对《诗》教化功能的认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100指出三者对于人的品性塑造、行为实践均有指导作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5]55则突出了孔子以“仁”为标准的诗教观。朱熹对《诗》的教化功能亦格外看重,他在《诗集传·序》中言明:“《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12]1这既承认诗之所作最初是用于表达情感的,又进一步对孔子“思无邪”的诗教观进行了发挥:“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16]2065朱熹认为并非每篇诗文内容都体现了“思无邪”,而是圣人以这三个字概括指出了“诗教”的目的:正因为“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12]1因此,诗篇必然是有好恶之分的,“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16]2090就做到合于“诗教”了。在朱熹看来,人们参与政治、进行社会交往、日常的学习思考都是以“天理”为准则进行的,《诗经》的教化实际上也是为了引导世人,使其性情、行为都能达到与“天理”相合的境界。
受“气禀有定”思想的影响,朱熹根据君主、臣子、民众身份的差异,有差别地发挥“诗教”。他认为:诸如尧舜、文王、孔子之类的圣王、圣人“是上知生知之资的人,他们禀气清明,赋质纯粹,没有一毫昏浊渣滓”[17],是不需要被教化的,他们的言行即可为万世所法,而禀气稍次的君主、国君则要向圣贤学习。《诗集传》中多处将国君政绩的好坏、社会治理的情况与“是否受到文王风化”紧密联系,认为《唐风》之诗“勤俭质朴,忧深思远”[12]103是受到了尧的影响。在对《黄鸟》一诗的注释中,朱熹采取了与毛传、郑笺不同的视角:“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又“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12]119,认为以活人殉葬是蛮夷风俗,三良之逝非唯穆公之责,亦是秦国君主未受天子教化而遗留的旧弊。当“诗教”的对象为臣子时,朱熹往往热衷于塑造“爱国”的臣子形象,这不仅体现在臣子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上,还突出表现在其对“隐者”形象的树立上。他对《考槃》的注解着重描绘隐者悠闲自足的生活状态,认为未体现《诗序》“见弃于君”之意,驳斥了郑笺“遂有誓不忘君之恶、誓不过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12]26的说法,认为是于义理有害的。对此,日本汉学家种村和史较为恳切地指出:“尽管是隐者,他们也并未从曾经的君臣关系中挣脱出来,其思想和言行举止仍然像国家政治的现任人员那样受到相应框架的制约。”[18]534
朱熹以“理”解《诗》的目的还在于凸显诗文中普通民众的道德性。他对《谷风》中“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12]32的解释与汉儒大相径庭。前引《谷风》二句,郑笺注为“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19],旨在强调遭受抛弃的妇人的怨愤。孔颖达看到了郑玄对诗文注解中对道德性的忽视,进一步辩解“母子至亲,当相忧念,言已无暇,所以自怨痛之极也。”[20]而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宋代,朱熹更为注重《诗经》的道德性表达,他重新诠释了“我后”二字——“何暇恤我已去之后哉!”[12]33朱熹认为弃妇所言并非后代,而是指离开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便完美地消解了作者情感与道德规范存在矛盾的可能性。总之,朱熹通过划分“诗教”的不同对象,对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构成者都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其以“理”解《诗》的终极目的,就是突出《诗经》中的道德意蕴,贯穿君臣以忠、父子以孝、夫妻以节的社会治理思想。
二、《诗集传》的解经方法与特色
朱熹经学研究成果丰富,囊括了“四书”与“五经”。其注解《诗经》用力颇多,在《诗集传》中对前人解《诗》合理之处加以批判性继承,亦能不囿于前说,根据诗文情感、史实材料提出创见,体现了在注经过程中不断反思的审慎精神。《诗集传》中的解经方法与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朱熹整个经学思想的方法特色。其中,主要解经方法可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
(一)经传分离,通经明理
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成熟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在与吕祖谦的探讨中,他察觉到《诗序》与诗文内容之间的相互抵牾,于是由一开始的“遵《序》解《诗》”发展到最终的“去《序》解《诗》”,使得其诗学成果由集解类转向理论型的传注类著作。另一方面,其《诗集传》中删掉了所引用的前人成说,真正做到分离经、传,是随着其理本论哲学体系的完善而发生的。
“经”的产生与学者们对圣人的崇拜不无关系,是“历史上被称作‘圣人’的先觉者为人们所制定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11]151在先秦时期,圣、贤非唯儒家独有,“经”也并非仅以指代《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者。当汉代经学与政治发生必然关系之后,儒家学者往往将自己的入世精神融入对经典的注释之中,坚信遵守人类历史上的先觉者所制定的思想准则、行为规范有助于个人的提升与社会的发展。朱熹在圣人之上树立了更高的标准——天理,并将圣人之所以有“圣”的一面归于天理的赋予,于是经也就从表达圣人之心意进一步发展为描述天理的具体要求。从这一层面上讲,研习经书就变成了体悟天理的途径与过程。
传是后人对经的注解所形成的文本。传在理论上依托于经而存在,在经典阅读中起着辅助初学者理解经文本义的作用,在实际中却往往存在着“看注忘经”的学术弊端,这在汉唐时期的经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朱熹认为,一味遵循传注的解释——曲从前人成说,难免被先儒们的穿凿附会所误,导致学者偏离圣贤所述之“天理”。他对吕子约道:“此亦是见近日说者多端,都将自然底道理穿凿坏了。”[21]针对这样的学术流弊,朱熹提出了经传分离的解经方法:他以《汉书·艺文志》将《诗》与《毛传》分离收录为依据,主张“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16]2093,以此区分《诗经》及《毛传》。
需要说明的是,朱熹强调经传分离的解经方法,并不是完全否认传注对于经学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及汉唐经学的研究成果。相反,他对汉唐经学家十分尊重,强调治经之人不敢妄自牵动己意而所言必有依据,主张宋后的学者们在解经时务必参考汉唐经学家的疏解。朱熹分离经传的目的是为了将经文中的“天理”从汉人的牵强附会中解放出来,而他主张会通经传则是为了对宋人不顾文义、擅自发挥的学术风气进行修正,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得经学的研究对象回归经文本身,在探明经义的基础上发明义理,皆体现出了朱熹经学研究“通经明理”的学术特色。
(二)以经解经,史论结合
以经解经是朱熹诠释经典的常用方法。在朱熹注解《诗经》的过程中,以经解经既指剥离《诗序》,以诗篇文本为解释依据,使得《诗集传》在内容解释、评判标准等方面保持一致性;亦指在《诗经》解释中援引《书》《礼》《易》《春秋》的言论来相互论证,突出了经典之间的贯通性。
朱熹在《诗集传》中将诗文与《诗序》分离开来,尤其对《小序》进行了反思与批驳。他认为,《诗经》虽有300余篇,但其思想本质均是围绕着道德性展开的。其“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不仅体现在以诗文文本为主体进行思想阐发,还体现在对《诗经》内容的前后联系与上下统一上。朱熹将《周南》的前五首诗看做一个整体,认为“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12]12,而每首诗又分别就行志在己、德惠及人等具体品质展开论事,究其根本则与文王之化相联系;又注《召南·鹊巢》“犹《周南》之有《关雎》也”;视《召南·采蘩》“犹《周南》之有《葛覃》也”[12]13;明言虽事有不同、地有不同、时有不同,《周南》与《召南》所述道德原则、精神力量是一致的。以《诗》说《诗》,以前者解后者,意在提纯《诗经》的道德约束性、宣扬《诗经》的道德普适性。
与其说“以经解经”体现了宋代儒者对经典皆是圣人之言,因而具有统一的衡量标准的认识,毋宁说是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为经典的互相诠释提供了可能。在《诗集传》中,朱熹以“《书》有司寇苏公,《春秋传》有苏忿生,战国及汉时有人姓暴,则固应有此二人矣”[12]47质疑《诗序》对《何人斯》一诗诗文擅自发挥;亦于《小雅·天保》中以“《书》所谓‘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语意正如此”[12]163解诗文涵义。朱熹引二程之言于《曹风·下泉》中以《易》之《剥》卦论述天理之循环、治乱之变化,亦是其以《易经》解《诗经》的具体表现。而对于《周南·桃夭》《召南·采蘩》之类,朱熹则引《仪礼》与之相合——“《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12]22;突出了《二南》乃修身齐家、风化天下之道。
朱熹经常援引《书》《礼》《易》《春秋》等经典来阐释诗文,旨在通过相互考证来恢复《诗经》中诗篇的本来面目,《春秋》一书尤其被高度重视:无论在《诗序辨说》中还是在诗篇的解释中,大约每注三首诗就会引一次《春秋》。朱熹惯于用《春秋》注解《诗经》,不仅仅是看重《春秋》的微言大义,还在于借重《春秋》的史书特质。正因如此,他在引用《春秋》时也多参照《史记》与《国语》,力求将经与史结合起来。作为儒家学者,在朱熹的观念中,圣人立经作典并非完全出于记载、陈述史事的目的,而是为了以此“明道”,即“借助先前的文献,来阐发他的价值理念”[11]140,其以是否存在教育意义为评判标准,从而得出了先经后史的结论。概言之,朱熹在以经解经的方法论中既强调史论结合,亦突出了先经后史、次第分明的特点。
(三)由情入理,以理束情
朱熹的《诗集传》之所以被看做宋代诗经研究的巅峰,一方面在于他对宋代《诗经》研究的各家成说进行了吸收借鉴,另一方面还在于朱熹敢于突破陈规旧说,发他人未敢发之论。在其之前,欧阳修注重诗歌语境,提出“据文求义”的《诗》学特点便已然开始注重将“情”作为重要解释方法——“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情,而古今人情一也”[22],表明“情”是一种超凡的、共通的道德标准,兼有对汉唐《诗经》学的继承和突破。苏辙在欧阳修的研究基础上将“‘情’看作诗篇内容及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多样性的产生源泉”[18]256,对《诗序》的作者展开质疑与考辨,更为朱熹去除《诗序》藩篱、以“理”解《诗》提供了理论借鉴。
朱熹在欧阳修、苏辙等的研究成果上,更直接地承认了《诗经》的情感因素,并从《诗经》的发生、诗文的分类、诗的教育意义三个层面突出了“情”的价值,并在肯定诗“情”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其理学思想。
第一,从《诗经》的发生来看,朱熹认为《诗》由情而生,“感物道情”才是古人作《诗》的本意。他直言“情之所感不同,则音之所成亦异”[12]5乃是《诗》的成因,又以“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是讥讽他人”[16]2076驳斥了《诗序》的美刺之说,以为汉唐儒生解《诗》过于僵化,妨碍了诗文的本来意蕴。可见,朱熹突出《诗经》表情达意的功用是为了突出《诗经》所承载的人类共通的情感,即圣人想要通过诗文传达的人人应有的道德性常识。这种道德性常识是超越时空的,董仲舒称之为天,朱熹则称之为理。
第二,从诗文的分类来看,朱熹“断定二十四篇为男女情爱之作”[23]并划分“淫诗”是前人所不敢道的。中国人表情达意的方式向来是含蓄的,汉唐时期的《诗经》阐释,主要将描写男女爱情抑或夫妻关系的诗篇解释为君臣、贤友等社会伦理关系。与之相比,朱熹的《诗经》解释显现出较前人及其同时代人更广阔的视野,他不认为对诗文中男女情感的直接描述会影响《诗》的道德表达,而是将“夫妇之正”纳入道德范畴、置于三纲之首,指出其乃天理之应然。傅斯年认为《诗集传》所体现的重视情感本义的文学性质实乃朱熹在经学上巨大的贡献,虽批评道:“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7]12,却也从侧面体现了朱熹在情诗阐发中所依据的理学标准。
第三,朱熹注重诗文对个人修养的教育意义,教导门人弟子通过涵泳诗篇以得性情之正,最终达到玩理养心的境界,亦是其由情入理的解《诗》方法的具体表现。《朱子语类》多处记载了朱熹的读诗之法及其对弟子的教诲之言,“且看他大意”“其话有未通者,略检注解看,却时时诵其文本,便见其语脉所在”[16]2083等言均是要求弟子门人理解诗文之价值倾向,以“守诚”“居敬”等理学修养方法加以践行,反对深埋书斋、为不甚重要的一字之解苦苦搜求。
朱熹《诗集传》对理学思想的阐发建立在肯定“人情”的基础上。他对诗篇情感的肯定既促进了其理学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其理学思想又反过来试图通过《诗经》向社会、民众传播一定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朱熹对人的性、情做出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情虽是性的发动却不同于性是全善的,而是善恶兼混的,不合于“中节”的情便落为了人的过分之欲(如情欲、物欲等),其“淫诗说”的划分、“灭人欲明天理”的思想,以及他和永康学派陈亮所展开的“王霸义利”之辩的价值观念均在《诗集传》中有所体现,最终目的都落脚于对人的欲望的节制上,从而使其由情入理的解经方法呈现出了“以理束情”的特点。
三、结语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解释《诗经》既是一种突破,亦是一种必然。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与标准是“理”。儒家经典的产生与古代学者的圣人崇拜思想息息相关,而经典的内容亦无外乎对尧舜等贤君、孔孟等圣人言行的记载,体现了天人相合的关系。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科技水平的进步,“理”代替“天”“道”成为了信仰对象。因此,无论从学术发展、政治实践抑或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朱熹都试图使《诗经》的解释合于“理”。而这种理不仅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形而上的物质本原,更带有普遍适用的道德律令的性质,以“理”解《诗》亦从侧面体现了朱熹身为儒士的政治抱负与终极关怀。《诗集传》是朱熹《诗经》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于体例的丰富、内容的驳杂而呈现出了较高的理论价值。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使用的解经方法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对其他经典的注释中,他主张分离经文与传注,通过直接阅读经文内容体悟圣贤之意;又主张以经解经,注重将史实与经文内容相合,将史论相结合,无法考证之处则直言阙疑,体现出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朱熹由情入理的解经方法是其《诗经》阐释所特有的,最能体现其经学与理学的融通。总的来说,朱熹的经学思想与理学思想互相联系,其经学思想为理学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其理学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经学研究,使其经典阐释取得了富有历史创新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