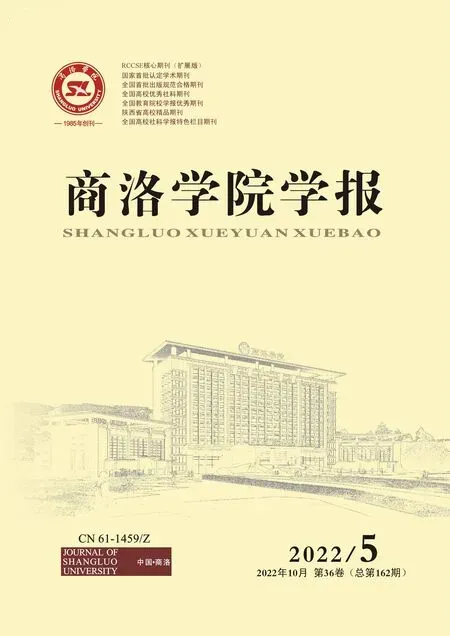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
严文珍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描绘了陕南商洛山地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贾平凹说,商州只是秦岭上的一个点,是他生命体验和文学实践中的一个小点,它既隶属于更广阔的地域概念,又保留了自己独立的文化特性。它与苍茫厚重的黄土地、粗粝质朴的三秦文化有深沉的联系,又与不同地域和文化接壤而显现出独特的气质和神韵。从地理位置看,商州位于秦岭南麓,属过渡交叉地带。从地理形态上看,商州境内沟壑连绵,巉岩峭崖、纵横交错的沟道构成了商州人生活的主要自然环境。商州秦头楚尾的位置使商州成为勾连秦楚文化的重要通道,老秦人的沉郁朴野和楚人的神秘幽邃在此交汇,形成商州独特的精神气质。贾平凹曾认为:“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经历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特质出什么样的作家,同样的道理,什么样的地理也是出什么样的作家。”[1]贾平凹在此谈到的地理既包括自然地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包括人文地理中的一些因素对作家气质、创作风格的影响。
迈克·克朗(Mike Crang)认为文学与地理之间具有双向作用,文学世界由位置与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视域组成,具有地理属性,同时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塑造这些地理景观[2]。商州为贾平凹提供了一个地理空间,以此揭示一种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真实,为实现真实的讲述目的,作者用熟悉的山水地貌绘图,以构建一种历史的,更是空间领域的独特的生存体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是作者对商洛地理形状、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的文学表征。这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集写作、阅读和解读的各种体验,在此过程中绘制出与空间诸元素相关的文学“地图”。
一直以来,文学地理与文学地域的界限并不明确,二者确有交叉,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文学地理建立在对自然地理考察的基础之上,研究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和地理现象对文学的影响,即注重地理性因素与文学现象的关联。文学地域研究以生活、风俗、物产、方言等文化现象作为切入点,注重人文地理中的文化性因素,即人文地理。文学地理是文学地理学的主体,采用地理视角考察文学与地理的外部关系;文学地域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采用地域视角研究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以空间视角为切入点,借助地理学的思维和方法,通过分析文学与地理的内在关系来揭示文学现象,以弥补单纯从纵向的、时间的、历史的维度,而没有从横向的、空间的、地理的维度考察文学现象的单一向度,给予“文学现象以通体的观照,还原文学的真实图景,解释文学的所以然。”[3]28本文以文学地理学研究视角为切入点,考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的文学地理学路径。
一、文学地理路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自古至今,中国文学走的是人与自然亲和的路线,文学作品中对山水的描述始终带着作家自然哲学的印记。中国文人以独特的审美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山水诗赋、山水书画等艺术形式。《山海经》是先秦时代对中华山川形貌、远古神话、物产及动植物的神话书写。全书记载了550座山,300条水道,山经以山为纲,叙述了每座山的地理位置、走向和物产,详细介绍了矿产分布、质地、光泽,硬度等,以及各种动植物的形态和药用价值。
古代最早记录秦岭的文字是《山海经》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禹贡》载中国的山脉分“三条四列”,秦岭被列于中条。广义的秦岭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与昆仑山脉相接,蜿蜒于甘肃、陕西两省南部。狭义的秦岭位于陕西省南部,东以灞河与丹江为界,西止于嘉陵江,是渭河中下游与汉江上游的分水岭。秦岭自西向东可分为三段,秦岭东段呈手指状,向东南展开。秦岭主脊草链岭和太华山,是丹江、南洛河及秦岭东段北坡山涧溪流的分水岭与发源地,构成了山河相间分布的岭谷地形,而在南洛河—丹江两侧的中低山丘陵中分布着一些宽谷盆地。商州—丹凤—商南一线的主要地形就是这种宽谷盆地,由于冲击的泥沙堆积,形成了比较肥沃的土壤,是商洛境内的粮食主产地,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也较为稠密。
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构建的地理空间座落在秦岭东段的商洛市,该市辖1区6县(商州区和镇安县、丹凤县、商南县、洛南县、山阳县、柞水县),境内有秦岭、蟒岭、流岭等山脉,洛河、丹江、金钱河等河流。商州封闭的地形地貌既使此地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又是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独立王国。这种环境滋养了商州人的禀赋、性格,他们既保守落后,与时代格格不入,又充满勇毅、坚韧的个性。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然和时间造化的烙印,既安于现状,又充满豪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商州作家,贾平凹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的商州系列小说大多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普遍受到改革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时,贾平凹却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生命之根维系于此的执念。小说中人物命运和道德的分化,似乎折射出他对于城、乡二元经济形态和社会观念的区分。《黑氏》《远山野情》中的黑氏和香香,在她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山地人纯真、厚道、坚韧的精神气质,而信贷员和队长则是向世人说明文化封闭与经济落后造成的道德的偏仄,这种深藏在商州人心灵深处的道德体系在经济和政治变革到来之后仍然会延续,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贾平凹以一种和解但不失为批评的姿态称赞了才才的随遇而安、安分守己,以无限的韧性接受窘迫生活的耐力,但似乎更支持王和尚、禾禾、石根他们重构富有锐气和活力的生活秩序的努力。贾平凹在讲述商州故事时始终带着两种指向不同的情感倾向,他既肯定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给商州带来的发展契机,也流露出一种对传统生活秩序、道德体系在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下难以为继的隐忧。
丹水发源于商州西北部的凤凰山南麓,流经商州、丹凤,经河南、湖北,于丹江口注入汉江。丹江径流量小,年际变化大,含沙量较多,洪水灾害频繁。受丹江侵蚀,丹江两侧许多支流河床因沙砾淤积而形成悬河床或平底谷地。丹江两岸的居民必须要修筑围堰阻止丹江肆虐,因此,商州系列小说描述丹江洪水及治理洪水的故事也比较多。“那山岭(马鞍岭)斜屹在丹江河边,逼着河水向北转向,拐了一个簸箕湾。从此,河水就大口大口吞噬北岸;良田没了,梨林没了……留下来的,就只有梨花村这个空名了。”[4]《姊妹本纪》中作者将治理丹江、改变人民生活境遇的努力放置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之下,使人物的性格、命运及人性的点滴在接踵而至的运动中展现无遗。在《浮躁》的序言中作者写道:“在这本书里,我仅写了一条河上的故事,这条河我叫它州河,商州是应该有这么一条河的,且这河又是商州唯一的大河。”[5]此处的州河是丹江的俗称,在作者笔下它是一条浮躁不安的河流。作者借“浮躁”一词描述丹江径流变化无常,又以此描述丹江边人民的生活境况及其与河相系的变化莫测的命运。州河向沿河居民们提供了猎物、柴薪和药材,更深刻影响了他们逾于常规的生活方式。流动不居的水与山民凝滞的生活相对照,生活在沿河的人则更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州河沿岸社会的最初变化来自于与水相关联的生活方式,而金狗和雷大空经历了生活的波折之后又回到州河,寄寓了作者对刚刚萌发的改革大潮的思考。《浮躁》描述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世相与心相,“浮躁”一词不仅概括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蠢蠢欲动的状态,更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对于改革的迫切需要,正如春雷一般,在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心灵上引起深沉的颤动。
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具有明确的地理指涉,很多空间位置的处理与实质性的空间相重叠。读者可以循着《小月前本》中的紫荆关了解商州独有的地理位置。在秦岭的一个山窝子里竟然交汇着湖北、陕西、河南三省的人物和风貌。以贾平凹的故乡棣花镇为空间坐标,读者可以在厚重的商州系列作品中标定一个个具体的位置:武关、纸坊沟、龙驹寨、仙游川等。贾平凹说过,他会根据熟知的一个地理位置作为故事的空间背景,甚至会具体到一个村庄的方位、形状、房舍的结构、巷道的排列,并且安置好一棵树、寺庙、戏楼、水井和石磨的位置。于他的写作而言,一些虚的创作都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上的。贾平凹的作品曾一度被读者当作“旅游指南”,他在《浮躁》的序言中说很多人以他的作品为指南到商州区考察,结果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作者欺骗。由此来看,商州因为贾平凹的作品而成就了一幅幅虚实互现的文学地图,他对商州的“深描”是一种重返本地人的文化、重回事发现场、重温事件本身的意义的写法。
二、文学地域路径
曾大兴在论及文学家受地域文化影响时援引周振鹤的观点:“籍贯与生长地往往是二而一,所以从人物的籍贯分布又可以窥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3]19文学地理学中所讲的文学家的籍贯指作家出生成长之地,即便很多文学家一生当中有多次迁徙,但本籍文化却是“文化母体”。原乡文化构成了他的文化原色,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以后的迁徙文化中沾染的“客籍”文化丰满或者滋养他的文化原色。
贾平凹的家乡商州自古有“秦头楚尾”之誉,不走进“秦骨楚韵”的商州,便不能深刻体味贾平凹文学艺术的精髓。班固在讲风俗习惯对文学的影响时说:“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6]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特点潜移默化中调和着秦地沉郁、厚重、凝滞的文化气质。因此,《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天狗》《火纸》《满月儿》《商州》《浮躁》《远山野情》等作品无不是对故土的深情刻画,呈现出商州天然的地域色调。批评者指出,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的重大收获就是对于一个“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的发现[7]。贾平凹在构建商州的地方社会空间时,用具体的婚丧嫁娶、民间文艺、风水巫术、起居饮食、方言、宗教文化等乡土社会的民间文化搭建了该空间形态的主要框架。他在作品中描绘的风景风俗并不是一种装饰,不是人为地附加和卖弄,而是将作品的主题渗透和流动于一切事件和人物当中的写法[7]。
(一)方言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变体,它深受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方言承载着某个文化形态历史的、地域的印记,并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嬗变。方言的存在和保护对于传承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的写作过程都是下意识地表现一定地域文化的过程,对于那些自觉使用方言进行写作的作家而言,方言可以更好地表现当地的乡土风情,使独具地方色彩的文化形态在语言再现的时候避免表意的违和感,可以说,作家的写作过程就是紧贴地面的飞行。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仍用方言土语书写的乡土作家,古白话、文言、土语的运用无疑是他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策略。贾平凹表示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习惯于生活在方言的天地里。他执着地用拙朴的书法手写书稿,叙写商洛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王素等[8]从政治话语的影响、现代性话语的规范及回归地方性的感性体验这三个层面探讨了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方言写作。贾平凹运用方言进行文学书写的语言形态逐渐呈现出与他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疏离”的态势,而且作者越来越重视方言在文学叙述中的“修辞性”意义[8]。
贾平凹的方言写作与他的文学道路的演进和转变相一致,表现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政治、思想的认知反应。郜元宝等以汉语文字为线索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若干问题时这样说:“20世纪中国语言经历了五四启蒙语言、文革语言、新时期新启蒙语言等一系列巨变,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随着语言走,被语言主宰,而不是相反。”[9]贾平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的,当时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对文学语言具有非常大的渗透作用,这种情况在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贾平凹最初的文学创作语言是一种自觉的无意识的流露。作为一位在商州农村生活了十几年的人,商州的土语方言早就渗透在他的血脉当中,即便面对强大的主流语言教化时,它仍然体现了顽固的力量。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多以人名为题,如《兵娃》《春女》及后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满月儿》,质朴的语言既是对乡土社会真实的表达,又冲淡了带有浓重“火药味”的话语表达。此时期,贾平凹以事件命名的小说题目也比较多,简明扼要的题目直接点明小说的主题,比如《参观之前》《选不掉》《派饭》《喝酒》等,数量可以和以人名为题者比肩。
1978年,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在《上海文学》发表,并于当年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较之前的作品,《满月儿》的语言具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话语、商洛方言与书面语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贾平凹在表现姐姐满儿锐意进取,在科研道路上的努力时,不时插入具有时代风貌的词汇和话语形式。如将新培育的种子命名为“攀登麦”“胜利麦”“争光38号”等,充满了作为建设者的自豪感。《满月儿》的创作既有现实生活的鲜活体验又得益于孙犁先生的名篇《山地姐妹》的影响。贾平凹曾在礼泉县烽火大队农科站遇到了一对淳朴可爱的姐妹花,后以她们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小说的语言清新、流露着诗意的乡土气息,然而小说创作仍然受“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语言规范的影响。贾平凹在小说构思的时候给自己定下基调,“调子要柔和,语言不要出现成语和歇后语一类太土的话,节奏和音响要有乡下少女言谈笑语式的韵味。”[10]
《满月儿》开篇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鲜活的生活场景,拽被面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和一个老婆婆的对话更具有现场感。“这死女子!让娘夸你力大哩?轻点,轻一点!”[11]246此处没有刻意对人物的外貌和性格做任何描述,“死女子”就足以衬托第一位闯入作品的姑娘开朗活泼的性格。似乎在这个地方,任何一种规范性的语言都很难传神地显露娘眼中的女儿的形象,这既带着亲昵又有点嗔怒的三个字极具画面感。而另一句“她一跳跳出二尺地来,叫道:‘出来晒晒日头吧,别尽坐着发了霉了!’”[11]246则从侧面微妙地表现了另一个女孩沉静的性格。满儿和月儿的性格并不是直接用描述性的语言表现的,夹杂着鲜明性格特征的日常口语像一颗颗掷地有声的珠子清新明快散落于全篇。
从《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开始,贾平凹开始逐渐摒弃原有的工农兵语言的书写形式,向沈从文和孙犁学习,注意大众语言的雅化。而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又吸取民间方言特有的表现力,如使用了大量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名词和动词,以及一些更具有民间文化气息的熟语、惯用语、谚语和民谣。贾平凹认为民间有许多十分好的需要留意的语言。他用“风刮得像刀子”来形容一个人讲话的声音。他也经常采集民间土语,如“避”“寡”“携”“欢实”“泼烦”“受活”“瓷”等。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以“瓷”或者由“瓷”字搭配组成的词语。“瓷”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有“呆傻”“愚笨”的意思。在陕西方言中搭配组成的词有“瓷眼儿”“瓷锤”“瓷球”“瓷脑”“瓷嘴笨舌”等,大多表示呆笨、迂腐、不通变故。《浮躁》中“瓷”作为陕西方言出现了多次。此外,还有几处“瓷”直接用作谓语,例如“乡政府的大院突然开进一辆小车,慌得田正中跑出来迎接,却见下来的是金狗和雷大空,当下就瓷在那里。”“福运瓷好久,末了还是进来。”这两处“瓷”都是作为谓语动词使用,表示“傻站着,愣住不动”的样子。而“瓷眼”看着,表示眼珠不动,目光呆滞的状态。“瓷”的介入和使用形象直观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瓷”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背后也倾注了用现代标准化语言无法传达的心理状况。
贾平凹将方言作为解密商州文化的符码,他对商州风土人情的讲述是基于他对商州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以及对故土的复杂情绪之上。新时期到来之后,很多作家如莫言、张炜、韩少功等人对方言独特青睐,贾平凹似乎更执着地回归由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老一辈作家创造的质朴的乡土话语之中。他以深藏于苍老大地的古语、俗语和谚语走进乡土,寻觅商州大地上隐匿于大山深处的话语。贾平凹作品中的方言是他对逐渐逝去的乡土、乡音、乡情的回望,是对那片土地上可能消失的古语、土语的收藏。他以特有的语言形式表现了那个偏僻却古老、清秀又粗犷、文明又野蛮、进步又保守的地方,用文字建构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神秘文化
商州秦头楚尾的地理位置,使它兼备巫楚之韵和秦汉之风。贾平凹的作品里喜谈鬼神、卦辞,文字中带有神秘的气息。有评论家认为在强调阳刚之美的众多西部作家中,贾平凹近于阴柔,其商州系列小说无处不缭绕着一股鬼气。在关于西北远山野情的叙述中,他越过主流文化模式,在异质性和诡秘中寻求叙事张力,在虚空的文化印记和沉重的现实之间叙述乡土中国的生存的人事物象,书写生存于其间的人们的生死、欲望和挣扎。因此,在商州人的生活中,人与鬼神共在,阴阳和谐调和着天地万物。贾平凹的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是出离了俗世,与鬼神相通,能够用剪纸、用堪舆之术、用特异的感官洞察俗人无法抵达的世界。
《太白山记》由十六篇笔记体故事组成,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短小奇崛。有人说或许是疾病改变了作者的性情,进而使他的文字带着阴郁、荒诞的气质。1987年作者因肝病住院治疗,这期间的作品似乎脱离了以《浮躁》为代表的关注当下现实的路径,作者以怪诞不经的故事挖掘隐匿在人性深处的潜意识。对此,贾平凹做过这样的解释:“这些病中病后之作散发着药味或许观点偏颇或许用情亢奋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久病人的变态情绪。”[12]《太白山记》极尽夸张之能事,叙事虚无缥缈,形象奇崛荒诞,在诡秘的氛围中读者不禁被卷入六朝时代的志怪故事。在作者勤勉经营的商州世界里,《太白山记》似乎受到商州神秘文化的影响更深,山林密布、雾气缭绕的自然地理造就了神秘的文化气息,使人本真的生活境况、潜意识心理的写作变得恍兮忽兮。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怪之书……”[13]《太白山记》等篇目正是对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魔幻表现。其中《寡妇》一篇更为读者和评论者频频提及。该篇讲述了儿子在睡梦中看到娘与别的男人偷情,儿子误以为是爹。某夜又见着爹(其实是别的男人)与娘偷情,儿子扔去一块砖头,砸中男跟。翌日清晨,儿子与娘去爹的坟地,看到棺木已开启,爹的尸首安好,“但身子中间的那个东西齐根没有了。”故事的怪诞之处在于死去的爹夜里还魂与守寡的娘过夫妻生活而娘却浑然不知。《挖参人》将不同空间里的三个男人在同一时间汇聚在门口的一面镜子里。妇人从镜子中看到丈夫与贼搏斗被刺,结果原本好端端的人,却怀揣着一沓钱票死在城中旅馆的床上。在西北农村,随处可见房院中悬置的用以驱邪避害的镜子,作者以镜中之像暗示人世宿命。《猎手》是《怀念狼》的先驱之作:人与狼界限不明,猎人在虚幻之际看到了狼子、狼妻、狼父、狼母,而当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身边躺着一个四十余岁的男子,如此说来与他搏命并一起坠落悬崖的不是狼而是该男子。在《怀念狼》的结尾,猎人傅山只有以“人狼”的形式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木匠以斧劈人砍下的人头竟是一层厚厚的垢甲(《杀人犯》),刑天式以乳为眼、以脐为口的香客(《香客》),幻化成娃娃鱼的公公,扒灰孕出畸儿(《公公》),这些故事以极其诡异而扭曲的姿态向天空延伸,以魔幻的故事情节将人类原始的性意识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自有一种独属于贾氏的诡谲神秘的美感。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贾平凹对阴阳五行的认识和表现似乎更为讲究,他在文学地理坐标中置入了个人对宇宙的理解。贾平凹,原名贾李平,父母图呼叫方便就叫他平娃,取万事顺遂之意。1973年8月,贾平凹的处女作《一双袜子》在原《群众文艺》上发表,他听从了同窗冯有源的建议,将“娃”改为“凹”(陕西话中,这两字同音同调),后沿用至今。他也认为“凹则不平”,不平,那么就陷下去,归顺到童真充盈的“娃”字上去。胡河清在《贾平凹论》中对“平凹”二字进行考究,在他看来,这二字中间也含有“阴阳”的意思。“平”指的是阳光所及之地,故为阳。至于“凹”的深意,依据贾平凹在《妊娠》中的描述可推就:“15年前,这学生从乡下初到中国西部的最大的一座城市的大学就读,教授问:名姓?他说××凹。教授对‘凹’字颇感兴趣,遂问籍贯,在回答:瘪家沟。教授惊叫‘荒唐!’立即将村名和‘凹’字相联系,对这学生很有些大瞧不起。”贾平凹解释改名的原因:“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崛。”[14]贾平凹从出生到成长,都要遵从阴阳先生的禁忌,小学的教室是一间“四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鬼神、人物的古庙”,劳动之余,读的是充满“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鬼神人物的”古代闲书。他所生活的商州,是一个鬼神并行,阴阳相融的“前现代”社会。在商州,风水关乎家族的命数和运道,主宰兴衰际遇。贾平凹对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空间布局的构建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空间布局的理解有意为之,他倾注笔力将村舍、古堡、家宅、阴宅布置于它们应有的位置。他的作品随处可见观阴阳、看风水、测字、相穴、卜卦等活动。贾平凹将古老的《易经》文化和商州的民间文化渗透到他建构的商州景观之中,以空间选择、日常的攘灾辟邪仪式、通灵想象构成这个文化形态中神秘又具体的现象。
《美穴地》以风水之地命名,反映了地理方位与人世之间的超自然联系。为了使祖先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或考虑墓地风水会福荫子孙,人们在安葬逝者的时候非常考究阴宅的风水地形。柳子言善踏吉穴,姚家的吉穴经他确证后果然使姚家数年内兴旺发达,而这吉穴一旦被下人苟百都破坏,姚家也便在数年间诸事不顺,连姚老爷心爱的四姨太,也成了土匪苟百都的压寨夫人。后来苟百都死于非命也与柳子言所踏凶穴密不可分。
风水这种从传统文化孕育而生的“专门处理方位与空间的艺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是对现实地理环境客观和精神的取舍,它体现了人文因素对于地理空间的介入。中国的风水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也称青乌术,在学术上称之为“堪舆”。“风水”一词语出晋代郭璞《葬经》,后人又以堪舆、相地、阴阳等词意指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勘测。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和谐,达到“天人合一”,在建都安邦、营宅建居、相穴择地时作为重要的参考。风水术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来概括风水观念中选择宅、村、城镇基址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唐李绅《移九江》诗云:“楚客喜风水,秦人悲异乡。”贾平凹的商州世界自古崇尚万物有灵之说,因此中国传统的风水之术早已浸淫于商州乡土文化的脉络之中。而贾平凹本人在建构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的时候,不自觉中将中国古人对空间选择的要旨融入其中。贾平凹在描述家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时营造了这样具有古老文化氛围的地方:“龙驹寨就坐落在河的北岸,地势从低向高,缓缓上进,一直到了北边的凤冠山上……龙驹寨背靠奇山,足蹬异水,历代被称为宝地。据说早年一州官到了此地,惊呼长叹:此帝王风水也!”[15]
贾平凹笔下商州是一块风水宝地,他对故乡的书写带着以“乡”字负载的所有文化记忆,这些保留在乡土空间中的乡音、乡俗、乡亲及乡愁是他乡土书写的永恒起点和归宿。
三、结语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长短不一,连通起来则呈现了贾氏对于“商州”的不断发现与建构,这也是贾平凹自我发现的过程。贾平凹行走于商州的山水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寻找商州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血脉,在对当地风气、民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岩层的尽力开掘的基础上,在对县志、戏曲、饮食、婚丧嫁娶等显性文化事相的考察之后,找到了关于自然的、地理的、地域的全景画面。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以秦岭为广袤的空间背景、以丹水为勾连自然与生活的具体意象,将文学中的各类景观准确地安放在现实坐标之中。那些由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环境造就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宏旨:他们生于兹,长于兹,在秦岭山地、在州河沿岸生生不息。他们的喜乐悲伤既浸透着历史文化的印记,又潜隐着个体的欲望。而这样原始的文化事相在最荒蛮、朴野的生活状态中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贾平凹的写作为何一再走向山地、走向最隐秘的生存状态。这种神秘的写作旨趣既是贾平凹个人的文化旨趣和修养使然,又烙刻着商州“秦头楚尾”的印迹。就贾氏偏向志怪、佛、道文化的执念而言,似乎巫楚文化的渗透更加深刻和明显。因此,“商州系列小说”带着极致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这或许是秦岭现实主义的深厚土壤上开出的奇异的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