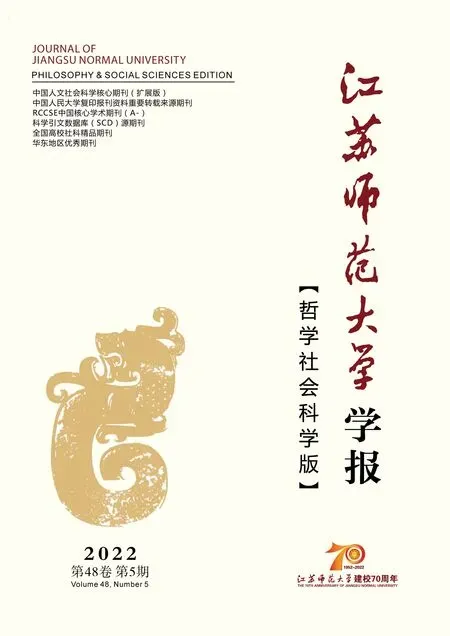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歌谣论的演进及其价值
陈书录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1)冯梦龙:《叙山歌》,《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冯梦龙《叙山歌》中的这段话值得人们深思。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曾经提出大小传统的概念,他认为“大传统是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2)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陈于太史者”的帝王将相与文人雅士的精英文化及雅文学等为“大传统”,那么,包括歌谣在内的“留于民间者”的大众文化及俗文学则为“小传统”,后者“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被禁闭在“大传统”之外。这禁闭者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上层统治者及某些士大夫,例如东晋晚期,“(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谢)石深衔之。”(3)《晋书》卷八十四《王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84页。时任中书令领太子詹事王恭等将“委巷之歌”(民歌民谣)痛斥为“淫声”,可见其鄙视之情与禁闭之意。明代后期官至吏部左侍郎的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指责“里巷童孺妇媪之所喜闻”的[山坡羊]等民歌时调“诲淫导欲,亦非盛世所宜有也”(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2页。。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清代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凭借皇帝的旨意查禁包括歌谣在内的所谓“淫词唱本”。他打着“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5)《江苏省例·藩政》“同治七年”,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旗号,禁毁包括《沈七哥山歌》《赵圣关山歌》《薛六郎山歌》等长篇民歌及[叹五更][文鲜花][新马头]等民歌时调,将禁闭之风推向极端。然而,纵观上下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见自先秦以来,不断有有识之士力图冲破这种“禁闭”,其中有的以歌谣论开拓“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新路,这相对于诗论、词论、文论者等来说,歌谣论作为一支借助“留于民间者”的大众文化及俗文学的特别的生力军,独辟蹊径,不断开拓,不仅创造新的审美特征,更是不断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的社会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一
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角度,纵观从先秦至明清歌谣论的历程,大体经历了禁闭中探究、存真与启蒙两大阶段。
中国歌谣论的第一阶段:禁闭中探究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上层统治者及士大夫出于维护正统文化(“大传统”)需要,往往禁闭包括民歌民谣在内的“小传统”,但在禁闭中时有某些松动乃至对“大小传统”的互动有某些探究。出身贵族并且后来曾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大传统”主要代表人物。对待“诗三百”(后人称之为《诗经》),他一方面肯定其“兴、观、群、怨”等价值;另一方面对“诗三百”中的《郑风》有贬斥与禁绝之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6)《论语·卫灵公》,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八,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39页。放,南宋朱熹《诗集注》云:“谓禁绝之。”(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孔子意在禁绝那些被他认为“淫”的《郑风》等民歌。显然,孔子以总论(论《诗》或“诗三百”)与分论(论“郑声”等)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歌谣论的源头。说到对包括“诗三百”中《国风》等歌谣的评论,还应关注一位重要的人物——季札,他是吴太伯十九世孙,吴王寿梦的第四子,曾以外交家的身份出使鲁国,乐工为之歌诗,季札对各地的歌谣均有一段精彩的评价。如果说,孔子论《诗》既有总论又有分论,点面结合地打通“大小传统”互动的道路,那么,季札侧重于分论,分别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等将各个地域的歌谣特色与国运盛衰联系在一起,分点突破地开《诗经·国风》与诸侯(地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歌谣论的先河。毋庸讳言,让“小传统”融入“大传统”并让前者成为后者中的经典,《诗》(或称“诗三百”)是个特例。 孔子对“诗三百”的整理、编订、传授,到战国时代儒家开始将《诗》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将原为“小传统”中民间歌谣的《诗》提升到作为“大传统”中的“经”。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专设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博士,从朝廷政策上要求士人必须学《诗经》等,说明在儒家学派内乃至朝廷政策上将出自民间的歌谣《诗经·国风》等纳入到“大传统”之中。当然,从歌谣论的层面来看,“大传统”向“小传统”开放是动态的,《诗经·国风》之外,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又不断有新的成分纳入其中,比如中国古代自成理论体系的文论专著——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设有《乐府》专章,论述从传说夏禹时代的歌谣《涂山歌》到汉魏乐府民歌,堪称一部歌谣批评简史,一方面维护崇雅斥《郑》、“中和之响”的传统,另一方面吸纳民间歌谣与文人拟乐府的积极因素,无疑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继续推进这种开放性的还有唐代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和《新乐府序》、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等,相继在雅俗文学乃至“大小传统”的互动中闪烁着理论的光彩。
中国歌谣论的第二阶段:存真与启蒙明清时期歌谣论者较之以前更是精彩纷呈,人才辈出,如李东阳、李梦阳、王廷相、杨慎、李开先、王世贞、吴国伦、王世懋、赵南星、胡应麟、冯梦龙、李贽、徐渭、袁宏道、江盈科、钟惺、谭元春、王士禛、赵翼、王廷绍、华广生、杜文澜、刘毓崧、黄遵宪等,而且较之以前有其新特点。歌谣(还有散曲、戏曲等),到明清时期又称为“时调”,即“时兴之曲调”,强调当时的歌谣等为“时兴”的“曲调”。显然,明清歌谣具有较多的当代性、时新味。在这种当代性、时新味的歌谣流传之中,歌谣论者一部分关注传统,较多地论乐府民歌(或有拟乐府),也有一部分追赶“时新”,走近“歌场”,阐发具有某种“在场”意味的歌谣论。明代中期的李梦阳走进街市,聆听“里巷妇女之口”的时兴歌谣,目击有感,即兴评论,道出“情词婉曲”与“真”的特色,强调“真诗乃在民间”(8)李梦阳:《诗集自序》,《空同子集》卷首,明万历三十年邓云霄刻本。。晚明的袁宏道等人为了摆脱程朱理学和复古模拟等“格套”,将目光转向闾巷歌谣,追求真情与真声:“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9)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简而言之,乃是“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10)袁宏道:《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因而,袁宏道等人在开拓文学之“流”中往往斩断与传统文学、传统文化的联系,转而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野语街谈随意取,懒将文学拟先秦。”(11)袁宏道:《斋中偶题》,《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09页。。晚明时期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指出:“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12)冯梦龙:《叙山歌》,冯梦龙编纂《山歌》卷首,《明清明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力求“存真”,努力接民间“地气”,使民间与文人两支队伍在民歌传播中的汇合,推动了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真”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冲击封建礼教和拟古文风的文学解放(启蒙)思潮的发展。晚清作为“诗界革命”旗帜的黄遵宪,关注民歌,走近“歌场”,目击成诗,有《山歌》十五首等。同时,主张吸取《粤讴》等民歌时调,创作“杂歌谣”,吸取天籁自鸣的民间歌谣的长处:“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13)黄遵宪:《山歌题记》,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第12页。由此可见,黄遵宪“杂歌谣”的主张与他“我手写我口”(14)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42页。等“诗界革命”论是相通的。显然,明清时期歌谣论的亮色为“存真”与启蒙。
二
20世纪上半叶,不少文人将眼光投向民歌民谣,在继承中国传统歌谣理论批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吸收西方有关民歌的观念,更新视角,勇于探索,推动中国歌谣理论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与新中国七十年中呈现出“承变与出新”的特色,这其中又细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为承变与出新的“新芽期”,新中国七十年为承变与出新的“新苗期”。在此,我们先说:
中国歌谣论的第三阶段:承变与出新——新芽期这个时期的歌谣论在承变中萌发出一片“新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借鉴国外经验与民歌整理及研究
意大利公使馆外交官卫太尔(Guido Vitale)(1858-1930)采录编辑了一本汉语教材《北京的歌谣》并于1896年由北京天主教北堂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民歌采集与整理的先导。胡适、周作人等人很欣赏,胡适从中“选出一些有文学趣味的俗歌,介绍给国中爱‘真诗’的文人们”(15)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载于《读书杂志》,1922年10月1日第2期。。周作人数次在《歌谣》周刊撰文介绍此书,还将他自己撰写的《〈北京的歌谣〉序》在《歌谣》周刊上刊载两次。在借鉴国外民歌整理与研究的经验方面,刘复著有《国外民歌译》《海外的中国民歌》等,周作人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Frank kids.n《英国民歌论》中的观点,指出:“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16)周作人:《中国民歌的特质》,《学艺》,1920年第2卷第1期。从歌谣征集与整理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歌谣》树立了榜样,这影响了当时许多民歌搜集与整理者,如刘半农(刘复)的《江阴船歌》、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乃至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整理歌谣》、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等对怎样搜集与整理歌谣进行探讨。后者说:“俗曲的搜集,虽然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的端,而孔德学校购入大批车王府曲本,却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17)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民国十四年(1925)秋,刘复无意中见到车王府流出的一批曲本,便促使孔德学校“以五十元买成,整整装满了两大书架,而车王府曲本的声名,竟喧传全国了”(18)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中国俗曲总目稿》中所收的俗曲“共有六千多种,其中标(车)字的即车王府曲本”(19)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这批收藏,对中国歌谣等整理与研究是一大贡献。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是歌谣论的基础,正是在歌谣搜集与整理的土壤中萌生出“承变与出新”的歌谣理论的“新芽”,当然其中也借助于西学东渐与欧风美雨。
2.歌谣的起源与特质及价值
朱自清有一部在大学的讲稿《中国歌谣》(1929-1931),分别从歌谣释名、起源与发展、历史、分类、结构、修辞等方面论述中国歌谣,是“五四”以来中国歌谣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专著。其中对于歌谣的起源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引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史纲要》稿本中《韵文先发生之痕迹》的观点,认为巫风(“以歌舞为职以乐人者”)是歌谣的滥觞;又介绍歌谣起源的多种传说:荧惑说、怨谤说、《子夜歌》传说、河南传说(“故事精”老人)、淮南传说、江南传说、两粤传说(歌仙“刘三妹”)等。进而阐明他自己的见解:“歌谣起于个人的创造。”(20)朱自清:《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中国歌谣》,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版。这个时期论者往往认为歌谣的特色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如李素英《吴歌的特质》中指出:“水柔山丽,‘文质彬彬’的江南,尤其是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风景天然,生活优裕。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歌谣,当然是温婉清丽,恰与苏州人一样。吴歌里确是一致的充溢着一种希有的灵秀之气,婉妙之情;任何人读了都会觉得神志清明,中心愉悦,何况‘吴侬软语’一向是被认为声调最优美的方言!”(21)李素英:《吴歌的特质》,《歌谣》周刊,1936年地卷第2期。陆孙《时调小曲》中对苏、扬二地的时调进行比较:“时调小曲,苏州与扬州,各独步大江南北……苏州小调媚而腻,扬州小调媚而爽,苏州质浊,扬州骨清,苏州甜而似猪油八宝饭,扬州甜而似杏仁橘肉汤。”(22)陆孙:《时调小曲》,《诚报》,1947年11月11日第2版。李广田《滇谣小记》以南北歌谣作为对比,对云南地区歌谣的一些特质如野性泼辣、金刚怒目等进行了挖掘。然而,其目的绝非在于平白的介绍与陈述,乃是从新诗的现状出发,指出当时“大多数高级的诗歌却又容易失之于苍白而虚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鲜泼野的力量”(23)李广田:《滇谣小记》,《观察》,1947年第9期。,主张从民间歌谣中汲取原始而野性的充沛精神。周作人也认为:“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24)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学艺》,1920年第2卷第1期。关于歌谣的价值界定,有社会价值与文艺价值两个维度。周作人强调歌谣在反映社会思潮上的功用,他曾于《歌谣》一文中明确指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共通的精魂”(25)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歌谣》周刊第16号,民国十二年(1923)4月29日。。常惠《谈北京的歌谣》以意大利人韦大列所编《北京的歌谣》与美国人何德兰所编《孺子歌图》中的几首北京童谣为例,通过对比坊间版本的歧异,对此类童谣中有关语言、风俗、民间故事的演变进行了考析,指出“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26)常惠:《谈北京的歌谣》,《歌谣》周刊,1924年第43期。,充分肯定了歌谣的民俗学价值。魏建功《歌谣之词语及调谱》中指出:在北大歌谣整理运动如火如荼的上世纪20年代,歌谣研究的诸多领军人物中,有一些人绝非仅仅为了文学而文学,而带有以歌谣类通俗文学体裁作为工具,进而启迪民智、组织民众乃至改造社会的宏大构想。胡适《〈吴歌甲集〉序》等中从方言与国语文学性的比较出发,认为“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27)胡适:《〈吴歌甲集〉序》,《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7期,1925年10月4日。,从文学史建构的角度肯定了方言文学相对于主流话语的独特地位,并对方言文学在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提出了展望。
3.歌谣的分类与表现手法
朱自清《中国歌谣》中有《歌谣分类》一章,提出歌谣分类的标准:音乐、实质、形式、风格、作法、母题、语言、韵脚、歌者、地域、时代、职业、民族、人数、效用等。他认为民歌可分类为:情歌(恋歌)、生活歌(家庭生活歌、社会生活歌、职业歌——农歌、渔歌、船歌、樵歌、采茶歌、商人歌、军人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猥亵歌、劝戒歌等。朱自清所说的歌谣分类的标准之一为母题。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以诗歌母题作为切入口研究民间歌谣尚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朱光潜《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以西方美学中的性欲母题模式介入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对“原始诗歌”——歌谣从潜意识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谓“性欲母题”概念乃是借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一个包含欲望、爱情、求偶等系列内容的宽泛概念。朱光潜以此为探索基石,结合中国苗人跳月及西方“俄狄浦斯情结” 等民俗现象及社会心态,对弗洛伊德等人有关歌谣的性欲起源问题有所怀疑,认为“性欲的表现虽是一般民歌的特色,但是说民歌起源于性欲的表现,也还有商酌的余地”,进而得出“在真正原始的社会中,性爱并不是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28)朱光潜:《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歌谣》周刊,1936年第2卷第2期。这一结论。
关于歌谣的表现手法,这时歌谣论涉及到多方面,其中歌谣的结构问题最为关注。朱自清《歌谣的结构》一方面对顾颉刚、钟敬文诸人的论争进行了梳理,将各家的意见概括为三种,即“重叠是个人的创作”“是合唱的结果”“乐工所编制”。另一方面,又不限于客观的追述,而是结合大量歌谣文献,认为歌谣是合唱的产物,并得出“中国歌谣的结构,赋叙实为正宗;但赋叙无确定的形式可言。有形式可言的,重叠是大宗”(29)朱自清:《歌谣的结构》,《中国歌谣》,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版。这一结论。有鉴于此,朱自清在文中以“无意义的重叠”“重章叠句”“和声”“回文”“接麻”“叠字”为例,对重叠的各类样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对诸如倡和、趁韵、嵌字、套句等中国传统歌谣所特有的表现法一一作了介绍。作为歌谣音乐特征的主要形式,重叠的实质即民间歌谣的音乐属性,朱自清对于歌谣这一类结构的重视,避开了仅把歌谣作为民间心理的构想误区,进而实现了对歌谣艺术性进行重估的目的,这在歌谣研究体系的建构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魏建功在《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中指出中国歌谣最为典型的表现法之一即重奏复沓。该文就时人在论述《诗经》歌谣时所关注的“诗中歌谣是否为已成乐章的歌谣”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比《诗经》与近代民间歌谣演唱中的复沓现象,指出“重奏复沓是歌谣的表现的一个最要紧的方法”(30)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歌谣》周刊,1924年第41期。,而其终极原因并非刻意讲求格调,而是为了服从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需要。
4.诗歌的歌谣化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如何从外国文学、中国古典诗学及民间歌谣三个维度汲取营养,是这个时期比较关注的话题。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性人物,朱自清同胡适、周作人等人类似,对于民间歌谣与诗歌的天然联系历来有所关注,曾撰写《歌谣与诗》《歌谣之诗》等文,以意大利人韦大列(卫太尔)“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的说法作为逻辑起点,对于一般人认同的歌谣“真诗”属性重新进行定义。朱自清从歌谣与新诗在雅俗之别的文化背景出发,认为尽管“诗起源于歌谣,是大家承认的”,且“歌谣可以供创作新诗的参考”(31)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周刊,1937年第3卷第1期。,但是如何避免新诗在汲取民间歌谣养分的同时流于表面,走上“止于偶然摹仿,当作玩艺儿”(32)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周刊,1937年第3卷第1期。的歧路,也是中国新诗开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关隘。梁实秋对于歌谣的看法往往兼具文艺学与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在《歌谣与新诗》中对于当时歌谣运动与新诗的建构问题予以回应。他首先以比较文学的眼光,对英国歌谣复兴与诗歌革新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的回顾,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形却与英国十八世纪中叶有一点仿佛”(33)梁实秋:《歌谣与新诗》,《歌谣》周刊,1936年第2卷第9期。。然而,对于当时歌谣整理运动是否真能效仿英国,最终推动本国新诗的进步,实则还是抱有模棱两可的犹疑态度。正因如此,其一方面从当时新诗所最感困难的音节问题出发,认为“我们的新诗与其模仿外国的‘无韵诗’‘十四行诗’之类,还不如回过头来就教于民间的歌谣”;另一方面又主张“须有一个文学的标准加以选择”(34)梁实秋:《歌谣与新诗》,《歌谣》周刊,1936年第2卷第9期。,从雅俗文学共进的角度,对于新诗歌谣的雅化问题提出了期待。朱光潜的歌谣学研究亦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大歌谣整理运动,在此前后撰写了《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性欲“母题”在原始诗歌中的位置》等文。作为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大量汲取克罗齐、布拉德雷等西方学人的美学理论,以“诗所写的情趣是特殊的,所以要一个特殊的形式”作为起点,重申了新诗中节奏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朱光潜又将目光投放到民间歌谣之上,从重叠、和声、衬字等方面对歌谣的形式与历史渊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对于诗的形式,我主张随时变迁,我却也反对完全抛弃传统”(35)朱光潜:《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歌谣》周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对于诗歌向民间歌谣汲取养分抱以深切的期待。
三
中国歌谣论的第四阶段:承变与出新——新苗期20世纪下半叶与21世纪初(1949-2022)(以下称为“新中国”),歌谣论的“承变中出新”由“新芽期”进入“新苗期”,一方面以歌谣如“引歌”等论歌谣,如“山歌无本句句真, 唱好两句停一停, 辫子甩出第三句, 眼乌珠一转四句成”(36)《山歌无本句句真》,江苏南通山歌,《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19页。;另一方面用文人的眼光以评论文论歌谣 ,如领导人毛泽东及郭沫若、周扬,与赵景深、郭绍虞、老舍、叶德均、贾芝、路工、姜彬、金煦、段宝林、雷达等,继承与弘扬中国历史上重视底层文化与文学——民歌民谣的优秀传统,贴近现实,推陈出新,将歌谣理论与歌谣创作、传播同步推进,引领中国歌谣理论的建构,其中涉及到歌谣的释名、内涵、价值、传播、影响,歌谣的母题、风格、原生态、大众化、抒情特色、叙事特色、审美形象,歌谣的曲调、歌谣与民俗、宗教、政治、经济、小说、诗词、戏曲、方言、地域文化,乡村歌谣、校园歌谣、流行歌曲,歌谣与新诗等,并围绕“民歌概念的转换”“王洛宾事件”“校园民谣”“原生态民歌”等问题展开讨论,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承变与出新”的亮色:
1.歌谣的特质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37)《大子夜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4页。口出真声,清新自然,是南朝民歌乃至中国歌谣最显著的特质。如江苏民歌《六月荷花出水鲜》:“六月荷花出水鲜,荷花爱藕藕爱莲,荷花爱藕满身白,藕爱荷花出水鲜。”(38)高福民、金熙:《吴歌遗产集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这首民歌真情真声,清新自然,将男女相悦之情真切而又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歌谣论者所说的“天籁之自鸣”(39)赵景深:《霓裳续谱·序》引葛兰波《霓裳续谱·跋》中语,《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天籁,是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自然是世间万物的本然状态,也是民歌的本然状态(真),本然(天然)——真,是民歌最主要的特质。这些“天籁”之声来自民众,也最为人民大众所欢迎。例如2002年10月,在国家文化部上海“天籁之声”全国民歌演唱会上,一支河曲“二人台”《走西口》获得了上海观众与在场的外国客人经久不息的如雷掌声。贾芝《中国歌谣集成·序》中指出:“民歌是人民大众的‘天籁’之声,心中怎么想就怎么唱,世界万物信手拈来,都可入诗。诗人们也不能不感叹地说:‘真诗乃在民间!’”(40)贾芝:《中国歌谣集成·序》,《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卷首。张德建等认为由明中期李梦阳发出并由后人不断引用的“真诗乃在民间”的核心逻辑是“真”,但“真”义认识本身没有为民歌进入文人创作提供可能性,于是“真诗乃在民间”陷于理论与创作相矛盾的困境(41)张德建:《“真诗乃在民间”论的再认识》,《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关于民歌“口出真声,清新自然”的特质,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原生态民歌。金兆钧《关于原生态和学院派之争的观察与思考》(《人民音乐》,2005年第4期)、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黄允箴《撞击与转型——论原生态民歌传播主体的萎缩》(《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付晓玲《原生态民歌的理性思考》(《民族音乐》,2006年第3期)、连赟《原生态民歌与舞台民歌关系探微》(《人民音乐》,2006年第4期)、王磊《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中国音乐》,2006 年第4期)、俞人豪《“原生态”的音乐与音乐的原生态》(《人民音乐》,2006年第9期)、冯光钰《叫民间唱法如何》(《当代电视》,2006年第9期)以及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原生态民歌的内涵进行讨论,其中有的论者认为原生态民歌是非创作作品,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用当地方言进行演唱的,靠的是人民生活中的口口相传。不过当前对原生态民歌内涵的界说,与以往传统民歌的定义相比,较为突出地强调了原生态民歌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的环境因素等。由此并结合近期多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云南印象”“原声黄河——十大乡土歌王歌后民歌演唱会”“天籁之音”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会等,特别是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原生态唱法比赛,引出了“当前原生态民歌比赛”问题的讨论,在对原生态民歌界定基本认同的前提下,目前论者对于原生态民歌比赛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尤其是对于比赛能否有效保护原生态民歌,论者存在着赞同、肯定与保留、怀疑两种相反意见。陈宗花等认为,这场研讨暴露出学界在原生态民歌及相关理论认知上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某些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如评价标准问题等亟需得到充分重视(42)陈宗花:《当前原生态民歌问题研究述评》,《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这些,均有待于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承变与创新,这对于建构以“口出真声、清新自然”为特质的歌谣理论颇有推动作用。显然,20世纪上半叶关于歌谣特质方面的论述侧重于地域性与民间性,而新中国七十年期间关于民歌特质方面的论述发展为“真声”、原生态与“天籁之音”,在理论上更接近歌谣的特质,由“新芽”成长为“新苗”。
2.歌谣“声与义的双重美感”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43)《毛诗正义》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7页。“丝竹发歌声,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44)《大子夜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四十五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4页。民歌中的歌词与音乐是合为一体的,歌词是其文学形态,曲调是其音乐形态,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歌词借声(曲调)而飞扬,民歌具有义与声的双重美感(45)参见贾芝《中国歌谣集成·总序》,《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卷首,第8页;陈书录等《二十世纪后期歌谣的新兴》,《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颇有“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46)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页。的审美效应。新中国歌谣论中,对于作为音乐形态曲调的研究,往往与作为文学形态的歌词研究相辅相成,如李焕之《调式研究》(47)李焕之:《调式研究》,《人民音乐》,1950年1卷2、3、4期。、方萌《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考》(48)方萌:《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考》,《人民音乐》,1993年第1期。、路行《小调介绍》(49)路行:《小调介绍》,《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等主编,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87-694页。、 万光治《民歌声词关系与词牌、曲牌的产生——以四川民歌〈月儿落西下〉为例》等。后者以《月儿落西下》等四川民歌为例说明:在民歌的原创阶段与传播过程中,民歌歌词已具备自然声律之美。歌手遵循以字定腔的原则,且由此确定了歌词与曲调的基本关系。“以字行腔”与“以情润腔”的结合,终于使民歌曲调与歌词间的关系臻于和谐。“无论民间还是文人,在歌曲的创作中,歌词总是第一义的。歌词的情感色彩是音乐情感处理的契机,具有自然声韵之美的歌词,其声调又是音乐旋律走向的依据。从歌词而到曲调,民歌完成了自己的原创。自此,相对固化的曲调,才有所谓的‘依声填词’,也才有可能开始自己词牌化与曲牌化的过程。”(50)万光治:《民歌声词关系与词牌、曲牌的产生——以四川民歌〈月儿落西下〉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跨入21世纪以来歌谣论者又有对歌谣的“再发现”:一是作为文本的歌谣,二是作为声音的歌谣。歌谣化新诗的音响节奏激活了那些外在于理性认知的、属于身体感官层面的因素。对歌谣音乐特质的承袭,必然是一种主动争夺身体记忆、塑造大众感官感知的尝试。而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各种诗歌形式的实验及其对应的评价体系,同时也伴随着持续的自我批评与焦虑,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民歌形式”这一论题的先声(51)康凌:《“大众化”的“节奏”——左翼新诗歌谣化运动中的身体动员与感官政治》,《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重视歌谣的声与义的双重美感,特别应该加强以文学为本位的歌谣研究,比如歌谣的母题、风格、原生态、大众化、抒情特色、叙事特色、审美形象(意象)以及比兴、排比、对比、夸张、衬托、重叠等艺术手法的研究,新中国的歌谣论在以上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歌谣审美意象的研究,更有创新特色。段友文《民歌的审美意象》以意象作为切入口,审视中国民歌的艺术特征,试图对民歌意象的主要性质、生成原因、组合方式、文化意蕴等予以观照,以期对民歌艺术的深层研究进行有益的探索,通过对民歌意象整体性的阐释,从设喻取象的意象创造、宏大鲜明的意象特征、丰富多变的构象组合等方面对中国民歌的艺术特征予以观照,并最终将其归结为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意蕴层面对民歌意象的源头进行了探索性的审视。如果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的关键是将民歌意象与文人诗歌意象进行比较,从而表明在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上,民歌与文人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段友文等论者指出:对诗人来说,社会生活是他感知、理解、把握的对象,是他情感理念作用的对象物,主、客体之间是一种观照与被观照、体验与被体验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距离与情感距离。民歌的创作则不然,它常常是伴随着物质生产或生活一道进行的,创作主体的情感冲动、直觉感受很少受到“精英文化”和上层思想体系的干扰,民歌的内容就是民众生活的直接显现,是他们内在情感的直接吐露,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相融无间,具有一体化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民歌创作具有髙速性、便捷性,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歌是民众蓄之既深的一种情感的凝聚物,它既是文学,又是人民抒发真情实感的重要方式,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有生活与文学的双重特性(52)段友文:《民歌的审美意象》,《东方丛刊》,2000第4辑,总第三十四辑。。中国歌谣论者既要“入乎其中”,将研究的视角对准歌谣的主要内涵——文学(歌词)与音乐(曲调),又要“出乎其外”,扩大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途径,力求将文学与文献学、音乐、民俗学、语言学、美学、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传播学、地域文化、民间思维等相结合,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明清民国歌谣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3.新诗的“歌谣化”
诗的歌谣化,早在20世纪上半叶也是歌谣论中的一个话题,而在新中国七十年期间更为深入,并结合实践中的得失进行考察,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的歌谣化理论从嫩绿的“新芽”演变为茁壮的“新苗”。晚清作为“诗界革命”旗帜的黄遵宪倡导“杂歌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刘半农、沈从文等宣扬并尝试“新诗的歌谣化”,“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周扬指出:中国现代新诗“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而以“大跃进”民歌为代表的新民歌则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量成功且有益的探索,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53)周扬:《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选自《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还有1980-90年代大众文化浪潮中出现了“新民谣”变奏与讨论。段宝林在《论民歌的体式与诗律》注意到:在讨论新诗发展的方向时,有人认为应以民歌为基础创造出一套新诗来,有人则反对这样做,认为那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这种争论此起彼落随形势而发展。过去是前一种意见占优势,现在则后一种意见又占了上风,认为诗歌要现代化,就要从国外引进新形式,民歌“原始”“古老”,早已过时,因而对学习民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种意见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而,他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民歌特点的梳理,对中国民歌的体式和诗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索,认为“民歌体”体裁众多、诗律丰富,对其诗律的研究对于当代新诗创作和文艺学、美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54)段宝林:《论民歌的体色与诗律》,《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1期。。张桃洲在《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中则持不同的意见,他通过从新诗建构的角度,考察歌谣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参与新诗寻求文类合法性、探索风格多样性和更新文本与文化形态的过程,辨析二者在互动过程中所取得成功与遭遇的困境,由此指出:在现代性语境中,歌谣自身的拘囿限制了其对新诗建构的可能性(55)张桃洲在:《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探究新诗“歌谣化”的得失,分析“大跃进”民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典型解剖。贺仲明认为: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新诗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民歌潮流,也是新诗和民歌最全面而广泛的一次“亲密接触”。“新民歌运动”的某些失误,可以看作是新诗发展中与生活和大众长期疏离积弊的报复性结果。“新民歌运动”对中国新诗发展基本上是负作用的,对新诗与民歌、与农民文化的关系也有严重的阻滞。当然,我们回顾新诗史上的民歌潮流,不是要求诗人简单地回归民歌、再造民歌,而主要是希望诗人从民歌中吸取精神的养分,真正使新诗民族化、本土化。如果能够从这方面来反思新诗史上的几次民歌潮流,深化对新诗与民歌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那么,它们也就有了足够的历史意义(56)贺仲明:《论民歌与新诗发展的复杂关系——以三次民歌潮流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应该说,新诗的“歌谣化”是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七十年来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既是歌谣理论的研究问题,也是新诗创作的实践课题。以往有关理论与实践表明:虽然新诗的“歌谣化”有利于发挥教育民众、鼓动大众的功用,但“歌谣化”的新诗往往出现某些“非诗化”的倾向,缺乏审美感染力。如何在歌谣参预新诗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激发创作活力,提高审美能力,这是歌谣论者的理论研究与新诗作者的创作实践面临的必须攻克的重点、难点课题。只要知难而进,久久为功,一定能走出一条歌谣理论创新与歌谣积极参预新诗发展进程的成功之路。
认真梳理中国历代特别是近百年歌谣论的进程,不难发现:新中国歌谣理论探究的深度与对现实的关注度,是中国传统歌谣理论批评中比较少见的,而且丰富多彩,不断在承变中出新,在歌谣的特质、歌谣声与义的双重美感、新诗的“歌谣化”等方面呈现出许多亮色,尤其不可估量的是新中国歌谣论在“大小传统”互动中的特殊意义,其中之一是歌谣从传统社会中被主流文化所冷落的点状的民间文学、底层文化,开始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有时还以点面结合的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中的高潮。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和1959年3月《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为配合经济生产领域的“大跃进”,号召大规模收集民间歌谣,在文艺界和群众领域开展“新民歌运动”,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大力引导作为大众文学、大众文化的民歌参预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中,甚至成主流文学和文化的中流砥柱。当然,这种高潮有回落,乃至有回流,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不少值得反省之处。但是,新中国的歌谣与理论批评已参预到主流文化的建设之中,开拓出一条“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崭新道路,歌谣论的“新苗”正在茁壮成长。
毋庸置疑,20世纪以来中国歌谣论的成果与歌谣大国的地位还难以匹配,对于歌谣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中也有某些误解或曲解。人们往往比较关注诗论、词论、文论等的价值的发掘,而比较忽视歌谣论价值的发掘。歌谣论作为一支大众文化及俗文学的特别的生力军,开拓出一条“大传统”与“小传统”(其实,所谓的“小传统”并非“小”,而是大众化的传统)互动的崭新道路,颇有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的文化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这对于拓展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领域,全面、系统地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与文学传统,建构中国优秀歌谣的传承体系与理论体系,激发中华文化的创造活力,特别是激发新诗的创造活力,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