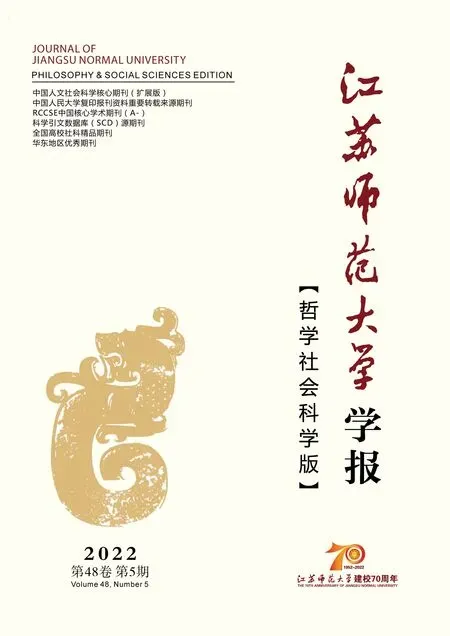情禅:闵齐伋《六幻西厢记》编撰思想之佛学解读
乔光辉 沈欣仪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闵齐伋(1580-1662)刊《六幻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幻因)、董解元《西厢记》(搊幻)、王实甫《西厢记》(剧幻)、关汉卿《续西厢记》(赓幻)、李日华《南西厢记》(更幻)、陆天池《南西厢记》(幻住)等六部作品汇集,以“六幻”加以统摄,且以“如幻”系列彩色套印图解西厢,不仅在《西厢记》版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开启了清初《西来意》等禅释西厢之先,在《西厢记》阐释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闵齐伋刊刻《六幻西厢记》与西厢版画之思想,集中体现在《六幻西厢记》卷首序言《会真六幻》中,为下文论述方便,特此引出:
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真曰幻。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真即幻、非真非幻。元才子记得千真万真,可可会在幻境;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攧翻簸弄,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真在耶!
曰微之记真得幻即不问,且道箇中落在甚地?昔有老禅,笃爱斯剧,人问佳境安在?曰:“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我则曰:“‘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举似‘西来意’,有无差别?”
古德有言:“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不然,莺莺老去矣,诗人安在哉?耽耽热眼,呆矣!
与汝说“会真六幻”竟。(1)闵齐伋:《明致和堂刻本六幻西厢记》第1册之首,文化艺术出版社影印本,2012年版。
闵齐伋借此论述了其禅释西厢的基本主张,然既有学界尚不见对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及该序的详尽解读。综观闵序之论述层次,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谈闵齐伋之真幻观,包括真与幻之关系;第二部分谈闵齐伋对西厢“句中玄”与“玄中玄”的理解,强调西厢之佳境在于“玄中玄”;第三部分正面提出禅意西厢阅读法;第四部分是其对“六幻西厢记”的具体划分(为节约篇幅,未引)。重点是前三部分,第四部分是其前三部分思想在编撰六部西厢系列作品中的运用。笔者拟由此入手,剖析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及套刻西厢版画之思想(2)笔者另文《如幻: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之于文本关系再探》有述,闵刻套印“西厢版画”,其思想根源于此。。
一、真幻观:闵释《西厢》之逻辑起点
闵齐伋提出禅释西厢,根源于其观世界的基本态度。闵序《会真六幻》首句“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真曰幻”,即如何看待“真与幻”,是一切世间基本解脱之法。“一切世”为秽土之总称。佛教之“世间”类别也多,说法不同。《大智度论》卷七十:“世间有三种,一者五众世间、二者众生世间、三者国土世间。”(3)释厚观:《大智度论讲义》,台湾大学哲学系汉传佛学研究室,2014年内部印,第1985页。《大乘起信论》称:“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停,须臾变坏。……世间一切有身,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4)[日]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丰子恺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因一切世皆有不净,故要寻求出世之法。“出世法”又称“出世间道”,即出离有为迷界之道。依闵齐伋句意,理解“真与幻”的关系便是出离一切世间迷界之前提。
佛学认为,一切法有真、妄二者,随无明之染缘而生起之法为妄,随三学(戒、定、慧)之净缘而生起之法为真。《大乘起信论》将大乘法分为二种门:真如门与生灭门。真如为体,生灭为相,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区别(5)[日]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丰子恺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闵齐伋之“曰真曰幻”与佛学之真、妄、真如与生灭当属同一意。“幻”指假相,一切事象皆无实体性,唯现如幻之假相,即幻相;其存在则谓幻有。所显现之如幻现象,犹如魔术师之化作,故称幻化。“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界有为之法,无得久停,须臾变坏……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于云,歘尔而起。”(6)[日]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丰子恺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金刚经》亦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闵齐伋之“曰真曰幻”,真为本体,幻为现象;与真如门不离生灭门、生灭门不离真如门一样。举真如之体,不离生灭幻相;举生灭幻相,不离真如之体。两者相互容受。
与第一句从正面说不同,第二句:“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真即幻、非真非幻。”则从反面言说,对第一句作拓展延伸。关于“非法非非法”的理解,可以参照无趣如空禅师的一段公案:
无趣空参,每呈见解,师谐不诺。一日谓趣曰:我有一言,要与汝说。空耸耳而听,师但笑而不语。空再四恳请。师复笑。空始具威仪作礼,跽而哀恳。师乃曰:“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贵在直下体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万缘,参个一归何处。”趣从此死心看话头,经三载,一日闻鸡鸣有省,诣师求证。师反覆徵诘,后付衣拂。
复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7)(清)聂先编:《续指月录》卷十四“嘉兴东塔野翁晓禅师”,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十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798页。
此段是无趣禅师(1491-1580,字如空)“放下万缘、死心看话头”“闻鸡鸣开悟”的公案。野翁晓禅师结尾所示“非法非非法”之偈语,对无趣如空禅师的开悟作了总结。用闵齐伋的话来说,就是“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真即幻、非真非幻” 。
解读这个公案的切入口就是野翁晓禅师的偈语。六祖慧能“风动幡动心动”公案为后世公案定下了基调。无论是风吹幡动还是经幡自己动,都是众生可以理解的客观现象。甚至根据物理定律,一旦测知风速与作用于经幡的受力面积,我们便可以计算出经幡所受之推力大小。但是,一个物理学可以解决的客观现象,被慧能转为主观的精神现象。以赵州和尚“柏树子”公案为例:
僧问赵州: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有。僧云:几时成佛?州云:待虚空落地。僧云:虚空几时落地?州云:待柏树子成佛。(8)(宋)赜藏主(僧挺守頤)编:《古尊宿语录》卷十四,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弟子想得知一个确切的答案,但赵州和尚以循环论证打破了弟子的执着。与此绕路说禅不同,归省禅师与弟子的对答,则从正面回应“柏树子”之机锋:

当归省禅师以“汝还闻檐头水滴声么”启发弟子时,弟子瞬间顿悟,以“檐头水滴,分明历历。打破乾坤,当下心息”作答,“师为忻然”意即归省禅师对学生的回答很满意。可见,归省禅师的发问:“汝还闻檐头水滴声么?”并不是希望得到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测试弟子能否将“檐头水滴声”觉悟为佛法,在“水滴声”中见自性之空。
明乎此,回头再看无趣如空禅师“一日闻鸡鸣有省”公案,鸡鸣声与水滴声、钟声一样,属自然现象,但“也可以把它听为另一些东西,如把它听作释迦牟尼的说法。于是,钟声就成为‘真空’或‘法’的现象了。……这里,钟声已经被从物理的时空背景剥离,而还原为纯粹的听觉现象。‘朝朝击鼓,夜夜钟声’,它们并非世俗生活的标志。”(10)张节末:《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借听声以觉悟不仅要将声音剥离特定的时空背景,还原为纯粹的精神现象,而且还要于声音中直观佛法,将声音观作佛法的见证。所以,百丈怀海说:“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11)(宋)赜藏主(僧挺守頤)编:《古尊宿语录》卷第二“大鉴下三世语之余”,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上。能否将声、色从变动不居的时空背景中剥离出来,并直观佛性,则视个体之资质与历练等而有差异。无趣如空禅师“经三载,一日闻鸡鸣有省”,也是量变引起质变之结果。
野翁晓禅师在反覆徵诘后,予以认可,并复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依据佛学解释,“法”指所有之存在,“性”指受外界影响亦不改变之本质,“心”指远离对象仍具有思量(缘虑)之作用者。“法、性、心”指修行的不同领域,晓禅师所传授的心法,指出概念与事实有联系但又不同,修行者应“既不执着于什么,又不执着于‘不执着于什么’”。“A即非A”也是《金刚经》常用言说句式,诸如“如来说一切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世间之色与声,不过是视觉与听觉表象,如果执着于声色,则为世俗所迷,不见如来。具有大乘佛法总经性质的《金刚经》称:“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法即无上觉,即无念,无念不可取;佛法离言说相,了无能说,故不可说。如果执着于般若或执着于没有般若,皆不见如来。修行者对于“法、非法、非非法”等,皆不应执着。
由此,野翁晓禅师之“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偈语,是对无趣禅师闻鸡鸣而开悟的学理总结。无趣如空禅师“闻鸡鸣有省”,此鸡鸣已非彼鸡鸣,已从报时等特定实用功能中剥离,化为单纯静观之表象,并被听作佛音之见证。鸡鸣声依旧,但于无趣禅师,三年前与如今,已经发生了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看山依旧是山,看水依旧是水”的质变。
再回到闵齐伋,其对“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的回答是“即真即幻、非真非幻”。如上所述,“非法非非法”是大乘佛学开悟之关键。“即真即幻”之“幻”指如幻而无实体之假相。以佛教立场而言,诸法皆由因缘和合而生,由因缘离散而灭,本身并无实体,其因缘和合之际,虽可形成一一之法,然实为幻假之相。《大智度论》曰:“众生如幻,听法者亦如幻。……我如幻、如梦,众生乃至知者、见者亦如幻、如梦。诸天子!色如幻、如梦,受想行识如幻、如梦。”(12)释厚观:《大智度论讲义》卷五十五“释幻人听法品第二十八”,第1547页。由此,闵齐伋“即真即幻、非真非幻”描述大乘法观世界之关键,在于从实体上超脱,在幻与真之间不作二分。
闵齐伋之“真幻”观用于西厢题材系列作品,称:“元才子记得千真万真,可可会在幻境;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攧翻簸弄,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真在耶!”其首先对作品作了“真”与“幻”的区分,即读者公认的“真”是元稹《会真记》(即《莺莺传》),因为该作有史实依据;而董、王、关、李、陆则是基于元稹《莺莺传》基础上的改编,属于虚构,皆是虚幻,“洵幻矣”!同时,他对这一看法又提出质疑:“元才子记得千真万真,可可会在幻境。”即元稹的《会真记》尽管有史实依据,但恰如一幻(13)闵齐伋“五剧笺疑”之“佛殿奇逢”释“行一步可人怜”称:“可,犹言恰恰也。”见《明致和堂刻本〈六幻西厢记〉》第8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会真记”的“真”指“仙真”崔莺莺,张生会莺莺,恍如一梦,恰恰是真中有幻;而“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攧翻簸弄,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真在耶!”董、王、关、李、陆之改编创作,虽属于虚构,但是戏如人生,其中也可悟出“真”来。闵齐伋《题〈西厢〉》又云:“使其升关、闽、濂、洛之堂,聪明胆识不下某某辈,成一家言,黼黻六经。即祭祀血食,宁异人任?……道器命性,徵角宫商,究竟亦无异。”(14)杨绪容整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6页。实际是将《西厢记》与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颢)之学并列,视《西厢记》为“黼黻六经”之作,道器不二,从“徵角宫商”的戏曲演唱中参透性命之学。
闵齐伋《六幻西厢记》之“赓幻·五剧笺疑”识语称:“世界原是疑局,古今共处疑团。不疑何从起信,信体仍是疑根。我今所疑,孰非前人之确信?我今所信,孰非来者之大疑?”(15)(明)闵齐伋:《明致和堂刻本〈六幻西厢记〉》第8册尾“五剧笺疑识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尽管他说“疑者不笺,笺者不疑”,但他并不执着,“我今所信,孰非来者之大疑?” 事实上,闵齐伋之“五剧笺疑”对于剧作字词的注音、释义、校勘很见功力。然“五剧笺疑”署名“湖上闵遇五戏墨”,“戏墨”就是随意戏作的笔墨,可见闵齐伋之淡然。
二、西来意:《西厢记》之“句中玄”与“玄中玄”
闵齐伋序言之第二部分,承袭第一部分意思展开:“曰微之记真得幻即不问,且道箇中落在甚地?”将议论由上转下,即使不追问元稹《莺莺传》的“真中寓幻”的“幻”究竟体现在哪里,那董、王、关、李、陆作品之“幻中寓真”的“真”又落在何处?“箇中”即其中,指与“真中寓幻”相对的“幻中寓真”作品。由此,闵齐伋以自问自答形式,提出了他对《西厢记》的理解:
昔有老禅,笃爱斯剧,人问佳境安在?曰:“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我则曰:“‘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举似‘西来意’,有无差别?”(16)(明)闵齐伋:《明致和堂刻本六幻西厢记》第1册之首,文化艺术出版社影印本,2012年版。
其中,闵齐伋所说的“句中玄”“玄中玄”源于临济宗创始人临济义玄。《五灯会元》卷十一载:“(义玄)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语须具三玄门,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17)(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5页。但对“三玄”,临济义玄禅师并没有留下明确论述。后代发扬者以“古塔主”荐福禅师(970-1045)为最。他将三玄释为“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言三玄非临济门风,而是诸佛普度众生之法(18)张云江:《北宋荐福承古承嗣云门文偃禅师之“公案”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二“青原八世·荐福古禅师”对“三玄”记录甚详:
古(即古塔主荐福承古禅师)曰:“三玄者,一体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门是佛祖正见。学道人但随人得一玄,已具正见,入得诸佛阃域。”
僧问:“依何圣教参详,悟得体中玄?”古曰:“……如此等,方是正见。才缺纤毫,即成邪见,便有剩法,不了唯心。”
僧曰:“何等语句是句中玄?” 古曰:“……若于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总通。所以体中玄,见解一时净尽。从此已后,总无佛法知见,便能与人去钉楔、脱笼头,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脱得知见见解,犹在于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为未悟道故。于他分上所有言句,谓之不答话。今世以此为极则,天下大行,祖风歇灭,为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须明玄中玄。”
僧曰:“何等语句时节因缘是玄中玄?”古曰:“……此等因缘方便门中以为玄极,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
僧曰:“三玄须得一时圆备,若未见圆备有何过?”古曰:“但得体中玄,未了句中玄。……谓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见,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须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返为此知见奴使,并无实行,有憎爱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体中玄也。……凡学道人,纵悟得一种玄门,又须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脱洒路上,始得平稳,脚踏实地。” ……古曰:“盖缘三世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体中玄。三世祖师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与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19)(宋)惠洪:《禅林僧宝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6-91页。
这段文字详尽叙述了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关联与差异。如其所云,“体中玄”是合于教乘、不脱义理逻辑的佛学正见,是“三世诸佛所有言句教法”;“句中玄”是“于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总通”,是“三世祖师所有言句并教法”,意在引导学人于言句下悟得真理;“玄中玄”则为“不涉言句”,是“十方三世佛之与祖所有心法”(20)关于“三玄”,可参读(释)鉴印著《试论义玄禅法思想与门庭设施》(《临济宗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及郭庆财之《惠洪的文字禅与句法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第63页)。。“体中玄”与“句中玄”均涉及言语,前者是如来教中正见言语;后者是以文字禅形式,于言语处令人醒悟。据荐福禅师所言,“三玄”中“学道人但随人得一玄,已具正见,入得诸佛阃域”,但“凡学道人,纵悟得一种玄门,又须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脱洒路上,始得平稳,脚踏实地。”很明显,“古塔主”荐福禅师所说的“玄中玄”,因不涉语言,属于比“体中玄”“句中玄”更高级别的悟法层次。明乎此,我们再看闵齐伋的论述。闵齐伋舍弃了“体中玄”,针对《西厢记》“箇中落在甚地”之发问,提出《西厢记》之“句中玄”与“玄中玄”读法,借以回答《西厢记》“幻中寓真”之“真谛”究竟落在甚地?
闵齐伋当作“句中玄”的剧本台词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句,出自第一本第一折末尾[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21)杨绪容整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明弘治戊午(1498)金台岳本《西厢记》首次将署名“西蜀璧山来凤道人著”之《新增秋波一转轮》作为附文本,置诸“引首”,其文称:
夫既因二五媾精而有此身,则情欲相感,本诸天而具于我。故凡夫妇……为欲念之所牵;况以生、莺才美无双,聪慧莫及,其能免是欲念乎?……况淑女于临去之时,敛媚凝娇,秋波一转,则彼酷嗜风流,素耽放逸者,宁不勃然而感动耶?(22)王实甫:《新刊大字魁本参增奇妙西厢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来凤道人以为天赋情欲,崔张为欲念所牵,勃然而感动,“秋波一转”实为男女传情之信号。至于此句与参禅结合,也有传统(23)王同轨《耳谈类增》、冯梦龙《古今谭概》、张岱《快园好古》等文献均有记载。。其中冯梦龙(1574-1646)称:“丘琼山过一寺,见四壁俱画西厢,曰:‘空门安得有此?’僧曰:‘老僧从此悟禅。’丘问:‘何处悟?’答曰:‘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24)(明)冯梦龙辑:《古今谭概》卷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6页。邱琼山即邱浚(1420-1495),广东琼山人,因称邱琼山。这表明,明代寺院一直存在“借西厢以禅悟”之现象。至清初尤侗(1618-1704)则视“秋波一转”为情禅,“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缭乱也哉!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语禅恰在个中。”(25)伏涤修等辑校:《〈西厢记〉资料汇编》,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667页。从而,本为男女传情之“秋波一转”演为僧家“禅悟”之机锋。
由来凤道人“情欲相感”到后来之僧家“禅语”,根源于观法之差异。剧中张生从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动作,读出崔莺莺对其有“顾盼”之意,“将一座梵王宫,化作武陵源”。仅仅靠与崔莺莺“打个照面”,便堕入情网。“临去秋波那一转”是个舞台科介动作,崔莺莺走下舞台之前,做了一个“旦-回顾-觑末-下”的动作,即回过头来深情地凝视张生,并对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便迅速走下舞台。由“秋波一转”引发了剧中崔张各种情事,诸家评点皆认为此句是“一部西厢关窍”。此句本是男女为“欲念之所牵”,是世间尘境;而“老僧从此悟禅”是寂灭之境。禅悟则要将“秋波那一转”从男女相悦的特定时空背景中剥离,仅作为一个静观符号。至于金圣叹评语:“眼如转,实未转也。在张生必争云‘转’,在我必为双文争‘不曾转’也。”(26)(元)王实甫著,(清)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眨一下眼睛,可视作女方有意为之,也可视作女方生理之自然反应。当然,特定语境下可以成为男女传情之信号。但究竟是自然现象还是传情之信号,可有多种解读。托名郭璞的《青囊海角经》卷四“点穴”有云:
昔有僧看西厢,官人见而呵之曰:“若晓得一部西厢,重在那一句,我便饶。”僧对曰:“只重在‘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此言深中肯綮。地理千言万语,门例虽多,有情无情亦难辨认。有身在千里,思忆不忘而有情者;有连袂同床,面合心离而无情者。山川性情大率相似。人能透得此关,方不被他瞒过。(27)托名郭璞的《青囊海角经》卷四“点穴”,古今图书集成本。
古人选择风水也如“临去秋波那一转”,有情无情依靠自己辨认,贵在两者相契。法身只有一个,因众生而异。对于张生而言,普救寺出现的崔莺莺就是“南海水月观音现”“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第一本第一折末尾《寄生草》唱词);对于“僧悟禅语”,则仅仅是一个静观的对象,已经脱离男女相恋的语境,又何来“勃然而感动”?
闵齐伋借用老僧“句中玄”,“于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总通”,将此句作为“一部西厢关窍”。毋庸置疑,“临去秋波那一转”带动了整个西厢剧情之发展。此句只是白描,并没有诉诸言语,与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也相吻合。闵齐伋赞叹老禅“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与诸家评论一样,他承认“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剧本最重要的情节,但依旧属于从《西厢记》文本中觅“文眼”,借文字以禅悟的“句中玄”层次。即没有脱离文字功夫,非为禅家第一义。
闵齐伋所说的“玄中玄”,指“不涉言句”的“十方三世佛之与祖所有心法”,他更推崇“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句,并认为这句可视为“祖师西来意”。该句出自第五本第四折[沈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这句叙写崔莺莺思念张生,纵有千种风情,见面后却说不出一句,只淡淡说了句“先生万福”(28)杨绪容整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闵齐伋称此为“玄中玄”,盖此种感情无法诉诸文字。崔莺莺原先准备着千言万语,及见面,瞬间化作乌有,大脑一片空白。钱锺书《宋诗选注》云:
此外还有经杨万里称赏而保存的《寄友人》一联好句:“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亲友久别重逢,要谈起来是话根儿剪不断的,可是千丝万缕,不知道拈起哪一个话头儿才好,情意的充沛反造成了语言的窘涩。尤袤的两句把这种情景真切而又经济地传达出来了。全首诗已经失传,断句也因此埋没,直到它经过扩充和引申,变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的《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待伸诉,及至相逢,一语也无,刚则道个‘先生万福!’”仿佛一根折断的杨柳枝儿,给人捡起来,插在好泥土里,长成了一棵亭亭柳树。(29)钱锺书校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钱锺书所指出的“情意的充沛反造成了语言的窘涩”现象,与“非言教经典”所能传达之禅悟现象颇为类似,均是某一刹那的瞬间直觉顿悟。初祖达摩说:“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三祖僧璨说:“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30)(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下。崔莺莺精心准备的“腹中愁恰待申诉”,刹那之间化作乌有。刘应袭本中李卓吾评云:“无上妙谛。”徐渭也评此句云:“欲言不言,若疏若亲。的的真情,亦的的至情。”(31)杨绪容整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此种语境下,非色即是空,或空即是色,而是色空合一,语言成为多余。此时,张生或理解,或不理解,已与莺莺无关。
前句“临去秋波那一转”描述肢体动作,“秋波一转”对张生而言是“留情”,是莺莺对其“顾盼”之意;对禅悟僧人而言,则属于自然生理反应,压根不存在眉目传情之说。剧本只是描述舞台动作,如何解读是另外一回事;“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则不然,盖瞬间销情,预设好的千种风情、千言万语,瞬间空化,进入色空一体之境。前者法身只有一个,因众生而异。对“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的张生而言,“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崔莺莺对自己发出的信号;其意义不啻五祖弘忍“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更入室”而得传法衣钵(32)齐云鹿:《坛经大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但临去“以杖击碓三下”,于他人而言终究为浮云;莺莺“秋波那一转”,于他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于相逢之刹那,当事人莺莺瞬间忘情;前者,于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刹那,张生则瞬间生情。情生则智隔,“秋波一转”恰是张生进入“疯魔”之时。
从文学角度而言,“秋波一转”都意味着女子留情,令男生“勃然而感动”,心领神会,从而引发剧情发展。金圣叹也不否认“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在《西厢记》文本中的关键作用,但他推崇“尽人调戏”四字,以为“天仙化人,目无下土,人尽调戏,曾不知也”,“《西厢记》只此四字,便是吃烟火人道杀不到。千载徒传‘临去秋波’,不知已是第二句。”(33)(元)王实甫著,(清)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突出莺莺之天真自然。但“尽人调戏”与“秋波一转”,孰为第一、二“关窍”句,属见仁见智,其质并无差别;“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句,在于言说一种生活体验,情至浓极必归平淡。
从禅悟角度而言,闵齐伋以“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为“玄中玄”,而“临去秋波那一转”为“句中玄”,旨在强调后者之重要。面对“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与众人反应不一。犹如佛祖拈花,“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34)(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闵齐伋强调“玄中玄”为“初祖西来意”,则将生活体验上升为本体真谛。崔莺莺“及至相逢一句也无”的心理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35)释宗镜校刻:《达摩大师血脉论》,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10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何谓祖师西来意?初祖达摩自西天来此传法,究竟意思如何?究此意思者,即究佛祖之心印也。“玄中玄”为“十方三世佛之与祖所有心法”,即《楞伽经》所言:“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子,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法离文字故”“我等诸佛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著,至竟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36)南怀瑾:《楞伽大意今译》卷第四,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页。“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体现为瞬间的直觉顿悟,那一刹那,言语成为障碍,女主从久别重遇的恋人情境中剥离,“相逢”成为静观之表象。闵齐伋举之比“西来意”,并无差别。《达摩大师血脉论》称:“道非声色,微妙难见。……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37)宗镜校刻:《达摩大师血脉论》,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10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从有形之文字中读出无字真义,这是闵齐伋禅释《西厢记》的核心内容。
三、情禅:闵齐伋之《西厢记》读法
闵齐伋序言《会真六幻》的第三部分是:“古德有言:‘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不然,莺莺老去矣,诗人安在哉?耽耽热眼,呆矣!与汝说‘会真六幻’竟。”核心在于“会得此意”,此意为何?即以西厢为禅的“情禅”阅读法。
此段引语中的“古德”,指临济祖师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俗姓骆,字无著,四川成都崇宁县人。声名卓著,皇帝多次召其问法,并赐紫衣和“佛果禅师”“圆悟”等,谥“真觉禅师”。克勤弟子耿延禧(?—1136)撰《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称:
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迦叶,乃此一音。……不作此音会,而作语言謷讹,妄生分别,无有是处。昔杨岐以此音,簧鼓天下。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师因频呼小玉之音与檀郎认得之音,然后大唱此音。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凡楼子“我若无心”之音,及盘山“红轮西去”之音,皆当立下风,尽是老冻脓。所以于建炎中兴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无敢鸣;云居安乐堂上,擅此一音,众人憎嫉,而无敢和。且道:此老子乘谁恩力,得恁么奇特?昔孔子穷于陈蔡之间,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乃曰:今之歌者其谁乎?是亦此音,而世未之知也,圆悟老师其知之矣。予蚤事佛鉴,晚见老师,叩此一音,更无别调。学徒若平亦唱师家曲者,集师语要将以刊行,求为序篇,以冠卷首。若知此音,则圆悟老师功不浪施。若不知此音,而以语言文字求会解者,是人行邪道,不能见老师云。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序。(38)(宋)耿延禧:《〈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耿延禧序之中心是讴歌圆悟克勤之弘法贡献。一音,一音声也,指如来之说法。《维摩经》“佛国品第一”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其意即“一雨普润,禀受不同;三兽渡河,证有深浅”(39)竺摩法师:《维摩经讲话》,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1991年版,第65页。。“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即指出临济宗克勤禅师开一代宗风,临济杨岐派由此震动天下。耿延禧提及圆悟禅师因艳情诗而开悟,《五灯会元》卷第十九“昭觉克勤禅师”也有记载:
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祇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祇认得声。”师曰:“祇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祇许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由此,所至推为上首。(40)(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十九“五祖演禅师法嗣·昭觉克勤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4页。
禅宗有以音声开悟之传统,《古尊宿语录》卷三十四记真净克文禅师(1025-1102)称:“南阎浮提众生以音声为佛事,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一从音声演出。乃至诸代祖师,天下老和尚,种种禅道,莫不皆从音声演出。”(41)(宋)赜藏主(僧挺守頤):《古尊宿语录》卷第四十三,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页下。此公案前半部叙五祖法演与提刑之交流,法演问提刑少时是否读过小艳诗,比如“频呼小玉元无事,祇要檀郎认得声”之类?提刑说读过。此时,圆悟克勤只是侍立于边的旁观者,但法演禅师与提刑的对话让他有所触动。之后他问:“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其中“会”自不同于“曾读”。接着圆悟克勤追问:“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同样声音,为什么“认得”却“不是”?法演回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
如前所述,以“柏树子”参究佛祖之心印,实即以柏树子当作禅法之见证,即“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频呼小玉元无事,祇要檀郎认得声”,小姐不断呼唤丫鬟小玉,并不是要丫鬟做啥事;只是通过自己的呼唤声,让情郎知道,小姐在这里。因此,檀郎认得声,明白小姐在这里;但此声尚不是“法身”。“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岂不是声?’”此鸡鸣声是鸡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或求偶或啼晨,当小姐“频呼小玉”与鸡“鼓翅而鸣”从世俗的实用功能中剥离时,从音声中听清净,从音声中悟佛法,便成为“一切声皆是佛声”。如释德洪(即惠洪,1071-1128)《注十明论》诗所云:“了知无性灭无明,空慧须从戒定生。频呼小玉元无意,只要檀郎认得声。”(42)(宋)释德洪:《石门文字禅》卷十五,见王国平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20册武林往哲遗著(七),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页。因此,无论“金鸭香销锦绣帏”,还是“少年一段风流事”,都可成为悟道的工具。
耿延禧序称:“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凡楼子‘我若无心’之音,及盘山‘红轮西去’之音,皆当立下风,尽是老冻脓。所以于建炎中兴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无敢鸣。”描叙了以圆悟克勤禅师为代表的临济杨歧派一枝独秀局面,超越了“德山歌,云门曲”(43)张培锋:《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天津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页。。云门曲,本指古乐曲之名,曲调艰深,公案以“云门一曲”比喻云门文偃(864-949)所立宗风孤危耸峻,人难凑泊。“凡楼子我若无心之音”之楼子和尚开悟事,见《禅林类聚》卷五:“楼子和尚因从街市过,经酒楼下,偶整袜带少住。闻楼上人唱曰:‘你既无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后录有三首出自不同禅师(慈受深、宝峰明瑄、佛慈鉴禅师)的颂古诗,其中慈受深(1077-1132)颂云:“唱歌楼上语风流,你既无心我也休。打着奴奴心里事,平生恩爱冷湫湫。”(44)(元)道泰、智境辑:《禅林类聚》卷五《悟道》,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08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下。“及盘山红轮西去之音”指与宝积禅师悟道相关的颂古诗,《禅林类聚》卷五“幽州盘山宝积禅师”载:“(嗣马祖)初参马祖。作街坊。一日出门,见人舁丧歌郎振铃云:‘红轮决定沉西去,未委魂灵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师覩之忽然省悟。举似马祖,祖印可之。”后录文殊道、佛灯珣、海印信、月林观禅师所作四首颂古诗句,其中文殊道禅师(1058-1129)颂曰:“歌声缭绕哭声悲,笑杀盘山老古锥。历劫无明昏暗处,一时顿觉发光辉。”(45)(元)道泰、智境辑:《禅林类聚》卷五《悟道》,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08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上。耿延禧所称“皆当立下风,尽是老冻脓”,表明克勤禅法后来居上。“建炎中兴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无敢鸣”指圆悟克勤受宋高宗召见,“驾幸维扬,有诏征见,顾问西竺道要。对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统万殊,真俗虽异,一心初无间然。’太上大悦,赐号圜悟禅师。”(46)(宋)祖琇:《僧宝正续传》卷第四,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00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下。众所周知,圆悟克勤《碧岩录》的“拈古”禅将公案、颂文和经教三者结合起来,用逻辑语言叙述和评判古德公案的意旨,“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超越云门等其他各宗,开启临济杨歧派一代宗风。
闵齐伋引用圆悟克勤禅师禅悟典故,其潜在用意是提出并推广其《西厢》“情禅”阅读法。“西厢”故事以崔张二人恋情为核心,圆悟克勤又因“小艳诗”而开悟;且圆悟克勤后来独领风骚,“四海寂默”。那么,《西厢》情禅解读法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并于诸多阅读法中独领风骚?闵齐伋称:“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耽耽热眼,呆矣!”“此意”为何?即与“耽耽热眼”相对立的“情禅”阅读法。
“情禅”即以情求道,情与修行本为悖论。众所周知,对于佛教各宗派而言,情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始终是被超越的对象,诸家佛典都强调“情生则智隔”。《紫柏尊者全集》之“净土偈”:“觉即情不生,情生成杀佛。杀佛堕地狱,难生莲花国。能使情不生,弥陀自来迎。”(47)(明)达观真可撰,憨山德清校:《紫栢尊者全集》卷二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05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上。《大乘起信论》云:“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48)[日]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第七章,丰子恺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其中“心生灭门”即宇宙万象,为随缘起灭的世间情感,其与真如为一体两面关系,真如是本体,生灭是现象。但如果停留在“心生灭门”,则无法见如来。故佛典多云“一念情生,万劫羁锁”“一念情生,即堕异趣”等。《五灯会元》“鼎州德山宣鉴禅师”称:“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49)(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页。均将情视为禅悟之障碍。
欲与情一样,泛指对一切可意之根尘境界的贪执。《庞居士语录》云:“相见论修道,更莫著淫欲。淫欲暂时情,长劫入地狱。”(50)谭伟:《庞居士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页。《憨山老人梦游集》称:“盖寻常男女,纯以淫欲之心求之,故多愚痴,原非智慧心所生也;今不以淫欲心求,而求之于大士,则是原出智慧。”(51)(明)憨山德清:《〈白衣陀罗尼经〉后跋》,见曹越编《明清四大高僧文集憨山老人梦游集》上册“题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页。《圆悟克勤禅法心要》称:“正欲确然清身洁意。内守虚闲、外廓闻见,密运慧刃,剸割情欲,返照回光,如灵云见桃花,香严闻击竹,以至‘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非风、铃鸣,我心鸣耳。”(52)圆悟克勤:《圆悟克勤禅法心要》,明尧、明洁校注,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453页。均主张去欲。不随情欲,方见如来。
但是,禅宗主张色上悟空。如《大乘起信论》说生灭门与真如门不一不异,真如是宇宙本体,生灭是宇宙现象;但并非真如之外还有生灭,生灭现象之外还有真如本体,二者不相离,真如即生灭,生灭即真如(53)[日]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丰子恺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坛经》中慧能亦云:“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此是二乘见解。……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54)齐云鹿:《坛经大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男女情欲本为生灭,是修行障碍。西厢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相遇相爱之过程,虽有波折,终得团圆。即于烦恼证菩提,修得正果。
六根所对之六尘,恰是悟道之所必须,男女情爱与佛学修行本是水火不容,但经历禅观转化后,色相剥离了特定的时空背景,便无所着落,成为单纯静观之符号。《大智度论》卷六载文殊师利为胜意菩萨时,与喜根菩萨辩论。喜根语诸弟子:“一切诸法淫欲相,瞋恚相,愚痴相,此诸法相即是诸法实相,无所挂碍。”胜意菩萨以此说:“是杂行人,非纯清净。”后胜意菩萨身入地狱。“喜根集僧,一心说偈:淫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若有人分别,淫怒痴及道,是人去佛远,譬如天与地。”(55)释厚观编:《大智度论讲义》,台湾大学哲学系汉传佛学研究室,2014年内部印,第186页。文殊师利赞扬喜根,实即肯定“淫欲即是道”。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五说:“今问:淫事秽污,佛道清净,安指秽事名为净道?答:观淫怒痴,相同水月,了染净体,性如虚空。遇顺无着,逢违不瞋。于恶境界,得解脱门,乃行非道,通达佛道,是名无碍人。”(56)(宋)法云著(富世平校注):《翻译名义集校注》卷五,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20页。此从体相、净染之范畴道出了“淫欲即是道”的成因。
《维摩诘经》中提出“在欲行禅”观念,即借色相以悟空,于五欲淤泥中生出莲花。“佛道品第八”云:“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57)竺摩法师:《维摩经讲话》,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1991年版,第326页。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而粪壤之地乃能滋茂。所以,绝缘女色,等于把种子殖在空中,终不得升华。只有经受一番欲火中烧的考验,才能得其真谛。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示有妻妾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烧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58)竺摩法师:《维摩经讲话》,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1991年版,第326页。食色乃人之本性,菩萨行于非道而自能生出佛法。食色与五浊一样,在欲行禅,便从特定时空背景中剥离,从世俗功能中超脱,心不再为色相所羁绊。身为在家居士,示受无欲而不贪,如火中生莲花,“在欲行禅”虽很罕见又并非不能。“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 达观禅师(紫柏大师)《观音菩萨赞》之《鱼篮》中即谓:“菩萨无地可站立,无奈去作马郎妇,以欲钩牵度众苦。譬如以毒攻毒疾,疾除毒亦了无所,何妨鬼脸与神头!”称“在欲行禅”如以毒攻毒,疾除毒亦无。龚自珍《夜坐》诗句:“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59)(清)龚自珍:《夜作》诗句,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7页。所言正属此类。
上引“楼子我若无心”之典故中,慈受深、宝峰明瑄、佛慈鉴禅师之诗偈,慈受深禅师之“打着奴奴心里事,平生恩爱冷啾啾”,便是男女恩爱后的醒悟;宝峰明禅师云:“你既无心我亦休,此身无喜亦无忧。饥来吃饭困来睡,花落从教逐水流。”则视五浊色相如吃饭睡觉,以平常心待之;佛慈鉴禅师云:“你若无心我也休,鸳鸯怅里懒抬头。家童为问深深意,笑指纱窗月正秋。”此“有心无心”之情欲不过如纱窗秋月,逢场作戏,五浊焉能缚我?虽说爱情只是一场虚幻,而透过虚幻,或许更容易看到世间的真相。一如苏曼殊所言:“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60)苏曼殊:《寄调筝人》三首的第二首,见《苏曼殊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尽管西厢描写男女情欲,然视西厢为情禅,“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即便“朝夕把玩”,也不会为情所迷。
与情禅读法相对立,是“耽耽热眼”读法。闵齐伋从不能将文本坐实入手,进而正面提出论点。此段后半部称:“不然,莺莺老去矣,诗人安在哉?耽耽热眼,呆矣!与汝说‘会真六幻’竟。”其中“莺莺老去,诗人安在?”句出自苏轼之《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61)(宋)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子野即北宋词人张先(990-1078),字子野。“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意味老夫少妻,东坡对高龄纳妾的张先予以嘲讽。此处,闵齐伋反其次序用之,“莺莺老去,诗人安在?”莺莺本为文学人物,不同时代的“诗人”们如董、王、关、李、陆等皆对其歌咏,毕竟青春、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对西厢故事的改编也将持续。就此意义而言,诗人们可以老去,但“莺莺”不会老去。如果将文本视为实有,则莺莺不会永远年轻,也会经历生老病死,幻身终将归去。“莺莺老去,诗人安在?”莺莺既然已经老去,又何来诗人歌咏?
由此,闵氏以“耽耽热眼”读西厢是呆读法。“耽耽”即“眈眈”,出自《周易》,《易·颐》云:“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来知德注曰:“人欲重叠而来故曰‘逐逐’。”(62)(明)来知德撰:《周易集注》上册卷六“颐”,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即瞪目逼视而急欲攫取,背后是欲望,是情随物迁。“热眼”即目光热切,犹如匹夫之面红耳赤。如果怀着窥视、猎艳心理阅读西厢,情溺于中,则不免被文本牵着走,沉溺于情节则不能超脱。
可见,“情禅”阅读客观上要求读者拉开与文本的距离。读者阅读文本,但不能被文本牵着鼻子走,应适当保持与文本之间的距离。美学家鲍山葵《美学三讲》称:
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不快多少是一种单调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有能力把你的不快经验的对象和素材提了出来,或者使之具有想象的形状,那么你的经验就必须经过一次改变。你的情感就被纳入一个对象的那些规律里面。它必须具备稳定性、秩序、和谐、意义,总之,必须具备价值。……最后表现了的情感是一个新的创造,并不是人开头感到的简单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痛苦了。这里的情感或情感体验是你没有的。这里的体现,当你感到时,是审美的情感。”(63)[英]鲍山葵:《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其所说的生活情感“被纳入一个对象的那些规律里面”,与色相被修行者从客观背景中剥离,在学理路径上是一致的。情感被规格化,经过脱胎换骨的变化,最终成为审美情感;苏珊·朗格《感受与形式》中称,大多数人“或过于繁忙或过于慵懒,无法将心灵从他们的日常利害中抽出来”,听众或者观众只有以“强烈的无利害观照”状态,“才会真正知觉到了艺术品并经历了审美情感。”(64)[美]苏珊·朗格:《感受与形式》,高艳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作为深谙中国美学精神的宗白华(1897-1986),其视美感为“人生对于世界之一种态度”,只有客观的态度才是审美的态度:
如见一开花之树,即直接看其树之本身色彩、背景,将树与己之关系完全划开,用客观的目光视察之,树之本体与原质乃毕现。此种态度,乃审美条件之一,绝无占有的、利害计算的、研究的、解剖的各种观念,必须如此才可审美。
……Contemplation(静观)此字之意,即停止一切冲动,用极冷静之眼光观察之。叔本华谓吾人若用Contemplation之状态,去观察,实为审美之要道。……如看失火——初见之则恐怖,因一切财产悉将毁坏,计算心生,即不能生美感。若能将此种观念消除,……此等愉快,即因为客观的、无关自身利害的一种观察,所谓Contemplation之状态是也。(65)宗白华:《美学》之“美感”“审美方法:静观论”,见《宗白华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7-438页。
Contemplation本为沉思、冥想之意,尤指基督教徒向上帝的凝神默祷。宗白华译为“静观”,是“无关自身利害的一种观察”;而“禅观”则为坐禅而观念真理。如此,“静观”理路上与“禅观”并无区别。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有句:“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66)(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2册第444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山中习静观朝槿”即于禅坐状态“静观”木槿花的朝开午萎,即是“禅观”。“禅”意即“静虑”,“静虑”包括﹕静其思虑与静中思虑,前者属“止”(“定”)﹐后者属“观”(“慧”)。禅观为禅宗修习之基本功﹐能制伏烦恼﹐能引发智慧。
“情禅”强调与文本保持距离,以使读者不为剧情所牵。“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逢场作戏”是将文本当作幻戏;“褏手旁观”则与我无关,情不附物;“朝夕把玩”,即作设身处地的体验,终能不沉溺于中。客观上将读者与文本分开,读者不再“耽耽热眼”,而阅读情感也转为无关功利的审美情感,阅读成为心灵净化的方式。
由于崔张故事发生地为普救寺,使剧本天然与佛学结下姻缘。待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首次提出禅释西厢。观其所论,侧重世界观与方法论,并没有将剧情与禅宗一一对应。嗣后,金圣叹也继承此路(67)康保成:《金批〈西厢〉》中的“无”字及其“绮语谈禅”解谜探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至潘廷璋(1612-1702后)《西来意》达顶峰,其“通过严格的文本求证,以‘色空’观念统贯全篇将《西厢记》……有意误读成喻示佛教教义的象征主义之作。”(68)张小芳:《〈西来意〉:〈西厢记〉哲思批评的终结》,《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可贵的是,尽管闵齐伋也提出禅释西厢,但没有“严格的文本求证”,强调保持与文本的审美距离,体现出其作为刊刻家的救世之心(69)可参见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这正是闵齐伋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