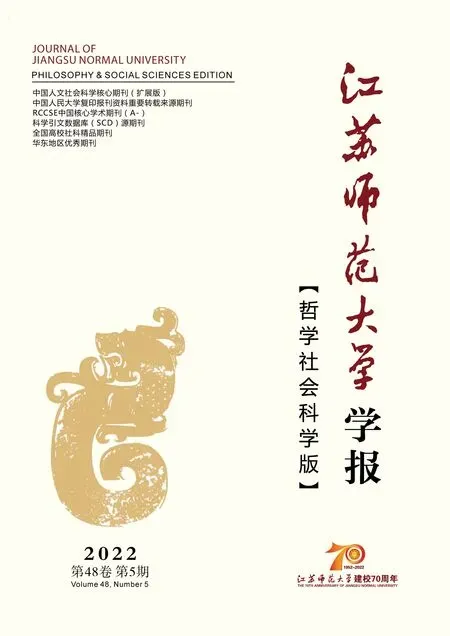“大道和同学”新论
钱耕森 沈素珍
(1.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大道和同学”是继“大道和生学”后的又一新论。“大道和生学”所要回答的是世界万物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突出了“和”在“生物”中的价值与意义;“大道和同学”在进一步探讨“和”与“同”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同”“和同”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的共同点,都是探讨“和”与“同”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不同的是探讨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
一、“大道和同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大道和同学”是以“同”“和同”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揭示“同”“和同”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
“同”除了“同则不继”“同而不和”的负能量一面,亦有不排斥“和”的正能量一面,诸如“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等等。
“同”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具有多样性含义,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和”与“同”结合为“和同”,“和同”即“由和而同”,它与“专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生态;“同”与“大”结合为“大同”,“大同”顾名思义即“大而同”,“大同”必然是由“大和”而达到“大同”,“大和”是“大同”的前题,没有“大和”,则无法形成“大同”。“大同”使“和”与“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是儒家以及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与最高的社会理想;“同”与“共”结合为“共同”,如“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共同富裕”,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必备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将整个人类以及人与自然作为和谐的共同体,来探索其发展,它是符合时代精神,体现人类共同意愿的战略思想。有关“同”的这方面内容,正是“大道和同学”所要研究探索的重要问题。它是对中国传统“和生”“和同”“大同”“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可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有关“大道和同学”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好评。牟钟鉴先生说:“大作《大道和生学》已见报拜读,确实很好”“吾兄所思与弟一致,即‘同’除了‘同而不和’的负义,亦有不排斥‘和’的正解,如‘大同’…… ‘同’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具有多样性含义,正需要学人深入阐发。吾兄年事渐高而理论创造力不减反增,令我钦佩。”(1)钱耕森:《大道和生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页。牟钟鉴先生与其他学者激励了笔者与同仁对“和”“同”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本文在前期初论的基础上,再一次深入阐述,故为新论。
二、“大道和同学”的提出
2012年笔者撰写的《大道和生学简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史伯的“和生”思想,在文中第三部分对“大道和同学”作了初步探索。
孙国柱评价说:“钱耕森教授将同异之间的关系也纳入‘和实生物’的讨论范围,拓展并深化了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今世界,很多人过于看重差异性,甚至走到否定同一性的地步,现在重新肯定‘同’的积极意义适得其时——当然,这种肯定最好建立在‘不同同之’的基础之上。其实,所谓‘不同同之’,决不是‘同而不和’的‘同’,而只能是‘和而不同’的‘和’。”“钱耕森教授主张不仅要提倡‘大道和生学’,也要提倡‘大道和同学’”(2)孙国柱:《钱耕森教授“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突破与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016年笔者撰写的《史伯论“和合”“和生”“和同”》一文,又对史伯的“和合”“和生”“和同”的“三和”进行了阐述。文章首先指出:在《国语·郑语》中,“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史伯在评价商契时提出了“合和”,“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在论证“周朝必亡”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生”)的哲理;在总结周先王用和谐政治来治国达到“和之至”时,提出这是“务和同也”。这三个“和”的含义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呢?文章分析了史伯提出这三个“和”的语境,结论是“在史伯那里,‘和合’只具有方法的意思”“‘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西周末年,史伯在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史上,率先提出了“和同之辩”。“和同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都有阐发。
史伯的“和同之辩”,主要阐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指出了“和”与“同”对事物发展的不同意义。随后又提出先王的“和同”与周幽王的“专同”两种政治理念的异同。春秋末期,晏婴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和”与“同”的差异,并且以烹调和羹、对待不同意见和演奏音乐为例,说明“和”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问》),深化了史伯的“和同之辩”。但是晏婴更重视“中”的意义,反对“过”与“不济”。他指出君臣之间在治理国家中应秉承“和”的关系,使其政治决策避免个人决策的偏差,而归于更加全面与正确,这是对史伯之论的补充与发展。孔子将“和”与“同”上升到道德层面,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论语·子路》)。这是对史伯、晏子“和同之辩”精神的理论提升。中国历史上的这场“和同之辩”,将“和”与“同”作为哲学概念提出,并进行深入探讨,影响深远。
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探讨“和”与“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价值,是对先哲“和”“同”思想的又一次传承与发展。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大道和同学”的理论渊源
史伯“和同之辩”中的“和”“同”说是“大道和同学”的理论渊源。
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讨论西周的命运以及郑桓公个人的前途时,提出“和同之辩”。主要记载在《国语·郑语》的《史伯为桓公论兴衰》(3)薛安勤、王连生注译《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为了全面掌握史伯的这一思想,现将有关内容选摘如下:
“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上述史伯“和同之辩”中的“和”与“同”的思想,是从“周朝必亡”这一论点展开的,他从六个方面加以论证:
1.史伯断言西周“殆于必弊”。其依据首先是“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周幽王在其治国理政中采取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的执政理念与错误的用人制度。
2.史伯为了进一步支撑西周“殆于必弊”的论点,又进一步揭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错误,他将“和”与“同”的思想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加以论证:“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说明了“和”与“同”在万物生存发展上的不同价值。
3.史伯进一步论证“和实生物”中的“和生”思想,强调“和”的多元性,多元的“他他”通过“平”才能“和生”万物。他以先王为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说先王也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杂”(实即“和”)在一起就能成百物。以“五行”来代表“他他”的多元性。
然后,他又运用一系列数字来进一步论证“他他”的多元性。他指出:“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五至十、百、千、万、亿、兆、经、姟极(最大数,古时认为万万兆为一姟),代表多元的“他他”,相互结合在一起,通过“以他平他”,就能“丰长而物归之”,产生出宇宙万物,这就形成了万物由多元的“和”而“生”的和谐宇宙观。
4.史伯又用先王“和谐”理念治国的成功经验来证实“和实生物”的哲理。“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先王正是运用了“和实生物”的和谐理念来治国,所以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这样就达到了“和之至也”,即最大的和、和谐的顶点。这是先王进行“务和同”的有效成果。
5.史伯接着又对“同则不继”进行了哲学证明,“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里的“一”为“同一的东西”,“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同”是简单的重复或者相加,归根到底都只能是“自我同一”“自我相加”“自我重复”而已,用尽了,便没有了,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实质上,这是对周幽王持“去和而取同”错误治国理念而误国从哲学上进行的论证与批判。
6.史伯断言西周“殆于必弊”,从哲理高度和执政角度深刻分析了周王朝垮台的必然性:“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周幽王抛弃先王“和谐”“和同”的理念与法则,而只搞“剸同”,只相信重用身边那些阿谀奉承、应声附和的佞臣。“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国语·郑语》)。这样下去,周朝将要亡了。这是周幽王“剸同”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史伯既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他将现实中具体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提到了“和同之辩”的哲理高度。最为可贵的是,他在论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理后,并没有简单地排斥“同”,而是将“同”辩证地区分为“和同”与“剸(专)同”。如果说他在回答万物生存发展的哲学问题上,为了进一步揭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理,将“和”与“同”对立,但在政治领域,他将“同”作了“和同”与“专同”的区分,这是十分睿智的,体现了他对“和”与“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与深刻性。他将“和生”哲学思想用于政治分析,揭示出“和同”与“剸同”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所导致天下兴衰的不同结局:一种是亡国,一种是达到了社会的“和之至”(和之极)。体现了他的“和同”政治观的价值与意义。他既鄙视“剸同”,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赞扬“和同”,寄希望于统治者以“和同”的理念来治国,形成了他的“和同”政治观。
由上述可知,史伯在“和同之辩”的论证中,既有“和生”的哲学思想,又有“和同”的政治思想。这两个思想分别成为“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的理论渊源。
四、“大道和同学”的理论内容
“大道和同学”传承与发展了史伯的“和同”思想,并将其上升到“道”的高度。
(一)“和同”的辩证哲学观
史伯的“和同之辩”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同”的对立,到政治观的“务和同”,又达到了“和”与“同”的辩证统一。
“和同”是“由和而同”,内含着“和”“异”“同”三个理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同”与“和”“异”是有区别的。“和”与“同”内涵不同。“同”是“单一”的。“和”是多元的,包含着“异”。但“同”与“和”“异”之间,又有联系。“和”“异”之中有“同”。“异”突出了“个性”,“同”突出了“共性”,有了“共性”,我们才能形成“统(同)一体”,才能和谐共生。反之,没有“共性”,也就无法形成统一体的共生。
“同”之中还有“和”“异”。“同”的“共性”,不能消灭“异”的“个性”。因而,只有“求同存异”的平衡,才能解决统一体的矛盾,从而和谐共生。
在这里,“求同存异”的平衡是其关键。相异事物的“他”与“他”组合成的矛盾统一体,经过“平”“平衡”,达到“和”“和谐”,就能“生物”“生万物”,其实这也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求同存异”解决了统一体内相异事物如何“平衡”的问题。没有这种“求同存异”,对立的各方只讲独立性,不讲统一(同一)性,这样矛盾统一体内就无法形成合力,也就无法“和谐共生”,不能得到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
“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即“平”“平衡”,即“求同存异”。“和”是多元的相异事物的统一体,因而“和”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求同存异”统一的一面。
事物发展由“和而不同”的多元到“由和而同”的和谐共生,即达到了“和同”,“和”与“同”在更高层次达到了统一。
“求同存异”是一个过程。多元事物通过“求同存异”的平衡,达到“统一”,旧的矛盾解决了。但“同”并不能消除“异”的个性,内部的各异力量此消彼长,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于是要再进行“求同存异”的平衡,也就是晏婴强调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儒家强调的“中和”。社会发展就是在异—和—和同—异—和—和同……,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循环往复的发展。这就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的体现。
“和同”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指不同的认识由“和”(“以他平他”“求同存异” )而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排斥异,而是在多元互补、集思广益后达到“和同”的新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和同”的共识,达到接近真理性认识,掌握规律。
“和同”体现在价值观上,就是在对待“和”与“同”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与“同”是辩证的关系,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既要分清主次,也要辩证对待。在“和”(突出个性的差异)时,要看到“同”的价值,不能一味地强调个性而否定共性,破坏共性。在“同”(突出统一性)时,要看到“和”(多元性)的价值。在社会组织或家庭中,既不能丧失个性,又要维护“同”的共性。
“和”具有多元性、相异性、平衡性、和谐性、新生性等基本特性及其所派生的开放性、包容性、持续性等等。可见,除了单一的“同”、自我的“同”、重复的“同”之类的“同”以外,还有许多正能量的“同”,如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共同富裕等,都体现了“同”的价值。这里的“同”,显然已具有了史伯提出的“和同”意义。
因此,我们在充分认识“和”的价值的同时,也要辩证地认识“和同”的价值。
(二)“和同”的和谐政治观
“和同”与“专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生态。深刻揭示这两种“同”的区别,对于今天和谐政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和同”的“同”与“专同”的“同”显然有别。“专同”的“同”,是“单一的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同”;“和同”是“由和而同”,是“多元”“和谐”基础上的“同”,是可以促进社会政治发展的“同”。
1.“专同”即“去和而取同”
“专同”表现为政治上的专制、专断,即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个人说了算,造成表面上的一致状态。如同周幽王“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喜欢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讨厌贤明正直的人,亲近愚顽鄙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正确主张。
这种“专同”,其危害是背弃了兼听则明的“和”的原则,导致偏听则暗的政治局面。政治只有一种声音,则万马齐喑究可哀,国家的兴盛,荡然无存。周幽王这种“专同”的治国理政的错误遭到了史伯的严厉批判,并断定周朝的衰亡将要来临。历史也已证明用这种“专同”来治国,最后总是逃脱不了亡国悲剧,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耿春红教授在评论史伯政治观时指出:史伯的“和实生物”学说的提出“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动,对中国两千年政治文化生态亦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具体来说即反对一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君主独裁的政治模式、一家一姓的国家属性。”“如果历代国王君主能够真正领会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国家政治文化的意义并遵循之,也许中国的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模样。”(4)耿春红:《“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政治文化生态解读》,《孔孟月刊》(台北),2018年第673-674期。
这种“专同”在今天来说,就是领导的主观意志排斥别人意见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表现为“去和而取同”的个人独断。它有碍于集思广益的民主决策,有碍于民主和谐政治局面的形成,有碍于民主政治体制建设的进程,更有碍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蓬勃发展。史伯对这种“专同”的批判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2.“和同”是“由和而同”
“和同”是在“多元”“和”的基础上的“同”,即是“对立”后的“统一”。这种“和同”包含了“和生”的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具有“和生”的属性。如同史伯所举先王的例子,用“和实生物”的“和同”原则来治国,就能达到“和乐如一”的“和之至”(最高的“和”、最大的“和”)的和谐社会。
“和同”的治国理念,在古代,即在朝的臣子要站在国家前途与人民安居乐业的立场上,各抒己见。君主也要承认臣子的独立人格,倾听与接纳不同意见,坚持兼听则明的原则,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这显然不同于君主个人独断,排斥异己的“专同”。中国历史上的明君无不是坚守这样的理念,从而实现社会繁荣发展的盛世,如唐太宗李世民。
晏婴发展了史伯的“和同”思想。他在论述“和同之异”时,认为君臣之间的“和”应该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其意为:君王所认为可(对的),如果其中还有否(不对的),臣子就应该指出那不对的部分,使对的部分更加完备;君王所认为不对的,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对的,臣子就应该指出那对的部分,把那不对的完全去掉。这就可以达到政治决策的公平,没有错误,比较全面,民众也就不会因感到社会不公正而生争斗之心。所谓“以成其可”“以去其否”,指的就是通过臣对君的不同意见进行切磋、争辩,在“可”或“否”上使君臣之间不同的认识达成共识,使君主抛弃原来的错误主张,或使其原有的正确主张得到进一步完善。这样达到君臣共识的“同”,是在“和”基础上的“同”,就可称之为“和同”。这种君臣的共商共议,避免了个人决策的偏差,而归于更加全面与正确。
“在历史上,赵高藉淫威所搞的‘指鹿为马’闹剧 ,造成秦二世身边无一谔谔之士,结果如殷纣王一样‘墨墨而亡’。这就是搞‘专同’的典型。而丞相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谏与纳谏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情境。唐太宗十分尊重并听取魏征的谔谔之言,推行正确的政策而‘谔谔以昌’,成就了‘贞观之治’。这就是君臣达成‘和同’的典范。”(5)朱贻庭:《“和”的本质在于“生”——“大道和生学”之我见》,《江汉论坛》,2016年第6期。
史伯与晏婴的“和同”思想与现代的民主精神是相通的,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政治领域的领导决策,关乎国家、集体与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因此更要集体领导,而不允许个人专断。由于个人认知的差异性,个人专断往往会出现决策的偏差,只有集思广益,坚持人民的民主参与,共谋国家发展大计,才是和谐的政治体制。
(三)“和同”的和谐社会观
在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既要讲“和”又要讲“同”,这种“同”不是“专同”而是“和同”,是在“和”基础上的“同”。
“和同”既包含了多元的“和”的“差异性”,又包含了“同”的“统一性”,是二者的合一。因此,“和”与“同”的关系内含着“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我们在承认“差异性”时,又要坚持“同一性”,在讲“同一性”时,又要肯定“差异性”,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哲学基础,即既要民主自由,又要统一意志。
如果我们只讲“同一性”的统一意志,不讲“差异性”的民主自由,束缚了个性,社会就会失去“多元性”,丧失了社会多元和谐发展的勃勃生机,必然萎缩倒退。多元才能互补,多元的和谐才能共生,合作共赢,才能生生不息地可持续发展。合作如果只讲单赢,则不能长久,合作只有多赢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原来“和平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又加上“合作共赢”的补充,既考虑到了统一性,又考虑到了多元性。达到了统一性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
但若我们只讲“差异性”不讲“同一性”,社会将处于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合作共赢、和谐共生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更不要说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合作共赢、和谐共生都是以社会的有序发展为前提的。社会只有在有序中才能前进。社会的法律、法规、制度、规章、规范,都要求人们行为的统一(同一),没有统一意志,就不会有统一行动。这种“同”是在“和”的基础上的“同”,即史伯所说的“和同”。这是在人民利益至上基础上的“同”,是社会和谐共生基础上的“同”。这种“同” 显然已具有了“和生”的属性,故能推进社会生生不息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无不如此。
市场经济中的某些价值取向是追逐个人利益至上,强调自我,看重差异性,否定同一性,甚至于以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诸如社会上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市场的恶性竞争、经济的以利为重、政治领域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等,尤其是国家在大灾大难时,个人利益至上,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辩证地正确认识差异性与同一性、民主自由与统一意志,是十分必要的,差异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是有差异性的同一性,这也就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所以,既要差异性又要同一性,既要民主自由又要统一意志,以此世界观与认识论来指导实践,个人与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周易》所讲的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同人》卦,就是专门讲“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不仅“和”与“同”二者可为一,而且“和”与“同”与“善”三者可为一。
因此,“和同”在社会建设中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如,在社会建设中的“同心同德”、在遇到民族灾难时的“同舟共济”、在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的“同仇敌忾”、在今天努力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今天我们所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强调多元,强调“和”,又强调“同”(统一),即是“和同”价值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体现。
五、中华民族从“和同”到“大同”的追求
1.对“和同”的和谐社会追求
在《国语·郑语》中,史伯论述了“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理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所以,君王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实现了“和乐如一”“和之至”(至高的和至极的和)。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娶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众多的事情,都是坚持了“和同”的原则。从而也就证明了“务和同”才能实现和谐同一(统一)的社会。
早在5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提出了“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主张,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明理念源远流长,它为世世代代开创了和谐政治、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并直接影响到了其五世孙尧帝。尧帝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尚书·尧典》第一段写道:“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舜帝提出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的原则。
周王朝总结夏商灭亡的教训,更加重视政治和谐。《尚书·无逸》记载,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其意为周文王从早上到太阳偏西,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和睦幸福的生活。《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阴:通“荫”:庇护。 骘:安定。相:助。协:和谐。)上天庇护安定下民,君王教导他们和睦相处。周公旦所著《周礼》提出:“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大宰》)。他告诫成王,努力实现政治和谐,提醒成王在行动上要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周成王也谆谆告诫百官要“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尚书·周书·周官第二十二》)。“万国咸宁”源于《周易·乾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国语·周语》记载了虢文公在谏宣王不籍千亩时,多次运用“和”这一概念,如“和协辑睦”“民用和同”“和于民”(《国语·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等等。这说明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在周朝已有了共识。
中华民族一以贯之地追求着和谐,“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精髓,成了中华文化的标识。
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社会矛盾激化,如何使社会实现安定和谐,诸子百家争相献言。各家主张虽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治国思想的探索,都在谋划自己理想的和谐社会。
儒家讲“和谐”着重于“礼制”,其高足有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为典型代表,并建立“仁学”体系,用“仁爱”“仁者爱人”的德治原则来进行“修齐治平”,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墨家讲“和谐”着重于“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家讲“和谐”更关注的则是由宇宙和谐的本原和规律衍生出来的人间和谐,高度探求“天和”“人和”“心和”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老子与庄子都曾设计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国。法家讲“和谐”着重于以法制为载体,通过法制的实施与履行来实现和谐。虽然在当时法律为政权服务,具有强制性与专制性,但在社会除恶扬善方面,对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简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虽是百家争鸣,但“和谐治国”成了儒、墨、道、法四大家的一致认识。春秋战国后的历朝历代,始终追求构建和谐社会,并代代相传。
2.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
西周末史伯提出的“和同”的和谐社会建设理念,到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
“大同”的概念已在《尚书·洪范》中出现,“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意思是,如果你赞同,龟卜赞同, 蓍筮赞同,朝廷大臣赞同,民众赞同,这就叫大同。这个“同”不是单一的同,而是多元的“大同”。
《庄子·在宥》提出:“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其意是人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战国末《吕氏春秋·有始览》提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孔子及儒家将“大同”作为理想社会的追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是谓大同”句下注曰:“同,犹和也,平也。”在这里“同”“和”“平”为一体。
大同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由和而同”的多元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不分彼此,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人都讲信修睦,友爱团结,没有争斗,社会和谐。因而是“大同”“大和”“大平”的社会。
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为历代儒家以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改革家所推崇,成为他们所向往的目标。如近代的康有为著有《大同书》,谭嗣同、孙中山的思想中都含有“大同”的理念。“大同”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史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崇高追求。
六、“大道和同学”以“天下大同”为最高追求
孔子及儒家将“天下为公”的“大同”提升为自己追求的大道。“道”是孔子最高的信仰与一生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早晨听到了道,学到了道,得到了道和行到了道,即使当晚因此而死,那也是很值得的。可见,孔子极大地彰显了道的价值。他为道而献身的精神十分崇高!
“大道”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天下”是“为公”而不是“为家”。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各自“为私”的。但是,由于这个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以变“私”为“公”,甚至变为“大公”。“大公”即人人无私,从而社会就实现了公平,人人平等;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在“大同”社会里,充满了“和而不同”“由和而同”的多元和谐,它既是多元的,又是同一(统一)的,是在多元和谐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即“和之至”(至高的和至极的和)。因而,“大同社会”是“大公”“大同”“大和”“大平”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真、善、美”的社会。
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80岁那年总结出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多元的美;“美人之美”,就是要包容欣赏别人的美;“美美与共”,就是要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融合在一起;“天下大同”,就会实现大同理想中的美。大同之美的本质就是融合不同的美。这一思想与精神体现了人类社会各种文明由“和而不同”走向“由和而同”“由和而大同”“由和而大美”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发展规律。
道家老子与庄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都突出其美。老子的理想社会是“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老子·六十七章》)的“小国寡民”。庄子的理想社会是“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在“至德之世”里,万物众生,比邻而居,亲密无间,人人平等。自然界生机盎然,禽兽众多,草木茂盛。人与禽兽为友,可以随意牵引着禽兽到处游玩,也可以任意攀爬鸟窠窥看鸟儿。《庄子·在宥》提出:“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其意为人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真正实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大同”“大美”的社会。
庄子将理想社会称之为“至德之世”,是一个道德至高至极的社会,凸显了社会道德的力量。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德莫大于和”,他不仅把“和”视为“德”,而且还把“和”视为“最大的德”。“天下为公”有了“和”的最大道德的支撑,使多元的人人都讲信修睦,相亲相爱,这样才能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大美”的社会。可见,“真”“善”“美”在“大同社会”中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大同社会”也就是“真、善、美”的社会。
“大道和同学”将“和同”提高到大道的高度,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最高理想,以“天下大同”为最高追求,同时也是对“真、善、美”的最大追求。
以上主要从“大道和同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理论的提出、理论来源、理论内容、中华民族从“和同”到“大同”的追求以及“大道和同学”以“天下大同”为最高追求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大道和同学”理论主要包括“和同”的辩证哲学观、和谐政治观与和谐社会观,这些思想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大道和同学”内容极其丰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中有着丰富的“和同”思想资源,本文所论仅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整理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