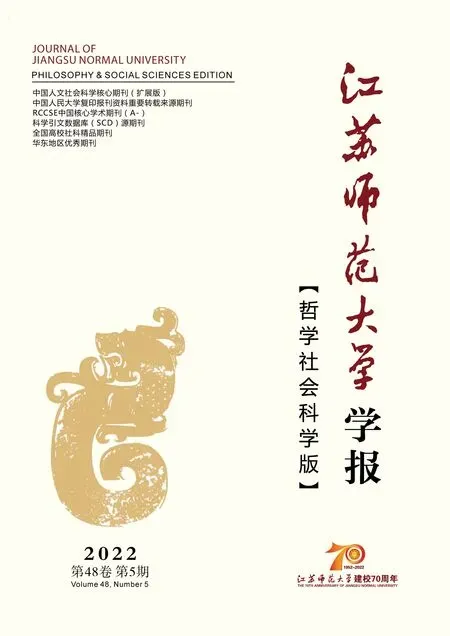艺术的祛魅
——艺术社会学的历史谱系与问题视域
周计武 李 星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8)
目前,从社会学视角对艺术与艺术史的研究已经成为艺术学中百花齐放的学术领域,“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主张,才华横溢但孤立的洞见以及类型丰富的研究,但尚未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领域”(1)Wendy Griswold, "Recent Move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3, vol.19, p.455.。换言之,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符号学等为取向的艺术研究不同,艺术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以社会学为主要取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它们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问题视域与学术路径依然是未定型的、开放的,富有争议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学科反思的视角追溯它们的历史谱系、主要观点和问题视域。社会学取向的艺术研究主要包括艺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art)与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两个分支领域。前者属于艺术理论与批评的分支学科,致力于在静态的社会结构中辨析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艺术的社会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规律;后者属于艺术史的分支学科,致力于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与社会变迁中探索艺术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不过,二者之间同大于异。两者都受到各种社会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都反对形而上学的艺术观念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单一取向,都承认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在此意义上,艺术社会史可以理解为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艺术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把二者统一称为艺术社会学。我们将首先概述艺术社会学的历史谱系;然后分析艺术研究从“内结构”到“外结构”、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社会学的范式转向;接着论述两种范式之争,即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社会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社会学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差异;继而阐释艺术社会学中的核心议题和研究策略;最后提出跨学科整合研究的思路,来协调两种范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历史谱系
(一)艺术社会学的初创期
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艺术研究者以艺术批评和鉴赏为主,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到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都擅长从形式分析的视角传达对艺术品的细腻感受(2)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艺术形式批评传统中少数的例外,其艺术设计观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作为19世纪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艺术设计要密切联系群众生活,并于1879年发表了《人民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eople)系列文章。不过,这些文章直到1942年才由凯尔文(Norman Kelvin)以《威廉·莫里斯论艺术与社会主义》(William Morris on Art and Socialism)之名编辑出版。。
德语世界的艺术研究者则醉心于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的建构,主张把艺术作为艺术史知识建构的对象。陶辛(Moriz Thausing)在1879年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的就职演讲《作为一门科学的艺术史的地位》中就立场鲜明地主张,艺术史是一种实证科学,它的目标不是审美判断,而是发掘历史事实,以图证史,从而把艺术史与美学分离开来(3)Moriz Thausing, Die Stellungder Kunstgeschichte als Wissenschaft, Wiener Kunstbriefe, 1883, p.5.。从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1764)到库格勒(Franz Kugler)的《艺术史手册》(1842)、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再到李格尔(Alois Riegl)的《风格问题》(1893)、希尔德勃兰德(Adolf Hildebrand)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1893)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中的风格发展问题》(1915),基本上都是以形式分析为基础的艺术风格史(4)需要补充的是,格罗塞(Ernst Grosse)的艺术人类学对德语世界的艺术社会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发性。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文化系统内部的“艺术”事件、行为和经验,其典型对象有雕刻在工具和器皿上的图案和装饰,有人体彩绘、面具和权杖,有洞穴壁画和盾牌、武器上的图像,这些常常被视为以图腾和巫术为导向的交流系统内部的元素。在《艺术的起源》(1894)中,格罗塞借助民族志的图文资料与实物,通过对世界各民族艺术起源的考察研究,探索了艺术起源、艺术演变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辨析了艺术的起源、性质、动因与社会功能。。
与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不同,法语世界的艺术研究者具有明显的“社会批评”倾向,致力于探索艺术与社会之间的文化逻辑。
法国的艺术批评家杜波斯(L’Abbé J.B. Dubos)在《诗画评论》(RéflexionsCritiquesurlaPoésieetlaPeinture,1719)一书中,尝试从环境、气候方面探讨墨西哥与秘鲁原住民在民族艺术的形式特征、艺术才能与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天主教哲学家与政治家波纳德(Louis de Bonald)在《从市民社会观察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的理论》(1796)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学是社会表现”(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的观点。他所倡导的“社会科学(science de société)”理论是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和孔德(Auguste Comte)社会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l)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被视为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第一次尝试(6)该书被认为是文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是“法国把文学概念和社会概念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它分析了文学与宗教、风俗、法律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较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之间的差异,并把文学的特色归因于社会状况、气候与地缘的影响。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8)中提出了“社会学(sociologique)”之名。他企图将哲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离开思辨,强调实证,形成像物理学那样的“社会物理学”。作为系统研究人类群体及其社会行为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应建立在观察、实验和分析的实证主义之上。遵循孔德的研究路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创办了《社会学年鉴》,致力于社会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强调,要回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基本问题,社会学必须从社会事实出发,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换言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观察、划分、解释并求证社会事实的准则是社会学的基本任务。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它不能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等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必须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来解释。社会学的解释主要是建立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只能通过科学的比较方法,在社会语境的具体变迁中来考察(7)[法]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1、95页。。 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1893)、《自杀论》(1897)就是从回应工业时代变革的社会事实入手,以社会结构的转变为基本框架,分析社会的秩序与失序,寻找建构、维护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
受实证主义思想的启发,丹纳(Taine)在《英国文学史》(1864-1869)和《艺术哲学》(1865-1869)中,把艺术品视为社会事实,把美学视为采用自然科学原则的精神科学,试图从艺术品的整体性出发,重构艺术诞生、发展、繁荣、变化与衰落的各种不同的时代精神,分析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对艺术家创作和艺术品风格的影响,提出了“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动因公式。这个公式是丹纳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主义出发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具体实践。虽然丹纳的学说具有生物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的简化论倾向,但它在方法论上使艺术社会学获得了明晰的轮廓,依然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在丹纳之后,他的观点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受到了质疑和修正。美学家居约(Jean-Marie Guyau)在《当代美学问题》(1884)和《从社会学视角看艺术》(1889)中,同样把艺术视为社会现象,把艺术品视为完整的有机体,主张艺术应蕴含深刻的道德性和社会性。不过,受到康德的天才观影响,居约从失范(anomie)的视角出发,主张艺术的道德不仅是自主的,而且是可变的。
(二)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期
20世纪上半叶是艺术社会学的体系化发展阶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与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共同形成了艺术社会学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
与丹纳、居约等人的实证主义研究相比,马克思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论述融入了许多社会历史元素。他直接评论艺术现象的文章不多,但他在论述价值、劳动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片段中,尤其在《政治经济学导言》《剩余价值理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与文学艺术相敌对”等相关命题,对艺术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功能、艺术的社会生产与消费、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思考,为20世纪的艺术社会学批评提供了思想的起点(8)马克思的艺术观念与方法形成于19世纪,但相关论述并未引起重视。直到20世纪,其艺术观点才逐渐引起重视,并对艺术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归入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期,而不是艺术社会学的初创期。。
与孔德、涂尔干的经验-实证主义倾向不同,韦伯倡导价值中立的理想类型(idea type)研究。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理解社会行为的科学,而社会行为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结构。理解意味着把握行为者赋予行为的意义,它涉及的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这就需要选择事实,提炼概念,把人类行为的独特性与普遍有效的命题结合起来。这种经过高度抽象出来的分析概念就是理想类型。理想类型分析旨在比较不同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根据结构一致性原则,从概念上理解社会体制及其运作情况。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提出了许多理想类型的分析概念,如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世界的祛魅、合理化、天职观、科层体制等。这些概念为后来学者分析艺术的社会变迁、艺术家的社会角色、现代艺术体制以及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武器。
沿着马克思和韦伯开辟的问题视域,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系统理解知识与社会、思想与存在的关系,分析知识结构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整体风格及其演变规律,继而揭示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社会根源。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中,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析与知识社会学结合起来,使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成了研究社会和思想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系统的怀疑论,它质疑一切公开宣称的主义,转而强调思想与行为模式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之下,艺术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开始了体系化的系统探索。这种探索主要表现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以普列汉诺夫、卢卡奇(Georg Lukács)、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二是以安塔尔(Fredrick Antal)、豪泽尔(Arnold Hauser)、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等人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史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传承了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批判精神,但它批判资本主义的焦点开始从政治经济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文化,旨在通过艺术批评与审美实践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修正与发展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是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心。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在《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7)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镜子,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表现。因此,艺术研究应从生物学转向社会学,从时代特点、社会经济和阶级矛盾等社会因素入手,分析艺术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当然,艺术的社会生产并非直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的中间环节。社会结构至少包含五个层次:生产力的状况;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9)[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5页。。五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的矛盾和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艺术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生产力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二者之间存在着三层环节:社会心理、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社会心理决定的;社会心理是由政治制度的境况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尽管这是一个略显粗糙的理论框架,但毕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命题。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小说理论》(1914-1915)、《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现实主义问题》(1954)等。《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是以总体性(totality)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合理的机械化计算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成可计算的物与物的关系。“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10)[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一方面,劳动的过程分化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使工作成为机械的重复;另一方面,工人也被机械化地组织到机械体系中,分裂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了克服物化的命运,卢卡奇坚信,现实主义是最能通达总体性的艺术原则,因为它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把典型人物的刻画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为观者提供一幅关于现实的完整画面。相反,以表现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失去了总体性,文学与艺术中的“人从根本上就是孤独的、反社会的,无法与其他人建立联系。”(11)Georg Lukács, "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eds., 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144-145.因此,他批判现代主义是一种颓废的艺术。这种观点忽视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力量与实验精神,遭到了布莱希特和阿多诺等人的批评。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本雅明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主张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艺术的社会生产情况。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中,本雅明从“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出发,呼吁“进步的”艺术家如工人一样,介入艺术生产的种种手段,改变传统媒介的“技术”,转变资产阶级文化的“装备”,争夺文化的“领导权”。尽管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失去了原作的“光韵”,即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但“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置入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地方”,使艺术的膜拜价值全面让位于展示价值,彻底“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反应”,有助于实现艺术的民主化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潜能(12)[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5、254页。。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相比,艺术社会史是在知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的共同影响下孕育、发展的。与古典艺术史相比,它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主张,反对把艺术史简化成艺术形式发展的风格史,主张把艺术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艺术形式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根据艺术史观念倾向上的不同,艺术社会史大致形成了两条研究路线: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宏观艺术社会史研究;一是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的微观艺术社会史研究。
宏观艺术社会史研究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经典概念、范畴或命题,试图把艺术品分析与艺术家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理解并阐释艺术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它涉及那些活跃在20世纪中叶的中欧艺术史家,如安塔尔、豪泽尔、沃克内格尔(Martin Wackernagel)和克林根德等。
安塔尔和豪泽尔经常参加以卢卡奇为首,以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电影批评家巴拉兹(Béla Balázs)为核心的左翼阵营“星期天社团(Sunday circle)”。20世纪30年代,曼海姆、安塔尔和豪泽尔流亡英国,使英国艺术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赢得了艺术史家克林根德和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追随(13)[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至于瑞士巴塞尔大学艺术史家沃克内格尔,他和安塔尔虽然是沃尔夫林的弟子,但都不满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把艺术史演变的价值降低到几对基本范畴。其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世界》(1938)一书中,主张佛罗伦萨艺术是市民社会要求的反映,是统治阶级合作与宽容的产物。前者为艺术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后者鼓励了艺术创新。这和安塔尔在《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1948)中的观点惊人相似。他认为,佛罗伦萨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市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表达或反映。乔托(Giotto)和马萨乔(Masaccio)的风格是理性的,源于佛罗伦萨上层中产阶级的视觉要求;那些哥特式风格则是情感的、感伤的、戏剧化的,源于北欧的小资产阶级;而所有14世纪的艺术风格都徘徊于这两级之间,比如,湿壁画就是当时视觉形式的竞技场,它把不同阶级的审美趣味和风格表现的方式融合起来。显然,安塔尔是把艺术当作阶级结构的反映来研究的。这种社会反映论影响了跟随者克林根德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艺术》(1943)和《艺术与工业革命》(1947)中的批评立场。不过,由于形式分析的艺术史方法依然占据主导,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艺术社会史研究成果并未引起欧美艺术史界足够的重视。
豪泽尔是这个时期推动艺术社会学发展的核心人物。他的《艺术的社会史》(1951)由于受到贡布里希在《艺术通报》(1953)中的批评,引起了艺术史学界广泛的争鸣。在书中,豪泽尔把艺术与种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冲突的关系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辨析了艺术风格、世界观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反映”关系。比如,他在书中讨论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阶级斗争”“作为中产阶级运动的浪漫主义”,以及“电影时代”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系。他把理性、秩序、明晰的古典主义风格视为贵族阶级保守趣味的表达,把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视为积极向上的中产阶级的视觉冲动,而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对立视为不同风格相互并存的原因。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氛围中,这种过于简化的阶级“反映”论倾向,招致了贡布里希猛烈的批评。他认为,豪泽尔往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假设出发,罔顾事实,使其在艺术史叙事上理论粗陋、逻辑混乱、材料武断、阐释空洞,很少提及具体的艺术品,也没有“努力寻找文本与历史文献之间生动的联系”,更没有具体分析“艺术家接受委托、进行创作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14)[英]贡布里希:《艺术社会史》,《木马沉思录——艺术理论文集》,曾四凯等译、杨思梁校,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7页。。豪泽尔坦诚接受了这些批评,在《艺术史的哲学》(1958)、《样式主义:文艺复兴的危机与现代艺术的起源》(1964)和《艺术社会学》(1974)三本书中对其方法论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和修正,系统建构了艺术社会史的方法论体系。
与宏观艺术社会史相比,微观艺术社会史更倾向于以经验主义的态度,从艺术家、艺术赞助人、艺术市场、图像的意义等角度,对具体艺术案例进行细腻地图像学分析(iconological analysis)。图像学分析是瓦尔堡(Aby Warburg)提出、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发展成熟的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
受到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的启发,瓦尔堡把艺术史纳入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史传统之中加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整体性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驱逐各学科的“边界警察”,开拓艺术史作为文化史的问题域。图像与文化是通过隐秘的精神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象征散布在文本边缘、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附属的运动形式”(accessory forms in motion)之中,如女神的衣饰和褶纹、维纳斯随风而动的秀发等。“捕捉这些运动中的生命形象” 乃是吸引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关注古典艺术传统的深层动因(15)[德]Aby Warburg,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Britt,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p.141.。正是对符号历史和古典传统的兴趣,使艺术史家萨克斯尔(Fritz Saxl)、温德(Edgar Wind)、潘诺夫斯基和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学者聚结在一起,形成了瓦尔堡学派。
如果说瓦尔堡是奠基者,潘诺夫斯基则是集大成者。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1939)中首次将文本阐释的方式运用于图像的阐释,把图像学方法与具体例证结合起来;并在《视觉艺术的意义》(1955)中区别图像志与图像学的概念,提出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图像学阐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和阐释的矫正原则(corrective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三个层次说,使图像学成为以分析内容为基础,完整阐释视觉艺术品的严密体系。他把图像的寓意、主题与象征符号视为人类心灵史的象征,从而使图像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等人文主义学科融合起来。
从广义上来说,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和法国艺术史家弗朗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的研究也属于这种微观艺术社会史的研究传统。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1919)之中,以凡·艾克兄弟的绘画为例,通过对写实、象征和拟人化三种艺术手法的研究,把艺术特征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描述“时代的肖像”。他认为,15世纪的“艺术和文学仍属于中世纪的思想体系,正处在即将终结的完美阶段。”(16)[荷]Johan Huizinga, The Autumn of Middle Ages, Trans.,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300.弗朗卡斯特尔早期代表作《凡尔赛的雕塑:论法国古典品味的诞生与演变》(1930),从古典雕塑的风格入手,理解艺术品的造型语言和社会结构的象征系统,试图通过古典品味的演变来把握特定社会的精神史。
(三)艺术社会学的成熟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是艺术社会学的当代发展阶段,也是其作为一个分支学科逐渐成熟的阶段。这是多学科、多视角探讨艺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论的时期,也是各种精彩的案例分析与微观研究成果频现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艺术学理论界出现了社会学与美学的融合倾向。面对过去的经验主义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社会学开始向两方面发展。其一开始关注艺术作品内部的审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艺术学理论与社会学结合时的有效性,试图将美学纳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二则以微观视角展开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在“艺术界”及其上下文的视域中讨论机制、组织、程序等一系列理论建构,力图系统地理解微观中的“艺术”如何与其宏观背景中的社会互动。
在艺术社会学领域中,对艺术作品内在意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词语与图像之间关系的辨析,这不仅是他后来开启机械复制与“光韵”研究的起点,更是他在文化批判中比较视觉经验模式与语言经验模式的线索。在《德国悲剧的起源》(TheOriginofGermanTragicDrama)中,他通过研究巴洛克式的悲剧策略,在其“寓言”的形式中找到了“词语与图像之间必然的不可补偿的不完全联系”(17)[英]保罗·史密斯、卡罗琳·瓦尔德:《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页。。而这种“不完全联系”正是当代都市艺术王国中表象与含义分裂的最佳注脚(18)比较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与《单向街》两本著作,凯吉尔发现其中有一条问题线索,即巴洛克的寓言式戏剧延伸到其当代都市中,便发生了“近代早期表象与含义之间的分裂”。这样看,自《德国悲剧的起源》中讨论的语言-图像问题,在《单向街》中便演变成了表象与含义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本雅明开始将视觉文化领域纳入到文化批判中来,最终使语言-图像的关系问题,在他的“拱廊计划”中,以一种“废除词语的纯视觉语言”结束。。沿着词语-图像的关系问题,以及表象与含义的分裂问题,本雅明最终在李格尔围绕“艺术意志”的文化史写作中找到了理解艺术作品表达形式的关键逻辑:“将艺术作品视为它那个时代宗教、形而上学、政治与经济倾向的一种整体性表达,不受任何地域概念的限制”(19)陈平:《本雅明与李格尔——艺术作品与知觉方式的历史变迁》,《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这一逻辑延续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写作时,便实现了从语言经验模式到“图画写作”(picture writing)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审美政治化”(20)[英]保罗·史密斯、卡罗琳·瓦尔德编:《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这一概念,把社会关系纳入到视觉生产及复制技术的宏观文化语境中。
本雅明的理论涉及艺术作品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意义,这些成果在其后继者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那里演化出了新的研究转向。与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不同,洛文塔尔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把批判理论的思辨精神与英美的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雅俗艺术同时展开研究,继而在对“雅”与“俗”的不同阐释中找到其背后社会语境的差异,并最终以文学艺术展开对社会的阐释。如果说本雅明的“文化批评”“灵韵”等概念侧重将艺术作品的解读与知觉方式相结合,那么洛文塔尔则以具体的社会系统为视角,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本雅明在现代艺术中发现“图画写作”的新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新的视觉经验模式,它将语言经验的模式纳入其中。而洛文塔尔对作品的关注点,则从对文学形式的知觉心理学分析,向内容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过渡。在这种对文本内容展开的功能分析中,其历史情境、社会系统、作家与读者的身份等因素,都需要再次经过社会学的检测。具体而言,“文学社会学家在传播研究领域的本职工作在于阐明‘阅读’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对作品完成了历史学、传纪学以及文本分析等方面工作之后,他不能简单地把责任都推给他的经验主义学者同行。”(21)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p.153.因为“相关的社会因素也必须经过社会学的审视。”(22)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p.154.
在艺术社会学成熟期的开端,除了本雅明、洛文塔尔这种有意识地关注审美内在逻辑的研究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其背后的学科转换趋势。薇拉·佐尔伯格(Vera Zolberg)曾分析过二战前后学院对学科发展的不同侧重,她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私立文科院校挂钩的人文学,特别是古典学,名声斐然,到战争期间及结束之后,就理论成就的高下而言,科学获得了更高的声望。”(23)[美]维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原百玲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这意味着,从科学学科而来的中立价值观,在20世纪中叶成为学科领域中的主流,其定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使人们逐渐怀疑定性的或人文主题的方法(24)[美]维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原百玲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但这种学科方法论上的转变也同样面临质疑,科学实证作为替代人文研究的一条理论路径,究竟是否有效也使人反思。如洛文塔尔 “拒绝那种放弃了道德职责的‘科学价值中立’观念”,因为“在公众生活和科学事业领域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愤怒。”(25)Martin Jay, ed.,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165.这种方法论上非此即彼的思路,伴随艺术社会学的发展逐渐显露其局限性。正如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r Harris)在梳理新艺术史时所提出的那样,70年代后的艺术社会学批判中,迸发出了诸多新的议题:性别、族裔、身份、地域、机制、体制等等都被纳入研究视域。此时再难以“客观”和“科学”的价值标准去衡量研究方法的有效性(26)[英]乔纳森·哈里斯:《新艺术史批评导论》,徐建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实际上,在艺术史传统与艺术社会学新方法融合的节点上,与洛文塔尔同时期的皮埃尔·弗朗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比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更早地提到了艺术的体制特征。他在分析当代艺术的过程当中,发现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学论争的中心,与其背后一系列的美学家、设计师、工匠、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工业美学运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正是由艺术领域中不同身份的人的运作,使得当代艺术逐渐获得艺术史上的合法性。他这样总结道:“艺术是知识关系相互重叠的网络,需要创作者和公众的积极参与。”(27)Pierre Francastel, Art and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 Randall Cherr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p.285.这种将艺术视为一种集体活动及其结果的思路,在贝克尔那里得到了延续,也成为艺术社会学从学理上的成熟走向多元化发展的开始。贝克尔提出“艺术界(Art Worlds)”的概念,用以指代从生产到分配的整个艺术活动。在这里,艺术家不再拥有传统艺术史中的权威,而仅是一种拥有才能的人。将“艺术家的天才”这一观念本身解构为一种社会建构,贝克尔的这种思路影响了艺术社会学学者对文化生产的重新认识。其中,彼得森(Peterson)与赫斯奇(Hirsch)都开始更细致地分析艺术界中从事生产的运作机制及体系,后者更是将组织社会学的方法引入艺术社会学(28)[美]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戴安娜·克兰(Crane)也曾就艺术界的报酬体系展开分析,并且通过区分艺术到达公众的路径,可以划分文化产业、非营利组织及地区性网络(29)[美]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2020年,亚历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的《艺术社会学(第二版)》出版,其第四部分的总结中仍保留了第一版中这样一段比喻,“我回顾艺术社会学的目标是想在马赛克中铺上最好的瓷砖……我希望这能创造一幅有用的艺术社会学画卷,并希望使人感受到审美的愉悦和社会学的美。”(30)[美]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由此可见,艺术社会学的成熟期仍在继续,它正在反思、整合其研究范式中两种倾向,并在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下,从其范式之争中探索其核心议题的新解。
二、范式转向
作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在从传统艺术史到艺术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被解读为不同的意义载体,更多地,它在两套研究范式之间不断提出新问题。当“艺术”以复数形式“the arts”出现在艺术社会学中时,它已经籍此多样性将传统艺术史中的“fine arts”范围扩大,突破了那种尊崇意义上的艺术定义。要回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非艺术”。这意味着在艺术社会学的逻辑中,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仅从内部已无法解决艺术的基本范畴问题,而必须将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情境纳入到研究视野。在这种思路下,具有一定自主性内在结构的艺术史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还需要将其置于与外部社会、历史等情境的关系结构中去分析、阐释、反思。伴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过去基于艺术本体论宏观思辨的艺术哲学,也逐渐转向微观具象的文化社会学辩证。
(一)从“内结构”到“外结构”
艺术史书写的开端奠定了其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范式。在普莱齐奥西(Donald Preziosi)的《艺术史的艺术》中,他曾总结道:“后来的艺术史家普遍公认的学科知识的两位奠基者——在阿雷佐出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艺术家-历史学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和身为普鲁士古物学家-美学家的罗马市民约翰·乔基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他们的写作动机是要解决他们时代的困惑,这种困惑产生于那个时代对前述的‘艺术’作品的假设进行研究。”(31)[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支,其知识生产奠基者拥有着独特的身份及经历。而二者不同的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又为艺术史这一学科后来的发展路径铺垫了方向。具有艺术创作经历的瓦萨里,同时兼有历史学的学养,当他观察思考艺术的历史时,艺术的“时代性”是不容忽视的命题。在这层意义上看,温克尔曼延续了瓦萨里对艺术史的思考,但他引入了其自身古物学家看待历史的眼光。当瓦萨里认为“当下就标志着以前成就的顶峰”(32)[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时,温克尔曼则将艺术的辉煌时代定位至他想象中“真正的古代”(33)[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如果仅考虑瓦萨里和温克尔曼在艺术史写作中凝聚的历史观及反思的话,我们也可以提炼出他们对艺术作品历史性的重视。但以历史发展坐标为基础的艺术史观,实际上融合了古典学、语文学、美学、艺术批评等理论实践基础,并以此塑造了艺术史这一学科内部的理论结构。
16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学院中出现了专为艺术家开设的讨论场所,其中较早的就是由瓦萨里和托斯卡纳大公科斯莫一世(the Grand Duck of Tuscany, Cosimo 1)共同建立的设计学院(Accademia del Disegno)。该学院曾致力于以艺术的概念“disegno”来组织艺术家,并且“disegno”一词来自拉丁文de+signum,意为“借助符号表达”,传达出一种将艺术与语言等而视之的意味(34)[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这一方面将有助于通过培训艺术家对艺术的认识来激发其创造力,另一方面将促进艺术学及艺术史在人文学科中的定位。也就是说,瓦萨里的学院通过“disegno”的概念,将艺术研究的内容锚定在艺术独有的形式范畴上,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艺术史的书写。正是由于同样进行艺术创作,瓦萨里书写艺术史时能够看到艺术创作中的延续性。佛罗伦萨的普通艺术家和古代艺术家并非因由时代不同而不能分享技艺。实际上,他们都要解决自然的再现与模仿问题,只是他们创作的艺术由于分列历史发展线上的不同位置,而在艺术成就上有所不同。“艺术是怎样类似于我们身体所显示的自然律;它们都有出生、成长、成熟和死亡的进程”(35)[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艺术的历史不是受制于外界环境被动制约的历史,而是具有自身独立性,同时又自觉地与历史规则——瓦萨里基于自然律的历史观相统一。
相较于瓦萨里,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中纳入了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观。如果说瓦萨里的艺术史基础是“先例的历史(history of precedents)”(36)[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那么温克尔曼则将先例抽象为样式,更有针对性地处理艺术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部独特性。在这种艺术史观中,温克尔曼可以重新划分并阐释艺术史的经典,更重要的,他可以脱离其时代去定义艺术史。换句话说,瓦萨里的艺术史书写尚且是他“先例的历史”中延续的传统,而温克尔曼则以样式的连续切断先例的连续,传统可以重新排列,艺术史的经典可以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阐释。而这也反过来使艺术史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具备了自身学理上的独立性,并且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艺术自身的样式发展上。惠尼特·戴维斯曾这样总结过温克尔曼的代表作《艺术史》:“一开始就综合了后来成为专业化艺术史学科的两种方法——即‘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37)[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如果说这两种方法是传统艺术史写作的“内结构”叙事基础,那么温克尔曼的确如普莱齐奥西所言是瓦萨里“创建的艺术史(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个别的研究)的新副本”(38)[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也恰恰是19世纪开启的艺术社会学所面对的研究范式。
纳塔莉·海因里希(Nathalie Heinich)在《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中谈到19世纪建立在“独特性(régime de singularité)”基础上的现代艺术价值体系。她提到“使命感、天赋、启示、牺牲、无私、灵感、超脱”(39)[法]纳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这些品质作为艺术创作推崇的价值观,与强调“社会的、广义的、集体的、无个性的与公共性”(40)[法]纳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的“共同性(régime de communauté)”截然相反。而这种价值体系上的对立正对应了传统艺术史与艺术社会学两种研究范式中暗含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在传统艺术史的“内结构”叙事中,温克尔曼建立起了具有独立性的学科研究基础:样式。这种样式实际上与19世纪出现的艺术价值体系不能完全相容。因为样式作为艺术史发展规律的一种逻辑,并不强调其作者的精神品质。以艺术家之名来定义艺术价值,其实与海因里希指出的19世纪艺术世界中一对概念的流行有关。正是由于有社会学对“共同性”的讨论,才有艺术界对“独特性”的推崇。而这种理论争鸣恰恰验证了艺术史写作的转向,即一种社会学语境论逻辑下的“外结构”叙事开始了。
艺术社会学在艺术史中开展的“外结构”叙事实践是艺术社会史。简·透纳(Jane Turner)在《艺术词典》中曾简明指出:艺术社会史“与艺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Art)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艺术社会学主要关注作为理解社会的一种手段的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史的主要目的确实对艺术本身的深入理解。”(41)Jane Turner,ed.,The Dictionary of Art,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1996,p.915,pp.914-915.这样看,艺术社会史的基本立场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息息相关。艺术社会学的“外结构”叙事将文化生产、分配、消费等各项环节中的社会因素都纳入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中,使得艺术社会史家们在思考艺术本身之前,会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关切作为实践的整个艺术活动。即使研究艺术品,其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艺术品的形式属性与审美风格,而是从功能论出发“在产生和决定作品的语境中观看作品”,“通过重构那些参与其中的条件和论断,也许能牵引出从前不被人注意的某些作品构造的具体特征”(42)[德]汉斯·贝尔廷:《语境中的作品》,《艺术史导论》,汉斯·贝尔廷、海因里希·迪利、沃尔夫冈·肯普、威利巴尔德·绍尔兰德、马丁·瓦恩克等著,贺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页。。因此,当社会学照进传统人文学科时,文化生产的社会学和文本社会学作为互相补充的两种分析,为艺术史、文学批评和美学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改进方法。同时,艺术社会学的“外结构”叙事作为传统艺术史学科“内结构”叙事的后继者,它不仅意味着一种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向,其背后还有不同学科领域中核心议题的重心迁移。它不再以艺术品为中心,而是聚焦艺术活动或艺术实践,考察“语境中的作品”以及作品在社会的生产、流通与传播中的机制。
(二)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社会学
在艺术史叙事从“内结构”到“外结构”转化的同时,人文学院中关于艺术的讨论及研究也发生了研究范式上的转向。自瓦萨里的设计学院开始,到1768年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立,专门的艺术学院逐渐向人文学院建立的理论话语体系看齐,其开展的一系列艺术实践活动也逐渐具有明显的理论特征。1764年,温克尔曼出版了《古代艺术史》,稍早于莱辛(Lessing)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在二人所处的学界及艺术界中,虽然比较诗画早已有之,但人文学科领域里的美学家的关注往往在诗画是否分离的问题上。当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说出“ut pictura po⊇sis(诗如画)”时,他的上下文旨在讨论人们对绘画与诗歌相似的多样感应(43)[波兰]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而当诗画分离问题延续到莱辛这里时,媒介问题超越再现问题就成为诗画问题的焦点。诗歌作为在时间中展开的叙事虚构,与造型艺术在空间中展示的瞬间场景有着媒介本质上的不同。虽然莱辛并不意在通过这种比较抬高造型艺术的美学价值,但他在侧面点明了当时造型艺术应当(或许也正在)摆脱对叙事文本的依赖。
在美学文本中受到温克尔曼启发的除了莱辛,还有黑格尔。迈克尔·波德罗(Michael Podro)在梳理艺术史写作方向的变化节点时,曾将黑格尔置于艺术史批判式写作的分水岭上。因为黑格尔所代表的19世纪美学界,是以康德(Kant)、席勒(Schiller)、赫尔巴特(Herbart)为线索的,他对温克尔曼艺术史观的改造,是后来艺术史学界讨论绕不开的基本命题。并且,黑格尔的艺术史美学叙事思路,引起了与以鲁莫尔(Rumohr)为代表的历史学界的理论争鸣。这意味着,在黑格尔之前,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已然存在两种方向;在黑格尔之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逐渐有了一条美学主线。波德罗这样总结道:“1827年似乎是个恰当的起点……那一年,黑格尔植入其框架式艺术史中的那种美学,招致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鲁莫尔的强烈反对。这次对峙,为后来的论争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和出发点。”(44)[美]迈克尔·波伦:《批评的艺术史家》,杨振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页。
这样看,传统艺术史并非在人文学科中单打独斗。从其奠基者瓦萨里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他有意识地将艺术与语文学相融合。这种意识到了温克尔曼时就与文学史这门学科相融合。温克尔曼之后,人文学科中的美学、历史学、文学等都有学者关注温克尔曼提出的艺术史观。黑格尔曾为艺术史划分了三个阶段:象征型阶段、古典阶段、浪漫主义阶段。三个阶段之间艺术形式上的转变,其根由是在时间线上承续发展的“理念”(45)[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黑格尔论述道:“因为理念只有凭自己的活动来独立发展时,它才是真正的理念;而且理念作为理想既然是直接的显现,也就是与它的显现同一的美的理念,所以在理念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特殊阶段上,就有一种不同的实在的表现方式和该阶段的内在定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启发,里格尔将触觉性艺术与视觉性艺术进行了时间上的排序,而沃尔夫林则在艺术史中抽离出了从线条型到涂绘型的形式转变。这种历史研究范式在艺术史学科中的地位正如米奈所说:“黑格尔、里格尔以及沃尔夫林制定了风格发展的系统,从而为艺术史这门学科确立了法则、创造了方法论。”(46)[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统观艺术史研究范式从温克尔曼到黑格尔,再到沃尔夫林的过程,可以发现当艺术史处于“内结构”叙事时,它与其他人文学科一道处于时代独特的理论环境中,这些不同学院的理论又总在构建一套在艺术世界中通用的“话语”体系。
如果考察莱辛所处的18世纪艺术学界,可以发现其对绘画的评判标准,仍然通过诗歌等书面文本对照人文学界。在艺术学院建成之前,艺术生产都聚集在专门的行会中展开。也就是说,艺术学院成立之初,面对的是艺术类手工业行会与人文学科的学院。因此,当学院的艺术理论选择这种依附于人文学科的内结构叙事时,其理论“话语”体系具有对排他性的追求。从区别于行会的优越性理论论调开始,学院有计划地使用艺术理论区别于行会中那种对艺术实践活动的章程化、学徒式教学。保罗·杜罗(Paul Duro)在分析这一时期学院中的艺术及艺术史理论知识生产时曾说:“这些学院几乎全部都在选择性地模仿自然和参考古代原型这一模式基础上,并根据脱离艺术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导的重要性,整理出了一种用法说明书”(47)[英]保罗·史密斯、卡罗琳·瓦尔德编:《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基于这种理论排他性,当莱辛美学提出视觉有相对于文字的独特性及不可化约性时,现代艺术批评中对视觉意识、生产制作、接受等问题的讨论就已蕴含其中。
乔纳森·哈里斯曾将艺术史比作“一种机器去‘打造’学生,以便‘生产’所谓具有某种技术、知识和思维方法的专家式研究生。”(48)[英]乔纳森·哈里斯:《新艺术史批评导论》,徐建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而学院中艺术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与20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及其理论反思相关。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理论学界已经把目光转向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其中,“阶级和性别政治,伴随着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早期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本质的质疑充当了艺术史激进发展的原动力。”(49)[英]乔纳森·哈里斯:《新艺术史批评导论》,徐建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这意味着,传统艺术史的研究范式在艺术学院中已不再占据主流话语权,其背后那种以规律统观历史的逻辑,以美学考察并阐释艺术品形式的价值的研究范式亦亟待革新。
如前所述,陶辛曾在19世纪末所作的《作为一门科学的艺术史的地位》中提出,要将艺术史作为一门实证主义的科学看待。这意味着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开始渗入艺术史研究中。从最开始仅仅指涉某些门类艺术的社会学,到打破艺术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单一分析,当“艺术社会学”这一亚学科作为论题出现在艺术学院中时,艺术史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之间就包蕴着一种理论张力。从讨论艺术本质问题的宏观式艺术哲学思辨,到聚焦具体艺术实践的微观式文化社会学辩证,学院中的艺术理论从如何定义艺术开始,就面临着从其内部或外部展开的问题。这样看,伴随艺术社会学在学院中的发展,它一直面临着两种研究范式的争鸣:一种是艺术史的人文学科式研究,一种是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
三、范式之争
在艺术社会史的范式转向中,仍有一个基础议题亟待解决。作为艺术社会史的理论基础,围绕艺术社会学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的议题,研究者们展开了对两种理论范式的辩护与讨论。在讨论这两种范式之争时,需要注意的历史节点分别是19世纪艺术社会学的开端(对应人文学科时期的范式讨论),及艺术社会学的成熟期(对应社会科学时期的范式讨论)。早期所谓人文学科时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内部还有两种理论范式的争辩。伴随20世纪中后叶艺术社会学微观视角的转向,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逐渐挤占人文学科的理论有效性,成为艺术社会学成熟前的主导性力量。但实证主义又为艺术社会学带来新的质疑,两种范式之争最终仍指向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融合。
(一)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作为与艺术社会史相伴产生的亚学科,当在艺术史领域理解它时,它天然地在艺术史的上级学科——人文学科(humanities)那里取得理论有效性。而humanities一词的来源是拉丁文humanitas,而该词又来自更古老的希腊概念。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演讲术是其公民行使公共权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钥匙,也是其全面教育的集中体现。希腊的教育作为名词时为paideia,其词根是pais或paides,意为男孩或儿童。随后在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逐渐完成系统化发展。具体而言有四个特点:1.以7门文科学科为基础系统记述人类的知识;2.在纸质媒介缺失的情况下,展开论辩的技巧;3.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塑造人的个性及发展;4.肯定并向着人的优越性发展(50)[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经过帝国的征服与吞并,希腊的paideia有了更具体的形制,罗马人有目的地着重训练“提出论点或者批驳论点的思维能力,这就需要在文科学科中受到全面的教育。”(51)[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希腊时期称这种全面教育为enkyklia paideia(亦为英文Encyclopaedia的词源),在西塞罗那里则转译为humanitas,意指“发扬哪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5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在希腊教育paideia出现伊始就已经成为其主要内容。从一定层面上看,paideia中对“人”的肯定与humanities对人的训练相辅相成,这种教育方式值得保存至今。实际上,在现代西方大学中,以牛津大学为例,其开设的“大课程(literae humaniores)”仍以“希腊和拉丁原文学习古代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思想”(53)[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这样看,人文学科与古代教育的渊源颇深,那么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概念来源何处?虽然希腊罗马的传统一直延续至19世纪的西方教育,但是“人文主义”一词却并没有在古代世界,甚至文艺复兴时期,都没有出现。直至1808年的德国教育家F. J. 尼哈麦(Niehammer)在讨论教育中古代经典的地位时,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来指代人文主义(54)[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此前人们往往用humanist来称呼古典语言及文学教师。这些教师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教授的科目为studia humanitatis,即英文中的the humanities,涵盖一套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55)[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自1860年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围绕人文主义一词的争论也随之而来。讨论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地肯定或否定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断裂。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信条看似与经院哲学论题中的“以上帝为中心”相抵牾,但其背后还有方法论上的较量。正如彼特拉克所指责的那样,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总是对“人的本性,我们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走向哪里去”(56)[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页。不加理会。而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人是“一种有理性的灵魂,他分享了上帝的智慧,但是,要靠肉体来行动”(57)[美]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前者将“人”排除在对形而上学绝对性的追求外,后者则在认识到人的局限性基础上讨论理性。
中世纪的学者们同样研习人文学科,在他们的七种自由艺术中(58)[波兰]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七种自由艺术是:逻辑、修辞学、文法、算数、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如果依照我们的了解,它们都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有两类(修辞学与文法)同古代的人文学科知识相通。但不同于人文主义者,中世纪提及的humanities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客观性及工具性的知识。因此,在理解人文主义时还需要认清其背后与中世纪不同的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当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在考古中发现古人的世界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套独立存在的文明,而非可以被任意筛选的片段。人文主义者与经院中的学者描绘的是两种古代世界,其背后是两套处理历史意义及其线索的逻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彼特拉克1337年在罗马废墟遗址的慨叹。经过这次游历,他创制了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以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所代表的辉煌时代与基督教罗马的黑暗时代之间的对比,来代替异教徒时代的黑暗与基督降生后所开始的基督教时代之间的传统对比。”(59)[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可以说,humanities在中世纪并没有销声匿迹,但正是经过人文主义对古代世界(特别是古物、遗址、文献等)的反思,人文学科才能再纳入关于人切身经验的新内容。因此,当潘诺夫斯基重申“艺术史家也就成了人文主义学者”(60)[美]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时,他正是在人文主义者的这种知识语境下提出的。
将艺术史家称为人文主义学者,是将艺术史称为人文学科的另一种表述。在此基础上,作为艺术史亚学科之一的艺术社会史也具有人文学科的性质。那么,艺术社会史的理论基础,艺术社会学是否能被称为一种人文学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人文主义。我们知道,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既要处理中世纪遗留的经院式知识生产方式,又要在考古发现的“原始资料”中构建古典世界中的人文学科式知识生产。但反过来看,如果将艺术史看作人文主义的一个学科,则是在一种反思的语境下重新看待艺术史与humanities的关系。潘诺夫斯基这样总结道:“人文主义者研究历史记载时,要应用各种文献,而这些文献本身就是在一个他要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61)[美]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也就是说,在研究开展伊始,艺术史所处理的“原始资料”就不能局限在某一学科门类内。比如研究祭坛屏风,其他的间接资料都非常重要,书信、编年史、传记、日记、诗歌等都可以称为某一观点的佐证。
实际上,潘诺夫斯基这种对待艺术史与其他人文学科的方式,与艺术社会学初创期的丹纳有相似之处。如前所述,丹纳把艺术品视为社会事实,以“种族、环境、时代”的整体性来阐释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对艺术家创作和艺术品风格的影响。受实证主义思想的启发,丹纳将美学视为采用自然科学原则的精神科学,这种理论视野无疑将人文学科的复数形式纳入艺术社会学。换句话说,艺术社会学在创建理论之初就既要处理人文学科内部诸如艺术史、美学的问题,又带有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从艺术史那里分享的人文学科属性,在艺术社会学理论内部,始终作为理论的基本挑战存在。由于这种来自理论内部的冲突,艺术社会学在随后的发展中更关注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就像佐尔伯格(Vera Zolberg)所说:“为了填补理解的漏洞,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外部视角是极有意义的。”(62)[美]维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原百玲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二)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社会学
回顾艺术社会学的初创期,其论及的“社会学”是以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为落脚点的。如果仅仅按字面意义理解human science,人文科学的内容则限定在人的科学(63)还应注意的是,“科学(science)”一词在学界往往指代自然科学,它在语法上更像一个词根,反映在学界则更像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及方法。也就是李醒民所说的“在英语中,science在不加修饰词时,只指称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它并不把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包括在内。”——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内,与humanities的研究内容有重叠。实际运用中,human science与humanities在学界的用法并不完全区分,但学者们往往将前者视为学科,后者视为学科群(64)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前者是“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人文主义方法的学科”(65)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后者是“研究人本身或与个体精神直接相关的信仰、情感、心态、理想、道德、审美、意义、价值等的各门学科的总称。”(66)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这样看,human science更强调人文主义的属性,humanities更直接关照人本身及精神,二者在研究“人”的层面上是互通的。而从“人”的层面上宽泛地说,“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67)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p.191.。为社会学(sociologique)命名的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8)中也曾有这样一段话解释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的关系:“科学应当或以自己的方法,或以自己在各方面的成果,决定社会理论的重新组织。将来,一旦系统化后,科学就将与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共存,永远称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68)[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在这种关照“人”的理论视角下,human science与humanities并不对立。也正因为此,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够突破其19世纪早期发展的不稳定,继而像孔德所言,“作为一门科学出现是可能的”(69)[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1830年,孔德在其知识发展的“三阶段法则”(70)“在早期阶段,解释事物的依据是宗教信仰或某种神圣和超自然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形而上学阶段,逻辑、数学和其他形式的理性体系主导了对事件的解释。进一步的发展是,从形而上学的形式理性中产生了‘实证主义’或者说科学,在这一阶段中,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产生规范的陈述。孔德认为,世界上任何领域的知识积累——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都依次经历上述三阶段。”——[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基础上提出社会学最终将进入实证主义的阶段,并就此号召“运用科学来发展有关人类事物的知识”(71)[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但社会科学是否能被称作科学,社会学家们仍各执一词。实际上,当社会学面对作为自然科学的科学,与人文主义学科群时,它必然地需要在分析社会现象及事件时不断转换视角,继而产生多元的知识活动。在这种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为社会学划分出两种理论派别,其一是“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其二是“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前者往往使用一种整体观来理解历史及社会,极具批判性;后者则更多使用实证主义传统,且“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72)[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前者以19世纪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代表,后者则以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经验社会学为主。其中,将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分析它们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影响了一批艺术社会学家,特别在经过20世纪中后叶微观视角的批判发展,艺术学与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与量化方法结合得愈发紧密。
艺术社会学的成熟期,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上下文中,一些艺术社会学家开启了微观转向的理论尝试,他们反思自马克思、卢卡奇,乃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艺术批判文本。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影响力较大,他代表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批判接受路径。他的资本、习性和场等概念已经不同于马克思,而是将视角聚焦到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具体关系。对于布尔迪厄所提供的艺术社会学新问题,詹妮特·沃尔夫(Janet Wolff)、伊安·海伍德(Ian Heywood)、佐尔伯格等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艺术社会学自带的理论张力,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遗产。此外,T. J. 克拉克(Timothy James Clark)则提供了另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方案。通过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意识形态、阶级等),克拉克以一种关注具体艺术因素的艺术社会学展开书写。艺术家、作品、观众的个体性和独特性不直接以形式或概念体现,而是在艺术生产及消费的过程和环境中实现。代表艺术社会学微观转向的克拉克,在其理论实践中不仅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他探索了一种以微观视角管窥宏观图景的可能性,即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尝试。
以布尔迪厄和克拉克为代表,可以看出,这些艺术社会学家通过将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家、现象置于其社会历史语境中,继而重新理解形式、内容、风格等关于作品内在审美价值的阐释方式。他们的意图不在于解构现存的艺术史阐释框架,也不在于建构艺术生产消费的逻辑及机制,而是把“社会学式”的思考内嵌于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社会学中,使其为艺术史及艺术理论打开新领域。正如海因里希在反思这一亚学科时所说:“艺术社会学触及比艺术本身还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学的整体实践。艺术领域的价值观与‘社会的’共同性价值体系相对,是一个需要大量阐释的领域,会对社会学的假设提出挑战,或曰,对社会学的方式能否理解其他领域提出挑战。”(73)[法]纳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因此,艺术社会学家同时面对着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理论境遇不禁让我们想起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向,甚至人文主义者同时面对的中世纪与古代世界。也就是说,回到艺术史叙事中“内结构”与“外结构”的范式之争,我们就已经看到艺术社会学发轫时蕴含的理论张力。如果再向前推,回到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面对的“形而上”的神学历史,与“现实可感”的人的历史,我们又能够理解人文学科(群)必要的多元内涵。所以,就艺术社会学本身来说,其理论内核中的冲突也是其发展的动力,艺术史为社会学带来的价值问题,也推动了艺术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亦即:“个体对应集体、主体对应社会、内在性对应外在性、先天对应后天、自然天赋对应文化习得:这些艺术领域经常出现的价值观,恰恰也是社会学要处理的问题。”(74)[法]纳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除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以外,我们仍可以使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来理解艺术社会学。因为无论是人文学科(群)还是社会科学,它们发展至今都在拓宽理论视野,其开放性能不断促进学科间的理论交流。研究范式上能够多种观点并存,其基础在于这种“人文科学”的共识(75)关于这一点,皮亚杰有很深刻的见解:“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性’还带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的要求,以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做任何区分了。”——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在这种理论趋势下,为什么仍以Sociology为定语命名艺术社会学,特别是艺术社会史(the Sociology of Art History)呢?能否有其他的命名方式?如果有,那么例如社会艺术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具有理论有效性吗?在此,海因里希给出一种“中肯性考验”的解决方案,即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突破同行内部交流的,对理论话语中肯性本身也进行的考验。通过这种做法,“艺术社会学家的研究很容易被那些参与或欣赏艺术创作的人阅读、理解和接受”(76)[法]纳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其理论研究就能够突破学科及学院的围墙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流传,等待未来知识思想史的裁判。
四、艺术社会学的议题与路径
沿寻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学科不断延续的一系列核心议题。首先是学科的研究路径议题,包括传统艺术史中的美学研究路径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温克尔曼书写的艺术史为这一学科真正在学界获得独立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树立了一种向“内”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沃尔夫林那里得到更加形而上,或说概念化的发展,继而使得艺术史以系统的人文科学的面貌立于人文学界。但同时,沃尔夫林的老师布克哈特仍为历史语境论留下了一条理论线索,也为19世纪艺术理论与社会学融合提供了新契机。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在人文学界逐渐夺得青睐,其理论范式辐射到其他人文学科。当社会学的目光进入传统艺术史时,对艺术本身的讨论便转向艺术所处的环境中。在此基础上再反观艺术本身,社会学便为艺术史带来了新的展望。艺术史从“内结构”的叙事转向“外结构”叙事,其背后经历了艺术理论从辨析哲思式的宏观本质,到分析经验式的微观因素的范式转向。
学院派的理论转向可以引申到艺术社会学的第二项议题,即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两套不同方法论。艺术哲学与文化社会学都绕不开一个基础问题: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内在于艺术品的一种本质属性,还是内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关系属性?这是横亘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出发点。对于人文学者尤其是学院派美学家来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艺术性当然内在于艺术品之中,正是艺术性构成了艺术品纯粹、永恒的审美品质,使其历久而弥新,成为鉴赏者凝视或谛听的独立自主的审美对象。对于社会学者来说,没有任何物体具有内在的艺术特质,艺术品的艺术性不过是利益集团为之贴上的标签,它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政治氛围中的。“艺术”“艺术品”“艺术家”等审美“星丛”不过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代发明,并非自古有之。通过一系列程序接受或拒绝为某个或某些对象贴上艺术的标签,利益集团使艺术活动机制为国际秩序或社会治理服务。如果艺术仅仅是一项现代的、西方的发明,那么来自亚非拉与南美洲的所谓“艺术”之名,不过是艺术学界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为其贴上的西方标签。当它们从原创的社会语境挪用到西方博物馆、展厅、画廊、剧院、音乐厅等艺术空间时,它们便失去了审美人类学的仪式性价值及其社会交流的象征功能。
伴随这两套方法论的理论争鸣,艺术的内涵被不断扩大、泛化,甚至去定义化。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以“美”“审美愉悦”“审美价值”等来限定内涵的艺术,在社会科学中则以“语境”“意识形态”“阶级”等来理解,甚至随着艺术社会学的发展,这些概念本身又有了新的内涵。当“艺术”一词的内涵及外延都难以界定时,与“艺术”相关的人、物、事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艺术家”是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者属性?如果把艺术家视为生产者是否会抹煞其独特性?“艺术品”的价值在于“艺术”本身,还是在于“艺术家”的技艺?应该在怎样的“艺术”框架中去解读“艺术品”?这些问题的提出得益于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正是理解艺术的视角变化,才使观看艺术的视野不断被拓宽。当然,仅仅用“文化形式”“文化产品”“文化生产者”等术语取代“艺术”“艺术品”“艺术家”等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艺术社会学致力于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艺术,就必然涉及艺术(艺术品、艺术家)与社会(社会关系、结构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及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艺术社会学着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任重而道远。
通过梳理艺术社会学的历史谱系、问题视域及其理论本身蕴含的范式之争,我们可以推论,一劳永逸地解决艺术社会学普遍存在的争论和异议并不是这一亚学科的未来,跨学科整合的研究策略才是艺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所谓跨学科整合并非融两门学科于一处。实际上,正是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带有的人文学科独立性,以及社会学带有的社会科学独立性,使艺术社会学作为一门亚学科具有独特的理论有效性。正是在此基础上,跨学科才能够成立。正如佐尔伯格总结艺术社会学的今天和明天时所说:“他们(社会科学家与人文主义者)最好是努力达成一个局部封闭或暂时的综合阐释框架,而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是走向综合的重要一步。”(77)[美]维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原百玲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