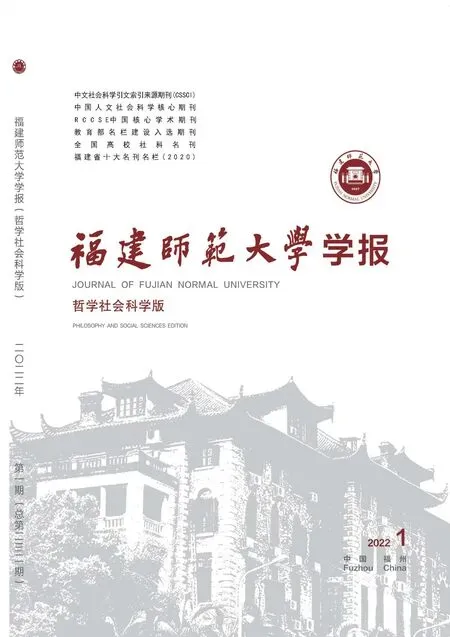东晋诗僧群的五言体写作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蔡彦峰,孙银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东晋以来,佛教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开始有较显著的体现。从文学角度来看,东晋时期僧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于诗坛,(1)从现存文献来看,“诗僧”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皎然《答权从事德舆书》又云:“灵澈上人,足下素识,其文章挺拔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说明唐代人认为诗僧从齐梁开始就有。追溯僧人的诗歌创作实始于东晋,因此诗僧的出现也应该从东晋算起。东晋诗僧群体虽然不具有文学家集团的性质,但相似的家族出身及僧人身份,使他们的诗歌观念相近,具有比较明显的群体特征。对诗史产生了影响(2)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76页。。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二十“释氏”,收录15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诗人的作品,除杨苕华为竺僧度的未成礼之妻外,其余14人皆为东晋僧人,(3)其中题为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当为庐山僧人个人所作而集体署名。所收诗歌34首,五言体32首,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玄言诗占主流、五言诗创作处于低谷的背景下,这个数量是比较可观的。此外,还可以看到与东晋诗僧关系密切的一些士人,如张翼、孙绰、许询、王羲之、谢安、王乔之、刘遗民等也都擅长五言诗,这在东晋诗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歌创作既继承了汉魏西晋五言诗传统,又在转向山水描写中结合言咏写怀、名理奇藻而形成了新的五言诗风格。由于东晋以来士僧交往的广泛和深入,诗僧群创作的这种融合新旧的五言诗,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弥缝了东晋士人以五言诗为俗体与汉魏西晋诗歌传统的隔阂。至东晋中期,孙绰、许询、王羲之、谢安等人开始比较明显地重启了五言诗的写作风潮。这些原本偏离了汉魏五言诗传统的士人,为何又选择了五言体,成为研究东晋前中期诗歌发展、转变,准确把握东晋诗歌史,需要厘清的一个关键问题。分析东晋士僧五言诗的语言、内容、风格等,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从士僧交往及诗歌具体的写作时间等来看,东晋士人的五言诗写作显然受到了诗僧的影响。东晋中后期士、僧五言诗创作的相互交融影响,共同塑造了晋宋新诗风。
就晋宋诗歌的发展而言,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五言诗史的一种建构。东晋诗僧之所以能担负起这一诗史任务,从客观的方面来看是东晋前期诗坛“溺乎玄风”(4)(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页。,四言体玄言诗的盛行及汉魏五言诗传统的式微,僧人继承汉魏西晋传统的五言诗创作反而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开创性;从主观方面来说,则是东晋诗僧群出身于中下层,比较自然地继承了汉魏西晋的五言诗传统,并在融合山水审美、表现佛玄义理中开创了五言诗的新风格,得到士人的接受和学习,开启了晋宋五言诗新的发展轨迹。东晋诗僧群这种承上启下的创作,使被玄言诗遮蔽的东晋五言诗史得以完整地建构起来。
但是,在东晋玄言诗为主流的背景下,诗僧群五言诗创作的历史功绩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南朝檀道鸾、沈约、刘勰、钟嵘等诗论家建构的东晋诗歌史中,注意突出玄言诗独盛的现象,包括诗僧的其他诗歌则被忽略了,以诗歌数量和艺术都很突出的支遁为例,檀、沈、刘、钟等人皆不置一语,可见南朝诗史家对东晋诗僧群及其创作的忽视。因此,南朝诗论家的诗歌史建构,自然未能准确、全面地勾勒出东晋诗歌史的真实面貌。基于这样一个诗歌史事实,我们应该注意到玄言诗之外东晋的其他诗歌种类,而这其中,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士人的五言诗歌创作,是东晋诗歌史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脉络。这是东晋诗僧群五言诗创作在东晋五言诗史建构上的重要意义。
一、东晋诗僧群的形成及其五言诗写作
东晋僧人多出自中下层家族(5)徐清祥认为东晋有士族身份的高僧只有15人,其中唯有竺法潜和竺道宝出自琅琊王氏,其他人都非出自高门士族。(详见徐清祥:《东晋出家士族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第40页)。,这种家族继承了汉末以来儒学、文史博综的学风,钱志熙先生分析这种学风与文学的关系说:“汉末以来这种博涉的学风与文学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博学就等于文学。”(6)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6页。从《高僧传》可以看到,博学、属文、言辩乃至各种技艺也是两晋僧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康僧会“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谶,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支谦“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技艺,多所综习”。竺法护“笃志好学,博览六经,游心七籍”。曇无谶“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于道邃“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释道恒“学该内外才思清敏”。释僧肇“历观经史,备尽坟籍”。东晋高僧则在继承博综的学风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了文学创作能力,如道安“外涉群书,善为属文。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7)(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221、222、164、229、207页。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善属文章,辞气清雅”(8)(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221、222、164、229、207页。。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9)(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221、222、164、229、207页。。释慧持“善文史,巧制艺”(10)(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221、222、164、229、207页。。帛道猷“少以篇牍著称”(11)(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221、222、164、229、207页。。可见,东晋时期,不少擅长文史之学的僧人还比较明显地带有文学之士的特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晋开始出现了诗僧这一群体。
东晋诗僧群承袭了汉魏博学、善属文的风气,因此比较自然地接受、继承了汉魏西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从创作实践上看,东晋僧诗与汉魏西晋诗歌有明显的艺术渊源。如康僧渊《又答张君祖诗》:
遥望华阳岭,紫霄笼三辰。琼岩朗璧室,玉润洒灵津。丹谷挺樛树,季颖奋晖薪。融飙冲天籁,逸响互相因。鸾凤翔回仪,虬龙洒飞鳞。中有冲漠士,耽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息自宾。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尘。翘想晞眇踪,矫步寻若人。咏啸舍之去,荣丽何足珍。濯志八解渊,辽朗豁冥神。研几通长妙,遗觉忽忘身。居士成有党,顾盼非畴亲。借问守常徒,何以知反真。
康僧渊在《代答张君祖诗序》中谓自己的答诗“未足尽美亦各言其志也”。因此,其诗虽多涉佛玄义理,但他认为也是属于言志之作,也就是继承了传统儒家言志的诗学观,如此诗表现的耽道、濯志、冥神、研机、反真等体道的追求,就是他所谓的“言志”,这虽然主要是义理上的体验和追求,但诗人主观上则是有意承继汉魏晋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故多以咏叹来表现义理。而且,诗中的立意、用语、章法结构等颇多来自汉魏晋诗歌,如“中有冲漠士,耽道玩妙均”,出自郭璞《游仙诗十九》其二“清溪千余刃,中有一道士”;“荣丽何足珍”出自《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翘想晞眇踪,矫步寻若人”“濯志八解渊”出自左思《咏史八首》其五:“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而诗歌之语言如:紫霄、琼岩、璧室、玉润、灵津、丹谷、晖薪、融飙、鸾凤、回仪、虬龙、飞鳞,这种藻丽的修辞,正是陆机、潘岳等代表的太康绮靡诗风的继承,而迥异于玄言诗“淡乎寡味”的平淡之体。
东晋僧人中诗歌成就最大的支遁,其诗学也主要源于汉魏晋诗歌。如其《咏怀诗》五首、《抒怀诗》二首,虽多玄、佛内容,但以玄理抒怀,有意学习阮籍的《咏怀诗》、左思《咏史》及郭璞《游仙诗》一类。试举《咏怀诗》其三:
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彷佛岩阶仰。泠风洒兰林,管濑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
此诗融合了魏晋多种诗歌笔法,开头以魏晋诗人常用的感物兴思起调,中间“泠风洒兰林”至“寥寥石室朗”一段的写景,杂取张协《杂诗》、左思《招隐诗》的写景之法,如“泠风洒兰林”出自张协《杂诗十首》其二“飞雨洒朝兰”,“丹沙映翠濑”出自左思《招隐诗》“丹葩耀阳林”、张协《杂诗十首》其二“浮阳映翠林”。“中有寻化士”以下的运思结构则明显学郭璞《游仙诗》其二:“青溪千馀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钟嵘《诗品》谓郭璞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12)(南朝梁)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9页。支遁《咏怀》诸作,在情理结合中表现了体道者的形象和心境,颇多咏叹,带有陶写情怀的色彩,其诗歌精神乃从阮籍《咏怀诗》而来,对阮籍、郭璞等人实有继承之处。(13)萧驰认为支遁诗歌对山水的表现“未能脱离郭璞结合招隐和游仙的框架”(详见萧驰:《佛法与诗境》,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37页)。其实支遁诗歌常融合了招隐、游仙、咏怀等多种艺术手法,由此可见支遁对五言诗传统的广泛学习。
又如《八关斋诗三首》其三,叙述与何充等人举行八关斋会后,诗人登山采药的山水游赏,诗中写景清蔚,音节流畅,是出自左思、张协的一种山水写景之法,对仗工整又颇学太康诗风。其他如《咏禅思道人》《四月八日赞佛诗》《五月长斋诗》等,都是篇幅超过三十句的长诗,内容虽主要表现佛玄义理,但诗人用丰富典雅的辞藻,有意避免成为枯燥的玄理演绎一体,如“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回壑佇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蹊路”(《咏禅思道人》),“绿澜颓龙首,缥蕊翳流泠。芙蕖育神葩,倾柯献朝荣。芬津霈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黄曜紫庭”(《四月八日赞佛诗》)。语言皆极富丽,与康僧渊诗一样,其体亦从太康体而来。
庐山著名的高僧慧远也擅长文学创作,如其《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崇岩”以下四句描写庐山清幽的山水之景,慧远《庐山略记》记载:“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受道于仙人,共游此山,遂托室崖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此诗所说的“神迹”既是指庐山是“神仙之庐”,又以之表现庐山富于神秘气氛之美的“神丽”。慧远与其弟子的诗中都有意用神仙来衬托山水的幽深之境,如“腾九霄”“冲天翮”,及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眇若凌太清”,这种山水境界渊源于郭璞的《游仙诗》。“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两句写山水清音,出自左思《招隐诗二首》其一“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以下,则塑造出一个独游而悟道的诗人形象,这种孤独的悟道者形象比较明显地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可以说是从曹植、阮籍、嵇康、郭璞等人所塑造的诗人形象的延续。总体来看,慧远此诗借景抒怀,由山水审美而体道悟理,正是康僧渊所说的“言志”。可见慧远此诗亦源自魏晋五言诗艺术传统。
又如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明代杨慎谓曾在沃洲(亦作“沃州”,今浙江省新昌县东)看到此诗一、三两联的石刻,认为“此四句千古绝唱也”(14)(明)杨慎撰、王仲镛笺证:《升庵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页。。这四句的确更符合唐以后之人的诗美观,也就是更具有兴象之美和想象的空间。但是帛道猷在这四句之外,还增加了纪实性的内容,如“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即叙述了他在上山采药观赏山水之后,探访山林中的茅屋的活动,最后兴发起在百代之后,仍有像上古三皇时代那样自然自足的人民的感慨。相对于杨慎所说的具有兴象、空灵之美的四句,整首诗更带有纪实和描述的性质,这正是魏晋早期山水诗体的特点。帛道猷此诗带有写景、记游、抒怀的内容,这种章法是从陆机、左思等的《招隐诗》发展而来的,从魏晋诗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此诗的艺术已很成功,辞体省净、写景苍蔚、音韵清新流转,颇能得五言体之声情。
此外还可注意的是竺僧度与杨苕华的赠答之作。僧度的答诗虽受到佛教影响,情感没有杨苕华赠诗之深切,但其诗能针对苕华的诗意而出新,可见他对五言诗艺术本是颇为熟悉的。又如与康僧渊、竺法頵酬赠的张翼,其《咏怀诗三首》《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康僧渊诗》等,皆以咏怀的方式表现佛、玄义理,其写景、言理之体与僧诗相类,可见东晋僧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士人,其诗歌主要是从汉魏晋发展而来的,与玄言诗的诗学渊源不同。又如《晋书》载道安与习凿齿相嘲之作,是魏晋流行的五言俳谐体。此外,支遁等人的赞体诸作也都以五言为主,可见东晋僧人喜用五言体写作的风气。
从现存的僧诗来看,东晋诗僧群对五言体是极为熟悉的,他们的五言诗艺术源于汉魏西晋诗歌,这与东晋诗僧群的出身及其继承汉末以来儒学、文史之学的学风正相契合。在东晋玄言诗盛行、传统诗歌陷入低潮的背景下,东晋诗僧群继承汉魏西晋的五言诗创作,对东晋中后期诗歌的发展变化、五言诗歌史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批评与建构:东晋僧诗的诗学渊源
东晋诗歌史观是檀道鸾、沈约、刘勰、钟嵘等南朝诗史家首先建构起来的,其中以檀道鸾的诗史观影响最大,稍后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诗品序》都明显受其影响。(15)余嘉锡云:“学者诚欲扬榷千古,尚论六朝,试取道鸾此篇,与休文、彦和、仲伟之书合而观之,则于魏、晋以下诗歌一门,兴衰得失,了如指掌矣。”又云:“三家之言皆源于檀氏。”(见(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檀道鸾《续晋阳秋》云:
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16)(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这是有关玄言诗发生、发展的一则重要材料,其对东晋诗歌史研究的价值,已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檀氏基于汉魏晋诗歌史的大背景来把握东晋诗歌,认为东晋诗歌偏离了诗、骚传统,是传统诗歌的一种歧异。稍晚于檀氏的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在建构东晋诗歌史时都明显受到檀氏诗史观的影响。经过南朝这些诗史家、批评家的建构,以玄言诗为主体的东晋诗歌史成为一个基本认识。但是檀道鸾等南朝诗史家是在玄言诗风被否定和扭转的宋齐时期建构其东晋诗史观的,在批判玄言诗风的背景下,这一诗史观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否定性的建构却正否定了一代诗史本身。(17)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因此,为了揭示东晋诗史的真相,需要对檀道鸾这则有关东晋诗史的重要材料进一步加以辨析:一是“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即郭璞诗歌的性质及其与东晋诗歌的关系;二是“加以三世之辞”对诗歌的影响;三是“《诗》、《骚》之体尽矣”的内涵。对这三点的理解,关涉对东晋僧诗的评价与东晋诗歌史的把握。
首先,檀道鸾谓:“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18)(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可见檀氏将郭璞《游仙诗》纳入东晋玄言诗史的范畴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则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19)(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701页。《才略篇》也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20)(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701页。钟嵘《诗品》对郭璞诗歌做了更全面的评价:“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乘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21)(南朝梁)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刘勰、钟嵘强调郭璞与玄言诗在诗歌精神、诗体、艺术等方面的区别,对郭璞诗歌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从前文对东晋诗僧群的创作的分析来看,郭璞《游仙诗》是其重要的诗学渊源,东晋诗僧群学习了郭璞瑰奇艳丽的辞藻,并有意地效法郭璞以隐逸、游仙、悟理寄托情怀的咏怀写法。《诗品》中品说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与檀道鸾相反,钟嵘认为郭璞是改变玄言诗体的人,从这一点来讲,东晋诗僧群对郭璞的学习,某种意义上也有变革玄言诗“淡乎寡味”的自觉意识。但《诗品序》又说:“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22)(南朝梁)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518页。认为郭璞变革诗体的努力,在东晋前中期未得到回响,直到后期的谢混才得以继承,这其实是忽略了东晋中期诗僧群对郭璞的学习,郭璞的诗学史意义其实首先是由支遁等东晋诗僧发现的,东晋诗僧群中下层的出身及文史博学之风皆与郭璞颇相似,这使郭璞的诗歌成为他们重要的效法对象,也成为东晋诗僧建构五言诗史的重要诗学渊源。
其次,“三世之辞”指佛教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说教,檀氏以之代指佛教。佛教对东晋诗歌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内容,二是诗歌体制,即内容和形式。孙绰、许询等人现存的诗歌中,几乎看不到表现佛教义理的内容,最早在诗歌中“加以三世之辞”的是支遁、竺法頵等诗僧(23)孙昌武认为支遁“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他有开创之功”(详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1页)。。东晋僧诗几乎都是五言体,与东晋诗僧群出身于中下层,比较自然地接受出自寒素的五言诗有关。从僧人的身份来说,也与东晋以来佛教偈颂以五言为主的形制有关。陈允吉先生《东晋玄言诗与佛偈》说:“玄言诗依靠‘三世之辞’佛偈的加入而诞生。”将玄言诗的产生归因于佛教当然不符诗史,但陈氏在分析佛理诗与玄言诗的关系时又指出:“这种浸润互融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普遍,根本原因要归结到它们诗体来源上的一致性。”(24)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09-116页。注意到“三世之辞”对诗歌体制的影响,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黄侃,他在《诗品讲疏》中说:“若孙、许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偈语,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25)(南朝梁)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518页。黄氏所关注的也是孙、许等人在诗歌体制上受佛教的影响。从诗体的角度来探讨佛教在东晋诗歌发展上的意义,会得出与南朝诗史家们不同的认识,孙、许乃是当时写作五言诗的能手,而二人皆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按檀道鸾《续晋阳秋》的说法,他们引“三世之辞”入诗,因此“三世之辞”与五言诗存在什么关系?这是当前尚未深入分析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西晋永嘉以来玄言诗以四言体为主的诗学背景下,许询作为玄言诗的代表又能成为写作五言诗的妙手,恰恰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26)蔡彦峰:《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8页。也就是说孙、许等人通过佛教而接受了五言体。
再次,檀道鸾总结东晋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为:“《诗》、《骚》之体尽矣。”从檀道鸾的叙述来看,这个“体”是文学本质之义,“《诗》、《骚》之体”即《诗》《骚》所体现的抒情言志的诗歌本质。汉魏西晋的诗歌中承载抒情言志诗歌传统的主体是五言诗,所以从诗歌体制上来说,“《诗》、《骚》之体尽矣”还指五言体的衰落。从这一点来说,檀道鸾《续晋语阳秋》所建构的东晋诗歌史,也可以说是五言体衰落、而以四言为主体的玄言诗歌史。所以就诗歌体制而言,“《诗》、《骚》之体尽矣”并不符合诗史,“三世之辞”的加入反倒是东晋五言诗得以发展的一个契机。
从以上对檀道鸾这段材料的辨析,可以看出,佛教、诗僧与东晋五言诗的发展有重要关系。东晋诗僧出身中下层家族及其僧人身份,使这一群体与传统五言古诗、佛经五言偈颂等五言体有一种天然的关系。魏晋以来,五言诗在抒情言志之外,还强调诗歌自身之美,如曹丕《典论·论文》主张“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总结西晋以来的诗风是“析文以为妙,流靡以自妍”;在佛经偈颂翻译上,鸠摩罗什批评当时存在的问题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27)(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3页。这其实是主张偈颂的翻译要做到“大意”和“藻蔚”并重。值得注意的是,《高僧传》在鸠摩罗什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录了他的《赠沙门法和》:“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后面两句是对法和品德的赞颂,鸠摩罗什以“哀鸾”栖于“孤桐”之上,“清音”响彻“九天”,“极写一种‘伟大的孤独’,一种崇高的气质,以突出法和对世情人生的无限悲愿。而这种描写,也正是从传统诗歌中转化而来,因此也特别能够感人”。(28)张伯伟:《禅与诗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此外如支遁《咏怀诗》其二“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慧远《庐山东林杂诗》“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都塑造了孤独而感人的悟道者形象,而这显然是受到了曹植、阮籍、郭璞等人形成的优秀诗歌艺术传统的影响。《高僧传》在录鸠摩罗什《赠沙门法和》后说:“凡为十偈,辞喻皆尔。”可知这类作品鸠摩罗什作了十首,说明鸠摩罗什对传统诗歌有广泛的学习,这其实也代表着东晋诗僧群的一种普遍意识。在这种背景下,诗僧对传统诗歌的追摩、体认,远较东晋士人来得自觉而深入。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序》云:
省赠法頵诗,经通妙远,亹亹清绮。虽云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玄解,神无不畅。夫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吾想茂得之形容,虽栖守殊途,标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尽美,亦各言其志也。
这是很难得的东晋诗僧的诗论,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诗歌之美,如序的开头赞赏张翼赠法頵诗“娓娓清绮”,结尾又说自己所作“未足尽美”,皆以美为诗歌的追求;二是以诗为寄兴、悟理,如序云“意迹之所寄,忘解玄妙,神无不畅”“标寄玄同”;三是主张诗以言志,即诗序所说“夫诗者,志之所之”“各言其志”。这几点也是魏晋诗学的基本内容。东晋僧诗多以“咏怀”“述怀”为题,又多有辞藻之美,有追求诗歌语言之美的意识,如支遁《五月长斋诗》:“掇烦炼陈句,临危折婉章。浩若惊飚散,囧若辉夜光。”此数句自谓其在诗歌上追求如“惊飚”“夜光”一样纷披藻丽的语言之美。可见东晋诗僧群的诗学主张主要是从汉魏西晋发展而来的。
对东晋僧诗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郭璞《游仙诗》是东晋诗僧一个重要的诗学渊源,他们不仅学习郭璞藻丽语言,还学习郭璞悟理、咏怀相结合的写法,以及游仙中遗世之想的神秘气氛。郭璞之外,左思和张协也是他们重要的学习对象,由此而上溯至阮籍等汉魏诗人。从东晋诗僧群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们有自觉取法、继承汉魏西晋诗歌的诗史意识,这是之前的东晋诗歌史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却是建构东晋诗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东晋诗僧群的影响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创作,促进了四言向五言的转变,扭转了东晋中后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并影响了晋宋之际新诗风的形成。从这一点来讲,东晋诗僧的五言诗创作本身即具有诗史建构的历史意义。
钱志熙先生指出:“东晋初的玄言诗,实为雅颂体。到了中叶,张翼、支道林等多改用五言诗为酬赠之体,直接导致了中期五言体玄言诗的盛行。”(29)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东晋前期的雅颂体玄言诗主要是四言,支遁等诗僧之作则多用五言体,并且在写法上“已趋于一般五言诗的叙述之体,语言也趋于通俗”。(30)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所谓的“语言趋于通俗”,指的是东晋诗僧的五言诗,已摆脱玄言诗缺乏表现力的品鉴式的语言特点,接近于汉魏西晋五言诗语言的一般风格。《诗纪》谓张翼、康僧渊相酬赠之作“皆恬淡雅逸有晋风”。(3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1页。“晋风”所指的当是西晋诗风,这与我们前文有关东晋诗僧自觉取法汉魏西晋诗风的论述相契合。东晋诗僧群对东晋诗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诗歌从玄言诗的虚述、泛咏中解脱出来,重新赋予诗歌叙述、抒情、体物等功能和表现力。如建元元年(343)十月十二日,支遁与何充组织了一次僧俗二十四人参加的八关斋(32)汤用彤云:“按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以何充领扬州刺史,镇京口,则土山会或约在此时。”(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6页),支遁作有《八关斋诗三首》,其序云:
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往。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遂援笔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八关斋诗三首》,明嘉靖杨仪七桧山房钞本题为《土山会集诗三首》(33)沈津:《书城挹翠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邵武徐氏刻本、宛委别藏本题作《土山会集诗三首并序》(34)张富春:《支遁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127页。,可见这次由支遁与何充等名僧、名士组织的佛教活动,还带有文士雅会的性质。序的最后说,“遂援笔染翰,以慰二三之情”,所谓的“二三之情”也就是诗歌所要表现的情怀,如“众贤各去”之后“望路之想”这种离别之情;“静拱虚房”领悟“外身之真”的悟理;“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对山水之美的欣赏表现。诗人赋予诗歌叙述、抒情、写景、悟理等丰富的表现内容,这正是东晋前期玄言诗所缺乏的质感。如《八关斋诗三首》其二:
三悔启前朝,双忏暨中夕。鸣禽戒朗旦,备礼寝玄役。萧索庭宾离,飘摇随风适。踟蹰歧路隅,挥手谢内析。轻轩驰中田,习习陵电击。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领望征人,怅恨孤思积。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咏归虚房,守真玩幽赜。虽非一往游,且以闲自释。
此诗写八关斋活动结束后,诗人送别参与者离去之后的心境,诗歌的结尾稍涉言理,但总体上却是以情感人、以情运理的,如“萧索庭宾离,飘摇随风适。踟蹰歧路隅,挥手谢内析”。“引领望征人,怅恨孤思积”乃是典型的汉魏西晋赠别诗的写法,其语言和风格多从古诗和汉魏诗歌中来。第三首则多写山水之游和景物之美,学左思、张协之法,是西晋写景诗的继承。这组诗是支遁早期之作,于此可以窥见其诗歌艺术和观念。此后的《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虽多佛玄义理,但以自抒其怀出之,《咏禅思道人》《四月八日赞佛诗》《五月长斋诗》一类则辞藻丰富。可见支遁对五言诗艺术多方面的探索,其诗的语言、句法颇多效法汉魏诗歌及左思、张协、郭璞等西晋诗人之作。
支遁五言诗源自魏晋诗歌传统,又被晋宋诗人所广泛取法。支遁是东晋士僧交往中的核心人物,清谈、文学皆引领一时风气,《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3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072页。“言咏属文”即清谈和文学创作,这是玄学名士集团第一次兼有文学集团的性质,支遁之外的清谈名士之间的交往,极少看到这种清谈、写作相结合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清谈和文学创作相结合的交往中,许询、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五言诗写作都明显受到支遁的影响。
永和九年兰亭集会所作《兰亭诗》组诗,是东晋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兰亭》组诗37首诗中23首为五言诗,作诗的26人中12人只作五言诗,11人四言、五言各作一首,只有3人只作四言诗,说明东晋中期五言诗在上层士人中已颇为流行。许询更是被晋简文帝赞叹“五言诗妙绝时人”(36)(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可见五言诗已被士人普遍接受,不再视为俗体了,这是东晋中期诗歌观念上一个重要的转变。诗体观念的这种转变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询、孙绰、王羲之、谢安,这些体现了东晋诗歌观念转变的代表人物,恰恰都与支遁有密切的交往,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
现存许询诗如“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虽未冠绝当代,但颇雕琢字句,犹有潘、陆之遗,这也颇近支遁五言诗的特点。许文雨《诗品讲疏》谓《剡溪诗话》:“引许询诗‘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丹葩耀芳蕤,绿竹阴闲敞’,‘曲棂激鲜飚,石室有幽响’,均善造状。而询诗‘丹葩’二句,尤与左思‘白雪停阴冈,丹葩耀芳林’迫似。若谓太冲宗归建安,则询诗又岂尽异趣哉?”(37)(南朝梁)钟嵘撰、许文雨讲疏:《钟嵘诗品讲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第15页。“丹葩”“曲棂”这几句其实是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许征君自叙》拟许询诗之句,许询的《钟嵘自叙诗》已不存,但从江淹的拟作中我们还能看出许询诗歌的一些特点,即山水描写与高情远致的抒发相结合。许文雨说:“若谓太冲宗归建安,则询诗又岂尽异趣哉?”将许询的诗歌宗归由左思而上溯至建安,从江淹的拟作来看,其写法比较接近左思的《招隐诗》,这是江淹对许询诗歌艺术的认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摹拟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善于摹拟者能从中获得最高成就,江淹最为典型。”(38)张伟:《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摹拟的现象、成因与艺术价值》,《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5-113页。江淹的拟作很好地把握了许询诗歌的艺术特点,所以可由江淹的拟作进一步了解许询的诗学。檀道鸾《续晋阳秋》谓许询、孙绰的玄言诗改变了汉魏以来诗歌的宗归,造成“诗、骚之体尽矣”,许文雨则认为许询诗歌之宗归也在建安。之所以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认为其实是关注点不同。东晋玄言诗原有两脉,一是玄理演绎、酬赠,这类多四言雅颂体;二是抒怀、言志、山水审美,此类则多五言体。许询等人既创作缺乏诗味的四言体玄言诗,又开始创作趋于叙述之体的五体玄言诗。所以,许询诸人既将玄言诗推向极致,又在四言向五言的转变中改变了玄言诗的发展。而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转变,与支遁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左思诗是支遁诗歌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支遁《咏怀诗五首》其三“晞阳熙春圃”、《咏禅思道人》都比较明显模拟左思《招隐诗》,支遁诗歌中一些句子更是直接出自左思,如“蔼若庆云浮”(《八关斋诗三首》其一)出自左思《咏史》“飞宇若云浮”;“高步振策杖”(《咏怀五首》其三)、“高步寻帝先”(《述怀诗二首》其一)出自左思《咏史》“高步追许由”;“濯足戏流澜”(《述怀诗二首》其一)出自左思《咏史》“濯足万里流”;“长啸归林岭”(《咏利城山居》)出自左思《咏史》“长啸激清风”。江淹拟许询诗而风格近于左思,可见许询的原作也与左思有重要的关系。左思是寒素诗人,他的诗歌得到东晋士人的接受,恐怕与支遁的学习、创作有很大的关系,考虑到许询与支遁密切的交往,许询之学左思,当很大程度上来自支遁的影响。江淹的拟诗中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曲棂激鲜飚”,“鲜”字极生新,支遁《咏怀诗五首》其一“彩彩冲怀鲜”也运用了“鲜”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江淹了解支遁对许询诗歌的重要影响,故在拟诗中特意效支遁的用字之法。
支遁对兰亭雅集及其诗歌也产生了影响。兰亭雅集之前,支遁即与许询、孙绰、谢安、王羲之等“渔弋山水,言咏属文”,已具有文人集会的性质,支遁对这些名士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时即已开始,而集中体现于《兰亭》组诗中。比较一下支遁的诗、赞,与王、谢等名士之作,即可发现在意象、用语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如王羲之《兰亭诗》“廖朗无厓观”,与支遁《八关斋诗》其三“廖朗神气畅,钦若盤春薮”、《咏怀诗》其一“廖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所表现的于自然山水中体玄悟理的虚朗心境很接近。孙绰《兰亭诗》其二“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其内涵、句法当出自支遁《咏怀诗》其一“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兰亭诗》颇多兴、寄、畅、想,即在山水审美中兴发对佛、玄义理的领悟,如“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孙嗣《兰停诗》),“端坐兴远想,薄言游近郊”(郗曇《兰亭诗》),“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庾蕴《兰亭诗》),“尚想方外宾,迢迢有余闲”(曹茂之《兰亭诗》),“遐想逸民轨,遗音良可玩”(袁峤之《兰亭诗二首》其二),与支遁《咏利城山居》“寻元存终古,洞往想逸民”,《咏怀诗》其三“尚想天台峻,仿佛岩阶仰”,《弥勒赞》“廖朗高怀兴,八音畅自然。恬智冥微妙,亹亹玄轮奏”,《善思菩萨赞》“登台发春咏,高兴希遐踪”,亦极相类似。从支遁的诗歌造诣及诸名士与支遁的关系来看,东晋中后期士人在诗歌上明显受到支遁的影响。(39)蔡彦峰:《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9页。
东晋诗僧群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慧远。慧远极富文学才华,其五言诗虽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但是慧远在庐山组织了多次群体性的诗歌创作,如现在还可以看到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等人的同题之作《奉和慧远游庐山诗》。慧远还编有《念佛三昧诗集》,是庐山僧俗的群体之作。此外,署名为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庐山诸沙弥的《观化决疑诗》,很可能也是慧远组织的群体创作所留下的作品。在慧远的影响下,庐山僧俗群体形成了浓厚诗歌创作风气,尤其是五言诗取得了比较高的艺术成就。试举王乔之《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为例: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彻彼虚明域,暧然尘有封。众阜平寥廓,一岫独凌空。霄景凭岩落,清气与时雍。有标造神极,有客越其峰。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嗈。遐丽既悠然,余盼觌九江。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
除了第二句,整首几不涉及义理,已是五言叙述、写景之体,如“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嗈”,皆善于写景,其艺术即从张协、左思、郭璞等人的诗歌发展而来。在山水描写之外,诗歌有意营造神秘气氛,“绝冥”“灵壑”“遐丽”这类语言皆来自这种审美意识,其风格与慧远《庐山东林杂诗》相近。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谓:“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40)(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8页。从慧远等人的庐山诗歌来看,他们的五言诗在言理之外,已比较注意描写山水,并有意识地营造幽远神秘之美,这正是源于“举其灵变”的郭璞《游仙诗》。郭璞成为东晋诗僧群重要的学习对象,一方面与仙、道、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郭璞在游仙、隐逸意象描写中寄托情志,契合了东晋诗僧的诗学主张。
东晋诗僧群包括围绕在其周围深受其影响的一些士人,如张翼、张奴、刘遗民、张野、王乔之,以及与支遁在文义上交往密切的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等人,创作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五言诗,构成了东晋中期诗歌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五言诗创作并没有进入南朝诗歌史家的东晋诗史建构之中,东晋五言诗史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和遮蔽了。重新勾勒东晋五言诗史可以发现,在东晋前期五言诗衰落的局面下,是东晋诗僧群率先重启了五言诗的写作风尚。东晋诗僧群由于其出身中下层,比较自然地继承了带有寒素文学特点的五言诗歌艺术,加以佛经五言偈颂的广泛流行,他们与五言体有天然的关系。
从创作实践和诗学观念来看,东晋诗僧群有学习、继承汉魏西晋五言诗艺术传统的自觉意识,使他们成为东晋中期五言诗创作的主要群体。由于士僧交往的深入,诗僧的五言诗创作对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士人视五言为俗体的观念,重新认识、接受五言诗及汉魏诗歌艺术传统,并且由于佛理与山水的融合,东晋五言诗形成了新的风格,开启了晋宋山水诗风。东晋诗僧群通过郭璞、左思、张协等人进而上溯至汉魏,下启许询、孙绰乃至谢灵运等人,形成了一条五言诗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像郭璞这种在东晋前中期不被重视的诗人,正是通过向东晋诗僧的学习,才开始确立其诗史地位的,这正是东晋诗僧群以其创作重建五言诗史的体现。在南朝玄言诗歌史之外,东晋诗僧群从创作和诗学理论上建构的这个五言诗史,有必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揭示东晋诗歌史的真相,并厘清晋宋的诗歌变革诗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