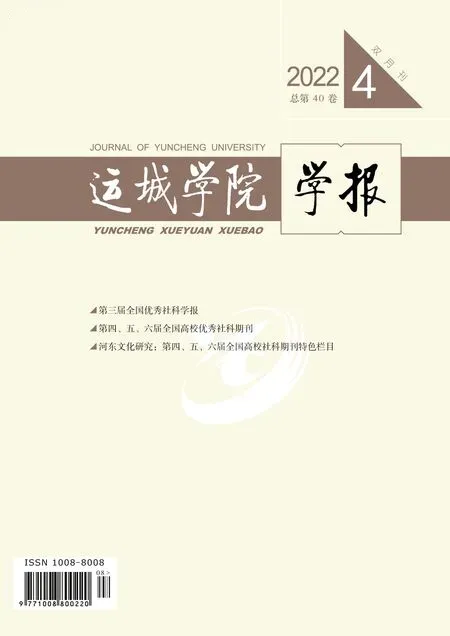郭璞奏疏文的政治思想探究
蒋 绘 燕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成都 274000)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博学有高才,但讷于言论,性情放散而不拘于礼节。东晋初,郭璞因卜筮之能被王导引荐给晋元帝,又因文笔俱佳被晋元帝提携为佐著作郎,又迁尚书郎,后来被王敦胁迫做了记室参军。王敦谋反时让郭璞占卜,郭璞以卜筮不吉劝阻王敦,王敦恼羞成怒,杀害了郭璞。王敦之乱平后,郭璞被追赠为弘农太守。
郭璞现存奏疏文共五篇,分别为《省刑疏》《因天变上疏》《皇孙生请布泽疏》《平刑疏》和《弹任谷疏》。郭璞的奏疏文集中创作于佐著作郎与尚书郎任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郎承担着史官的任务,规谏国君就成为郭璞义不容辞的责任。如郭璞所说:“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谏留任谷宫中疏》)郭璞奏疏文的创作目的是为了统治者巩固王朝政权服务的,因而,其思想内涵也是围绕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
目前学界对郭璞奏疏文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阴阳灾异思想,儒道思想等方面。
高刚在《郭璞辞赋与散文研究》中指出,郭璞奏疏文中的阴阳灾异思想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学说,还传承了董仲舒奏疏儒雅雍容的风格,又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郭璞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为百姓代言。与同时代的庾亮、温峤相比,郭璞更多的是站在老百姓立场谏言刺世,虽然官职低微,却不惧权贵,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1]赵华超的《东晋奏议文研究》同样指出,郭璞奏疏文中充满了阴阳灾异思想,该文将郭璞奏疏文与西汉时谷永奏议文对比分析,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别。谷永奏议文直言敢谏,行文一气呵成,作者认为这源于汉代人对君主关系的客观认识,郭璞奏疏文注重阴阳灾异思想的推演,增加了论述角度,是对汉代此类奏议文的发展。[2]连镇标的《郭璞研究》对郭璞奏疏文中的思想成分剖析透彻,深刻阐释了奏疏文中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3]胡中胜的《东晋爱国文学研究》主要对东晋爱国文学进行研究,认为“上念国政,下悲小己”始终是郭璞诗文创作的主旋律。以仅存一句话的《谏禁荻地疏》为例,胡中胜指出,郭璞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阐发了儒家爱民思想,借此谏阻统治者“禁荻地”之举措,郭璞此举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正道直行的处世态度。[4]
综上,对于郭璞奏疏文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学者们往往以郭璞的具体人生经历为底本,对其思想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从郭璞的生活环境、社会现实和奏疏文文本出发,挖掘郭璞思想的渊源和流变,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政治和思想倾向。
一、阴阳灾异思想
郭璞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往往以阴阳灾异思想应对。
(一)阴阳灾异说的起源与发展
阴阳灾异又称为天人感应说,这一理论正式形成是在汉代,但它的起源很早。“阴阳”“五行”观念在《尚书·洪范》中已有表现。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们把五行提升为“五德终始”,并把五行与阴阳附会起来。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在《周书》《夏小正》和邹衍学说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此为经,再综合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因素和政治行为,使万物万象都组合到了阴阳五行里面去,形成一种神秘的大有机体。《淮南子》把《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完全吸收进《时则训》中,以十二纪纪首的五帝五神为《天文训》中的五星。在汉代思想家中,受十二纪纪首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继承了十二纪纪首的观点,运用以类相推的方法,由人推及于天,强调“以类退之”“以合和之”,由类推以言灾异,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继董仲舒后,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卦气思想还在发展,孟喜易学把传统周易的八卦与五行完全结合起来,构成天地之体和宇宙的基元。[5]292京房对孟喜的易学又有建树性的发展,京房以阴阳为基础,糅合了天文、律历、人事、五行、方位、岁时、天干等,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大统一体,鲜明地反映了汉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特点。
三国时期还有一位卜算大师叫管辂,《三国志·管辂传》[6]675有专门介绍。管辂,字公明,平原人,精通卜筮之学,其弟管辰作《辂别传》,使后世对管辂有所了解。《辂别传》主要介绍了管辂关于占卜的一些奇妙故事,《管辂传》是放置在《三国志》的《方技传》中,因此,管辂并不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方士。但管辂本身也是一位精通易学思想的大师,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思想被忽略,然而也不能完全被抹杀。目前关于管辂的研究很少,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中专有一节讲管辂之象数。牟宗三分析了治易的三种体系,也通过分析《辂别传》中管辂占卜的实践过程,解读管辂术数学的理论和方法。他把易学研究分为三系。[7]78对于管辂的术数学,牟宗三指出,数术的根本还是阴阳感应的变化。也就是说,具体的或常或变的征象都来源于阴阳的感应。[7]83谷继明对这些问题又做了深入探讨,他在《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8]一文中指出,术数无法用现代科学去解释,因为科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术数没有规律性,因此术数要“入神”,才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超越也就是打通人与神之间的界限,通神灵,才能准确地演绎神秘化的真意。
(二)郭璞阴阳灾异思想的体现
《晋书·郭璞传》:“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9]1900《晋书》在介绍郭璞生平时,为了凸显他占卜的能力,把他与汉代京房、三国管辂相媲美,甚至认为超过了他们,可见郭璞攘灾转祸的能力非常突出。
按照牟宗三先生对于易学思想的划分,再结合郭璞的人生经历,可以做出以下论断:
首先,郭璞在经王导推荐做官之前,一直是以占卜为生,这就属于术数系。根据《晋书·郭璞传》的记载,西晋后期,国家动荡,郭璞卜筮到河东会有大乱,就带着亲戚朋友去东南避灾。这一路上,为了生活,每到之处都会给那些地方官员乡绅占卜,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郭璞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如在将军赵固之处,郭璞用术数使赵固的良马死而复生,赵固给了他一笔不菲的物资。[9]1900郭璞过江后,宣城太守听说了他的名声,援引他为参军,这时候郭璞的名声在江南也渐渐建立了。郭璞此时的占卜往往是用术数解决问题,不掺加经与注的内容,因此,郭璞与管辂有相仿之处。两者在卜筮之时,不附会经书的内容,只是方技之士。但是,方士因为未进入政治中心,就没有很高的地位。如管辂,虽是闻名四方的占卜大师,却被收录在“方技”一类中。
郭璞南渡后,所携物品数量有限,在新地方落户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他还是携老扶幼,很多地方需要安置,在财力上,郭璞无疑是不充足的。起初,郭璞做一些官员的参军,提升自己的个人地位,然后又寻找机会,得到王导的青睐,王导顺势而为,再把他推荐给晋元帝。当时有一句俗语,“王与马,共天下”。王导是晋元帝渡江后最信赖的人,元帝对他的话自然言听计从,郭璞渐渐地进入了政府机关。郭璞自己知道占卜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光鲜的职业,然而他为了生计,只能靠给人占卜赚取钱财。但郭璞并非只是一个方士,他还是一个文学家,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司马相如一样,通过辞赋驰骋官场,因此他作了《江赋》。一经上呈便得到了晋元帝的赞赏,郭璞却并未由此就受到了重用,晋元帝只给了他一个佐著作郎的官职。
其次,牟宗三先生提出,第二种是术数系附会上经注。郭璞本身是卜筮者,做著作佐郎之类的官员正是让他承担劝谏之类的政治任务,郭璞也全力以赴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创作了一系列的奏疏文,如《省刑疏》《因天变上疏》《皇孙生请布泽疏》《平刑疏》等,其创作目的皆是通过阴阳灾异思想劝阻皇帝减轻刑法。郭璞奏疏文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承继了董仲舒的“尚德去刑”理论,不仅理论上相同,论证上也继承了董仲舒的方法,以阴阳灾异干预政治。其中最精彩的是在《省刑疏》中对于天象人事的分析,郭璞把阴阳、四时、人事、天文、气候、八卦、经传等统统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借以引起晋元帝的警惕。郭璞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了问题,还在于摆明了“消复之救”。第一篇疏文上奏以后,晋元帝虽然有所警惕,但并未采取行动,郭璞又借天变再次上疏,还是接着上次卜卦的内容,郭璞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卦象的真实性,同时也催促晋元帝尽快行动。
郭璞在他的奏疏文中引经据典,这就符合把经书内容附会到自己的卦象上,借以干预政治。如《省刑疏》中有言“谨寻案旧经,《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10]46“案《洪范传》,君道亏则日蚀,人愤怨则水涌溢,阴气积则下代上。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谬中,必贻陛下侧席之忧。”[10]46徐复观曾指出,《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对汉代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对灾异的解释与对策;第二,是对刑赏的归正和运用。”[11]41汉代思想家接受《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影响,郭璞又把前代思想融通起来,用阴阳灾异干预刑法,主张刑法分明。阴阳灾异思想是天人感应思想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
通过对郭璞散文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天人感应思想在郭璞的散文中无处不在,不管是在其奏疏文还是图赞文中都不可或缺,这也是郭璞作为一个占卜者的表现,正如同他在《客傲》中所说的那样:“吾不几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10]77作为一个卜者,天人感应思想是他面对天地间问题时近乎本能的反映。
二、儒家思想
根据《晋书·郭璞传》可知,郭璞的青年时代是在老家河东地区度过的,河东属于黄河以北,据《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三国时期的新学风兴起于河南,大河以北及长江以南此时一般仍守汉人传统,所谓南北之分乃是河南北,而非江南北……魏晋期间的江南学风是比较保守的。”[12]75又言:“在魏晋时黄河北岸的学风和江南一样保守,因此他(葛洪)的学问纯为汉人之旧。”[12]]80唐长孺明确指出,魏晋时期的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学风主要还是以汉代传统思想为主。关于郭璞的身世,历史上的记载很少,《晋书·郭璞传》只有简单的几句话:“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9]1899魏晋时代,尚书都令史是尚书郎下的一个书吏,《晋书》中并未给郭瑗立传,因而郭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吏,由此也可知郭璞并非出身于胄族。郭璞并未生在世家大族,父亲是从书吏一步步走到了太守的职位。因此,郭璞虽不是锦衣玉食养大的,但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在郭璞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痕迹。在郭璞奏疏文中,儒家思想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广泛征引儒家典籍
郭璞在奏疏文中还广泛征引儒家典籍,构成他的话语主题。郭璞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并大量运用于其文章中。不仅在其奏疏文中有体现,在其他类的散文和诗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易经》《尚书》《春秋》《左传》《礼记》《诗经》《史记》《汉书》等都是他征引的对象。郭璞不仅征引古书,还吸收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政治家的主张和见解,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涵养。以郭璞奏疏文为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10]]46“宋景言善,荧惑退次;光武宁乱,呼沲结冰。”[10]]52儒家经典的运用构成了郭璞奏疏文的主要内容。郭璞本身就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研究,再加上他站在一个史官的位置上,主要任务就是规劝皇帝。因此,郭璞想要使自己的话语权更有说服力,必须大量征引儒家典籍,体现了郭璞浓厚的儒家思想。
除此以外,郭璞在其奏疏文中还多次劝诫晋元帝勤政爱民,减税减刑等。郭璞总是条理分明地指出问题,又提出了解决方法。“臣愚以为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10]46郭璞认为面对国家现存的问题,晋元帝应该采取行动,发布诏书,承担责任,把不完美不公平的现象扫除干净,施恩布泽,让那些含冤而去的人重获新生,郁结之气随风而散。
(二)抒忠君爱国之情
忠君爱国就是心念天下苍生百姓,尽管郭璞在《省刑疏》中运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他的阴阳灾异说,企图干预政治,但他的终极目的还是解决现实问题,体现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在《省刑疏》中,郭璞主张“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10]]46在《皇孙生请布泽疏》中提到:“臣言无隐,而陛下纳之,适所以显君明臣直之义耳。”[10]55郭璞在这篇奏疏文中规谏晋元帝通过皇孙降生的国之喜事大赦天下,开阳布惠,充满了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和热忱。
《皇孙生请布泽疏》有言,“君道亏则日蚀,人愤怨则水涌溢,阴气积则下代上。”[10]56郭璞直白地表示,日蚀出现是因为国君没有尽到责任,阴雨连绵是因为民众心中有怨恨之气,阴蔽阳时间长了会出现以下犯上的情况。郭璞在这句话里面不仅直白地表现了对晋元帝的不满意,还催促元帝要尽快采取行动。其中,“阴气积则下代上”,有一种隐约提醒晋元帝的味道。郭璞作为占卜大师,对于东晋王朝的前途肯定是提前预知到了的。因而,他不断提醒晋元帝采取行动,否则,阴气郁结时间长了会出现内乱。只可惜就算晋元帝会意了也试着改变现状,然而东晋王朝本身就是建立在门阀贵族的掌握之中,晋元帝乃至整个东晋王朝都无法摆脱现状。所以一切想法都只能是白白费力,徒劳无功。尽管如此,郭璞为官期间,还是不断地通过奏疏形式劝诫元帝。
(三)儒家的鬼神观
在《弹任谷疏》中,郭璞展现了自己的鬼神观。开篇直接切入正题,任谷是妖异,晋元帝把他留在宫里是不符合礼正思想的。接着,郭璞举出《周礼》来论证他的观点,“奇服怪人不入宫”,把任谷留在宫里,“尘点日月,秽乱天听”,郭璞个人感觉是不可取的。然后郭璞又提出三种可解决的方法,其一,如果把任谷奉若神明,应该敬而远之。其二,若把任谷当作蛊惑人心的妖孽,应该把他流放到边疆。其三,如果任谷是神祇驱使来降罪于人间,应该克己修礼,而不是让任谷安然放肆地行事。最后郭璞提出自己的观点,任谷是妖孽,应该把他遣出去,又申述自己因为担任了史官一职必须正义直笔。
郭璞本身就是一位占卜大师,通神灵,但他对于鬼神之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痴迷,他继承了儒家的鬼神观念。《弹任谷疏》表明郭璞对于自称是神灵的任谷是不相信的。他以《周礼》的“奇服怪人不入宫”为依据,批判晋元帝允许任谷入宫的行为,并且还继承了传统儒家对于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祭祀观和认识论。
总而言之,郭璞在奏疏文中表现出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在放荡不羁、自我嘲讽的外衣下,掩盖的是他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但无奈世人总把他看成术士,就忽略了他的才华和胸怀,在屡次上书屡次被忽略的悲剧情况下,郭璞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被重用,再加上对于自己的命数非常了解,就借母亲去世丁忧回家,但回去后也免不了被杀的命运,于是安然从容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三、法治思想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对于东晋门阀制度的本质剖析得非常透彻。“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制度,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13]门阀制度是东晋王朝的根本制度,这种制度统领下的社会,必然是士族之间为了利益互相倾轧,而法律制度势必不完善、不公平。面对“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的时代问题,郭璞奏疏文切中时弊,五篇中有四篇都涉及了刑法问题。由此可知郭璞对于法律制度的重视,也可以了解到郭璞的法治思想。
一是强调刑法制定的合理性。《皇孙生请布泽疏》:“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勋业至大,而中兴之祚不隆,圣敬之风未跻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众乖,此自然之势也。”[10]56郭璞认为晋元帝至今还未使东晋达到中兴的盛世气象,原因之一是刑法太过繁重,因此主张适时大赦天下,让那些本不该被关进牢狱的百姓得以重见天日,使恩泽布惠于天下苍生,又能对之前的大兴牢狱之风有所补救。由此可以看出郭璞强调法律制度要合情合理。
二是强调刑法实施的公正性。《平刑疏》:“刑无轻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难,思在断之为难。”[10]58刑法不分轻重,而在于是否公正,但公正的评判标准并非刑法本身,而在断案的审判上。在具体审判过程中要公正严明,刑法审判的公正性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稳定与长久,不公平的审判是不能使民心所向的关键。
三是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平刑疏》中“是以刑法不专则名幸者兴,政令骤变,则人志无系,子产患其如此,故矫先正议事之制,而主刑书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10]58若法律制定后,又有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让法律朝令夕改,只会造成人心惶惶、民心不稳的局势,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郭璞举子产铸法于鼎上的故事是为了强调法律制定后的长期坚持。
由此可知,郭璞的法治思想切中时弊,是针对东晋初期法律朝令夕改的社会现状而提出的,展现了郭璞政治手段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四、黄老思想
“黄老”中的“老”是指老子的《道德经》,“黄”是指“黄帝”,关于黄老思想,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指出,黄老思想面向政治和社会,发展出一套和儒家对立的社会、政治、军事思想。[5]18长沙马王堆汉墓于1973年12月出土了帛书《老子》甲卷和乙卷,乙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这四篇帛书被学界称为《黄帝四经》。黄老思想起源于战国,在汉惠帝至武帝在位前的七十年间成为一种政治指导思想。黄老思想表面上主张清静无为,实质是站在法治的立场,主张法治精神。因此在无为表象下,汉初统治者遵守的是黄老思想或者法家思想的理论主张。汉初的君臣上下皆强调休息无为,以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力,而黄老思想正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郭璞政治思想中也有典型的黄老思想,“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10]58曹参是实践黄老思想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当时百姓纷纷歌咏:“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4]2466郭璞在《省刑疏》中举曹参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制度制定之后的实践性和长久性,不能朝令夕改,应该如曹参一样长久坚持。
《省刑疏》又言:“《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夫无为而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体者也。”[10]58郭璞依据《老子》立论,希望晋元帝不要繁礼缛节,任意刑罚,而倡导无为而治、不宰而宰的治世主张。由此可知,郭璞奏疏文中黄老思想体现的是坚持在法制建立之后对其兢兢业业的坚持。
总之,郭璞虽然有浓厚的儒学思想基础,但本身就思想驳杂的他不会限定自己的思维。惺惺惜惺惺,所以,对于子产,郭璞充满了赞赏。子产在倡导铸法于鼎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连孔子也不例外。铸法于鼎上对于孔子来说是一种术,孔子是主张道的,当然不能表示支持。但子产是一位敢于革新的政治家,主张道术兼而有之。他还曾提出政治要宽猛相济的原则,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通过分析郭璞奏疏文,可以发现郭璞是一个思维非常灵活的人,不会仅限于一家思想中,而与魏晋时期的自觉意识有关,思想融通解放,政治思想也更加灵活。
结语
《晋书·郭璞传》记载:“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戒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横恐不得尽,亲乃忧酒色之为患乎!’”[9]1905郭璞并非一个纯儒,儒家思想只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平时行为放荡、纵酒好色,这就说明了郭璞思想的驳杂性和丰富性,这也是两晋士人的共同特点。相比于两汉时期思想家的纯粹,魏晋时期,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更加灵活多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郭璞在仕宦方面一直都不显达,是一位普通的史官,没有实权,也没有受到晋元帝充分的重视。因此,他一直是以术士的身份立于朝廷之上。在《客傲》中,他才会有最后一句感叹,“吾不几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10]76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在自嘲外表下的款款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