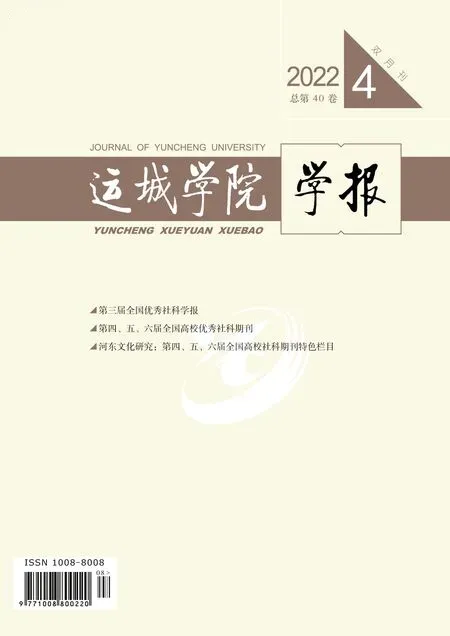论郭璞《游仙诗》中的三重空间
张 萍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207)
根据文学地理学的观点,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作品中的时间向来颇受关注,但是对空间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在“游仙”题材的作品中,“游”这一行为必须依托空间而存在,使得空间的展现尤为重要。文学地理学学者邹建军教授在《文学地理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中提出:“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三重空间,即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1]。下面试从这三个方面分析郭璞的《游仙诗》,以期对诗歌内容及郭璞的复杂情感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游仙诗》中的想象空间
之所以把想象空间置于现实空间之前进行分析,意在对郭璞《游仙诗》的主旨争辩作一点简单的说明。自从钟嵘在《诗品》中论及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2]之后,关于《游仙诗》主题的争辩无非围绕着是否“列仙之趣”展开。然而自古至今,认为其《游仙诗》有所寄托,乃“非列仙之趣”者居多。李善注《文选》言: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3]306
沈德潜《古诗源》甚至直袭钟嵘语意,以为:
游仙诗本有托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4]
今人也多遵循这看法。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传统。”[5]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也认为郭璞的“游仙诗实在是假托神仙来抒写人世间那些悲愤感慨。你要想在郭璞的现实里寻找神仙的志趣,那是绝对找不到的”[6]。虽这一看法乃郭璞《游仙诗》主旨研究中的主流,但实在缺乏辩证思维。若从诗歌中郭璞所展现的想象空间来看,其“列仙之趣”的意味不可以说不浓厚。
文学地理学意义上所谓文学作品里的想象空间,“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事物往往是作家审美认识与艺术想象的产物,并且多半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从性质上来说是作家自己的艺术创造。”[1]诗歌中神仙世界这一想象空间,在范围上是大于现实空间的。首先,郭璞的《游仙诗》中出现了一系列仙人世界的意象,这些意象并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包括:
1. 仙境意象:“丹溪”(其四)、“蓬莱”(其六)、“昆岭”(1)其十的“昆岭”当不同于其九的“昆仑”。从语境来看,后者写诗人成仙升天后俯视人间,“昆仑”应理解为今新疆西藏间的昆仑山脉;前者写筑有玉饰之台的,为与“西海”相对应的仙山昆仑。、“少广”(其十)、“西海”(其十)、“玉阙”(其十二)。仙境乃神仙居住之所,在诗中有仙国,如丹溪,不死之国,曹丕《典论》:“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7]有仙山,如昆仑,古代神话传说,昆仑山上有瑶池、阆苑、增城、县圃等仙境。有仙岛,如蓬莱,《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8]仙境是仙人活动的标志性场所。
2. 仙人形象:“灵妃”(其二)、“赤松”、“浮丘”“洪崖”(其三)、“陵阳”、“容成”、“姮娥”(其六)、“安期”(其七)、“羲和”(其九)、“子乔”(其十)。仙人中有水中神灵妃,有雨师赤松子,有服食仙药飘升天宫的嫦娥仙子,有驾驭日车的神人羲和,有凡人好道修炼成仙的子乔……
3. 仙药意象:“丹荑”(其一)、“奇草”、“灵液”、“五石”(其七)、“五芝”、“六草”(其十四)。仙药乃道人修炼以延年永生之物,它们或草或水或石,本皆自然之物,在神话传说中被赋予了神奇的功效。
4. 神仙世界其他特有的意象:“阊阖”(其二)、“紫烟”(其三)、“云螭”(其四)、“长烟”、“九垓”(其六)、“龙驷”(其九)、“盘虬”、“云轺”(其十)。或天宫之门,或游戏之地,或车驾之物,都是与仙境或仙人相关的东西。
神仙世界的各种意象出现在诗歌中,只是想象的空间初步构建。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孤立分散的,而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相互关联而表现了传统游仙诗中的“列仙之趣”。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9]
这是一幅完整的群仙嬉戏图。在人间即将面临一场大灾之时,神仙的世界是怎样的呢?在华美富贵的金银台上,仙人排云而出:陵阳子酌取丹溜,容成公挥动玉杯,嫦娥仙子妙歌清音,洪崖仙人颔首称赞,宁封子在长烟中随风上下,汗漫神携友人漫游于九垓,他们的年龄都超过了长寿的五龙,即便已经千岁仍拥有婴孩般的容颜。反观尘世燕昭王、汉武帝,不过只是缺乏灵气和仙才的凡俗之辈,岂能跻身仙人之列?郭璞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就是典型的“列仙之趣”,即修道成仙并与仙人遨游仙界,逍遥自在,并且能够容颜不老、青春永驻,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除此之外,郭璞《游仙诗》中还有“人仙共游”的场景。“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三)与仙人左右相携,亲密无间,共享欢乐;“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振发晞翠霞,解褐礼绛霄。总辔临少广,盘虬舞云轺。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其十)寻觅仙人三十多年,终于得以在少广山上携手仙侣,千年逍遥。这些正是所谓“正格游仙诗”的常见内容。
近年来的研究对郭璞《游仙诗》旨趣多了辩证的观点。王钟陵先生认为,“景纯诗兼有咏怀和仙趣的特征。”[10]连镇标先生也提出:“郭璞把表现列仙之趣与坎壈咏怀的两种内容都集中在游仙诗中,发扬光大了曹魏时代游仙诗的传统,故其游仙诗‘拔文秀于丛荟’,振响两晋。”[11]郭璞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神仙世界的企慕是由衷的,对于道家修炼长生的信仰是真诚的,这些正是历代论者所称“列仙之趣”的主要内容。因此,“列仙之趣”是分析郭璞《游仙诗》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二、《游仙诗》中的现实空间
“(何劭)游仙正体,弘农其变”[12],郭璞《游仙诗》被视为“变格”,就是因为在“列仙之趣”之外加入了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内容。关于这一点,前人的分析已经很丰富,兹且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进入诗歌中的现实空间,从而有更直接的体认。所谓文学作品的现实空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以一种现实的眼光如实地描写自然地理形态,作品中存在的空间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景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形,可以唤起我们对于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1]。郭璞《游仙诗》虽是以“游历仙境”这一传统题材为诗,不离“列仙之趣”的描写,但是诗中却又有大量的现实世界的意象。
首先,在《游仙诗》中出现了真实可考的现实世界中的地名:
1. 灵溪:“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其一)《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3]306《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水无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13]灵溪是位于荆州境内一条河流,环境清幽,为隐居胜地。
2. 青溪:“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其二)青溪,山名。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曰:“临沮县有青溪山,山东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郭景纯尝作临沮县,故游仙诗嗟青溪之美。”弘治《夷陵州志》记载:“远安县,邑名;临沮,汉名;高安,晋名。建置沿革,县治在州东北一百八十里,东汉临沮县,地属南郡,晋析置高安县,属汶阳郡……”[14]32“云梦山,在县西南六十里,峰峦耸翠,又名青溪山。”[14]52青溪山又名云梦山,是临沮县内的一座山,高俊苍翠,属荆州。以上两地皆在荆州。《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以母忧离开朝廷,之后,“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15]1908据张恕考证,时年在太宁元年(323),王敦任荆州刺史。所以,郭璞应该是曾亲赴灵溪水和青溪山两地,这两处不再是神话传说中那种想象的空间,而是真实存在的郭璞曾经踏足的现实空间。
3. 此外,“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其九)中的“东海”“昆仑”,“四渎流如泪,五岳罗若垤”(其十三)中的“四渎”“五岳”,虽然不是具体的描写对象,但仍属于现实可考的地理空间。
其次,诗歌中还有一些地理意象,并非神仙世界特有,而是属于人间世界的。游侠出没之地的“京华”,隐者栖居之所的“山林”(其一);富贵豪华的“朱门”,清贫困顿的“蓬藜”(2)有学者认为,有人篡改“藜”为“莱”。参考连镇标《郭璞研究》291页,连引黄侃、程千帆观点,并从修辞学和音韵学角度分析,“莱”当作“藜”,今从。(其一);白“云”萦绕着“梁栋”,清“风”吹拂着“窗户”(其二);“翡翠”在“兰苕”间嬉戏,鲜丽明亮,“绿萝”在“高林”中生长,葱茏繁盛(其三);“潜颖”因“清阳”晚至而迟开,“陵苕”因“素秋”早到而先衰(其五);在“晦朔”循环,“月盈”月缺的时光流逝中,“寒露”拂过“陵苕”,“女萝”辞谢“松柏”,人生有如“蕣荣”“蜉蝣”般短暂(其七);“朱霞”东升,“朝日”明亮(其八)……这些地理意象有自然的,如“山林”“蓬藜”“兰苕”,也有人文的,如“京华”“朱门”“梁栋”。高山河流、植被动物、天文景观、人类活动,一应俱全。
此外,诗歌中还出现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身影时时出现在这个人间现实世界中,如庄子、老莱子之妻、鬼谷子等,他们的出现更增强了诗歌中现实世界的真实性。郭璞在以想象世界为主的游仙世界中,又营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现实世界。直接呈现一些具体可考的山水地名,描绘人间世界的各色景观,甚至可以说,如果剔除掉其诗歌中的神仙世界成分,这组诗是非常出色的山水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释了诗歌中游仙内容的虚幻迷离性,从而强化其真实可感性。
游仙诗有两个书写传统:一是《楚辞·远游》的传统,有曹植的《游仙诗》《五游泳》《仙人篇》《远游篇》,阮籍《咏怀》等,借游仙抒忧生愤世之情;二是秦始皇时《仙真人诗》,有汉乐府游仙诗,如《吟叹曲·王子乔》《长歌行》《董逃行》,以求仙长生为主旨。郭璞的《游仙诗》主要是继承了前者,但这个传统的创作在郭璞之前较少。萧统在《文选》中诗歌部分“游仙”类收诗八首,除郭璞的七首外,另有时代稍早于郭璞的何劭《游仙诗》一首: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
吉士怀真心,悟物思远托。
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
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
迢遽陵峻岳,连翩御飞鹤。
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
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3]306
何劭的这首《游仙诗》历来被推为游仙诗的正统,即前述的第二种传统。诗人虽然以“松”“柏”这样寻常可见的植物发端,但主要是表明自己寻仙的坚贞之心,希望如王子乔那样驾鹤而去,隔绝人世,云游万里,全诗呈现的是想象的神仙世界。张华今存《游仙诗》四首,现录二首如下:
云霓垂藻旒,羽袿扬轻裾。
飘登清云间,论道神皇庐。
箫史登凤音,王后吹鸣竽。
守精味玄妙,逍遥无为墟。(其一)
玉佩连浮星,轻冠结朝霞。
列坐王母堂,艳体餐瑶华。
湘妃咏涉江,汉女奏阳阿。(其二)[9]621
此二首游仙诗中无论是处所、人物,还是活动,无不是神仙世界的专属,而并无任何现实世界的意象,仍属于只有单一想象空间的“列仙之趣”之作。林田慎之助在《郭璞作为诗人的命运》一文中提到,自《楚辞》之后,“彭咸、赤松子、王子乔的故事就不断在诗里闪现,因为神仙思想以及道家的理念,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诗里,以致游仙诗的观念大体上都是以游玩的平淡形象为结尾的。”[16]所以,相比于所谓“正格的游仙诗”而言,郭璞的《游仙诗》因为植入了现实的世界,才呈现出了其对现实世界清醒理智的关注。正是对现实的关注,诗歌也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不仅在同时代的游仙诗歌中独标一格,而且将游仙诗的成就提升到了文学传统中的高位。
三、《游仙诗》中的心理空间
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中,所谓心理空间,“是指文学作品存在的,与作家的心理密切相关的自然山水空间,虽然是想象性的,但主要是作家情感与心理的一种直接现实。”[1]文学作品中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作家的艺术创造,借以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游仙诗》中仙人的世界与凡俗的世界,都是郭璞在诗歌中建构的心理空间。但是,在郭璞之前的游仙诗写作中,很少甚至说没有谁如此明显地将这两种空间统一起来,并且在二者微妙的关系变化中有所表达和寄托。因此,郭璞《游仙诗》中的心理空间,是存在于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之间的。
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二者对立的心理空间。体现在诗歌中,便是郭璞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以两种异质的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遯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藜。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其一)
这首诗始终采用对比手法,“京华”与“山林”、“游侠窟”与“隐遁栖”、“朱门”与“蓬藜”、“保龙见”与“触藩羝”、“傲吏”“逸妻”与“夷齐”,每一组对比前者属想象空间,后者属现实空间,而诗人的态度是扬前抑后,突出隐逸之乐与入世之难,对仕宦的蔑视和对隐逸的向往之心不言而喻。“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其三)现实世界中朝生夕死的“蜉蝣”与仙人世界中长寿千年的“龟鹤”对比,流露出对生命易逝的忧惧和对延年益寿的渴望。“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其七)“王孙”“当途人”与“安期”“山林客”对比,“列八珍”与“炼五石”对比,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厌弃,对仙境世界的企慕显而易见。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在诗人的特意安排下,形成两个对比鲜明的空间,呈现出的便是表现作者爱憎之情的心理空间。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二者统一的心理空间。以矛盾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郭璞在《游仙诗》中设置现实与想象两种空间,表面来看,作者的倾向似乎很明确,但实际上这两重空间又是统一的。“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其一)离城不远的灵溪水便可潜隐盘桓,何必凭云飞升上天?庄周、莱氏妻不就是人间的仙人吗?按理来说,飞升仙境就要远离人间。仙境和人间在距离上是遥远的,在性质上是对立的。但是在郭璞的《游仙诗》中,人间也有绝佳的修炼场所,仙人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人物。“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其二)鬼谷子隐居在青溪山,居室云雾缭绕、清风阵阵,隐士所居之地的幽静与仙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三)隐士食琼蕊、饮飞泉,何其高洁。他还与赤松、浮丘、洪崖同游仙界,亲密无间。虚无缥缈的仙人进入人间世界,人间世界的隐士也可以在山中修炼而得道成仙。诗人不仅在有形的物质上,既想游历仙境,又想留在人间,而且在无形的精神上,一面渴望逍遥,一面关切尘世,当身处仙国回望人间时,只见“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其九),一片渺茫混沌,又不忍心离去。
当然,郭璞在诗歌中所写的在山中修炼以求永生的观念,受到了魏晋时期神仙道教思想发展的影响。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便提出“地仙”说:“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17]20葛洪把先天的“神”降格为懂得长生之术的“人”,完成了“神人”到“地仙”概念的转变。在山中隐居与修炼便可统一起来,“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17]187这就是游仙诗传统中郭璞独创的“仙隐”内容,这更是其人生追求的写照。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两晋,出身寒门的郭璞根本无法凭借自己的才能施展政治抱负。南渡之后,草创于江左的新政权更需要依赖北方大士族及土著的南方大士族,郭璞无法得到重用。而郭璞“妙于阴阳算历”“好卜筮,缙绅多笑之”[15]1905,难登高堂殿宇。但同时,郭璞又“并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且“以才学见重”[15]1904,似乎又给了郭璞进阶的希望。从郭璞的其他著作中可见出,他本人也是一个关注百姓命运、国家前途的典型儒家知识分子。所以,他在遭遇冷落和挫折之时想要退身于仙境这个想象的世界,在受到重视的时候又满心欢喜地预备进入仕途这个现实的世界,但他无法完全进入他所期望的现实世界,又不忍离它太远。于是,郭璞选择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找一个最合适的距离,作为自己栖居的家园,以缓解自己的痛苦。
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分裂后的心理空间。郭璞尽力在诗歌中将现实和想象的两重空间弥合起来,但是他又深知,这种理想化的认知心理空间只是暂时的安慰剂。在他见到粲然而笑的宓妃心生向往时,却只能感叹“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其二)诗人也深知,“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其四)“虽欲思灵化,龙津未易上。(其十七)不死之国难以到达,因为它本身就虚妄不实的。凡尘世俗之士想要最终长留仙国永游仙境只能梦寐以求。而一旦认真审视现实世界,又悲哀于“在世无千岁,命如秋叶蒂”(其十四),生命短暂,祸福难测。同时又悲愤于“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其五),抱负难施,丹心见弃。最终只能面向东逝之水“抚心独悲吒”(其四),对着凋零花木“零泪缘缨流”(其五)。现实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二者无法调和,诗人只能选择其一,却发现二者都无法安顿自身,二重空间再度分裂,最终看到一个欲仕不能、欲隐不忍、欲仙不得的痛苦灵魂顽强的抗争,及抗争失败后清醒的绝望!
四、结论
以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作品,相对来说更加客观。“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组合)与功能,是解读作品的主题、思想、情感、人物和艺术表现方式的重要手段。”[18]将郭璞《游仙诗》中的想象空间书写展示出来,则难以否认其“列仙之趣”,也能对郭璞的神仙道教思想有一定了解,完善郭璞的形象——一个笃厚又清醒的道教信奉者。将现实空间分析出来,则更好理解郭璞的《游仙诗》为何会有独特的艺术成就。从横向来看,其不同于当时“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溺乎玄风”之作,能“挺拔而为俊矣”[19];从纵向来看,其《游仙诗》在“列仙之趣”的传统主题中注入了“坎壈咏怀”的内容,加上对“游仙”题材的大量集中书写,使得游仙诗的写作发展到了顶峰,并对后来的同类题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成就的交叉点正在于其现实内容上。将心理空间解读出来,对郭璞的丰富情感有更深入真切的体验。
关于郭璞《游仙诗》的创作时间、创作动机也可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当然,《游仙诗》本身提供的相关信息非常有限,因此还得结合更多的文献展开研究,比如对郭璞本人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史书记载,郭璞其他的诗赋作品等,分析他的地理空间意识及其对《游仙诗》创作的影响,进而对其诗、其人、其时有更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