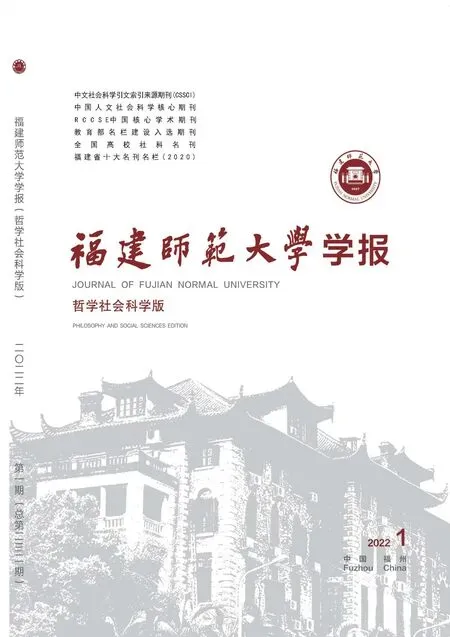从温和启蒙到激进启蒙
——阿伦·盖尔对生态文明出路的哲学考辨及其理论得失
陈 云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当代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Arran Gare)(1)阿伦·盖尔(Arran Gare)生于1948年,国际著名环境哲学家,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环境思想史、过程形而上学、复杂性理论、人类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盖尔著作等身,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自然情怀,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小约翰·B.柯布曾评价其为环境哲学领域中的“真正哲学家”(a true philosopher)。盖尔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非常关注,曾多次受邀到访北京、海南等地参加生态文明学术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引起了非同凡响。是国外为数不多对“生态文明”专门进行过哲学研究的学者,并非常看好“生态文明”这一美好愿景。他说:“我是生态文明的坚定支持者,我也相信生态文明应该被视为全球文明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我认为中国必然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2)陈云、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种大胆的哲学思考——澳大利亚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先生访谈》,《福建省哲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第37页。“生态文明使我们能够澄清文明的含义,使人们关注资本主义晚期的颓废与野蛮,并更清楚地设想对它的超越性……生态文明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愿景。”(3)Arran Gare,“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Vol.23,No.4, 2012,pp.10-26.更为难得的是,盖尔进一步从哲学的维度给出了他对生态文明未来出路的探寻,认为只有走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之路方可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盖尔究竟基于何种缘由开启了这条激进启蒙之路?为何温和启蒙(moderate enlightenment)在他看来不可行而激进启蒙则是一种好的选择?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这条道路的理论价值何在?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回答好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较为客观公允地对待某些西方“绿色”观点,从而更加科学全面地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之路。
一、哲学危机及其对大自然的威胁
全球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理论界正从多维视角探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出路。其中,盖尔将视线放在了一条哲学之路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哲学和哲学家是很自然的事情。”(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4、9、11、12.盖尔非常注重哲学对人类思维或价值观的启迪,期望能够将大自然纳入人类所关切的对象范围中,呵护大自然,从而实现“一种新的未来憧憬”(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4、9、11、12.,这里的未来憧憬指的就是生态文明。盖尔赞同美国哲学家大卫·亚伯兰(David Abram)的观点:“生态科学仍然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学科,主要局限于机械论生物学。如果没有哲学家的一致关注,生态科学就缺乏一种与其目标相适应的连贯的共同语言;因此,它就只不过是一些不断积累的事实与仇恨的碎片以及无法言传的梦幻罢了。”(6)David Abram,“Merleau-Ponty and the Voice of the Earth,” In D. Macauley ed.,Minding Nature:The Philosophers of Ecology,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6,p.82.从这个意义上看,哲学之于自然科学(例如生态科学)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哲学之于生态文明的未来憧憬更是不言而喻。
盖尔之所以这么注重以哲学的立场来审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探寻一种新的文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哲学能够破除支离破碎的思维形式,从而为人们综合理解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提供坚实基础,当然这里所讲的哲学主要是源于古希腊的传统哲学。盖尔说:“传统哲学家关注他们文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努力克服导致灾难的片面、支离破碎的思维形式,使人们能够在生活中的任何情况下都有意义,同时为他们提供创造未来的方法……根据古希腊的源头,哲学的目标就是为人们综合认识宇宙及其在其中的位置奠定基础,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这样的整体性理解来实现自身的终极目标。”(7)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4、9、11、12.换言之,具有某种哲学思辨的人能够充分理解宇宙中的人类角色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能够作出某种批判而又合乎理性的行动以实现人类健康生存和良好发展的美好愿景。然而遗憾的是,现时代的哲学却遭遇了危机,这里的危机在盖尔看来主要指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的流行所带来的现代哲学危机。盖尔认为,那些当初转向哲学以寻求应对生态危机出路的所谓哲学家们似乎变化了,他们将哲学推向了危机之中,“除了一些极少的例外,那些拥有大学所提供的特权条件来应对这一最大挑战的哲学家们,都对哲学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背弃道德、政治哲学甚至认识论,陶醉于哲学的无用之中。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结果中”(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4、9、11、12.。而“这种结果”即为哲学的危机或者说分析哲学的现代危机,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哲学理论只做纯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盖尔认为哲学的纯概念或语言研究会使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高高在上而蔑视其他一切哲学话语,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了对伦理、政治与社会的关心。二是哲学学科被技术科学牵引或宰制。盖尔认为英语世界的大学哲学学科被分割成了一系列高度技术性的专业,他们的实践者越来越多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哲学失去了人文色彩。当诸多大学面对政府的种种压力而要求设置以职业为导向的科目并增加技术教学的比重时,盖尔感慨于约翰·科汀汉(John Cottingham)的评论:“随着那些志存高远的哲学专业学生的愈加深入学习,他们的挫败感或失落感则接踵而至。”(9)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三是哲学本质遭遇了消极怀疑论的攻击。哲学的本质在于对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但是盖尔认为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家却“正在鼓吹一种使人堕落的消极怀疑论,他们甚至在诋毁和谴责专业哲学家或其他人对这种怀疑主义的任何质疑,这不仅削弱了哲学,而且还削弱了人文、艺术、大学、教育、民主和文明,以及人类应对当前所面临威胁的能力”(10)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总之,哲学陷入了一种理论概念化、学科技术化、本质消解化的现代困境,这导致哲学不是为“己”所误用(文字概念游戏),就是为权势所滥用,哲学正逐渐远离生活、疏离自然、淡化人文,一些哲学家似乎也正背弃伦理与政治哲学,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无法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无法参与权力中心者的议程,无法抵制并克服意义的分裂或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实现自我支配”。(11)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
处于这种危机中的现代哲学对大自然来说便是一种遗忘和威胁。一方面,盖尔认为分析哲学支持还原主义,注重分析思维,从而忽视了对大自然的意义理解。例如,盖尔对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家、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 (W. V. Quine)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蒯因哲学的“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本质上“意味着对还原主义的支持”(12)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揭示其认识论就是“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一种物理性的人类对象。这个对象被设置了某种可实验控制的输入……”(1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盖尔对蒯因观点的批判意在揭露分析哲学的还原主义倾向,指出其结果便是只注重物理作用的嵌入式解释,而不在乎语言或其他一切事物本身的意义理解,盖尔认为“这实际上就是通过简化为其他(如真理条件)来努力消除某种‘意义’”(1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显然,作为一种“意义”被消除了的哲学观念,在启迪人们深刻理解大自然内在价值或权利尊严层面注定成为一种奢望。另外,这种还原主义倾向从思维方法上看,注重的是一种原子主义、机械主义和物理主义的“零敲碎打”(piecemeal and in fragments)分析,他们“只专注于狭隘的主题和哲学的‘零敲碎打’,而回避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大问题’作描述”(1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这就忽视了在此之外充分利用宗教学、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对宇宙世界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这对于正确对待大自然这个有机整体来说是不利的。另一方面,盖尔认为分析哲学捍卫科学主义,盲崇技术科学,从而造成了对大自然的宰制和破坏。盖尔说:“我们现在拥有的‘技术科学’是由分析哲学家描绘和捍卫的科学,也是由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者所指导的科学。”(16)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意在表明,技术科学当前已沦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并被他们操控。盖尔指出,这种情况促成了那些利己主义、计算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崛起,而基于对技术科学的掌控或盲目滥用,大自然便遭受着严重的宰制和破坏,因为他们总是试图从中获得利润。盖尔以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的《政治的终结:企业权力和公共领域的衰落》(TheEndofPolitics:CorporatePowerandtheDeclineofthePublicSphere)为例,揭露了技术科学是如何为企业提供创造利润的手段从而攫取自然资源的。盖尔还以布鲁斯·查尔顿(Bruce Charlton)的《毋庸尝试:真科学的堕落》(NotEvenTrying:theCorruptionofRealScience)为例,指出一些科学家所研制的东西毫无用处,完全是一种资源浪费和对空间的占用。盖尔还指出,如果继续这样,那么“我们目前的道路将加速生态破坏,直到大规模的环境变化,例如失控的温室效应将导致一种生态系统向另一种生态系统转化,这将使人类在目前人口稠密的世界上几乎不可能生存,就像在纽芬兰岛周围过度捕捞鳕鱼所导致的鳕鱼的几乎灭绝一样”(17)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2、12、19、41、41、40、39、17、9.。
二、寻求生态文明的出路:从温和启蒙到激进启蒙的哲学考辨
既然大自然的种种问题来源于哲学危机,那么问题的解决必然要回归哲学而不是回避哲学。为了扭转上述局面并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即生态文明的未来,盖尔勾画了一条哲学的激进启蒙之路,认为只有“恢复激进启蒙和对自由的追求,在这个时代,人类将开始创造一个生态上可持续的文明,一种生态文明”(1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7,p.29、158、153、150、20.。然而,当前却存在一种与之相反的论调,即温和启蒙论。盖尔认为,唯有大胆揭露这种论调的缺陷方能避免误入歧途,并进一步彰显出激进启蒙之于生态文明未来出路的独特优势。所谓温和启蒙,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打着某种“启蒙”的幌子或掩盖着某种“真实”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或寻求生态危机化解之路的一种哲学论调,其实这种论调是在做无用功,它被认为在“同伴的世界中破坏了忠诚”(19)Josiah Royce,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 [1908], Nashville & Londo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5,p.56.,无法赢得环保人士的认可,也无法改善同这个世界的关系。
温和启蒙论表面上打着“启蒙”的幌子进行“环境”之思,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nihilism)。盖尔指出:“我把激进启蒙等同于‘真正的’启蒙,而把温和启蒙等同于‘虚假’启蒙。”(20)Arran Gare,“Reviving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rocess Philosophy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Franz Riffert and Hans Joachim Sander, eds.,Researching with Whitehead:System and Adventure,Freiburg/Muenchen:Verlag Karl Alber,2008,pp.25-28.温和启蒙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的未来并无实质的指导意义。盖尔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新自由主义温和启蒙论的虚假性揭露,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温和启蒙的复兴”(21)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7,p.29、158、153、150、20.,并“创造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22)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7,p.29、158、153、150、20.。盖尔指出,新自由主义打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旗号宣扬自然资源私有化及其市场化配置更能够解决资源浪费或环境破坏的问题,因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汲取了古典自由主义(如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道德约束成分而不至于“滥用私权”侵占资源,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资源合理配置或均衡发展”的市场化原则,能够在产权明确情况下使原先的环境成本外部性得到有效解决。对此,盖尔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假象。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已经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走向了极端,即极端的私有化、个体化和市场化并且强烈反对政府的干预或管控,其并没有参入古典自由主义的“道德情操”或其他值得称赞的东西,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必然是各种威胁和破坏,盖尔揭露新自由主义“不受约束的市场被主流经济学合法化,将财富集中在地区、国家和公司以及个人,直到它们破坏经济、腐化政治和破坏社区、耗尽储备、破坏资源和破坏生态系统”(2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7,p.29、158、153、150、20.。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应对生态危机诸多努力的失败,体现出了现代文明中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2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7,p.29、158、153、150、20.换言之,基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温和启蒙论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构建这一层面上最终是无法真实体现其启蒙意义的。
为什么温和启蒙论对生态环境的致思是虚假的?从温和启蒙论的哲学基础来看,可知其端倪。盖尔指出,温和启蒙论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机械论哲学(mechanical philosophy)基础之上的,而机械论哲学本质上却是占有式的控制自然或反生态的,“它不仅要支配自然,而且要创造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将被完全控制”,并认为本质上这就是一种“致力于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温和启蒙”。(2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盖尔阐明,机械论哲学是在马林·梅森、皮埃尔·伽桑狄、笛卡尔和霍布斯那里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关于人和自然的机械论哲学观,助长了占有式个人主义。这种机械的占有式个人主义也直接影响到了洛克和牛顿。盖尔指出,“从霍布斯到洛克就是占有式个人主义”(26)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在洛克和牛顿的启发下,温和启蒙致力于自然的技术统治和占有式个人主义,即理性地掌控世界”(27)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可见,机械论哲学的内在特点就是占有式个人主义,就是征服和宰制大自然。一些机械论哲学家曾非常反感“布鲁诺及其因热衷大自然带来的影响”,并指责布鲁诺是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之一”,(2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这显然表现出机械论哲学无视大自然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可知,温和启蒙论的根是机械论哲学,这种哲学主要是以占有式个人主义、支配自然和掌控世界为价值观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温和启蒙论再怎么打着“启蒙”的幌子来推进可持续性发展或寻求生态文明的出路显然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必须超越温和启蒙,要让激进启蒙出场并取而代之,正如盖尔进一步说:“在现代性中,有一种被压制的传统即‘激进启蒙’,它不是毫无作为的,它一直都在竭力反对原子主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所主导的‘温和启蒙’。”(29)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
温和启蒙论是建立在机械论哲学基础之上的,这就最终决定了温和启蒙论的人文精神必然是苍白无力的。霍布斯曾公开拒绝或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承诺要用一种基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来取代它;而笛卡尔更是基于身心二元论的立场,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性切除了自然物质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痕迹,使这个领域变成了没有生机而只有惰性的纯自然物质大块,它们之间进行着机械和野蛮的撞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建立在以功利、计算、宰制为特点的机械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温和启蒙论,它在人文主义的场域中显得何等的消极、自私甚至懦弱。盖尔明确指出,作为与激进启蒙相反的温和启蒙,“它对于维护自治、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建构完全是无力的”(30)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它只是“致力于占有欲的个人主义,捍卫宽容作为民主的弱替代品”(31)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而这恰恰显示出了“温和启蒙的原子主义以及对待生命和人性的堕落观”(32)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那么,为什么盖尔要揭露出温和启蒙论在人文精神层面的苍白与缺失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盖尔认为走向生态文明必须推动文化的转型,要重视人文科学和弘扬人文精神,这样“才能够塑造追求真理、正义和美的社会主体,能够重新审视和改变他们的文化和自身,从而改善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3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而相反,温和启蒙是难以做到这种文化转型的,因为其根基是机械论的,其内在基因是原子主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其在人文精神的弘扬层面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盖尔在其著作《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The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ManifestoforTheFuture)的第一章就事先交代:“恢复整个人文科学在智性和文化生活中的适当地位……恢复激进启蒙和对自由的追求……人类将开始创造一个生态上可持续的文明,一种生态文明。”(3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
通过对温和启蒙论的上述缺陷揭露,盖尔告诉我们,温和启蒙之于生态文明未来出路的诠释显然不可行,唯有实现启蒙的哲学转换,走一条激进启蒙之路方能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所谓激进启蒙,本质上就是指基于对温和启蒙论的超越而试图恢复的一种宏大叙事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盖尔说,“人们对这种温和启蒙的原子主义、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给予了反击,并共同捍卫自由和民主,致力于复兴一种人文主义和对自然的热情”,并认为这就是一种“激进启蒙”。(3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7、154、28、156、23、8、157、35、160、29、157.在现代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社会,盖尔曾发问:“我们究竟还需要人文吗?我们是否需要培养有人文精神的人?”(36)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其追问意图事实上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人文主义或精神的重视,从而能够正确引导人们去创造和欣赏最高的价值观,去思考如何选择人生中的目标,去组织何种有意义的生活,从而让自己明白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盖尔曾引述俄罗斯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的观点,认为人文主义本质上就是在研究人本身,就是在创造人性。“研究人本身也意味着创造人性;对人的每一次描述都是自我建构的事件。从整体的实践意义上讲,人文主义创造了人,因为人是通过对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而发生转变的:人因而有了人性。”(37)Mikhail Epstein,The Transformative Humanities:A Manifesto,New York:Bloomsbury,2012,p.7.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激进启蒙终归所言的就是要重拾过往所丢失的人性,呼吁每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正义和美的过程中能够以一种宏大叙事的人文视野去重新审视和改善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恢复一种“自然热情”(nature enthusiasm)(3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就此而言,较之于温和启蒙论的人文情怀缺失及其可能导致的对大自然漠视这一点来说,激进启蒙之于生态文明出路的叙事显然更具说服力。
当然,需进一步指出的是,盖尔所倡导的这种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激进启蒙并不是像温和启蒙论那样堂而皇之、虚情假意的,而是真正地从哲学意义上做了有力铺垫。其一,激进启蒙以过程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盖尔说:“过程形而上学,在中国思想的熏陶下,被证明是超越欧洲文明、创造环境上可持续的全球文明所必需的哲学。”(39)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怀特海过程哲学给我们展现了一副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活动过程、一切有机体都是进化着的以及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活生生的画面。盖尔指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本质强调宇宙世界的有机性和融贯性(coherence),其能够为激进启蒙提供整体意义上的人文叙事框架,从而超越以往哲学的碎片化或独占式个体主义思维方式。怀特海曾说,“作为计划所依据的基本思想,彼此假定,彼此孤立,便毫无意义”(40)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1929],New York:Free Press,1978,p.3.,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要“建立一个融贯、合乎逻辑和必要的一般性思想体系,从而使我们经验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根据这一体系得到解释”(41)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1929],New York:Free Press,1978,p.3.。因此,盖尔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激进启蒙“提供了最好的整体描述和辩护”(42)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从这个意义上看,怀特海过程哲学内蕴着究竟如何理解和描述整个宇宙系统的哲学特质,因此在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一层面上,建立在过程哲学基础之上的激进启蒙显然更优于温和启蒙,因为温和启蒙建立在机械论哲学基础之上,呈现的是一种二元论立场。其二,激进启蒙以恢复政治和伦理作为哲学内核。盖尔认同:“政治和伦理是而且一直都是人文主义的核心。”(4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然而,温和启蒙论基本都丢掉了政治和伦理,他们有的只是控制与被控制以及占有式个体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例如,盖尔曾批判了梅森、伽桑狄、笛卡尔和霍布斯对自由和民主的曲解,谴责了洛克和牛顿对大自然支配和控制的观点,也揭露了弗雷德里克·泰罗的“科学管理”或“泰勒主义”对人的控制以及对大自然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等。“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恢复和重新思考政治和伦理。”(4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当然,这里的恢复和重新思考之路在盖尔看来便是要回到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要恢复这一点,首先需要回到历史。正是在这里,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最重要工作已经并正在进行……这些人确实在为另一次复兴而奋斗,以恢复和重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4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6、157、20、116、155、154、155-157.盖尔这里所讲的“回到历史”说的就是要回到古希腊以寻求城邦民主、善、共同利益、正义以及美德,也要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寻求价值与尊严等,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复杂多变的世界秩序中重塑一种人文精神。其三,激进启蒙以“思辨自然主义”(speculative naturalism)作为哲学形态。激进启蒙何以可能?盖尔紧接着提出要“通过思辨自然主义复兴激进启蒙”(46)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4、5-6、166.。思辨自然主义是一种“在基本立场上坚持自然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思辨性,在哲学方法上强调辩证法,在运作路径上发展假说性以及在价值旨趣上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哲学价值观,其倡导以人文科学复兴生态启蒙、以宇宙的自我创造性提升生命感知、以“对话式辩证法”建构良好的生态政治、以“美”的有效假说塑造人们的环境美德以及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理解整个宇宙生态系统等。(47)关于“思辨自然主义”等相关问题,详见陈云:《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阿伦·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44-153页。盖尔之所以提出“思辨自然主义”这一创新性概念,目的就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并拓展人文主义的跨界视野,在范围上要辐射生态学、生态符号学与人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乃至数学以及其他技术科学等,他说:“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克服这种支离破碎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文明奠定基础。”(4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4、5-6、166.显然,思辨自然主义所蕴含或折射的人文主义色彩更具宏大叙事性和针对性,它能够以学科的跨界整合或审视从而更加顾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多样化关系,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盖尔提出要通过思辨自然主义来复兴激进启蒙。所以,盖尔最终指出,在思辨自然主义的哲学推动下,“这种激进启蒙更能够置人类于自我创造的历史环境中走向一个新的文明”(49)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44、5-6、166.,即生态文明。
三、激进启蒙之于生态文明出路的理论得失
生态文明路在何方?立足哲学视域,盖尔向我们开辟了一条激进启蒙之路。这条道路主要沿着哲学的意义(价值观铸模作用)→哲学的危机(分析哲学的负面效应)→哲学的救赎(温和启蒙与激进启蒙的博弈)这一线索加以展开,旨在表达一种以过程哲学为基础,以恢复古希腊的政治和伦理为内核,以思辨自然主义为形态的人文主义精神,弘扬这种精神需要学科跨界与宏大叙事,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的“零敲碎打”(piecemeal and in fragments)思维或技术行话(technical Jargon)(50)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p.272.现象,从而真正实现文化的转型,为走向生态文明铺平道路。
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之于一种文明形式(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从人类文明或社会进步的跃迁过程来看,哲学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例如,马克思通过对比分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时代发展脉象,以一种“原则高度”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扬弃了旧哲学的市民社会基础,开启了以“实践”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或新唯物主义,而其立脚点便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这种社会是代表着全人类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论著为中国的革命和文明重建提供了可行方案,指明了前进道路。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看家本领,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哲学智慧。正如习近平所言:“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5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可见,哲学在任何文明时代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式,一种真正的哲学启蒙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盖尔从哲学的维度所探寻的这条生态文明激进启蒙之路已然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之于一种文明形式(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例如,盖尔认同怀特海所言的“哲学是思想和生活的根本基础……它塑造了我们的文明形式”(53)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New York :Free Press,1938,p.63.这句话,并进一步指出了“在过去,哲学在文明形成中一直居于核心位置”(5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5.这一重要观点。那么,为什么哲学有这样一种塑造文明形式的功能或地位?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哲学具有思辨性和批判性的双重特质。按照盖尔的观点,思辨性揭示的是一种融贯性思维,批判性表明的是一种质疑性态度。盖尔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对于人在宇宙中的伦理普遍性以及人与大自然内在关系的思考最为深刻,而现代西方哲学(分析哲学)却把这一点丢了,哲学家们都专注于冷冰冰的语言分析,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机甚至是危机重重。所以,这就必须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大胆质疑以往的种种假设和规定,为人类新型文明(生态文明)的铸造开辟道路,这是哲学应该做而且也能够做到的,盖尔为此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即“思辨自然主义”,认为这是铸造生态文明的“一种好的哲学”(55)陈云、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种大胆的哲学思考——澳大利亚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先生访谈》,《福建省哲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第38、4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之于一种文明形式(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而盖尔所探寻的这条激进启蒙之路有力彰显了哲学的时代地位和重要价值,这一点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人文主义之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诠释意义。探寻生态文明的未来之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正确把握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210页。又称:“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210页。由此可知,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与大自然同根同源共属于一个整体,更是一种对象性自然存在物,与大自然相互依赖而共生共荣。换言之,人与自然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呈现出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0页。那么,就盖尔所论及的激进启蒙之路而言,事实上其以一种宏大叙事的人文主义深化了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进一步诠释,明确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整体性关系,揭示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我、善待自然就是善待生命本身的深刻内涵。正如盖尔说:“人们不应把自己视为自然之外的人,而应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生命的意义。”(59)陈云、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种大胆的哲学思考——澳大利亚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先生访谈》,《福建省哲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第38、42页。盖尔通过对分析哲学的批判告诉我们哲学不能“遗忘自然”,对待大自然要有“温度”而不是“冰度”,通过对温和启蒙的批判告诉我们哲学不能“虚情假意”,对待大自然要摒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要释放“自然热情”。盖尔还提出必须破除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零敲碎打”思维,要以思辨自然主义来拓展对大自然得以充分理解的整体性跨界视野,大自然不应轻易沦为科学技术的宰制对象,而应成为各种人文学科所诠释和观照的对象。对此,盖尔通过考察英国哲学家C.D.布劳德(C. D. Broad)所提出的思辨哲学方法即“分析(analysis)—提炼(归纳)(synopsis)—综合(synthesis)”,进一步强调要从人类经验的多重领域以及生态学、社会学、美学和宗教学等多维人文视角去整体把握这个宇宙世界的本质,并且定位好人类自身在其中的正确位置,由此而形成一种能够公平对待宇宙万物的整体实在观(A view of Reality as a whole)(60)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33、3.。很明显,盖尔提出的这条激进启蒙之路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共同体意蕴及其价值观诉求,其以一种人文主义的叙事方式深刻诠释着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性和生命共融性,对于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盖尔的激进启蒙之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虽有着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但其理论旨趣亦蕴藏着某些风险。
其一,去政治化倾向。探寻生态文明的出路,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盖尔认为其中的“病因”是一种哲学危机(或社会文化危机)(61)陈云、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种大胆的哲学思考——澳大利亚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先生访谈》,《福建省哲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第38页。,并由此开出了从哲学危机到哲学救赎的激进启蒙之“药方”。不可否认,从上文相关内容来看,盖尔的“哲学危机”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似乎也存在一个不足,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其并没有直击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性问题(原因或许是基于一种无奈(62)盖尔曾指责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激进分子所领导的最激烈的环境政治运动也只是一些抗议呐喊而已,他们对未来美好愿景并没有任何设想和规划,且即使这些人获得了权力,最终也会被他们随意糟蹋。因为在盖尔看来,任何资本主义政党当权,他们贯彻的都是相同的政策,诸如过度市场化、倡导管理主义、贩卖公共财产、削弱公共安全并以新技术取代工人、对富豪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等等。盖尔认为,一般的常识无法理解这些,而只有哲学才能为此提供有力诠释和有效出路。详见: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p.2-3.),因而其对生态文明未来之路的探寻多少也呈现出了一种去政治化倾向。盖尔有言:“如果常识不够充分,那么除非人们像许多人一样接受非政治化,否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学者来提供更好的解释方案。”(6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33、3.换言之,要从政治层面审视生态危机的根源显得有些恍惚,而要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来探寻生态文明之路更是一件难事,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哲学或哲学学者的诊治之中。其实,生态文明是一个有着明显意识形态属性的关键词,它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体系,对生态危机的溯源终究不宜作去政治化的诠释,否则对生态文明未来之路的探寻必将缺乏现实基础或实践可能性。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政治化内涵,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增殖,而在增殖这一原则下,资本家将以追求利润为中心而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攫取和占有各种资源,从而引发马克思所言的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所以,马克思进而指出,要真正复活自然,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要革除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对于盖尔的观点,无论是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究还是生态文明出路的探寻,其走的似乎只是一条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重构路径,结果到最后我们也没发现这条生态文明激进启蒙之路到底该如何操作,正如其自己亦言:“要找到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还有一定难度,我们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64)陈云、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种大胆的哲学思考——澳大利亚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先生访谈》,《福建省哲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第38页。哲学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在此我们无意淡化哲学,而是说对于有着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态文明,我们要将哲学落地,要着眼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现实去直击生态危机的根源,寻求生态文明的出路。
其二,伦理至上主义。盖尔认为,寻求生态文明的出路应该倡导一种人文主义,要关爱他者、关爱自然。对此,在探寻生态文明的激进启蒙之路上,盖尔给出了政治和伦理这两个维度的人文指向,然而遗憾的是,盖尔似乎更加强调政治之于伦理的依赖性,更加凸显伦理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当盖尔讲到政治与伦理是作为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核时,他又说“政治却总是与伦理联系在一起的……”(65)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4、155、163、210、199.,言下之意便是讲政治(如民主、自治、自由等)必然离不开伦理(如美德、正义、善等),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盖尔在具体探讨如何担负起倡导人文主义的哲学使命时,一种伦理至上主义的倾向就表现出来了。从理论层面看,在论及恢复古希腊城邦民主和共同利益时,盖尔提出:“这种历史工作仅仅是为了恢复非常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思想,如作为亚里士多德第一原则的伦理政治假定,如果没有这个指引,人们只不过是在各说各话。”(66)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4、155、163、210、199.在论及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理性或自由意志时,盖尔汲取了“最终要通过参与伦理和文化生活而获得普遍性”(67)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4、155、163、210、199.这一重要观点。而从现实层面看,当盖尔提出如何才能打造一个摆脱奴役的、自治的生态社区时,他捍卫了一种美德伦理。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想改善生活,那么在参与社区的治理、政策制定以及从事其他工作时必须要获得对整体的感觉,这是支撑其他美德的终极美德。”(68)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4、155、163、210、199.又称:“而归根结底,其问题便是要定义和塑造所需要的美德,以创造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从而增强生态系统和社区的生命……。”(69)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154、155、163、210、199.很明显,盖尔过于抬高了伦理的地位,给人的感觉便是生态文明的激进启蒙之路似乎就是走一条伦理之路,这或许与盖尔之前所言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哲学危机有关。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够科学的,正如J.B.福斯特(J. B. Foster)所言:“这种道德改革的呼吁对于我们社会的核心体制,即所谓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treadmill of production)常常视而不见。”(70)J. B. 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44.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要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靠伦理呼吁是行不通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从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这也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同样,在当今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未来如果单纯依赖伦理道德显然也是不够全面的,它必须多管齐下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协同作用。
其三,宗教神学困境。在寻求生态文明的激进启蒙之路上,从哲学危机的批判到哲学救赎的展开,这条路走到最后很可能会陷入宗教神学的困境(即便盖尔曾表示避谈有神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激进启蒙是建立在怀特海过程哲学基础之上的,而怀特海过程哲学本身就裹挟着宗教神学的特质。过程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一切现实性的有机联系以及动态变化,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现实性在怀特海看来却来自上帝,正如其所言:“实在世界是选择的结果,最终决定这一选择的是上帝。上帝把限制施于无限多的可能世界,才使这个唯一的世界得以实际产生。所以上帝是现实性的源泉。”(7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哲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怀特海甚至还说:“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伟大的挚友——相互理解、患难与共的挚友。”(72)[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30页。因此,从逻辑起点上看,建立在过程哲学基础上的激进启蒙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宗教神学或上帝的笼罩和主宰。事实上,当盖尔在具体铺展这一激进启蒙之路时,一种宗教神学化倾向确实体现出来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盖尔在激进启蒙之路背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体系即思辨自然主义,并以此作为复兴激进启蒙的推动力。思辨自然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讲求宏大叙事性,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宏大叙事性却给激进启蒙之路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在盖尔看来:“寻求这样一种能够激励人们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宏大叙事,需要一个宗教的维度,这证明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把全球生态系统命名为‘盖娅’以及过程哲学家努力使科学返魅是合理的。”(73)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209、172.盖尔认为洛夫洛克所提出的“盖娅假说”非常必要且十分合理,因为他给我们呈现出的正是一个作为“超级有机体”的大地之神,这对于人们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视野去看待大自然并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觉”(feel for the whole)具有重要的生态启蒙意义。因此,盖尔最后给出结论:“宗教也将是创造生态文明的核心……而思辨自然主义澄清和推进了这一追求。”(74)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7,p.209、172.我们不否认,一种宗教信仰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变得更加体恤和关爱大自然,但要知道,激进启蒙一旦真的走向宗教神学的人文救赎,无论其如何为自己的良好初衷作辩护,到最后注定是反理性、反科学的,这对于生态文明的未来之路来说显然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关于生态文明出路的探索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甚至跨时代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从哲学的维度诠释生态危机的根源、探寻生态文明的出路属于其中一个视角。盖尔给我们展现了一条从温和启蒙到激进启蒙的哲学考辨之路。他深刻批判了温和启蒙的“绿色”虚假性或误导性,重新建构了一条激进启蒙之路,旨在通过恢复或倡导一种宏大叙事的人文主义或精神来推动文化的转型,为生态文明的未来之路奠定基础或扫除障碍。不言而喻,这一哲学维度的探讨凸显了极其深刻的启发性意义,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就科学而全面地研判生态文明的未来之路而言,对这一理论探讨甚至其他西方“绿色”观点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谨慎或理性态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生态相协同、生态哲学与政治生态相统一、生态美德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应是探寻生态文明未来之路需要总体把握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