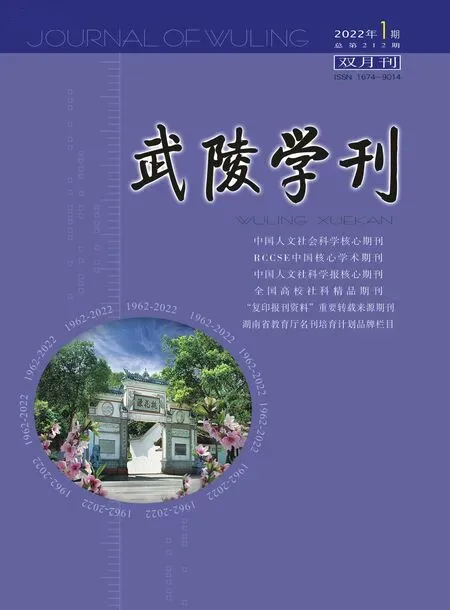《时间的噪音》中肖斯塔科维奇懦夫形象及其成因
罗海燕,王桃花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作为一位具有很强历史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这样谈论自己的写作:“我的小说通常从一种情境开始,可能是一个道德上的失误,然后,我问,下面会发生什么。”[1]245《时间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2016)这部小说主要围绕肖斯塔科维奇(以下简称肖氏)选择成为“懦夫”的人生经历展开。他究竟是被迫向当局妥协,还是主动成为“懦夫”?在肖氏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其争论不休。有些评论者认为是因为主人公肖氏生活在“政治阴影下”[2];也有人认为社会对肖氏实行双重道德标准,评论者不愿意把“英雄”一词用在肖氏身上,因而才认为他是一个懦夫[3]。此外,在有些评论者看来,这是一部“探索压抑和反抗的作品”[4],它“描绘了肖氏作为作曲家对正直的渴望和他对生存的本能之间的冲突”[5],并非单纯的“懦夫”。总之,这些评论几乎都聚焦于肖氏成为“懦夫”的外部因素,却忽视了从肖氏主体层面探究造成其成为“懦夫”的内部因素。
“懦夫”,中文含义为怯弱、软弱无能之人[6],反义词是强者或英雄。“懦夫”的英文单词为coward,译为胆小者,胆怯者[7],实际上,这个意义就是一个常规的道德性定义。肖氏的爱情、亲情、政治的伦理选择看起来都是“懦弱”的,但又是复杂的,之所以出现英雄与怯懦的争议是因为现代伦理范畴无法简单地概括肖氏的形象。
在后现代社会中,旧的伦理体系不足以解释人们的伦理选择。鲍曼认为,后现代伦理必须拒绝许多被认为是现代伦理的东西,如后现代伦理必须拒绝强制性规定之类的东西,拒绝寻求普遍性和绝对性之类的东西[8]243。后现代伦理不是抛弃道德,“而是反对现代规范伦理,主张将人从外在的伦理权威中解放出来,唤醒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道德良知”[9]。从后现代伦理的角度来看,道德规范充满了犹豫不决和矛盾,唯一的终极伦理权威在于个人的主体性[8]243-244。个人的主体性在解释婚恋伦理、代际伦理、政治伦理等方面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婚恋伦理中,个人的主体性可以加深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在代际伦理中,个人的主体性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亲情;在政治伦理中,“主体为自由——即摆脱武断和统治、达到自决和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奠定基础”[10]。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后现代伦理角度来探讨肖氏的婚恋伦理、代际伦理和政治伦理,审视其成为“懦夫”的主体因素,进一步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后现代伦理关怀。
一、颠覆传统爱情的婚恋伦理
后现代社会是个令人不安的世界,人们有充分的道德选择,但他们没有一个总体道德准则的指引。后现代伦理学家认为,“人不应受制于各种‘权力’的支配,人应该从各种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11]。后现代伦理旨在超越现代伦理,强调个人主体的觉醒。在爱情和婚姻中,人们更加注重自我感受,而不是为了繁衍、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而结婚。后现代爱情与个人主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个人情感不希望受到传统道德规范的控制和约束,试图摆脱社会强制规范的桎梏。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理性束缚,重视感性、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爱情中更是如此,他们强烈地相信直观和想象力。鲍曼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从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12]24正因为如此,巴恩斯笔下的肖氏不断探索和追寻爱情的奥秘。就婚恋伦理而言,《时间的噪音》主要通过描写肖氏的几段恋爱经历来揭示他甘愿成为“懦夫”的复杂心态,以颠覆传统爱情的婚恋伦理。肖氏不断寻求真正的爱情,“他试着让思绪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脑子不听话……它落在了塔尼娅身上……然后它又嗡嗡嗡跑到了另一个女孩身上,那是罗扎利娅”[1]10。塔尼娅是肖氏的第一个爱人,罗扎利娅是他差点与之结婚的一个妓女,最后几经波折之后,妮塔成为了他的妻子。肖氏反叛传统禁欲主义道德的爱情轨迹,挑战传统社会婚姻体制对男女生活的束缚,都显示出现实道德与主体生命感的紧张和冲突。
(一)反叛传统禁欲主义道德的爱情轨迹
在后现代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被破坏,人们喜欢尽情享受当下,拥抱前所未有的自由。肖氏认为“你应该这样去爱,没有恐惧,没有障碍,不用去想明天。然后,之后没有遗憾”[1]44。肖氏打破了传统的以生育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爱情,“将自由恋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一开始是和塔尼娅,然后是和妮塔。事实上,是同时和她俩”[1]67。当肖氏摆脱传统爱情的束缚,同时又面临无数爱情机会时,伦理选择也许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后现代社会人们强调即时体验,不考虑过去和未来。
肖氏在爱情中总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发现爱情“会让他难为情,让他为难”[1]41。和女人在一起时,他会在殷勤可笑和犹豫沮丧间摇摆不定,他总是踩错点,因为“爱是感觉,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对于这种主观的东西,统一无能为力”[13]200。肖氏对自由爱情的看法是:“女人也完全有权追求外遇,只要她想,而如果她之后想离婚,男人必须接受,承担责任。”[1]21这就为后来他妻子的出轨埋下了伏笔,这是他追求自由爱情的代价,因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13]201。恋爱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巴恩斯在小说中将肖氏的爱情和婚姻置于艰难的道德选择中,以此来反映人们在追求后现代爱情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性和道德普遍性,充满了不确定性。
肖氏追求自我解放的爱情。他喜欢塔尼娅,认为自己和她是天生一对、命中注定的恋人,因为两人同岁,生日分别是新历和旧历的9月25日。遭到母亲反对后,他们仍在高加索像夫妻那样生活了一段时间。肖氏通过多种手段想要赢得塔尼娅全部的爱,“他试图惹她嫉妒,描绘和其他女人的调情……他还威胁要自杀”[1]41。结果塔尼娅对肖氏以死相逼的爱情置之不理,她和别人结婚了,她扼杀了他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期待和希望。罗素认为:“一个感到不为人爱的人……为了赢得情爱,他也许会不遗余力,做出异常亲善的举动,然而,这么做,他很可能是白费力气,因为这亲善的动机很容易让其受益者识破。”[14]肖氏对塔尼娅这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为他后来不幸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伏笔。
在后现代社会中,鲍曼指出,“人类的现实是杂乱的和模糊的——因此,不像抽象的伦理原理,道德决断也是摇摆不定的”[12]37。与传统恋爱观相比,后现代恋爱更强调双方关系是相互促进、提高的过程。爱情伦理关系到两个人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各人持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信念。作为恋爱双方,肖氏和塔尼娅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并不平等。肖氏对塔尼娅主动奉献自己的热情,希望博得她的好感以确认自己的价值。而塔尼娅享受着对方的服务,没有对他的付出作出应有的回应。这种爱情关系变得碎片化,而且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折射出肖氏在后现代社会追求婚姻幸福的艰难历程。
(二)挑战传统社会婚姻体制对男女生活的束缚
肖氏的婚姻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讽刺意味。肖氏和妮塔选择秘密结婚,没有经过传统婚姻的媒人介绍,也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因为性格内向,肖氏被充满活力的妮塔所吸引,她“是如此满怀欢乐,如此充满生命力,如此外向,身体如此令人赏心悦目”[1]176。但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且也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因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很容易出现第三者。一个叫做A.的男子经常开着别克车带妮塔出去兜风。小说通过镶嵌一个莫泊桑小说中的婚外情故事来展示肖氏的心灵创伤,解开他痛苦、迷茫、无奈的内心世界,表达巴恩斯对他的深切同情和伦理关怀。肖氏“努力做到最好,男人能做的只有这个”[1]176。努力维持着婚姻的他逐渐变得麻木,在无奈和痛苦下,“他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之中,这占据了他全部的注意力”[1]176。肖氏的婚姻是不健全的,缺乏忠贞的爱情基础导致他妻子妮塔出轨,使肖氏陷入婚姻的伦理困境。
幸福的婚姻需要双方维护,然而,肖氏的妻子妮塔在兽性因子的驱动下与情人A.在亚美尼亚约会,她忘记了自己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成为了婚外情人。但妮塔并未觉得自己背叛了婚姻和家庭,也没有顾及自己对肖氏和子女造成的情感伤害。在肖氏问她是否会离开他时,她笑着回答:“不会,除非A.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得了诺贝尔奖”[1]177。妮塔的笑显示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更不用说忏悔了。作为妻子,她本应该尽到相应的伦理义务,然而书中却这样写到,“妮塔不适合家庭生活。无论气质上,还是习性上”[1]176。妮塔自由恋爱的权利让肖氏陷入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他选择尊重妻子的决定,因为他认为妻子有追求自己真爱的权利。
肖氏选择成为“懦夫”,因为他的自我认知和外在形象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他人的凝视当中,他是苏联大使、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主席,但在他自我意识中,他认为自己有很多值得谴责的地方:“疏忽之举、不合格的行为、喜欢妥协”[1]190,因而“厌恶自己,几近崩溃”[1]171。肖氏备受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作为一位作曲家,肖氏极其渴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可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权力的傀儡,接受了政府给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他渴望在生活中得到理解,特别是伴侣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容忍妻子妮塔的不忠行为,因为她是“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保护者”[1]182。这正体现出后现代伦理的道德价值处于不断分化状态,也说明后现代爱情是以包容为主的多元爱情。在后现代社会,人们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同时也面临一些违背伦理的道德选择,如肖氏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小说呈现了肖氏追求自由爱情背后精神缺失的伦理困境。
在传统伦理观念下,忍受妻子的出轨就是一种懦夫行为,而肖氏的这种懦夫行为却是他后现代伦理观念选择的结果,因为后现代伦理注重个体的自由选择。无论在爱情,还是婚姻当中,肖氏都可以做到尊重他者,容忍差异,尊重女性的自由选择,这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伦理的包容性,也反映了后现代伦理更加注重个人自我主体的确立。现代伦理强制个体符合道德规范,要求人们在正确与不正确之间做出选择,后现代伦理对现代伦理持批判态度,把个体的自发行为看成是真正的道德行为[15]441。巴恩斯通过展示后现代语境下肖氏颠覆传统的爱情和婚姻体验表明,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之中,传统的婚恋观念被解构,人们渴望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享受人性的自由。
二、突破母性桎梏的代际伦理
现代伦理认为人类道德的模糊性是不健康的,把人类目标的多元化看成是一种挑战,“道德哲学家把努力的目标定为减少多元性和驱逐道德上的双重标准”[12]25。对此,后现代伦理试图寻求一种新的突破口,因为“现在的个体不再是偶然出生所铸造的不可改变之模型,也不再被偶然赋予的狭隘人性所限制”[12]25。“后现代的人们对道德多元和相对道德需求旺盛,既要有归属感,也要有自我的空间。”[16]人们更加注重按照自我的意愿成长,强调自我发展。有评论者认为,巴恩斯对肖氏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肖氏是一个胆小怯弱的男孩,容易急躁,在其生活中,强势的女性一直在指导他的生活,肖氏母亲为他“掌舵”,而他只能进行“空洞的威胁”[17]。肖氏因为受到母亲的过多束缚,自我被遮蔽、被弱化、被低估,呈现出“懦弱”的形象,但经过时间的磨练,他试图突破母性的桎梏,不断克服自我认同的焦虑,从而引发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童年时期陷入自我认同焦虑
童年时期的个体一般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自我被遮蔽、弱化和低估,而且处于社会和家庭权力的边缘。小说中肖氏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对代际伦理问题的思考。由于肖氏的父亲是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肖氏的母亲便拥有家庭的权威,成为家庭的引导者、保护者和支持者。在诺曼·N.霍兰德看来,孩子除了受父母亲、环境或社会的影响,一个积极主动的孩子会昂首阔步地穿越由他自己的生物性、他的双亲以及他们所体现的社会与环境结构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会对自己家庭所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18]。肖氏意识到母亲对自己管制过严,他努力消除或减少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小时候他曾威胁母亲要离家出走和勤杂工住在一起。在他逃离的时候,他母亲抓着他的手朝他说的地方走去,“但慢慢的,他的步伐迟疑了,他的手腕,然后是手,开始从母亲的手里溜脱出来……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他泪如泉涌,跑回了家”[1]16。可以看出,在肖氏的成长道路上,他母亲对他影响至深,即便身体可以逃脱,他的精神也和母亲绑在一起。他的家庭伦理概念与他母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代际伦理叙事中,作者提倡儿女拥有自由选择的精神。肖氏的母亲强势而严厉,对他的爱情和事业都经常干预,导致他缺乏自我认同。肖氏的母亲送他去学钢琴,希望他将来可以支撑起整个家庭,然而,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提出愿意赞助肖氏的职业发展、建议搬到莫斯科时,肖氏的母亲极力反对,因为她一直认为儿子很弱小。肖氏的母亲“保护了他,为了他工作,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1]29。在肖氏的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导致他过于依赖母亲,这不利于他独立自主地发展。父亲去世之后,肖氏的母亲试图维护代际伦理秩序的权威角色,显得冷漠甚至不通人情,掌握着肖氏灵魂的钥匙。虽然儿时的肖氏陷入自我认同的焦虑,但由于童年时期的伦理道德观还具有可塑性,这为肖氏多元化价值选择提供了空间,也有助于后来他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成年后自我意识的觉醒
随着年龄的增长,肖氏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他有了新的伦理观念,不再对母亲唯命是从,敢于违抗母亲的命令。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代际差异,代际冲突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肖氏挑战母亲的权威,但母亲经常看他的日记,发现儿子在日记里写着要“自杀”或“结婚”这样的词时,用她自己的方式恐吓:“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1]30在理想的情况下,“母亲应该鼓励孩子逐渐独立并最终与她分离,而且这种态度应成为她的生活的必要成分”[19],显然肖氏的母亲没有这种达观的态度,冲突也就再所难免。
当爱情和亲情发生冲突时,肖氏毅然选择了爱情。在母亲要求前女友塔尼娅滚出去时,肖氏公然反抗她的母亲:“不,我要塔尼娅留在这里。”[1]40后来他又瞒着母亲,私下和妮塔结婚。肖氏没有和母亲商量,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反映出他突破母性桎梏,追求爱情至上的后现代理念。可以看出,除了婚姻观念上的改变,肖氏的代际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有人认为小说中一些场景展现出肖氏的懦弱[20],肖氏从小听从母亲的安排显得畏缩是肖氏的懦夫行为,表现了他处于逃避现实的懦弱姿态。父亲的不谙世事和母亲的专制权威使得家庭伦理失序。长期忍受身体和精神上双重压迫的肖氏尽管力量弱小,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对母亲的权威进行了反抗。肖氏的反抗不是简单的逆反心理,而是为了拥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意识到如果自己还一直听从母亲的安排,他将逐渐失去自我。肖氏怀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努力获得个人自由,找回自己的主体性。无论是父亲榜样的丧失,还是对母性桎梏的质疑,都体现出家庭伦理秩序的混乱,也揭示出肖氏要以强硬的姿态突破母性的桎梏,解构家长的权威。
三、反对黑暗统治的政治伦理
《时间的噪音》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既讽刺当时的集权社会,也体现巴恩斯呼唤尊重生命、坚持正义的崇高政治伦理思想。在采访过程中,巴恩斯表达了对肖氏的看法:“他向当局妥协,最终保住了他的家人,保住了他的音乐,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1]238有学者认为,巴恩斯并没有回答关于肖氏多大程度上屈服于权力的问题,而是让这些不确定的问题助长肖氏的自我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让肖氏不断折磨自己,因为他是体制内的懦夫[21]。肖氏面对权力威胁时所体现的政治伦理,很值得读者关注。政治伦理可以包括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政治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品质[22]。肖氏通过音乐表达人道主义关怀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尽管他处于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
(一)通过音乐表达人道主义关怀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小说中纷繁复杂的人道主义政治伦理观和肖氏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存在,提倡以仁爱的精神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伦理观。“人道主义是一种道德精神……人道主义……对人性是疏导而不是压抑。”[23]肖氏“把所有残存的勇气放进了音乐,把怯懦放进了生活”[1]197。肖氏的音乐被认为“不讲政治、杂乱无章”[1]34。当局通过《真理报》发表了对肖氏音乐的评论:“混乱取代了音乐”[1]33,这是“一份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声明”[1]36。肖氏的《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是一部关于和平与战争主题的作品。肖氏的音乐表达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残酷战争的谴责,“渗透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24]。肖氏用音乐来表达他对人性的伦理关怀,“我们举不出当代任何其它的交响乐作品是起了这样巨大的思想作用和政治作用的”[25]。
由于出色的音乐才能,肖氏被任命为俄国作曲家协会主席,但他不想和政治有所联系。他鼓起勇气百般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我真的一无是处,非常不适合。我缺乏政治素质”[1]191。这是他内心独白的体现,但当局一次次地紧追不舍,直到最后肖氏迫于无奈而不得不接受这个政治命令。当时肖氏被政治代表人物帕斯佩洛夫穷追不舍,“这个人甚至停留在他(肖氏)梦里,永远在用平静、然而会让他发疯的声音在说话”[1]194。肖氏认为这就是命运,“人无法逃避命运”[1]197。由此可见,当时肖氏不得不被迫卷入这种政治生活。正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言,“暴力存在于一切似乎是孤独行事的一切行为之中……暴力也是我们不曾合作而忍受的一切行为”[26]。肖氏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暴力被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在评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历史剧《包里斯·戈杜诺夫》时,肖氏表达了对伦理的看法:“我总觉得《包里斯》的伦理基础是我自己的。作者以不妥协的态度谴责一个反人民的政府的无道德,这个政府必然是犯罪的,甚至在犯罪时丝毫无动于衷,它从内部腐烂,尤其令人厌恶的是它隐藏在人民的名义之下。”[27]《包里斯》这部剧表达了遭受苦难的人们与腐败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暗示肖氏一直处在政治的旋涡中。
由于政治原因,肖氏的音乐远远被低估,实际上他的音乐有着很强的创新精神和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然而有学者认为“肖氏不愿意在音乐上挑战当时的政权,即使他本可以在没有不合理风险的情况下这样做。……他是一个懦夫”[28]。他们认为巴恩斯试图把肖氏描写为一位“试图不出卖自己灵魂的艺术家,但没有成功”[21]。也就是说,肖氏在很多人眼中是个懦夫的形象。事实上,肖氏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就算他们砍掉我的双手,我也要口衔钢笔继续创作”[1]60。他敢于为犹太人写作交响曲,讽刺纳粹国家。表面上他是作曲家,内心里他却是一个不屈服于现实的知识分子。肖氏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充满了暴力和不确定性,知识分子被边缘化,肖氏无法遵从自己内心的理想而公开摇旗呐喊,只能通过音乐来戏谑当权者的残暴统治。他的音乐是一种理性的曲线表达,既明晰又隐晦,没有明说但意已尽。“肖氏显然站在党派路线的同时创作了杰作……作为一名苏联作曲家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音乐比其他形式的人类表达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是正确的。”[29]肖氏通过音乐表达政治伦理价值观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
(二)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
政治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治的实施越是强大……凝聚力和共同体越是遭到破坏”[30]124。肖氏通过政治妥协的方式寻求生存和尊严给读者带来深刻的触动和启示,他很难在政治生活中遵循内心的道德准则,“权力羞辱了他,夺走了他的生计,命令他忏悔。权力告诉他怎样工作,怎样生活”[1]54。
肖氏越善良老实、言听计从,权力越狡猾地利用他来为政治服务。“只要绝对主权的民族国家存在一天,我们就不得不做出妥协。”[30]128巴恩斯把肖氏比喻成鹦鹉,这是一种只会重复和模仿别人的动物,说明肖氏发表的那些政治言论,并非他本意。作者借鹦鹉来隐喻权力的专制,同时也阐释了肖氏的政治伦理选择,“他鹦鹉学舌,模仿斯大林向艺术家同行许诺”[1]86。正如巴恩斯在另外一部作品《福楼拜的鹦鹉》中所阐述的那样,真相是很难追寻的,到底哪只是福楼拜用过的鹦鹉,人们永远无法确认。肖氏落入集权社会专制统治之下,“他发表了别人为他写的政治演说”[1]86。他变得有点麻木不仁,他被迫打破对生命的禁忌,认为活着是一种厄运。之前他极其畏惧死亡,现在他的伦理选择完全相反,在他看来生命就像一只猫在不断地迫害他。猫在西方文学中是丑恶的形象,是撒旦的化身,与巫婆为伍,巴恩斯借助隐喻批评了集权社会的专制主义。肖氏做出违心的政治伦理选择,与权力为伍,去诋毁自己曾经最尊敬的音乐家之一斯特拉文斯基,“他背叛了契诃夫,在揭发信上签了名。他也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其他人仍然对他怀有的好评”[1]208。作者以此表达对这种集权政治的伦理批判。
在后现代社会,“我们注定要承受一种充满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的生活。由于没有一个主导的伦理模式,人们只有转向他们自身的个体道德”[31]。作为一个无比热爱音乐的“政治家”,肖氏认为,“艺术家们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政治上的引导,将帮助他们的人类伙伴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灵魂”[1]51。肖氏一直被权力支配去做一些他不乐意的事,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他变得越来越冷漠,“肖斯塔科维奇被接收进了权力的神圣殿堂”[1]204,“就像虾被放进蘸虾调料里一样,他徜徉在荣誉中”[1]148。他的心里一直充满愧疚,他深深明白这是违背他内心真正意愿的,他十分清楚,“他尽力了,但生命跟他还没完。生命就像那只拽着鹦鹉尾巴把它拖下楼的猫;他的脑袋撞到了每一级台阶”[1]209。
在当时极端的社会环境下,肖氏主动伪装成“懦夫”,回应权力对他的各种要求。“在伦理——政治的矛盾面前,伦理的远景要么是谴责政治,要么是接受妥协。”[30]130“鲍曼指出,人类注定是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存在,即一开始,人就不得不面对他者的挑战,面对为他者承担责任的挑战。人类的境况首先是一种道德问题,面对生活的选择首先是道德的两难选择。”[15]442肖氏坚持认为“他只是个作曲家,不是个演说家”[1]125,“他对自己演说的公然冷漠,会显示出一种道德上的中立”[1]128。他将这种情形看作只是个人的一个困境,“因为这是别无选择的,同样也就没有可能避免道德堕落”[1]139-140。在当时的集权社会里,肖氏选择了“正直并堕落”[1]205。
有评论者指出,“巴恩斯的肖斯塔科维奇不是角斗士,他尽可能不抵抗”[32],进而对肖氏进行批评:肖氏拒绝阅读自己被迫签署的声明,谴责自己喜爱的作曲家,是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内心的纯洁,还是一种卑鄙的逃避?他们认为巴恩斯激发了人们对政权政治下的艺术家的回忆,这是一种耻辱[21]。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肖氏向当局妥协的行为是一种耻辱和懦夫的行为。其实,肖氏的“懦弱”是具有目的性的伪装,是他进行政治伦理选择的主要手段。他没有公开和当权者起冲突,而是选择用音乐来反对黑暗的政治,正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33]读者可以透过音乐领会肖氏的政治伦理选择,理解巴恩斯在反思肖氏主动成为“懦夫”的伦理抉择行为的基础上,批判现代伦理道德对个体的束缚和规范,多层次、多维度地表明后现代伦理呈现复杂而自由的个人化倾向,因为“唯有多样化的自我才能抵制统治”[10]。
综上所述,肖氏这一“懦夫”形象与集权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有关,也与巴恩斯的后现代伦理观有关。为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肖氏主动选择成为“懦夫”以颠覆传统的婚恋伦理;为了获得自我成长,肖氏突破母性的桎梏,自己克服生存焦虑;为了履行对家庭的责任,肖氏用音乐反对黑暗统治的政治伦理。作者批判了当权者对人性造成的极大扭曲,对“懦弱”的英雄给予了道德解释,这是个体在暴力统治下寻求生存的方式,体现出巴恩斯对后现代社会伦理的反思和深切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