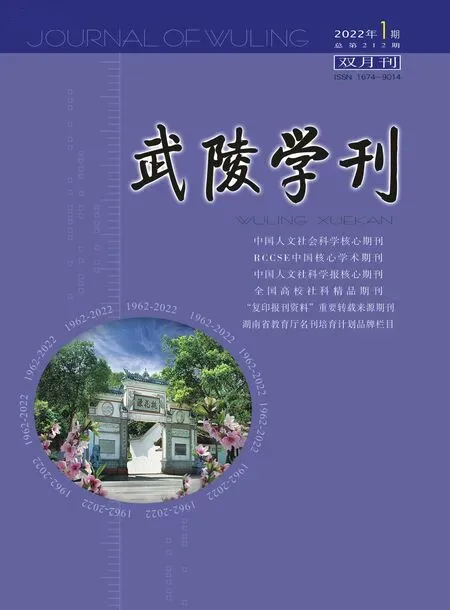《周易》“圣人”辨析
张 齐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周易》所涉人格类型颇多,其境界亦各有差等,其所推崇者,除了“君子”(仁人、贤者)之外,又悬设了“圣人”这一至高无上、最为理想的人格。针对《周易》中的圣人观,学界已有颇多探讨,其说各有启发。笔者试图综合《周易》关于“圣人”的论述,分辨其内涵与层次。此外,《周易》中的“圣人”与其他人格概念诸如“大人”及“君子”,又存在颇多纠葛。虽然学界在这方面也有较多讨论,但在重新厘清“圣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再作考辨,故不揣浅陋,拟就此申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易》之“圣人”
作为“圣人”的“圣”字,繁体为“聖”,《说文》释曰:“聖,通也。从耳,呈声。”[1]段玉裁曰:“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2]从字形起源来看,“聖”与“耳”相关,其本义应是表示听觉之敏锐,“通”当为其引申义。不过,“通”这一义涵在后来的诠释中几成为共识,且由“一事精通”扩大到“无事不通”,如《尚书·大禹谟》中“乃圣乃神”,孔安国传曰:“圣,无所不通。”[3]87《尚书·洪范》“睿作圣”,孔传亦与此同:“于事无不通谓之圣。”[3]303而《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孔颖达疏曰:“圣者,通也。博达众务,庶事尽通也。”[4]严格来说,无论是“圣”还是“通”,都是形容词,其本身对于所要表现的对象只有形式的规定,而无内涵的规定,人们尽可以根据所“通”之内容而赋予“圣”以不同的意涵。这些解释表明“圣”在处理事务方面具有极为高超的境界,但仅得其一端。倘究其极来看,“圣”之“无所不通”,可以表现于官能、德性、技艺、才干、事业等各个方面。根据这种解释,“圣人”无疑表达了人们对于完人、全人之理想人格的向往。
应该说,只要人生在世,没有对这世界完全绝望,希贤希圣的心理就会一直存在,对圣贤的崇敬也不会过时。只不过,因着时代及人生境遇的差异,不同学派的圣哲们所瞩目的价值观念不尽一致,故其赋予理想人格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学派内部,尽管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也不会千人一面。
具体到《周易》一书,因其主要构成部分《易经》与《易传》各篇成书于不同年代,故需分别来看。《易经》中无“圣”,《易传》中《大象》《小象》及《序卦》和《杂卦》也无“圣”,“圣”多见于《十翼》中的《彖传》《系辞》以及《乾·文言》,这是受到春秋战国时期愈益显盛的圣人崇拜思潮的启发。《易传》圣人观的思想底色虽然是儒家,但也融合了道家神韵。儒家有其理想的圣人观,这自不必说;道家如老子虽言“绝圣弃知”①,庄子学派也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的愤激言论,但这只是否定那种好玩弄巧智而日丧其真纯者,并没有否定“无为复朴”“体性抱神”的圣人。儒道两家的圣人观在《易传》中都有所体现,都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内涵。
目前学界对于《易传》圣人观的阐释,有的集中于特定某篇如《系辞》或《彖传》,有的注重《易传》涉及“圣人”论述的历时性差异,有的则对其进行综合性探讨。这些论述均有一定启发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单就某篇《易传》进行研究,虽然精细,但不够全面。而进行综合性探讨的,虽然所作分类比较详尽,但各种类别之间存在的颇多矛盾并未得到更好的处理。比如,圣人既然德智功位崇高已极,又何需修德?圣人既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何只有包牺这一位圣人才能创制八卦?后世圣人观象制器,为何只做出一件器物而未能全部制作出来?(当时世人所需肯定不只此一件)……除了“圣人”概念的内涵还存在疑问外,与“圣人”颇似的“大人”这一称谓,其内涵也有待进一步申释。
我们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论述对《周易》中的“圣人”基本都作了平面化的类型划分,忽视了《周易》在不同语境下所说的“圣人”,不仅有类型之差,亦有境界之别。如果能从应然与实然角度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圣人”,即“作为理念的圣人”与“作为典型的圣人”,则可对由“圣人”概念衍生的这些问题作出较为通贯的解释②。所谓“作为理念的圣人”,就是那种在德、智、才、事、位诸方面臻于极致且能圆融贯通者。严格来说,这是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的。虽人人都有成圣的潜质,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成圣亦有其客观限制,即使历史上真实的尧舜也未必能达到那种至为完满的状态,正如孔子在回答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所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但这不妨碍人们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卓越人物称为圣人,这就是“作为典型的圣人”。惟有如此,才能凭借着经验世界中的卓越者去摹画那只存在于理想世界中的至为完满的圣人,亦即“作为理念的圣人”,才能引领现实中的人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趋近于圣人的境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孔子否认自己是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他也说自己从未见过圣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语·述而》)但孔子仍然被孟子及后世儒者乃至社会各阶层人士推尊为圣人。此外,孟子除了将尧舜禹汤这些远古帝王视作圣人之外,也把没有帝王身份的伊尹、伯夷、周公、柳下惠、孔子视作圣人。其实,这些被人们推许为圣人者,均可看成“作为典型的圣人”;人们需要这样的圣人作为可感可知的具体典范,以便向“作为理念的圣人”趋近。
《周易》中所论及的诸种“圣人”,亦可据此区分加以观照。《周易》中的圣人,首先是具有极为崇高道德的人。《系辞上》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朱熹释曰:“此圣人尽性之事也。”[5]140圣人不仅自己的德性与功用至为完满,而且像天地一样广大悠久,但与天地不关心人类的祸福忧乐不同,天地之道是“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系辞上》),这恰恰说明,圣人对人世始终有一份未能割舍的忧患之情,他能做到“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上》),他的最终目的乃为使普天下之人同登福乐之地,正如《咸·彖》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像日月经天,恒久地照耀世间;又像四时有序,持续地变化生成,“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彖》)。正因如此,《乾·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德被天下,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众生利见此圣人。应当说,这样的“圣人”在历史上任何时代、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未出现过。这里“圣人”境界已不是经验世界的人而只有全能的“神”才能达到。所以,这种“圣人”只能是“作为理念的圣人”。
圣人还是具有极高智慧和才能的人,他可以创造出人难以想象的伟大事业。在《周易》中,所谓“圣人”,有两个最为显著的身份,一是作《易》者,一是帝王;前者侧重其渊深的智慧,后者侧重其崇高的地位。
圣人作《易》,是效法“天生神物”“天地变化”“天垂象,见吉凶”“河出图、洛出书”而来,凡此皆意味着他必须对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因为卦象的创作是仰观俯察、远取近譬的结果,需要“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爻辞的创作则是“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所以,圣人据此“极深而研几”,能够“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便是既能致广大,又能尽精微。其实,很难说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易》作者果然有这样神奇伟大的功能。因为作为对象世界的“天下”“天地”是无有穷尽的,人对此绝无可能达到“尽意”“尽情伪”“尽言”“尽利”“尽神”的地步。这勿宁说是后人为了强调《易》之伟大而渲染出来的《易》作者之境界。这境界是幽赞神明、参天两地、观变于阴阳的结果。在赞《易》者看来,《易》是伟大的,所以《易》作者同样伟大,故冠以“圣人”之称号,将“作为理念的圣人”之境界附加于《易》作者身上。这在包牺氏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据《系辞下》,包牺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当然是夸张了。至于后世观象制器的圣人,无论是黄帝、尧、舜,还是其他无名姓的圣人,从实际情况来看,既然他们的创造都来源于《周易》卦象,其境界能为自然不会高于《易》作者,他们被称为“圣人”,也是后世推尊的结果。
再看作为帝王的圣人。其实“圣人”自有其伟大价值,“圣人”并非一定要具有帝王身份,“圣人”之指帝王,勿宁说是在“圣人”成为理想人格的称谓之后,被人们用来对经验世界的帝王所作的一种赞誉。这种赞誉在后世或多半出于恭维敬畏,但在《周易》中则是悬设了至为理想的境界而对世俗帝王的积极策勉,如《颐·彖》“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鼎·彖》“圣人……大亨以养圣贤”,《说卦》言圣人应当效法《离》明之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其中“圣人”的所作所为,实际隐含着“帝王应当如此”之意。
总之,无论是作为具体历史人物的《易》作者,还是作为具有抽象政治身份的帝王,他们在《周易》中被称作“圣人”,并不是说他们真正达到“作为理念的圣人”的那种境界,而实际上是说他们可以被视为“作为典型的圣人”。
倘若从价值内涵的角度来界定“作为理念的圣人”这一人格类型,那么这种“圣人”,就是不仅能使自己的道德达到至为完善的程度,也能拥有足够的智慧、才能、地位、机遇等获得与之精确配称的幸福的人。此外,这种“圣人”之实现德福配称,不仅限于一身,亦可推之于天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配称,即是康德所说的“至善”之境,牟宗三先生将之译为“圆善”。不过,牟先生虽以“德福之诡谲的相即”证成了圆善之境,并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等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确已臻于此境,但事实上牟宗三并未解决“德福配称”所应具备的“能力”问题,因此,其“圆善”仍是停留于境界形态,而不能真正落实[6]。为此,我们将真正达到德福配称的“圣人”看成“作为理念的圣人”,而将后世人们推尊为圣人的人看成“作为典型的圣人”,就不致出现这种问题。同理,《周易》中所论及的诸种“圣人”亦可作如是观。
二、《易》之“圣人”与“大人”
《周易》中还出现了“大人”这种人格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圣人”的另一种称谓。“大人”在《易经》卦爻辞中多处出现,其中卦辞六处,分别是《讼》《蹇》《萃》《升》《困》《巽》六卦,爻辞中六处,分别为《乾》九二及九五、《否》六二及九五、《蹇》上六以及《革》九五。《彖传》中出现“大人”六处,皆为重复卦辞所言。《乾·文言》“大人”四处,两处重复九二爻辞,另两处则承九五爻辞而言。《小象》中“大人”五处,除《乾》九五“大人造也”并非完全重复卦辞外,其他皆袭自卦辞。《大象》中“大人”仅见于《离》卦。这些涉及“大人”处,除《革》九五“大人虎变”及《离·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是描述其能力作为之外,其他多为占断语,以“利见大人”(《升》为“用见大人”)居多,或如《困》卦辞及《否》九五爻辞曰“大人吉”,《否》六二则曰“大人否”,亦是判断吉凶之语。仅从这些论述,无法判定“大人”的特性及内涵。
若就出现“大人”的爻辞在各自卦象中的位置来看,则可见出一些端倪。“大人”或在二位,如《乾》九二、《否》六二;或在五位,如《乾》九五、《否》九五以及《革》九五。只有《蹇》出现于上六,其卦辞曰:“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本义》释曰:“已在卦极,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与之济蹇,则有硕大之功。”[5]54《小象》则以“志在内”释“往蹇来硕”,以“从贵”释“利见大人”,程颐更是明确指出:“谓从九五之贵也。恐人不知大人为指五也。”[7]900所以,“大人”的政治地位与九五之位所象征的天子、帝是等同的,可见其尊贵。不过,“大人”并不专指有九五之位者。如前所述,《乾》九二亦曰“利见大人”,《文言》认为九二虽无君位,但具备“君德”。王弼亦承此说,孔颖达据此认为先儒之释“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其义非也,“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8]4。据此,“大人”乃是与帝王等同者,其可能有帝王之位,也可能仅有帝王之德。这与经验世界中的“圣人”有帝王身份是一致的。
这意味着将“圣人”与“大人”进行互诠的可能性。这种互诠在《乾·文言》中就已存在,如释九五“利见大人”曰“圣人作而万物睹”。这种“大人”正与那种因位尊德高而被推许为“圣人”的人一样,乃是“作为典型的大人”。人们一般为经验世界中的帝王赋予这种称谓。例如,《正义》释《革》九五“大人虎变”,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不劳占决,信德自著。”[8]204除此之外,《乾·文言》中亦凸显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人”,此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这种人的境界之高,已不是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所能达到的,在经验世界中是无法寻到的,所以只能是“作为理念的大人”。
有趣的是,《易经》之中,只有“作为典型的大人”,而《易传》之中,却二者兼而有之。“圣人”之称则全部出现于《易传》之中,且尤以“作为理念的圣人”而特显。《易经》中具有至高政治地位“作为典型的大人”也可以置换成“作为典型的圣人”。《易传》中“作为理念的圣人”无疑也可看作“作为理念的大人”。《周易》经传之间最高理想人格称谓的变化,无疑也暗合了《易传》的道德形而上学倾向。从后世的接受来看,“圣人”的称号最终基本取代了“大人”而广为众人所接受。
三、《易》之“圣人”与“君子”
此外,还应辨析“圣人”(大人)与“君子”之联系与区别。毫无疑问,“君子”与“圣人”(大人)都是《周易》所推崇的人格类型,在《易经》卦爻辞中,没有“圣人”,只有“大人”。其中《革》九五“大人虎变”,《革》上六“君子豹变”,这两种称谓虽然出自不同爻辞,但亦可视为对举。郭沫若先生据此认为:“虎强于豹,大约大人比君子还要强一点罢?”[9]这一判断当然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明大人比君子到底强在何处。孔颖达对此也有阐释,他认为九五“以大人之德为革之主,损益前王,创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8]204,上六“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故曰‘君子豹变’”[8]205。这是从创制者与继承者的角度来看“大人”与“君子”之别。显然,这里的“大人”“君子”仍是就政治地位而言,并非人格类型。程颐释《姤·象》,言及“先王”“后”“君子”“大人”的区别时说:“‘君子’则上下之通称,‘大人’者,王公之通称。”[7]925这是就政治地位而言,不是将其作为人格类型来分析的。
《易传》中也偶有“圣人”与“君子”对举之处。如《系辞上》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主要是从《易》的创制与接受角度,以见“圣人”与“君子”之分。倘不泥于《易》之创制,结合前说来看,则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人格类型的“圣人”(大人)可引申指称所有文明的始创者,而“君子”则是“文明”的继承者。但这仍无法见出“君子”与“圣人”的境界差别,因为就历史事实来看,继承者的事功成就不一定就低于始创者。《彖》传之中,有两处言及圣人、贤人关系,鉴于贤人可视作君子,故亦可借此一窥圣人与君子关系。这两处分别见于《颐·彖》“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以及《鼎·彖》“圣人……大亨以养圣贤”,前者设置了“圣人—贤人—民”由上及下的三层结构,可以见出鲜明的政治地位差异;而后者虽云“养圣贤”,其实偏重的仍是“养贤”,所谓“养”,乃是出于政治管理的需求。故而,这里的“圣人”“贤人”仍是就政治地位来看的,而非人格类型。
《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韩康伯注曾论及“圣人”与“贤人”之别:“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德业既成,则入于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10]孔颖达疏曰:“行天地之道,总天地之功,唯圣人能。然今云贤人者,圣人则隐迹藏用,事在无境。今云‘可久’‘可大’,则是离无入有,贤人则事在有境,故‘可久’‘可大’,以贤人目之也。”[8]260这是以道家“有无”之玄理而判断圣贤境界之差等。二人对《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章的解释,以“君子”为“圣人”的观点,我们并不赞同;不过,其说论及“圣人”与“仁者”“智者”的差别,谓“仁知虽贤犹有偏……不能遍晓”[8]270,却可视作“圣人”与“君子”的境界之分。二人均以玄理释圣人君子之别,颇见出其境界之差等,但是他们也只得一端,未见全体。
依据前文重新界定的“君子”与“圣人”(大人)人格类型的内涵来看,如果说君子是以德为本兼及求福者,那么可将圣人视作德福圆融者。盖“圣人”是至高的理想人格,无论是内在的德性还是外在的事功,都能达到极为圆满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圣人”不仅能使自己达到这样的程度,也可以使天下的人都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说,圣人不但使自己德福配称,而且亦使他人德福配称。这样的“圣人”本身只能作为一种虚灵的理念式存在,不会出现于经验世界。而“君子”则以修德为第一要义,“福”乃是附带而来的第二义,至于能否尽其圆满的获得,虽然也为他所关注,但并非居于首位。凡是一念转变,以德为尚者,皆可目之为“君子”;然“德”是一价值概念,本身具备无限的含容性与伸缩性,好比一滴水也是水,全大海的水亦是水,“君子”也是如此。发一善念,行一善事,可为君子;德被一国,行济一邦,亦为君子。“作为典型的圣人”,其实本来只是“君子”,他们被称为圣人,是后世人追认的,如孔子便曾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为“六君子”[11],而这六者之中,除了成王之外,其他均被后世尊为圣人。至于“作为理念的圣人”,则只能作为“君子”所祈慕的形而上的理想境界,而不是实有的存在。
根据以上辨析,可以对《周易》中出现的人格称谓进行分类,而不致生出过多混淆与扞格。对《周易》“圣人”做出这种区分和界定,可以杜绝动辄以圣人气象作夸炫的虚伪,同时也可以避免以圣人为标准对他人做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孔颖达论君子与圣人行“元亨利贞”四德之差异所说:“圣人行此四德,能尽其极也。君子行此四德,各量力而为,多少各有其分。”[8]13其实不独行此四德之境界差异如此,诸德皆然、诸事皆然。真正对圣人境界心有所会的人,只有先立志使自己成为“君子”,并孜孜不倦地以圣人为鹄的,向此精进不息,才有可能在历史中获得“圣人”的殊荣。因为真正说来,“圣人”的称号只能付诸于后来者恳切的历史评判。
注 释:
①或谓此非老子所言,但总归是道家某派所论则无疑。此外,“绝圣”亦未必便与“崇圣”全然抵牾,因为“绝圣”之“绝”,可理解为作用层面的“绝”,而非实存层面的“绝”。
②此处两种不同性质的圣人的区分,乃是受到黄克剑先生相关论述的启发。参见黄克剑著《〈论语〉解读》第127-128页、第1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以A学院为例